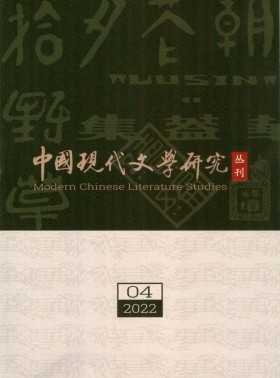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文学阶段小说创作,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
陈若曦在“现代文学”阶段的小说创作在风格技巧与主题立意上呈现出了极为斑斓的色调。这里面既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稚嫩仿品《巴里的旅程》,又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原型意象“疾病与疗治”的重述之作《收魂》;既有给予道德场景以一种生存论展现的《辛庄》与《燃烧的夜》,又有融合了乡土、神秘、情感等多种叙事元素的《妇人桃花》。这些小说作品显示了陈若曦在其小说创作尚未形成固定风格之时的探索痕迹。
关键词:
陈若曦;现代文学;小说创作
作为“现代文学”派的四大主将之一,陈若曦在《现代文学》杂志上一共发表了七篇小说。这七篇小说在风格技巧与主题立意上呈现出斑斓的色调,显示出陈若曦在其小说创作尚未形成固定风格之时的探索痕迹。本文从四个方面重点论述陈若曦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几部作品。
一、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稚嫩仿品———《巴里的旅程》
《巴里的旅程》发表于《现代文学》第二期。这是陈若曦初试现代主义之作,也是其全部小说创作中最具有现代主义意味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出身为“现代文学”社主将的陈若曦对于《现代文学》杂志办刊宗旨的热烈响应与主动迎合。虽然《巴里的旅程》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篇失败之作,但仍可视为小说家为拓展创作路径而做的有益尝试。“巴里的旅程”走出街市,走过荒野,走向大山,最后却仍然走不脱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双重迷失。《巴里的旅程》在其文本中着力构建了一个“在路上”的存在意象。“在路上”一词源于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凯鲁亚克1957年出版的小说《在路上》(OntheRoad),原意指的是二战以后美国青年的一种离经叛道、回归自然的生存状态,也同时喻指现代人的一种无家可归、价值迷失的存在境遇以及一种没有终点、永无止息的精神探求状态。《巴里的旅程》的文本叙述剥离了具体的时空背景,正是在一种人类普遍生存的意义上来呈现巴里“在路上”的流徙与追寻情形的。“巴里的旅程”经过了几个阶段,起始点却选在一个喧闹的街市上,这无疑正是对于人类不断都市化的生存现实的一种喻指。因为,如果说所有的问题提出与答案追寻都起源于对当下生存境遇的应对,在都市化俨然已经成为现代生存基本形态的历史情形中,现代小说的精神流徙与探寻起点的都市情景设置也就成了一种必然,但《巴里的旅程》的都市叙述也只能是对于一种都市喻象的呈现。文本中,游走逗留在都市街头的都是一些具有神经病气质、近乎符号化的人影,人的行为举止也被赋予了高度抽象的意味,看似混乱无序的都市情景却处处隐指人类最为基本的存在形态与存在处境:百货商店里的货物是出生用的尿布与死亡用的棺材的陈杂,被兜售的期票日子订在三十年后,乞讨的老妇人因为拒绝进养老院而被警察拼命追赶。其中,闹市中横亘的教堂意象成为《巴里的旅程》中这段都市叙述里最醒目的叙述景观。文本伊始,“巴里转进大街”的开头,教堂的钟声就开始鸣响在《巴里的旅程》的文本世界里:“于是,教堂钟响,‘当’,‘当’……”[1]67在巴里走出街市的最后,路过的正是教堂的门口,叙述者在这里设置了《巴里的旅程》的第一个场景叙述:一个坐在教堂大门台阶、怀抱婴儿的年轻母亲因为婴儿父亲身份的不明而被人群围观与议论:“霎时,尖叫、呼啸、咒骂、哗笑……排山倒海而来。”[1]69场景叙述对于闹市中教堂的地点选取以及围观人群对于年轻母亲以及一个醉汉所分别给予的“圣母玛利亚”与“施洗约翰”的戏称,使得这样的场景叙述成为对圣经故事的戏仿,亦将现代人类生存处境的荒诞性呈现无遗:天使坠于凡间,污秽与圣洁杂陈。这种在现代生存样态揭示中引入圣经原型的书写方式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在巴里旅程的中途,不再有对于人类生存处境的直接展示,而是展示了各式人等与各式理论对于现代人类生存命运的感叹、探讨与争辩。相伴而行的两个人躲在黑布伞下喃喃抱怨:“痛苦的存在呵……何得解脱……”[1]70。菩提树下的三个年轻人在争辩着究竟是科学还是宗教可以挽救20世纪人类的命运。一长队人则在宣传着基督教义,准备发起又一场十字军东征。这种对现代生存荒诞性与困惑性的揭示无疑构成了《巴里的旅程》的思想主题。在对巴里的旅程的都市化阶段进行了这种思想主题的情景化表现以后,叙述者对巴里旅程中途情形的叙述却转入到小说中人物对小说思想主题的直接探讨上,自然可以视为小说家尚无力把一种关于现代生存的思想理念有效地转化成一种现代生存叙述。《巴里的旅程》这一阶段的叙述在叙述情景与人物构型上都与西方现代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之作《等待戈多》极为神似:消隐了时空背景的荒野与路途,两三人等在其中漫无目的的游走与交谈。只是,《等待戈多》有效地抹去了理念痕迹,将关于现代人类生存的思想理念完全融化在了文本叙述之中,极为有力地展示了现代人类生存的荒诞处境。《巴里的旅程》这一阶段的叙述则只是在叙述的外在形式上与这部西方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取得了某种相似性,却在更为内在的现代生存叙述的叙述品质上留下了缺憾,这自然是初试现代主义的陈若曦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巴里旅程的结尾,叙述者的叙述又转入情景化的叙述当中:一位老人分别用了诱捕与武力的方法去扑捉一群鸡,结果无不徒劳无功:“天黑了下来,旷野一片幽暗。远远地,只见老人蹒跚奔路的身影,鸡群已不见踪迹。”[1]75老人与鸡群的关系正象征了人类的生存探求与追寻永远“在路上”的存在处境。
二、“疾病与疗治”———《收魂》
“疾病与疗治”是中国现代小说写作中的重要主题。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其他主题一样,“疾病与疗治”的书写传统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所开创的,他的《狂人日记》《药》等一系列杰作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疾病与疗治”的复杂关系与历史寓意。自鲁迅以后,现代文学的几代作家都走进了“疾病与疗治”的梦魇之中,他们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不约而同地重复了“疾病与疗治”的话题。可以说,“疾病与疗治”的意象书写承负着现代国人的全部焦虑与期待,成为中华民族艰难推进现代进程的重要文学镜像。自称一生服膺鲁迅的陈若曦与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小说主流叙述传统的承继关系已被包括夏志清在内的多位学者所指出,其现代启蒙意识在其更早的小说作品《灰眼黑猫》中已初步显露。《收魂》在叙述表面上几可视为“疾病与疗治”原型书写的典型副本,其故事构型更是与鲁迅《药》中华家的故事几近相同:因为儿子的疾病而陷入绝望的父母寄望于以一种迷信的方式来拯救儿子,儿子最后却仍然不治身亡。在《药》中,这种迷信行为因为与革命烈士鲜血的纠缠而愈发显得意味深长,对于现代启蒙主题的阐发也因此愈显深刻与复杂。《收魂》的叙述焦点仍是这样一次以疗治为目的的迷信行为,但其中寄寓的主题意旨已与《药》有所区别,呈现出了多重歧义的特征。毋庸置疑,《收魂》的隐指作者对于“收魂”的疗治效果持根本的怀疑态度,因此其用重彩浓墨渲染的“收魂”活动处处投射出反讽的意味,道士不但在“收魂”中丑态自现,叙述者更借助小说中大学生女儿的口直接对其展开批判:“突然间她开始厌恶这个道士,她想他是多么愚妄,无知而又虚伪夸张呀!同时她又发现父亲竟有相信的神情,不免使她惊讶,甚至有点失望。”[1]256“收魂”收场,道士在走过大门时却惊讶地发现了一个“仁心诊所”的招牌,才知道请自己为其儿子“收魂”的原来是一个医生,更使得这样的反讽式叙述达到了高潮。科学与迷信之间的对立不但为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女儿”与以迷信作为谋生手段的道士所明白,即使是“父亲”与“母亲”也心知肚明,因为在“收魂”之前,“儿子”已经在台大医院接受过多次手术,结果却仍然命悬一线,为其收魂不过是在确认现代医学徒劳无功后的无奈之举。在对迷信性的“收魂”展开批判以后,《收魂》的隐指作者并没有将《收魂》的主题意旨自动引向现代启蒙的宏大主题:“迷信是愚昧,自信又何尝没有罪过?生是不可思议的,人也是,一切都是。”[1]257人类自信的构建与膨胀本是现代启蒙的根基所在,对人之自信的质疑也即意味着现代启蒙在其心目中的价值陷落。而对于“人生是不可思议”的价值判断则将《收魂》的文本叙述引向了生存论叙述的境地,从而使得《收魂》的主题意旨在某种程度上超脱于“疾病与疗治”的框架拘限。“收魂”在《收魂》中首先是一种被饱含痛楚的亲情所投射与浸润的行为,它因此而具有意义,并不因为它的任何其它属性而减损这种意义;其次它才是一种迷信活动,文本中不断出现的具有反讽意味的叙述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的,《收魂》隐指作者的现代启蒙意识也由此得以体现。《收魂》在主题意旨上所表现出的这种歧义性与暧昧性让人想起小说家更早的一篇小说作品《灰眼黑猫》。只是,与《灰眼黑猫》高度服膺于充满乡间迷信色彩的“灰眼黑猫”故事原型不同,《收魂》中同样充满了迷信色彩的“收魂”活动已是受尽嘲弄。虽然小说家在《收魂》中仍然没有建立起其纯粹坚定的现代启蒙意识,但比之于《灰眼黑猫》,其进步无疑是明显的。
三、道德场景下的生存呈现———《辛庄》与《燃烧的夜》
《辛庄》与《燃烧的夜》的故事叙述都源于一个情感背叛的事件,但这两篇小说都并不是专门来讲述一个情感背叛的故事的。这个情感背叛的故事实际上只是充当了小说叙述的原动力,整体的小说叙述则走向了对更深广的人生状态的揭示与表现。这使得像情感越轨这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里深具道德意味的事件获取了更多的生存论的内涵,也显示出陈若曦对世俗人生的体认与悲悯。《辛庄》讲述了一个名叫辛庄的人因生存重担的压迫而积劳成疾的故事。小说中现在时刻的他面临着老婆红杏出墙的事,这无疑是让他更难以承受的苦难。小说刻意营造出一种道德化的故事氛围,更加凸显了这种苦难性。小说开头叙述主人公田野漫步回来,一进村子即感受到这种氛围的强大存在,几个街坊邻居正在议论他的老婆与人偷情的事情,并且认为这是一个人的奇耻大辱。日常生存的高度道德化是中国文化的常态,对此种生存景观的自觉呈现也是以展示国人日常生存状态为目的的小说生成现实主义美学品质的重要手段。中国传统的世情小说在这点上自不例外,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类小说的主题意旨往往也是被高度道德化的,所以,所有在日常生活中违背了伦理道德的人在小说中都会受到道德的审判,在小说叙述中其人生结局也多是毁灭性的,如中国传统世情小说代表之作的《金瓶梅》,一方面在相当大程度上真实地展现了晚明市井社会的生存景观,另一方面又渗透着浓重的道德说教,对小说人物的叙述暗含了一种道德化的标准,显示了小说的隐指作者与其描写的社会生存现实在道德意识上的叠合。也正是在这里,《辛庄》显示了陈若曦作为一个现代中国小说家所具有的可贵品格。在《辛庄》中,《辛庄》隐指作者的意旨与主人公所处的高度道德化的生存现实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分裂。文本中,主人公辛庄承受了妻子红杏出墙这个道德化事件所带来的所有苦难,却无法对其进行道德宣判,因为在辛庄看来,这种苦难不过是其苦难的日常生存的自然拓展,而妻子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却属于对于由于受自己牵累而变得日益恶劣的生存境况的正常反抗行为。小说的重点即是叙述辛庄为了养家糊口,偿还盖新房欠下的债务,除了在街市上摆摊卖水果以外,还兼了一份印刷厂的工作,以致积劳成疾,并且,由于长年奔波劳碌,身心都变得疲惫不堪,以致常常疏忽了妻子的存在,夫妻分床而居,正常的夫妻交流因此中断。这其实是一种不断将辛庄之妻的所作所为合理化的叙述方式,红杏出墙的故事在这样的叙述逻辑下变成了一个生存论的事件。存在主义主张存在先于本质、个人选择的不可谴责性以及人类生存的根本苦难性,这些都在《辛庄》的文本叙述中得到了极为鲜明的表现。辛庄对苦难生存的高度忍耐以及其妻对此所作出的反抗都被视为生存论领域下的自然选择,道德标准在此被悬置起来。其实在相当大程度上,《辛庄》中的故事仍然是潘金莲、武大与武松三角情爱故事的重述。与白先勇同样是重述了潘金莲、武大与武松故事原型的小说作品《闷雷》不同的是,《闷雷》采取了潘金莲式的女人福生嫂的叙述视角,《辛庄》却是以武大式的男人辛庄的视角展开叙述的。《辛庄》开头,病弱的辛庄田野漫步途中路遇强壮的男人长脚高,即对其健壮的体魄羡慕不已,而这个长脚高即是这个三角故事中的另外一个男主角。长脚高曾经租住在辛庄家里,经常为辛庄代劳讲故事给辛庄的三个孩子听。在小说最后,辛庄的老婆云英一番梳洗打扮,借看戏为由又出去和长脚高约会,辛庄却无力阻拦,任由她去。红杏出墙事件在《辛庄》文本世界里的无限期延展使得《辛庄》对于这个道德化事件的颠覆达到极致,而潘金莲们在取得道德的豁免权以后近乎肆无忌惮的“胡作非为”却也同时让人不免有胆战心惊之感。与《辛庄》一样,《燃烧的夜》的视角人物仍然是一个男人,而且,正是这个叫作子光的男人在妻子远离家门时不慎出轨。如果说,《辛庄》注重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文本叙述,情感越轨者豁免于道德规范标准的裁决,《燃烧的夜》却是反其道而行之,道德律令像是一道枷锁禁锢了背叛者与被背叛者日常生活的步伐,使得他们一夜难度。同样是作为情感越轨者的乡村女人与都市男人却被给予了截然不同的叙述待遇,不知这是否应该被视为一向被认为与女性主义无涉的陈若曦女权意识的悄然显露?但小说家对于乡村女人出墙与都市男人出轨的取材本身却呼应了一种意味深长的文学叙述现象,那就是,与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情感背叛事件一直被热衷于用作小说素材一样,现代都市男人出轨的事件在现代小说写作中也倍受青睐。在男权中心的传统社会中,正因为男性在情感问题上的“胡作非为”享有道德上的豁免权,所以才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最稀松平常的日常现象,从而在小说写作中失去了诱惑力。都市男性出轨事件在小说选材上的被青睐正昭示了人类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在人类社会从乡村形态行进到都市形态以后,原来在道德上天然享有豁免权的男性对于情感的背叛问题被得以重新审视,也因此更易于成为小说写作的对象。《燃烧的夜》中的出轨事件本身即带有浓重的都市意味。子光在妻子暂时离家时由于耐不住寂寞和对方勾引而行为出轨,在相当大程度上其实并不关涉情感之事。情感在出轨事件中的这种缺失状态正彰显了现代都市社会欲望本位的生存现实。只是,《燃烧的夜》在进一步的叙述中并没有被处理成一个典型的都市文本,主人公现代都市欲望化的行为受到了传统道德律令的宣判。这样的处理方式其实隐含了小说隐指作者的一种主观意旨。与《辛庄》中在道德上为女性松绑的写作思路一脉相承,《燃烧的夜》以对男性的行为加以道德禁锢的叙述方式显示了小说家的写作仍然走在颠覆中国传统世情小说写作模式的道路上。男主人公的一次失足使他罪恶难赎,这个“燃烧的夜”正是一个罪与罚的时刻。子光的妻子安曼以对自己丈夫轻蔑、冷漠与嘲讽的方式惩罚其出轨的行为,使得子光更加觉得自己罪不可赦,道德律令的杀伤性也因此更显巨大。子光经历了出轨事件的身体在安曼看来已变得肮脏不堪,所以不再允许其靠近自己,安曼的这种道德洁癖正彰显了《燃烧的夜》主题意旨中的道德化生存维度。在小说最后,子光终于没敢跨入妻子的卧室,而是走进黑暗之中,道德律令仍在发挥它的效力。
四、乡土•神秘•情感———《妇人桃花》
在陈若曦早期小说创作中发表时间上的殿后地位与文本叙述上的集大成品格在《妇人桃花》中的遇合显示了小说家的小说创作正日趋走向一种自觉。与《灰眼黑猫》与《收魂》一样,《妇人桃花》的文本叙述充满了神秘主义力量对乡村日常生活的干预与控制。不同的是,少了与五四文学的纠缠,而成为了一种融合了乡土、情感与神秘的自足性叙述。妇人桃花的情爱悲剧不关涉朽腐的旧社会制度,关于她的疾病与疗治的叙述更没有被赋予启蒙维度。乡村生活本身构成了陈若曦的童年与少年经验,而神秘性则起源和植根于人类的童年体验,作为《妇人桃花》叙述主体的情欲纠缠也因此散发出极为原始的力量,这也使得《妇人桃花》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关于欲望原型的书写文本。《妇人桃花》的文本叙述是一种典型的分层叙述。其第一层次叙述妇人桃花久病不愈,只好求助巫婆,在进行了一番穿越时空与阴阳的对话之后,妇人终于无药而愈。因为小说对阴阳对话的情景极力渲染,使得这一层次的叙述几乎占据了小说的大半篇幅,所以在表面上似乎整篇小说只是讲述了一个神秘主义的故事。而实际上,第一层次的那番阴阳对话复现了一个发生在多年以前的爱恨情仇的故事,这也构成了小说文本的第二层叙述。在这两层叙述中,第二层叙述才是整篇小说文本叙述的重心与主体,也即叙述学意义上所谓的主叙述:桃花是梁在禾家里的童养媳,与梁在禾从小一起长大。长大以后的桃花出落成了一个漂亮少女,情窦初开,早已把梁在禾视为情郎,只是梁在禾却浑浑噩噩,全然未觉。桃花对梁在禾于是由爱转恨,实施报复。在通过各种引诱手段让梁在禾疯狂迷恋上自己以后,自己却疯狂地与多人偷情,直至被梁母发现。随后桃花被勒令嫁人,梁在禾也很快郁郁而终。桃花近乎狰狞的爱恨转换彰显了原始欲望的强大威力,桃花的复仇计划以其自身的苟活与对方的病死,至少是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而告终,《妇人桃花》也至此完成了其第二层次的叙述。如果《妇人桃花》的文本叙述只此一层,无疑只是展示了欲望的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尚不足以呈现更为丰富复杂的人性维度。对于后者,《妇人桃花》是依赖于第一层次叙述来完成的。虽然一人已死,但两人的恩怨并没有被阴阳割断,生者仍时时受到死者的纠缠。小说开头叙述桃花多方求医仍然不愈,正表明她与梁在禾的恩怨故事已成为其疾病的症结所在。在复仇的一时快感之后,桃花终于陷入到了日复一日的良知折磨之中。这样的叙述丝毫不带有中国传统小说所惯有的道德批判色彩,而是展示了一个罪与罚、救与赎的心灵世界。桃花以一场充满忏悔与承诺的阴阳对话释放了心魔,其病也无药而愈。对于叙述分层在小说叙述中的功用,赵毅衡认为:“叙述分层的主要功用是给下一层次叙述者一个实体……叙述分层能使这抽象的叙述者在高叙述层次中变成一个似乎是‘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使叙述信息不至于来自一个令人无法捉摸的虚空。”[2]为了使得作为小说主叙述的第二层次叙述的叙述者显得足够“有血有肉”,《妇人桃花》在第一层次的叙述中对第二层次叙述者参与的神秘事件极力铺叙渲染,几有喧宾夺主之嫌,使我们恍惚于这篇小说的重心究竟是在讲一个神秘故事还是一个情爱故事。陈若曦巨大声名的获取无疑是依赖了其在70年代所发表的一系列题材小说创作,但这个时段的小说试验的重要性仍不容抹煞。正是借助于这个时段对各种小说体式与立意的不断尝试,陈若曦才找寻到自己最为擅长的小说叙述方式,并最终成为了少数建立了国际名声的华人女作家之一。
作者:尤作勇 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陈若曦.贵州女人[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
[2]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