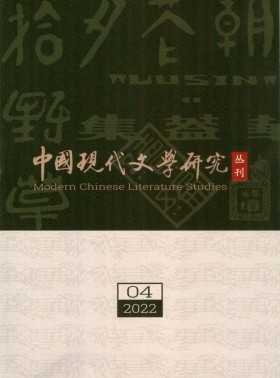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文学副文本的史料价值综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副文本中的史料
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序跋往往涉及关于作家、作品及文学史的多方面史料。序跋能反映作家的生平经历尤其是其文事交际关系,如作家与作家、批评家、编辑、出版家的关系,作家参与的文学论争等,像《<呐喊>自序》所记录的对鲁迅有重大人生转折的“幻灯片事件”、许钦文《无妻之累》序跋中对他卷入的当时轰动沪杭的凶杀案的交待等。序跋本身更是作家与序跋写作者关系的见证,如鲁迅为左翼青年作家所写的大量序跋,周作人为自己学生所写的那些序跋等。作家的思想、艺术观也常常通过序跋来表达,序跋中更有关于作品的写作动机、生产过程、出版、传播、接受等方面的信息。序跋甚至构成了文学史的重要事件,如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中交待鲁迅、周作人、俞平伯等众多文坛名家所参与的《尝试集》删诗事件,1932年《地泉》重版时的五篇序所形成的“革命文学”批评事件等。所以,序跋是副文本中最丰富的现代文学史料来源地之一。另外,有些作品所收的附录文章,往往是与作家尤其是作品相关的评论、说明文字,其内容和史料价值差不多等同于序跋。现代文学作品的序跋数量最大,居其次的副文本当属广告。有依附于作品单行本的大量广告,如鲁迅《野草》中附有8页包括《野草》在内的25部作品的广告,《良友》文学丛书附有关于丛书的众多广告。众多的现代文学期刊也刊登了难以计数的广告,如《文学》曾为133部作品作过广告,《现代》更有多达500多则作品广告。这些篇幅短小的广告在推介、宣传作家作品的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学史料。关于作品的广告往往会介绍作品的内容、特点、价值、字数、价格、装帧、修改、版本、出版机构、发行人等史料。如《志摩的诗》的再版广告就介绍该诗集的增删、修改问题,为该诗集的版本、异文研究提供了指导。韦丛芜《君山》诗集的广告提到了“林凤眠封面,司徒乔插图十幅”,为这本书的装帧研究提供了证据。关于期刊的广告往往会交待期刊的办刊宗旨、组织机构,刊物的栏目、特色、撰稿人等信息,如《文学》杂志在《生活周刊》上刊登的广告就成为研究该刊的创刊、发展等方面的重要史料。这些广告还会涉及新文学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家掌故、文坛现象乃至一些重要文学事件。如鲁迅、高长虹、韦素园写的一些广告就成为鲁高交恶事件的细节和证据。丁玲被捕事件也在《现代》《文学》等期刊上的广告中有所反映。总之,这些广告成为新文学生产、传播、接受的重要文献和证据。扉页或题下的题辞(或引语)是现代文学作品才有的,它一般比广告更短,只能称为语句或语段。它虽然短小却蕴含着大量史料。其中,扉页引语引的是中外经典或古今诗文中语句,类似于用典,将古代或西方的文献史料片断移植于现代的文本中,既凸现了古代或西方的史料,又使这些史料在新的语境中化作了新的史料的一部分。如郁达夫的小说《采石矶》引杜甫诗作《天末怀李白》中的诗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小说中又写了清代诗人黄仲则与考据大师戴东原的矛盾,借此隐喻郁达夫自己与胡适的关系。结果这句诗成了郁达夫对胡适的泄愤之辞。高长虹在《走到出版界》一书的扉页“卷头语”引《庄子•秋水》中庄子与惠子相交的故事来影射他与鲁迅的关系,也是一种史料的勾连。所以,引语本身是史料,同时它又成为中西、古今史料的粘合剂。至于那些自题的题辞所含的史料价值就更明显了。那些“献给某某某”的题辞是作家与被献者人际关系的见证,如苏雪林《绿页》扉页的题辞“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证明苏雪林结婚初期有过一段甜蜜的婚姻生活。于赓虞诗集《魔鬼的舞蹈》题辞“献与庐隐女士”显示了他们之间的友情。有些题辞隐含着作家与文学运动的关联,如叶圣陶《未厌集》扉页题辞既解释了书名的含义,更暗示了他与1928年文学论争的关系。至于像《暴风骤雨》等作品扉页引用语录,那是作家和作品意识形态倾向的表征,《日出》等作品扉页引宗教经典,则是作家和作品宗教意识的见证。另外,题辞和引语在作品的某一版本中出现,却在其另一版本中删去等,这往往是辨识版本的标志,这时它又成为文学作品版本研究的史料了。注释虽然有作家自己的即时注释,但更多的是他人和后人的注释,所以它主要是一种外生的和后生的副文本,但它终究会加入到正文本的意义生成和结构之中。注释是对作品作细部的说明和解释,它有助于作品的意义增值和深度理解。而从史料角度看,它提供了关于作品和作家的全方位的史料,其广度超过序跋。正文本中又可分题注和文内注。题注会涉及作品的发表处、版本变迁、标题变异乃至作品写作的背景等。内文注释的内容更广。以《鲁迅全集》为例,注释内容包括①人物类(人名、神话传说和各类作品中人名),②书籍和作品类,③报纸、刊物类,④团体、流派、机构类,⑤国家、民族、地名类,⑥历史事件及其他事项类,⑦引语、掌故、名物、词语类,⑧外文词语类,⑨鲁迅生平活动类,⑩鲁迅笔名类。所以,这些注释不仅蕴含关于文学的史料,也涉及文学以外多种学科门类的史料。图像包括封面画、插图、照片等,尤其是封面画和插图有图解正文本意义的功能,是视觉史料或直观史料。故有由图出史或以图证史的文学史写法。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杨义等人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一些现代期刊中更有具体的以图写(画)史的例子。如1936年2月15日创刊号《六艺》杂志上的“文坛茶语图”再现了30年文坛格局、动向及其沙龙性质。1956年第1期《文艺报》上的“万象更新图”,也以漫画形式表现了新中国一体化文学生产中作家的队伍布阵、生活变化、艺术走向乃至文艺运动(如批胡风)等。一些图像则留下了更具体的文学史料,如,叶灵凤所作的载于《戈壁》半月刊上的漫画“鲁迅先生”画出了他与鲁迅先生之间的文人恩怨。孟克所作的刊于《杂文》月刊第三号的“鲁迅漫画像”则记录了鲁迅对小品文危机的批判。而与正文本同时出现的那些封面画、插图等也具有史料性。如鲁迅在《坟》的扉页所画的那只敛翅于胸、睁只眼闭只眼的猫头鹰正是鲁迅此时心绪和形象的写照。萧红自画的《生死场》封面也形像地体现了东三省沦陷的历史事件和东北作家的乡愁。叶灵凤所画的郭沫若诗集《瓶》的封面画则曲折地指向了郭沫若《孤山的梅花》一文所记录的爱情佚事。一些图像则是作家与作家或画家文事交往的见证。如鲁迅为高长虹《心的探险》所作封面画,陶元庆所画的“大红袍”经鲁迅之手用作许钦文小说集《故乡》的封面,还有闻一多为徐志摩《猛虎集》《巴黎的鳞爪》所作的封面画等等。有时一部作品有不同的封面画或插图,它们就成为了作品版本研究的鉴别史料。如张爱玲小说《传奇》初版本、再版本、增订本不同的封面画,钱钟书《围城》不同版本的不同封面画等都是如此。
二、副文本史料的特点及价值
许多历史学家都讨论过古代的经、史、子、集等的史料价值差序。其中,谈到集部之书,翦伯赞说:“集部之书,并非专记史实之书,大抵皆系纯文学的,至少亦为含有文学性的著作,其为研究文学史之主要的资料,尽人皆知。章实斋曰:‘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其实……诗词歌赋、小说剧本,又何尝不是历史资料,而且又何只一人之史。……而且其中的历史记录,往往是正史上找不出来的。”梁启超早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谈到类似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具有启发意义。现代文学作品的正文本作为纯文学文本,当然可以提供关于现代史的史料,但是要在正文本中找出更具体更真实的文学史料就得靠我们去挖掘、比较和分析了。而副文本总体而言是偏重于实用的,它们不仅呈现了更多的文学史细节,如作品的装帧、出版、传播等,作品的写作、修改、接受等,作家的身世、创作动机等,还有文坛现象、时局变化、历史语境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历史材料具有相对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科学性。说到具体的副文本要素,它们则可能体现出不同的史料价值特点和等差。如序跋一般是作者或与作者相熟的师友即时所写,是对作家和作品等内容的一种真实、及时的交待和评价。其史料的真实性远在作家的回忆录、口述历史等之上,其史料的时效性不亚于作家的日记或当时的创作谈。符合梁启超提到的“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的史料学原则,即所谓“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而在这第一等的史料中,其史料价值还可分等。如,分出“证据”类史料和“证词”类史料。作家或师友的序跋及序跋中对基本史实的交待可谓“证据”;而对作品思想倾向、历史地位、艺术特征或风格等的评价,则可能会受个人情感、时代风气等所限,所以只能算是“证词”。如汪静之《蕙的风》有胡适序、朱自清序、刘延陵序等众序及序中对交往关系的介绍等是证据,而他们对汪诗风格及地位的评价则为证词,需要后来的研究者拿出更可信的证据去加强或否定它。正如柯林武德所说“由摘录和拼凑各种不同的权威们的证词而建立的历名学,……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历史学”一样,序跋中的证词可以去质疑,需要去验证。因为证词式的话语中可能有谀词或不实之词。这种现象在现代文学的广告中体现得更明显。因为广告出于商业目的,需要招来读者,所以往往会以夸张的吹捧的语句去评价作家和作品,往往会以“最”“第一”等有违历史真实的极端语言去写“证词”。郁达夫就曾抨击这种做法:“我最怕的就是书店的广告,如‘以一手奠定中国文坛’,‘中国有新文学以来的第一部书’、‘天才作家’等文句,所以当出书之际,我要求书店同人,广告不要太做得过火。”所以,序跋及广告中的这一类证词只能是一种有意的或经意的史料,甚至只能是一种历史的烟幕弹,没有可信度。正像傅斯年所言:“经意便难免于有作用,有作用便失史料之信实。”不过,广告也留下了大量不经意的史料。如《志摩的诗》的再版广告,本意是要宣传诗集经诗人修改后“内容焕然一新”,却无意中提供了诗集的修改及版本变迁的史料。上文提到的《君山》的广告也有意拉名画家来招揽读者,却不经意中留下了装帧、辑佚方面的史料。总之,经意的“证词”的史料价值不及不经意的“证据”。当然,有许多现代文学广告是鲁迅、巴金、叶圣陶等名家所写,其史料总体上是真实可信的。注释尤其是经典性作品的注释往往能提供最完备的史料。它在副文本中不但涉及史料内容最全,而且还可以不断生长、完善。有的作品既有作者原注,又有研究者的新注,如收入周良沛《中国新诗库》中的卞之琳的一些诗歌。又如陈永志的《女神校释》则汇集了《女神》作者原注、不同版本的注和校释者的新注,已相当于古藉研究中的“集注”。但现代文学的注释者们基本秉持的是研究者的科学态度,不断改正旧注中的错误,使得注释提供的史料,不仅完备,而且基本上真实可靠。如《鲁迅全集》经过一代代注释者的努力,到2005年的最新版,注释最多且相对最可靠,成为现代文学中注释中的范本。注释可以有集注,图像也可以汇集。作品不同版本或者作者在不同年代的不同的图像材料,都会是一种真实可信的史料,而且是直观的形象的史料。如鲁迅画的两种猫头鹰图像,郭沫若50寿辰时怀抱五尺多高、上刻“以清妖孽”四字的巨笔并手扶幼子的照片,张爱玲《传奇》的三个不同的封面等都是极为珍贵的可视史料,是我们真正能返回历史现场的凭据。而且这些原有的图像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遗迹,它们和作家的故居、故物一样具有文物的价值。其他如扉页题辞、笔名等皆可分析出其历史信息,挖掘出其中隐含的经意的或不经意的史料。如笔名是作家或逃避文网或隐藏深意的结果,是经意的史料。但它在不经意中又成为后来者搜集作家佚文的凭据了。
三、副文本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影响
副文本所提供的史料会对现代文学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首先,副文本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为现代文学研究另辟了一块史料园地。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来源通常有几个方面:一是历史遗物,包括作家的故居、故物、手稿等,作为文物的报纸、期刊、作品的原版本等;二是纯历史文本,如家谱、年谱、年鉴、档案、方志、文学史著述等;三是纯文学文本,即作家的纯文学创作部分,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文艺性散文;四是介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文本,可称之为副文学或亚文学文本,包括书信、日记、传记、游记、回忆录、掌故散文、书话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能忽视一些介于文学、历史和传播、出版之间的文本,如序跋、广告文案、发刊词。当然更不重视那些一般称不上文本的文本碎片,如扉页题辞或引语、注释、笔名、图像文本等。而实际上,它们蕴藏着丰富的文学史料,是现代文学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同时,即便是我们注意到这些文本和文本碎片的史料性,但又孤立地去看待和使用它们,其文学史料价值也不能很好地体现。而当我们用“副文本”这个概念把它们统一起来,它就更能够引起文学史家的注意,并更能凸现其特色和价值。其一,在与正文本的文学本体特性的比较中,我们更能体认副文本的纪实性、真实性特征,它的偏于历史文本的性质,它的文学史料价值。其二,副文本所提供的史料既指向正文本也指向正文本之外的广大领域,让我们注意到正文本其实是存在于副文本所呈现的史料语境之中或当时的文学生态圈之中。所以,副文本的概念不仅让现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更细化,而且会使现代文学的史料来源更独特。其次,副文本中的史料也参与了现代文学史的建构。副文本的内容甚至形式本身就是遗留态的文学历史,或者说就是现代文学史的史实。其中,它们所体现出的文学事件,甚至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原态历史。如《地泉》的五人序的会集、《中国新文学大系》众导言的写作、良友文学丛书系列广告的刊登、鲁迅和高长虹通过广告所进行的交锋等。同时,副文本为正文本的解读提供着历史信息和历史语境,书写着某一作品的生产史、传播史、版本史等,书写着某位作家的交往史、成长史等。扩大来看,副文本写出了整个现代文学的出版文化史、文学思潮及论争史、文学社团流派史、文类发展史等。若把某些副文本系统地整合起来,也可以建构更有特色的现代文学史。如已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图志》,正在编写中的现代广告文学史,还可以去写现代序跋文学史。总之,副文本与现代文学史共生同步,是纪实的、即时的、极具时效性的现代文学史。它显现、还原并建构着现代文学史。不过,副文本提供的史料也有可能对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的写作形成某种遮蔽。这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副文本有特定的写作目的,所以提供的可能是经意的史料或虚假的史料,如序跋的写作受个人情感左右,广告的写作有营销的意识等。另一方面,副文本的写作还受到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如序跋、广告往往是即时写作,对许多文学现象或作家、作品等还不能作准确或正确地把握,或突出或不见某些史料。又如不同时代的注释就会受到文学体制、政治风气或官方意识形态的制约,《鲁迅全集》的注释就很典型。由于这些原因,副文本提供的史料就可能不真实、不可信,或误导或偏颇或虚假,从而遮蔽我们的视野,遮蔽文学史的真相。所以,对这些史料,我们应加以分析、比较和考证。总之,对副文本的史料价值,我们应有辩证的认知态度,既能看到其正面价值,也能看到其负面效应。
作者:金宏宇 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