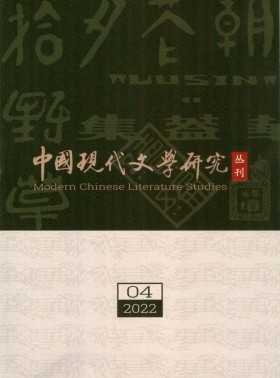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文学公共领域空间构成与话语向度,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20世纪初开始,中国现代文学公共领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文学公共领域作为一种文学生态系统从参与主体、存在形态、运行机制等的结构上的根本转型。其结构形式由文学期刊、文学社团、书局、书店等构成,并出现了以这些空间结构方式为核心的作家群和系列创作的局面。文学公共领域开始真正担负起哈贝马斯所说的“自我启蒙”的功能,成为公众关于社会与人生的严肃认真的思考和公开的理性批判与讨论的自由交往空间。
关键词:现代文学;文学公共领域;文学机制
应该说,清末民初的报纸、学会和新式学堂作为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在那时承担的还是政治改良、民族救亡的政治功能,文学的公共领域还不能算真正形成。相较于晚清和民初,从“五四”开始的文学公共领域可谓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文学公共领域作为一种文学生态系统从参与主体、存在形态、运行机制等的结构上的根本转型。
一、公共领域主体的新变
到“五四”时期,现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就参与者的身份来说,经历着一个从封建士大夫阶层向平民知识分子的转变。清末“士绅”型知识分子尽管有了西方文化视界,但仍然不能算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读书人开始与上层社会的生存模式和思维方式相分离。尤其是留学潮和现代大学的创办,西式教育体制在民国的全面确立,形成了新型师生关系和群体聚合空间的革命性变化。围绕学校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以新式教师和学生队伍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它构筑了中国现代文学公共领域的主体和文化基础。新式学校和留学制度培养了大量的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士绅阶层既渴望革新图强又慕恋既有的文化秩序,和现存政治体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式知识分子大多接受的是现代西方模式下的教育,而此时,掌握传统思想意识话语权的传统士绅阶层全面衰退,启蒙知识分子开始影响并逐渐占领知识界、思想界、舆论界的文化高地。他们宣传西方文化,提倡个性、自由、民主、理性,从此开始了知识阶层完成了脱胎换骨式的现代化转变。不仅创作主体,接受主体(读者)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公共领域的丰厚的思想文化成果吸引、影响、积聚、培育了中国民众的阅读群体,造就了一大批新思想的传承者。尤其是青年人,《新青年》、“创造社”、晨报、时事新报成为他们普遍接触并融入其中的社会空间领域。它们所倡导和信奉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成为青年人精神塑造的规范,对于传统的挑战和社会的反叛成为了新时代的青年人的人格特征。这与文学公共领域的新型主体参与和影响力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这个新型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是以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集结和对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和人文精神的吸收过程同步的,它逐渐摆脱传统社会代表型公共领域和晚清政治型公共领域的特征,开始呈现了一种追求自我独立的脱离其他依附的真正具有“私人言说”性质的社会公共话语空间。“五四”时期,作为文学公共领域的参与主体,知识分子大都有着多重社会身份,这与晚清和民初时期主体的士大夫政治追求和生计需要而活跃于公共领域有着根本区别。以《新青年》为例,鲁迅、陈独秀、、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高一涵等编辑中,除鲁迅之外均供职于高等学府,他们均拥有稳定的社会职业,有着自由灵活的社会身份和活动空间,生活收入的充分保障和思想行动的自由使得他们可以以独立人格进入到文学的公共领域。知识分子的职业身份使他们成为了不依附任何势力而存在的“私人”。可以就“普遍的文学话题”展开理性辩论,真正的“私人言说”也随之产生并且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思想影响力度和舆论扩张能量。与之相较,晚清和民初时期的各种无形的道统规范束缚所造成的创作空间和自由的严重挤压,虽然随着传播媒介的商业化与市民阶层的出现而有所改变,但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消闲滥情、狭邪猥琐。掌握了最新世界思想潮流的新式知识分子,却能引领社会变革的,传播现代人类精神文化先进成果,实现国民的自我启蒙。五四以后新一代知识分子和公共领域的共同价值追求,直接导致了文学公共领域的全新转型。
二、结构形式和运行机制的转型
作为文学的公共领域,报纸等在最初的萌芽时期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许多报纸和副刊是那时的主要空间形式。“五四”以后,参与者主体的变化和现代教育、出版业的繁荣,文学公共领域的结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报纸副刊作为主要形式变为由纯粹的文学期刊、文学社团、书局、书店等形式,并出现了以这些空间结构方式为核心的作家群和系列创作的局面。“五四”时期,随着市场化机制的发展和文化生产商业模式的形成,书籍的出版发行己由原先初级的官办、社团自办及小范围交流发售等逐步扩大为规模性、社会化、市场化的资本主义文化工商业,从业队伍与专业水准急遽提高。这不仅表现在新式的书局、杂志、社团的大量诞生,出版发行机构数量上的增长上,还体现在其空间地域的分布变动上。晚清及民国初年,文化业的重镇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和沿海殖民化商业城市,但从“五四”前后,文化出版发行机构已开始逐渐向内地省份和相关城市蔓延,浙江、江苏、山东、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先后成为文化出版的重镇,各类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报刊杂志和书籍纷纷应运而生。五四以后,杂志的出版成为新文化展开及其成就展示的重要标志。据统计,从1917到1921年的5年间,全国就新出报刊1000种以上。[1]文学刊物更是直线增长,1917年到1927年有144种,1928年到1937年有418种,而1872年到1901年仅有5种,1902年到1916年也只有57种。[2]1934年更有“杂志年”之称,在此前后,鲁迅、茅盾、巴金、丁玲、施蛰存、徐志摩、梁实秋、沈起予、朱光潜、沈从文、郑伯奇、林语堂等文化人创办、发行了大量文化刊物和书籍,《北斗》《现代》《文季月刊》《新月》《作家》《光明》《文学杂志》等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学类刊物。书局往往是多种期刊杂志的出版者和发行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各自都创办和发行多种期刊杂志,发行量多达数十万份。除了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样大型的出版社之外,更多的是大量小型的图书、杂志的生产和流通机构。由新文学作家自己出资创建并参与经营的书局也适时而生,独立或合伙创办出版社,经营书店的已是普遍现象。例如北新书局、泰东书局、亚东书局等,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就承担了大量新文学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它们与新文学社团创造社、莽原、未名、语丝、新月等合作,在出版新文学著作方面,表现出强劲的开拓性和生命力。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推动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高涨,形成了对文学公共领域的空间既有格局的突破和更新,从而催生了新文学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多元化繁荣发展。晚清的文学团体不多,但“五四”以后,由陈独秀等现代知识分子所发起和领导的社会与文化改造运动再次席卷中国。作家群体组成的文学社团流派蜂起,这些团体的数量非常之多。在《新青年》的带动下,仅从1921到1923年,全国就出现文学社团40余个,到1925年,文学社团已激增到100多个。[3]同时,社团还与报刊、丛书相呼应,有的是作家直接参与报刊专栏创作,有的是文学社团和作家群与出版机构合作,他们以报刊杂志和丛书出版为联结,纷纷形成为文学公共领域的一极,展示了其多元话语的言说姿态。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文学社团、作家和文学刊物、文学流派之间,诸多因素常常交织在一起。无论是北京大学和新文化风云人物及《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杂志,还是文学研究会、社会问题小说家及《小说月报》《文学旬刊》,还是创造社、留日青年学生和泰东书局及《创造月刊》《创造周报》,还是新月社和英美留学生和《诗》月刊、《晨报副刊》等,都显示出这样的模式。作家们以相同的价值立场、审美理念,凝聚成强大的文学话语力量,共同汇成了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彰显着文学公共领域的发展壮大和走向成熟。
三、多维度的文学话语空间
民初的文学公共领域作为传统士绅精英在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在混乱的社会现实面前彻底崩溃之后的纵情恣意的精神空间,其文学所表现出的人性价值内涵和审美格调是不高的。在哈贝马斯看来,文学公共领域作为一种非政治形式的公共领域,其功能是使公众能形成一种针对自身的批判性公共反思。“五四”之后,公共领域的参与主体转变为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人文理性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作为文学的生产者、接受者、消费者、批评者使文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文学公共领域开始真正担负起哈贝马斯所说的“自我启蒙”的功能,成为公众关于社会与人生的严肃认真的思考和公开的理性批判与讨论的自由交往空间。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则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具备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它形成了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与国家公共权力领域相疏离的公众的空间,它所完成的不同于清末民初的结构转型,既是现代西方文化所带来的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又是现代文学意识不断向深层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文学由此开始摆脱传统文学“载道”“传道”思维模式,汇入现代文学发展的世界潮流之中。作为文学意识觉醒的最初表现,对于文学本体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论争成为文学公共领域持续不断的普遍话题。“五四”时期有新旧之争、文白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三十年代有“左联”与民族主义文艺的论战,与“新月派”的论战,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战,此外,还有“帮忙”与“帮闲”的有“京派”、“海派”之争;四十年代则有“暴露与讽刺”、“与抗战无关论”和“真伪现实主义”等论争,显示出文学公共领域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强大基础性功能。不同时期,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私人和团体,从各自所理解的价值标准出发,对文学进行公开讨论和争辩。在反复的论争中,突破传统和既有的文学规范束缚,为文学的自由发展争取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从而拓展出最大的话语空间。作为这种讨论和争辩的具体实践则是文学思潮、流派创作的群峰并峙,这种多元化的格局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日益突出而逐渐消退。由于文学公共领域的主体是接受西式教育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西方文学思潮的大规模横向移植便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公共领域的突出现象,众多的流派和社团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潮、文学思潮的本土代言者。本来,欧洲文学思潮演进是有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审美理想所决定而形成的有序性,自文艺复兴开始,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各种时代艺术思潮都有着明确的时代前进的自然发展脉络。但在中国,由于公共领域所并存的多种接受不同时期西方文学思潮参与主体,西方思潮,只要能成为打破和成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束缚,统统被用来作为追求文学自由发展的精神武器。文学的价值空间维度也就出现了同时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例如,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提出“为人生的”文学,就是受到十九世纪欧洲激烈社会对立冲突之下的现实批判文学的影响,倡导“写实”精神,关注社会问题。而与其并足而立的“创造社”则较多地接受了十九世纪初打破理性规训,追求反叛个性的浪漫文学的影响,喊出“为艺术而艺术”。尊重自我内心世界,否定外在压迫,同样具有关注人生和改变现实的精神诉求。李金发、穆木天等的诗歌则显示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对中国的影响,由此,外国现代主义思潮和众多的创作流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艺术资源,例如从三十年代的《现代》杂志和新感觉派小说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借鉴,到四十年代的卞之琳、冯至、九叶派诗歌等对德国、美国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经验的吸取。此时的文学,它将个体生命的体验带入小说,促使小说从“民族/国家”的政治叙事的模式中摆脱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社会关怀相并列,成为一个自我启蒙的、自给自足的世界。它开始沿着自身的存在方式和生产机制而运作,摆脱以往政治公共领域的钳制,成为社会场域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美)周策纵.史[M].陈永明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261.
[2]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M].北京:中华书店,1959:510-580.
[3]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6.
作者:杨永明 单位:北部湾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