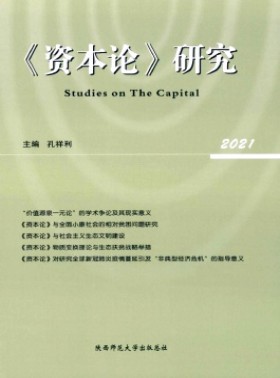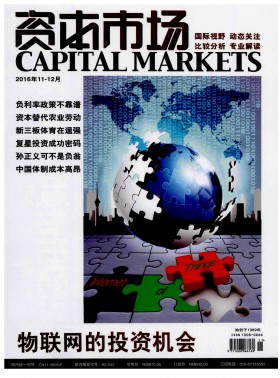摘要:根据中国当代实践,以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回答中国问题,是发展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如何根据当代中国吸收资本元素的最新实践,从理论高度,用中国话语、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对与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关系、对中国新型现代化建设的探究,这是当代中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绕不开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资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实践。在这个需要理论和思想的时代,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因此,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尤其要注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
一、吸收资本元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必须回答的一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中,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生产力不断发展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两个显著的内在特征。生产力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先在保证,共同富裕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指引。如何既保证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又确保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向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方案的实践给了我们明确的启示:一方面,在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方面,不是完全的隔绝资本因素的存在,而是在逐步引进过程中积极的运用。199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资本”概念。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使用了“公有资本”范畴。200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运用了“国有资本”范畴。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民间资本与公有资本“公平竞争”。200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资本可以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200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新农村发展要注意资本要素的运用。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另一方面,虽然注重运用资本因素对生产力发展的潜在推动,但并非放任资本因素的随意发展,而是立足于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并加强顶层设计的驾驭运用。社会主义的先在前提决定了中国对资本的运用,是建基于无产阶级为领导阶级的、旨在服务广大人民的政治上层建筑之上的,譬如依托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而非三权分立的西式“宪政”;坚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而非本质归属资产阶级执政的多党选举制。虽然逐利是资本的天然本性,但中国对资本的运用,更注意运用上的顶层设计,譬如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多层次的监管体系,既确保资本运转的合法化,又多层面增加全民在资本运转上的利益共享。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认知上对资本的漠视、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驾驭对资本的运用,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精髓,又与时俱进地做到了合乎时代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因素的引入,深刻地丰富、扩展了社会主义的内涵。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融入资本因素的新型实践推进探究,才能更加科学、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二、吸收资本元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当前学界对两种制度关系的已有探究来看,大体上存在三种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前者逐步扬弃后者的过程。这种观点的理论根据在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明确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视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更高级别的社会发展形式。第二种观点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同质不同样。这种观点的理论根据在于,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也存在市场经济,也应用了资本元素,因而它们之间很难说有本质上的不同。一些学者,尤其国外的右翼学者甚至把现实社会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变形形式。第三种观点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实际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处于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我们暂称其为社会主义Ⅰ),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肯定是前后替代的关系;一类是人类社会发展序列中与资本主义并行共处于我们整个当今所处大时代的社会主义(我们暂称其为社会主义Ⅱ),这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是一种并行共处的关系,现实社会主义存在蜕变为资本主义的危险。客观而言,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是怎样的互动关系,之所以引起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重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重要课题,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第一,20世纪,以苏联、东欧为代表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把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将很快衰亡,但在资本主义的实践中并未得到验证。第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以福山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狂呼“资本主义”是终结历史的最后一种社会发展形式,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在中消沉下去,反而从变革中加深了对资本、资本主义的认识、实践,在其后加固了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作用。第三,随着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的编辑和陆续出版,随着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发展阶段思想认识的深化,在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东方地区、国家可能出现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发展形式,是否直接就是马克思在论述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发展形式,日益受到学界的质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现实世界并存的两种典型的社会发展形式。社会主义正确对待与资本、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发展就相对顺利;社会主义未能正确处理与资本、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发展就经历曲折。实践证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必须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探究。
三、吸收资本元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认识,是又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存在怎样的一种辩证关系呢?我们知道,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执政权力的赢得,从理论上而言,源自于列宁的“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权和经济文化稳固后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基于列宁的下列共产主义发展阶段思想: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把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把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但实际上,马克思一生并未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做过上述之类的区分。而且,在马克思明确涉及共产主义不同阶段特质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共产主义并不曾被做过严谨科学意义上的阶段划分。“《哥达纲领批判》直接目的是全面清算拉萨尔主义,带有浓厚的论战色彩,而不是专门研究共产主义社会,并解决其具体发展阶段的。”[2]《哥达纲领批判》中确实出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等词语,但这两个词语仅在上述文献中出现过一次,而且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并不能作为臆想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同义语,“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也不能作为臆想的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的同义语。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视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把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等同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进而得出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只有两个阶段的认识是不正确的。马克思认为,以俄国、中国为代表的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地区、国家,它们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社会存在的“农村公社”等因素,“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3]765。然而,“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立的新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不是直接就是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呢(虽然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的较低发展阶段)?如果直接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必然是存在于现代资本文明之后的经济形态阶段,那马克思又怎么称俄国、中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建立的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只是“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4]?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思想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可以直接建立共产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深读马克思晚年文献可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是指绕开此发展成路,以避免按此路行进,遭受一些资本主义相应必然铁律的支配,因为“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的其他民族一样受到那些铁面无情规律的支配。”[3]466不选择资本主义,而选择其他发展道路,都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3]466从资本哲学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相比之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二者对资本要素的认知、实践存在区别,并无政治上层建筑层面上的质的差异。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的新的社会发展道路,这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一种怎样的承继关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需要在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
四、吸收资本元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现代化建设的顶层引领,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课题。现代化的目标倾向是力推置身其中的地区、国家的发展逐步达到并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的境态。现代化的这一目标倾向本质上归属于资本文明状态,资本是现展的基础牵引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要实现对中国现代化的引领,需要也必须注重资本因素。但因为资本的二重性,一方面,资本不断扩展式再循环增殖自身的趋势,带动了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5]。另一方面,资本不断扩展式再循环增殖自身的特质依托于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对立性关系存在。资本不断革命化对生产力推动的同时,又在不断地造就着新的空间界限。“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5]。资本的生产总是在矛盾中运动着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运用资本因素引领中国现代化时,需要注意下列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既存在质的区别,譬如二者不仅实施的阶级、预期目标不同,而且在实施手段、实现途径等方面也存有差异;也存在相似的方面,譬如都需要资本因素的参与,都有助于现代化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后发型的现代化,如何做到既确保与资本主义式现代化的区别,又能最大程度地借鉴资本主义式现代化的精粹,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现代化引领,必须注意。第二,社会主义主推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是中国现展最为典型的特征,但现代化并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只是其基本目标。具体而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其中一个阶段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代化实现之后,还会进一步推动社会的高度发展,并在资本全球发展达到其历史极限时,联合全世界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发展的最大限制的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消灭资本”,进而和全世界人民一道迈向共产主义社会。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2]邓昌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J].探索,2007(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7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390.
作者:陈广亮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