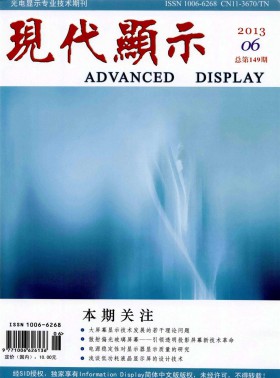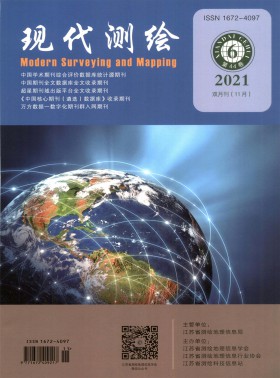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语文教学知识建构逻辑学论文,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在近代中国教育转型过程中,教育界有识之士认识到普及逻辑学知识对培养现代国民的重要意义。1920年代初期,夏丏尊通过借鉴日本论理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探索一条将逻辑知识寓于中学现代语文教学的独特路径,在实现逻辑知识更大范围普及的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语文知识体系。1930年代,夏丏尊在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过程中,于形式逻辑之外,又补充了辩证逻辑的内容,并针对逻辑学和语文的关系,提出了逻辑知识应用以情境为要的总体要求。
关键词:语文知识;逻辑学;思维科学;形式逻辑;辩证逻辑;情境
在现代语文知识建构中,除语音、汉字、词汇、语法、修辞、文学及文章等与语言文字直接相关的本体知识外,作为思维科学的逻辑知识既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语文教育理论的重要维度。现代语文学对现代逻辑学的吸纳与接受,不仅促进了自身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而且也使语文教育踏上了科学化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陈望道、孙俍工等众多语文学家,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其中贡献最为卓著的当属夏丏尊。
一、语文教学对逻辑知识的初步吸纳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有识之士已经逐渐认识到,除了在器物制度的层面学习西方以外,开启民智、启蒙思想才是富国强民的根本手段。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指出,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础在于造就“新民”。与之相似,严复也提出,“吾国之最患者”在于愚、贫、弱,“尤以瘉愚为最急”[1]。而启蒙民众思想所依靠的现代知识基础,就是“名、数、质、力”四种科学。居于首位的“名学”,即日本所谓的论理学和西方所谓的逻辑学。在新式人才的培养和造就中,“改易思理”,以西方现代逻辑知识变革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推动思想革新,成为疗愈国民愚疾的一剂处方。随着西方逻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思维科学的价值和功能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正式进入学校课程。1902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了“名学大意”和“演绎法”两门课程及其学习时数[2]。1904年,《奏定大学堂章程》用“辨学”来指称论理学,并将其列为随意科目;《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则将“辨学”列为必须修习的科目。此外,辨学课程作为教育科的内容被列入师范学堂章程。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规程》,论理学被确定为“教育首先宜教授”的内容[2]。这一时期,逻辑学知识作为课程主要在大学堂、高等学堂和师范学堂内设置,由于普通中等教育并没有安排相关课程,因此,逻辑学知识主要还是一种专业教育。为了进一步普及逻辑学,教育界有识之士提议在普通中学教授论理学,这就为现代语文知识体系对现代逻辑学的吸纳提供了契机。1918年,夏宇众在《中学国文科教授之商榷》一文中,倡导在中学四年级增加对“论理学”大纲的教授。因为中学高年级学生“宜兼习论辩说理文字,而自中文字非慎思明辨者不办,欲思之慎辨之明必有待于Logic”[3]。立足于培养中学生正确而良好的思维习惯,夏宇众阐述了中等国文教授论理学课程的紧迫性。他认为论理学的缺失,造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弊端:首先,中学常出令人“瞿然骇也”的命题,这是导致中学生写作水平差的重要原因;其次,即便是被视为佳作的习作,也不过是翻来覆去地“捃摭”传统名篇中的个别语词或观念,发出“空泛的、笼统的、荒谬的”议论;再次,教师诸如“老气横秋”“骎骎入古”“笔情奔放”“操纵自如”等无的放矢的评语,将学生的思考力导向了“虚妄”。夏宇众提出在中学国文课程中增授论理学,并不仅仅为了解决学生写作的问题,而是希望学生能够“构思审究,观察推理,略识趋真避妄之途径”,进而能在社会生活中明察是非、慎思明辨、祛除虚妄,避免被现实中的恶潮流所惑。夏宇众在文末还附录了《中学校论理学大纲讲义》的目次。蔡元培对夏宇众的观点及做法曾给予肯定和赞许,认为夏宇众对“教者、学者之通病”进行了“极精确之抉摘”,特别是在中等学校增授论理学大纲一项,“尤足矫专己守残之习惯”[4]。何仲英在《中等学生的国文学习法》中将学习国文的笔记与论理学相结合,尤其指出批评式的笔记文章写作,“先要看一两部有名的论理学书”[5]。自此,语文教育界在思想观念上已经充分认识到逻辑学知识在教育学上的重要价值,即利用逻辑学革除语文教学中的种种弊端,完善语文学科自身的知识体系,从一个新的维度建构现代语文知识体系。但作为语文学本体性知识以外的另一门独立的学科知识,逻辑学知识与语文课程并无必然联系,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学阶段应该学习哪些具体的逻辑学知识,以及逻辑学应当如何与语文教学的实际相结合,当时学界尚缺乏具体可行的方案。
二、形式逻辑寓于语文教学的尝试
1908年春,夏丏尊在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日籍教员中桐确太郎的通译助教”[6]。中桐确太郎曾在早稻田大学讲授论理学,其讲义收录于1906年出版的《早稻田大学三十九年度政治经济科第一学年讲义录》中,该讲义系统地论述了形式逻辑的由来及意义,命题、推理的方法等内容[7]。中桐确太郎任教于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期间,曾教授教育、伦理、心理、论理等科目,夏丏尊因此较早地接触到了逻辑学知识。1919年,夏丏尊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改革国文教学,对诸多现代语文教学理论中的重要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8],这使他有机会对中等教育中语文与逻辑学相结合的问题做出实践上的探索和理论上的总结。夏丏尊与陈望道、沈仲九、刘大白等共同拟定的《国文教授法大纲》,将使用白话“明白、普遍”地表现思想感情作为语文教学的形式目的之一[9],对学生如何掌握正确认识和思考客观世界的方法,养成符合逻辑规则的表达习惯,提出了必然的要求。1920年秋,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国文科期间,进一步探讨了以逻辑学指导写作教学的具体策略。这一时期,陈望道、孙俍工、梁启超等都曾做过相关探讨,同他们的论述相比较,夏丏尊在借鉴逻辑学建构和完善现代语文知识体系,同时把逻辑知识寓于语文教学方面,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路径。
1.引入逻辑学术语,调整逻辑知识编排顺序
“命题”是现代逻辑学的核心术语之一,夏丏尊将其直接引入到现代文体知识的建构中。他以“命题”作为议论文的根本,并围绕这一概念来定义该文体。他认为,议论文“实际上就是对于所提出的命题所给的证明———必要的时候,还加上相当的说明”,而作者提出命题则被夏丏尊认定为议论文写作的第一步骤。夏丏尊进一步从数量和语气上明确命题的性质,即命题必须是一个“表明语句”(indicative),而“疑问语句(interrogative)、命令语句(imperative)、愿望语句(optative)、惊叹语句(exclamatory)”等语气,则逐一被夏丏尊排除。这一时期,陈望道、孙俍工等在论述中尽量避免或减少逻辑术语的使用,多以描述的方式来叙述逻辑学的知识。陈望道从形式、数量、在写作中的呈现、表达等方面对议论文的题目加以规定[10]。孙俍工在此基础上,更为详尽地论述了判断的含义。他认为判断是“含有主词与表词的形式意义都完全的句子”,这其实是从语法中的句类、句式两个角度描述了“命题”这一概念。他还进一步从内容、语法、表达等方面对论辩文的题目提出了要求,如:“题目必须弄得很窄,只含一个要紧的意思”,“题目必须用正面的语气”[11]即为命题的属性。与陈望道、孙俍工等人比较而言,夏丏尊通过“命题”这一术语,以简驭繁,极为精练地概括了议论文体的本质特征,在一个框架内囊括了陈、孙等人从不同角度对论题提出的限制和要求。对于命题类型的阐述,夏丏尊和孙俍工对于知识内容安排的顺序存在较大差异。逻辑学中,对命题性质的阐述一般从“质”“量”以及这两个维度的综合展开。孙俍工袭用这一思路,没有采用任何概念式描述,围绕“竞赛运动废止”来说明议论文的题目类型,从“质”上分肯定和否定,从“量”上分全称和特称,将这两个维度总合,分为全称的肯定、全称的否定、特称的肯定、特称的否定。夏丏尊虽然在语文知识体系中较早地引入了“命题”这一概念,但是在接下来的探讨中,仅提到命题在“质”上的分类,即肯定和否定命题,且同样以“竞争运动(不)应该废止”加以说明。出于对写作的实际情况的考虑,夏丏尊围绕此例对两类命题常常出现在文章中的各种形式详加讨论,却并不急于和盘托出逻辑学中命题的全部性质类型,而是将命题“量”上的类型这一知识内容留待议论文教学的最后才加以阐述。他认为,议论文从预设敌论的存在这一意义上来说,均是驳论文。夏丏尊特别强调,在驳论过程中要重视对敌论论辩思路的提炼、把握和分析。换句话说,驳论的第一步,在于找出敌论的立脚点,包括总结敌论的根本命题和发现敌论证明的根据和法式。但是,由于检查发现敌论中论证法式的漏洞,未必能推翻敌论的根本命题,因此,对命题的攻讦才是驳击中最彻底最重要的一点[12]。至此,夏丏尊通过对命题各种类型的综合考察,以审视敌论命题为契机,补充介绍命题性质这一做法,不仅在作文教学中完善了对逻辑学中“命题”概念相关知识的讨论,而且以驳论为出发点,从对敌论命题的关注中全面反观命题性质,也向学生提示了议论文章写作之初思路的起点和思考的焦点,这本身就是对学生思维的规范和训练。
2.以论证方法的研究取作框架的限制
逻辑学之于语文教学的核心价值在于思维的整理,所以逻辑知识最集中的运用在于指导议论文章的关键主体———论证的写作。陈望道将论证过程分为引论、议论本体和结论三部分。孙俍工的观点与之相似,不同的是将第二部分称为“辩证”,且强调了论辩的结构框架,具体地规定了各部分特定的写作内容。对于引论,陈望道认为其任务“在乎解释论题底要领”。据此,他确定了若干条引论所允许解释的内容,包括论题的由来、用语的意义、撇开论外事项、承认共许事项、正反两面意见的分歧点、本文的中心论点、引论中可列入的解释等[10],这可以看作是对引论所包含的内容的最广泛的说明。陈望道还通过细致的陈述,划分了这七条内容出现的必要性层次。虽然孙俍工在这一方面不及陈望道阐述明晰,但是,对于辩证,孙俍工指出“辩”即主张某论点的理由,“证”即举出该论点的例子。对于第三部分结论,孙俍工也阐述了其具体内容,即断定和总结,较陈望道更为详尽明确。夏丏尊指出,论证是论辩中最主要的部分,但是与陈望道和孙俍工对论证过程进行剥离和剖析不同,夏丏尊并未对文章中的逻辑论证过程设置精细的框架,而是直接切入论证方法的研究。夏丏尊认为,论证“须求之于论理学”,基本方法包括演绎法、归纳法和类推法三种,在方法以外不刻意预设和限制论证的构成部分、顺序以及各部分的具体内容。陈望道和孙俍工对逻辑论证的阐述,虽然对思想的整理提出了可行的具体步骤,但对于语文课程中写作教学而言,则于无形中束缚了文章的结构,导致文章样态的固化。夏丏尊在讲义中透露,严谨的论证过程当从科学的方法入手,而非程式化的表达,这似乎更加接近写作这一创造性活动的实际和逻辑这一思维科学的本质。
3.形式逻辑论证方法的引介
梁启超曾在《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提出了写作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即“该说的话或要说的话不多不少地照原样说出,令读者完全了解”。他指出,许多古文之所以不能准确地达意、完全地使人明了,原因在于作者缺乏逻辑学的修养。针对议论性质的文章,梁启超进一步强调了逻辑学的价值,是使辩论“耐驳”和“动听”。梁启超这里所说的逻辑学修养,实际上指的是有效地发挥演绎法在表达中的形式功能,“在真确的事实之上施行严密的推理,拿妥当的形式发表出来”[13]。而妥当的形式,即三段论法的形式:(1)大前提;(2)小前提;(3)断案。梁启超虽然强调三段论是一种最为普通且必须使用的发表形式,但对于三段论的解说,梁启超仅举一例,其使用中的情况,未见其详。与梁启超所不同的是,夏丏尊在论证方法的阐述中,特别重视演绎法的具体应用问题,如他在对演绎法的探讨和解说中使用了大量的示例、对演绎法体式的说明涵盖了最基本的形式及其各种变式。孙俍工则从论式的句法结构特点出发,阐述三段论在形式上的规定性。他将三段分成大前提、小前提和断定,从句法角度来说,它们都是“有主词有表词而语义完足”[11]。根据主词和表词在句中特定的位置,孙俍工又引入了大词、媒词和小词一组概念。同样列举三段论的各种变格形式,孙俍工只提出了日常谈话以及作文过程中为求意义的表达,形式可以自由,不必拘泥于三段论的排列顺序的观点,至于如何在实际表达中进行用语上的调整,并未加以讨论。夏丏尊则在允许三段论顺序变更和省略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写作过程中的实际操作问题,对三段论在实际使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同情况,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讨论,并提出了检验演绎法可靠性的方法。
4.四种性质的论据组成的严密的论据体系
夏丏尊和孙俍工二人对论据属性的阐述较为一致。夏丏尊将逻辑学中的因果论、例证论、譬喻论、符号论作为证据的构成基础,认为“二种以上的议论连结起来,就成有力的议论了”。在具体阐述论据属性划分时,夏丏尊从思考和论辩的严密性出发,提出了很多论据使用的规则、要义和禁忌。对于因果论,夏丏尊强调了以证据为原因来证明命题这一单向的过程,而孙俍工则强调证据与断定之间的因果互证性。孙俍工认为,因果论与例证论有很大的连带关系,因为罗列多条具有因果关系的证据就是进行例证的方式,但他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暴露了因果论的不可靠性,而这一点正是夏丏尊所要强调的。夏丏尊指出,由于一件事往往可以做出正反相对的因果论,因此,这种证据准确度很小。同时,夏丏尊还补充了更为严谨的使用规则,即使用时必须添加“大概”“或”等推量语词。与因果论据颇有关联的是符号论,孙俍工称其为记号论。由于孙俍工在因果论的使用中认为因果可以互推,所以他将记号论简单地定义为“由结果而推论原因”,只不过必须在“一个结果只有一个原因”的情况下才能准确使用。在孙俍工所建构的论据性质的体系中,记号论不具有独立的地位,而是作为因果论的特例来对待。夏丏尊则将其并作一种独立的论据类型来加以保留,因果论和符号论相反相成,两种性质的论据得以并列,论据体系结构也更加均衡。对于例证论,孙俍工认为可以参考归纳法,但夏丏尊则指出这一类论据的使用除了遵循以部分推全体的归纳法规则外,还应遵循以甲部分推乙部分的类推法则,且联系其在语文学科中的应用实际,强调“人事和物理”在类推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例证的真实可靠性。对于譬喻论,孙俍工称作比喻论,他通过对比实例指出,此类论据和例证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立足两件事理的相似点推论相似的断定,后者是通过事实推论未知。夏丏尊不仅用同样的方式阐释了这一点,还强调了这种相似性之间的恰当关联是譬喻论使用得当的关键,并提出了两种检验其可靠性的方法。最后,他分析了使用频次,认为譬喻论的使用古多今少,易于欺人,提醒学生留意辨识。与孙俍工相比,夏丏尊多次提示学生重视对论据可靠性的考量,并明确地给出了总结式说明:因果论和符号论不全然可靠,例证论和譬喻论只可做补充。为了思考的严密和论证的可靠,夏丏尊重视各种性质论据之间的综合使用,在语文知识安排中设置“各种议论的联络”专题,对各种论据在实际中的综合运用进行了探讨。
5.规定写作顺序以提高论证可靠性
文章写作的过程,也是学生不断整理思维的过程;文章呈现出来的内容编排顺序,也体现着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对不同事象、不同问题进行书写,必然采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夏丏尊通过对写作顺序的规定,指导学生调整论证思路,增强文章的可靠性和说服力。与陈望道、孙俍工侧重安排论证每一部分的顺序和内容这样的细枝末节不同,命题与论证的论辩结构安排,是夏丏尊着重探讨的问题。他认为,命题是根本,所以出现的位置才是论辩顺序安排的关键。最普通的议论文,为了让读者在开篇明晰主旨,应该先提出命题。此外,夏丏尊还特别强调了两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特殊情况:命题容易引起反对和命题太平凡时,应当从自己主张的必要性等方面说起,而后提出命题。夏丏尊对论证顺序的规定,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安排各种性质的证据的出现顺序,以实现证明的说服力度和可靠性最大化的策略。他认为,如果各种性质的论据均具备的时候,应当遵循因果论、譬喻论、例证论和符号论的顺序,才能令读者“深切地信从”。不难看出,这也是夏丏尊为了照应证明顺序问题而作出的有意安排。
三、辩证逻辑的补充及以情境为旨归的逻辑知识应用观
1929年《高级中学普通科国文暂行课程标准》在教法要点的作文练习一项中,提出要让学生养成“证据的批评”的习惯[14]。1932年《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在教材大纲中对文章做法作出说明,其中就包括辩论术。在实施方法概要中,则规定高中国文“应注重辩论之方式,证据之搜集,判断之正确,敌论之反驳等,以养成学生明晰之头脑”[14]。同年,教育部颁布的《初级高级中学课程标准总纲》将论理列为一门独立的课程,作为教授学生综合性科学方法论的“高中课程之殿”。1930年代,夏丏尊通过国文教科书的出版编写,将逻辑学知识正式引进初级中学国文课程,不仅为高中国文、论理课程目标的实现打下了重要基础,也为方法论与具体学科相结合做出尝试,语文课程中的逻辑知识与独立的论理课程形成了有益的互补。这一时期,夏丏尊进一步扩展了演绎和归纳两种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在语文课程中的应用领域,即不仅把二者作为服务于议论文的论证方法加以介绍,还将它们看作记叙文的写作思维方式来加以阐述,这是现代逻辑学术语在教科书中的首次出现。1932年,在《开明国文讲义》(第一册)第十四篇文话《小说》中,夏丏尊根据演绎和归纳的不同,对叙述文的典型体裁———小说进行分类,并且在《文选•三一》《文选•三二》分别选编鲁迅的《孔乙己》和MD的《大泽乡》作为例文:其一用归纳的方法,就是作者先从现实里去看出意义来,然后,或者就把现实的事情、人物记录下来,使人家看了,也看出作者所看出的那点意义,或者另造事情、人物,作为材料,使那点意义格外明显。……又其一用演绎的方法,就是作者先有了一种意义,然后创造事情、人物来寄托它,使人家看了,也悟出作者所见到的那点意义[15]。《开明国文讲义》(第二册)第二十二篇文话中,夏丏尊又将演绎法和归纳法作为日常生活中“下论断、立主张”的“思想方法”,对二者的形式进行了详细的说解。这一时期,夏丏尊还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中小学国文教学的诸多问题。1935年,夏丏尊在《国文百八课》(第四册)的文话中指出,作者写作议论文时为证明自己的主张所经历的“从理由到达判断”叫做“推理”。演绎法和归纳法统称为“推理方式”,分别在第十六和第十七课文话中论述。从强调思维方法的形式步骤,到强调写作的推理进程,夏丏尊通过引入“推理”这一概念,阐述了思维在心理层面上动态推进的过程。此外,夏丏尊还增补了一种推理方式———辩证,这意味着在既有的形式逻辑的基础上,辩证逻辑通过国文教科书的编写也被纳入到语文教学的视野当中。形式逻辑,以同一律为基础,其推理的过程是对事物相对静止或量变过程的表述;辩证逻辑,则以对立统一为基础,其推理的过程是对客观事物辩证发展过程的正确反映。夏丏尊首先分析了形式逻辑不切合事物实际之处。他认为:“演绎推理只用概念来处理事物,把事物当作独立静止的东西来看,事物本身的变化和相互间的关系是不顾及的。归纳推理所依据的是个别的事例,对于各个事例平等看待,也不能顾到事物本身的变化和事物相互间的变化关系。”[16]夏丏尊既认识到了事物运动的普遍性,同时,也认识到事物间相互联系的普遍性和矛盾复杂性,并指出下判断要视社会上的各种复杂情形而定,“不能一概凭空”。基于此,夏丏尊详细举例介绍了辩证法的三个原则:(1)矛盾对立,这是事物发展的原因,而辩证法却以矛盾为出发点,认为世间万物本来自身含有矛盾;(2)量影响到质,这是事物发展的状态,“一种事物因了量的改变,性质就会变化”;(3)否定的否定,是事物发展进步的顺序。但是,夏丏尊清醒地认识到如若死板地恪守这三种原则,那无疑违背了辩证精神本身。因此,他特别指出,这三种原则并非推理的定律或公式,不可一味套袭。排除静止的孤立事物观,把事物看作连续进展的东西,遵循“实际事物上的实践”,才是夏丏尊对辩证逻辑运用的真正要求。193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文章讲话》一书,该书由夏丏尊在《中学生》杂志《文章偶话》栏目中发表的文章汇编而成。夏丏尊在此书开篇《句读和段落》一文中,对逻辑学在阅读和写作中的运用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服务于情境,以修辞制约逻辑,以理解和表达为旨归。句读和段落是逻辑思维外化的形式标记,二者具有增强“意味”的修辞作用,因此句读的使用、段落的出现本应遵守逻辑的规范、体现逻辑的要求。但是,夏丏尊认为,根据修辞效果的需要,句读和分段不妨打破“论理上的规矩”,“变化活用”。对于句读,夏丏尊首先从阅读的角度出发,以朱自清《背影》的首句“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为例,通过四种不同的句读方式,辨析各种表达方式所体现的“文章的意味”;进而从写作的角度出发,强调句读法“要合乎情境”,“写作的时候不妨依照自己的意思情感的重点决定文章的句读”[17]。对于段落,夏丏尊认为,分段的规则“可有种种的变化,有些时候,由于分段的不同,文章的意味和情调也会不同”。他以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为例,打破此文在《归震川集》中无段落划分的状态,并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分段方式加以比较,分析其表达效果的不同。夏丏尊主张将“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独立成段,虽然在论理上没有必要,但却使文章更具情味。在文章的实际阅读和写作过程中,夏丏尊主张将修辞的需要与逻辑规则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强调理解和表达“要依据两个条件:一是文法的、论理的法则;二是作者心情的自然流露。有时应注重前者,有时应注重后者”[17]。不可因逻辑而废文辞的要求,就是要以文章的实际情况突破逻辑定式的束缚,从而赋予逻辑知识在语文中运用的灵活性。夏丏尊将包含有读者的接受和作者的切身感受两方面的“情境”与逻辑同列,共同作为句读和段落的最终标准,是对语文规律深刻的认识和尊重。
四、结语
夏丏尊建构现代语文知识体系时,通过对形式逻辑、辩证逻辑的引入,在语文教学中融入了逻辑知识,尤其为作文教学中议论文体的教学提供了有效的文章写作策略方法,同时,更为现代逻辑学知识进入普通中等教育课程,寻找到了可以寄寓的恰当的领域。夏丏尊将现代逻辑学作为探讨议论文体的基石,建构了以逻辑学为纲的议论文知识体系,不仅借助作文教学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加以训练,而且通过逻辑知识的渗透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水平。同时,夏丏尊还根据客观的写作实际,以文章的情境来限制逻辑学在语文知识中的参与度,提出了以情境为旨归的逻辑知识运用标准。
作者:刘正伟 王荣辰 单位:浙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