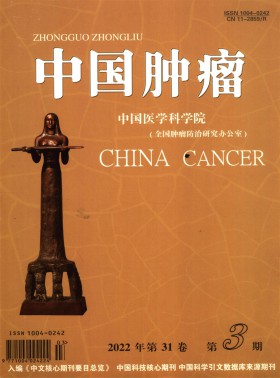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中国古代艺术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范文1
【摘 要 题】古代文论研究
【 正 文】
“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具有原创意义,它既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本质规定,又是这本质规定的由来。
一、体验的世界与世界的本真
中国古人的世界建立在情感体验的基础上,情感体验的世界是“天人合一”的世界。中国古代艺术在这样的世界中形成与发展。
1.“情”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原创性
从艺术文化学的角度说,文学艺术从属于文化并规定于文化,因此,阐释“情”的文化原创性,同时也就是在揭示“情”的文学艺术的原创意义。
原创的含义不仅在于本质规定,更在于本质生成。把“情”提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原创位置,是指认中国古代文化的缘“情”而生与缘“情”而立。
缘“情”而生,是说中国古代文化是其先民及后来者情感生活的产物。这涉及生存论及文化学的基本问题,即中国古人的生存就是情感体验的生存,中国古代文化也就是情感体验型文化。
把中国古代文化指认为以情感体验为特征的文化,这可以说是百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化学研究与生存论研究在不少学者中日渐取得共识的一个基本观点。如中国现代较早的文化反思者之一梁漱溟,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体验,提出中国传统生活与传统文化的重心在于“家”,在于“家”所特有的情感关系,由“家”的情感关系扩延至社会,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生活中喜欢斟酌情理情面”的生存特性(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金元浦、谭好哲、陆学明主编《中国文化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148页。)。他这是在为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情感的寻根,并把这根确定在“家”的血缘情感上。林语堂在分析中国文化精神时,对比中国与英国民族文化的异同,也得出结论说:“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此刻所要指明者,只是说中国文化,本是以人情为前提的文化,并没有难懂之处。”(注: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引自《中国文化概论》,第195页。)林语堂所说的“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便是难以言说的直觉体验,这正是中国古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以人情为前提”,便是体验的文化特征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有研究的当代学者张岱年,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四个要点,即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及天人协调。细究他这四个要点,会发现这些要点的形成,就社会文化心理而言,具出于重行为目的、重行为反馈、重行为体验的实践理性,直觉体验及情感体验是其基本理性特色。李泽厚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提出一个“乐感文化”的命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应概括为“乐感文化”,以此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应。他对此概括说:“这种智慧表现在思维模式和智力结构上,更重视整体性的模糊的直观把握、领悟和体验,而不重分析型的知识逻辑的清晰。总起来说,这种智慧是审美型的。”(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页。)李泽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乐感”型、审美型的概括,正是突出了这一文化的情感体验的本性。我在《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一书中,曾专题分析过这个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的本体特征概括为情感体验特征,并分别对之进行了文化特质的、文化思维的、文化哲学的及艺术论的思考(注:拙著《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2.“情”的本真规定
先考察一下“情”的字义。“情”,《说文》:“人之阴气,有欲者。”按阴阳说,阴阳为生命之本并化生人的万有万能,说“情”为阴气,这是将“情”推到了生化生命的本真之处。段玉裁注,情乃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是生理自然需要不学而能,这又是将“情”归入人的本真状态。《吕氏春秋》强调“情”的天生自然:“欲有情,情有节……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吕氏春秋·》)这是在确定“情”的生命自然即直接的感官根据,是耳、目、口对声、色、味的自然欲求。“情”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然又是这生命活动的本真。《尚书》“情”有一见:“天畏fěi@①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孔安国《尚书传》对这一“情”字作“人情”解,即民群的真实感情,“人情”被看作天是否辅助的尺度。此后,“情”便与事物之真、实相关,与人的自然本性相关。“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左传》庄公十年);“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鲁有名而无情”(《左传》哀公八年);“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国语·鲁语上》)。这“情”,都是事物、事情的真实情况。《论语》用“情”两处,都与人的自然本真相关:“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
因为“情”本义于生命本真状况,所以它常与另一个表生命之本真的字“性”连用,称为“性情”。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荀子·正名》)这“天”便是自然,自然天赋。荀子提出“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情”是自然天赋的本质,是生命的本真。荀子之后,“性”、“情”、“欲”三者关系的哲学之思也就逐渐多起来,形成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之辩——“性情”之辩。
中国古人热衷于各种社会现象的本真追问,把本真作为文化建构、艺术实践的基点或出发点,并在本真追问中把握判断事物及行为的标准。如儒家先哲孔子与孟子,在推衍他们的人世之道与道德之天时,便从本质设定出发。“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羞耻感在这里被推为不言面喻的本真标准;“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情”被指定为“性”本善的根据;“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这是孟子对羞耻感的进一步的本真强调。管子本于“情”的人事道德推衍更为直接,“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管子·禁藏》);“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管子·君臣上》)。道家进行的道德推衍其实也本于“情”,与儒家对“情”的人世社会比附与推入不同的是,道家本于“情”却比附于“自然”,再由“自然”而推入社会人生;当然,道家对于“情”的本真设定或本真理解也不同于儒家,道家更强调“情”的自然性。“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无情不是否定“情”而是不动情,这里有一种超越喜怒哀乐的更为广博深厚的“情”,这便是宇宙人生之自然,是融于宇宙大道的生命冲动。至于墨家的“君子进不败其志,内究其情”(《墨子·亲士》);法家的“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韩非子·难三》)等,也都可以看出他们按照各自的“情”的本真理解,进行各自的“情”的本真推衍与强调。
二、建构体验世界的心灵方式
在中国古代,本真之“情”涌发本真之欲,本真之欲又实现于本真的血缘亲情关系。血缘亲情关系是“情”的本真关系。由此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便也可以说是充分社会化的血缘亲情关系的意识形态。而建构、接受、运用这样的意识形态,又必须有与之相应的思维形态或思维方式,这思维形态或思维方式必然也是血缘亲情关系型的。所谓思维形态的血缘亲情关系型,即它与血缘亲情关系共同发生与发展起来,它以血缘亲情关系为思维对象,在对血缘亲情关系的思维中不断完善这一思维结构,并思维地解决社会化的血缘亲情关系的各种问题。对这一思维形态或思维方式,我在《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一书中,曾将之概括为情感关系思维或情感思维,这种思维的特点是:①客观的感情依据;②思维主体现实体验向感性对象的融入;③过去经验对于现实感性对象的渗入;④表诸于形象或含有形象因素的一般判断形式(注:拙著《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学阐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在这样的思维形态中,“情”有了本真之外又一重原创意蕴,即它是中国古人建构与把握世界的心灵方式。经由这样的思维形态,中国古人日常社会文化生活活动与艺术活动有直接的关联——社会文化活动直接关系着艺术活动,艺术活动也直接关联着日常社会文化活动,甚至不少时候,社会文化活动就是艺术活动。
且看《吕氏春秋》这段话:
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于音乐以论其教。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叹,有进乎音者矣。大飨之礼,上玄尊而俎生鱼,大羹不和,有进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吕氏春秋·适音》)
由音乐而民俗民风,由民俗民风而理义之行、国家之治。对这段文字的解读,不仅要注意它指出了艺术与人伦政治的关系,更要注意它对于艺术与人伦政治的情感关系的揭示,它们面对同一的情感关系,把握同一的人伦情感世界,所以它们才能由此及彼地互相指认互相通达。艺术与人伦世界的同一关系,在孔子论诗、庄子寓言、韩柳论文中都被作为通则而运用,这不是他们对于艺术的误解与偏见,而恰恰是他们对艺术与现实生活情感思维同一性的深悟。
对“情”的思维形态意义,中国古人多有论述。如《淮南子》,从“情”感物而生并形于外的方面加以揭示:“情系于中,行形于外,凡行戴情,虽过无怨;不戴其情,虽忠来恶。”(《淮南子·缪称训》)汉代从石渠阁奏议到白虎观奏议,涉及“情”的思维规定性,并以此作为制定国家等级制度的根据:“情性者何谓也?性者阳之施,情者阴之化也。人禀阴阳气而生,故内怀五性六情。情者静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故《钩命诀》曰:‘情生于阴,欲以时念也;性生于阳,以理也。阳气者仁,阴气者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白虎通德论·情性》)这指出情是阴化、静也、贪也、利欲也;性为阳施、生也、理也、仁也,二者在生存的心灵活动中各有所重,各有其活动特点,又相辅相成地展开心灵活动的过程。东汉王充基于情性阴阳之说,指出要更好地运“性”用“情”,就必须注意对之制约与调节:“故厚情性之极,礼为之防,乐为之节。性有卑谦辞让,故制礼以适其宜;情有好恶喜怒哀乐,故作乐以通其敬;礼所以制,乐所以作者,情与性也。”(《论衡·本性》)这实际上是揭示了礼乐乃“性”、“情”思维的结果,因此礼乐才能反转来制约与调节性情。刘勰基于“情”的过程性理解,进一步作了“情”的艺术思维的揭示:“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这指出“情”组织文学语言,使之由隐而显的表现功能。“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这是揭示“情”的文学发生过程。“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文心雕龙·神思》),这是在讲“情”与艺术想象的关系。
体验情感型思维形态关注现实与历史的各种情感关系,包括人与人的情感关系,人与社会的情感关系,人与自然的情感关系;长于对这类情感关系进行丰富复杂的情感体验,并以真切细腻地表现这类情感体验为思维目的。这一思维的艺术成果便是创造出生动地表现各种情感关系与情感体验的艺术形式。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在进行中国古代美学与西方古代美学的对比时,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尽管古希腊美学也并不否认艺术对人的情感的影响和作用,但从整体上看,它更为强调的毕竟是艺术对现实的再现的认识作用。而中国美学所强调的则首先是艺术的情感方面,它总是从情感的表现和感染作用去说明艺术的起源和本质。这种不同,也分明地表现在东西方艺术的发展上。”(注: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
由此可见,“情”确实是中国古人情感关系地建构与把握世界(包括艺术世界)的思维形态与心灵方式。
三、创生艺术的母体
强烈的抒情要求形成中国古代艺术不同于西方的明显差异。突出的抒情特征的形成,则源于中国古代文艺史中抒情艺术的早熟及对于各种文艺形式的创生。
中国古代最早形成自觉并走向成熟的艺术是音乐,音乐的抒情本质早已不言而喻。
固然,不仅中国,在世界艺术史中,音乐也是出现最早的艺术,这已被很多学者认同。不过,最早出现的艺术与最早形成自觉并走向成熟的艺术并不是一回事。
《周礼》有一段话,证明至少在周初,音乐的创作与应用便已进入自觉阶段:“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谕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磐、大夏、大@②、大武……”。(《周礼·春官·宗伯》)尽管有资料证明,“礼”的观念周初已开始形成,但“礼”在当时生活中的作用却无法与“乐”相比。“乐”所感受并表现的秩序与和谐进一步理性化,才明确为“礼”。“礼”是规定了的秩序与和谐。对此,中国古人早有认识——“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礼记·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记·乐记》)“乐”先于“礼”又通于“礼”,“乐”、“礼”共同规定与生发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乐”、“礼”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情感体验与情感理性形态,滋润与繁荣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抒情特征。
而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早熟,也证明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情”的根基。
中国古诗“情”的根基与“乐”相通,中国古代文艺史不乏诗乐舞原本一体的记载。如刘勰说:“或葛天乐辞,玄鸟在曲;黄帝《云门》,理不空弦”(《文心雕龙·明诗》),孔颖达说:“大庭有鼓之器,黄帝有《云门》之乐,至周尚有《云门》,明昔音声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诗也。”(《诗谱序正义》)诗生于歌舞,亦即诗生于“情”。
“乐”与“诗”这类抒情艺术在中国古代率先自觉并成熟,在于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化根基——人伦情感的艺术形态,它们表现出的艺术感召力和普通有效的接受效果,使统治者与施教者把它们用作人伦教育的得力手段。中国古代抒情艺术率先发展与自觉,是人伦文化建构的必然。这个过程中,孔子以“乐教”、“诗教”为核心的艺术观同时也是文化观,起了重要的理性指导作用。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对此作过分析,透视了其中血缘亲情的文化根基(注: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很有说服力。
总之,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根基于中国古代人伦文化,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伦情感本质就自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本质;由于“乐”、“诗”抒发人伦情感方面很早便自觉与成熟,也由于孔子的理性概括与引导,使的“乐”、“诗”的“情”的本质规定成为后来因“乐”、“诗”而生发的其他门类的文学艺术也获得了“情”的本质规定。
四、文论诸范畴的总领
文论是文学实践的理论形态。“情”的文学艺术的原创意义体现在文论中,则在于它具有范畴总领意义。也可以说,“情”的文论诸范畴的总领意义,正证明它的文艺原创性。
“情”的范畴总领意义可以从思维形态、文论范畴发生及范畴构成角度加以论证。
①中国古代文论诸范畴都是情感体验思维的产物。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生成物,分有情感关系的本体属性并运用与发展着情感体验型思维。所不同的是,文化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创生与建构,由于社会实践的物质规定性,情感体验型思维常因实践对象的客观定性而难以充分施展;即是说,对象的客观性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它否定体验的主观性。这时,活跃的便只能是主体的认知而非主体的情感。在文学中,对象的客观定性消融于文学创作主体,情感体验的特征性思维有了充分实现的条件。充分实现的情感体验思维,创造着情感体验的中国古代文学,也形成与之相应的文论范畴。由此说,中国古代文论诸范畴也是情感体验型思维的产物,是这一思维形态的理性成果。“情”在情感体验型思维中具有发生、运作、课题与衡定意义,“情”的生理与心理规定直接成为思维规定。作为范畴的“情”正以文艺的情感活动为对象,以揭示情感活动规律为旨归,因此,“情”范畴的研究也是情感体验型思维本身的研究。文论其他范畴孕生于情感体验型思维,所以也正在“情”范畴的研究之中。换句话说,“情”的情感体验型思维研究自然蕴含着文论其他范畴的研究,而且在文论其他范畴的研究中处处见出“情”的规定。
就拿“理”来说,在西方,“理”与“情”是对举的两个范畴,它们经常在二元对立的情况下运用。在中国古代文论,“理”却是“情”的构成范畴,“理”主要是揭示“情”的发生、运作及表现根据。如刘勰所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体性》),叶燮所说“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耶”(《原诗·内篇》)等,都是在讲“情”、“理”相一的关系。李泽厚则把这种“情”、“理”相一相融的关系概括为“中国的传统精神”,“中国的智慧”(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311页。)。
②中国古代文论诸范畴都是“情”的生发
如前所述,最充分地体现“情”的本体意义的艺术是乐与诗,乐与诗的最先自觉与成熟,决定了它的理性形态“情”范畴是最早提出的艺术论与文论范畴之一。
《国语》记载周王与单穆公、伶州鸠关于声乐与声乐接受效果的对话,虽没有直接就“情”字展开,但二人由声乐大小、强弱、疾缓作用于感官引起的体验与感受的分析,及对这种微妙、复杂的体验与感受所唤起的道德感与所引起的道德行为的分析,都已深刻涉及情感心理学内蕴,都能从中看到较丰富的情感唤起与情感运用的经验(《周语下》)。《国语》还有一段“情”与“文”的对话,涉及“情”、“貌”、“言”的关系:“阳处父如卫,反,过宁,舍于逆旅宁赢氏。……(宁赢氏)曰:‘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国语·晋语五》)这段记述提出了“情”与其外部表现相合相离的问题,也涉及“情”的话语表述问题。这类问题对此后的“情形”、“情言”、“情貌”、“情理”等艺术论与文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开启作用。此后文论众多范畴课题的提出与展开,如“诗言志”课题、“性情”课题、“形神”课题、“神思”课题、“比兴”课题、“象”与“象外之象”课题、“旨味”课题、“虚实”课题、“言意”课题、“意境”课题等,无不与“情”的文学发生意义、“情”的范畴延展意义密切相关。
“情”对于“志”、“礼”、“性”、“心”、“德”、“神”这类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的基本范畴的发生意义,更可以由孔子及其后学对于《诗》的多元解释见出。对艺术深有造诣的孔子,对《诗》却经常作非“诗”的解释,这类解释看似出格,其实,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以情感体验思维为特征的,文化系统的众多方面、众多范围都与“情”相通,可以互相生发彼此转化,就会少一些大惊小怪,这类解释只是顺“情”成章。如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致,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治《齐诗》的匡衡总论《风》诗时说:“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汉书》卷八十一《匡衡传》)这都是在强调艺术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情感同一性,艺术与各种社会活动都是“情”的生发。这一点在《毛诗》序中说得更为清楚也更为具体。如《召南·草虫》序,说这是“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郑风·将仲子》序则说是“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小不忍以致大乱焉。”这类读解,不管距当时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是近是远,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孔子以降,确有很多哲人与文论家悟及“情”在生活中在文学与文论中具有重要的发生意义。
③“情”对文论诸范畴的构成
“情”对文论诸范畴的构成,是指文论诸范畴都合于“情”的定性,都分有“情”的性质。由于文论范畴为数众多,无法逐一分析,这里只能举诸范围之要,择几个基本范畴,进行“情”的构成性阐释。
a.“意”与“情”
“意”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范畴,它是文学创作的所欲表达,文学作品的已然表达,文学接受的理应获取。
“意”的提出与运用由来已久。《易传·系辞》中有“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此说法后来广为引用,它不仅提出了言、意、象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意”不可尽言的属性。《庄子,天道》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外物》又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些说法都认为“意”是有一定认知内容的心理活动,它要经由语言而表述,但语言又无法对“意”充分地表述。
陆机大概是最先在文论中运用“意”范畴的,他的《文赋》可以说就是为了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问题而作。此后,范晔的“情志所托,以意为主”(《狱中与诸诸甥侄书》);杜牧的“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答庄元书》);邵雍的“炼辞得奇句,炼意得余味”(《论诗吟》);刘熙载的“意在笔先”(《艺概·文概》)等,都非常强调“意”之于文学的重要性,但也都认为虽则“意”之于诗文绝对不可或缺,但诗文又难于尽“意”。“意”的无可尽言,是中国古代文论对于“意”范畴的普遍看法。
那么,“意”为何物?为什么它如此重要却又言说不尽或言说不清?对这个问题,范晔的一段话说得很精当:“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可类工巧图绩,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狱中与诸甥侄书》)从这段话可以看到,范晔从“意”的心理发生角度体悟到,“意”乃“情”与“志”的统一,是创作主体有感于生活而形成的“情志所托”的体验,这类“情志所托”的体验酿成具体的文学创作之“意”,这“意”便是具体化了的“情”、“志”融合的心理活动。“文”不能尽“意”,在于构成“意”的“情”的活动变化极为微妙,“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狱中与诸甥侄书》)对“意”的“情志所托”的心理发生过程,范晔之前的陆机曾进行形象地描述,揭示了“意”发生的感官依据,在“意”的发生中有“志”的萌动,有“史”的感悟与“文”的陶冶,而这一切又都涌荡“情”的波流,这才“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文赋》)。
正是情感体验的浑然而动和微妙之动,正因为“情”包融着感性、心志、既往的文史修养与现实的情境激发,这一切都难于为语言所分解所确定地指认,这就决定了“情志所托”的“意”的非尽言性——“意”的非尽言性来于“情”的构成。
b.“风骨”与“情”
“风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高标准追求,也是很高层次上被运用的鉴赏与批评标准。
“风骨”的不易求,一个重要原因是“风骨”意蕴的不易把握。这种不易把握与“风骨”追求所必然伴随的“情”的活动分不开。“情”一经融入,大量无可言说的东西便活跃起来,更何况“风骨”本身就是一种情感体验,就是一种情感体验效果。与构成抒情作品内容的情感不同,“风骨”的情感体验是对于作品的情感体验内容所进行的表现的体验。
因为“风骨”是对一定内容的表现情况的体验,所以有“风骨”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范畴(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风骨》、寇效信:《论风骨》、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都持“风骨”乃内容与形式的说法。);也有学者注意到“风骨”的情感体验性质,把“风骨”理解为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注:张海明:《经与纬的交结》,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265页。),并将之纳入道德规范。
宗白华曾深入地研究“风骨”,他的看法被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论者所引证。这里且把宗白华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摘引如下:“我认为‘骨’和词是有关系的。但词是有概念内容的。词清楚了,它所表现的现实形象或对于形象的思想也清楚了。‘结言端直’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辩。这种正确的表达,就产生了文骨。但光有‘骨’还不够,还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所以‘骨’之外还要有‘风’。‘风’可以动人,‘风’是从情感中来的。中国古典美学既重视思想——表现为‘骨’,又重视情感——表现为‘风’。”(注: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9页。)这段话确实指出了“风”从情感中来,“骨”从思想中来这一层意思,但从什么中来并不意味着这来者就是什么。说“他从家中来”,这来者是他而不是家。这是简单的类比。“‘风’从情感中来”,“风”未必就是情感或情感倾向。“骨”也是一样。
那么“风”、“骨”是什么?还是前面那句话,“风”、“骨”是对于情感体验内容所进行的表现的情感体验。所表现的情感体验内容自然含有一定的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自然也有一定的道德规范在其中,但宗白华并未止于此,他强调的是如何表现这一定的情感倾向与思想倾向。他分析刘勰的“结言端直”,说这“就是一句话要明白正确,不是歪曲,不是诡辨”;他说“必须从逻辑性走到艺术性,才能感动人”,毫无疑问,这都不是说表现什么而是说如何表现,是就表现特点与表现效果而言。
从中国古人长于进行的类比思维来说,他们总习惯于把某种言说不清的属性、功能、效果等通过形象比喻加以述说。这种类比思维的要点在于被述说的东西与用来述说的东西,必在比与被比的基本点上能唤起认知与体验的一致性。“风”取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它的最基本的特征性类比,当是自然流动,无所阻碍。“骨”取于人或动物的机体之骨,它的最基本的特征性类比,当是坚实鲜明,刚正硬朗。不管对“风骨”的具体内容做出多少解释,都应该就类比的基本特征展开。刘勰“风骨”论的意蕴正是在如是的特征性中展开的,“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情与气偕,辞共体并,文明以健,guī@③璋乃骋。蔚彼风力,严此骨鲠。才锋峻立,符采克炳”(《文心雕龙·风骨》)。这些类比的精言妙语,确乎有些扑朔迷离,但根据类比思维的一般规律,抓住基本的类比特征,仔细地思索与体验进去,则不难发现,“风”者确实讲的是情感抒发所达到的自然流动、无所阻碍的表现境界;“骨”者确实讲的是思想阐发所求得的坚定鲜明、刚正硬朗的表述效果。不过,无论情感抒发达到的表现境界也好,思想阐发求得的表述效果也好,都是共见于表现的;而且,对这种表现境界或者效果的追求与接受,又都依凭于情感体验。
既然如此,既然“风骨”是以其表现性而见于情感体验的范畴,“情”对这一范畴的构成性,当毋庸赘言。
④“味”与“情”
“味”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是一个广泛使用的范畴。这一范畴的文论意义存于文学文本与读者的接受关系中,是在这接受关系中读者对文本所形成的读解感受。对这样的读解感受,出于类比思维,中国古人觉得这就像嗅到或尝到的令人陶然的美味,“味”便于读解感受联系起来,成为这类感受的指代,“味”也便逐渐被用做文学与文论的接受范畴。
最早取譬于“味”者,大概是《左传》载晏子论“和与同异”(《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以“味”喻一种特殊的音乐接受效果,即“声乐如味”。这种接受效果来于音调与节律的相成与相济,亦即和谐,产生的直接接受效果是平心,进一步的效果便是和德,即协调人伦之序。由这段最早的取譬于“味”的文字,起码能找出“味”的三点规定:“味”生于“声”与“听”的相互作用中;“声”被“听”而得“味”,又并非所有的“声”都能有“味”,有“味”之声必是音调节律相成相济之“声”,这是被接受的艺术一方的规定;“味”的接受效果,是接受主体的平心和德。再进一步分析,合于这三点规定而成“味”,就在于被“味”者能唤起一定的情感体验。为什么把这接受的规定确定于一定的情感体验?可以拿出三点根据:首先,音乐作为特殊的艺术门类,就是情感体验的艺术,它无法表述更多的认知内容,它是通过声音变化唤起情感体验,所以,产生“味”的这种“声”与“听”的相互关系就是一定的情感体验关系;其次,“声”被“听”而得“味”,这能“听”出“味”的“声”其实就是能唤起某种情感体验的“声”,“声”的唤情作用,不同“声”的不同唤情效果,当下心理学已进行了很细致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声音唤起情感的生理根据;再次,“味”的接受效果,即平心和德,也是情感体验的效果,根据情感心理学,和谐音乐的接受,可以平和焦虑、放松紧张,主体可由此进入安适宁静的心境,这正是情感效果。可见,“味”的最初提出,便是意指情感体验的接受过程与接受效果。
此后“味”被引入文学与文论,它的情感体验性质也就一并被引入。文论中经典的“味”论者有三人,即刘勰、钟嵘、司空图。此三人谈“味”都不离开情感体验,也可以说,对他们的“味”论都应作“情”的理解。
如刘勰说:“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文心雕龙·物色》)“入兴贵闲”,“析辞尚简”,讲的就是由“文”而“味”的唤情规定。钟嵘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这里的“兴”、“比”、“赋”不仅被视为作诗的基本手法,这同时也是手法对于相应内容的要求与规定。“兴”与“比”表现“意”与“志”,“意”与“志”都是一定的情感体验,这情感体验生发于“物”,“物”又靠“赋”而入诗,所以诗的“比”、“兴”离不开“赋”。作诗的关键就是协调“兴”、“比”、“赋”三种手法,即所谓“宏斯三义,酌而用之”。这样,“味”的接受效果就可以求得,即使“味之者无极”。可见,钟嵘的“味”同样是情感体验的接受效果。
司空图谈“味”更恍惚一些:“文之难,而诗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tíng@④蓄、温雅,皆在其间矣。……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矣。”(《与李生论诗书》)在司空图看来,“味”是一种难于指陈的接受效果,“味”具有超象超知的接受性。超象超知又有所接受,司空图便把“味”更充分地交付给情感体验,因为从心理接受根据而言,惟有情感体验才能超象超知甚至超验地接受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微妙信息。对此,国外的格式塔学派、瓦尔堡学派及现象学心理学派已多有揭示。司空图当然未达到这些当代心理学的专门程度,但司空图凭丰富的艺术经验对此却有所感悟。至于司空图此段文字所提出的单一之“味”与调和之“味”的差异,对调和之“味”作的“醇美”及“味外之旨”的赞美,则是对“味”的情感接受关系及情感体验进行了更细微的区分,提出了更高的情感体验要求。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非下加木
@②原字为艹加(氵加隼去十加又)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范文2
但从整体上看,宋代山水画在差异中又有统一,在个性中又见共性,他们代表了宋代山水画的艺术风格。
北宋是以中原画派和院体山水画为主流,在艺术语言上,北宋山水画经常采用全景式构图,或山峦重迭,或树木繁杂,或者境地宽远、视野开阔,或铺天盖地、丰满错综,或一望无际。笔墨繁而含蓄,爽利而凝重。这种基本塞满画面的、客观的全景整体性描绘自然,使北宋山水画富有深厚的内容感,给予我们以丰满而不确定的感受。[1]
宗白华先生在《论中国意境之诞生》一文中指出:“意境”是化实景为虚景,是艺术形象或情景中呈现出的情景交融,能够蕴含和昭示深刻的人生哲理及宇宙意识的至高境界,它是主体情感与客观形象的有机统一。“意”,侧重于艺术家情志、理想的主观创造,心与物、情与理的结合;“境”,则侧重于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是形与神的统一。[2]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是宋代山画中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标准,既是创作原则,也是鉴赏原则。
一、心物统一,情景交融
心与物的统一。“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表现为审美主体,也就是人;“物”是审美的对象,是客体。石涛在《画语录》中主张心与物的高度统一,这里的统一就是“神遇迹化”。他说:“山川脱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是而迹化也,所以归于涤也”。 [3]所谓“山川与予神是而迹化也”指的就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相融合的产物,是情与景、意与境的有机统一,也就是情思与景物的统一。宋代山水画所描绘的景物、事物是情感的载体,因而是情感化的景物、事物,这就是“化景物为情思”。同时,艺术家在表达感情时,又必须渗透、融化于景物和事物之中,也就是“化情思为景物”。意境就是“化景物为情思”和“化情思为景物”二者的有机统一。因此,宋代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与郭熙的《林泉高致》这两幅山水作品所呈现的意境,正是心物统一、情景交融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体现。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一幅宋代山水画的优秀典范,此画给人以山势逼人之感,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一是构图,主峰巍峨浩大,面积占画面的三分之二,而逼近画幅顶端,构图给人以威压的感觉,下部以三堆巨石作底层,承受主峰的重量,形成上下部位的紧张关系,但是画家巧妙的运用水平线上的白色云烟和S形的溪水,又使画面形成了空间和疏朗气氛。一行山间行旅者把观者的视线引向画面外边,从树背面隐约显现的楼阁,有意安排在极右的一侧,构成行旅者向左行进的开阔前景,使画下方形成律动感。二是用笔用墨,范宽用墨之法近似江南画风,用墨皴与雨点皴结合表现主峰的体积与重量感,苍莽雄浑的气势。
北宋的山水画主要是沿袭五代以荆、关为代表的北方画派,着重塑造黄河两岸关洛一带的山水形象。作品主要借助山、石、云、树木等景象来反映画家的审美情趣。因此,当我们在欣赏北宋时期的山水画时,可以感受到画家们借助各种景物的完美融合来抒发自己内心的审美情趣和山水画的意境。如宋代郭熙的《林泉高致》中强调了描绘自然山水时,不是只绘制一山一水,而是通过山水景物的出神入化在环境中的各种关系显现出来。一方面,处于四时天气变化环境与近观远望不同景象关系中,山水本身也表现出不同的物象,“真山水之烟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画见起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则烟岚之景象正矣。真正的山水之风雨远望可得,而近者不能得明晦隐见之迹”。另一方面,要想表现出真山真水的生命活力来,也借助它周围的景物来相互映衬,也就是说,充满生机的意境是通过景物间的相互关系得到的。正所谓“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得亭榭为眉目,以鱼钓为精神。山无烟云,如春无花草。山无云则不秀,无水则不媚,无道路则不活,无林木则不生”,天地之骨也,骨贵坚深而不浅露。水者,天地之血也,血贵周流而不凝滞”等。[4]因此,这种事物之间的辨证关系正是中国古典美学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的体现。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许多艺术家隐居山林,追求自然情趣,在审美标准上提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大巧若拙、天趣大补”。 [5]因此,艺术不可能是单纯客体,也不可能是单纯主体,而应当是主客体的完美融合,主体的表现必须借助于客体,客体的再现必也表现主体,主体的表现必也反映着客体。二者的割裂,必使双方的表达受到损害,二者的结合则使二者相得益彰。
二、虚实相生,像外有像
“钟厚必哑,耳塞必聋,万苦不坏,其惟虚空”,钟和耳只有在“实”中保持适当的“虚”才能听其音,闻其声。[4]所谓实境,是指通过客观事物的形象的描绘而直接把信息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在宋代山水画
中主要指我们看得见的画面的外在形式;所谓虚境是指艺术作品借助实境的描绘间接地暗示象征而表现出来的形象。它不是直接由感官把握到的,而是必须通过想象才能感受到,有时并没有直接表露或者抒发艺术家的某种情感、思想,却通过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晰地表达了艺术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这种虚实相生的特征,给欣赏者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的余地,欣赏者可以在对对象的联想中进一步补充、丰富作品的整体意境。
“虚实对比”、“虚实相生”是老子提出的思想。虚与实是艺术辩证法中最重要的一对矛盾统一体,虚实对比、虚实相生,是我国传统文艺最常用的艺术手法。具有意境的文艺作品、艺术形象往往虚实结合,相互转化,以虚为实,以实为虚,构成一种虚虚实实,发人联想的艺术境界。
北宋画家郭熙说:“诗是无声画,画是有形诗。”诗中要有画境,画中要有诗境,可以说,不能给人以想象的诗与画不是好的诗与画。“好”体现的意境就是“虚”与“实”审美关系的统一。[4]“虚”与“实”这一审美关系的统一正是南宋山水画艺术意境的体现,因此,自从宋室南迁之后,虽然处于动乱之中,但是南宋的山水画弃置北宋的全景式的构图,而采用“一角半边”式的构图,所谓“一角半边”就是采用两对角远近对照的方法形成对角线构图,使画面的重心偏离正中,作品中山水往往偏于一边,开阔画面的空白,形成暗示的空间,画面出现的是颇有选择取舍地从某个角落、某个局部、某些对象的某一部分出发的着意经营,安排位置,苦心孤诣,在这些为有限的对象的细节忠实描绘里,表达出某种较为确定的诗趣、情调、思绪感受。同时,对称走向均衡,空间更具意义,以少胜多,以虚代实,以白当黑,以一当十,以简代繁等等,这样的构图使南宋山水画的意境美在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像被称为:“马一角”的马远的《踏歌图》构图虽然很小,但是空间感非常突出,画面大部分是空白或者远水平原,只一角有一点点画,给人们一种“虚实相生”的感觉,这与“意在言外”、“此时无声胜有声”一脉相通。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范文3
中国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的。20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考古学家不仅重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工制品作准确的地层比较、断代和器物类型的划分等研究,而且开始强调研究制造这些人工制品的人类的意识形态方面。正如俞伟超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所走过的历程的分析:“在考古学研究的总体中,第一步自然应先作好年代学的研究。谁都知道,在我们面前的一大堆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如果连早晚都分不清楚,任何史的研究都将无从下手。第二步似乎应该理清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要整理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谱系。但所有这一些,基本上还是直观性质的研究,主要还是说明人类的具体行动的。我想,第三步就应该透过那些最最具体的考古材料,进而探索人们的社会关系,乃至意识形态”[1](P.120)。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得了第一步和第二步重大成就的今天,第三步的探索工作,逐渐被考古学家提上了议事日程,古代艺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自然倍受关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为艺术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艺术考古学又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基础上的。艺术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的建立,在中国是相当晚近的事。20世纪初期,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东南大学(后称中央大学)开设关于艺术学的课程,首次把西方艺术学引入中国。但当时的艺术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从事艺术实践的人才。对艺术学的真正重视则要到80年代末,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应该建立“艺术学”的口号和在东南大学创建艺术学系的实践,已经为艺术学在中国的学科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受到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响应,建立艺术学系已成为综合性大学学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艺术字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艺术学框架的构建开始受到普遍关注,有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论着、论文陆续出版发表,艺术学研究在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开端。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史和古代艺术特征的交叉学科,在考古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之间达到共识,考古学家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艺术遗物和艺术遗迹出发,阐明了建立美术考古学的可能性;艺术理论家则从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历史和规律的需要出发,阐述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的必要性。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沦又是在艺术考古实践的不断丰富,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实践活动姗姗来迟。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形成,迄今不过七八十年,由于战乱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考古学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考古学的发展比较缓慢。1949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连外国人也不禁大发感叹:“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2](P.3)。这一时期,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依然是重建古代的物质文化史,即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特别强调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剩余财富的增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反作用。因此,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的研究,一直被冷落、被忽略。
从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的目光开始在重建物质文化史建构方面,转向与古代人类关系更为密切的精神文化创造,时代向考古学家发出了“在田野工作中要贯穿研究精神”、“应具备更广泛的知识修养”的召唤[3],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能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又能进行古代艺术品研究的考古工作者。艺术考古实践活动开始蓬勃兴起。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改变了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开始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汉唐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正是有了日渐深厚的艺术考古实践基础,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才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卷、美术卷使美术考古学先后占了一席之地。稍后出版的美术卷,对美术考古学有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包括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山东大学的刘风君先生所着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与雕塑艺术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泓先生编写的《美术考古半世纪》,是对美术考古学理论的初步探讨。
从目前中国艺术考古实践活动的现状和有关艺术考古学理论的不同观点来看,完整的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确立还有待于将来艺术理论的成熟和艺术考古实践取得的更大成就。然而,不可否认,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尤其是中国的艺术考古学,它既有各种不同质地、不同艺术形式、数量众多的考古艺术品可以研究,又拥有世所难匹的浩瀚的历史文献和传世的艺术品可供参考,两者交相辉映,使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简单地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 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以古代钱币为例,作为流通使用的方孔圆形的五铢钱和通宝钱,主要是用作在社会流通领域进行等价交换的媒介物,而专为辟邪、祝寿铸造的压胜钱或称“花钱”,却缺失了使用价值,突出了审美艺术价值。因此,从纷繁复杂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中划分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远远不能如此简单地量化。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范文4
【关键词】古代文学;情感;体验式思维;本真;原创
文学作品脱离不了关于“情”的描述,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又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点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脱离“情”字,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艺术也就没有了生命与灵魂;因此,分析古代文学艺术作品,必须习惯于从“情”字入手,解剖开了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情”的元素,也就能够充分把握住古代文学作品的脉搏所在了。
一、古代文学中“情”的要素具有原创意义
古人对世界的认知,以“天人合一”为主要特征,其情感体验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情感体验属于一种感性活动,这就决定了古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出来的“情”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学艺术本身是文化的子项目,其必然是从属于文化并受文化的制约的,因此,揭开了“情”在古代文化中的原创意义,也就自然揭开了“情”在古代文学中的原创意义;对于古代文学而言,其显著的特征就是缘情而生与缘情而立;对于古人而言,其生存的过程就是情感体验的过程,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可避免的成其为一种情感体验类型的文化,所谓“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便是对这种情感体验文化的直观描写,充分体现了难以言说的直觉体验的文化特征,这也构成我们古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正因为古人的情感来自于生活中直观的体验,因此,古代文学中关于情的内涵意义,首先就是一种原创性质的意义。
二、古代文学中“情”的要素具有本真规定
情是属于一种人性的本能,是不需要去特意学习而能具备的一种特质,表现为喜怒哀乐爱恶等等方便,这是一种本能生理需求,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的自然行为;因为情发端于生命的本真,所以情的状物又往往和另外一个用来表述生命存在特征的“性”连接起来使用,通称性情之谓;古人热衷于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探究,以追求其本真为目的,古人在建构文化和艺术实践方面,往往是从追求其本真的角度出发,并基于本真的标准来把握事物的发生发展的原理,评判行为的标准。因此,可以理解在古代文学中体现的“情”的要素,本身就是古人对事物本真的一种探索和尝试,所以可以这么说,古代文学中体现出来的“情”,符合本真的规定。
三、古代文学中的“情”具有原创意味
古人的思维形态中,其情发乎于本真,而本真出于血缘亲情,因此,古代文学中的情之一字,是具有原创特征的,其本质上是古人建构和把握世界的心灵方式;古人通过这种思维形态来关联日常社会文化生活活动与艺术活动,并使二者之间不存在于直接明显的界限和区别。古人的情感主要是一种体验型的情感思维模式,其关注点在于现实与历史的各种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的包含范围相当广泛,不但包括人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包含个体的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的情感关系,还涉及到社会的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情感关系,通过对这些情感关系的体验,并细腻真切的表述出这种情感体验,便构成情在古代文学中的体现。
四、古代文学中“情”是创生艺术的母体
中国古代艺术不同于西方艺术的明显差异,在于中国古代艺术中往往充满了强烈的抒情要求,这种早熟的抒情艺术,催生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各种形式的创造性涌现。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形式中最早出现的无疑是音乐,而音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抒情性;音乐不但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最早出现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其中国古代音乐的出现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并在这种自觉中走向成熟。音乐之外中国古代艺术中另一个很早就出现的艺术形式就是诗,而无论是音乐还是古诗,其都是以抒情为基础,并通过情与乐将诗与音乐有机结合,形成了璀璨的艺术隗宝。音乐与古诗通过情的粘合而为一体,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的人伦文化,这种人伦文化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本质。
五、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论以“情”为统领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范文5
考察中国古代致力于提升文人修养的美术教育,对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术课程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选择魏晋、宋元文人为主要考察对象,认为古代文人普遍学习的内容是书法和绘画(文人画)。其中,书法的历史更为悠久,其作用与意义尤其突出。书法的主要学习方法有师父的言传身教、临师经典以及以笔会的形式讨论、交流。
关键词:
文人;书法;文人画;美术教育
美术教育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专业发展的美术教育;二是作为素养提升的美术教育。文章对古代文人美术教育的考察,仅限定在致力于提升文人修养的美术教育范畴。首先,在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上,笔者追随这样的观点:任何历史人物或事件,只有将之还原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研究,才能称得上是历史学的研究。基于这样的观点,探究古代文人的美术教育,第一步必须了解古代文人所说的“美术”指的是什么,第二步则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了解古代文人对不同美术种类的态度和学习情况。
一、中国古代文人眼中的美术
对于古代文人眼中的美术,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在方法上也有多种选择,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古代文人对哪些事物给予了较高的审美评价;也可以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创作者的社会地位与身份等。德国学者雷德侯是一位态度严谨的中国美术研究者,他对中国美术的研究更为审慎,他的文章让中国学者读起来常常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慨。这位德国学者通过考察中国18世纪的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历代皇家、贵族的艺术收藏,置身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将中国古人的审美活动与其他功利活动相区别,解读“中国古人以什么为艺术”这一命题。雷德侯回答这一命题的角度与考察方式恰恰是笔者所需要的,笔者非常庆幸能及时看到他的相关论述。在对《古今图书集成》各部类进行梳理之后,雷德侯得出这样的结论:“18世纪中国的大百科全书内没有相应于现代艺术的概念。今日所称的中国艺术,在当时或列于价值较低的‘考工’‘神异’类,或划归地位较高的‘字学’‘艺术’类。书法居于最高的地位,是因为其与文献的联系,而绘画有着紧随其次的地位,是因为其与书法的联系:两种媒介最接近于艺术的现代定义。制造业的成品只有具备‘文献’价值,才能获得进入更高级别的资格,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即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证。”在考证了与美术现代定义相近的中国古代书法与绘画(文人画)的地位后,雷德侯又对中国古代帝王、贵族的艺术收藏进行了考察。这一工作帮助他进一步求证,书法与绘画(文人画)不仅与文献相关,而且在类书典籍中拥有一定的地位,同时受到上流社会的追捧。书法最早作为艺术品被收藏始于4世纪,紧随其后的是绘画作品,而绘画作品直到清代被人们收藏的主要是“具有长篇题跋的宗教画、水墨画、名家之作——简而言之,有文学意味的画作”,很明显,历史上作为艺术品收藏的绘画作品基本上就是人们常说的文人画。青铜器在这里再次被提及,排在绘画之后。不过,青铜器被纳入收藏品的时间是宋代,与前者相隔久远,而且明显与文人修身养性联系不够紧密,因而这里不作议论。书法和文人画是受古代文人推崇的两种美术形式,其中书法尤甚。这一结论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算不得新鲜,但雷德侯教授的严谨论证使之更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
二、书法和文人画在文人修养教化中的意义
这一部分要考察的内容是,古代文人以为的艺术——书法和文人画,在文人修养教化中的意义,主要选择了中国古代的三个时期:魏晋、唐、宋元。之所以选择这三个时期,是因为这三个时期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还是在中国传统美术发展的历程中,都具有十分独特的意义。魏晋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名士群体,穿越数千年的沧海桑田而光芒不减。我们能明晰地感受到魏晋之风对后世文人的影响,在那时建构的文人心态、核心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意趣,经历千年而不曾更改。中国美术在魏晋时期也呈现出多彩的面貌,独立的美术作品、专业画家、专门的画论都出现在这个时期,书法最早作为艺术品被人们收藏也是在这个时期。唐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美术发展的盛世。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形成了强有力的士大夫文人阶层。唐代之后,五代宋元艺术格外繁荣。文人画在宋元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产生了文同、苏轼、黄公望、倪瓒等一大批文人画家。文章探讨中国古代文人美术教育,希望通过论述更好地明晰美术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笔者相信这有助于开发出更优秀的课程,从而在学校美术课堂上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承。
作者:曾瑜 单位:湖南美术出版社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艺术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中国古典舞;身韵;美学
中图分类号:J7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174-0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人类自然生活中,人们欣赏美、表达美、追求美。什么是“美”?就像歌德所说:“美如自然一样,丰富多彩。”也就是说,对于美的说法众多,且各不相同。但是都没有说到美的“本质”和“内涵”。科学的含义应该说:美是世界上自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切事物“好”的总和。
舞蹈艺术是美的艺术,中国古典舞隶属于中国各类舞蹈艺术中,这一舞种最初起源于戏曲舞蹈,体系衍生于当代,最终在中国民族民间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提炼、整理、加工、创造,以及长期艺术实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具有典范意义和古典风格特色的舞蹈,中华的审美与美学智慧造就了中国古典舞的美学思想。
一、中国古典舞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古典舞是一个特指的概念,这里的“古典”并不是指“古代”,而是代表着“经典”,中国古代舞蹈艺术经过长期发展最终积累形成的一种具有典范性的表演艺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老一辈舞蹈艺术家们开始对中国古典舞蹈进行挖掘与恢复。戏曲舞蹈家欧阳予倩最早提出了“中国古典舞”这一概念,并得到舞界响应由此传开。
中国古典舞集百家之长,即向艺术美学中的各类艺术之长处学习,提高舞蹈艺术的水平和质量。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大花园中,舞蹈艺术向戏曲艺术学舞蹈,向武术学习“精”、“气”、“神”,学手法、眼法、身法、步发、韵律、劲头等,使舞蹈艺术有了飞速的提高。创建者结合中国戏曲、武术的美学理论,概括了中国古典舞的新理论。创建者总结了中国古典舞身韵的四大基本动作要素――“形、神、劲、律”,这四个字高度概括了身韵的全部内涵。形,外部一切动作,包含舞姿造型及其动作连接路线。神,即内在的意蕴,以神领形,起主导支配作用。劲,即处理舞蹈动作长短、轻重、强弱、缓急等特点的力。律,是指动作本身的运动规律。四大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经过劲、律达到形神兼备,内外统一。最终确定了“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力与形合”的美学规律。
二、中国古典舞的审美意蕴与内涵
中国古典舞有明显的两大美学意蕴:一、回旋、圆转的形势美;二、在舞蹈动作的内在心动中体现和谐与协调之美。
(一)“圆”的形势美。中国古典舞内在的韵律感与意蕴可以用一个“圆”字概括。其运动规律,身体及手臂的运动轨迹都遵循着三种圆形在运动(平圆、立圆与8字圆),这就是著名的“三圆运动”的理论。
中国古典舞通过外部看得见的“形”与路线的“圆”来展现形体的美,演化出形形的体态、千变万化的动作与动作的衔接。“形”作为古典舞之美的传达媒介是形象艺术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国古典舞之灵魂。这种“形”贯穿于中国古典舞的典型动作: 大小五花、穿手、云手、大刀花、风火轮、燕子穿林、青龙探爪等等。表现了古典舞者丰富的身法性和鲜明的风格性,极具生命力和艺术表现力。
古典舞“圆”的形势美主要表现为圆、游、变、幻之美,因此,中国古典舞又常以“行云流水”、“龙飞凤舞”、“曲回婉转”、“闪展腾挪”等形象化的词语加以描述与赞誉。中国古典舞身韵中有七大动作元素:“提、沉、冲、靠、含、腆、移”,这些动作的贯穿与运用形成了“逢冲必靠、欲左先右、逢开必合、欲前先后、欲纵必收、欲提先沉”的律韵之态势,派生出古典舞更丰富、更典型的“形”。
(二)内在的“心动”与意蕴美。舞蹈既可用来表现人们的情感,又能表现人们的思想。普列汉诺夫在谈到艺术的主要特点时曾说:“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又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的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
在中国古典舞中不仅用动作来表达情感,还可以运用演员的丰富的面部表情。在面部直接表现出快乐、悲伤、忧郁等情绪特点,通过夸张修饰过的表情来配合舞蹈动作。中国古典舞中男女的动作是不可混用的,拥有各自不同的体系,从风格上看,男性动作展现阳刚之美,而女性舞蹈动作多表现阴柔之美,反差极大。这就是中国舞蹈文化在舞蹈动作的内在“心动”中体现出一种和谐、协调的意蕴之美。
如今,中国古典舞这一舞种已被世界所认可,具有独立的舞蹈审美价值。中国古典舞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呈现的是状态,展示的是艺术,表达的是情感,蕴含的是文化。它所蕴含的美学意蕴对中国舞蹈文化有着很大的影响,有待我们每个舞蹈工作者更为深入的发掘与探究。
参考文献:
[1]金浩.论中国古典舞的当代审美取向[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5.
[2]刘克宁.试论中国古典舞身韵的韵律特征[N].文化艺术报,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