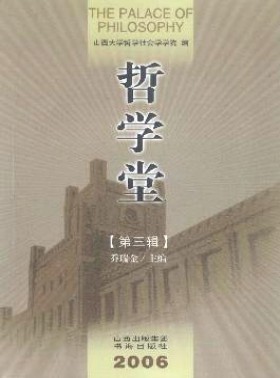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学堂赋创作与中国古代教育综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关于辟雍的形制规模,历来就争论颇多,从此赋的描绘,我们虽然无法确定它的具体形态,但“规矩圆方”一语,已透露出其形制模式在古代必然有着神秘的象征意义。东汉桓谭的解释:“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①显然有一定的合理性。赋文最后写辟雍内的活动:王公卿士、儒士诸生云集一堂,帝王祭天地、颁政令;举行射礼,参加庆功大典、接受四方使节朝觐,气势恢宏,场面浩大。此赋虽短,但描绘辟雍形制、规模与活动,生动形象,其浓烈的教化色彩,鲜明地体现出我国古代教育政教不分、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特点。
关于辟雍的政治教化功能,唐代王履贞的《辟雍赋》写得更全面:“辟雍之裁,"化之方。辟者象旋,圆而不极。雍者以流,转而有常。行于历代,创自前王。崇此乃理,废之斯亡。革鉩#浇,何莫由之。而克著化人成俗,靡不因兹而允臧。”追述辟雍得名之由,命名之意;再论其功用:行礼乐,宣教化,化民成俗,历代推行,决定天下兴亡。“公宫之南,灵台之下。赫巍$以层构,规制度于众寡。区别远采于虞庠,经始不差于周雅。”彰显辟雍在京师中的突显地位,规模宏大,合乎前规。“其学习以时,诗书兴教,惟司成是典,惟古则是效。诏夏弦春诵,俾民不覼。%三老五更,俾民知孝。惟胄也太子齿矣,惟学也元后视之。合语于此,释菜有时。以崇其道,以尊其师。俾百工允理,庶绩咸&。”论辟雍之功用,则在诗书兴教,形成重道尊师、养老兴孝的社会风习。又如赵郰翁的《辟雍赋》,论述学校兴起是为了“阐王化”、“宣人文”,以教化为目的;在形式上则有上下之别、东西之异;天子亲临辟雍视学观礼,国人围观,实施道德教化,体现出中国古代教育强烈的政治性和鲜明的等差性。
对辟雍的教育功用,元代杨宗瑞《辟雍赋》体现得较明显。其写辟雍陈设:“罗石鼓兮庭闱”、“九楹俨雅兮壁奎”。石鼓又称陈仓石鼓,康有为誉之为“中华第一古物”,石鼓上的“石鼓文”﹙大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风格独特,文字珍贵,历代都受重视。如宋徽宗时将其迁到忭京国学,并用金符字相嵌。元大德年间,石鼓又被移到国子学大成门内的石坛上,并置铁栅栏保护。元代罗曾、周伯温、李丙奎均作有《石鼓赋》。可以说,石鼓是中国文字与文化的见证。“壁奎”即“奎壁”,因协韵而置换,是奎宿与壁宿的并称,在古人认为此二宿主宰文运。东汉纬书《孝经援神契》中有“奎主文章”之说,东汉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划。”后来“奎星”遂渐被演化成天上文官之首,被当作主宰文运与文章兴衰之神,又建“奎星阁”,兴起崇祀之风。“奎”又作“魁”,科举时代,“魁星点斗”被认为是文运兴旺之兆。奎壁楹帖,说明辟雍教化已不限于政治,还与文章乃至文运相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官学与科举、与官员选拔密切相关。石鼓陈列,奎壁联辉,已尽显学校文雅气象。至于赋文所写“鼓钟颂其于乐,振铎宣其教辞”,“踀芹藻兮澄碧,俯菁莪兮中坻”,“澹文鱼兮游戏,肃威凤兮来仪”似乎应当是室内装饰的壁画,“鼓钟”、“振铎”都是古代颂乐宣教的工具;“芹藻”语出《鲁颂•泮水》,关于此诗,《毛诗序》曰:“颂僖公能修泮宫也。”泮宫即地方学宫。“菁莪”语出《小雅•菁菁者莪》,其序为:“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后因以“菁莪”指育材。《尚书•益稷》说:“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箫韶,尚书中指虞舜乐,又称《九韶》,先秦时期,被推为最美好的音乐。《论语•述而》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箫韶九成,也称圣主之盛德至极,因此产生瑞应,而瑞应就是“凤凰来仪”。可见此间装饰都与教育、教化相关,富有文教特点。赋文铺叙辟雍活动,讲经论史虽颇有政治色彩,但强调“集天下之英才,轨行艺于京国”,显然已侧重于规矩和统领艺坛的功效。
太学是中国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历代多有咏诵太学的赋作。如唐代周存的《观太学射堂赋》,元代赵'翁、干文传、王沂、欧阳玄都作《辟雍赋》,清代有沈德潜《临雍赋》、罗绕典《圣驾临雍讲学赋》、罗文俊《辟雍赋》等。纵观这些赋文,都带有强烈的政论色彩,在结构规模上,多以颂皇德、兴教化起篇,而后写辟雍的外在形制规模,再叙辟雍内陈设、活动礼仪等,在教化功能上,则主要突显辟雍的德育教化功能。
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学,又称乡学、学宫,始于西汉文翁在蜀郡设置学宫。汉武帝诏令天下郡国皆设学宫,至汉平帝元年﹙公元3年﹚始建立了地方官学制度。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乡曰庠,聚曰序,学校名称由此而来。写郡学的赋如唐代许荛佐的《五经阁赋》。五经阁是四明州郡学的藏书处,类似于现在的学校图书馆,从其名“五经阁”就已彰显出儒学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不有载籍,何以垂教?必由乎文字,使知乎忠孝。”赋文首先强调书籍对推行封建伦理的重要,然后论创建学校对邦国的意义,“命儒官兮,至公以居。所崇惟学,所宝惟书。搜群言而斯在,立重阁以藏诸”,肯定任命学官,创建五经阁对于收集和保存典籍、推行教育的重要性。至于“知忠孝”、“命儒官”,以及认为五经阁虽“陋于明堂”,但“饰不及侈,俭而中礼”,显示出儒家思想在教育评价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赋文所云“天禄”,指天禄阁,是汉宫存放文史典籍的地方,后亦通称皇家藏书之所。“校则同于天禄”,表明五经阁虽属郡学藏书阁却如同皇家书阁一样具有校理刊正图书的功能。秦始皇焚书,孔子第九代孙孔鲋不忍书毁,将《尚书》《礼》《论语》及《孝经》等经典偷偷地藏于墙壁内。孔鲋冒死藏书,但所收不过是一家一己之书。“藏乃异于鲁壁”这一颇富感情色彩的典故说明了学校藏书合法且非常丰富。官学制度发展到唐代已相当完备,除儒学外,算学、律学、书学、医学以及天文历法、兽医等专业教育也开始确立。因此,不难理解学校藏书所表现出的广收博蓄的特征。“睹兹阁之?(,谅吾道之宏益”再次表现出对儒家教化推行的颂美情怀。郡学赋还有明代陆綰的《嘉禾郡学赋》①。叙写郡学七百年历史及衰败颓坏景象,赞誉郡候修复之功:“谓政化之所施以学校为之首”、“因子来于庶民,匪画殚税于百姓”,强调学校对于教化的重要意义,并颂美修建学校野外采材,不收税于百姓,是仁爱庶民之举。铺写新郡学之雄伟外观和内部华美陈设,通过主客对郡学土木奢靡与教化之本的辩论,得出内外合一、本末非异和重视德行的教育观。#p#分页标题#e#
县学赋如明汤显祖《浮梁县新作讲堂赋》。浮梁县讲堂毁于元末,至万历年间,由知县周侯和钱侯相继修建而成。作者经友人黄龙光告知讲堂的气象、规模,因而作赋颂美。先叙浮梁县风土之美,地理之优:“乡老提朝夕之塾,游童遵出入之伦。国游藏于经解,家韫席于儒珍。道山东其证圣,里江西而近仁。凡兹宦游适若期契,莫不欣其风土,安其气味。”再叙讲堂体势之美,学风之盛。“今夫浮梁之茗,闻于天下。惟清惟馨,系其揉者。浮梁之瓷,莹于水玉,亦系其钧火侯。是足然则无清英之意者,不可以及远,鲜阴阳之力者,不可以致用。故夫通人学士,坐进此道。”以地方特产茶叶和瓷器的制作为喻论学习的方法、态度及修习之乐。类似的还有元代陈樵《东阳县学辉映楼赋》、汪克宽《泮宫赋》、清代陈仁言《学校赋》等。相比于中央官学赋,乡学赋更能体现出学校教育特点,在赋文写作上,作家更能用一种平实的情怀,对学校历史、现状、功用,对学习内容和方法予以抒写。在教育功能上,更强调教育对地方人文教化的作用。
总之,中国古代官学具有明显的等级性,以培养统治人才为宗旨,这直接影响到官学赋创作,在情感上多表现出对圣贤、王化的颂美情怀;在学校描写上多用夸饰的手法写室宇规模之宏伟、礼仪场面之盛大。在论述上多从宏观上议学校与教化对国家、对社会的重要,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教化色彩。
书院赋与中国古代私学
私学与官学相对,是私人或民间团体办理的学校,在形式上主要有用于子弟教育的家庭书塾和私人创办、面向社会的学堂。家庭书塾赋虽以书斋为描写对象,但侧重于子女教育,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教育思想,因此,也属私学赋。如元代陈旅的《味经堂赋》。根据序文,以及虞集《味经堂诗》序言所说“国子祭酒鲁公伯子?父作味经堂,自为记,以勖其子”。可知味经堂是南阳鲁?父所作,并为教育子弟作《味经堂记》,此赋是相和之作,赋文内容和创作目的,主要是针对子弟教育。赋文用比喻的形式,围绕“味经堂”之“味”,论述学习经书应有的态度和方法,反映了室主要求子弟博览群收的开阔胸襟和通达眼光,体现出一种博学的教育思想。私人学堂赋,如元代戴表元的《君子轩铭》赞扬古君子风范,高度肯定贤师孔子和孟子在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杰出贡献,强调为师者德识感化的重要意义和学生以德润身、端正自身的必要性。
唐代以后,私学发展的重要表现是书院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书院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种独立的特殊的教育机构。它源于私学,但又不同私学。最早用书院命名的一般认为是唐玄宗时期的官府书院:丽正书院和集贤书院。集贤书院又名集贤殿书院、集贤院。其前身是丽正书院。《新唐书•百官志》:“唐开元五年﹙717年﹚,乾元殿写﹙经、史、子、集﹚四部书,置乾元院使。……六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十三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①集贤书院虽具书院之名,但本为官署,其主要职责据《唐六典•中书省》记载:“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之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②是中央掌管刊辑、校理经籍,搜集图书,承旨撰集文章的文化机构,但事实上又具有征遗逸、访名士、议典则、辩国事,以济治于当世的议政参政功能。其功能的多样性特别是其官署职能,直接影响到赋文创作的主旨和情感倾向。如唐代杜靑《集贤院山池赋》通过对书院山池四季景象的描绘,体现出院中贤士心怀魏阙,悠游雅思,身处书院的适意。“图书载暇,缨弁以序”,说明贤士们在校理经籍之暇,不仅可以读书游宴、吟咏作文,还可以招贤论典、顾问应对,议论时政,干预天下。赋文结尾作者自然生发出对山中人不识此乐的嘲讽,表达出愿于此“赏无极”的感叹,表现出对官方书院的认同和一种强烈的归属感。
与官办书院相对的是私人书院。最早的私人书院赋是朱熹的《白鹿洞赋》:径北原以东骛,陟李氏之崇冈。揆厥号之所繇,得颓址于榛荒。曰昔山人之处,至今永久而流芳。自升元之有土,始变塾而为庠。俨衣冠与弦诵,纷济济而洋洋。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运。皇穆穆以当天,一轨文而来混。念敦笃于化原,乃搜剔乎遗遁。鳷黄卷以置邮,广青衿之疑问。乐菁莪之长育,隽髦而登进。迨继照于咸平,又增修而罔倦。旋锡冕以华其归,琛亦肯堂而诒孙。怅茂草于照宁,尚兹今其奚论。夫既启余以堂坛,友又订余以册书。谓此前修之逸迹,复关我圣之宏模。亦既震于余衷,乃谋度而咨诹。尹悉心以纲纪,吏竭蹶而奔趋。士释经而敦事,工殚巧而献图。曾日月之几何,屹厦屋之渠渠。“李氏”指唐代李渤。朱熹在自注③中引陈舜俞《庐山记》云:“唐李渤字浚之,与兄)偕*白鹿洞,后为江州刺史。乃即洞创台榭,环以流水,杂植花木,为一时之胜。”可知白鹿洞原是李渤兄弟隐居读书之处;按《庐山记》:“南唐升元中,因洞建学馆,置田以给诸生,学者大集。乃以国子监九经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授。《江南野史》亦云。当时谓之‘白鹿国庠’。”至五代南唐升元年间,建学馆,置田地,延洞主,始变私塾为“庐山国学”。白鹿洞书院此后累经兴废。至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经朱熹竭力倡导,又重建了白鹿洞书院。“鳷黄卷以置邮”,“黄卷”即诏敕,是皇帝颁发的命令;“邮”是古代传递文书的驿站。按《国朝会要》:“太平兴国二年,知江州周述,乞以九经赐白鹿洞。诏从其请,仍驿送之。”“九经”是九部儒家经典的合称,朱熹曾“奏乞赐书院敕额及《九经》注疏”﹙王懋?《朱子年谱》﹚。赋文叙写白鹿洞书院历史,清晰地体现出书院民间承办,官府相助的形态。书院最先由富室、望族或学者筹款兴建,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从性质上讲,属民办的学馆,从功能上说,属私人聚徒传授、开引地方士民的教学机构。但书院在发展过程中又往往受经济和政治限制,因而对朝廷和官府具有依附性,因为朝廷赐敕额、书籍,委派教官,调拨田亩和经费等,书院逐步呈现出官学化色彩。书院的官化色彩在书院赋中十分明显,如李梦阳《河中书院赋》序文陈说谏官吕氏欲废庙建书院,先“以问其守”,又“程问之校”;赋文赞美谏官吕氏“知教之本”,斥庙之愚妄,“巡守忘废歇,明堂载黜”,主持创建河中书院,体现出朝廷官员在书院创建中的重要作用。#p#分页标题#e#
书院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①,自宋代始,理学传播与书院教育联系起来,许多理学大家充分利用书院的学术传播功能,讲学传道,书院成为学术研究、自由讲学、问难论辩的场所,并日渐成熟和完善为一种制度化的私学。因为理学的发展,再加上朝廷对书院的认可和资助,书院日益发展兴盛,这就促进了宋代以来书院赋的兴起。如宋代朱熹的《白麓洞赋》、方岳《白鹿洞赋》、王柏《宋文书院赋》、杨万里《学林赋》、方回《石峡书院赋》;元代刘瞷《寿文堂赋》、任士林《宝麓赋》;明代李梦阳《河中书院赋》、胡缵宗《东湖书院赋》、唐龙《白鹿洞赋》、舒芬《白鹿洞赋》、廖道南《凤山书院赋》、陆綰《思贤书院赋》、孟思《东山书院赋》、江躌《东山书院赋》等。从这些书院赋,我们可以看到书院赋创作与宋明理学的兴起、发展及流派有着密切的关系。透过这些书院赋,我们可领略到儒家知识分子浓厚的学术意识和兴教传道的济世情怀。
从元代开始,统治者对书院的师资任用、组织管理、教材乃至财政供给等各方面都加以控制,书院呈现出官学化趋势。明代中叶,科举与官学一体化,程朱理学定于一尊,成为士子们猎取功名和统治者牢笼人心的凭借。到清代,书院已经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书院中盛行考课括帖和八股文,反映到书院赋的创作,就是课士赋的兴盛。关于这一点,许结先生的《论清代书院与辞赋创作》②有详细论述,可以参看。
儒家教育的主体地位与学堂赋的德育情结和道学情怀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儒家经典《孟子•尽心上》:“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③认为得到天下英才对他们加以教育,这是君子“三乐”之一,而且这种快乐要远远高于“王天下”之乐,这就说明儒家对英才与教育的重视。所谓教,《说文解字》释作“上所施下所效”,即教的方法是上行下效;育,“养子使作善也”,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为了传授知识或技能,而是重在德,即使之“善”。至于“善”的标准,自然取决于统治者即教育的授权者。汉武帝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认为“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提出“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④的建议。汉武帝接受建议,开设太学,立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独尊儒术”的政教政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仁”为核心和最高道德标准,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提倡德政和礼治,强调道德感化。《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反映到学校赋中,是浸润其中的深厚的德育情结和道学情怀。如周存《观太学射堂赋》写太学观射,“射”是太学教学六艺之一。《礼记•射义》云:“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可知射礼并非单纯的射击竞技运动,而是注重通过“射”的仪式,表现射者礼让、庄重、谦和的德行,强调通过“射”这一种技艺使人产生道德自省。可以说,太学射艺是华夏先民寓德于射、寓教于射的道德实践方式。因此,赋文曰:“非取善于主皮,盖绎心而正已”,不苛求发矢中的,而重在观射者之德行,“射宫观美,莫不比乎礼乐,和其容止,将申明于德行,必审固夫弓矢,皇家之阐化也。”强调以射取士是“国之恒规,而择贤之盛事”,并进行曩今对比说明射之重德是社会发展形式使然,过去征战不息、崇尚武力,因而射术注重“训人以知战”,当今四海无虞、天下一统,因而注重以射立德。这不仅是因时合宜的变革,而且能达到德化天下的效果:“彩侯不张而远国来属,贡士不习而盛德必敦。”“故夫五帝殊仪,三王异礼。咸登太和与至理,莫不雍雍而济济。是知崇乐非钟鼓之器,立德为正鹄之体也。”认为习射与习乐一样,不注重钟鼓、箭术本身,而只是修养和立世的工具,因而赋文对历代重德育给予了极高肯定和颂扬。
儒家强调师德风范,《礼记•学记》云:“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①孔子提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的为师标准;汉代董仲舒提出“独崇儒术”的文教政策,认为“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②学堂赋也体现出对师德的重视。如戴表元《君子轩铭》:君子轩是秦张+授徒之室。其岳父蜀牟先生为其室命名,取意于《孟子•尽心上》:“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③认为君子教育人的方式有五种:像及时雨一样滋润化育;成全其品德;培养才能;解答疑问;以学识风范感化使之成为私淑弟子。赋文赞扬古君子风范,高度肯定贤师素王和邹公孟子在教育史上的崇高地位和杰出贡献,并由此提出对女婿为师的殷切期望:“逆拂顺磨,明滋阴润”,从师者角度强调德识感化的重要性。“莫尊匪礼,莫善匪文。咨尔君子,各敬其身”则从学生角度强调遵循师教,以德润身,反省端正自身的必要性。陆綰《思贤书院赋》④叙陆贽忠言极谏,拯救唐朝于危亡之际,感叹其在当时黑白巅倒的现实下,狷直难容的遭遇,书院以“思贤”为名,对其“上不负一天子”“一不负所学”的衷忠给予了极大的推崇,认为其千古芳魂将润泽青衿、照耀邦人,体现出对德的推崇。
自孔子始,儒家知识分子就以“道”自任,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儒家传道系统,主张排斥佛老,恢复三代以来儒学的真精神。朱熹更是高举道德理性旗帜,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⑤的心性理论,主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穷理尽性,为恢复与发扬儒家精神,以毕生精力提倡书院教育。他批判科举以利欲噬学,认为游学于官学者“不过以追时好,取世资为事,至于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则寂乎其未有闻也,岂是国家所为立学教人之本意哉?”⑥其《白鹿洞赋》云:“请姑诵其昔闻,庶有开于时习。曰明诚其两进,抑敬义其偕立。允莘賊之所怀,谨巷颜之攸执。”表明书院的办学宗旨在教人为学,开于时习。所云“明诚”、“敬义”既是其道学主张,也是他办学宗旨,这种崇儒重德的理论和作法对中国古代书院有着重大的影响。朱熹《白鹿洞赋》一经传出,即被广为诵唱,历代名流纷纷追仿和创作,清陈元龙所辑《历代赋汇》所录六篇《白鹿洞赋》,除朱熹外,宋代方岳,明代林俊、祁顺、舒芬、唐龙所作之赋都标注“次晦翁韵”。朱熹道学及其创学之举成为以后众多书院赋吟咏感叹的标的。如方岳《白鹿洞赋》写自己日夕沉绕于书院,“朝余乐兮紫阳,夕余梦兮朱塘。讯风泉与云壑,劳降騋而陟冈。慨夫子其未远,宁吾道之易荒。言琅琅以犹在,将弥久而弥芳。”感伤道学易荒,物是人非,迷漫着一股浓烈的感伤情调。方回在《石峡书院赋》中批判科举导致人心世道之不古:噫!近世之不古兮,薻名场之?网。科举之坏人心兮,竞区区之得丧。厉夜生子而取火兮,幼尝视以无诳。以干禄为始教兮,将终身其奚仗。天或者恶其然兮,斯革弊而矫枉。无所为而为学兮,真儒庶其可访。声乃心于希瑟兮,盘厥躬于陋巷。颜曾固何必仕兮,胜齐鲁之卿相。或塾居而授书兮,或野芸而植杖。君子衎盎以润身兮,小人给夫一饷。化?锋而牛犊兮,息薺?之鹬蚌。春豳酒以介眉寿兮,岂太平之无象。婴更徽而弗予蜕兮,言及兹而?颡。予固将引而去之兮,畴敢卜邻于思旷。#p#分页标题#e#
“厉夜生子”语出《庄子•天地篇》:“厉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视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丑人半夜里生下儿子,赶紧取火照看,唯恐像了自己。这里显然是比喻父亲得子便寄予极高期望,生动展现了世人热衷于科举利禄的急切心情。科举在宋代非常盛行,不仅统治者倡导,许多家庭也以科举为家族振兴的途径,热衷于科举:“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①。赋文所云“以干禄为始教兮,将终身其奚仗”,“干禄”即追求禄位、追求功名,批判科举导致士人以仕进为目的,腐蚀人心,危害社会。作者标榜素以德行著称的颜回和曾参,推崇“无所为而为学”,对历史上不以仕进为意,独善其身的君子儒表示出由衷的崇敬。这显然也就是朱子所推崇的成人之道。明代胡居仁的《碧峰书院赋》也表现出对圣道的忧虑,并提出主敬存心、穷理致知、躬践其实的道学主张。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居教育主体地位,受之影响,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往往表现出浓厚的涉世精神,关注现实,以道自任,这就使古代以学校题材的赋文在内容上多叙历代政教、考学校盛衰、论斯文振兴,表现出深厚的道学情怀和德育情结。
本文作者:易永姣 单位: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