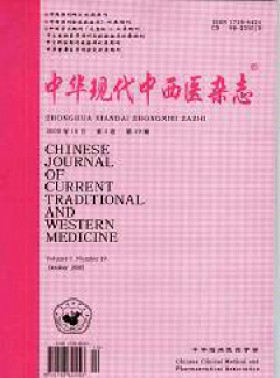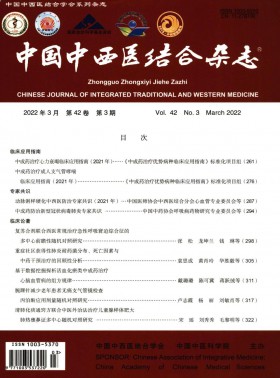中西文化范文1
【关键词】警务英语培训;中西文化;差异
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机遇,人类的政治经济活动呈现出“无国界”特征,国际间交往活动的日益增多,使得警务工作者们有了更多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经济发展的连锁反应,引起全球犯罪率居高不下,犯罪手段也趋向高科技、智能化和国际化,这些情形都给我们的警务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对我们警务英语培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了解英美国家地域特点、风俗人情、等方面的文化差异,才能真正消除文化障碍,避免交流上的障碍,有效提高警务工作者的语言应用能力,使警务英语培训工作步入崭新的历史阶段,让警员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工作环境。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文化的折射。一种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它不仅包含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还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1]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曾指出:“一种语言基本上植根于说该语言的民族文化、社会生活和习俗,不参照这些广泛的语境便难以正确理解该语言。”[2]语言是社会交际的工具,语言交流离不开文化背景,学习语言就必须要注重了解文化的差异。为了能更好地与外国人交流,避免一些语用失误现象,警务英语培训中应融入中西文化差异的教学内容,真正培养警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下面,笔者就中西文化在言语交际环境、地域文化、历史传统、习俗文化、宗教文化、非语言交际等方面的差异逐一进行阐述。
1. 言语交际环境的文化差异
开放的现代社会,跨文化的言语交际显得尤为重要,成为现代交际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随处可见,言语交际环境中的文化因素也受到普遍重视。下面是中西文化中十大常见差异。
1.1回答提问
中国人对别人的问话,总是以肯定或否定对方的话来确定用“对”或者“不对”;英语中,对别人的问话,总是依据事实结果的肯定或否定用“Yes”或者“No”。
1.2亲属称谓
西方国家的亲属以家庭为中心,一代人为一个称谓板块,只区别男性、女性,显示出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如:“grandparents,uncle,aunt”是通称。汉语重视配偶双方的关系以及不同的性别区分,则出现称谓的差异,如“外公、爷爷、叔叔、舅舅、姑妈、姨妈、堂兄、表妹”等不同称谓。
1.3考虑问题的主体
中国人喜欢以对方为中心,考虑对方的情感,如“您有什么事吗?” 。而英语中,往往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如“Can I help you? What can I do for you?” 。
1.4问候用语
中国人打招呼,一般都以对方处境或动向为思维出发点,如“您去哪里? ”“您吃了吗?” 而西方人往往认为这些纯属个人私事,不能随便问,他们见面打招呼总是说:“ Hi/Hello! How are you?”或是谈论天气等其它事件,“ It's a lovely day.”
1.5面对恭维
中国人对别人的恭维和夸奖一般都是推辞,因为谦虚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如:“ 饭菜做得很好吃。” “过奖,过奖,做得不好,多包涵!” 西方人不会过分谦虚,对恭维和夸奖会欣然接受,并表示谢意,这是西方人自强自信的信念所决定的,如: “You can speak very good French.” “Thank you.”他们往往会将中国人的谦虚、推辞的表现看作是不礼貌,甚至是虚伪。
1.6电话用语
中国人打电话时的用语与平时讲话用语没有多少差异,“喂,您好。麻烦您让××接电话。”而西方人打电话与平时用语差别很大,接到电话一般都先报自己的号码或者工作单位的名称,如:“Hello,this is John speaking.”“Hello,52164768,this is Jim.”。
1.7接受礼物
中国人收到礼物时,一般会在确信客人走后,才打开礼物,在接受礼物时连声说:“哎呀,还送礼物干什么?下不为例啊。”“让您破费了。”西方人收到礼物时,一般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 “Very beautiful!Wow!” “What a wonderful gift it is!” “Thank you for your present.”
1.8称呼用语
中国人见面时喜欢问对方的年龄、收入、家庭等,而西方人很反感别人问及这些私事。西方人之间,如没有血缘关系,会对男子统称Mr.,对未婚女士统称Miss,对已婚女士统称Mrs.。而中国人重视家庭、亲情,认为血浓于水,在日常交际中为了表示礼貌和亲热程度,对陌生人也要以亲属关系称呼,如: “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大哥、大姐等”。
1.9体贴他人
在西方,向别人提供帮助、关心、同情等的方式和程度是根据接受方愿意接受的程度来定的;而中国人帮起忙来一般是热情洋溢,无微不至。比如,中国人为了表示真诚的关心,会建议患上感冒的人马上去看医生,而美国人对此不理解,会误认为自己好像已经病入膏肓了。因此,这种情形下,只要回答:“I'm sorry to hear that.”就够了。
1.10请客吃饭
中国人招待客人时,一般都准备了满桌美味佳肴,不断地劝客人享用,以主人为客人夹菜为礼,并谦虚说到:“没什么菜,吃顿便饭。薄酒一杯,不成敬意。”西方人会对此大惑不解,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行为。西方人请客吃饭,菜肴特别简单,经常以数量不多的蔬菜为可口的上等菜,席间劝客仅仅说:“Help yourself,please.”吃喝由客人自便自定。
2. 地域文化的差异
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言语形式来表达。中国处于东半球,主要是温带大陆性气候;而英国处于西半球,主要是温带海洋性气候。汉语中常用“西风”来表示“凄凉、萧萧”,马致远的“古道西风瘦马”就表现那种秋风萧萧的凄凉场景;而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那脍炙人口的《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中曾有这样的千古佳句“O, wind,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啊!西风,若是冬天已来临,那春天还会远吗?),这又表明“西风” 会给英伦三岛带来春天,故而有“西风报春”之说。又如,莎士比亚在赞美他的爱人时说:“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这句话中并不是说他的爱人热情如火,如夏日骄阳。由于英国海洋性气候,夏季温暖,气候宜人,莎翁以此作比,是为了表现他的爱人柔美温婉。[3]
另外,由于英国是个岛国,它以捕鱼和航海业为主。因此,众多英语词汇均与海洋、捕鱼、航海等有着关联。如:all at sea不知所措;the sea has fish for everyone机会人人有,全靠自己抓;miss the boat错过机会;see how the land lies观察形势;know the ropes懂得诀窍。而对中国这个内陆国而言,古代居民多以土地为生。所以,和徒弟有关的词比较多,如“土皇帝”、“土豪”等。比喻花钱浪费,大手大脚,英语会用短语“spend money like water”来表示,而汉语则翻译为“挥土如金”。
3. 历史传统的差异
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同,使得他们所形成的历史传统也有所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的思想为主导,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行为准则,以现实性的人伦关系为核心,通过协调性的伦理意识来实现文化社会的自我肯定;“中庸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观念,主张对己要“克己复礼、不喜形色”,处世要“不偏不倚、公正和谐”。一些俗语和民谚中反映了这一民族观念,如“吃亏是福”、“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西方传统文化是以“天人相分”的思想为核心,崇尚个人为中心,宣传个人主义至上,强调自我发展、自我表现,追崇独立、自主、自强、自立。比如说, individualism一词在英语中强调的是个人独立意识、个人自由与权利及实现自我价值的独立奋斗精神,而中文则认为是“个人主义”。 landlord(地主)、capitalist(资本家)等词在英语中往往有积极的涵义,但对中国人而言,这类词有着强烈的贬义。
4. 习俗文化的差异
习俗文化差异是指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当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而形成的文化。以颜色为例,中西文化对它的理解和应用方式都存在差异。如“Mr. Green is very white man. He was looking rather green the other day. He has been feeling blue lately. When I saw him, he was in a brown study. I hope he’ll soon be the pink again.”(格林先生是个很忠诚可信之人。那天他脸上颇显病色。近来他总感闷闷不乐。当我见到他时,他处于忧郁之中。我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健康。)由此看来,white表示忠诚;green表示病态;blue表示郁闷;in a brown表示处于沉思、忧郁之中;pink则表健康。[4]
在中国,红色象征着喜庆、吉祥、幸福。新婚之时,新人要披红戴彩,满堂处处粘贴大红喜字。这表示婚姻幸福美满。在西方,人们却视红色为愤怒、权势的标志,同时暗示存在某种危险。中国在行葬之时会披麻戴孝,全身皆白,以示悲哀;在西方的婚礼上,往往看到新娘身穿白色婚纱,以表示纯洁、圣洁。在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里,同一种颜色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以动物为例,同样能看出中西文化中的差异。如:like a key in a lion hide 狐假虎威;come in like a lion and go out like a lamb虎头蛇尾。中国人视老虎为百兽之一,而英国则将lion视为国家的象征,是勇猛、权威的象征。在英、美国家,人们特别喜欢狗,所以常从词中体现出对狗的忠爱之情。
5. 宗教文化的差异
中西文化范文2
所以现在的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在追求着财富和金钱,只是希望自己能够有所依靠,不会再面临着被饿死的风险。
可是我想我们现在应该是能够知道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所了解,我们的生活是为了追求梦想而梦想却并不等于金钱和地位。我们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找一个工作而养加糊口。
我们想要在未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而不是死死的守着一个固定的岗位,拿着死工资,每天过着机器人一样重复的生活。
中西文化范文3
1.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国的鬼文化可以追溯到千年以前,先秦典籍中涉及到“鬼”的的文字很多,孔子在《论语》中明确告诫弟子:“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可见儒家是信奉鬼神的,态度是“敬”的。中国人在鬼节的习俗,如扫墓、烧纸钱、供灵牌等代代相传,虽然现代人崇尚科学,已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但对于这些文化习俗的传承仍然很难改变。我们在鬼节的祭祀不能简单地看成是迷信,它是中华民族对于“孝”文化的反映和传承,与我们千秋万代的宗族血缘观念息息相关,是血脉的召唤和亲情的延伸。这种深厚的道德内涵赋予了中国鬼节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人对于祖先的祭祀已成为一种文化深入到我们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和追忆,体现了孝道的传承和道德的涵养,也体现了中国人家族观念的根深蒂固和思本思源的精神。而在西方的基督教里面,对于先祖的祭祀是不允许的。在基督教的文化里,每个人在上帝的眼里都是平等的,相对于中国人对于祖先的信仰,西方人更愿意信奉上帝,他们希望人死后能够得到上帝的宽恕,升入天堂。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人的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人们对于“鬼”的敬畏和避忌并没有多么严重。
2.思想观念的差异。中国鬼文化的源头可以说是祭祀文化,古人的祭祀主要是对自然万物之神的祭祀和对已逝先祖的祭祀,所以对祖先之鬼的祭祀和对自然之神的祭祀一样都是敬重肃穆的,他们相信已逝的祖先能够在冥冥之中保佑着自己生活的安宁,有着消病除灾的无形力量。这种对于无形神秘力量的敬畏,使得人们对于鬼节的态度是认真严肃的。文化巨人唐君毅先生曾经说过:“吾人之祭父母、圣贤、天地,皆非因自觉自己有罪,以之为赎罪之仪式。亦非因自觉有苦痛,求其废除。吾人之祭,唯在使吾人之精神,超越吾人之自我,以伸展通达于祖宗、圣贤、天地,而别无所求者。”[3]所以中国人对于“敬鬼”的思想观念是和对祖先的信仰和孝道的道德源头分不开的。人们对于“鬼”是有所忌讳的,更不习惯和“鬼”开玩笑、“扮鬼”、“闹鬼”。而在西方万圣节的来历里头,“鬼”的出现是要来找活人当替身以求再生的,人们对于鬼的态度是要“驱鬼”、“吓鬼”,据说万圣夜是一年当中最“闹鬼”的时候,中世纪时人们就穿上可怕怪物造型的服饰,带上鬼怪的面具来驱赶黑暗当中的妖魔鬼怪。后来现代的人们更加上了喜剧和狂欢的元素,想着在万圣夜的舞会上要扮演什么样的可怕鬼怪,有的人把自己的房子装饰成“鬼屋”的样子,墙壁和窗户上贴着纸糊的巫婆、怪物、精灵等,屋里播放着“鬼音乐”,即使是念过六旬的老太太,可能也会恶搞一把,变成“幽灵”什么的。在现在的西方人眼里这个节日已经被演化成借鬼神使得人们轻松搞笑的一种方式,特别是让孩子们开心,邻里之间也通过这种方式互相走动,热闹一下。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的祭祖文化里是不能相容的。
3.教育理念的差异。中西方在大人们对待孩子在鬼节的活动上有着截然不同的相反态度。国外孩子在过万圣节时,会进行一些装扮,有些装扮成吸血鬼之类比较恐怖的形象,但是家长似乎也不会阻止,甚至还出谋划策地帮助孩子们设计和装饰。学校也会组织一些活动比赛谁的奇装异服更古灵精怪,谁设计的万圣节的图画更有创意等等。但在中国家长普遍不想让孩子接触过于恐怖的玩具,在鬼节这段时间,有些家长告诫孩子不准乱跑,小心遇上不该遇到的东西,晚上更是早早地关门闭户,谈论“鬼”都是很忌讳的,更不要说扮成他们的样子走在大街上了。不管是出于迷信还是对传统思想的继承,中西方的孩子从小接受的教育理念是有很大差异的。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宗族观念思想和权势地位等级理念,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子女不能对父母有大不敬,对待宗族先辈的态度自然也是尊重肃穆的,开不得半点玩笑。这种等级和孝道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延续和渲染着世代子嗣,使他们不能“离经叛道”,挑衅长辈的尊严,更不许有任何“忤逆”和“背叛”。现代社会虽然使旧的观念有了很大的转变,但是孩子要听父母的话,长幼有序,长辈在上的思念还是根深蒂固的,孩子还是要礼让、尊重长辈,即使长辈有错,也要讲求方法和话语的委婉,不能毫无顾忌地争辩,更不可斥责。另外中国人高度地重视宗族和家庭,很多活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中国在鬼节的祭祖、扫墓、烧纸钱等都是多以各家各户的方式进行,本族和本家的观念比较重,祭祀自己家族已故的亲人,希望庇佑自己家族的后代安宁福康,也希望自己的先祖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总体来看,中国人的家文化相对比较重一些。比起中国,西方的孩子接受到的家族地位等级理念相对较轻,西方人讲求人人平等,尤其在现代社会,孩子和父母在地位上是可以“平起平坐”的,对孩子的教育讲求自由、平等、民主,孩子可以有跟父母不同的主见和看法,也可以提出问题和父母辩论,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同时总体来说,西方人对家庭的观念也没有中国人那么浓烈,现代西方的文明基础是古希腊、罗马,地中海文化,几千年前就是街头辩论,选举,很多事物都是围绕社会化展开的,[4]他们更多地把孩子看成是社会的人,希望孩子多参加社会的活动,探索未知的世界。
二、如何看待“洋节日”
中国人随着与世界的接轨,很多“洋节日”已经进入了国门,来到了我们身边。不管是“圣诞节”、“感念节”还是“情人节”、“万圣节”等很多商家、机构、年轻人都搞得红红火火,有滋有味,不但体验到了洋节的乐趣,也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节日没有孰好孰坏,中西方的节日都是人类文明悠远文化底蕴的体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传统的文化节日是一个民族历史积淀下来的关于这个国家人们文化背景、思维理念、多方面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的体现,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发展状况、文化体系相对应的,因此不能盲目崇拜、盲目利用,比如把万圣节强行移植到中国人以祭祀为主题的文化体系中是格格不入的,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来生和往世都是两个比较严肃谨忌的话题,谈到“鬼”也太容易用玩笑、嘻哈的情感去接受。一些商家制作过于恐怖、血腥的销售活动也仅能限于对于成年人、年轻人的刺激,而不太适合使儿童、老人参与。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认识的提高,我们也可以把“洋节日”好的方面应用到适合我国的国情发展之中去,比如使用活泼可爱的方式举办万圣节派对,告诉孩子们万圣节的来历和发展,营造快乐的气氛,使孩子们不怕鬼,不怕精怪,鼓励他们习惯并亲近未知的神秘事物,发挥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把派对举办成社会化活动,邀请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给彼此的交流和互动创造条件。
三、结语
中西文化范文4
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当代中国文论界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学术工程。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我们能否克服中国文论的失语症,建立一套自己的(而非从西方借用的)文论话语系统,是21世纪中国文化与文论能否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能否贡献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文论家和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理论的关键问题〔1〕。然而,要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则必须首先清理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话语系统,寻求中国文化与文论所赖以形成、发展的基本生成机制和学术规制,从意义生成方式、话语解读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等方面清理出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基本规则,然后才可能进一步清理古代文论范畴群及其文化架构、文化运作机制和文化与文论的发展规律。由于这种文化探源式的研究,是从文化基本生成规律和学术运作规则入手,因而不但具有探本求源的意义,而且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是一条追寻东西方文化生成运作机制和规律的切实可行的路径。从这条路径,我们不但可以比较东西方各异质文化圈的不同文化精神,而且可以总结出各类文化生成与运作规律,这种规律,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东西方文论特征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给当今的文学理论建设提供一种“活的”文化运作机制和规则。只要我们能真正认识到这种文化运作机制与规则,那么不但可以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而且还可以为建构新的文论体系,或者说建构一般的(或总体的General)文论体系提供若干“活生生的”学术规则和运作方式,而不仅仅是提供一堆“死的”材料和人物。作为文论史固然要借鉴古人,要研究“秦砖汉瓦”、“古希腊、罗马”、“吠陀、奥义书”等等“死的”材料,但我们更需要从生生不已的文化传统中寻求其文化生成方式与运作规则,发现其“活的”文化生成方式与运作机制。同时,也只有在探索其文化生成方式与运作机制的同时,才可能真正进行深入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真正回答清楚东西方文化为什么会“分道扬镳”的基本原因;也才可能真正认识东西方各异质文化的不同路径、文论特色及其互识的必要性和互补的巨大价值。“道”与“逻各斯”,这两个古老的术语,在中外当代学术界和文论界又开始时髦走红起来。甚至有学者将这两个术语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或专著的题目,如张隆溪《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TheTaoandtheLogos:LiteraryHermeneutics,EastandWest,DukeUniversityPress,1992)又如邬昆如《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道》〔2〕。连西方的大学者海德格尔,也对“道”与“逻各斯”情有独钟,在《早期希腊思想》(EarlyGreekThinking)一书中〔3〕,列专章讨论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所提出的“逻各斯”(Logos,λσγos)。与此同时,海德格尔对中国老子的“道”也颇有兴趣。有学者指出:“海德格尔的Eregins(大道)就含有老子的‘道’的影子,是受过老子思想启发的。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曾与中国学人合译过老子的《道德经》,对东方思想有过充分的关注,对老子的‘道’大有兴趣。”〔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往往将“道”与“逻各斯”相提并论。他指出:Ereigins(大道)这个词语,“就像希腊的逻各斯(Logos)和中国的道(Tao)一样不可译”〔5〕。在《走向语言之途》一书中:海德格尔指出:“老子的诗意运思的主导词语即是‘道’(Tao),根本上意味着道路。……‘道’或许就是产生一切道路的道路。我们由之而来才能去思考理性、精神、意义和逻各斯”〔6〕。当代中国著名学者钱钟书也指出:“‘道可道,非常道’;第
一、三两‘道’字为道理之‘道’,第二‘道’字为道白之‘道’,如《诗·墙有茨》‘不可道也’之‘道’,即文字语言。古希腊文‘道’(Logos)兼‘理’与‘言’两义,可以相参”。(《管锥编》第二册第408页)为什么钱钟书等人将“道”与“逻各斯”相提并论?显然,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确有相通之处;为什么海德格尔对“道”与“逻各斯”情有独钟?显然,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在各自的文化构成与传承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过,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道”与“逻各斯”的相似之处及其各自在中西文化与文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道”与“逻各斯”从相似的起点迈步,却各自奔向不同的路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规则、学术话语和意义生成方式?这一点,恰恰是学术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还是让我们从“道”与“逻各斯”的起点开始追索吧。《老子》一书开篇即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老子》1章)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的第1条说:“这个‘逻各斯’,虽然永恒地存在着,但是人们在听见人说到它以前,以及在初次听到人说到它以后,都不能了解它,虽然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D1)〔7〕^从以上两段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有这样一些共同或相似之处:第一,“逻各斯”与“道”,都是“永恒”的,是“常”(恒久)的。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之“永恒”与老子道的“常”是可以通约的,二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认识到,在这千变万化的宇宙中,有一个永恒的、恒常之物,这就是“道”和“逻各斯”。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25章)“逻各斯”同样如此。正如有学者指出:“虽然道不是逻各斯,逻各斯不是道,可是这种相异只是由于文化背景以及语言的不同,而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却相同,甚至它们的超越目的也相同,它们也有相同的实词,这种实词不但超越了感官世界的变化,而且超越所有时空的束缚,超越了时空,同时也就超越了运动变化,‘逻各斯’是‘永恒’的,‘道’是‘常’的,因此,‘逻各斯’与‘道’——世界的最终原理原则,都能用实词——‘永恒’与‘常’来形容,而且,也由于这‘永恒’概念和‘常’概念而变成超越的,再进一步,唯有在这种超越的境地里,才有一种保险,保证自己在‘万物流转’中不变不动,不失去自己的存在,使自己不变成虚无,在动中不变,在毁灭中永远存在”〔8〕。“逻各斯”与“道”不但是“永恒”的,而且都是万物的本原,是产生一切的东西,是万物之“母”。此即我们前面所说过的“道”产生一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41章)“逻各斯”是万物的本质,“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D1)。第二,“道”与“逻各斯”都有“说话”,“言谈”,“道说”之意。“逻各斯”(λσγos)一词有字、语言、断言、谈话、讲演、思想、理性、理由、意见、计算、比例等等含义〔9〕,从词源上来看,“逻各斯”的词源出希腊文Legein,意为“说”(tospeak)。有学者明确指出:逻各斯的第一个意义是“言语”、“谈论”,或是说出来的一个“字”。这意义在纪元前六世纪时,是古希腊文最普遍的用法。赫氏断片(残卷)第1、第87、第108都用这种意义表达逻各斯〔10〕。老子的“道”同样有“言说”之意。杨适在《哲学的童年》一书中曾比较过这一点,他指出:这里(指《残卷》第1条)最初出现的“逻各斯”一词直译只能是“话语”、“叙述”、“报告”等等,它同“听”众相关。在这里对照一下老子的用语是很有意思的。《老子》这部我国的哲学文献也是古代的哲学诗,它一开头是:“道可道,非常道。”如译成现代汉语,这第一个“道”字显然是双关的,第二个“道”字只能译为“说出来”、“用言辞表达”〔11〕。第三,“逻各斯”与“道”都与规律或理性相关。韩非《解老》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韩非子·解老》)韩非是最早解说《老子》的学者,他对《老子》道的理解,显然看到了道是万物之“所以然”的规律,是万理之所用。而这一点,也正与赫拉克利特“逻各斯”相似。杨适指出:“道可道,非常道”中的这第三个“道”字,作为“常道”,含义就明显地向客观的道理或规律转化去了。而这后一含义,在以后的表述中越来越清楚,并不断得到了丰富和充实。这种表述方式同赫拉克利特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非偶然的巧合〔12〕。对这一点,台湾学者邬昆如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逻各斯”的第二个含义是“理性”,赫拉克利特是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把逻各斯概念提升到最高之宇宙原则,这可在许多断片(残卷)中找到(如第1、第2、第31、第45、第50、第72、第115等)。理性是万物的型式因,是万物的掌管者,是永恒的,对万物是一种共相,但仍然有能力把万物之杂多性融通为一。因此,在这些观点之下,逻各斯的意义包括了理性、艺术、智慧以及各种关系。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逻各斯的共相意义,这共相包括了原因概念。这原因概念保证了下面一项原理原则:“宇宙万物来自一体,而一体亦来自万物”。邬昆如紧接着指出,中国老子的“道”,同样具有与赫氏“逻各斯”相近似的“理性”的意义:因为中国“道”之概念有一种潜能,能统合一总之杂多性,而且使多变为一,这显然是有“理性”的意义。难怪西方学者从开始接触中国文化之后,就一直用“逻各斯”概念来释“道”概念,尤其是他们在注释《道德经》第1章时。更觉得“逻各斯”和“道”的相同性〔13〕。尽管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有如上三点(或许还可找出更多)共同或相似之处,但为什么这种相似甚至相同的“道”与“逻各斯”,却对中西文化与文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显然,“道”与“逻各斯”在根本上有着其完全不同之处。我们更感兴趣的正是这种不同之处,因为这种根本上的不同,才使得中西文化与文论分道扬镳,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学术规则与文论话语。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真正寻到了中西文化与文论之根。“道”与“逻各斯”的不同之处,大致可以分为“有与无”、“可言者与不可言”、“分析与体悟”这样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恰恰是与上述三个相同或相似方面相对应的,这种“二律背反”现象确是意味深长的。限于篇幅,我们只比较论述前两个方面。我们前面说过,“道”与“逻各斯”都是“永恒”的,“恒常”的,同时又都是万物之本原,是产生一切的东西,是万物之“母”。不过,就在这相似之中蕴含着极为不同之处,那就是老子的“道”更倾向于“无”,而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更倾向于“有”。也正是这一基本倾向,从起点上确定了中西方文化与文论的话语的基本方向和路径。老子的“道”,其根本是“无”。《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1章)王弼注曰:“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及其有形有名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言道也无形无名始成万物。”也就是说,虽然道是产生天地万物之本原,是万物之“母”,但这个本原自身却是“无”。正如老子明确指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40章)王弼注曰:“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在这里,老子对于“道”的根本特征——“无”已表述得很明确、很充分了。这种“无”,并非虚无,并非真正的空空如也的“无”,而是一种无在之“在”,是一种以“无”为本的“无物之物”。老子这样描述这种“无”的情态:“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25章)显然,这种以“无”为本的“道”,仍然是一种“物”(“有物混成”),只不过它不是具体的物,而是宇宙间“有”的本原,是万物的来源。这个本原之“无”,是看不见,摸不着,听不见的;“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老子》14章)老子的“道”就是这样一种以“无”为特征的无物之“象”,无物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也具有某些“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特征。赫氏常常把“逻各斯”描述得似乎有些“近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的意味,他指出:“这个‘逻各斯’(λσγos),虽然永恒地存在着,但是人们在听见人说到它以前,以及在初次听见人说到它以后,都不能了解它。虽然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但是我在分别每一事物的本性并表明其实质时所说出的那些话语和事实,人们在加以体会时却显得毫无经验。另外一些人则不知道他们醒时所作的事,就像忘了自己睡梦中所作的事一样”。(D1)不过,只要我们仔细体会一下这段文字,便不难见出赫拉克利特与老子的不一样之处。老子从根本上就认为“道”就是一种“无”,所以无论谁都看不见,听不着。而赫拉克利特则并非认为“逻各斯”本身是“无”,只是人们理解力不高,不能懂得它、了解它。所以赫拉克利特说:“我在分别每一事物的本性并表明其实质时所说出的那些话语和事实,人们在加以体会时却显得毫无经验。”请注意赫氏这句话中提到的是“事物的本性”、“实质”,这个“本性”与“实质”,决不是“无”,而是“有”,是一种存在之物,是万物的“实质”与“本性”,人们听不懂的正是事物的“本性”与“实质”,而表明“实质”与“本性”的,正是赫拉克利特本人,即此段文字中的“我”。这说明至少赫氏本人是看见了或听见了“逻各斯”的,如此他才可以“分别”事物的“本性”,“表明”事物的“实质”。这就是赫氏“逻各斯”与老子“道”的一个根本区别。所以说,“逻各斯”的根本特征是“有”(或存在)。赫拉克利特进一步指出:“因此,应当遵从那人人共有的东西。可是,‘逻各斯’虽是人人共有的,多数人却不加理会地生活。”(D2)赫拉克利特明确指出“逻各斯”是人人共有的,只是人们不加以理会,或没有能力去理解它,听从它,因为“自然喜欢躲藏起来”。(D123)因此,赫氏主张去爱智慧,去寻求听从和遵循“逻各斯”。他说:“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D41)“如果你不听从我本人而听从我的‘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那就是智慧的。”(D51)听从“逻各斯”,实际上就是遵循万物的规律,认识那驾驭一切的思想,寻求事物生灭变化的规律与本质。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必然会走向“有”,而不会走向“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赫拉克利特曾摇摆于“有”与“无”之间,他说:“任何人都不能设想同一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像有些人认为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那样”。((形而上学》第4卷第5章1006b)的确,赫氏常常具有辩证的相对论观点:“不死的就是有死的,有死的就是不死的。”(D62)“善与恶是一回事”。(D58)这与老子的看法何其相似。但赫拉克利特最终走向了“有”,走上了从“有”寻求万物原因和规律之途,并把这个“有”陈述为实实在在的东西——“火”。赫氏认为,万物是由“火”构成,他说:“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D30)这“火”,决不是“无”,决不是老子所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的“无物之象”,而是“有”,是实实在在之物,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正如邬昆如指出:存在的追求是赫拉克利特哲学的目的。若用“太初”的问题来衡量赫拉克利特,则“逻各斯”是实体,“火”是表象,那么“太初是火”或“太初是逻各斯”,有同一意义。这里的哲学方法是:抓紧逻各斯,以逻各斯为出发点,通过“思想”达到哲学追求的对象——存在〔14〕。赫拉克利特终于从“逻各斯”走向了物质实体“火”,即从“求智慧”中观察万物,从观察万物中追问原因,寻求规律,“爱智慧的人应当熟悉很多的事物”,(D35)“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驾驭一切的思想”。(D41)而这条由求知——观察——追问原因——总结规律的链条组成的哲学话语规则和路径,正是西方文化与文论的基本学术话语特征。哲学大师亚里士多德,正是在对“有”,对“存在”的研究追问之中,建立起了西方科学理性话语和确立逻辑分析推论的意义生成方式的。而这种话语系统,正是当代海德格尔与德里达(JacquesDerrida)等人所激烈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从赫拉克利特使“逻各斯”偏向“有”而肇其端的。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正是固执于“言谈所及的东西”,才把“逻各斯”解释为理性、判断、定义、根据等,也即把“逻各斯”归约为逻辑了。正因为总是以外在的“有”,即现成存在者为取向,古希腊哲学家们(如亚里士多德)在分析“逻各斯”时就不可避免地“误入歧途”,将西方文化导向一种外在的“判断理论”——逻辑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海德格尔指出:“古代存在论在论述生长于其上的方法基础时不够源始。逻各斯被经验为现成的东西,被阐释为现成的东西;同样,逻各斯所展示的存在者也具有现成性的意义。”〔15〕因而,传统存在论的迷误就是“逻各斯”的不幸,此不幸即是:“逻各斯”沦为现存事物的逻辑了。于是乎海德格尔便力图重新审视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的本源意义,企图克服和改造传统以“有”为核心的存在论,站在全新的生存论存在论的基点上来理解语言现象,“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从而拯救“逻各斯”〔16〕。无论海德格尔能否“拯救”逻各斯,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西方文化执着(或拘执)于“有”的特征。同时也可以发现中西方文化中“道”与“逻各斯”这种“无”与“有”的特征,或许还可以发现“道”与“逻各斯”互释互补的价值。老子“道”的崇尚“无”与赫拉克利特“逻各斯”的偏向“有”,都对中西文化与文论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学艺术及文论中的“虚实相生”论,“虚静”论等,显然与老子的“尚无”密切相关,“无中生有”(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话语方式,使中国文学与文论更注重“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空灵和“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的隽永深长。同样,“逻各斯”对“有”的探索、追问与分析,也使得西方文化与文论显得更加严密而系统,更注重逻辑因果、注重情节结构。老子的重“无”,将中国文论引向了重神遗形,而赫拉克利特的偏“有”将西方文论引向了注重对现实事物的摹仿,注重外在的比例、对称美、注重外在形式美的文论路径。老子的“道”是不可道,不可言的,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已经非常清楚地表述了这一点。但是“道”虽不可以道,不可以言说,然如果完全不用语言文字,就根本无法论述道;而老子既然著书立说,肯定又非用语言文字来言说不可,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刘勰《文心雕龙·情采》指出:“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钱钟书说:“道不可说、无能名,固须卷舌缄口,不著一字,顾又滋生横说竖说,千名万号”〔17〕。具有“大智”的老子,实际上是认识到了这一两难悖论的,他清楚地知晓,“道”是不可以言说的,但他要著书论道,却又必须以语言来表述这不可言之道,以名号来名不可名之名。老子于是迫不得已走向了“强为之名”、强为之言之途,“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25章)这种“强为之名”,实际上必然造成“道”之本真的失落。王弼注曰:“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称最大也,责其字定之所由,则系于大,大有系则必有分,有分则失其极矣。故曰‘强为之名’”。显然,这种“强为之名”,是“失其极”的,老子之所以曰“强为之名”,实是不得已。不过,在这不得已之中,老子实际上闯出了一条“以言去言”之路,即通过有言,教人去认识、去领悟那无言之道,从而超越语言,直达“道”之本真。魏源《老子本义》说:“圣人知有名者之不可常,是故终日为而未尝为,终日言而来尝言,岂自知其为美为善哉!斯则观*而得妙也。若然者,万物之来,虽亦未尝不因应,而生不有,为不恃,终不居其名矣。”(《老子本义)第2章)魏源的解说是准确的,老子正是以言达到无言,以名寻求无名,从语言描述之中令人捕捉那微妙之道,去体悟那纯真之道。正如熊十力先生所说:“体不可以言说显,而又不得不以言说显则亦无妨于无可建立处而假有设施,即于非名言安立处而强设名言,……体不可名,而假为之名以彰之。”〔18〕所以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种“不言之教”,正是以“有言”来加以导引的,于是乎,语言便成为了桥梁与津渡,引导着人们通向“道”之本真。老子这样为我们描述那纯真之“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老子》21章)王弼注曰:“至真之极,不可得名,无名则是其名也。”这就是无名之名,无言之言。“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老子》22章)在通过有言来达到无言的津渡中,老子处处提醒人们,不要拘执于言,而要追求超越语言的“无言”;这就是后人强调的“不落言筌”,“不要死在言下”,“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意。老子指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37章)道虽无名、无象、无言,但却是本真,是大音、大象,“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41章)从“无名”到“有名”,最终还是要回到“无名”,回到“道”之本真。这就是老子“道”“不可言”的特征,这种特征是言无言,以不言言之,或者说通过言说使人明白道不可言说。对这一点,庄子表述得更为明确,“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外物》)所以庄子说:“终身言,未尝言。”(《庄子·寓言》)言说的关键是直指“道”本身,而不必拘执于语言,这样就可以超越语言之拘囿,这就是庄子著名的“得意忘言”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海德格尔对老子的“道”的这一不可言说特征亦颇有体会,他指出:“也许在‘道路’(way),即‘道’(Tao)一词中隐藏着运思之道说的一切神秘的神秘,如果我们让这一名称回复到它未曾说出的东西那里并且能够这样做的话。”〔19〕因此,海德格尔反对西方人将老子的“道”译为“理性”或“逻各斯”,他说:“老子的诗意运思的主导词语即是“道”(Tao),根本上意味着道路。但是由于人们容易把道路仅只设想为两个位置之间的连续路段,所以人们就仓促地认为我们的‘道路’一词是不适合于命名‘道,所言说的意思的。因此他们把‘道’译为理性(reason)、精神(mind)、理由(raison)、意义(meaning)和逻各斯(Logos)等。”〔20〕看来,海德格尔已经觉察出“道”与“逻各斯”虽同为不可言说之道,但中西方的哲人们对“道”与“逻各斯”的理解与阐释是有差异的。海德格尔在《讲与论文集》中指出:“在西方思想开始之际,语言之本质在存在之光亮中偶有闪现,赫拉克利特也一度把‘逻各斯’视为主导词的光芒,接近它所照亮的东西。”〔21〕在这里,海德格尔所谓“没有人抓住它的光芒”,实际上是指出了在西方哲学史上,“逻各斯”没有被引向不可言说的道之本真——“大道”(Ereignis),而是最终导向了可以言说的理性、规律与逻辑。而这,正是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逻各斯”又一个根本不同之处。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传统哲学对“逻各斯”的解释并没有触着其基本含义。“逻各斯”之本义乃“言谈”,传统的解释却把“逻各斯”归纳为“逻辑”,从而把语言当作逻辑的体现。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存在论的迷误就是“逻各斯”的不幸,此不幸即是:“逻各斯”沦为现成事物的逻辑了〔22〕。应该说海德格尔的眼光是极为锐利的,他的确洞察到了“逻各斯”的“惊鸿一瞥”,但也仅仅是“一瞥”而已。因为根据赫拉克利特著作《残卷)所显示,赫氏的“逻各斯”,仍然是倾向于可以言说的理性,可以认识的规律以及可以把握的外在事物。赫拉克利特曾明确要求人们,不但应当去遵循、去听从“逻各斯”,而且应当去认识、去把握“逻各斯”。他说:“‘逻各斯’虽是人人共有的,多数人却不加理会地生活着。”(D2)〔23〕“人们既不懂得怎样去听,也不懂得怎样说话。”(D19)因此他倡导人们听从逻各斯,并进而认识逻各斯。“如果你不听从我本人而听从我的“逻各斯”,承认一切是一,那就是智慧的。”(D50)所谓“智慧”,就是听从“逻各斯”,而“逻各斯”在何处呢?赫氏暗示,“逻各斯”就在自然之中,因此,智慧就是听从自然,认识自然。他说:“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D12)从以上论述来看,“逻各斯”是完全可以被表述、被言说的。正如赫氏所云:“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显然,“说出真理”,就是可以言说,也正因为“逻各斯”是可以言说的,赫氏才指责有些人“既不懂得怎样听,也不懂得怎样说话”。(D19)这里指责的只是人们“不懂得怎样说”,而不是指“逻各斯”根本不可说。怎样才能够“懂得说”呢?在赫氏看来,那就是去认识万物,去寻求规律,去言说驾驭万物的“逻各斯”。赫氏强调的是认识外在之物质世界,强调感官的重要性,主张从外在世界中去探寻原因,把握规律。他说:“爱智慧的人应当熟悉很多的事物。”(D35)“可以看见、听见和学习的东西,是我所喜爱的”。(D55)“人们认为对可见的事物的认识是最好的,正如荷马一样,然而他却是希腊人中间最智慧的人”。(D56)显然,在赫氏看来,事物是可以认识的,通过学习探索,不但可以懂得怎样“听”,而且可以懂得怎样“说”,可以把握万物的规律,“智慧只在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D41)“最优秀的人宁取一件东西,而不要其他的一切,就是:宁取永恒的光荣而不要变灭的事物。”(D29)如果你要想理智地说话,就应当用这个人人共有的“逻各斯”武装起来,你就能理智地说话。古希腊哲学,正是从这种可以认识,可以言说的逻各斯出发,强调理性、强调万物的规律,强调对自然万物的认识和把握,于是便走向了从“求知”(求智慧)到“观察”(认识自然)再到“追问原因”和“逻辑推理”的逻辑分析话语系统,建立了以可以言说为基础的科学理性分析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正如有学者指出:赫拉克利特强调了运用“逻各斯”,亦即运用理性认识能力的重要,但他并没有走向极端而否认感性认识的作用,相反,他充分肯定了感性认识的地位和作用。他对“逻各斯”的强调,从理论上看,即力图将物质性的世界运动的规律性与主观世界的运动的规律性统一起来,亦即企图把存在和思维在物质的基础上统一起来。〔24〕还有学者指出:赫拉克利特用“逻各斯”概念,指出了“智慧”之概念,说明人类虽因愚笨而丧失了理性,但是,人之求知仍然可以在“逻各斯”的保护下,重新回到理性的怀抱中〔25〕。显然,通过“求知”去认识自然,掌握规律,从而达到“用‘逻各斯’武装起来,就能理智地说话”,(D14)这正是赫氏“逻各斯”的言说之方法。这与老子主张的“绝圣去智”(《老子》19章)“行不言之教”(《老子》2章)的“言无言”的言说方式,从根本上是不同的。“绝圣去智”式的不可言说的方式导向了“得意忘言”,追求“不落言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文化与文论话语方式。而以求取智慧、探寻万物规律为己任的“逻各斯”,推崇的是“理智地说话”的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将西方文化与文论导向了科学理性的逻辑分析话语方式,导致了西方文论那种理性的、条分缕析的系统性科学性特征。而这种科学理性逻辑分析话语,正是从赫氏“逻各斯”起步,最终由亚里士多德来完成的。恰如有学者指出:逻辑学(Logik)在希腊哲学中是关于逻各斯(Logos)的科学。希腊哲学把Logos解为陈述(Aus-sage)。所以逻辑学也就是关于陈述的科学。逻辑学从陈述方面来规定思想,也即在思想的表达中来寻找思想的法则和形式。逻辑学提供出思想的逻辑法则。人们认为,思想是以逻辑为本质的,逻辑与思想,几乎就是一回事。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样的逻辑和思想与源始意义的Logos和思想,相距已经不止千里了。逻辑植根于形而上学中。在希腊形而上学中,发生了从源始的Logos到逻辑的演变。这就是源始的思想的隐失过程〔26〕。海德格尔指出:“Logos成为陈述,成为真理即正确性的处所,成为范畴的本源,成为关于存在之可能性的基本原理。‘理念’和‘范畴’,后来是统辖西方思想、行为和评价即整个此在的两个名称。Physis(存在)和Logos的变化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变化,是开端性的开端的沦落。希腊哲学在西方获得统治地位并不是由于它的源始的开端,而是由于它开端性的终结,此终结在黑格尔那里最后构成了伟大的完成。”〔27〕显然,海德格尔认为,“逻各斯”成为“陈述”,或者说成为可以言说之陈述时,便意味着从古希腊哲学的“开端性”沦落,这使得与中国“道”相似的、含蕴丰富而深刻的“逻各斯”,终于沦落为关于存在之可能性的基本原理,甚至成为思维形式,成为逻辑。海氏所谓“沦落”,显然带有他主观性的贬义色彩。不过,在我看来,与其说是古希腊哲学的“沦落”,不如说是中西文化的“分道”:或者说是中西哲学分道扬镳的肇端,“道”与“逻各斯”,正是从“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的两难境地之中,各自选择了一条路,各奔前程,从而形成了两套截然不同的文化与文论话语言说系统。这种话语言说系统,一经铸就,便成为规范文化的强大力量,具有不以某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强大的约束力。尽管西方文化与文论不断有反判科学性、反叛“逻各斯中心”思潮的产生,如西方的某些宗教思想、现代的非理性主义,乃至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当代解构主义大师们对“逻各斯中心论”的激烈批判,实际上都未能真正彻底摆脱西方文化那根深蒂固的科学理性的逻辑分析话语系统。就连极为睿智、洞见“逻各斯”开端性“沦落”并决心寻回“大道”(Ereignis)的海德格尔,在激烈批判“逻各斯中心论”的同时,也身不由己地重新“沦落”进了西方传统话语言说方式的窠臼之中。孙周兴在《说不可说之神秘》一书中指出:“我们也确实感到,正是在‘大道’(Ereignis)一词上,体现着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深刻的‘两难’:一方面,海氏力求挣脱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概念方式和学院哲学的言说方式,寻求以诗意语汇表达思想;而另一方面,海氏所确定的‘大道’以及相关的词语,恐怕最终也透露了一种不自觉的恢复形而上学的努力”〔28〕。为什么海德格尔最终无法摆脱西方言说方式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还没有(大约也不可能)彻底改换一整套话语言说方式,既然他终归要“言说”,要“陈述”,而且是西方式的言说与陈述,那么他不可避免地注定要“沦落”:“打破了‘沉默’,终难逃被误解的厄运。诉诸言谈的东西终归要获得非生成性的本质内核。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的日子里,围绕海德格尔的‘大道’思想的争辩仍将进一步展开,而此种争辩的中心题目脱不了的是:是否从‘大道’中可见出海德格尔重振形而上学、恢复哲学的‘元叙述’的努力?或者,‘大道’可能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终极能指’吗?如在德里达(JacquesDerrida)那里,我们已然可见关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这样一种责难了。不过,德里达本人,恐怕终究也难逃这同一种责难”〔29〕。海德格尔与德里达这种似乎在劫“难逃”的命运,不正显示了西方文化与文论话语强大的约束力么!而中西方文化与文论的这种约束力之初源,正滥觞于老子的“道”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老子“道”的“不可言”与赫拉克利特的“可言”,对中国与西方文化与文论的影响是根源性的、重大而深远的。注释:〔1〕请参阅拙文《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年第3期),《文化病态与文论失语症》(《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2〕邬昆如《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道》,台湾国立编译馆,1972年版。〔3〕MartinHeidegger,EarlyGreekThinkingHarper&RowPubilishers,SanFrancisce,1984。〔4〕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83页。〔5〕MartinHeidegger,IdentityandDifference,Pfullingen,1957。〔6〕MartinHeidegger,OntheWaytoLanguage,HarperCollinsPublishers.1971。pp.72。〔7〕《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8页。“D1”为柏林版第尔斯(Diels)辑《苏格拉底以前哲学残篇》的标准序数,下同。〔8〕邬昆如《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道》,第189—190页。〔9〕参见《希腊语—英语词典》,李德尔与斯柯特编,牛津,1883年版。〔10〕邬昆如《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道》,第180页。〔11〕杨适《哲学的童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175页。〔12〕参见杨适《哲学的童年》,第175页。〔13〕参见邬昆如《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道》,第181—182页。〔14〕邬昆如《西洋哲学史》,台湾国立编译馆,1972年版,第40页。〔15〕MartinHeidegger,BeringandTime,Harper&Row,1982。中文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16〕参见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第51—52页。〔17〕《管锥编》第2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10页。〔18〕熊十力《破破新唯识论》,台北广文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8—19页。〔19〕arnHeidegger,OntheWaytoLanguage,pp.92。〔20〕MartinHeidegger,OntheWaytoLanguager,pp.92。〔21〕参见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第270—271页。〔22〕上书,第58、52页。〔23〕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下同。〔24〕叶秀山等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154页。〔25〕邬昆如《庄子与古希腊哲学中的道》,第182页。〔26〕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第109页。〔27〕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图宾根,1987年版,第102页。〔28〕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第303页。〔29〕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第304页。
中西文化范文5
关键词:隐喻 文化内涵 透视
一、引言
隐喻从传统意义上来说是被界定为修辞学中的一种修辞格。然而,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它与社会文化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萨丕尔说:“Language is a guide to social reality.” 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是社会符号系统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一种“意义潜在系统”meaning potential。它由三部分组成:音位系统、词汇―语法系统和语义系统,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实现”realization的关系。语言体现文化,是文化的编码手段之一。语言学家莱斯认为,语言系统受两个结构制约,一个是“底层结构”substructure,即人类共同的生理特征和世界的原有结构,它使人类语言趋向于具有相同之处。另一种是“超结构”或“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即各民族不同的文化结构,它导致各民族的语言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差异。
二、隐喻中的文化内涵
1.隐喻中的宗教文化内涵。著名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有句名言,说“宗教是文化的灵魂,文化是宗教的形式.”由此可见宗教在文化中的比重及其重要作用是无可否认的。那么,隐喻中的喻体常常体现出特定民族的宗教文化是不言而喻的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与西方属于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古希腊罗马文学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中分别体现出来世俗与人本色彩和神圣与超越色彩共同构成了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两个源头。恩格斯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所以,在西方文化中,我们不难觅到希腊神话和《圣经》的踪迹。而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由于深受儒教、道教、佛教的影响,因而我们随时可以发现它们在东方文化中的透。如英语中的Black Friday:黑色星期五,源自宗教节日复活节,喻指大灾大难,凶险不祥以及经济恐慌到来的日子。汉语中与宗教有关的喻体也比比皆是,例如“痴人说梦”:源自佛教,喻指讲的话荒诞无稽;又如“顶礼膜拜”:源自佛教,喻指对人特别崇拜。
2.隐喻的民族文化内涵。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假说之一的“语言相对论”Language relativity中提到:“言语这一人类活动,从一个社会集体到另一个社会集体,它的差别是无限度的,因为它纯然是一个集体的历史遗产,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文化传统,它们自然而然会反映在语言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用不同的事物表达相同的语用意义。
动物喻体。⑴拦路虎:a lion in the way。“虎”在汉族人眼里是百兽之王,汉语中许多带“虎”字的词语就体现了这一喻义.如“虎门无犬子、老虎屁股摸不得、龙潭虎穴、虎踞龙盘、虎头蛇尾、狐假虎威、骑虎难下、虎视眈眈”。但在英语里,“虎”的地位就被“狮”所取代.众多词语如:beard the lion in his den〈太岁头上动土〉,the lion's share〈最大或最好的份额〉,a lion's provider〈豺狼,走狗〉,lionheart〈勇士〉。
⑵色狼:goat。汉语中用“色狼”喻指“不正经的人”,而英语中的wolf不含此喻义,用goat喻指“不正经的人”。
⑶“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贬多褒少。汉语里有“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癞皮狗、疯狗”等贬义词语用作喻体;而英语中dog却是褒多贬少。在英美文化中,狗是可爱的宠物,是忠实的朋友,如:a gay dog快活的人;love me, love my dog爱屋及乌;be top dog处于支配地位。
颜色喻体。(1)红色。在汉语文化中,红色可以用来喻指吉祥、喜庆、顺利、成功、进步、革命、美丽、漂亮等意义。如红娘、红火、又红又专、红人、走红、红妆、红颜;而在西方文化中的红色(red)则是一个贬义相当强的词,是“火”、“血”的联想,喻指残暴、流血、激进、暴力革命、放荡、淫侈、危险、紧张等。.如red revenge血腥复仇,a red battle血战,red activities左派激进活动,red alert空袭警报,a red light district花街柳巷,“Is she really so red as she is?”难道她真的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放荡吗?。
(2)白色。在中国文化中,白色可用来喻指死亡、凶兆、腐朽、反动、落后、失败、愚蠢、奸邪、阴险、知识浅薄、没有功名等。如:白色恐怖、举白旗、、白费力、白干、唱白脸、白衣、白面书生;西方文化中,白色可用来喻指高雅纯洁、纯真无邪、正直、诚实、廉洁、幸运、吉利、合法、无恶意等。如:a white soul纯洁的心灵,a white spirit正直的精神,whiteman高尚有教养的人,white market合法市场,a white lie无害的谎言。
(3)黑色。黑色原来在中国文化里只有沉重的神秘之感,是一种庄重而严肃的色调。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它的喻指意义显得较为复杂,它可以既用来喻指严肃正义,又可以用来喻指邪恶反动犯罪违法等。如:黑脸包公、黑市、黑心肠、黑幕、黑帮、黑名单、黑道、黑店、黑货、黑钱等。在西方文化中,黑色是基本禁忌色,可以用来喻指死亡、凶兆、灾难、邪恶、犯罪、耻辱、不光彩、沮丧、愤怒等意义。如:Black Mass安灵弥撒,black words不吉利的话,Black Man 邪恶的魔鬼,black guard恶棍流氓,blackmail敲诈勒索,a black mark污点,black sheep败家子,black dog沮丧情绪。
3.隐喻中历史文化内涵。由于各个民族的历史经历不同,隐喻中的喻体就自然地烙上了历史的印痕,刻录了不同的历史轨迹。英汉语言中与历史人物或事件有关的喻体不胜枚举,如汉语中:指鹿为马赵高、请君入瓮武则天、望梅止渴曹操、老当益壮黄中、身在曹营心在汉关羽、卧薪尝胆勾践、嗟来之食孟子、才高八斗曹植、无事生非张飞、三顾茅庐刘备等等。英语中:①meet one's Waterloo四面楚歌,喻指惨遭失败源自滑铁卢战役;②Watergate水门,喻指被揭发出来的高层丑闻源自美国总统尼克松选举作弊事件)。有趣的是现代英语中-gate也成了一个表此喻义的构词后缀,如:Billygate比利门,Dabatgate辩论门,Cattlegate牲畜门,Ricegate大米门;③by the grapevine顺着葡萄藤,喻指小道消息、马路新闻与美国大发明家莫尔斯Damuel F.B.Morse,1791-1872发明的电报机有关;④Left wing左翼,喻指激进派自由党源自法王路易斯十六召开的第一次国民会议;⑤Your name will be mud.喻指你将要倒霉了,你将为人们所讨厌mud与“泥”无关,而是因为替刺杀林肯的凶手治病的麦德〔Mudd〕医生的名字谐音而来;⑥an ax to grind磨斧头,喻指居心叵测、另有企图、有个人打算源自美国大政治家大发明家富兰克林少年时代的一段趣事。
4.隐喻中价值文化内涵。 中西不同的文化所体现出来的是个体价值观和群体价值观的差异,西方人的个体价值观的形成可以追至古希腊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基督教的《圣经》的影响,美国哲学家洛克曾断言,生物个体是自然界的基本单位,社会制度是存在于社会秩序之先,并为利己的目的而行动的个体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Bellah et al.i985:143。美国人认为,人类社会的个体不仅是独立的生物存在,而且是独立的心理存在和社会秩序中的独立成员。个体主义将自我作为社会的文化量子,个体主义的实质就是在个体自我与他人之间划定明确的疆界,在此界线内,自我作为知觉的主体、行动的源端、社会关系中的独立个体、以及对于环境的理性控制者。虽然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涉及他人,但自我始终保持主体的地位;虽然中国文化也曾经出现注重个体自我认同的道家思想,但随着历史的演进,儒家的群体原则逐渐与墨家的“尚同”观点、法家的“废私”主张相融合,经过不断强化而取得了支配地位,并成为传统价值观的主导方面,使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系统形成了重群体轻个体的特征张岱年等,1994:417。儒家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修己以安人”等主张,最终是为了实现群体的稳定和发展。在孔子学说中所倡导的由“仁”与“礼”进而产生出“人和”的价值观,所谓“礼之用,和为贵”,是群体原则在社会关系上的又一体现。由于中国文化中的自我理念并不强调个体的主体性,而是将自我看作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同构和共同参与者,因此在价值取向上形成了平衡和适度的原则,并且这种原则也体现在人们的行为规范、审美和语言表达等方面.如英语中有许多表现个人进取、个人力量和个人意志的喻体: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有志者,事竟成..Every man is the architects of his own fortune个人的幸福靠自己.You may have to blow your own horn应该吹自己的号角.The world is your oyster有志者,事竟成.If you lie upon roses when young, you will lie upon thorns when old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而在汉语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许多崇尚社团价值,无我精神的经典喻体,如:“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大公无私”、“人怕出名猪怕壮”、“树大招风,人大惹议”等等。
三、结论
不难看出,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已远远超出了自身的定义,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现象,而同时也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文化现象,它就像一本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不同文化内涵的亮丽风景线,让习者目不暇接,回味无穷。也为习者提供了一个了解不同文化的平台,使习者的视野在语言学习中变得更加深遂、更加辽阔。
参考文献:
1.顾嘉祖、陆晟、郑立信:《语言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中西文化范文6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教学 和谐主义图式 人类中心主义图式
一、引言
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教授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1]所以,要用和谐主义图式去指导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教学,促进文明间的对话与沟通,促进中西文化的和谐发展,帮助学生建构起和谐的跨文化交际图式。
二、图式理论
“图式”是指个人过去获得的知识、经验等在头脑中系统的、有条理的储存单元或方式,可分为语言图式(linguistic schema)、内容图式(content schema)和形式图式(formal schema)。文化图式(cultural schema),属于内容图式,是指以文化背景知识为基础形成的图式,它通过一种知识组织模式把人类先前的知识储存在大脑之中。中国文化中的和谐主义图式能够使不同文化和谐相处,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交流,有助于构建和谐的跨文化交际图式。人类中心主义没有摆脱二元对立的框架,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文明间的对立及跨文化交际的紧张局面。
三、和谐主义图式和人类中心主义图式的文化渊源
(一)以中庸为特点的和谐主义图式
《说文解字》对“和”的解释是:“和,相应也。”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尚书·舜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尧典》载:“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左传·襄》)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国语·郑语》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这些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谐”的概念,但是却蕴含和谐统一的思维倾向。“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中国古代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周易》整本书中,“和谐”如同是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周易》中的和谐就是差别甚至是对立基础上的统一,如乾与坤、阳与阴、高和低、天和地等。《周易》中的和谐既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又是人与社会的和谐,如它的阴阳和谐观念贯通天、地、人三才,希望实现天地通泰、政通人和。窗体底端
和谐是标志事物之间平衡稳定、协调有序的关系状态,如果把追求和谐看做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话,那么中庸的思维方法与追求和谐的思维方法是相通的[2]。《礼记·中庸》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可见和谐不是趋同,不是一刀切,而是有差别的平衡、稳定和统一。最重要的是在差别和对立中把握好“度”。《广韵》载:“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新书·道术》:“刚柔得适谓之和,反和为乖。”这些都是说要和谐就要把握好“度”。
可见和谐就是在差别和对立基础上的统一,它很好地把握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度”,正是如此丰富的关于和谐主义的思想,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和谐文化与和谐主义图式。
(二)人类中心主义图式
人类中心主义就是把人作为价值判断的唯一主体,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标准和依据。人类中心主义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古希腊辩士学派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到了近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中心主义随之膨胀。培根说:“哲学的目的是控制自然。”“呼吁‘人类的知识与人类的权利是合一的’要建立人对万物统治的帝国。”[3]笛卡尔则说“我思故我在。”
《圣经》在西方文化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圣经》中较为充分地体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卡森指出:“基督教教义把人作为自然之中心的观念统治了我们的思想。”于是“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事物的主人,认为地球上的一切东西——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连地球自身——都是专为人造的”[4]。“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就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的根源”,它鼓励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去对待大自然”[5]。“基督教鼓励人类把自身当成自然的绝对主宰,对于人类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专门为他安排的”。“这种对待自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的人类中心”[6]。
可见,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有很深的文化和历史渊源,正是因为这些文化的累积和沉淀,形成了一种固有的思维图式和思维结构——人类中心主义图式:考虑问题的利益出发点和道德价值的评价依据都是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为中心,很少顾及其他方面的利益。
“人类中心主义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坚持以人为中心,这相对于自然中心主义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它“削弱了人的社会性”,“加剧了环境危机”[7]。与之相反,中国的和谐主义整体思维图式,能够包容多元文化和多样文明,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因此,倡导和谐主义,用和谐主义图式指导跨文化交际,这是解决世界上的矛盾和冲突、保证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和平共处、建构不同文明间和谐的跨文化交际图式的根本途径,青年是祖国和世界未来的主人,用和谐主义图式指导我们的跨文化交际教学,并且作为同学们跨文化交际活动的准则,必将有利于他们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四、中西文化和谐及策略
(一)用和谐主义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缺点与不足
人类中心主义没有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图式,看问题存在“非此即彼”的片面性,过于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其他,而和谐主义能够包容事物之间的差别甚至对立,使不同的事物和谐相处。所以要在国内、国际大力宣传和谐主义,使和谐主义成为不同文明对话的行为准则,成为世界人民普遍接受的思想共识,以此消除由人类中心主义所造成的国家、民族间的冲突和对立,消除发达国家所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欧洲中心论等所造成的危害,建构起以和谐主义图式为基础的正确合理的跨文化交际图式。因此,在外语教学中,我们不能一味地去全盘照搬照抄西方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而是要教给学生积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用和谐主义理念去批判的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同时应该避免被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所同化。
(二)用中庸思想指导跨文化交际实践
中庸是和谐主义的重要特点和处事原则,要倡导中庸思想,就要把握好做事情的“度”,凡事“过犹不及”,跨文化交际是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因此要学习不同文明的长处,取长补短。一方面对于国学可以提倡,但要警惕“闭关锁国”,“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对于西学既要坚持学习,又要坚决抵制“全盘西化”的思想。因此,对于中西文化都要把握好“度”,倡导中西文化的和谐共存。教师应该引导学生经常运用中庸的思想看问题,讨论文化间的差异,同时增强同学们对于文化间的包容性,例如经常组织外语系的学生和外国留学生交朋友,结对子,增强彼此的理解和包容性,同时教导学生坚持原则,不应该崇洋。
(三)用“和为贵”的思想解决国家间的冲突和争端
“和为贵”,这里的“和”既是“和谐”又是“和平”,世界多极化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存的时代,各个国家和民族间的矛盾凸显,对于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力求通过谈判、协商、对话,解决争端,坚持国家间的“和平”、“和谐”,不应该一味地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在跨文化交际教学中,以及中国学生与外国学生的交往中都要坚持“和为贵”,学习容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矛盾甚至冲突。
五、结语
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复杂,要保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开展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教导学生正确的进行跨文化交际,就要用和谐主义图式指导我们的跨文化交际实践,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特别是人类中心主义,建构起“世界公民“的科学、合理、和谐的跨文化交际图式,使学生真正具备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进行和谐的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乐黛云.文化自觉与中西文化会通[J].河北学刊,2008,28(1):185-189.
[2]孙文营.中华传统思维对和谐社会建构的几点方法论启示[J].求实,2007,(12):47-50.
[3]培根.新工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114.
[4]Rachel Carson.Of Man and the Stream of Time(commencement address,Scripps College,Clarement,Calif.,1962),Carol B.Gartner:Rachel Carson,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120.
[5]Lynn White: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Press,1996: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