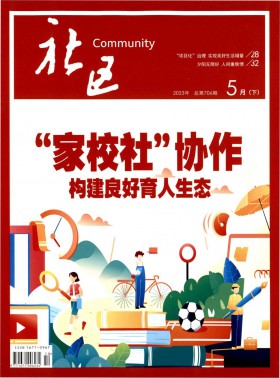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体系的革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第一,居(村)委会“内卷化”成为制约社区自治能力生长的组织因素。居(村)委会在社区治理和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居(村)委会既作为附属在城乡基层政权组织及其派出机构之下的准行政组织,又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双重身份,使其在承担完成政府交办的大量行政性工作和任务之余,无暇专注从事与居民自治事务有关的工作,从而无法履行“自治”这一应然角色。“‘内卷化’(involution)源于拉丁语,原意是‘转或卷起来’。主要含义是内卷、内缠、纠缠不清的事物,以及退化复旧等意。”3在社会学领域使用时主要用来描述一种不理想的变革、演化形态,即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严格约束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回顾近一二十年我国社区建设的探索经历,不难发现“在居委会的组织变革过程中,虽然新的组织形式要素(例如社区代表大会、居委会委员的直选等)已经产生,但居委会组织变革真正要指向的组织性质和实际运作机制却没有根本转变。”4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农村社区内部。居(村)委会“内卷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组织功能的行政化。这显然与培育社区自治力量的目标背道而驰。
第二,“乡土社会”情结成为阻碍社区共同体生成的文化因素。共同体的存在是实现社区治理的基础。共同体的生成依托于社区内部的共同关系和社会互动,或者叫做情感归属与传统认同。相对于西方的契约文化,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一直是源自宗族制度的“乡土社会”文化。传统社会里,社区共同体的形成往往是自发的。进入到现代社会,家庭结构核心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似乎正在消解“乡土社会”的文化影响力,但是就日益原子化的个体而言,这种影响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因为社会流动性的加快,在一些具体行为模式的表现上有所增强。例如:人们宁愿选择与远在千万里之外的亲友沟通,或者参加同乡、同学会组织,也不会想到去主动结识近在咫尺的邻居。这一方面说明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改变了人们旧有的居住方式,人与人的隔离感日渐加深。另一方面也深刻反映出“乡土社会”情结反而成为现代居住环境下阻碍社区共同体生成的文化因素。
第三,资金投入水平不高成为影响社区服务效能的经济因素。社区服务是社区治理体制的“产品输出”环节。产品质量高低直接反映了体制设计是否合理、运行是否健康。社区服务的发展离不开大量资金的支持。综观世界各国,社区服务资金来源呈现多元化特点。其中既有政府的财政拨款,又有慈善公益组织、公民的个人捐款,也有自治组织的自筹经费以及非营利组织适度的服务收费。我国社区服务资金筹集渠道则比较单一,主要依靠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资助拨款,而且资金投入总量偏低。如果考虑到东、中、西部和城乡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一些贫困地区的政府对于社区服务方面的财政支持更加困难有限。第四,社区治理主体权能配置模糊成为遏制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体制因素。现代社区治理模式的根本差异取决于社区治理主体,即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民众之间权能的配置方式。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践摸索,我国社区治理模式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但是也应理性看到,在经历最初运动式的社区建设热潮之后,各地社区治理模式创新进入了一个“瓶颈期”。说明在这一轮社区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转变尚不够彻底。该收缩的权力没有收缩,而是变相强化和扩张;该尽到的职责没有尽到,而是推给社会和市场。关于社区治理各主体角色定位的理论认知在学界和社会上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但是对于它们之间的权能配置关系始终没有给出一个准确定位。这成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向纵深推进的掣肘。
二、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目标与路径
社区治理体制创新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调整定位国家和社会的职能,重构基层政权与社区自治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努力构建的社区治理体制是结构合理、主体多元、运行有效的新型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内部,国家与社会均化身为不同的治理主体,来自政府的行政权威不再被无限放大,而是与其他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保持互动合作关系,共同目标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此,围绕体制改革创新的前提基本条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我国的社区治理体制创新。
一是营造民主政治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培育社区自治文化。西方文化体系中,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存在一个民间组织及其活动领域,叫“市民社会”,后来发展为“公民社会”理论。它是以契约关系为轴线,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宗旨的高度理性化社会。与此相对应,中国文化体系孕育发展出的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宗族制度和礼治秩序。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5基础上的“差序格局”文化。居(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除了地域共同之外,还缺乏构成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要素:共同关系和社会互动。因此,创新社区治理体制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产生创造条件。否则居(村)民的自治精神培养也就无从谈起。中国当下正在酝酿的民主政治改革将成为社区自治文化生成的一个契机。有学者提出,“民主政治的基础是个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民主是在尊重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多数决定,或者说是以多数决定来防止共同体的人格化身的为所欲为,从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一种机制。”6归根结底,个人民主权力的觉醒能够催生社区自治文化。因为只有参与有可能影响政府决策行为的活动,才有可能达到直接维护参与者自身权益的目的,也才会真正有效提升居(村)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意识。实现这一目标主要有赖于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二是依托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收缩社区行政力量。长期以来,人们把社区治理视为政府的一项行政职能。这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直实行的是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不无关系。收缩社区行政力量与培育社区自治文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行政力量在社区无限扩张的结果,只能是以其他社会力量的萎缩为代价。目前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以简政放权为要义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核心和重点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突破和进展。在改革的第一阶段我们实现了“政企分开”,发挥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这一关键阶段,我们的目标无疑是加快实施“政社分开”。社区治理体制要创新就必须先解决“政社分开”问题,这是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在社区治理层面,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构需要将该缩减、取消的行政权力交由具备资质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应严格界定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能边界,限制行政力量的过多过频介入。只有行政力量收缩了,社会力量才能伸展。
三是探索社区服务项目化运作方式,实现社区治理多元共治。社区服务项目化运作方式,主要是从微观层面探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项目化运作是使用一种专业方法和技术,实现基层政府、居(村)委会、社会组织、社区居(村)民协同服务社区的有效载体,是对传统服务方式的一种改革和创新。首先,项目化运作是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模式。项目开始之初,往往要先对社区服务需求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避免服务供需之间的脱节,可以使有限的项目资金效益最大化。这与政府主导下的某些“形象工程”、“参观工程”服务有了本质区别。其次,项目化运作为社会组织的能力建设提供了平台。通过实施服务项目,社会组织获得一定的权力、资源和空间,其发展壮大对于社区治理的多元共治格局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最后,项目化运作可以使得政府在社区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地借助社会力量,通过购买服务关系,切实转变职能。
作者:张静 单位: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