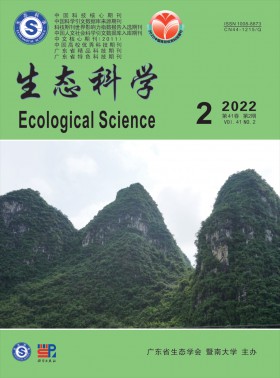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下的喜福会,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谭恩美是当代华裔美国作家中声望颇高的一位女作家。她的处女作《喜福会》一经推出,就引起了美国文坛的关注并获得多个重要奖项。《喜福会》包括16个相互交织的小故事,以四位中国移民母亲与美国长大的女儿之间的文化冲突为素材,描述了华裔美国女性在中美两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过程中对其身份的认知和寻求的心路历程。 目前,华裔美国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成为学者们越来越关注的焦点,对《喜福会》的研究论文多集中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上。生态女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妇女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这一名词最早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西丝娃•德奥博纳(Francoised’Eaubonne)于1974年在其著作《女性或死亡》(LeFeminiseouLaMort)中提出。后期随着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也开始在文学领域内对自然和性别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应将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和父权制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态度联系起来,因为两者都是男权社会压迫的对象,倡导建立一个两性和谐、物种平等、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 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批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的开放性、交叉性和宽泛性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方法。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这个崭新而独特的视角解读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剖析华裔女性在重重压力下不断找寻和实现自我身份构建的过程。 一、女性和自然 德奥博纳在其《女权主义或死亡》(LeFeminiseoulaMort)中指出:“对妇女的压迫与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天然的联系”(高利,徐玉凤,2009:36)。这一观点首次在女性和自然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并为女性的社会存在以及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批评视角。生态女性主义者们相信女性与自然之间有极大的亲近性。“大地之母”的理论展现了女性与自然的相联性,女性也是弱者一方的代表,她们也遭受着压迫和统治,她们“代表了父权统治下人类社会中的他者,她们在公众场合中被迫缄默,成为社会的二等公民”(高利,徐玉凤,2009:38)。生态女性主义通过深入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关系,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压迫性结构,为我们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建立新型平等关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一)《喜福会》中“父权制”下的女性和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卡伦J.沃伦(KarenJ.Warren)认为,在西方“父权制”文化中,统治女性与统治自然之间有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父权制”世界观。父权制表示一种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性不平等的制度、父权制就是将男性身体和生活模式视为正式和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它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二元思维方式、价值等级观念和统治的逻辑。从众多的关于父权制的定义来看,在西方的学术话语中“男权制”与“父权制”完全重叠,可以视为同义词(孙刚,2010:139)。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是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妇女,森严的父权制文化使她们处于社会边缘地位,使其沦为男性统治下的局外人,牺牲品,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父权制”社会要求女性成为以父权至上,具有牺牲精神,无条件的服从男性统治的配角。她们在醒悟前,扮演的都是忍气吞声或沉默,或优柔寡断,牺牲权利、自主、甚至自我生命的角色。例如,安梅母亲第一个丈夫死后改嫁,已是件丢脸的事了,更不用说嫁给人家当小老婆了,而她丈夫,作为男人,却可以妻妾成群,而不受任何指责,但是由于中国父权社会持有顽固的贞操观念,安梅母亲与安梅的外婆,断绝了关系。映映的奶妈告诉她,女儿家不能问,只能听着,以这种方式把父权制社会下的妇道传授给她,并向她灌输了悲观消极的处世哲学。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虽然从小在美国文化的灌溉和熏陶下成长,但也遇到了父权制社会下的压迫。当韦弗利在唐人街的公园里找老头下棋的时候,没人愿意同她下棋:他们告诉她,他们不想和小女孩玩,看到她能在男人擅长的游戏中表现不俗,还感到非常惊讶。罗斯对特德逆来顺受,按照固定的性别角色行事;男人要有主动性,要英勇无畏,女人要温顺,甘做牺牲品。莉娜帮丈夫成立建筑设计公司,答应只做个副手,并同意只拿他工资的一部分。她的这些行为都是因为她接受了父权制社会下所鼓吹的妇道。 无论身处传统的东方还是现代的西方,无论是母亲们还是女儿们,作为女性,她们都生活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尤其是,作为华裔女性,她们身处男权社会和白人统治的双重压迫,被美国主流文化所排斥,在西方人的眼中她们依然是“他者”。这些女性们生活压抑,渴望自由、平等、独立、却苦于找不到生活的出口,最终不得不以生命为代价挑战父权制度,为女性呐喊,生命回归自然,以此向男权中心文化抗议。 (二)《喜福会》中女性与自然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指出,女性与自然交织融合,密切联系,这种联系包括符号上或象征上的,经验上或地位上的联系。《喜福会》中女性与自然也是密切联系的:女性是自然细心的呵护者,而大自然是女性的避难所和力量的源泉,他们相互慰藉,又相互依赖。《喜福会》中围绕天鹅、红烛等自然意象来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以此来揭示女性梦想借助自然的力量,实现自己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天鹅:小说中包含着一个丰富的意象,这一意象贯穿全文。如今她已经上了年纪了,却依然清晰记得,好多好多年以前,在上海,糊里糊涂地出了个大价钱,从菜市小贩手里买回一只所谓的天鹅,这只给小贩吹得花好桃好、天花乱坠的‘天鹅’,伸长着脖子扑棱着翅膀拼命地挣扎着,就像丑小鸭一心想折腾成天鹅一样……说也怪,后来它倒也真有几分优雅动人,令人简直舍不得在宰了下肚。———谭恩美,2010:3#p#分页标题#e# 这一故事象征着母亲在旧中国的悲惨经历和她们对新生活的渴望,,还预示着女儿将像天鹅一样出类拔萃,不负众望,在充满机遇的新国家里成长。可是,当这位妇女抵达美国的时候,移民官没收了天鹅,使这位妇女最后只剩下了一根天鹅毛,这不仅象征着母亲同祖国的联系被无情地切断了,而且还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创伤,并暗示华裔女性在种族歧视下的压迫、孤独、恐惧及愤怒的情感体验。 红烛:琳达结婚时,与丈夫点燃了一支两端带有烛捻的红烛。烛的一端刻着新娘的名字,另一端刻着新郎的名字。如果红烛燃了一夜,两端都没有提前灭,就意味着这桩婚姻将会美满。在中国文化中,红烛的象征意义———“美满姻缘”。但在故事中,红烛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它体现了有关婚姻大事上的一些古老习俗和观念。 琳达吹灭了蜡烛,就是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手中,终于使自己摆脱了这桩不幸的婚姻。因此,红烛也象征自己当家作主、自己把握自己命运。红烛首先是传统的象征,其次是个性变现的象征。最后象征着利用这个传统习俗取得独立人格和个人权利的行为。 二、《喜福会》中华裔女性自我身份的求索 小说塑造了母女两代人在美国这个白人至上的社会中生存的感受以及他们在遭遇中美两种文化撞击时的尴尬境遇和抗争,集中展现两代人在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相融的愿望,展现了处于两种文化背景、两种民族精神影响下的华裔美国女性独特的心路历程。 《喜福会》中的母亲们是第一代移民,中西方文化冲突在她们身上体现的最为显著。她们虽已身处异国,却仍是彻头彻尾的中国女性,因为她们每一个人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灌溉。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母亲们采用中国语言、中国思维、中国行为方式,把自己封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她们拒绝、排斥美国主流文化,她们把美国准则当成嗤之以鼻的“游戏规则”。她们身上处处烙下中国的印记,但她们这些独特的生活方式在西方人甚至是自己女儿的眼中则是另一番情景。例如,对于“喜福会”的成立,母亲们认为:“我们每个星期都有一次期盼,期盼着一次欢悦,这种期盼心情就称为希望,成了我们唯一的快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自己的聚会命名为‘喜福会’(谭恩美,2010:11)”。对母亲们而言,喜福会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它还能够使社会团体得到改造、使爱的方式、养育方式以及环境都得到改变。而女儿们则一直以为“喜福会是一个有着令我感到脸红的,许多魑魅荒唐的中国陈规习俗的社团,好比三K党的秘密集会,或者电视中那些印第安人出征前围着火堆跳通通舞,反正有着一套什么繁琐的仪式(谭恩美,2010:15)”。女儿们把母亲的习惯和品位都当成过时的东西,甚至觉得可笑。可见母亲们在美国社会完全处于他者的地位,她们切身经历着两种文化的强烈对撞与冲击,导致自我身份的迷失与分裂。 母亲与女儿无法推心置腹地交流,最终母亲们不得不发出感慨:“我还生了一个女儿,她似与我隔着一条河,我永远只能站在对岸看她,我不得不接受她的那套生活方式———美国生活方式(谭恩美,2010:245)”。这就是华裔美国母亲的困惑。她们在等待着与女儿的相互理解,却又知道这种等待只是徒劳,像期待夏荷与冬雪共舞一般。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的基因是中国的,但她们是由“可口可乐和意大利面喂大的”,她们在美国主流文化的教育下成长,她们的内部全部由美国制造。她们不了解中国,她们把中国式的文字称为一种游戏,一种措辞技巧的卖弄。正如精美说:“在中国,十分注意措辞和用词,即使是反对的意见,也要尽量使之婉转含蓄,不要显得太唐突地表示出来,这一套我是永远学不会的”(谭恩美,2010:6)。女儿们也笃爱着自己的母亲,却不能忍受中国母亲的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母爱。因为“中国母亲对孩子的爱,通常不是表现在拥抱和亲吻上,而是坚定而又不断的,给他们蒸汤团、煮鸭肫和螃蟹……”(谭恩美,2010:201)。女儿们对中国母亲的填鸭式喂食,一心一意望女成凤而丝毫不尊重女儿们个人的意愿,那种专横而又慈爱的干涉,令美国女儿们哭笑不得,有时也恼怒不已。因此,从小她们就不得不苦苦地为自己的一丁点独立和权利而与中国母亲们抗争着。从抗争下做个神童宁可做个普通孩子,直到结婚后离婚这样的大事,都不愿母亲来干涉。 无论女儿们的思想情感、行为举止多么美国化,她们还是华裔:她们身上有东方女性的根脉。尽管对自己“根”的文化不甚了解,甚至排斥,然而有意无意间,传统的文化总会悄然袭来。女儿们的双重文化身份注定她们挣扎于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错中:“我看着镜中我们母女俩,我又想到自己的为人处世的准则,我实在弄不明白,哪个是中国式的,哪个是美国式的。反正我只能两者舍其一,取其一。多年来,我一直在两者中徘徊,考虑取舍”(谭恩美,2010:260)。女儿们既不愿完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又不能完全融于美国主流文化之中,她们常常被“边缘人”的无归属感所困扰,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迷惑、彷徨。她们被主流文化视为他者,她们自身由于内部殖民的精神烙印排斥母亲和其所代表的文化,但最终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的身份危机。 总之,《喜福会》中的母亲们生长在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在她们的身上根深蒂固,挥之不去;而女儿们是在迥异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环境即美国主流文化的灌输下成长。对处于种族、文化夹缝中的中美母女而言,她们之间的对立不仅仅是两代人的冲突,而是隐藏在其背后的中美两种文化与价值观的冲撞。因此,她们根本不会成为纯中国式,或纯美国式的人。 三、和谐社会———自我身份的重塑 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既是“生态的”,又是“女性的”。生态批评基于生态思想的基本原则,即整体、和谐、多样化又相互依存的原则,批评文学作品是否有助于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是否有助于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及是否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均衡。生态女性主义旨在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以改变自然和女性等在当今社会受到压迫的群体的从属地位。#p#分页标题#e# 《喜福会》中的母亲和女儿们都经历了从认同单一文化到认同多种文化混合体的心理过程。尤其是女儿们超越了非此即彼或妥协认同的认知方式,其文化内蕴上远远超越了前代华裔女性形象。在小说的结尾,精美说:“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一部分中国血液了。呵,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国的基因,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开始沸腾昂起(谭恩美,2010:279)”。这印证了精美的母亲之前说的“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这种感觉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腾的时刻。”(谭恩美,2010:261)这充分说明了她们在理解对方之后,消除了母女两代人的隔膜,及其背后所代表的中西方二元文化的对立,使中美文化加以交汇和融合,从而走出夹缝中他者的形象,构建了兼具中美两种文化身份的独特自我。 谭恩美通过母亲讲故事的方式体现了其深层的意图:让她们代表华裔女性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华裔美国女性的形象从模糊到清晰,从弱势边缘的地位勇敢地走向与主流文化和男权社会的对话,从中国血统、美国国籍的矛盾和困惑中逐渐醒悟,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和交融中寻求平衡,以自身的独特气质和聪明才智稳稳地站在了主流文化的群体之中,成为了耀眼瞩目的新星,引导人们从生态整体观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履行保护自然、重建生态平衡的责任,最终重返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四、结论 《喜福会》承认差异,不回避冲突。它坚信,经过碰撞与摩擦,不同文化最终会达到融合;不同文化的人最终将跨越文化上的鸿沟,达到互相沟通与和解。通过剖析中美文化的差异,加深了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有助于人类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在跨文化交际中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并为身处在多元文化中,少数人群对自己身份困惑与抉择提供有益的参考指导。华裔女性只要打破文化和性别的沉默,按照自己独特的方式自信、自主的生活,必能实现华裔女性身份的重塑,最终进入“喜”与“福”的境界,从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