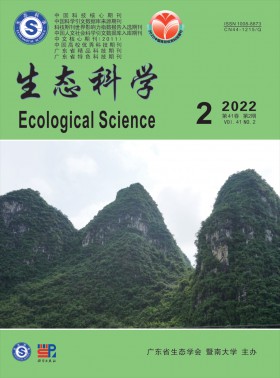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生态女性观下对菊花的解读,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约翰﹒斯坦贝克(JohnSteinbeck,1902~1968)作为20世纪蜚声美国文坛的作家和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生为美国及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声誉主要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中、长篇小说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4次作为欧•亨利短篇小说奖的得主,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亦出类拔萃,收录在《长谷》中的短篇小说《菊花》就是这样的典范之作。斯坦贝克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在萨林纳斯山谷的生活经历以及后来和海洋生物学家———爱德华•里基茨的交往使他对自然环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并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其作品中常见对大自然充满生命力的描绘,表达了斯坦贝克对自然的热爱和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因此,许多评论家说他“既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又是一个环境论者”[1]。同时,他具有强烈的性别意识,斯坦贝克凭着他对女性的敏感,在《菊花》中,细致地刻画了伊莉莎这个角色。在《菊花》中,斯坦贝克笔下的自然和女性有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女主人公伊莉莎把大自然作为潜意识活动的平台,用爱来呵护自然,同时自然也为伊莉莎提供追求女性自我意识的原动力,她们之间有一种和谐的生命共感。然而,在父权制社会中,她们又不可避免地承受着悲剧性的命运。 一、生态女性主义述评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其主要观点是:“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2]在西方的指涉系统中,女性同自然俱属弱势的集合概念,而且相互指代和象征。女性身体成为自然土地的意象,自然也被赋予女性的特质———都是男性“播种”的被动接受者。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人类”暗指男性。基于以上事实,生态女性主义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乃是男性中心主义,是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超出人类社会在整体生态范畴的衍化。”[3]痛感于现今的生态危机和女性的边缘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力图颠覆压迫性的男权中心主义,并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理念。他们反对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大力宣扬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所在。”[4]同时,“生态女性主义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这个当前社会的异质空间尊重差异,强调相互依存,以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社会)的维护而非发展为终极目的。显而易见,拥有浓重群体意识的生态女性主义是向女性美学的复归,它彻底否定男性个人主义,倡导女性的‘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ty)。继而,女性﹑自然以及她们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贬抑性的概念指代,而是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5] 二、对《菊花》的文本解读 《菊花》自发表以来就受到批评家的好评,被誉为“斯坦贝克在艺术上最成功的小说”[6]、“世界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7]等。其情节并不复杂,讲述的是加利福尼亚萨利纳斯山谷一个农场里一对夫妇在特定的一天的生活,以及发生在女主人公伊莉莎与一位流浪补锅匠之间的故事。伊莉莎是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35岁,热爱并擅长种菊花,和丈夫亨利一起过着平淡的日子。在平淡的生活中伊莉莎的内心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向往。补锅匠的来访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也在她原本就不平静的内心世界激起了波澜。她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位理解并欣赏自己的人了。于是,她把她所珍爱的寄托了她渴望和梦想的菊花交给了补锅匠,内心世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和强大。然而,后来当她和亨利驾车去萨利纳斯时却发现菊花被抛弃在路边,花盆却被拿走了。伊莉莎失望至极,躲着亨利像个老妇人似的哭了起来。 故事的情节虽然简单,但里面刻画的人物却是丰富而又深刻的。就像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内涵时,斯坦贝克在给乔治•阿尔比(GeorgeAlbee)的信中提到的那样:“他(读者)不经意地读完故事后会体会到某种很深刻的东西,但却说不出是什么东西,怎样深刻。”评论家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挖掘故事中的那种深刻的东西及其原因,主要集中在女主人公形象分析和菊花象征意义解析两个方面。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伊莉莎和自然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关系,揭示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中女性和自然遭受男性压迫和掠夺的悲剧,解读作者对自然和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 (一)伊莉莎与自然之间精神的耦合 “由于具有创造和养育生命的能力(像大自然那样),女性历来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灵更适合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8]斯坦贝克在《菊花》中对伊莉莎进行刻画时,把她安置在大自然中,来探求伊莉莎和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试图像生态女性主义者那样“对所谓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在生物学和精神上)神秘的亲和关系的复原”[9]。在《菊花》中,伊莉莎与自然有一种认同感,她以一种具体的﹑爱的行动与自然相连系。 伊莉莎精心地呵护着菊花,她是菊花的护卫者和保护者。菊花在她的精心照料下,枝叶繁茂,“没有蚜虫、土鳖、蜗牛和夜盗蛾。她能在虫子还来不及跑动前就将它们杀死”[10]。为了更好地保护菊花,她还建起了围栏“挡住牛、狗和鸡不进入菊园”[11]。伊莉莎是菊花的照看者,在某种程度上她把菊花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她用镘刀把土壤翻了几遍,然后又将其整平和拍打结实。”[12]如此的细心﹑温柔,举手投足中散发着爱,体现着慈母形象。当她把菊花托付给铜匠时,她把菊花放进了“一个崭新的红色的大花盆里”[13],足以看出她对菊花的爱护和珍视。伊莉莎还是菊花心心相印的密友,她可以敏锐地体会到菊花的感觉并且她尊重菊花。当她告诉铜匠如何去掉不想要的花芽的时候,她说:“手指能发挥他们的最大作用。他们能凭感觉去把一个个的芽子掐掉,从来不会出错。和植物在一起,你明白吗?我是说手指和植物在一起,你的胳膊能感觉到的。胳膊有感觉,从不会出错。”[14]在和菊花即将分别时,伊莉莎非常不舍。“她把花盆递给他,缓缓地放在他的胳膊上说:‘好啦,放在车上,放在你看得见的地方。’”[15]#p#分页标题#e# 伊莉莎自己就是菊花。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权统治在压迫‘自然化的女人’的同时,也在压迫‘女人化的自然界。’”[16]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下,就像菊花一样,伊莉莎渴望自由﹑空间﹑关爱﹑理解以及尊重。当亨利提议:“星期六了,我看我们下午去萨林纳斯镇,去一家餐馆吃饭,然后看电影,庆祝一下好吗?”[17]伊莉莎热切地回应着“好,当然好啦!”[18]这对她来讲是一次很好的放松机会,可以暂时摆脱农场生活的枯燥、乏味,呼吸一下外界的自由气息。伊莉莎已经与菊花相融,她对菊花的认同﹑爱护和维持达到了虔诚忘我的程度。当伊莉莎得知铜匠可以帮菊花带来一个更好的环境而且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时,她激动地跑到房子的后面,在移栽菊花的时候“忘记了戴手套,跪在沙地的一头,用手把沙土挖起来,捧进刚取出的崭新的花盆里”[19]。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菊花承载着她的梦想,寄托着她的期待和渴望。大自然蕴涵的催人自新的力量可以调和个人内心一度失和的生命节奏,可以使伊莉莎迷茫沉沦的灵魂重获新生和喜悦,最终两者相互融合感应,达到天人合一般的共振。 伊莉莎和自然的亲密关系也体现在她对动物的态度和与动物的关系上。西方人认为,动物是人类和上帝的桥梁,它们要比人类更加接近真理。她并不认同亨利和铜匠把动物当作利己手段的男性个人主义行为。当亨利在她面前炫耀“我卖了三十头有三个年头的菜牛。几乎赶上我要的价”[20]时,伊莉莎并没有像她的丈夫那么高兴和兴奋,只是平淡地回答到:“好啊,对你讲是件好事。”[21]她具有泛亲属意识,对她而言,动物不只是对男人而言的谋生手段,在某种程度上,动物是她忠诚的护卫和伴侣。当铜匠和他的队伍突然闯入伊莉莎的农场,他的“杂种狗从轮下跑出,冲到前面”[22],给伊莉莎的安全带来威胁时,“即刻,两只牧羊犬迎了上去”[23],给伊莉莎一种安全感。伊莉莎和铜匠告别在那里低语时,“突然,她被自己的低语声吓呆了。她放松了一下身子,四周看看有没有人在听。只有狗在那里叫。狗从地上爬起来,抬头看着她,然后又伸长下巴睡去了”[24]。当伊莉莎遭到男性世界的排斥,成了失语的边缘化“他者”时,只有动物才愿意倾听她的心思,解读她的思想。伊莉莎的女性特质和自然之爱具有生态女性主义特征,体现了关爱﹑相互依存和无私利他的价值观。 (二)男权制压迫下伊莉莎与自然的悲剧命运 生态女性主义学者萝特认为:“父权制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对自然界主宰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25]“实际上大多数妇女都敏锐地意识到当一个人被忽视、轻视,变得不重要时会是什么感觉。也许就是这方面的经验使她们对其他边缘群体,包括动物,在自己的观点很难被别人听取时更加敏感。”[26]女性和动物之间,女性和自然之间以及他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共同经历的压迫由于交流的缺失会使她们变得越发痛苦。 在小说中,伊莉莎对自由的向往和生活的改变寄托在菊花上。她深感压抑,她渴望尊重﹑自由﹑平等和交流,但是她丈夫对此却浑然不知,他不知道如何和伊莉莎交流,更无法触摸伊莉莎心灵的每一个角落。 在生活中,亨利扮演的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支配型的男性角色。对土地掠夺式的开垦,急切地出卖牲畜以获得经济利益,对机器的着迷和尊崇,以及对女性角色的既定和约束,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这一点。对于亨利而言,女性就像自然一样是可以被控制和被征服的。他已经习惯了伊莉莎的顺从和附属,伊莉莎和他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必须要服务他、取悦他的。亨利不仅想控制住伊莉莎的身体,还想控制住她的思想。 铜匠的出现似乎给伊莉莎的生活带来转机。伊莉莎本来以为铜匠能知道自己的需要而且理解自己的思想,她梦想着铜匠能改变自己的生活。然而,不幸的是,铜匠本人也是父权制的代表。他讨厌被别人、特别是被女人质疑﹑贬低。作为一个男人,铜匠认为自己永远都不应该在征服女性和自然的过程中让步或退却。当伊莉莎说“你的车子是走不出沙路的”[27],他立刻回答到“你可能不知道,这些牲畜挺行的”[28]。这一点足以证明铜匠非常急切地想展示自己的权威和统治力,动物在他的眼中仅仅是施加权威和施展统治力的工具。 作为一个自私和飞扬跋扈的人,铜匠根本就不在乎伊莉莎是否被羞辱或者如何受到了伤害,他所在乎的只是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利用了自己的小花招骗取了伊莉莎的同情、欣赏和金钱。当他达到自己的目标时,他就再也不在乎伊莉莎的感受,也不想费心和她交流了。当伊莉莎问他为什么说他的那种生活对女人不合适时,铜匠说:“我不知道,夫人,我当然不清楚。”[29]这时,他已经失去了对伊莉莎的耐心。在铜匠的眼里,女人应该按照她们被设定的角色来做事。当伊莉莎的自我意识被激发并向他发出挑战时说:“说不定你会碰上对手的,我也能磨剪刀,也能把小锅的凹痕敲开,或许我能给你看一个女人能做些什么。”[30]他警告伊莉莎说:“对女人来说,这是很寂寞的生活,也很害怕。”[31]在他看来,只有男人才可以作为征服者和胜利者。在他的世界里如果把他和伊莉莎的短暂相逢看成是一场较量的话,那么只有他才是胜利者。 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的共同特征,那种认可性别压迫的意识形态同样也认可了对于自然的压迫[32]。在亨利的眼里,菊花没有任何的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因此,他排斥菊花,希望伊莉莎能改种苹果;对于铜匠而言,菊花就像另一个人的寄托和梦想一样,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实际价值,因此,他抛弃了菊花,留下了花盆。伊莉莎和菊花都经历了相似的悲剧,她们在父权制社会里被剥夺、被贬抑、被排斥。 在父权制社会里,动物也难逃悲剧命运。它们仅仅被当成可以满足男人需要的物体,被开发、出卖、利用和虐待。铜匠的马车“拉车的是一匹衰老的栗色马和一匹矮小的灰白相间的驴子”[33]。尽管这些动物对于铜匠来说是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爱,“马和驴就像没浇水的花一样耷拉着身子”[34]。动物的悲剧命运不止于此。当亨利开着“小型敞篷汽车在河边的土路上颠簸前进时,鸟和兔子都惊恐地逃进林子,两只鹤使劲地在柳树间拍打着翅膀,落在河床”[35]。#p#分页标题#e# 尽管《菊花》的篇幅有限,它也提供了一些信息证明了这一点。在故事的开篇,“冬天萨林纳斯山谷灰蒙蒙的浓雾高高地悬在空中,遮住了天空,也将山谷同外界隔离起来。雾停留在四周的山脉上,宛如给山谷扣上的一口黑锅”,“东南方向吹来的一阵微风给农场主们带来了小小的期盼,说不定不久会有场好雨。但是,有雾的日子往往不会有雨”[36]。这些描绘萨林纳斯山谷的苍凉的画面,揭示了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恶化。 《菊花》中伊莉莎和自然的悲剧是由当时所处的年代以及工业化所造成的。她们都是工业化进程波及乡村造成社会分化的受害者。20世纪30年代,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为主,植被被大面积毁坏,土地及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大平原地区常见的景象是,当大风刮起来时,灰尘漫天飞舞,遮天蔽日。同时,在加利福尼亚萨利那斯地区,机械化带来了一种新的耕作方式,但是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斯坦贝克经常亲眼目睹的事实是:农业工人的贫困,基本食物价格的上涨,还有大范围的失业。当时尽管已经出现了第一位内阁女部长,女性意识开始觉醒,但是在这样的自然﹑经济及社会背景下,谋生成了人们的首要任务,这样“人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故事里的两个男人表现出的对待生活的实用主义﹑叛逆以及对抗性的态度”[37]。因此,自然和女性被剥夺、贬抑和排斥,共同承受悲剧命运。 在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看来,女性与自然关系源远流长,与自然相对立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建立,加深了对女性的压迫。“人类对于自然的侵犯等同于男性对于女性肉体的侵犯。”[38]因此,当妇女行动起来反抗对于生态的破坏和蹂躏时,很自然地意识到男权统治在女性压迫和自然压迫两者当中所起到的相似作用。 斯坦贝克在《菊花》中,通过对与自然息息相通的伊莉莎这一角色的刻画,借助伊莉莎和菊花精神上的情结关系,以亨利轻视菊花和无视伊莉莎的情感生活与铜匠骗花、弃花的行径作为隐语,暗示男性从征服自然到控制女性的殊途同归,展现了父权制下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困境。 在小说中,作者倾注了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关注,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觉察到了压迫女性和压迫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他对自然﹑性别这些生态女性主义者所关注的主题的探索中,展示了拓展的﹑进化的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体现了解放女性与自然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或许希瓦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只有一条路可以拯救和解放自然,女性和男性,那就是针对所有物种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以及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