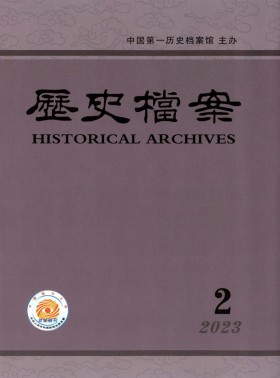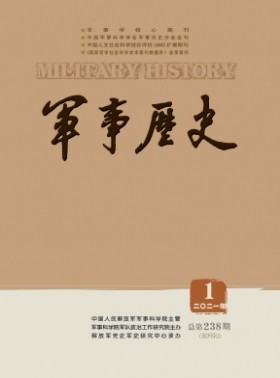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谈历史文学艺术想象,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再造隆想象与创造性想象
本文所说的历史文学想象,按心理学的观点“就是我们的大脑两半球在条件刺激物的影响之下,以我们从知觉所得来而且在记忆中所保存的回忆的表象为材料,通过分析与综合的加工作用,创造出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过程。”〔‘〕由于想象致力于“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所以它比之于联想更具创造性,在整个历史文学创作过程中也显得尤为重要,向来作为作家进行思维活动的主要形式和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至今我们见到的历史文学作品,包括自诩为“无一字无来历”的冯梦龙和蔡东藩的《东周列国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在内,可以说没有一部是没有想象参与的。据说有人统计过,郭沫若的十八部史默包括取材于历史的诗剧)共创造了120多个艺术形象,其中28个便是作家通过表象为材料,想象创造出来的。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以“致辞者”的名义说过一番传诵千古的精彩言词:“在座的诸君,请原谅吧!象咱们这样低微的小人物,居然在这几块破板搭成的戏台上,也搬演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难道说,这么一个‘斗鸡场’容得下法兰西的万里江山?还是我们这个木头的圆框里塞得进那么多将士?……让我们就凭这渺小的作用,来激发你们庞夭的想象力吧。……把我们的帝王装扮着象个样儿,这也全靠你们的想象帮忙了;凭着那想象力,把他们搬东移西,在时间里飞跃,叫多少年代的事迹都塞在一个时辰里。”以一个“斗鸡场”之大的舞台,容纳法兰西的万里江山,把帝王“搬东移西”,让其“在时间里飞跃”,这就是想象的特点,也是想象的功能所在。历史文学的想象按其内容的新颖性、独立性和创造性的不同,可以分为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两类:“再造想象是根据词的表述或条件的描绛图样、图解、说明书等),在头脑中形成这一事物的形象。创造想象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的形象。”仁“〕在历史文学创作及欣赏中,这两类想象各有侧重,同时又互相联系,彼此渗透。
再造想象可以以《三国演义》为例。这是因为这部作品七实三虚,虽有不少人事对史实作了超越式处理,但总体来看,其故事情节的基本框架和人物形象的基本貌态多来自历史,是在历史原型基础上加工创造的。题材对象对作家的想象活动具有客观的制约性,并且规定着他想象的范围和内容。当罗贯中对现成历史素材之在头脑形成的种种表象进行分解、综合处理时,他虽然也动用了作家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知识积累、形象记忆和情绪记忆去加以领会、体验和补充,不只是对对象本身进行简单接受和原封不动的复制;但是,作家在综合转化时,着眼点却放在一个固定的历史对象身上,他通过对表象的综合在脑中再造出来的形象,与已有历史对象是基本相近或一致的。小说中六次重大战役:十七镇诸候讨伐董卓、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诸葛亮征南夷的所谓七擒七纵和六出祁山即北伐曹魏,除六出祁山历史上是二出祁山、五出汉中以外,大都符合历史记载。且以作为“智慧”化身的诸葛亮来说,历史原型到文学典型,经过了历代艺人和作家的再创造,两者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形象的主要经历和思想性格的基本方面,包括政治思想军事观点、用人路线、治学态度、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等等,也都符合和接近历史原貌。即或是改动最大、被不少人视为“歪曲”了历史真实的曹操,他的“奸诈”一面的塑写,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史料可凭,作家只是作了强化突出而已,并非纯粹无中生有。冯骥才在谈《三国演义》等作品的人物塑造时说,把历史人物作为主要人物放在前台表现,这“有如填词,只能在规定的字句和韵脚里创造。”闭用“填词”一词来形容和概括再造想象并不妥当,但确也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再造想象的性质和特点,这就是它必须根据历史原型的规定来展开想象,契住题材对象的基本属性进行再现组构。为此,再造想象的成功与否,与作家选取的题材对象是否鲜明生动、丰富多彩常常关系极大。
创造想象虽然也来源于客观历史,要以历史中获得的表象作为基础,但由于它的表象运动方式不是对已有某一固定客体对象再现式的重造,而是出自对不同对象或多个对象此一部分、彼一部分抽取复合的表现性的改造,所以往往具有极大的自由性、能动性、创造性,是历史文学创作构思活动中最重要的心理因素之一。创造性想象是多个客体的一种创造性的综合,它的“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鲁迅语)这是根据典型化原则的一种新的合成创造。例如姚雪垠《李自成》中的红娘子,就是作者创造想象的产物,明末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人物。作者写她,实在不是有什么历史依据,他只不过按照可然律、必然律对多个历史对象的表象单位加以集中典型罢了:“虽然红娘子是一个莫须有的人物,但是自新莽时代直到清代,妇女参加农民起义的史不绝书,而有些妇女竟是起义的发难人和领袖,这就给我提供了塑造红娘子的历史基础。”〔峨”历史文学中的虚构性人物的塑造,其思维活动的形式,都可归属于创造性想象的范畴。不仅如此,创造性想象在进行表象分解、综合的实践过程中,还常常对原有客体对象作富有意味的夸张和形变,以期造成奇特、独创的审美效果。此一特点之作,罗丹的雕象“乌谷利诺父子挨饿”可谓一绝。这是这样一种景观:暴君乌谷利诺父子被起义者囚禁在高塔里活活饿死,他的一个小儿子刚断气,另一个还在凄惨地挣扎;乌谷利诺对儿子的哀号充耳不闻,却伏在已死儿子的身上,准备用尸肉充饥,但是又下不了口,瘦削的脸孔在抽搐,内心深处兽性和人性正在进行剧烈的格斗。罗丹这座雕象,是在看了法国加尔波同题材的雕象后才创作的。加尔波的雕象,刻画的是另一种景观:乌谷利诺的两个儿子已经饿死在他身旁,他肝肠寸断,呼天号地。罗丹叹息加尔波糟蹋了这个惊心动魄的题材。他用自己成功的实践将加尔波的创作大大提高了一步。而罗丹这所以如斯,他的秘诀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创造性想象强调甚至夸张客体特征的缘故。
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对于历史文学创作及欣赏,都同样重要。它们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有时候不仅在具体一部作品,就是在具体一个情节、具体一个人物的描写上也往往兼而并用,互相胶合在一起,纯而又纯的再造想象或创造想象是很少的。这一点,我们只要举一个极简单的例子:中国历代绘画中的不知有多少人画过的“屈子行吟”、“昭君出塞”、“竹林七贤”、“渊明采菊”、“太白醉酒”、“东坡泛舟”等等,但除了仿制,从来不会有两幅画完全一样。这些画,从根本类型上说应属于再造想象,然而它们却又或多或少地参用了创造想象,得到了创造想象的有益补充。自然,无论何种想象,它们只是思维形式差异的标志,彼此与作品的价值没有必然的联系。近来有的同志根据史实含量多少来对新时期历史文学归类时,有意无意地贬再造性想象而扬创造性想象,似乎历史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务虚含实、只虚不实。虚的含量愈多,作品价值愈高;反之,价值就愈低。且不说这样的概括不符合历史文学实际,就是从想象的本体角度看也解释不通。这实质上是将思维形式和艺术价值混为一谈,简单划上等号。不过,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注视,当作家在进行这两种想象活动时,他们面前确也有着一个容易失足的陷井值得警惕。#p#分页标题#e#
对于再造想象来说,审美化的问题是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鉴于再造想象是以现成的历史素村为依据,表象运动方式是对某一固定对象的复归为趋向,故也常常使一些庸常和好走捷径的作家无意滋生了“吃现成饭”的惰性思想。中国明清以降的历史小说在这方面是有深刻的教训的。经们之中相当一部分,不是把再造想象纳入“审美化”的机制而是纳入“史学化”的轨道,结果再造想象就蜕变成了简单的“补史”而失去了形象思维的特性,出现了鲁迅所批评的,’大抵效《三国志演义》而不及,虽其上者,亦复拘牵史实,袭用陈言,故既拙于措辞,又颇惮于叙事”的通病。〔5〕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就曾引证当时悲剧诗人即广义上的历史文学作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悲剧中,诗人们却坚持采用历史人名,理由是:可能的事是可信的;未曾发生的事,我们还难以相信是可能的,但已发生的事,我们却相信显然是可能的;因为不可能的事不会发生。”这些悲剧诗人完全是用历史头脑考虑再造想象问题,他们的思想还仅仅仃留在依赖史实、吃现成饭的级次上。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有些论者在引用为亚氏引证过的这句话时竟还把它当作亚氏的精辟之见而大加击赏。这岂止是误解,恐泊还有个思想共鸣的问题。有人说,文学中的史实不是“记”进去而是“融化”进去。“融化”就是作家对史实“审美化”的一种处理。再造想象之于史实的处理,就作如是观。
至于创造想象,主要还是谨防主体意识任意驰聘的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创造想象“不依据现成的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的形象”,它的表象的分解、组合是不受任何一个具体历史对象的制约。惟其如此,它就使作家在进行创造性思维活动的过程中,为过重和过强的目的、情感的驱策,创作主体容易变得肆无忌惮,目空一切,从而取消了题材对象应有的实在性、严峻性。大仲马有一句名言:“什么是历史?那不过是挂小说的一根钉子”。他们绝大多数的历史小说,实践的就是这样一种被黑格尔称为“任性”的自由想象的主张。这些作品,想象力的确很大胆也够丰富,它们成批成批地从他开办的历史小说“加工厂”生产了来。故事情节紧张离奇,颇可读但价值度却不高,遂为后人所垢。个中原委就在于,展开想象思维时,主体心灵过于姿肆放达。大仲马的主张及其实践在西方很有代表性。此后乃至今天西方历史文学中主观随意、消遣消闲之作一直盛行不衰、很有市场都不能说与此无关。就是拉萨尔的《济金根》,撇开他的政治意图不说,又何偿不是如此。他在反驳恩格斯对他们批评时说:“你的大多数反对意见仅仅适合于历史上的济金根,而不适合于我的济金根”。〔“〕联系他的整个创作思想,和大仲马“挂钉子”之说实在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从思维角度探究,问题的症结就出在创造想象时主体意识恶性膨胀,无所节制。
可能有人因此向我们提出具体创作和想象方式的关系,这里也顺便稍作陈述。作家在具体创作时选择何种想象方式,这无一定之规。就主体内在的主观条件看,这牵涉到作家自我的创作个性、气质、旨趣、修养等。作家总要采用最适合于主体、能与之同化的思维模式。就处在的客观条件讲,那还要视描写对象史料以及史料搜集的具体情况。这也有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比如可以凭用的史料很少,那采用再造想象就勉为其难。冯骥才向人介绍《神灯前传》时自述,他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所以把虚构人物作为主要人物放在前台,而将如红灯照首领林黑儿等真实历史人物放在次要位置,原因有三。其中第一条就是因为“红灯照的史料极少”。第二条是史料本身的“传奇色彩”所致。他认为:“如果将这些传奇性用在历史人物身上,难免给人不真实之感;用在虚构人物身上,则较便当,因为虚构的人物不受史实限制。对于材料不足的历史人物,作为背景处理,则更好写。”〔7“这是作家的睿智和睿智作家的表现。他还具体地谈到,历史文学对实有其人、虚实相杂、纯粹虚构的这三种人物的塑写,要求是不一样的。不妨说,对于实有其人的主角描写时,作家就不能不更多地借助于再造想象;而对纯粹虚构一类的人物,他则必须靠创造想象予以组构。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它惟有在与内容谐调一致的情况下才能显映其奇妙的功能。这是一条基本的创作规律。自然,不管何种想象,目前都是为了求真,步入更高的典型度,以使创造出来的题材对象更加审美化、本质化。这也是再造想象和创造想象作为一种有意想象的合目的的必然归趋:“在有意想象时,人给自己提出想象的目的,按一定的任务进行想象活动。川幻阿尼克斯特在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时指出:“莎士比亚一般是严格尊重历史真实的。偏离历史真实是为了迫求两个目的:一是增强剧情的事变性,而此类事变的发生是人们自觉追求的结果;二是把个别历史事件提到对社会生活规律加以艺术概括的高度。”〔9,他说的“偏离历史真实”,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不为历史事实所囿的艺术虚构,主要似乎是针对创造想象而言。再造想象迫求的艺术目标也同样如此。正因此,我们认为当一个作家碰到一个本已相当典型的原型对象,或者本已相当典型的情节场面,他应当毫不迟疑地将它“拿来”为我所用。大可不必象席勒写《贞德》那样,历史事实提供的结局明明比剧本本身“不但更自然,而且更雄伟壮美”,可他却偏偏“在事实的神话色彩之外,又加上了人为的神话色彩”,结果使这个题材的严肃性真实性遭到“削弱”,〔’。〕从而成为剧本的一大败笔。因为这不是自然式地简单照搬历史,而是题材对象的原生美、自然美正好暗合了作家崇高艺术目的的需要。
二、审美形式规范的一般要求
以上,我们分别从再想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两个层面论述了历史文学创作活动中作家主体思维机制的特点,它的创造性和能动性。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可指出,作家在进行“未曾知觉过的甚或是未曾存在过的事物的形象”的想象活动是受一定审美形式规范的,并非象一般题材的艺术想象那样可以完全不顾生活原型对象的貌态,俱指艺术和主观的驱使进行自由式的创造。因为历史文学毕竟是以一定历史事实为基础加工创造的一种文学,它虽然不可以也不应该是史实的简单复制和再现,但它作为主客相融的艺术结晶,特别是作为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独特的艺术种类,又毕竟与一定历史事实具有难以切割的营养脐带的关系,受一定历史事实的制约。历史文学想象之所以为历史文学的想象,重要的就在于此。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在讲历史文学的艺术想象之后,再进而就它审美形式规范问题展开探讨,就显得自然而合乎情理。说到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规范,我认为最突出、最集中就体现在框架真实或骨架真实上,它要求作家在“基本事实,基本是非”方面应与历史原貌保持异质同构的联系。#p#分页标题#e#
所谓框架,当然是指大关节目的、轮廓性方面的东西,不是全部的一切。这是历史文学真实性的基点,它最能充分显现历史文学的独特风彩。历史文学离开了框架真实,这座文学大厦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情状,其真实也将变成了非我,无以体现独特的个性特征。正是这个缘故,框架真实不仅向来为历史文学作家所看重、所迫求,而且也不期而期地成为历史文学批评家品评作品真实的一个重要标尺。高乃依就认为,与历史靠得较紧的作品,一般不应在主要行动和历史结局上去虚构。〔’1〕黑格尔也持此观点,认为历史文学虽然迥异于历史,但也应该同史实保持“大体上的正确”。L’2〕郭沫若等我国学者对此更是十分强调,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认为:历史文学既以历史为题材,就“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大抵在大关节目上,非有正确的研究,不能把既成的史案推翻。’八‘3〕那么,什么是历史文学的框架之真呢?具体细论,我认为主要包括人物、事件、地点三方面内容。人物:主要人物思想性格、功过是非的基本貌态要尊重历史,一般不宜随意改变。写南宋遗恨,无论艺术虚构多以需要,总不能把秦桧写成中华民族的功臣,把岳飞写成不耻于人类的汗分之辈。叙隋唐轶事,无论有多少理由,总不能将隋场帝描绘为雄才大略的英主,将李世民处理成荒淫小堪的昏君。如果连人物性格的基调都不顾,那历史文学之真所特具的个性和优势就将丧失殆尽。从具体的作品来看,它的固有的历史感、质定性也就变得浮泛飘忽,并由此及彼,造成作品整体真实的严重倾斜。郭老《孔雀胆》对段功的处理,在这方面就是一个可资的教训。历史上的段功,原本因镇压红巾农民起义军,保护管辖云南的梁王有功,才被梁王收为附马的,作者却将他作为正面形象来歌烦,歌颂他是“云南人的重生父母”,歌颂他“光辉普照”使“云南蛮子不敢再造反”,这就不仅在“基本事实”而且在“基本是非”上违反了历史文学审美形式的规范。所以,出来后当即受到了同志的批评,当然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以至在他的《剧作选》中从不收入此作。
事件:主要事件的关系经过、基本脉胳一般应史有其实,不宜任意地加减乘除,作可塑性太大的虚构。史事的发生,多有它的独特性。尤其是关系重大、影响深远史事的发生,它是彼时彼地特定历史条件、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更有它严密的逻辑性,是不可重复的,因而我们没有理由不予以足够的尊重。从创作角度来看,文学是追求“这一个”的形象的艺术,它不同于史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致力于表现历史的生动性、具体性而不是将其抽象化概念化,这也决定了它不能对史事轻加改变或随意怠慢。我们很难相信,一部描写太平天国革命的作品,如果将先在金田起义,以后定都天京发生内江,再以后石达开出走等重大历史事件,虚构为天国领导人自始至终精诚团结,亲如兄弟,最后率兵直捣北京,把咸丰皇帝赶下龙庭,它能映显历史的独特性和具体性而为人们所认同接受—不,即使写得最热闹,人们也不会领它的情。斯大林时期,苏联影片《攻克柏林》所以为人所垢,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叫从未到过德国的斯大林出现在柏林的机场上,对重大历史事件过分随意,类似例子,象我国明清时的一批所谓“雪恨传奇”、“补恨传奇”,如叶宪祖的《易水寒》写荆柯入秦刺死秦皇,张大复的《如是观》写岳飞还朝及秦桧受戮,夏纶的《南阳乐》写诸葛亮辅佐刘禅完成统一大业等。这些作品之所以不能在文学史扎根立脚,除了“互相骗骗”的“国民性”外,还因为它们描写的重大事件超越了人们熟知的史实形式的规范,为图逞快,随意翻变,不受节制。所以,“虽能大快人心,究难取信于世”。〔‘们地点:与上述彰明昭著的人事相关的地点,最好也有所规范,不宜随便虚构。例如万里长城建造在中国西北部,总不能将其移置西南方域;赤壁大战发生在长江,总不能将它改写在珠江上打;辛亥革命发难于武昌、建都在南京,总不能改写成在长沙起事,在上海建立新政府。文艺复兴时期的卡斯特尔维特洛早就对历史文学创作提出了这样的告诫:“不要替一个实有其人的大人物、特别是君王乱编故事,也不要凭空捏造国家、城市、山河、习俗、法律,更不要更改自然事物的程序。”L‘5〕他所说的“不要”显然也具有地理学方面的含义。阿•托尔斯泰也有类似的意见,他认为历史上“有些日期是受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历史辩证法制约的。这些日期就如同是打在历史上的纽结。’,〔‘6〕时呵日期)是如此,空凤地点)也是如此,原因就在于它受历史事件的逻辑和历史辩证法制约,如同打在历史上的纽结。如果我们随心所欲地处理,那么就同纽结被解散一样,作品固有的真实就会倾刻分崩滑脱,无所拴系;许多史事亦将变得莫名其妙,不可思议。当然,毋容多说,一如上面所讲的人物和事件是对历史具有重大直接影响、并且已有定评的人物和事件一样,这里所讲的地点是对历史事件发展具有直接意义、并且影响深广的地点,至于其他一般性的地点,诚如阿•托尔斯泰在论“偶然性”日期时所说的,“艺术家怎样方便,就可以怎样处理”,〔‘7〕则又应该区别开来。
历史文学形式规范主要是框架的规范。除此之外,细节规范也值得重视。细节是作家致真的重要手段和构成作品真实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说,框架是骨骼,细节是血肉,这是很有道理的。没有框架真实,细节真实再多,也失去附丽而导致个性的抹灭。反之,没有细节真实,框架真实勾画再好,那也流于概念、平板和空泛,干巴巴的不可能感动人。从生活本身来看,有些细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包含着特定深刻的历史成分,是历史真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将其抽去,那就等于把历史内容也抽掉了,致使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恩格斯甚至认为,如果私事一类的细节涉及重大,也应当写进历史。他说:“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原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的这虽然是针对史学研究而言,但它包含的道理对历史文学也同样适应。事实的确也是这样。拿电影《少林寺》结尾觉远头顶焚点戒疤来说吧,编导者拍摄这个细节,意在表示觉远为忠于少林寺决心舍弃爱情,遁入佛门,用心是好的。和尚事佛,头上点戒疤,仿佛也是人所皆知的常识,无可非议。可是上海玉佛寺方丈观看此片后却认为这个细节描写“不符合历史真实”,他说:“僧侣头上有戒疤始于元代,当时民族压迫十分沉重,元代统治者继续把他们认为有反抗思想行为的汉人强制遣入寺庙,削发为僧。为对这些人进行严密控制,就在头顶上焚上戒疤,以留印痕,便于监视,利于追捕。”〔‘的若把戒疤的出现推前到唐朝就已存在,这在客观上岂不是为元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抹去一项罪证!象这样一些涉及是非、功罪的历史细节,便不能轻易虚构。#p#分页标题#e#
当然,以上例子毕竟是少见的。就实践意义上说,历史文学的所谓细节规范,注要、大量的表现,还是历史可能性的规范:它是可以虚构的,但却应自觉地j妾受特定历史时代的制约,并成为映现特定历史时代的重要途径。如《李自成》有关北京布告颁贴及红娘子婚仪描写,《金欧缺》有关东京灯节、龙舟比赛和市井俗语描写等等。看似漫不经心、非常轻松自由,实则一丝不拘,与当时人情风俗完全吻合,经得起历史的推敲。作者在为此进行描写时,也惨淡经营,付出了很艰苦的艺术劳动。然而,惟其如此,这些作品才有较强的历史时代感,而且显得灵动鲜活,颇富生活的韵味。有的历史文学作者不懂这个道理,加上文史功底浅薄而又不愿深入历史,结果致使写出来的作品漏洞百出.从而由小及大,严重损失作品整体真实。也有的作者“聪明”一点,自知对历史钻研不够,把握不准,就对应该描写的时代风貌和生活环境一概通璧,结果创作而成的作品时代难分,环境不明。这种消极的办法同样是不可取的,它从反面说明了细节规范之对历史文学创作的重要和必要。上面所述的两点是历史文学审美形式规范的独特之处。毫无疑问,它只是历史文学创作低层次的一个基准点,而不是包涵真实的所有方面。情况既然是如此,那么我们就不应产生这样的误解:以为历史文学创作只要做到了这两条就可以大功告成。不能这么看。历史文学创作同样要反映本质真实而不是现象真实,整体真实而不是局部真实;在这些问题上,它与其它任何题材文学创作没有什么两样。马恩对《济金根》批评,主要就指意于违反了历史本质真实,卢卡契称道莎士比亚作品虽有细节失实却仍具有高度的真,主要也就指出它写出了本质之真。
还有一点也需要说明:以上所说的两条规范不仅是历史文学创作的基准点,而且规范本身诚如标题所示也只是形式规范的“一般要求”。正如世上万物不一可能是纯然绝对一样,每一个历史文学作家用来规范创作的要求也不可能纯然绝对,例外的情况总是少的。以主要人事描写为例,我们前面说过,一般都要求有历史原型为基础,不宜随意生造。然而象普希金的《上尉的儿女》、李劫人白0((大波》、鲍昌的《庚子风云》等,它们的主人公如格林略夫、蔡大嫂、李大海等,就是想象虚构出来的。这个题怎么看呢?我认为首先要立足于作品整体、主要方面的评价,将他与其他主要人事的描写联系起来考察。如果其他主要人事描写能循守规范,那也就可矣,应该基本得到认肯。其次,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这样的处理是随意而为还是别有深意。如果是后者,亦要给予合理的评价。基于这样的原则,再来看《上尉的女儿》、((大波》、《庚子风云》,我们就不会因此对它轻率地加以否定。因为它们这样非规范的描写只是局部个别而不是整体全影除了格林略夫、蔡大嫂、李大海外,其他主要人事大多信守规范),是别有深意而不是随意而为(普希金没以历史人物普加乔夫为主角而以虚构的贵族青年军官格林略夫为主人公,是迫了当时沙皇政府的高压政策;李劫人和鲍昌写蔡大嫂、李大海、从艺术看,至少可以藉此将本来散乱不经的历史人事串演起来,使其结构乃茧有序)。我们要看到艺术规范的约定性和原则性,同时又可看到它的随机性和相对性,不能把它当作不二法宝,以为只要凭持几条形而上学的条条框框就可以包打天下,对历史文学创作作出确当的评定。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而且我们所说的规范还常有浓重的类型学的意义,它对同样取材于历史生活但却全然不受史实规范的虚构性作品如《红楼梦》、《儒林外史》一一这类作品鲁迅将它称为“历史的文岸义小说)”在价值上是一视同仁的。大体则有,定体则无,恐怕只能这么看。一切精神性的东西,它的劳动是没有也不应该用纯然绝对的标尺去衡量的,这可以说是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之间潜在悖论在作怪了。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对上述有关规范的否定。规范还是可以的,并且不可少。有了规范虽然并不一定就等于创作成功,但毫无规范制约而听凭自我主观倏兴驱使的创作却总是令人幻灭的创作。我们只是说不要将规范简单化、绝对化,给子形而上学的理解,要看到问题的复杂性,这是一个很复的美学范畴。所谓规范,完整意义上看,我认为应作如是观。这也就是本节标题为什么用“一般要求”而不用“绝对原则”一类字眼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