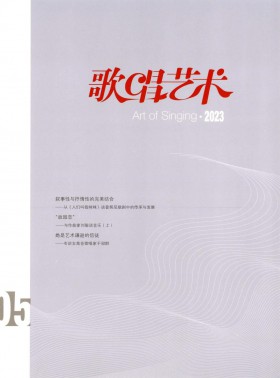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艺术体验的认知性和实践性,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体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释义为:通过实践来认识周围的事物;亲身经历。两个义项都只强调体验的认知性和实践性而忽略了其主观感受性、情感性及意趣性。“体验”在德文中为“Erlebnis”,“这个词在19世纪70年代才成为与‘经历’(Erleben)相区别的惯用词。”[1]心理学告诉我们,“体验的过程是大脑皮质从抑制到兴奋的过程,是相对稳定的主体审美经验的激发流动、重新组合的过程,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进行聚精会神的体验时所感受到无穷意味的心灵战栗。”[2]即“所谓体验是经验中见出意义、思想、诗意的部分。”[3] 显然,体验活动所具有的情感性乃至形而上意义是不能忽视的。 要讲清楚体验,就要分析体验与经验的区别和联系。一般来说,经验的意义较宽泛,“作为人的生物的与社会阅历的个人的见闻和经历及获得的知识和技能”[4]都可以统称为经验,经验具有明显的历史积淀性和普遍认同性,是相对静态的。体验则是主动的、富有个性和创造性的;在体验活动中,随着情感、想象、理解、灵感等多种心理因素的交融、重迭、激荡、回流而出现不同的情感及情绪形态,从而易于呈现为审美过程,因此常常与艺术品味密不可分。然而,任何体验都是以一定的经验为基础的,体验“是经验中见出意义、思想和诗意的部分。”[5]如伽达默尔所说的:“如果某个东西不仅被经历过,而且它的经历存在还获得一种使自身具有继续存在意义的特征,那么这东西就属于体验,以这种方式成为体验的东西,在艺术表现里就完全获得一种新的存在状态。”[6]这种新的存在状态,便是胡塞尔所说的“交互性主体”通过巴赫金所说的“参与性思维”所建立的“沟通的世界”,即具有“共在性”的世界。所谓“沟通”,指的是“内在地与世界、身体和他人建立联系,和它们在一起,而不是在它们的旁边。”[7] 一、艺术世界中的体验 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其独特之处就在于,艺术并不是哲学、政治、科学、道德思想的特殊形式的简单重复。艺术作品的世界与人的存在、生命、世界同构,这就决定了艺术的宽广范围和深刻内蕴不是任何文化现象所能比拟的。哲学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政治集中在阶级之间的关系之上,而艺术则是将视界投注在人与世界的诸多关系,包括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关系之中。艺术世界有如梅洛-庞蒂所说是“现象学的世界”:“现象学的世界不属于纯粹的存在,而是通过我的体验的相互作用显现的意义,因此,主体性和主体间性是不可分离的,它们通过我过去的体验在我现在的体验中的再现,他人的体验在我的体验中的再现形成它们的统一性。”[8]梅洛-庞蒂是这样理解现象学与艺术世界的一致性的:“现象学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普鲁斯特的作品、瓦莱里的作品或塞尚的作品一样在辛勤耕耘,——靠着同样的关注和同样的惊讶,靠着同样的意识要求,靠着同样的思想理解世界的意识要求,靠着同样的想理解世界或初始状态的历史的意义的愿望。”[9]由此看来,艺术体验的基本意义就在于:“使人较充分地发挥其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作用,从而进入到一种具有高度统一的意象性世界中。”[10] (一)体验中的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之区别和联系要对艺术家及艺术欣赏主体的审美体验进行发生学的、历时性的考察之前,有必要首先分析一下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的联系及区别。 艺术世界不同于现实生活,如果说现实生活相对于艺术世界来说是“自在的”,那么艺术世界相对于现实生活来说就是“自为的”。从郑板桥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三阶段来看,生活世界便是艺术家之“眼中之竹”。没有现实生活中农妇劳动步履的艰险,就不会有凡高画笔下的“鞋具”,这“鞋具”已不是审美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而是因“真理的自行置入”而向我们敞开世界性意义的“自为之物”。因此,艺术世界相对于生活世界是“自由的”。艺术的创造是审美创造,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实践活动,因而可以达到“自由”的审美境界。 任何艺术创作,都是创作主体以其审美理想、审美能力、审美观念、审美趣味,把在生活中得到的零散的审美体验组织起来,集中概括,予以系统化、情感升华之后形成新的审美体验,并以艺术符号的方式凝定下来形成艺术作品的过程。歌德说过:“诗人不是生下来就知道法庭怎样判案,议会怎样工作,国王怎样加冕,如果要写这类题材而不愿违背真理,他就必须向经验或文化遗产请教。”[11]实际上,艺术家一开始观察生活,就已经把自己的主观因素带入其中,映入艺术家眼帘的生活情景已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经过选择、概括和创造的了。泰戈尔就这样说过:“我发现,我一打开门,生活的记忆不是生活的历史,而是一个不知名的画家的创作,到处涂抹的五彩斑斓的颜色,不是外面光线的反映,而是出自画家自己的,来自他心中情感的渲染。”[12]因此应该说,艺术家是站在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的临界点上将“生活世界”与“艺术世界”联系起来的。 (二)形——象——境的相激而生审美体验是多种心理功能(感知、情感、想象、联想、理解等)共同活动层层演进,由初级体验向高级体验、由外部体验向内部体验,由浅层感受到深层体味的动态过程,主体往往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阶段,才能体验到真正的美的喜悦。 这一动态过程,概括而言之,即是“形”——“象”——“境”三个层次的相激而生,即审美客体在不同的体验阶段相对于主体的“合律”、“成韵”、“通神”(朱寿兴语),也就是南朝宗炳所说的“应目”、“会心”、“畅神”。#p#分页标题#e# 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曾提出:“艺术意境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的自然的再现,而是一个境界层深的创构。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次。蔡小石在《拜石山房词》序里形容词里面的这三境层极为精妙:“夫意以曲而善托,调以杳而弥深。始读之则万萼春深,百色妖露,积雪缟地,余霞齐天,一境也。(按:这是直观感相的渲染)再读之则烟涛 洞,双飙飞扬,骏马下坡,波鳞出水,又一境也。(按:这是活跃生命的传达)卒读之而皎皎明月,仙仙白云,红眼高翔,坠叶如雨,不知其何以冲然而澹, 然而远也。(按:这是最高灵境的启示)”[13]宗白华先生将艺术意境分为三层:第一层“直观感相的模写”,特点在于其呈现为静态的表象;第二层“活跃生命的传达”,特点在于灵动而韵致;第三层“最高灵境的启示”,特点在于虚空而神圣。宗先生所指的意境构成就是审美体验在不同层次所显现的审美状态,对于艺术创作者来说是这样,对于艺术欣赏者来说也是这样。 第一层即“有形”的“应目”,借用人的眼耳可以直接视听的静而实的形象,但这种形象自身的形式必须对于审美主体而言是“合律”的,符合“美的规律”的。然后才能进入对审美客体的深度体验,也就是第二层:“会心”之后的“未形”(不见其形,象外之象,即意象),是艺术欣赏者或创作者情感表现性与客体对象现实之景与作品形象的融合。严羽之“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即如是。而在此基础上的再度体验,即是第三层:“通神”之后趋于“无形”(大象无形,天地人“三才”),是超越情与象、宇宙本心、天地之道的“天人合一”,代表了中国人的宇宙意识。“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即是如此,从而进入到真正的艺术境界。 二、艺术体验中的世界 在对艺术体验的动态演进作历时性的分析之后,极有必要对艺术创作主体和艺术欣赏主体透过艺术体验所感受的审美世界作共时性的阐释,以呈现其丰富、充实、自由和深邃。一、你——我——他之共在关系的显现海德格尔曾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在世界之中存在”,言下之意,作为“此在”——我们,与“我”之外的一切存在者皆是“在世界之中”的。他明确指出:“如今人们习以为常仍把认识当作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而这种看法所包含的‘真理’却还是空洞的。主体和客体同此在和世界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14]这意味着“我”和世界的关系,也意味着我与“在世界之中”一切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即“你”——“我”——“他”之间共在世界之中的关系。对于艺术体验更是如此,艺术体验的每一个瞬间,我都已不只是我,而是通过艺术体验,在“你”与“他”的对话之中,在与世界的交融之中。 除海德格尔之外,梅洛-庞蒂也用他的“身体图式”向我们诠释了这一点——人通过身体向自我、他人、向世界开放,世界同时向“我”开放。其原因在于:“我的身体同时是能看的和可见的。身体注视一切事物,它也能够注视它自己,并因此在它看到的东西当中认出它的能看能力的‘另一面’。它能够看到自己在看,能够摸到自己在摸,它是对于它自身而言的可见者和可感者。 这是一种自我,但不是相思维那样的透明般的自我(对于无论什么东西,思维只是通过同化它构造它,把它转化成思维,才能思考它),而是从看者到它之所看,从触者到它之触,从感觉者到被感觉者的想混、自恋、内在意义上的自我——因此是一个被容纳到万物之中的,有一个正面和一个背面、一个过去和一个将来的自我”[15]如果说体验换言之是“以身体之,以心验之”,那么这种“身”与“心”的“体”与“验”就完全整合在了梅洛-庞蒂的“身体”之中,无所谓主体与客体,无所谓“你”与“我”、“我”与“他”,无所谓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一切都由一个“身体”广延开去,深入下去总之,“我不是按照空间的外部形状来看空间的,我在它里面经验到它,我被包围在空间中。总之,世界环绕着我,而不是面对着我。”[16]法国著名作家福楼拜在自述他写《包法利夫人》的经过时就描述了他类似于这般的艺术体验:写书时把自己完全忘去,创造什么人物就过什么人物的生活,真是一件快事。比如我今天同时是丈夫和妻子,是情人和他的姘头,我骑马在树林里游行,当着秋天的薄暮,满林是黄叶,我觉得自己是马,是风,就是他俩的甜蜜的情话,就是使他们的填满清波的眼睛眯着的太阳。[17] 艺术创作中“我”,与其说是在世界之中,不如说世界由我伸展开去,从看者到“我”之所看,从触者到“我”之触,从感觉者到被感觉者如此种种,都是在“我”“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体验中完成的,只是这里的“其”既是“我”,又是我之身体可感与不可感,可触与不可触的一切。而艺术活动(包括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一切艺术活动)就应该是在这种“我”与“你”或者“他”的互融体验中完成的。一、对生命整体性的回归提到生命的整体性,我们不得不为古先哲的智慧所折服,有关“三才”——天、地、人的著述。顶于天而立于地,居住于其间的便是“人”(与人相关的一切,自然的或社会的),然后统称“生命”,历时追溯是海德格尔的“时间性”,立足转瞬即逝的现在,向着历史与将来绵延开去,横向延展便是中国艺术精神中的“宇宙大化”——包纳万象。我们每一个人都横向广延,纵向深入地存在于这样一个生命整体之中。而体验就是个体在永恒的生命之流中由其自身与无限世界交相融合而成的意义生命统一体,人生活在体验中,也通过体验来生活。#p#分页标题#e# 艺术,在我看来应该是离哲学最近,将自己的世界投注在人与世界这个生命整体之上的,且艺术因此而具有生命。如伽达默尔的一段论述:通过艺术作品的效力使感受者一下子摆脱了其生命关联并且同时使感受者顾及到了此在的整体。在艺术的体验中,就存在着一种意义的充满,这种意义的充满不单单地是属于这种特殊的内容和对象,而且,更多的是代表了生命的意义整体。某个审美的体验,总是含有着对某个无限整体的经验,正由于这种体验没有与其它达到某个公开的经验进程之统一体的体验相关联,而是直接再现了整体,这种体验的意义就成了一种无限的意义。[18] 正是有了“某个无限整体的经验”即艺术创作者或欣赏者体验到的整体性生命,才有了在艺术体验世界中可感的“意义生命整体”,而唯一的区别是,创作者将生命纳入艺术,而欣赏者则是将艺术纳入生命。 我想对这种艺术体验的最好注解之一,是南唐后主李煜的亲身经历:从一代帝王到阶下囚徒,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其对于生命的反思体验,不言而喻。从对往事的追慕:“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到对人生无奈,生命无常的感慨:“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后主通过在艺术创作的体验中,将其对自身生命体验的回忆和对世事沧桑的感喟倾入艺术作品,使作品获得本身的意义生命,而艺术欣赏者,将在艺术作品世界的体验中,通过与作品的“视界融合”重新发掘这种生命意义完整性,使其趋于无限。“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再仅仅是李煜之“愁”,而或许是“你”之愁,“他”之愁,“我”之愁愁的也将不再仅仅是“亡国之痛”,而是向着无数个可能狄尔泰曾强调主体应该以生命本身去认识生命,而艺术体验本身就是这样一种生命体验活动。可是,在后工业文明日益繁荣今天,越来越多的来自于诸多方面压力与困惑,使得现代人的精神日益零散化、破碎化、审美日益表象化、平面化,从而在内心深处,渴望着一个充满生命本真和诗意的世界——灵心静谧,清明逍遥我想,这应该是艺术的旨归之所在,也正是审美体验的价值之所趋——每个生活在体验中,也通过体验活着的生命主体,都能用“诗”的方式,去探求“思”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