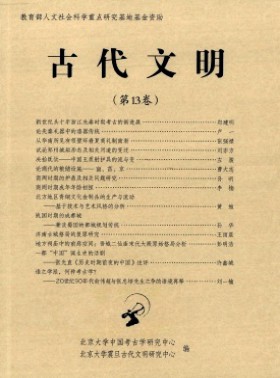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古代法律的传统转变,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问题的提出:由韦伯的理论谈起 韦伯关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由秦汉一直到明清历时数千年,中国传统法律一直都未曾发生任何实质性变化。一直以来,民间的调解都重于官方的审判,伦理的考量重于法律的考量。而官府的审判重视的是实质的正义而非形式的法律,法律和司法的运作是建立在“考虑个案牵涉的人是谁”的原则之上。法律外伦理道德的智慧和公道,当事人具体的个人状况和社会关系,才是影响判决的最为重要的因素,而非概括的、形式的法条。法律与道德、法律与政治乃至行政浑然难分,所以中国传统司法始终缺乏独立运作的空间,具有“实质的——非理性的”特征,充满着自由裁量和不可预计性。[1](P7-8) 这样,通过将秦汉至清末两千多年的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化约为一副凝固的静物素描,韦伯就构建起了他关于中国传统法律和社会的“理想类型”。 晚近以来,无论是韦伯关于中国古代法律的“理想型”本身,还是受其影响的类似研究都受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批判。首先,关于韦伯的理论,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其理论的出发点是要为了“彰显现代西方的独特类型”,其法律社会学关于法律发展的预设是一种由习惯法-传统法-自然法-实定法线性发展的理论构想;其分析模式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把一切问题都看作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从未设想过或许还存在“既此又彼”的关系。而同时,韦伯的文化比较既包括了西方中世纪法律和现代法律的文化内的比较,也包括了中国固有法和西方现代法的文化间的比较。然而有意无意中,韦伯又将两者混同起来,在彰显现代西方独特性的目的指引下,将比较对象两极化。在中西法文化的对比中,将中国与西方相反的地方刻意挑选传来,以达到将西方原有类型在强烈对比之下益形清晰透彻的目的。[2](P1) 在这样一种强烈的目的关照下,使得他的分析刻上了深深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烙印,将一切非西方社会的发展阶段等同于西方现代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期。尤其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研究,由于语言、资料等的局限,再加上其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的固有局限,使韦伯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产生了诸多误解乃至错误的认知。 二、宋代法律传统的内生性转变 事实上,对于将中国古代文明固化、静止化的作法,东西方早已传来了不同的声音。法国汉学巨匠谢和耐就曾写道:“人们惯常妄下结论,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成不变的方面,这实在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任何未被分辨清晰的事物,总是显得缺乏特点。”[3](P1) 他进而强调,经历过诸阶段之发展的并不只是西方的文明,所谓“不变的中国”,只不过是笼罩在历史真相上的一团迷雾。而当我们真正深入中国历史的深层,“我们就将发现,中国的历史并非存在于连续性和不变性之中,而是存在于接踵而至的一连串剧烈震荡、动乱和毁坏之中。”[4](P1) 以下,本文将由司法和法律观念两个层面分别论述宋代法律传统的近代转变。 (一)宋代司法传统的转变 论及宋代司法传统的特色,中外学者早有颇多论述。在宋代早已建立起了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各级审判机构。同时,司法官员在当时的身份也是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真宗朝臣僚孙何上言:“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悬,太宗尝降手诏,诸州司理、司法,峻其秩,益其俸。……欲望自今司理、司法,并择明法出身者授之”。[5] 由此可见,当时的司法官无论在身份地位还是俸禄上,都是和其他官员有明显不同的。同时,当时也还出现了司法官员必须由通过明法科考试的候补官员中选任的主张。不仅如此,对于司法官员因判案不当的处罚也是极为严厉的,“吏一坐深,或终身不得进”,[6]如仁宗朝,“刑部尝荐详覆官,帝记其姓名,曰:‘是尝出入人罪不得迁官者,乌可任法吏?’举者皆罚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司法官群体地位的特殊性。 同时,在法律智识方面,国家在国子监、太学之外,又专门另设了研习法律的教育机构——律学,徽宗政和三年六月还专门修订了《国子监、律学敕令格式》一百卷,对国子监、律学等教育机构进行规制。与此同时,为了针对应明法科考的举人的需求,也出现了专门的法律教科书。 在进士科、九经科之外,尚有专门的法律科考试——明法科。这样,由法律教育、法律研究到法律考试、司法官员的任用,宋代士大夫中就开始形成一群学法、懂法并以法律为职业的特定群体。 美国学者昂格尔把法律职业定义为一个由活动、特权和训练所确定的特殊集团,这个集团操纵规则、充实法律机构及参加法律争讼实践。 [7](P47)而韦伯则认为法律职业是指受过专门训练的从事司法活动和系统阐述法律的职业法律工作者形成的特定群体。[8](P306) 从这两种意义上来说,早在宋代时期,中国社会已然出现了一个颇具近世意义的法律家阶层。正是在这一特殊群体的努力下,中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一种重视人的生命,重视证据,尊重个人尊严的崭新的近世司法理念得以发扬。司法逐步倾向独立,虽然由于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局限,此种独立直至最后也是不完全的,但是当时无论中书还是大理寺、审刑院,都可以站在相对独立的位置对案件发表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的司法独立是存在的,“至少也不能说它是隶属于行政权之下的。”[9](P279) (二)宋代社会各阶层法律观念的转变 司法制度的发展变革,其背后必然伴随着当时社会整体法律观念的变化。事实上,宋代社会,无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身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还是普通的升斗小民,其法律观念相较于唐以前的中世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p#分页标题#e# 首先,宋代历代君主普遍注重司法活动,且守法治国观念得到认可。如史载雍熙三年,太宗亲到在京各狱按问虑囚,谓宰臣曰:“‘或云有司细故,帝王不当亲决,朕意则异乎是。’……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则亲录系囚,多所原减。……后世遵行不废,各见帝纪。”[10]早在北宋时期,朝廷就制定了“罪法相当,中外一体”[11]的立法原则,南宋高宗论及立法时道:“有司立法,不可太重,恐难必行。”言下之意,显然是主张立法必行的。 其次,作为社会精英分子的士大夫集团的法律素养的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关于此点,法律史家陈景良先生曾著文有过专门的论述,得出结论认为:宋代士大夫对法律的重视和对律意的通晓是当时的一种风尚,并由此推动了宋代法律文化的发展。[12] 据史籍记载,宋代臣僚的上言中,类似“今既有成法,当令一切以三尺从事”、“唯法是守”、“自昔天下之所通行者,法也”、“举天下一之于通行之法”之类的言论可谓触目皆是。[13] “而就诉讼理念而言,士大夫不再视民事诉讼为‘民间细故’,而是精心审理,倍加关注,甚至‘为政者皆知以民事为急’。”[14](P35)在司法活动中,即便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纠纷,官员们也经常会依照律法的规定而非伦理礼法进行判决。曾经岿然高耸的人伦道德界限已然渐次倾颓,理性的判决渐次取代了古旧的教条。在司法官的判决中,理智性正日渐压倒了伦理性的考虑。 事实上,只需选取《宋史•循吏列传》与前代循吏列传及酷吏列传两相对照一番,宋代精英阶层的法观念的变化便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宋史》所列循吏共十二人,其中所载事迹中和诉讼有关的包括邵晔、鲁有恭、张逸、程师孟、韩晋卿等五人。其中大都是因判案如神、执法严明入选,比如其中的程师孟,史载“师孟累领剧镇,为政简而严,罪非死者不以属吏。发隐擿伏如神,得豪恶不逞跌宕者必痛惩艾之,至剿决乃已,所部肃然。”[15]将程师孟的事迹与《史记•酷吏列传》所载郅都的事迹两相对照,便会惊诧于汉宋两朝人观念的差异竟如同他们相隔的年岁一般遥远。 史载郅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济南瞷氏宗人三百余家,豪滑。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瞷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拾遗。”从上引史料中,我们不难发现程师孟和郅都二人无论在治民手段还是最后效果上,都极为相似。据史籍细论起来,郅都文能治邦,武能却敌,公廉无私,显然无论政绩、节操比之程师孟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若果二人泉下有知,大概也要彼此引为同道吧。然则就是这两位行事风格极为类似的司法官员,其生前身后的命运却是霄壤有别的。郅都生前死于非命,死后列于“酷吏列传”,蒙羞万古;程师孟生时得享天年,死后荣列“循吏列传”,史笔流芳。 综合上述史实,我们不难发现,在经历了近千年的时代变迁之后,社会精英阶层的法律理念已然发生了天翻地覆、甚至颠倒性的变化。至少在宋代的士大夫阶层的心目中,法律再也不只是道德的奴婢,而是“天下所恃以为治”的具有独立地位的规则体。 胡适先生曾指出:“历史上有三个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又说:“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跺式的人物。……民间的传说不知怎地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跺,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16](P1038)徐忠明先生以“包公与民间文学兴起的巧遇”解释了胡适先生的疑惑,认为正是借助于民间文学的力量,包公随之成为越来越神话化的人物。 事实上,这个解释并不是那么令人满意。因为它无法解释何以这样一个人物偏偏出现在宋代,而在后世明清民间文学更为发达的时代,为何没能创造出超越包公的神话性人物?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对社会现实的某种反映,这已是众所周知的道理。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宋代关于“包公故事”文学塑造,正是当时普通百姓对清官的深切热望的真实反映。而且,此时百姓心目中的清官,早已非如韩延寿、吴祐这般以“息讼”为最终的目的追求,以情动人、以礼化人的中世传统循吏,而是如包拯这般精明练达、敏于听讼,执法严明的清官。可见,在当时普通百姓的头脑中,产生纠纷时,更渴望的是获得法律的救济,而非伦理的妥协。 此一点,也可由当时文人笔记、名公判牍等史料中获得证实。据沈括《梦溪笔谈》所记:“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18]另据当时判牍称:“婺州东阳,习俗顽嚣,好斗兴讼,固其常也。”[19]甚至城市清洁工,即所谓“倾脚头”,彼此之间也存在某种固定的利益分割,他们“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至经府大讼,胜而后已。”[20]而当时社会对应民间词讼渐次增多的情形,开始形成一类专门协助当事人打官司的“讼师”。 更有甚者,民间还出现了专门教人词讼的机构——“讼学业嘴社”,从学者常数百人。[21] 为此,元丰七年朝廷专门制定了《聚集生徒教授辞讼文书编配法》,[22]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民间讼师讼学活动的“猖獗”。 三、宋代法律传统走向近世原因浅析 法律观念的转变,其最根本的原因必然是客观社会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事实上,由唐经五代至两宋,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此种深刻变革。五代和宋以后,中国舍弃交通不变的长安、洛阳,把国都迁往交通都市和商业都市的开封,展示出中国已然由内陆中心时代转向了运河中心时代。而大运河的机能就是交通运输,“所谓运河时代就是商业时代”,这也从一个方面表现了宋代社会的近世性格。[23](P164-171)#p#分页标题#e# 随着商业的繁盛,宋代最终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并导致知识更加普及,学者们甚至认为同时“一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在进行,科学思想得到发展,人性亦同时有更多觉醒。”[24](P159) 这样的观点在时下难免会遭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嘲讽,然而经济的发展带来知识的普及,却无疑真正导致了人性自觉意识的增强。余英时先生就认为“从现代的观点说,士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是贯通宋代政治文化的一条主要线索。”[25](P520) 当时士大夫作为政治主体的共同意识大为增强,范仲淹所倡导的士大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呼声得到了热烈的回响。发展至后世的熙宁变法时期,皇帝与士大夫“共定国是”这一北宋政治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原则开始获得皇帝与大臣的共同认可。同时,由于“殿试”制度的存在,宋代的进士都自夸是天子门生,“因此彼此官位纵有高下,但和天子的私人关系同样平等的想法出现”,一种“比肩事主”的观念强烈地支持着宋代士大夫维持个人人格独立的努力。而这一切,反应在司法上,就成了“鞫谳分司”、各级法吏独自审判等带有强烈近世色彩的制度。 总之,正是由于宋代商品经济繁盛,经济大都市开始形成,文化大规模普及,导致中世笼罩在人们心头的伦理枷锁渐次被经济的浪潮打碎,一种“近代的个人主义开始兴起”,[26](P279)人们的义利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导致人们的法律观念随之改变,惧讼再也掩压不住人性深处对具体利益的追求,调处息讼也让位给了“唯法是守”、“依法从事”的近世司法理念。在这一法律理念的催生下,借着商品经济的浪潮,中世的法律传统被大浪淘去,取而代之的则是展示着近世光辉的崭新的法律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