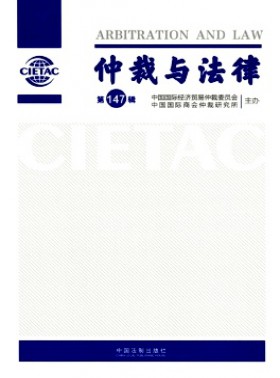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法律与政策中的立法意义,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立法就是指由特定的主体,依据一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的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社会规范的活动。说到底就是,由立法机关,依据一定的立法权限,依循一定的程序,运用一定的技巧,把权力与权利分配给各应享社会主体的活动。权力与权利的运作状况如何与权力与权利如何分配有着莫大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立法决定着权力与权利的运作状况,这就犹如潺潺细流赖清水源头,当然不能否认运作过程中也有决定性因素。法律是社会秩序调整、社会正义实现的工具,立法对社会秩序的调整、社会正义的实现也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同时,马克思认为:“立法的权力并不创造法律,它只是解释和表达法律。”①“在社会发展到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就变成了法律。’,这种共同规则、习惯、法律便源于社会活动过程中,立法权力揭示和表达的便是这般社会活动中的共同规则。 其实,对立法的如上分析仅局限了在立法活动本身。然而,在社会变迁如此迅速的时代,“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的法律应该调整发生变化,并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变化着的生活关系,也就是它至少应当暂时地引导这些变化走入制度性的轨道。’,③要走人制度性的轨道,国家立法机关的宏观调控亦不可缺少,政策与法律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纠缠不清,国家的立法活动与行政难解难分,法律与政策时常分庭抗争。 一、法律的理性与政策的非理性 “奥地利社会学家与政治家阿尔贝•谢弗莱指出,在社会一政治生活的任何时刻,都可以看出两个方面:其一是一系列的社会事件,他们有固定的模式并定期发生;其二是还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在单个情况下必须做出导致新的、独特的形式的决定。这位学者把第一个方面称为‘国家的例行事务’,把第二个方面称为‘政治”,。④法律具有稳定性、一般性、统一性的特征,通常作为固定的模式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政策具有灵活性、特殊性、应急性的特征,通常对新的、独特的形势进行调整。 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指出:“每个社会进程都可以分为理性化的领域和非理性的领域。理性化领域在井然有序地处理再发生的情况中有固定的和程式化的程序所组成,非理性领域是包围理性领域的领域。’,⑤法律便是这种固定的和程式化的社会规范之一,法律调整的领域便是理性化的领域;政策便是非固定性的社会规范之一,政策调整的领域便是非理性的领域。 其实,关于法律的理性问题可有启蒙运动说起,“启蒙运动的自然法学派力求建立以事物的本质和理性为基础的、独立于时间与空间的、同时也是非历史的法。’,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知识应该替代信仰。’,⑦替代了信仰的知识,(当然这里的信仰是对中世纪神法、神权的信仰),就是依据一定的固有模式,遵循一定的规律,对事物、事件的发展做出可靠的推理,非以盲目的图景为追求,个人的意志为动力。启蒙运动的自然法学派一次理性推毁了中世纪社会秩序,建立了理性的法治秩序。由此可见,法律的理性也就是法律的稳定性、一般性与统一性,政策的非理性也就是政策的灵活性、特殊性与应急性。法律与政策的矛盾通常也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 二、杜会转型与立法的困境 我国近代以来,法律发展首先否定的就是我国传统法律的理性,首先肯定的是西方法律的理性,因此,大量移植西方法律。法律移植本身是国家在社会形态巨变情势下的非理性政策的应对,并非传统法律理性的继承。当然,我国近代,大量移植西方法律,乃国家自主性削弱甚至被剥夺之结果,以西方法律文明为中心、经济决定论、单线条进化发展模式之结果。时过境迁,随着国家自主性的增强,这样一个问题引起诸多学者的思考:“我们能否走一条尊重传统的、平和的,较少社会震荡的变迁之路?走这样一条道路,是否有利于增进国民的福社,从而也有利于新的文明的生成?’,⑧当然,我们现在的法律生活也得益于近代由西舶来的法律模型,但是,正如巴士可所说“奇怪的很,一条河流竟成为法律的边界线,在Pyrenees这边被视为真理的事情,在另一边却是错误的。’,丈乳之所以如此,民族的因素不容忽视,更何况法律常常体现着民族精神德国学者马克斯•舍勒说“国家、法律、优雅的言语、哲学、艺术、科学以及一个群体的‘公众舆论’,则是建立在群体精神之上的。’,翎祥体精神绝不可能短时期内造就,需要一个民族短则百年,长则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文化积淀,法律理性的形成也绝非一日之功。如果把法律理性比作一棵树,其基干便是群体精神,即使是把它挪移到一个新的生长环境中,它需要长时间的适应过程,并在适应环境后,基干将继续长成。当前,我们所谓的法律理性是揉合了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明的产物,并在激荡的社会转型时期,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法律文明。随着社会转型趋于稳定,社会的“理性化的领域”将大于“非理性的领域”,法律的需求量就大于政策的需求量。接下来的问题是,清末法制改革是在外力强制下被迫在非理性政策领域做出的政策性应对,然而,当前如何处理传统法律理性与西方法律文明的矛盾呢?在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如何解决非理性政策与理性法律之间的矛盾,甚至是政策的非理性侵入法律理性的领域?三、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应答与评析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认为“社会主义的法来自无产阶级革命。”⑧也即“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与现有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开始了,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庞大的上层建筑更慢地或更快地被彻底改变。” 无产阶级革命产生社会主义的法律,由革命的特征所决定,革命显然属于“非理性的领域”,革命阶段权力与权利的分配由非理性的政策决定。当无产阶级的革命夺取、建立、并巩固了政权后,暴风骤雨般的社会改革方式逐渐为国家改革所代替,无产阶级革命为国家改革所代替,这是二战后诸多国家发展的共同趋势。在国家改革过程中,如果扩大“非理性的领域”,多以权宜之计行姑息之政,社会终将进人由非理性政策调整的恶性循环过程,法治国度终将欲走近却走远。如果扩大“理性化的领域”,那么传统法律理性、西方法律文明、非理性政策的关系又纠缠不清、难以理明。为避免两种极端,所需要做的或许是,由立法机关以高姿态凌驾于其上,沟通理性法律与非理性政策之间的对话,也即:正视传统法律的理性,总结民族精神;切实的把握正在形成的新型法律文明。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就是避免理性法律落人“非理性领域”,非理性政策陷入“理性化领域”。#p#分页标题#e# 同时,法具有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的本质原则之一。具体说来,也就是任何法律都是有利于统治阶级政党的法,并遵循特定的政治目的。社会主义的法律在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与转变而服务的政党决策中表达出来。 然而,正如魏德士指出的“没有比共产主义的法更倒退的法,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者取得权力后,它就禁止任何权力更迭,因为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丧失权力,就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预言相矛盾,也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义与目标相矛盾。因此,国家和法律体系动用一切可想到的强制手段,始终压制着一切不同观点,共产主义的国家和政党机器认为,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必然阶段。’,。若果真如此的话,共产主义国家和政党机器也就有了故意混淆理性法律与非理性政策、混淆“理性化领域”与“非理性领域”的嫌疑。试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通过革命这一非理性领域的活动获得政权,先由政策后由法律维护、巩固其政权,政权稍有松动时应急的还是非理性领域的活动,在其间过程中在某些事件发生时,强大的国家机器故意混淆两个领域,所取得的有利成果,有时为其所盼。 立法活动就是一理性法律与非理性政策的抗争过程,理性法律与非理性政策、“理性化领域”与“非理性领域”的混淆、界分清势,便是立法活动的难题之一,也是立法活动的主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