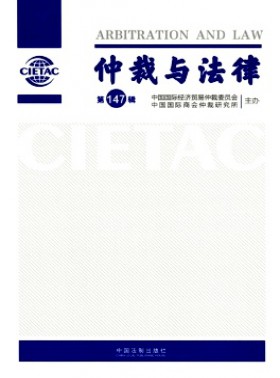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法律基础教育世俗化分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本文作者:张会峰 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法律基础教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分离到合并,由繁到简的沿革过程。特别“05方案”之后,法律基础教育无论在教材上、师资上,还是课时安排上,都已经完全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之中,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新的教育背景下,在极其有限的课时设置内,要把握法律基础教育的性质并将其落到实处、收到实效,首先就要在指导思想上,明确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法律基础教育的全新定位与教学侧重点。
一、法律基础教育是介于“问题”与“主义”之间的教育
近一个世纪之前,“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在北京大学的两位学者之间。孰优孰劣,在此不做评价,但借用“问题”与“主义”的提法,却可以很生动地概括法学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侧重点的不同。“问题”指代“形而下”的具体的知识教育,而“主义”则指代“形而上”的价值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从其内涵与内容来看,都更多指向“形而上”的观念教育、“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4该定义明确说明思想政治教育是围绕“观念”、“观点”展开的,虽然“道德规范”没有使用观念的提法,但是道德规范本身的属性就是是非善恶观念,因而也是观念性大于知识性,认同性重于识记性的教育。
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共产主义信仰教育人民,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动员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实践活动。具体而言就是对人们进行世界观、政治观、人生观、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教育。这些教育就其属性和侧重而言,都是偏向“主义”的教育。如果在“05方案”之前,法律基础教育在拥有独立教材、独立师资和相对宽裕的34-36个学时的情况下,还能勉强坚持知识教育定位的话,那么在“05方案”之后,通过10个学时甚至更少的时间来进行法律知识的传授,将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使命。而知识体系与课时之间的紧张关系却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要缓解这一紧张关系,首先就要改变对法律基础教育的认识和定位,即把法律基础教育由原来的知识教育上升到理念教育,由“问题”上升到“主义”。这也是符合思想政治教育宗旨的必要转变。准确地说,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法律基础教育,应该是介于“问题”与“主义”之间的全新教育形式。“问题”往往是法律教育的切入点,但“问题”本身不是目的,目的还是“主义”。不关注“问题”的“主义”是苍白无力的,而不提升到“主义”的“问题”则是缺乏向心力的知识碎片,达不到既定的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法律基础教育,就是由法律知识入手,并最终使学生生成法制观念的教育过程。具体而言,法律基础教育就是要实现“规范指引”、“理论奠基”和“理念启发”三个层面的功能。“规范指引”就是让学生了解一些实用的法律规范,能够指导其行为,并解决实际问题。中央16号文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既要教育人、引导人,又要关心人、帮助人,努力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
法律基础教育也不例外,贴近生活的法律规范指引,在让学生获取知识的同时,还让他们对法律产生认同感,感觉法律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法律基础教育不是教育者的强加,而是受教育者的内在需要,这是培养法治理念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也符合由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这种“问题”教育是法律基础教育的起点。“理论奠基”指的是让学生掌握法律学科的一些基本理论、入门常识,为日后进一步学习法律知识,分析法律事件奠定理论基础。“理念启发”首要的含义当然是启发学生树立民主法治、遵纪守法等观念,这就是法律基础教育中的“主义”,是法律基础教育的最终目的。此外,具体到本课程而言,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用有限的课堂教学,启发学生对法律知识和法律事件的无限关注,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让有限的法律基础课,成为大学生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的起点,而非终点。只有以此为目标,法律基础教育才能从纯粹的知识传授和对完整性、专业性的诉求中解脱出来,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对庞杂的知识体系进行取舍,以点带面,以课堂讲授带动课下学习,从而突破课时的局限,破解法律基础课所面临的重重矛盾。让法律基础教育由“问题”上升到“主义”。“主义”教育才是法律基础教育的终点。
二、法律基础教育应当还原到“世俗”
法律基础教育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就是专业化问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入法律教育,甚至被很多法学专家认为是一群不专业的人试图在做一件很专业的事情。从一定角度来看,法律的确是很专业的知识,“法律世界是对我们真实的生活世界加以高度技术性建构而形成的一个抽象的逻辑世界,法律是一门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科学知识。”[2]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法律又应该是世俗的,是与人们的经验常识可以兼容的普通知识。我国学者苏力指出:“法律是世俗的,是要回答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而不是一套说着好听、看着不错的逻辑或话语。”[3]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霍姆斯也曾指出“: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恰恰是法律的世俗性与经验性,使得针对一般人的法律基础教育成为必要和可能。但法律的专业性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要理解并解决法律的专业性与世俗性(非专业性)之间的矛盾,首先有必要对法律条文与法律规则、法律精神这几个概念进行区分。“法律规则不同于法律条文。法律规则是法律条文的内容,法律条文是指法律规则的文字表述形式。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做如下理解:首先,法律条文的基本内容是法律规则,但法律条文中除了法律规则之外,包括构成法的其他要素,如法律概念、法律原则。其次,法律规则与法律条文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一项法律规则的内容可以表现在不同的法律条文甚至不同的法律文件中,而一个法律条文可以完整地包括一个法律规则,也可以包括几个法律规则。”[4]#p#分页标题#e#
这是关于法律条文与法律规则之间关系的学术表述。说得通俗一些,法律条文是法律规则的表象,而法律规则是法律条文背后的意义。法律条文基于用语的抽象性、准确性和立法技术等原因,可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但是法律条文背后的意义,即法律规则,则是来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对我们普通人所熟知的社会规则、伦理道德的规范化和成文化。我们每个具有正常心智并深谙交往之道的人,都应该有自信通晓法律的基本规则,这种判断一方面基于法律与伦理道德在基本层面的吻合性。我国古代的文化讲究“出礼入刑”,即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自然也就也就遵守了法律规则。又比如,你可能不知道我国刑法对于盗窃罪是如何表述的,但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有这样的常识,就是偷偷拿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这种是非观念与盗窃罪所要表达的规则要求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民主社会的法律,本来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君主或政府强加给他们的学术作品或技术产品,法治是一种自治还是一种他治,决定了法治的真伪,决定了民主与专制的区分。民主时代的法律就是由普通老百姓制定出来并适用于老百姓的规则,我国绝大多数的人大代表不是法学专业的,但是他们却是法律的制定者。(当然有专业机构进行技术层面的提升,但这主要是法律条文层面的问题。)国外刑事审判中的陪审团也是由普通公民组成的,但他们却是罪与非罪的裁判者。“这些普通公民既没有接受过专业法律教育,更无司法经验。这是基于不能允许少数司法专业人员垄断的法律观念而规定的。普通公民以普通人的情感、常识和判断力参与司法活动,可以对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有更深切的了解,也有助于促进公众对法律的信心。”[5]
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类似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因为法律术语的专业化而拒法律于千里之外。而且只有消除这种神秘感和距离感,法律的实效性才会显现出来。就像美国学者伯尔曼所说:“除非人们觉得,那是他们的法律,否则,他们就不会尊重法律。”[6]法律精神则是对法律规则的进一步抽象和提升,是蕴涵于法律现象和法律制度之中,并对法的发展起支配性作用的一种内在的理念、信仰及价值取向。[7]就是前文所讲的法律中的“主义”,这些“主义”并非源于抽象的理性,而是由平实而鲜活的社会生活所决定。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8]这些法律精神是一定时期社会成员共享的精神,因而也应是大众化的文化,而非法学家的创造和独断。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有政治家懂政治,那么政治的民主化是没有希望的,如果只有法学家懂法律,那么真正的法治也是没有希望的。在专制时代,法律确实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是专业性很高的东西,统治者信奉的理念是“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这是臣民时代的产物,在公民社会中,法律不应该被官吏和专家所垄断。法律条文可以是专业化的,法学研究也可以是专业的,但是对法治国家中公民的法律教育,一定是世俗而平实的。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法律基础教育,就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应当剥去法律神秘的外衣,将法律还原到世俗,交还给大众。而这一任务,是小众化的法学专业教育所不能完成的,这恰恰是法律基础教育的使命和贡献。广大从事法律基础教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应该因此而充满自信和自豪。达成这种共识,还具有重要的教学方法论意义,它可以指导我们克服法条表面的抽象与枯燥,探寻法条背后的具体与生动,以克服教学矛盾,提升教学效果。
三、法律基础教育应当凸显出“权利”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作为传统的“思想品德课”的两个组成部分,尽管在“05方案”之后合并为一个科目,但前后两部分却具有不同的学科属性与教学侧重。除了“问题”与“主义”,专业化与通识化的不同。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即“思想道德修养”更注重于义务教育,而“法律基础”则应更注重于权利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泛指人类所有阶级社会共有的培养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特指无产阶级培养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1]5这种教育自古至今,都强调受教育者对国家、对集体、对他人的义务,是义务本位的教育。我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简单对应于宗法教育或礼法教育,其义务本位的色彩是非常浓郁的。不论是礼治、德治,还是人治,都充斥着义务思想。义务本位反映了古代中国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每个人(君主除外)都捆绑在义务的“牢笼”中,并且这些义务都是片面的,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权利。[9]虽然这些礼法思想对于维护当时的君权统治社会稳定具有进步意义,但是用今天的民主思想去衡量,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其说是“智民”教育,还不如说是“愚民”教育。
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历史上其他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本质的区别,它是工人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共产主义信仰教育人民,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动员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实践活动。这种教育从其终极意义上讲是为了解放人,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实施的教育,本质上应该是关于人权或权利的教育。但是,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角度去立论的,而不是从受教育者个体的需要去立论的。强调的更多是政治认同、价值认同的义务,以及相应的责任与奉献。就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包含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教育本身而言,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义务本位的教育。美国法哲学家福勒根据道德标尺或阶梯的不同,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两个等级,“如果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导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10]“义务的道德”要求人们做到,“愿望的道德”希望人们做到。但无论是要求做到,还是希望做到,都是一种偏向义务的表述。这种义务本位的教育属性,仅从形式而言,无法区分古代与现代、专制与民主的教育形式。#p#分页标题#e#
道德规范主要是由义务规范构成的,法律规范则不同,它是权利义务的组合体,既有权利规范,又有义务规范。在法律实践和法律教育中,是更多的强调国家权力,还是公民权利,或者仅就公民而言,是更加关注法律权利,还是更加关注法律义务,决定了法律是权利本位的还是义务本位的,也体现了政治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在我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中,国家权力思想亦即君权思想极为丰富,以至于淹没了臣民的一切权利。义务本位的思想在封建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法律部门的分布来看,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是刑法,次之为行政法,这是因为刑法、行政法都是主要规定臣民义务及其法律责任的法律规范;而作为规范臣民权利的基本法律的民商法则极不发达,并淹没在刑事法律之中,整个法律体系可以用“诸法合一,以刑为主”去概括,而整个法律文化,都以臣民的义务本位为特点。与封建法律的义务本位截然相反,社会主义法律则是权利本位的,宪法作为根本大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列宁曾说过:“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将这张“人民权利的纸”作为法律体系的核心,就为权利本位的法律观念奠定了基调。在我国宪法的结构顺序上,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为仅次于总纲的第二章排列:在“权利和义务”的排列顺序上,先为“权利”后为“义务”;在条文设立的多寡上,宪法以18个条文规定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广泛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只以5个条文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
并且规定了国家对公民权利自由的法律保障和物质保障。“与根本大法的规定相应,我国的基本法律,如民法、刑法、诉讼法等也本着权利本位的原则对公民权利作了广泛的具体的规定和保障。可见,社会主义法治之法的权利本位原则与儒家、法家治国主张中的义务本位思想及其指导下所制定的义务本位的法律,有着质的区别。”[9]即使在民法这样的“私法”(即民与民之间的法律、相对于民与国家之间的“公法”而言的)领域,尽管讲究的是权利义务的对等性。但我们仍然习惯于用人身权、物权、债权这样的权利概念来指代相应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这都是法律权利本位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