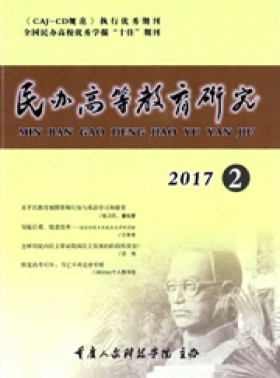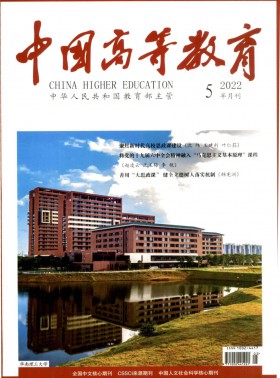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高等教育管理状况与革新建议,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当前,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出台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试点改革的推进,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已然进入深水区,改革实践对理论的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等教育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经济、文化之外而存在的自由个体,其每一步的发展都深深打下了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以及时代环境的烙印。对其发展规律的把握显然不能仅从高等教育自身来寻找,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社会、历史、经济所共同营造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中,高等教育既从中汲取发展的营养,又受到各方因素的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已走过了一百多年曲折发展的历程,其中体现的高等教育与外在环境的互动关系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它为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何以经过几十年的摸索,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变革仍然弊端时显、步履维艰呢?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从来不是超然外在的,而是深受我国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影响的、借用生态学的概念,把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放在文化生态的环境中加以分析,透视制度发生的内在结构和遗传性特征,或许能够解答一些当前制度变革面临的困惑,给改革的路径以启示。遗憾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缺少了从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来思考改革的困境,从而在改革出现了曲折和反复时没能很好地应对,也很难彻底转变其现实生态。文化生态的视角为透视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提供了新的维度,它使我们得以窥见制度变革中的文化制约因素和现实变革中的文化困境。
一、社会历史生态
中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及适宜农业的气候条件,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决定并塑造了中国独特的社会存在,这种独特性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家国一体的社会基本结构。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根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虽然经历了各种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以血缘宗法纽带为特色、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却很少变动[1](P297)。自夏代始,宗君合一的宗法制度就成为了全社会的组织原则,其根本特征是把血缘与政治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为构建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提供了现实基础。于是“国”成了“家”的延伸与放大,“家”则成了“国”的范型与摹本,家国一体的社会基本结构也随之得以确立[2]。这使得传统教育承袭了一种强烈的伦理政治精神。
中国传统社会表现出宗法社会、伦理教育的总特征,家(宗族)国同构与社会控制互为表里,呈现出鲜明的父权主义下的公共管理形态。在正统的儒家思想中,国家官员和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就如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一个关键的比喻)。父权主义是理想的政府及其官吏的施政状态,像家长那样,他们握有不受制约的无上权力,执政者很难具有权力是被授予的、委付的、的意识[3](P2)。权力制衡的理念始终未能发育起来,集权主义文化一脉相承,表现为社会的差异化格局和等级制特征,而奠基于血缘宗法之上的古代伦理教育塑造了国人的中庸思维和追求和谐的旨趣,也打下了我国古代人情化社会的烙印。等级制下的高等教育管理实现着不可替代的国家功能,政治教育化、教育政治化,学在官府、官师一体等都是古代社会的重要表征,这些功能性特点结合传统文化意识对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观西方高等教育,中世纪大学从诞生时起,就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大学与教会、国家的关系也得以制度化,其经久不息的发展得益于制度的构架体现了大学组织本身的特性。大学制度具有与生俱来的特质,即自治与自由。它通过无上权威的、不容撼动的“敕令”或“特许状”的形式来颁布,并由此建立了大学组织牢固的“边界”:“社会与大学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线,大学是历代所积累的知识的贮放中心,那里培养学者纯粹是为了传播学问。”[4]中世纪大学独特的社会存在为制度的建构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的理念得到倡导,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6世纪以后,随着教会的衰落和民族国家的崛起,大学与国家、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中世纪大学国际性和行会组织的特点已不复存在,大学办学多样化逐渐形成,科学开始进入大学。
社会结构的剧烈变革已经对大学的改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19世纪初柏林大学的制度创新正是在这种社会历史环境下应运而生。学术“独立”与物质“依赖”、大学“自治”与政府“控制”是大学在新的时代面临的新的矛盾和冲突,而“文化国家观”巧妙地化解了二者的冲突,大学的自治与独立传统得以维护和保持。根据文化国家观,国家是文化的体现,大学与国家服从于一种共同的理性原则,彼此相互依存。大学作为科学、学术机构本身就是国家事业的一部分,以发展理性为目的。同时,国家的行为也应服从于理性原则,它并不具有指挥理性的任务,而应当为科学活动提供保护和支持,使其理性地按自身的原则得以发展[4]。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成为大学管理制度坚守的根基,并升华为永恒的办学理念和精神。
我国大学自产生起,就打下了传统社会组织结构和传统文化的烙印,大学组织缺乏个性,独立性不强。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皇权统治,家国一体、权力崇拜的意识已经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高度集权的行政组织,缺乏社会公共组织,自治组织薄弱,是中国社会的一贯特征。整个社会的组织都按照行政组织模式构建,造成其同构性和划一性,体现出鲜明的等级制。行政力量的强化和泛化,导致行政逻辑的泛化,古代书院制度就没能脱离皇权政治的运行逻辑而最终凋敝。在我国古代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环境下,仅以西方知识本身为目的的学术自由事实上并不存在。政教合一的传统遭遇自由因素匮乏的文化环境,学术自由的理念自然难以生根开花。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遗传了我国大学与生俱来的基因,制约了近现代大学的自主发展。从1862年同文馆开始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延续了传统习气,完全缺乏西方大学的“行会”精神,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闻所未闻,倒是官僚控制成为一种新传统,学术自由受到行政力量的强烈钳制[5]。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脱胎于半殖民地的时代背景中,曾先后师法日、法、德、美,带有鲜明的“移植”特点,客观上说,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起点不低,汲取了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精华,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现代教育家们都践行着学术自由的原则。然而,透过历史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切终未能与当时社会大环境相契合,从西方移植来的现代大学制度是在“当时政治尚未上轨道的局面下实现的”[4]。蔡元培的教育独立主张也终于流产,其本人也愤然辞职,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终未能摆脱被政府收编的命运。民国初年的大学自治萌生于社会政治原因提供的制度空间,又受益于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人力资源,但却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育与发展。而随后各种政治、军事势力的持续战乱,对大学的组织特性的认识更加模糊甚至被歪曲,大学偏离了作为学术机构的价值,异化为政府的特性,历史积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管理文化和管理体制更加消解了大学自治的发展取向。#p#分页标题#e#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国内外环境,赶超型现代化所强化的行政力量对旧中国大学制度遗产的抛弃和对苏联模式的照搬都对我国大学造成了难以恢复的伤害。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力量和行政控制虽然在逐步退出经济领域,但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影响还相当深远[6](P181-182)。如前所述,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仍然是实质上制约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变革的主要矛盾,多中心的高等教育管理主体远未能培育起来,政府—大学的单一控制模式没有根本改变。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西方现代教育的兴起,无疑得益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裂变,以及教育被纳入新型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社会建构事业中。西方现代教育绝不只是教育观念转型的产物,这场革命的真正动力乃是来源于“现代民族国家、社会以及知识之综合体的形成”[5]。西方现代大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体现的重大作用,不仅体现在政府、市场、社会及大学自身等多方力量博弈中的准确定位,还得益于适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趋势和相对独立的高等教育公共组织的高效运行。
二、文化精神生态
血缘、情感、入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基本生态特征,血缘本位、情感机制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入世意向,使人们把对生命永恒的追求以及超人生的解脱都集中在现实生活中来加以解决。在中国教育传统中十分注意教育的现实性、世俗性,反对知识的纯粹性、客观性,拒绝向纯粹理性方向发展,从而阻碍了科学机制在中国文化中的形成与发展。入世意向的产生也使中国人的世俗文化充满功利主义,急功近利、缺乏理性成为每一个时代转折期的典型表现[2]。我国现代教育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当前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而产生的过度功利化倾向都可以见到其身影。
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承续着中庸心理、追求和谐、人情化社会以及缺乏冒险创新精神,它在适应迅速变动的近现代生活和科学前进的道路上显得蹒跚而艰难。近代中国引进西方高等教育时的工具理性取向和建国后实用主义经验论的泛滥,有着深刻的文化精神根源。高等教育是集中体现时代要求,引领社会变革的主要阵地,无论是“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论争,还是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与文化的大讨论,都关注了大学与现代社会的相融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平理想,有清醒理智又充满人际热情……这种传统精神和文化心理结构,是否在气质性格、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上,使中国人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呢?[1](P312-313)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理性结合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选择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首要的是政治上的原因,但从文化根源来看,主要是由于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有着内在精神的高度契合性。这也是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仍然从骨子里面体现出苏联模式特点的深层原因,高等教育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理念得到全面的贯彻。从文化精神层面来思考高等教育变迁的内在规律,或许能洞见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变革的制约性因素。
中世纪大学是欧洲中世纪文化精神的体现,它凝结着欧洲中世纪文化的核心———基督教文明的灵魂和精髓。基督教文化内含的怀疑与理性精神的萌芽,催生了灿烂的学术自由之花。经院哲学在长期辩论中所形成的理性精神及超然于经院哲学思想之外的自由力量,就是基督教文化为现代大学制度得以生成提供的一片沃土和重要源泉。而文艺复兴则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提供了最根本的精神动力,通过文艺复兴的一系列新文化运动,人文与科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形成了个性解放、崇尚理性的总体文化思潮。它最终积淀成欧洲现代化的文化精神底蕴,这个文化精神底蕴的内核即自由与理性。自由与理性成为西方文化传统之精华,通过文艺复兴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并不用再披上神学的外衣。从此,自由与理性成为贯穿于西方文化的一条主线,渗透于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制度的建构之中,也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所蕴含的精髓。柏林大学基于“纯粹科学”前提的制度设计就是其集中体现,浸润在人文与科学潮流中的大学制度,深刻打上了文化变迁的烙印,文艺复兴成为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文化契机[4]。由此,大学制度的孕育和成长需要良好的制度文化环境。西方现代大学制度遵循的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之所以能一以贯之,是得益于西方文化连绵不断的“自由”与“理性”精神的滋养。
西方大学制度现代化的过程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现代大学制度的演进是一个渐进的复杂过程,在处理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中,不宜用急功近利的政策和强势干预作为制度创新的主要手段。按照历史社会学家腾尼斯的考察,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以及市民工商社会的形成乃是最重要、最突出的“现代性”特征与成就。或者说,现代西方社会正是由这些历史现象建构而成的,从这些现象中能够归纳出现代西方的理性文化精神及其在不同领域的表现。所谓西方现代教育的文化动力,就是基于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对人自身的理性能力的无穷自信,以思考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需要人类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与能力为内在的理论支撑,以培养能够使现代民族国家的各项事业不断进步而个人也能在现代社会获得幸福的“公民”为最后皈依[5]。因此,社会的发展对大学管理制度的变革提出了迫切的需求,大学需要真正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以真正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为根本出发点,这就需要大学文化理念创新和管理制度文化的再造。
以上的历史和比较分析,引起了我们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深刻反思,文化生态的视角折射出了我国大学举步维艰的历史根源,也为相关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路。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植根于政治体制的现实语境和文化精神的历史土壤中,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民主化理应是我国制度文化创新的核心。文化视野中的大学是一个具有民主价值的机构,在去大学外部行政化的过程中,大学能做的就是通过对未来公民民主意识、民主能力的教育与培养,从而建立社会的民主价值体系,引领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从“官本位”转向“民本位”,推进行政体制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7]。我国文化的创新需要冲破大一统文化的桎梏,回归对个体的人文关怀,恢复人的主体性,为学术自由理念的落地生根破除体制和思想障碍。近现代中国文化上的割裂和徘徊,迫切需要一场新的启蒙意义上的文化创新,营造新世纪中西文化交融下的文化生态环境,为高等教育的变革提供文化动力。#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