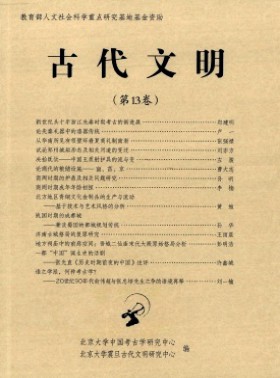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古代思维方式的西方认知,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
安乐哲和郝大维认为,这两种思维方式是并存的,没有优劣之分,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中西方文化发展的轨迹迥异。中国古代在文化发展中选择了关联性思维,而西方则选择了因果性思维。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西方文化的发展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安乐哲和郝大维认为,两个问题框架的思维模式决定了其对宇宙秩序的理解不同。第一问题框架对应的是“美学的秩序”,而第二问题框架则对应的是“理性的秩序”(也称“逻辑的秩序”)。从命名上看,我们能够感受到安乐哲和郝大维对中国文化的青睐。他们一改
西方汉学家“西方中心论”的视角,把中国文化置于与西方相对等的地位来考察。从他们的字里行间,我们甚至能感受到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更具诗性和活力。
二
中西方为何在思维方式上走着两种不同的路径,要廓清内中原因,首先应该考察中西方思维方式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而且是整个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础。古希腊人生活在希腊半岛上,岛上山脉连绵不断,农耕经济始终没有形成规模。海岸线很长,形成了多个港口,利于航海和海上贸易。以港口为中心,形成了大量的城市。海洋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发展了人的独立探索精神。而城市则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们在此自由争论,活跃了思想,促进了文化的多样发展。客观的生活环境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还影响了社会政治制度和思维方式。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城市的繁荣促进了城邦制的形成。人们关注政治,热衷于参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在此过程中,对不合理的旧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抗,要求改革。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天人两分,注重探究世界的本质,强调个体的自由、平等和独立。中国古人则完全不同。中华民族两大发源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以大河为中心的平原地带。人们拥有辽阔而肥沃的土地,可以在其中安居乐业。因此,古代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安土重迁。在生活方式方面,人们相互独立、自给自足而又群居生活。这就使得人和人之间既封闭又互相依赖。人们比较依赖自然,个人的力量常常被淹没。同时,生活的相对固定和地域的相对封闭使得人们关注自己与周围事物和人的关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封闭了人们的思维和视野,但同时却拉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农业经济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只有大自然提供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人类才能安居乐业。因此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就建立了“天人合一”的意识。人不用认识自然,只要顺应就够了。或者说,自然与人类本来就是一体的,认识了人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纵观中国古代文化,我们会发现,无论文人之间在思想认识上有多大的差异,但基本上都赞同天人合一的观点。
从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两个思想流派看,儒家强调人和自然之间应建立和谐的关系,人应该顺应自然;道家认为人本来就是自然的组成部分,人应该回归自然,物我为一。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人富有美学意味的自然观。宗白华对此评论说:“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的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石器铜器),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现出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现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有鉴于此,方才有人断言:“在世界古代各文化系统中,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人与自然,曾发生过像中国古代这样的亲和关系。”与此相对,西方人一直持有天人两分的观点。在这一观点之下,他们强调人类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认为自然是被动的,而人是主动的,人能认识、利用并征服自然。早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普罗太格拉就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认为事物的存在和状态是由人决定的。文艺复兴时期,人的主体性得到进一步彰显,“人是自然的主人”成为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思想。弗兰西斯•培根甚至提出天人对立的自然观,认为人具有强大的认识能力,人借助科学和技术能够战胜自然,并统治自然。因此,西方人崇尚人的主体性和理性。朱立元先生对此评论说:“西方从主客二分出发,人与自然处于相互外在、对立的状态,人对自然的态度是认识、征服、改造、开拓,缺乏亲和关系;反映在艺术和审美文化方面,则是对自然美的发现很晚,评价也较低。可以说,自然之美质在相当长时间里为这种文化所遮蔽。”[4]从中西天人关系的对比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在处理人与自然乃至万事万物的关系上,中国古人的态度更具有一种“美学的”意味———不是冷冰冰的对立,而是彼此亲密无间;不是一方优于另一方,而是平等和谐地共存。
三
用关联性思维来概括中国古代占主流的思维方式并不是从安乐哲和郝大维开始的,最早系统阐述中国关联性思维的是汉学家葛瑞汉。而把关联性思维所对应的第一问题框架思维的宇宙秩序称之为“美学的秩序”则是安乐哲和郝大维的独创。他们认为,与西方理性的、逻辑的思维相比,中国古代的关联性思维更具有“美学的”意味。为什么把中国古代文化所代表的关联性思维称之为“美学的”思维?关联性思维的“美学性”何在?安乐哲和郝大维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对关联性思维特征的描述以及对它与因果性思维的对比性分析来引导读者自己去体会。中国古人认为,宇宙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天人合一,人和自然都包含在这个整体之中。因此,中国人看问题特别讲求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反对离开整体去孤立地研究个体,重视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部分的联系,是一种整体思维。在考察事物时,中国古人习惯于从整体出发,把重点放在探寻不同事物之间的关联上,常常把事物放在一个系统中来观照,从而形成对事物完整的认识。
在思考过程中,常常走着从整体到局部的思维路线。西方人则相反,他们认为天人两分,注重个体的独立作用以及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在考察具体对象时,强调形式结构,注重细节分析,追求精确。在整体和个体的关系上,他们强调由小到大,由一到多,由部分到整体。西方学者用分析的方法观察事物,其目的是寻找事物间的差别和分歧;中国学者则相反,中国人往往从整体出发,用直觉的方法去寻找事物的共同点和联系。理查德•E•尼斯贝特(Richard E.Nisbett)在《人类推理》一书中引用了中国学生的一段话:“你知道,你我之间的差别在于我认为世界是一个圆圈,而你认为它是一条直线。中国人相信世界是在不断变化的,但事物总是不断地回到其先前的状态。他们关注许多现象,寻找事物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不能了解整体你就不能理解局部。西方人生活的世界较为简单、明确。他们把注意力放在突出的物体或人上,而不是更全面的现象上。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控制事件的发生,因为他们了解支配事物行为的规律。”季羡林在谈到中西文化的差别时说,中西文化体系迥异的原因关键在于思维方式:“东方综合、西方分析。所谓‘分析’,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是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许多部分,越分越细……所谓‘综合’就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联成一气,使之变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因此,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为一种“和”文化。这里的“和”有万事万物相互调和的意思,这里面也隐含了中国人一种思考和行为习惯———中庸。其目的就是消解事物的差异和矛盾,达到事物间以及事物内部的共生、共存。从整体上来把握事物,致使中国古代各个学科之间的界线模糊,有时候哲学、美学、文学浑然一体,使得一些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也使得一些看似互相独立的概念之中却有一些无法割断的关联性。如“史”和“诗”在古代就是常常交叉的概念。这些无疑会使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浓厚的“美学”意味。中国思维的整体性和直觉性又必然带来思维的意象性特点。思维的整体性与直觉性总是通过对具体可感的事物进行把握来实现。关联性思维注重事物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是通过实际的形象来表现。因此,观物取象、取象类比是中国古人常常采用的把握事物的方式。《周易》就是在意象性思维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它是对一些形象化的事物、事件或场景进行抽象,把宇宙人生的图景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来展示,使之成为一种可观之象,来指导人们趋吉避凶,从而形成系统的符号理论。在《周易》的基础上,汉代经学又把宇宙人生的图景发展为太极、两仪、三才、五行、天干等,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古代意象性思维的符号理论体系。中国古人在思考问题时常常离不开具体的形象,即使在思考抽象道理时,也往往以对感性事物的把握作为起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常见的比兴、象征、寓言等都是以形象为中介表达古人对外在世界和自身的一种体验和感悟。连道家哲学的基本概念,玄之又玄的“道”也离不开具体的形象:“道之为物,唯恍唯忽。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老子《道德经》第21章)凭直觉观察事物,以形象作为观点的依据,从而领悟到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概念、思想或情感。这种思维方式建立在经验和想象基础之上,是一种直觉思维,与西方逻辑思维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截然不同。安乐哲和郝大维在评价关联性思维的特征时说:“相对而言,关联思维对于逻辑分析不感兴趣,这意味着能够同形象和隐喻相联系的多义性、模糊性和不连贯性,扩展到更具形式的思想成分中了。与重视单义性的理性思维模式适成对照,关联思维将诸成分之间的联系包容于一组形象之中,这保证了这些组成部分的含义模糊而丰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安乐哲与郝大维之所以把中国古代占主流的关联性思维称之为美学的思维,其主要原因是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具有一种美学的意味:“更接近形象的创造和关联的活动,而非那种为理性和感性的证据提供说明的活动。”近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尝试从思维方式出发来研究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种研究思路是有价值的。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其思维方式决定,是其思维方式的外化。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其文化的风貌。希望本文能引起更多的学人从思维方式的视角研究中西文化的差异,重估中国古代文化。
作者:赵霞 刘雨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长春吉林省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