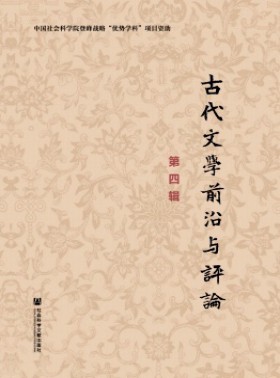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古代文学语图批评图像解读,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
语言和图像是符号世界的两翼,二者在表述与传播上各具特点,存在互补与竞争关系。在当今文学图像化的“读图时代”,随着文学图像学的兴起,“语图批评”应当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新方法,其在古代文学现象、文学活动研究及文学接受、文学史研究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语图批评;文学接受;文学史研究
一、语图关系与“语图批评”
语言和图像是符号世界的两翼,也是人类最为基本的两种叙述传播形式。语言,包括口头语和书面语,侧重于对事物、事件的转述,其生成基于理性思维和逻辑表述,其接受则需要抽象想象和模糊再生成;而图像则侧重于感性描述和具象呈现。也就是说,语言传播需要经过“思维加工→语言转述→抽象想象→逻辑转换→模糊生成”的思维过程,侧重于“思”,其优点是接受者可以发挥想象,具有无穷阐释的空间和可能,即所谓“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时,其生成和传播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语言转述会使表述对象失真,就像“传声筒”游戏一样。而图像传达则是通过“感性描述→具象呈现→感官观赏”来实现,给接受者直接的感官印象,更易保留原物的本真,但也囿于静态画面的局限,图像承载的信息量和解读的空间很有限。语言在复杂叙事和抽象化表述等方面优于图像,而图像在直观视觉传达方面又优于语言,二者因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在文学传播领域产生互补和竞争关系。赵宪章先生将语图关系史分为文字出现之前、文字产生之后和宋元后三个时期[1](P.7)。笔者认为应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前文字时期,先民们交流主要靠口头传达,记述传播主要靠图画,二者体现为“语图一体”的关系,如原始岩画等,具有“以图言说”的特点。这一时期图像是人类最主要的语言符号,纳西族的东巴文字和云南富宁的坡芽歌书即是“语图一体”的遗存。第二个时期是后文字时期。表意的图画符号经过不断演化产生文字,因其书写传播的便捷性和表达的自由性等优势“,以字言说”代替了“以图言说”,文字成为记述传播的主媒介。第三个时期是宋以后,由于纸张的普及和印刷术的发明,使传播进入一个以“纸印文本”为主要媒介的“语图合体”的新时代,文人画和题画诗非常繁盛,插图本戏曲、绣像小说、全相评话等文学样式大行其道,但是传播仍以文字为主、图像为辅。第四个时期是近现代以后,随着摄影、摄像技术的广泛应用,网络的普及及电子传媒的兴盛,传播迈入“电子时代”“读图时代”,文字和图像在传播领域的关系逐渐发生逆转。在文学快餐化的“图像时代”,文学的图像化已十分普遍,大众从影像接受文学的占比甚至超过了书面文字,文本的式微和图像的狂欢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态势。无怪乎有许多学者认为当今新兴传媒的繁荣会导致文学危机,应当打响文学保卫战。随着图像在传播领域的兴起,视觉研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对图像的应用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课题,从而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图像学”。图像学源于西方中世纪的“圣像学”,19世纪发展为图像理论,成为西方近代美术史的基本理论,20世纪前叶,因其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方法,逐渐扩展到各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图像学在语言和文学研究领域的应用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国外关于图像和语言文学的研究才逐渐兴起,产生了很多研究成果。然而,国内图像学研究却较为滞后,起初主要应用于考古学、美术学等领域,关于文学与图像的研究始于新世纪以后,且研究成果不多,主要集中在现当代文学领域,运用图像学的理论来开展古代文学研究者甚少。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古今中外关于二者的探讨可谓源远流长。在我国,早在西晋时期,就有“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张彦远《叙画之源流》)[2](P.6)之说。苏轼也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3](P.1125)至近现代,朱光潜、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等学者关于二者的论述就更多了。在西方,古希腊的西摩尼德斯提出“画是无声诗,诗是有声画”理论。图像学兴起以后,关于二者关系的理论就越来越多了。可见,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是有着深厚渊源和学术积累的。因此,赵宪章先生说:“参照图像研究文学定会呈现另一番天地”,并提出“语图批评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1](P.7),但未明确阐释“语图批评”的方法。笔者认为“,语图批评”是基于图像学的“图式转向”(PictorialTurn)理论和“图像研究分类系统”(IconographicClassificationSystem),利用“语图互文”的关系,来阐释、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西方图像学认为文学图像与文本之间有着明显的“互文性”。英国美术家哈斯克尔认为图像是“过去时代中人的内心精神的发展的一种见证,由此可以通向对特定时代思想及其表征结构的解读。”[4](P.230)鲁迅先生也说:“(读者)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5](P.458)。古代也有类似的记述:“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有以咏其美,不能备其象。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2](P.10),“夫简策有图,非徒工绘事也。盖记所未备者,可按图而穷其胜;记所已备者,可因图而索其精。图为贡幽阐邃之具也。”(欧阳东风《坐隐图跋》)[6](P.65)这些说法,都说明图像之于文学传播和解读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图像可以视为文本的视觉呈现,或者可理解为视觉化的文学形态。文学图像以无声之语,形象直观地讲述着文字不能或无法传达的言外之意。这种艺术再现,不仅仅是对文本简单的图解,更融入了画家对原作的理解和再创造,使图像具有画外之意,丰富和提升了文学作品的内涵旨趣和审美韵味。这也是文学图像学研究的逻辑起点。“语图批评”是基于文学图像学的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是图像学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它是以图像学和文学批评基本理论为基础,从画面入手,对读文本原作,探寻作者和画家对同一题材理解和表现的异同,阐释文字作品未描写或未言明的“言外之意“”韵外之旨”,使读者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
二、“语图批评”与古代文学研究
汉字属表意文字,由图画符号逐渐演化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脱胎于图像,文学和绘画是同源的。汉字的象形和表意特点,决定了图像学之于汉文学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左图右书”之说,《周易》中的象与辞“,河图“”洛书”之说也展现了我国图文并重的文化传统,还有汉赋与汉画、敦煌变文与变相、题画诗与诗意画、小说戏曲与插图、连环画、版画等,都是图文合一的表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图文体”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7](P.76)。因此,明人宋濂说:“古之善绘者,或画《诗》、或图《孝经》、或貌《尔雅》、或象《论语》暨《春秋》,皆附经而行,犹未失其初也。下逮汉魏齐梁之间,《讲学》之有图,《问礼》之有图,《烈女仁智》之有图,致使图史并传,助名教而翼群伦,亦有可观焉。”(《画原》)[8](P.95)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文本时代”,也有许多画家将文学经典摹绘成画以行世,一些教化之书也都是图文并茂的。因中国传统绘画和文学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在古代文艺界有一种“语图互仿”的潮流,即互为题材进行再创作。一是先秦绘画对神话传说的模仿。现今出土的青铜器纹样、帛画、墓室壁画、战国漆画等均有不少表现神话传说的画作,如帛画《人物驭龙图》等。二是汉画对经史故事的演绎。在汉代画像砖和石刻中有许多记述经史故事的作品,如“孔子见老子“”赵氏孤儿”等。三是魏晋以后佛经故事的图像化,如莫高窟壁画中的太子舍身饲虎图等。四是绘画对文学作品的再现,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等。五是文学作品对图像的模仿,如汉赋对汉画的模仿,唐以后大量出现的题画诗等。六是图文合体的形态,宋以后的“文人画”中“诗画一体”很常见。七是以文学典故为题材的画作,如《采薇图》《梦蝶图》等。八是元以后,随着通俗文学的兴起,插图本小说戏曲、全相平话等大量出现,如《全相评话五种》等。九是清代以降出现了许多只用图像表述故事的绘画形式,如行酒令的叶子、近代连环画、木刻版画,直至现当代兴起的漫画书等。图像除模范文学作品之外,还对许多文学现象、文学活动及作家行迹予以记述,如《屈子行吟图》《太白行吟图》《竹林七贤》等。明清时期,文人结社雅集之风兴盛,诗酒唱和的文人风流中大多伴有乐舞书画等艺术活动,分韵赋诗的同时往往作图纪事,如《西园雅集图》《随园雅集图》等。这些图画对直观了解文人结社雅集的场景是很有帮助的。还有许多画作对研究历史文化以及作家生平、思想大有益处,如清代书画鉴赏家卞永誉,正史无传,仅有《清史列传》在其父卞三元的传记后附录了一段简略的介绍,而且是从其46岁开始记述的。幸有《卞永誉画像》传世,共有20幅,记录了其从20岁至45岁期间的一些重要事迹,时间跨度26年,每幅画作者都有自题,且附有王士禛、罗坤、田雯、张豫章、汪元纲等名流文友的题咏。这对把握卞永誉的生平及思想、爱好,甚至康熙朝的一些历史事件,都是非常重要的。如作于其35岁时的《会兵金厦》就描绘了清廷对郑经之役。明清之际还有许多遗民画家,如方以智、屈大均、傅山等的人物画,透过其明人样式的发式、服饰等,即可见出画家的遗民情志和故国之思。再如叶衍兰、叶恭绰《清代学者象传》中侯方域手握画轴和魏礼手持展卷,说明二人也是工于书画的,但后人很少注意其画家身份;《象传》中的洪亮吉肩负长戈,洪亮吉为学者、文臣,乍一看似难以理解,如参照其《万里荷戈集》就会明了,洪亮吉曾因直谏被流放伊犁。从以上诸例,就可以看出图像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三、“语图批评”与文学接受研究
图像在文学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文学接受研究中相应地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大量的文学图像是研究文学发展史和接受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我国古代以文学名作为素材的绘画蔚为大观,如《诗经图》《离骚图》《洛神赋图》《桃源仙境图》《唐诗画谱》《赤壁赋图》等,还有浩如烟海的各类文学作品的插图。这些画作以文学作品为蓝本,融入画家对原作的理解和再创作,可藉以探究文学经典的传播和接受。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刊行版本很多,插图也种类繁多,对不同时期刻本的插图进行比照研究,可以窥见其故事演化及传播的脉络。以《西游记》为例,从唐玄奘取经到《大唐西域记》,从印度史事《罗摩衍那》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从众多“西游”戏到《西游记》的成书,再到种种“西游”续书,作家、画家包括读者赋予孙悟空越来越多的内涵,他逐渐成为“道义”的化身。这从各版本的插图就可形象直观地看出,孙悟空从一个充满野性的猴子逐渐演化为一个超凡入圣的人。《西游记》成书之后,其文本内容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其插图却千差万别,通过“语象”和“图像”的对比,就会对西游故事的传播、定型和接受有更深刻的理解。古代还有许多作家肖像画,较具代表性的有《屈子行吟图》《太白行吟图》《竹林七贤》《陶渊明像》等。这些人物图谱结合像主的人生经历和文学成就,成为其形象写真、精神气度的综合展示,而这些图画都基于画家对于像主人格气质和创作成就的接受。袁行霈先生就认为:“研究陶渊明的接受史,绘画中的陶渊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9](P.22)。他的《陶渊明影像———文学史与绘画史之交叉研究》一书,通过考察历代以陶渊明为题材的画作,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陶渊明人格、文学的影响和接受。
四、“语图批评”与文学史研究
长期以来,文字和图像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是极不平衡的,文学图像很少出现在文学史研究视阈中,即便出现也一般只作为文字的图解。然而,从文学发展的实际来看,图像不仅仅是对文字的图解,更包含着原作未言明的内涵和画家的再创作,从而与文字形成互补的关系。近20年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似乎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停滞,要走出困境,袁晓薇教授认为应当从文学图像学的角度寻找突破口[10](P.75)。对中国文学史的图像学研究是从图像证史开始的。早在20世纪初期,以郑振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学史不应只有文字,还应包含影像资料,这样才可以展现文学史的立体风貌。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率先尝试用图像志的方式叙说文学史,他主张应把许多“著名作家的面目“”书本原来的式样”“人物或其行事”呈现给读者,进而“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11](P.3)全书附录作家肖像、手稿、版本、书影等插图百余幅,初步体现出将图画作为文学史组成部分的意识。郑振铎将文学图像引入文学史研究范畴,向后世文学史家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杨义也主张在“大文学观”下“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至元代)》,一改往常文学史单一的、线性的叙述方式,运用“以图证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将大量的作家肖像、书信、手稿、书影、版本及演绎文学作品或描绘文学现象、文学活动的绘画植入文学史中,使读者对文学发展演变有了更为立体直观的感知。近年来,这种文学史观也逐渐得到学界响应,如傅璇琮《文学编年史》就倡导将“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纳入文学史观照的视野,以呈现文学发展“立体交叉”的真实场景(《文学编年史的设想》)[12](P.625)。廖群《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则利用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或出土文献来考察、解决文学问题。这些新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实际上都是将图像作为“可视证据”,用图像叙录的方式,对历史真相和文学原貌进行视觉重建,进而展示一个立体的、多维的文学生态发展史,这对于打破目前文学史研究的僵局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邱林山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赵宪章,黄春黎.文学与图像———赵宪章教授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2(4).
[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3]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
[4]丁宁.图像缤纷———视觉艺术的文化维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汪廷讷,汪耕.坐隐奕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包兆会“.图文”体中图像的叙述与功用———以传统文学和摄影文学中的图像为例[J].文艺理论研究,2006(4).
[8]俞剑华.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9]袁行霈.古代绘画中的陶渊明[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10]袁晓薇,王开春.从视觉史料到文学图像———文学史的图像学研究刍议[J].安徽史学,2012(3).
[1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12]傅璇琮.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