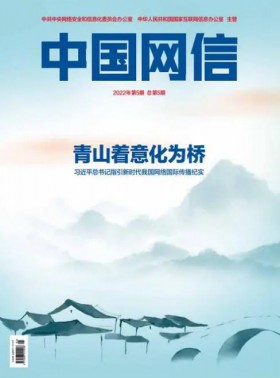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网络舆情事件特征与影响探讨,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网络舆情事件具有独特的特征,这类事件的产生具有偶然性与突发性,参与主体具有分散性和无关联性,事件传播快速,其指向具有公共性,其过程并存理性与非理性,虚拟和现实交织,其扩散表现为非线性,走向则呈现出难控性。网络舆情事件是网民表达民意和利益诉求的折射,通过即时性信息和直播,诠释与设置网络舆情事件的议题,既可倒逼事件的解决,也能加速网络负面消息和网络谣言的产生。网络舆情事件同时为破坏性政治动员提供了基础,对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可能形成严峻挑战。
关键词:网络舆情事件;特征;影响
1网络舆情事件的特征
1.1网络舆情事件的产生具有偶然性与突发性。网络舆情事件具有偶然性,并非所有的网络爆料和外部事件在网络上都能引发网络舆情。同样是信息爆料,能否为媒体和网络意见领袖关注转发引起围观是产生的主因。网络舆情事件具有突发性,表现为网络舆情事件何时爆发,以何种方式爆发、在事件的哪个节点爆发往往没有征兆,出乎人们意料。梳理网络舆情事件可以发现,爆发网络舆情事件有的有先兆,有的无先兆。有先兆的突发性是指造成事件发生的矛盾与问题已经形成,无先兆的突发性多表现为某种特定事件的刺激下的突然爆发。
1.2网络舆情事件的参与主体表现为分散性和无关联性。现实的群体性事件往往有具体的利益目标,参与者大多具有同质性和相似的利益诉求。而网络舆情事件没有特定的关系集群和利益共同体,其参与者不一定与事件有直接的或现实的利益关联,也不一定空间相邻。借助互联网,网民只要发帖、转帖、顶贴、关注、评论和围观,就可成为网络舆情事件的主体,甚至在网民无意识状态下的点赞、顶贴,也可能成为网络舆情事件的主体。事件参与主体可以是草根网民,也可以是体制内精英,他们对网络舆情事件起到不同的作用。青少年网民是重要的参与主体,他们有强烈的正义感和道德感,渴望表达,展现自我,成为关注的焦点,甚至运用恶搞的形式以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网络舆情事件参与主体一般来自不同地域,可能参与目的不同,没有事前的组织性、策划性,甚至与事件不一定有直接利益关系,也没有互相的关联性,随机加入,随机退出,是一种松散的结合。
1.3网络舆情事件的传播具有快速性。Web1.0时代,网络舆情事件一发生,一般在5分钟内就被新闻网站实时抓取,进入后台进行编辑加工2至3个小时后即可置顶,引发网民关注,24小时在网上的跟帖和讨论就会形成一个高潮。Web2.0时代,网络舆情事件中的现实事件发生的同时,微博就开始了“现场直播”,这种即时性使得微博成为第一时间一手信息的媒体。从传播扩散到形成网络舆情指向的大方向,需要的时间大概就是事发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之间,这一时间是危机处理和对舆情风向进行引导的最佳时机[1]。
1.4网络舆情事件的指向呈现出公共性。网络舆情事件虽然主题多元,内容十分丰富,但只有能够吸引网民眼球的事件才有可能引发网络舆情。网络舆情事件主要指向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共价值方面的事件。社会敏感问题经常成为网络舆情事件的焦点,据中国人民大学《舆情月度报告》分析体现为8个方面:一是政府官员违法乱纪行为。二是涉及代表强制国家机器的政法系统、城管队伍。三是涉及代表特权和垄断的政府部门、央企。四是衣食住行等全国性的民生问题。五是社会分配不合理、贫富分化。六是涉及国家利益、民族自豪感。七是重要或敏感国家、地区的突发性事件。八是影响力较大的热点明星的火爆事件等[2]。
1.5网络舆情事件的演化表现为虚拟与现实的交互性。互联网进入Web2.0时代,网络舆情事件呈现虚拟现实化和现实虚拟化交织的态势。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相互渗透趋势明显,界限越来越模糊。网络媒体的社会动员功能日益凸显。网络空间有可能引发现实事件,现实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又能助推网络舆情事件,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联动,甚至相互转化。
1.6网络舆情事件过程并存理性与非理性。网络舆情事件发生后,互联网空间既存在理性的声音,又通常具有明显的情绪性、非理性。情绪性既在网民个体心态中存在,也在网民群体中发生作用。网络舆情事件经过暗示、模仿、情绪感染,参与者的非理性因素增加,情绪性具有明显的“同频共振”效应。由于网络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缺乏现实社会的约束力,网民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表言论,宣泄情绪,其群体极化倾向频发,容易走向一种非理性的状态。分析网络舆情事件时可以发现,网民理性的争论对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而网民受到非理性情绪的支配,则仇官、仇富、仇腐情绪蔓延,出现了对当事人施以网络暴力、网络审判甚至现实生活中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
1.7网络舆情事件的扩散表现为非线性。网络的无界性,使网民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接受信息;网络的快速性,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网络舆情事件的扩散不再遵循传统媒体的线性扩散、单向扩散模式,而是呈现非线性的特征。网络舆情事件的扩散既可能从网络媒体扩散到传统媒体,也有可能是从传统媒体扩散到网络媒体,更可能是互动扩散;既可能是圈层化的网民小众传播几何级的增长,也可能是大众媒介的传播,也可能是网络舆情事件可能是小众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结合。网络舆情事件的扩散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是同质牵连,指与危机具有相同或类似品质的人、事或者产品会受到牵连;二是因果牵连,指某一种危机导致相关危机的爆发;三是扩散牵连,指由于危机造成的心理恐慌使得人们把危机人为扩大到那些根本不存在危机的领域[3]。
1.8网络群体性事件走向具有难控性。由于网络舆情事件具有非线性系统的特征,往往由于微小因素的变化而出现难以预料的演变,网络舆情事件的扩散、衍生、耦合、转化方向具有不确定性。网络舆情矛盾由于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就可能激化。网络舆情事件的走向难控性的原因在于:网络舆论主导权是博弈的产物,既可能是网络意见领袖主导,也可能是由参与议论的网民数量和表达的强度决定,亦有可能是政府权力主导,还有可能受商业资本影响。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有可能传播,网站管理者也无法对网上的海量信息进行控制。
2网络舆情事件的多重影响
网络舆情事件某种程度是网络民意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折射。移动互联网与自媒体融合促使信息传播高速化和实时化,信息内容海量化和多样化,传播方式超时空。一旦发生网络舆情事件,论坛、博客及微博等往往同时引发舆论热议[4]。具有多重影响:
2.1诠释与设置网络舆情事件的议题。媒介具有议程设置功能。Urban经过实证研究发现,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事件,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之中。传播媒介所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就会越高[5]。麦克姆斯(McCombs)和肖(Shaw)证实了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这一猜想。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公众更倾向于关注媒介所关注的议题,并且会依据媒介对各种议题的重视程度而确立自己对事物重要程度的优先顺序和看法[6]。即在媒介中被注意的内容,将被人们感知为最重要的内容。网络舆情事件中,各方通过信息的筛选与编排,冀以影响网民对当前议题以及议题重要程度的认识,引发网民对原议题和衍生议题的持续关注,在情绪以及意见尚未形成的阶段,媒介的议程设置就会影响网民的态度形成。网民作为信息的创造者、传播者和接受者同样可以形成议题。所以,议程设置不仅关注哪些议题应该被强调,同时也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被表达的,对受众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议程设置理论肯定了媒体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作用,并且为本研究中网民、网媒之间的互动提供了理论依据[7]。应该说,网络舆情事件的议题设置决定了什么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网络媒体也许不能决定你如何想、如何做,但在决定你想什么、想什么方面往往比较有效。
2.2倒逼网络舆情事件的解决。网络舆情事件一旦爆发,影响巨大,社会广泛关注,上级政府经常通过问责介入事件的解决,或者促使本级政府对事件高度重视并着力抓紧解决,使事件得以妥善处置,较快平息舆情;同时,对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减少公权行为不当,推进政策与制度的完善起到一定的作用。事件产生的强大舆论压力,倒逼政府治理相关网络事件。一方面,它往往能促使事件得到合理的解决,推动了相关问题公共治理的进程,促进了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网络舆论负面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相关问题的解决。尤其是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突出,对网络舆情事件的治理带来了不确定性和治理难度。
2.3加速了网络负面消息和网络谣言产生。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网民变为公民记者,手机变成直播设备,微博变成直播平台时,传统媒体中的把关人作用缺失。网民成为信息内容的生产者和者,未经核实的信息在互联网空间的传播,加速了网络负面消息和网络谣言产生和传播。谣言无疑是网络舆情事件从酝酿到爆发的催化剂。谣言的传播动员了社会底层民众的情感与力量,尤其在信息较为封闭的环境中,特别是在主流媒体集体“失语”的状态中,谣言便获得了极大的衍生空间。每一个获知事件某一细节的人、每一个渴望事件真相的网民都会变成积极主动的谣言传播者。
2.4为破坏性政治动员提供了基础。互联网和手机的信息传播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着组织动员作用,游行示威集结之快、人数之众、主题之明确、形式之松散、组织者之隐秘的特点,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现[7]。人称“互联网革命思考者”的克莱·舍基指出:“社会性软件让人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组建群体和共同行动的能力。”[8]其无边界、去中心的传播关系网络,使每个网民都能即时“动员”和“被动员”,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社会动员能力。网络舆情事件对现实群体性事件具有放大器和助推器的功能。掌握了互联网技术的普通民众或政治家,利用这些新的工具,在网上及网下组织动员活动,试图对现实事件产生影响甚至是推动社会变革。在突尼斯、埃及事件中,无一例外,网络舆情事件自始至终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不少专家认为,事件的根源还是两国现实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来自互联网的大规模破坏性政治动员,两国政坛不会这么快风云突变。互联网摧枯拉朽,在一些节点上发挥了有目共睹的巨大作用,起到了社会变迁加速器效应。
2.5对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可能形成严峻挑战。2010年底,在突尼斯发生的政局变动中,社会化网络媒体是关键的助推器。虽然在本·阿里的统治下,突尼斯的网络一直处于严密监控状态,但唯独Facebook没有被禁,而1100万突尼斯人中有200万Facebook用户。于是,Facebook和Twitter成为当地示威人群互相联系的最重要阵地,在突尼斯的政局变动中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2010年12月17日失业大学生青年自焚事件更是火上加油,将原本就积累已久的矛盾点燃。由此,在反对派的精心策划与推动下,触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抗议活动。事件爆发之后,本·阿里政府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突尼斯网络监管部门开始封锁关键的新闻网站以及由抗议者创建的Facebook页面,并试图通过窃取异议者和活跃分子的账号监视抗议活动、压制反对声音,政府开始“堵漏”。大量网民通过、加密和VPN(虚拟专用网络)绕过审查。此外,还有匿名组织发动了代号为“突尼斯行动”的网站攻击行为,迫使突尼斯监管机构的网站瘫痪[9]。社交网站等网络新技术带来的强大的传播能力和组织能力,构成了对国家治理的挑战,不仅是中东北非国家,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同等的风险。2011年8月,英国伦敦及周边地区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骚乱事件。8月4日,警方在伦敦北部托特纳姆区射杀了一名年轻男子马克·达根(MarkDuggan),这一事件成了骚乱的“导火索”。此事发生后有人在Facebook上为他建了一个页面,很快便吸引了上万名粉丝。管理员发起了“抗议警察暴行”游行。8月6日约300人聚集在伦敦托特纳姆路警察局附近抗议示威,晚上,示威演变为暴力事件,200多名青年在夜色中朝警察密集投掷砖块、酒瓶、鸡蛋等物品,发动骚乱。接下来的几天,骚乱的规模持续扩大,并且向伦敦周边的伯明翰、利物浦、诺丁汉等城市蔓延。一些骚乱分子利用黑莓手机互相通气,通报警方动向,商讨攻击目标。还有人用群发功能散布大量鼓动骚乱的言论[10]。从上述多个国家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网络舆情事件对现实事件具有放大器和助推器的功能。因此,研究和把握网络舆情事件的特征,对我们遵循新媒体的运作规律,创新观念和管理手段,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实现国家的有序治理具有重要的作用。
作者:王敏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