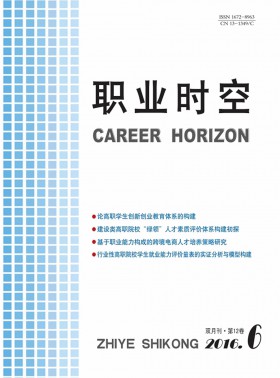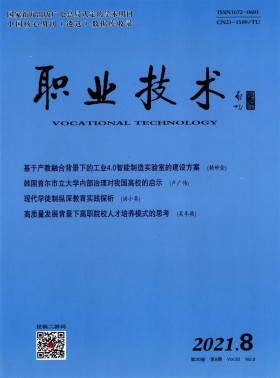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职业教育学重建研究,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
对于我国而言,职业教育是一个舶来品。职业教育概念长期存在争议。“职业教育”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了3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即“字面意义的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因此,基于概念纯净性的原则,当下所谓的职业教育学应该相应分为3个方面,即教育职业学、技术教育学与职业培训学。
关键词:
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名称;职业教育学
在我国,“职业教育”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可以说,我国职业教育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名称之争的历史。概念是学科建设的基石和逻辑起点。尽管职业教育学已经成为在大学传授的一门新兴学问,但是,职业教育概念本身存在的争议,使它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和变数。
一、冲突与融合:职业教育名称嬗变之因
西方社会作为职业教育的原发地,其概念是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比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从萌芽到名称的确立经历了差不多一个世纪之久。而我国作为职业教育的后发地,其发展史是一个对外国职业教育不断移植的历史,而这种移植往往是由各种社会因素激变的结果。从福州船政学堂的开办,到实业教育制度的确立,不过经过了数十年的时间。而自那时起,我国官方对“职业教育”的称谓经历了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从“职业教育”到“技术教育”、从“职业技术教育”到“职业教育”等不断地变换。在这些名称变换的背后,隐藏的是各种外来文化在我国传统土壤里的碰撞与融合。我国职业教育是抗敌御国的副产品,也就是说,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产生的动力不是源于工业化的需求,而是迫于抵抗外侮的压力。[1]鸦片战争的失败是第一股这样的力量。清政府把失败的原因归于列强的坚船利炮。因此,鸦片战争后,为了救亡图存,洋务派开始学习西方的现代科技和教育。它们把目光首先投向了欧洲。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职业技术学校,例如福州船政学堂,就是在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功利思想下创办的。然而,它们不但被顽固派视为“奇技淫巧”,就连洋务派自身也并没有把它们视为真正的教育。当时人们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称为“西艺”,与此相应,职业教育被称为“技艺学”或者“艺学”。但封建社会正统士大夫的价值观是“道本器末”“重义轻利”,而艺则属于“器”和“利”的范畴,因此,这一称呼暗含有贬低之意。到19世纪末维新派那里,职业教育开始出现农工商学、专门之学、专门业学、专门学校等明显西化的称呼。[2]与洋务派和顽固派相比,这些称呼显现了维新派对职业教育的进步态度。但这些称呼也只是对外国同类词语的移植,还说不上是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概念。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二股力量是甲午战争的失败。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产生的巨大威力。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趋势下,开始将学习的目光由欧洲转向日本。1903年创办的《实业教育制度》就是仿自日本,不但如此,就连“实业教育”一词也是转译自日本。[3]在“实业教育”英语原词上,严复和黄炎培的看法略有不同。严复1906年指出:“实业,西名Industries,而实业教育,则谓之Technicaleducation。至所谓实业教育,所抱尤隘,大抵同于工业教育。此诚彼中习俗相沿,我辈莫名其故。”而黄炎培1917年认为:“英语Industrialeducation之名词,依其本义,仅限于工业教育。东方译为实业教育,亦仅限于农工商3种,而医学、教师等不与焉。”[4]从这两位大师的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所面临的困惑,而这种困惑也为以后我国在职业教育概念方面旷日持久的争论埋下了伏笔。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三股力量是新文化运动。辛亥革命前的地主资产阶级,从洋务派到维新派,虽然在学习西方教育的内容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对待教育根本态度却从未改变,即把教育当作拯救垂危封建制度的工具。也就是说,对于职业教育,他们只注重了其经济性的一面。辛亥革命后兴起的作为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以反封建文化,开启民智,追求科学民主为己任,把教育视为一种人的解放的力量。而在这方面,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就是美国。因此,新文化运动把学习对象转移到美国。在向美国学习过程中,职业教育逐渐成为一个盛行的词汇,并汇集成了一股强大的职业教育思潮。在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中,“职业教育”最终取代了“实业教育”。“职业”一词,既体现了“实业”一词“实用”的基本意涵,又含有“个体”的意思,而正是后一点迎合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职业教育”一词对“实业教育”一词的取代,某种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教育观念的变化,即开始由社会本位转向个人本位。例如黄炎培就把“谋个性之发展”作为职业教育三要旨之一。然而,从根本来看,这不过是以一个新的西方概念取代了一个已经“东方化的西方概念”。在当时的职业教育界,围绕着“职业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概念进行了一些争论,这些争论集中体现在黄炎培式的矛盾中。黄炎培一方面认为,职业教育从广义而言,“曰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另一面又认为,从狭义而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能为限”。[5]这种矛盾实际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即杜威式的作为一种进步的教育思想的职业教育与凯兴斯泰纳式的作为欧洲双规学制之一轨的职业教育冲突。黄炎培式的这个矛盾,成为中国职业教育概念中的一个解不开的情结,而对这个情结的探究成为一门学科职业教育的学术开端。新中国的成立,形成了职业教育的第四次转折。按照社会主义精神制订的教育方针中两个原则,即教育与工农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确立了教育制度的基本形态,这就是单轨制和职业化。在各级通向社会的学校中,“专业”成了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专业教育”一词实际上取代了“职业教育”。但专业教育只是一个学科用语,而不是一个体制用语。作为一种体制的职业教育实际上消逝了。职业教育被融合在教育之内。“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了同义词。“”中实行开门办学,不但在专业教育领域,就是在基础教育领域中也呈现广泛的职业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似乎是对杜威“教育即生活”的教育思想的一种实验。改革开放为我国职业教育带来了第五次转变。单纯从职业教育制度自身看,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教育结构改革,实际上是对实业教育制度的复归。似乎一切都又回归到了世纪初的起点上:双轨制、学校本位、初、中、高完整的分级模式。有所不同的是,“实业教育”被一个新的名称“职业技术教育”取代。而与此同时,“职业教育”这一名称又复兴了。自此,人们围绕着这两个名称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最终,《职业教育法》虽然把官方地位赋予“职业教育”,但这场以法律形式形成的裁决,并没有将争论平息。直到今天,“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仍然成为代表不同观点的学者的常用术语。而对于参与争论的一些学者和官员来说,“为职业教育正名”成为他们心中始终无法解开的情结。
二、解构与重建:职业教育学发展之路
由上观之,职业教育概念和名称之争,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其中,既有我国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有各种外来文化之间的龃龉。这种冲突与龃龉,最终使职业教育名称之争演变成一个语言学问题,即如何使“职业教育”做到“名实相符”。其实,即使在西方,“职业教育”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正因为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才用“技术与职业教育与培训”这样一个冗长繁杂的词语来称谓“职业教育”。这就意味着,我国的“职业教育”一词,实际上包含了3个相对独立的概念,即“字面意义的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职业教育学”事实上成了由3种概念生发的相互交错的“知识混合体”。根据分析哲学的观点,概念的混乱实际上反映了人们对事物本身认识的不清。因此,要获得对“职业教育”的客观认识,必须从概念的厘清开始。“职业教育”一词的复杂与异质,影响了其作为“元概念”的学术纯净性。一门学科只有确保其基本概念的纯净性,才可能以它为起点构建起具有严密逻辑关系的知识体系。与“职业教育”一词包含的3个相对独立的概念相对应,当下所谓的职业教育学,实际上包括了性质不同的3个部分。对这3个部分的解析,即谓未来“科学的职业教育学”的3条发展路径。“职业教育学”解析之第一个部分是“教育职业学”。这一学问的基本概念是“字面意义的职业教育”,即“职业教育”一词的汉语语义。从性质来看,它是教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研究的是教育和职业的一般关系,主要涉及以下内容。一是教育对职业有可能形成的影响,比如教育与职业的专门化、职业声望、职业流动等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的研究,会涉及职业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二是作为社会经济之体现的职业有可能对教育形成的影响,比如职业结构对于教育结构、从业素质对于教育内容等等。这方面的研究除了涉及以上两个学科的知识外,还主要涉及教育经济学的知识。三是教育与人的职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这一内容很大部分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一门知识——职业指导学或者叫职业生涯发展规划。职业教育学常把这一学科挂在自己的名下,显然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职业指导作为一种实践学科,不独存在于职业学校内,而是广泛存在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一切教育类型之中。教育职业学没有必要把这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完全纳入自己的囊中,但是,关于人的职业生涯发展的理论部分,应该包括在其研究范围之内。职业教育学解析之第二个部分是“技术教育学”。这一学问的基本概念是“技术教育”,它反映的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在职业教育学的探索过程中,经过最初对普通教育学简单的模仿阶段,“职业教育”一词的先天缺陷为力图建立“独立”的职业教育学的学者所普遍洞悉。为此,他们为职业教育学寻找一个确切的基础概念和演绎范式,进行了颇为艰涩的探索。一种努力是希望继续将职业教育学建立在“职业教育”这一词汇之上。和一般把职业教育学看作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的观点不同,新的努力期望职业教育学以“职业科学”为依托,成为职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从而彻底摆脱对普通教育学的依附,并成为与教育学相平行的一级学科。这种设想的确为职业教育学作为一门学问的独立性展示了前景,然而,且不说所谓的职业学或者职业科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成熟性如何,在这里仍然存在着作为汉语的“职业”与西方职业概念之间的冲突。另一种努力是希望将职业教育学建立在“技术教育”这一词汇之上,也就是将“职业教育学”转换成“技术教育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同时存在着“职业教育学”和“技术教育学”两种名称的学术著作,只是后来由于技术教育在名称之争中的失利,导致这一术语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一些学者之所以重新发现它的价值,也是出于在将职业教育作为一门知识构建的过程中,“职业教育”一词表现出的逻辑性的阙如。从知识分类而言,汉语“技术”一词,准确表达了与理论相对应的那种实践性、应用性的知识,而这也正是狭义的职业教育概念。从职业而言,它界定了职业的一个方面,即技术性职业。因此,作为表达双轨制之一轨的职业教育学基本概念的词汇,“技术教育”比“职业教育”具有更大的纯净性。[6]职业教育学解析之第三个部分是“职业培训学”。这一学问的基本概念是“职业培训”。在我国,虽然法律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将职业培训包含在内,但由于在实践中我国职业教育是学校本位的,与之相应的理论体系——职业教育学,实际上是职业学校教育学。职业培训被视作是成人教育领域或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中的事情,从而被疏离在“正规的”职业教育学范围之外。教育和培训有着本质的区别。培训仅指向专业技能,而教育不但关注专业技能,更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教育,它们有各自的教育哲学和模式。我们引介的西方所谓先进的职教模式,例如CBE、双元制、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等,其实都是职业培训模式。包括被我们称谓的德国“职业教育法”,确切的译名应是“职业培训法”。西方所谓的先进职教模式,也许适合于我国中初级的职业学校,但却难以适应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技术或工程教育。另一方面,职业培训也并不限于狭义的职业教育,而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职业培训”是与“职业教育”或者“技术教育”相并列的概念。这就意味着,职业培训学应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
三、结束语:悲情的终结
我国职业教育是一项充满情怀的事业,这种情怀就是始终视“富国强民”为己任。同时,我国职业教育也是一项充满悲情的事业,在它百年的发展史中充满磕磕绊绊与沉沉浮浮。20世纪初,在“实业救国”的宏大情怀中,拉开了它悲壮的序幕。之后,经过从“实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转变,到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为它献上了华美的祭品。半个世纪后,改革开放为中国职教人为实现先辈未竟的情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不过,这时支撑这种情怀的动力,仍然是源于“弱势群体”的“超越意识”与“过分自尊”。因此,把建立一个可以和普通教育“平起平坐”的规模与体系,作为最现实的目标。改革开放后,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分别占到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总规模的半壁江山。2015年,本科院校转型战略的启动,象征着职业教育独立体系已初具形态。与外在建制的发展相呼应,在学术上也展现出了与普通教育学“平起平坐”的勃勃雄心,即职业教育学力求摆脱普通教育学的窠臼,成为独立设置的一级学科。然而,所谓从初等到高等再到研究生阶段的职业教育独立体系,并非是一个连续体,不同阶段或部分有着不同的特质。也就是说,外在建制的发展,非但没有消除职业教育概念旧有的矛盾,反而使它更加复杂化了。与职业教育外在建制的勃兴相比,作为学术的职业教育仍然困扰于自身的逻辑起点之中。今天,中国再也不是百年前那个“积弱难返”的穷国、弱国,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强国。可以说,我国职教人已圆满实现了前辈“职教报国”的宏大情怀。从某种意义上,工匠精神的提出,正是这一转折的象征。这种象征似乎和当年蔡元培的“大职业教育”有些许相似,但本质却决然不同。今天的职教人,完全可以有理由放下“过分的自尊”,而秉持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理性地去面对“职业教育正名”这样一个原本并非问题的问题;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理性地看清职业教育的来路和明天。
作者:孟景舟 单位:河南科技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周谈辉.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M].台北:三民书局,1985:27.
[2]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22.
[3]李蔺田,王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19.
[4][5]王炳照,阎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五)[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124,116.
[6]孟景舟.解读与重构:多元视角下的职业教育[M].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