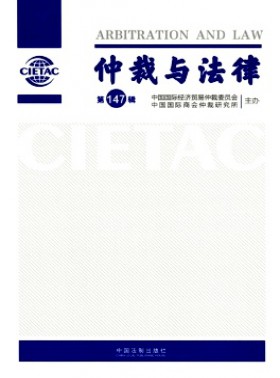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法律规则定义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法律规则定义范文1
(一)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后,未及时组织调查的;
(二)接到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审查或者移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
(三)未将应当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争议移交医学会组织鉴定的;
法律规则定义范文2
范一丁
法律的存在决定于它的实际作用,而法律 的操行则决定于实际的法律 家们的行为。也正是来自于法律 必然的操行需要,决定了律师做为必不可少的法律 从业人员构成法律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 所建立的制度本身就应该不可避免地包括它的实际运行方式,包括使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规则的执行者。固然法官们是在法律 被立法者制定后最核心的规则实在的象征,但毕竟不能等同于规则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需的实际保证,可诉范围似乎是秩序的规则获得法律 强制力保护的范围,但这并不等于社会的秩序范围本身,因为秩序显然来自人们对法律 规则的自觉遵从,这种遵从的自觉所需要的正确性和实在性都需要“从规则到事实的过渡”〈2〉而实现这种过渡的“阐释者”和“整合者”的引导和帮助的必要以及必然正是律 师制度的本原。事实上,有关引导和帮助的作用在法律 意识优先的前提下的重要性,应该是更普遍和更广泛 的。并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成文法)并不等于实际的行为规则的本身,那么,有关对规则的发现,实际上就是对法律的发现是法律 操行的自身需要,这就说明律 师制度并不产生于一种有关于公平实现的平衡 机制的需要,也不是法治所要求的民主的体现(虽然它体现了民主)。如果法律是合理地存在的,那么,它本身就是公平的。律 师制度来自于法律操行的需要,乃是在于法律的存在所决定的。因此,有关于律 师制度仅只是为完成诉讼程序的正义而有的设置的认识,是片面的和局限的。本文试图对律师制度存在的本原性做出探究,当然是从法律 的需要,从法律操行的需要中找到具体。并且,也只有通过这种具体,才有可能使我们对律师制度存在的准 确定位成为可能和必要。显然,律师制度并不是法律制度补充,因为律师职业更多地体现了法律 操行的必然而使律师成为裁判和行为(依照法律而行为)的合二为一者,虽然法律并不赋予其裁判的权力。因为由于法官并不是实际的依照法律规则的行为者,但律师首先要经历的是自我裁 判和对他人行为裁判,从而(参与)他依法律的规则而行为。这种本原性的价值体现对法律而言却往往被忽视、曲解,甚至是一种歧视(对代言人做为个别而决定取舍的任意,并不表明代言人可以没有),因此,我们要做的当然不是在于发现法律 自身应有的反省,而是在于发现我们应该怎样使这种实际存在的原意必然变得更加准确和具体,以致法律自身的存在不因丧失操行或被歪曲而成为空洞的条文。
一 、反题 .“不是” 后面的宾语:现实的曲解和曲解下的存在“存在是合理的”并不能解决“合理的”应该存在的问题,困惑的症结当然在于条件在现实状况下可能改变和未来对于现实条件的改变方面在哪里。也就是说,对应然的和实然的区别,有多少是非正当的,包括实然的存在的虚假和应然的认识的错误。黑格尔说“现实是本质与实在或内与外直接形成的统一。”〈3〉“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个著名的论题,所包含的当然是现实存在的并不等于合理性的全部,同样,合理的并不一定在现实中能得到完全体现,这仍是在于现实本身是一种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关于“不是”实际上应该是确指仍未能体现于现实的“合理”。
1、律师制度不是民主天平上的法码。有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命题其错误是在于法制并非专制。当然法制本身也并不一定体现了民主政治,专制社会同样会有法制 ,但民主社会下的法制所走向的法治化道 路是与人治背道 而驰的,而律师制度做为法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却是法治的必然体现。无疑,有关于民主,是政治学的概念,这是很清楚的,而律师制度是法律制度的必要构成,却并不必然体现民主。以律师制度做为民主的体现,其谬误是在于对专制而言的民主如果说没有法律的保护,同样是不可能通过律师制度来使民主得以体现的。如果法律制度本身没有体现民主,律师制度就无根据去维 护民主,当然,有关于这一论点的产生显然是受有关对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理论的偏狭理解所致,即认为国家意志做为“公意”的强权性,是与个人权利获得维护的“个人意志”的服从性相冲突的,律师因此是这种冲突的平衡需要,但这一认识的错误产生的根由是在于把法制的不恰当和不合理 衍变成“公意”的强权,从而误导了个体(众多个体)对这种不合理对抗,即民主的需要,使律师制度成为一种与法制相对抗的存在 ,这是完全脱离了律师制度本原性的错误。因为没有法律制度的需要,则不会产生律师制度,律师所从事的只能是法律所定制内的工作,而不可能在根本上与之形成对立,以律师制度做为民主制 度天平上的法码,难道 另一端是专制的强大(实际上在尚未摆脱人治影响的现有社会政治条件下,这种专制的存在并非法制设置的本来 含意)在法制范围内的矛盾?这当然不是法制所定义的它的操行的需要,因为法制所追求的是统一,而不是一种无所适从的冲突和矛盾。当然,在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的认识后,我们会发现一个世俗成见的背后,即对于权力拥有者而言,法律是否只是成为当权者(少数人)要求臣民服从的工具?律师制度因此而成为一种游离于这种被制定的法律之外的一种特许,以帮助不具备权力的人们以达到公平,从而体现民主?哈特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用法律的持续性来解释,即“法律有着比它们的制定者和习惯服从他们的那些人持有更长时期的顽强能力”〈4〉。当然,持续性固然可以说明法律是一种“自然”的规则,但不能说明法律仍不可否认的是“人为”的规则,即为当权者意志所左右的规则。当然,哈特也谈到社会的变化,“并不能保证它的持续存在。也许会发生一场革命,社会可能会停止接受这个规则”〈5〉。问题是这种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法律变化,当然会越来越多地体现了“公意”,即民主,但无论怎样,律师所遵循的规则,却是在于这个法律制度本身。也不是出其左右,并甚至与之形成对抗。公平、正义这一法律的基本命题同样也是社会整体观念的命题,并不能说明在法律不能兑现时,律师有超出其上的权力和理由来运用“法律”使之体现,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当然,从这一问题所引伸出的有关社会个体的“公众”(个别的一般)所要求的“正义”的实现和“公平”的保护,其代言人即律师们的存在,是否应在于法律之外的“合理”(对于权力的不受约束而言)?以及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的“公意”而言(整体的一般)在遭到背弃时(民主不能体现时)所需要的正义维 护者和牺牲者?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的律师制度的设置就并非是法律制度而是社会政治制度的需要,也就是我们在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1980年《律师暂行条例》第1条)和“律 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1996年《律师法》第2 条)不同定义之间选 择的犹豫和不清所反映出的问题:固然律师可以做为”法律 的发现者“而为法律操行,但法律 做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其产生是在于立法者,然而律 师仅仅是依 据 法律 的实践者。当然,我们在此有关于律 师制度不是民主天平一端的法码的认识需要,不是在于一种对概念定义恰当的寻求,对实际意义而言,那种过重对于使命和职责的加负,往往会导致在其权利不具有状况下的失 衡,以及因这种失衡所带来的种种责难,甚至是处罚(如权力对律 师行业的排斥,法律对律师调查中伪证的不合理追究)。另一方面,更进一步说,律师制度不是法律所体现的民主天平一端的法码,因为法律做为一种实在,其对民主的体现是法律自身的问题,诉讼中的对抗(公诉案件或民事诉讼中的抗辩式诉讼)并非是为体现民主,而是为体现法律 .从实际角度出发,有关对抗辩的”民主“,是把”公意“中的”正义“之要求强加于律师职责之中,那么,其对立方的不明不白(尤其对公诉案件而言,抗辩中这种出发点不明确所致的对抗,即便是出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但与维护国家权益的公诉人相比,显得如此的孱弱和无力),往往使公正和公平变成空谈(对一已之公正与对他人之公正被区别对待,等于无公正可言),显然,法律让律师为其操行,并不是出于一种政治上民主需要的考虑,乃是在于法律 所导向的法治如果是民主制度下的产物,那么,法律本身就是民主的,律师制度不再是一种”让人说话“的制 度(不是法律制度),而是让人遵守法律的制度。
2.律师制度不是程序公正的制衡杠杆程序的公正在于其自身本质以及对这种本质的表现是正常和有效的。引起程序的诉权得以正当体现和保护是程序实际存在基础,但有别于政治制度通过民主所体现的文明和进步,程序的文明和进步是在于其自身的素质,而不是通过“民主”来实现。如果程序是在法制体现专制的情况下产生的,那么,对它的遵循本身就是不民主的,不可能在这种程序规则范围内来实现民主。“当事人在诉讼中平等地享有诉权,这就决定了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上地位平等。”〈6〉诉权的平等所带来的衡平,并不是民主所对应的人权概念的体现,即在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人们对自身权力平等的要求是在于这种平等性体现本身往往是不充分和不确定的,因此,民主所体现的就是对人权平等要求的不断改进使之能够充分反映这种要求的制度。但法定程序无疑是确定的,如果程序的公正体现了民主,那么,这种体现也应该是在民主体制下才能实现的。当然,程序的公正所要求的衡平并非一定是民主的,即并非一定体现了人权平等的要求,但即便是对于不民主的程序而言,其衡平仍是可以实现的,即对诉权的相对平等的保证(在某种范围内对诉权范围的缩小,即是不民主的表现),那么,律师制度的代言和代行作用显然不能张扬“民主”,而代言和代行所遵循的程序规则只能是程序所要求实现的方向和目的的体现,即程序如果自身是有衡平的机制,那么,它就是衡平的,至少可以通过如前所言的诉权平等实现,而不必有律师的代行作用它才是衡平的,或者是只有在这种代言和代行作用充分有效体现时(正确体现)才有程序的衡平。不过,在有关于法律还没有被定制为规则时(这种情况应该是更多地普遍存在),也就是即便有法律的一般规则的存在,而尚需依靠法律职业人员去发现并实践那些在一般规则下的具体行为规则时,律师制度仍是程序的组成部份,而不是一种制度为体现或证明其是文明的(民主的)而做的选择。因为做为程序的运行所要求的操行者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律师职业不同于法官,是在于法律存在的两个必然前提:法律权力的体现者(法官)和法律的遵循行者(对律师而言是委托人)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律师职业是代表法律的遵循者的权利要有程序公正的待遇,这是相对角度不同的法律必需,但不是对立的,也不是一种来自于法律的关怀或防止法官的错误裁判的保险机制,它只是程序规则的必然构成。正是由于以上可能的某些导致错误认识发生和延伸的认识道 路的分岔口的存 在,往往会造成体制自身的部分紊乱而不易找到症结,在这方面,有以下几种表现是尚未被认识清楚的:(1)控辩对抗的支点失衡不是司法不能独立的表现。往往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不能充分发挥辩护应有的作用归结为司法活动受到政治和社会的条件因素的干扰,尤其是人治因素的干拢,从而不能体现实体法制的真正目的,这是自扰视线的做法,因为包括法官的素质(也包括法官的薪水不够高),党政领导,甚至是一级政法领导的旨意,均是左右法院独立司法的重要因素,与这些因素相比较,律师的(个人)辩护意见,显得何其微不足道 ,因此,控辩对抗失衡是“人自无力奈何天”的“现实状况”,但事实上,这些实际上确实左右(妨碍)了司法独立的重要因素,肯定不是程序规则内的,那么,这些因素无论如何其有决定性的重要影响力,都不是同一逻辑前提的对等问题,因为毕竟律师制度是法制规则所需要的必然构成,程序规则对律师的需要是对遵行规则的需要,对规则的不遵行,即政治的或社会的干扰因素,不是在程序规则范围内的因素,自然不可能由程序去解决,也就是说,控辩对抗失衡在当前普遍的存在,较多地引起人们重视和担忧,但更多地是去考虑程序之外的若干因素作用,以及对这些因素作用力的消除,但这对程序规则而言,无疑是强其所难的自我扰乱。固然法律应是政治和社会意志的反映,但这种反映毕竟是有所差距的,正是这种差距,使法律规则的缺漏成为不可避免。而对于程序而言,其实践性的重要对于其完善性何其重要,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对法律的实体性的长期的实践过程,是不可能找到有效(有用和有效率)的方法的,方法即是具体的行为规则,这无疑又是某二个差距。这一差距的存在同样会导致那种在观念上的差距去发现规则的漏洞,从而加以利用,但另一方面,则也存在着在技术上(实践性的差距)所导致的欲行不能,正方是找不到依据,反方是有漏洞可寻,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律师制度本身的属性所能做的论述,只能是在现有的程序规则下,对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改进进行讨论。这也就是如前所说的,我们对控辩对抗失衡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要找到它的问题所在,我们只能从程序规则本身缺漏上去找。当然,这样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这种失衡存在的原因是律 师制度在程序规则中的支点低(对公诉人制度而言),并且不牢靠,失衡是自然的,问题是似乎从形式上看这种失衡是人为的,或者导致另一种认识,即认为这种控辩对抗的程序规则是一种附加的设置,即来自于“民主”或者诸如避免错案,查明事实的需要而设置的,由于这种设置的需要是在于程序规则之外(程序规则无法体现社会公意性的“民主”,也无法体现政治权力对私权者的体恤,以及控辩对抗虽有助于查清事实,但律师制度决不是为查清事实而设定的等等),因此,程序规则对这种设置的“添加性”,显然存在着“异类”的“异体排斥”,当然,因此会造成法官和公诉人“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的当然正当。问题是我们一直回避(或忘记?),程序规则的这种“排异性”是如何地不正常,程序的正当被要求律师要如何诚实(老实从宽的被告人对坦白事实负责,而不是对规则的严格执行负责),如何地说情(说“法”法官难道 “不懂”)。这些显然不是规则的“规则”,让律师负担了不该有的责任和风险,失去程序规则要体现正当的本意,因为这种正当本身应当在规则之中,而不是在规则之外,难道 我们还不清楚程序规则在现有状况下的“目的”么?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状况下明显的“不是”背后的原因,当然这种原因有待进一步认识。(2)辩论式审判的律师制度不是程序公正的天平。程序规则中的律师制,并不能保证程序是公正的,但程序规则中若没有律师制,则程序一定是不公正的。因此,律师制在辩论式 审判中的对抗,是程序公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有了这种对抗中的律师制,就可以确保程序的公正,对这一问题的引伸是,似乎有了律师制,法律就已给了公正,就无须对实践的定制予以具体。律师制度在辩论式的审判中,被自封为公正的天平,法官居中,而律师是踩跷跷板的,天平职责的神圣但无根据(没有规则),与跷跷板的任意(有规则而不循的其实并不可能,这种认识只是一种假象)之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被假象所蒙蔽、扰乱,从而导致对律师制度的利用(用于装饰正义),蔑视(仍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不解(律师说话不算数),指责(对法律或事实可以不负责,任予以曲解),甚至愤怒(拉关系走后门)。当然问题似乎仍主要是制度的规则不完善,也就是程序设置的缺陷,这固然是正确的认识,但另一方面的问题被忽略的是,在症结之上的种种混乱认识被利用来制造假象,是这些假象后的混乱认识阻碍或扰乱了程序设置的自我完善,因此,清除这些错误的认识或理论则是首当其冲的。对于这些错误认识或理论,当然不可能一一例举,但可举其要而示之:A.审判中的法官中心主义论。即程序规则最终决定由法官对事实和证据做出取舍,对法律决定适用,那么一切既然都取决于法官,其它的制度设置只不过是形式上的需要。B.律师职责扩张论。即认为律师是公正的化身,是法制的天平,法官只是吹哨子的,因此律师为程序的不公正负责(不公正是律师造成的 )或律师能确保公正而不为(或为之甚少),是应该负有对委托的责任的(收钱办不了事),〈6〉以致负有对社会的责任。〈7〉C.律师与委托人责权等同论。律师的权利和责任是委托人权责的翻版,在诉讼中设置律师制度只不过是社会需要而被程序所允许,程序对律师制度的被动性,是在于给程序参与者(诉讼当事人)以相对于对法律的权力(专断的裁判权)的公正,是在诉权保障上的措施。给当事人说话的机会,也给律师说话的机,D.完全的国家或社会权力派生论。即律师制对程序公正而言,是国家职权或社会公意的需要。律师制的首要目的是对社会正义、程序公正负责。对当事人的委托的接收,只不过是通过这种委托的形式,以实现社会或国家所需要的秩序,这种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当事人的真正内在需要。把私权与公益权、公众的“合意”等同。如此等等 , 偏执和混同,似乎在根源上是由于无法或者是还没有找倒一种正确的表达,尤其对本土性而言,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法制和法治对律师制度的存在需要,还没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恰当表达,这不仅仅是对存在予以解释和认识,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清 和 认识不到根源,反过来表明律师制度对程序公正而言,尚未有充分本原意 义的 体现,或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 律师制度不是通常意义的中介组织制度的翻版。
将律师事务所定性为社会中介组织,意在通过其原有属性的转换,更明确或有效(具体的)地体现社会正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行等的需要,即将原有的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的具有从属国家主体的特性去掉,实际上是为保证国家行政机关在诉讼程序或其它法律 规则运行程序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当然,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者”从属于社会,这是无疑的,但“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仅只是其职业特征,并不是其属性定义,律师职业的工作性质,包括对象范围、工作内容等,是这一定义的全部,但这个陈述性的定义并不是属性定义,并不能从这一定义自然引伸出律师是中介人,律师事务所是中介组织,除非对“中介组织”特别定义,但对通常意义下的“中介组织”,是显然不能揭示律师制度的本质的。首先,“中介组织”没有表现出律师制度与法律不可分的关联性,因为做为“中介组织”在通常意义下是不能体现是为法律的操行而设置的;其次,“中介”做为“媒介”所要连接的对象意指不明。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对有关“中介组织”的定义详加议论,重要的是因这种概念的混乱实质上反映了律师制度的本质属性在未被认识清楚以前,其作用尚未被恰当和有效地充分发挥,同时,也正因为不恰当和无益的作用混杂,使法制规则所求秩序自身受到干扰,从而反过来让人怀凝,即律师度的作用何在?在这方面,可有如下一些表现反映了这些问题:A.掮客式的谋利者。“中介性”的职责根据(与法律的关系在此概念下变得模糊),并不是实质上的无法定职责,只是在非诉职业活动中,现有法律对律师职责均少有规定,熟习和对法律的认知并不是律师职责的根据,律师似乎因此而被社会认为仅只是为谋利而行事,正因为这种认识,律 师的做为更被认为是没有职业准则(内部的执业规范度江不为人们所认识),对法律可以凭其熟习而曲解(钻空子),因而是没有原则的,虽然他们是在操做法律 ,法律却因此而被减损其权威。B.是社会人员而无职业尊严。事实上,《律师法》所定义的“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 服务的人员”,并没有定义律师就是“自由职业者”,更准确地说,并没有否认律师制度是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因而没有清楚明确律师职业本身是法律所赋予的特定职业。“社会人员”显然是一个由“中介组织”概念所必然引发的认识概念,因为“中介组织”所反映出的职业无国家法定根据的特点,是其职责没有根据。不能说一个商人有其自身的法定职责,其存在就是为谋利,当然要在法定范围内谋利,但守法并不是法定职责(特定的),正因为如此,律师制度往往被认为是在法定程序之外,而与当事人等 同,因而享有与当事人等同的自由(无需为法律负责,应该注意,遵守法律并不是这种负责的体现),并因此只能得到与当事人同等的待遇(言论只代表一方的私利),调查、阅卷、甚至会见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并不是一种有法律特定职责的体现,而仅只是一种给予的方便,这种方便之所以是优待,是因为律师这种行业有固定性(中介组织的组织特性之一),因此,“中介性”降低了律师职业的“法律工作者”的地位,因此而不具有法律制度的必要构成的特性。C.职责模糊的“中间者”。对法律负责和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负责的规定(《律师法》第一条),并没有建立起有关这种责任的遵循规则。事实上,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言,既然是合法的权益,就应当是获得法律的保护,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也就是实现了这种保护,显然对律师职责的这种强调(指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指向的对立面,应该是其他有违法律的行为个体,包括司法裁判者、司法执行者。但这种对立所造 成的律师身份的混同,代表法律所体现的公意抑或从当事人利益出发的个人意志?这是职责不清楚的根源,显然某种明确的念意是确切定义为在法律实施和当事人合法利益实现之间充当沟通的“中间人”,那么,这种“中间人”的角色职责要求是向当事人阐释还是要法律了解事实(为合法权益而辩析、证明)?或者是两者皆而有之,甚至更进一步是为实现这种责任而创制规则?问题是这种“中间人”角色的职责不明立意,使其行为因缺少规则以及来自于“中间人”定义本身的含混,必然导致歧义,即律师因法律的赋予而获得权利,因当事人利益的需求而获得存在,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对权利的利用,即对法律 的适用成为利用,或者蒙蔽,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原因当然是在于法律 对其权利的赋予是形式上的,含混不清的,也就是既然律师的权利(特权)并不具有确切的内涵,那么对其违责的追究成为不可能,因为律师的特权既然是必需的,那么其角色就不是面目模糊的“中间人”,“中间人”降低了法律权威,将律师行为等同于一般的守法行为,而不是执法者行为,至少在执法者的职责主义上,律师不是“中间人”。
法律规则定义范文3
【关键词】法律要素 规则 原则 概念
一、法律微观结构的探析
法律结构是指由各个必备的法律要素有机构成的法律系统。而法律要素是具体组成法律结构的基本因素,由于认识和研究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所选取的理论角度存在差异,历史上也就产生了关于法律要素的诸多理论,主要代表是奥斯丁的命令说,哈特的规则说,德沃金的原则说,庞德的律令、理想、技术说,以及中国的三要素说。
奥斯丁法律定义的基本因素包括:命令、、责任以及法律制裁。 奥斯丁认为,每一种法律或规则就是一个命令。具体讲,首先,命令包含了一种希望和一种恶。其次,命令包含了责任、制裁和义务含义。奥斯丁去世后其理论对英国法学的影响有百年之久。
直到1961年, 牛津大学教授哈特出版了《法律的概念》一书,哈特分别从内容、起源模式和适用范围三个方面展开对奥斯汀的批判。哈特认为奥斯丁关于法律的定义是一个“失败的记录”。同时哈特提出“法律规则说”即主要规则与次要规则相结合,主要规则科以义务, 次要规则是寄生在第一种类型的规则之上的规则。此外还有三种补救规则, 分别是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
60年代中期由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德沃金发起哈特德沃金之争,从规则的缺陷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两个方面引出了德沃金的法律原则说,德沃金通过引述两个著名的疑难案件,提出了与法律规则全然不同的法律原则的概念,他认为原则的适用则具有一种分量的向度,且原则的属性包括内容上的妥当感和形式上的制度支持,妥当感居于首位,而仅以承认规则的形式并不能完全辨认原则;德沃金认为,法律原则同样是法官裁断案件时应当依据的标准,在没有规则遵循时,原则对法官的行为也具有约束力,所以原则是必不可少的。
庞德是社会法学家,所以其对法律结构的观点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的,他认为:“法律就是一种制度,它是依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运用权威性律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他所讲的律令、技术、理想说包括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的法律结构为三要素说,三要素包括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法律概念是指对各种法律的事件、状态、行为进行概括抽象出他们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或者说是法律术语。法律规则是指法律中赋予一种事实状态已明确法律效果的一般性规定,法律规则的特性具有普遍性、确定性、指导性、可预见性、可操作性。法律原则是指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其特征为抽象性、稳定性、涵盖面广、逻辑结构简单等。
中国之所以采取三要素说,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受前苏联及西方法律思想的影响。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决定当时处于摸索中的中国以苏联为模仿的对象,从而一些学术型的问题也照搬苏联的,受到原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体系的影响较大,并且当时奥斯丁的理论对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此中国的法的三要素中将法律概念作为要素之一,改革开放后我国受西方法理学的影响,自然也受到西方法理学说的影响,因此法律规则,法律原则也是法的要素。可见我国的法理学发展是建立在借鉴国外法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
二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虽然法的三要素是借鉴国外的理论,但也受中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为什么这三个内容作为中国的法的要素呢,首先是中国古代历来人们的思维就是认识一个问题,先要明白它的最本质的性质,这种性质就是从概念中表现出来的,且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制度虽未明确规定概念,但都对相关法律词汇做了说明。再者,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早就具有法律规则的一般特征了。最后,关于法律原则,古代立法中也有所体现,如“亲亲得相首匿”等,虽然这些都明显带有儒家政治特色,但都是法的组成部分。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马克思关于法的理论对中国有着影响深远。最明显的就是对法律概念的界定上,他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其统治目的而制定的,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称。而中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主人,所以说对法律概念的这个界定明确了法是维护人民的利益的,这也是对我国国体的体现。
因此,可以说,对法的要素的界定是借鉴外国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和国情而成立的,可以说法的三要素理论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从而也对中国的法律制度的认识和适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让人们从同一的共识出发认识法律,同时也从最大限度上缩小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使人民的利益能得到较好的维护。
二、结束语
笔者认为中国的法的三要素说就是适合当今的中国国情的理论,也为普遍的学者所认同,所以是适当的理论,当然随着时代的转变,及人们对法律更深层次的理解,它可能会被重新定义,这是知识发展的必然,相信我国的法学理论会有更深层次的发展的。
参考文献:
[1][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范围[M].刘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2]甘怀德.从命令到规则—哈特对奥斯丁的批判[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05).
法律规则定义范文4
我国《海商法》第42条关于托运人定义的规定,是借鉴了《汉堡规则》的规定,尽管二者在用词上略有不同,但基本含义却并没有什么重大差别。根据我国《海商法》第42条的规定,托运人有两种定义,它们之间用分号分开,给人的印象是:托运人可以是一个,也可以同时有两个,需要在实际业务中加以鉴别。而《汉堡规则》在规定两种托运人定义的条文之间使用了“或者”(or)一词,给人的印象是:托运人只有一个,但需要在每次运输中加以鉴别。《汉堡规则》之所以给托运人下了这样的定义,可能是基于如下考虑:第一,突破传统的合同法理论,将实际交付货物的人纳入托运人的范畴,避免使运输合同或相关法律被不恰当的规避;第二,通过运输合同之外的其他合同来明确买卖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且买方可通过受让提单而实现其权利,这就解除了承运人为何人履行运输合同的担心,只要交付的货物符合运输合同即可运送;再次,将卖方记载为托运人有利于卖方通过保留货物权利而保护货款请求权,这种服务于贸易的安排会促进贸易的开展;最后,卖方通过提单记载成为由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可以直接承担支付运费、申报货物等义务与责任,有利于承运人权利的保护。但这么规定,在给贸易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一定的不确定性:例如在FOB价格条件下,买方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而卖方将货物交付承运人,那么到底其中一方是托运人还是双方都应视作托运人?FOB价格条件下,卖方作为托运人,其权利义务如何确定?当FOB卖方实际将货物交予承运人,但其名称却没有载入提单“托运人”一栏,此时其法律地位又将如何确定?由于我国《海商法》基本采纳了《汉堡规则》的托运人的定义和其他相关条款,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法学家早在20年前就预见到的复杂问题。[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正式实施后,因为《合同法》并没有给托运人下定义,根据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特别法没有作出不同规定时,《合同法》总则与运输合同一章的规定适用于各种运输方式,因此在海上货物运输领域也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以下问题:
1、《合同法》第308条:“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当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问题是:此项权利由FOB货物的买方还是卖方享有,如果买卖双方都向承运人提出请求,承运人如何处理?
2、《合同法》第319条:“多式联运经营人收到托运人交付的货物时,应当签发多式联运单据。按照托运人的要求,多式联运单据可以是可转让单据,也可以是不可转让单据。”问题是:在多式联运的情况下,多式联运经营人是否必须将多式联运单据签发给FOB货物的卖方?究竟应该按哪个托运人的要求签发多式联运单据?
3、《合同法》第320条:“因托运人托运货物时的过错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的,即使托运人已经转让多式联运单据,托运人仍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是:当因为FOB货物的卖方的过错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的,FOB货物的买方是否需要对此种损失承担责任?
近几年来,我国已发生了多起与托运人概念相关的海事诉讼案,对同类型的案件,国内的司法判决往往差别很大,归根到底在于我国《海商法》关于托运人的定义存在缺陷。
一、 托运人定义的由来
《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中没有关于托运人定义的规定。《海牙规则》第1条定义中规定:“承运人”,包括与托运人订有运输契约的船舶所有人或承租人。《海牙——维斯比规则》没有对承运人的概念做出修改。虽然《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没有给“托运人”下定义,但由于它们规定承运人是指和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人,因此也可以理解为公约认为托运人是指和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人。
《汉堡规则》是第一个对托运人下定义的公约。在《汉堡规则》中设置托运人的定义的提案是由突尼斯和奥地利提出的,提案提出后引起了激烈的意见冲突。以印度为首的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明确限定作为运输合同权利、义务主体的托运人的定义是必不可少的;而日本、挪威等发达国家则认为,由于公约中和以前的《海牙规则》等一样,托运人根据情况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被使用的,设置定义反而会造成实体规定解释的困难。对提案投票的结果是27票赞成,25票反对,4票弃权。决定设置定义的提案虽勉强通过,但具体条文案怎么也得不到半数支持,经过特别工作组反复工作后,才最后通过。
国际公约是一种妥协的产物,《汉堡规则》虽然最后设置了“托运人”的定义,但对定义条文如何解释却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如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发运货物既然是两种标准,是同时符合两种标准才能称为托运人,还是只要符合标准之一就能称为托运人?如果是只要符合标准之一就能称为托运人,会不会根据两个标准会有两个托运人?这两个托运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汉堡规则》本身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公约的起草者希望各国根据自己的国内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二、 我国《海商法》托运人定义的不足
笔者认为,根据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海商法》关于托运人定义规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两类托运人之间的关系混乱
《海商法》关于托运人的定义在两者之间并无任何联结词,因此,第42条所定义的两种托运人之间的关系不得而知。国内学者通常认为,《海商法》中有关“托运人”的两个句子为选择关系,即只需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即可视为《海商法》下的托运人[2]。根据这个观点,在CIF和CFR价格条件下,一般只存在一个托运人,而在FOB价格条件下,则同时存在两个托运人。但这样解释,同样面临着如何划分两种托运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的难题。《海商法》所定义的两种托运人,其托运人法律地位的取得是基于不同的原因——交货或者缔约,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应该有所区别,但《海商法》却不加区分,仅笼统的规定了托运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这样必然导致两类托运人的权利、义务发生重叠,易引起当事人之间的商务纠纷并造成司法审判困难。
2、定义的表达语义重叠,晦涩难懂
《海商法》对托运人下定义时,无论缔约托运人还是实际托运人都规定了三种情况:①本人;②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③委托他人为本人。从法律角度来看,“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指的就是托运人的人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从严格意义上讲,本身就包括在托运人的概念中,以托运人的人的身份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等同于托运人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其法律后果是相同的,产生的责任也同样由托运人来承担。因此取消“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对托运人或实际托运人的定义并没有什么影响。
如何理解“委托他人为本人”目前仍有争议[3],笔者认为,从字面看,“委托他人为本人”应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受托人以委托人的名义从事所受托事项,此时构成直接,与托运人定义中的“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构成语义重复。第二种情况是受托人仅表明自己人的身份,而没有披露谁是被人,此时应构成隐名[4],适用《合同法》第402条[5]的规定。在《合同法》实施以前,《民法通则》关于的规定仅限于直接[6],《合同法》第402条突破了《民法通则》中仅限于显名的规定,据此规定,隐名的效果应该和显名的效果一致[7]。第三种情况是受托人直接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所受托的事项,根本不表明自己为他人的身份,更不指明委托人,此时应适用《合同法》第403条和第414条的规定。《合同法》第403条第1款实际上确立了委托人介入合同的规则,委托人介入的效果,大体上等同于未披露委托人的转化为披露委托人的,在这种情况下,托运人与实际托运人是确定的,这与《海商法》的立法意图一致;《合同法》第403条第2款的规定实际上确立了第三人的选择权,此时,托运人还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究竟谁是托运人取决于第三人的选择,这与《海商法》的立法本意并不一致。《合同法》第414条的规定[8]仅限于贸易活动的范围之内,而不适用于运输。可见,《海商法》第42条第3款托运人定义中规定的“委托他人为本人”应该仅指《合同法》第402条和第403条第1款规定的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9]尽管最终没有实施,但对于理论探讨来说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第11条规定:“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承运人,不管受托人是否以委托人名义办理委托事项,该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托运人均为委托人本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办理委托事项的,受托人与委托人对托运人的义务负连带责任。”也就是说,原则上委托人本人是托运人或实际托运人,在受托人以自己名义办理委托事项时,则受托人与委托人对托运人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规定与《合同法》委托合同的规定略有不同。前已述及,《合同法》第403条第2款实际上确立了第三人的选择权,即此时责任主体是单一的,不存在连带责任。最高院征求意见稿对承运人的保护较《合同法》和《海商法》规定为高。
《海商法》颁布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仅限于直接,对于实践中存在的间接问题,则要通过两个合同关系来解决。《海商法》之所以规定了“委托他人为本人”其意图就是想绕过人[10],通过法律直接赋予被人主体资格来解决承运人与托运人和实际托运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样的规定,在当时的立法背景下具有先进性,但同时也给托运人或实际托运人的识别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合同法》生效后,我国法律对制度的规定更加趋于完善。此外,《合同法》第403条第2款的规定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相对而言,善意第三人承运人的权利更应受到保护,此时赋予其选择权也是公平合理的。因此,建议取消《海商法》第42条中的“委托他人为本人”。
3、定义用语不规范
“委托”这一用语在《合同法》生效以后有了特定的涵义。《合同法》在第21章对委托合同做出了专门规定。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合同法》委托合同的规定与《海商法》托运人定义中“委托”的内涵并不一致。从《海商法》的立法意图来看,其托运人定义中的“委托”更应该理解为一种广义的关系。委托与是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11]。因此在《合同法》实施以后,《海商法》在给托运人下定义时,应回避这些用语,以免产生歧义。
4、定义范围涵盖不够完整
《海商法》第42条第三款规定的第二种托运人是“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承运人的人”,实践中存在很多将货物交给实际承运人的情况,超出了托运人概念所涵盖的范畴,此时将货物交给实际承运人的人能否取得托运人的地位则取决于实际承运人是否以承运人的人的身份出现。为了保护发货人的利益,建议增加“货物交给实际承运人的,视为交给承运人”的规定或将实际托运人定义为“将货物交给承运人或实际承运人的人”。
三、 国际上相关立法例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作为传统商法之一的海商法也进一步出现国际统一的趋势。纵观国际上关于托运人定义的规定,总体上来说共有以下几种模式:
1、单独式
采取这种立法模式的国际公约或相关国内法,一般没有托运人的定义或仅将托运人定义为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
《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中没有关于托运人定义的规定。《海牙规则》第1条定义中规定:“承运人”,包括与托运人订有运输契约的船舶所有人或承租人。虽然《海牙规则》没有给“托运人”下定义,但在实践中一般认为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契约的人为托运人。英国1924年《海上货物运输法》将《海牙规则》作为该法的附件生效。此外还有不少国家或者参加了《海牙规则》,或者将《海牙规则》直接作为国内法的一部分,或者依据《海牙规则》的精神,另行制定相应的国内法。《海牙——维斯比规则》没有对承运人的概念做出修改。至今为止,参加这两个公约或者与采用这两个公约基本一致的立法的国家仍居主流地位[12],可见,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中,托运人仅限于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
《1991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国际商会多式联运单证规则》第2条定义中规定:“托运人”是指与多式联运经营人签订多式联运合同的人。此规定也将托运人限定为缔约托运人,排除了将货物交给承运人的人成为托运人的可能性。
《日本1957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第2条定义第3款规定:本法律上所谓“托运人”指委托前条运输的租船者及发货人。《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第2条定义第(3)项则认为:本法所称“托运人”是指承租人或委托承运人完成前条规定的海上货物运输的人。其发展方向是将托运人限定为与承运人有合同关系的人。
《国内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3条第(六)款:“托运人”,是指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托运人限定为缔约托运人。
2、并列式
采用这种立法模式的国家主要是中国。这种立法模式突破了合同相对性的限制,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采用FOB贸易术语的情况下,运输合同将同时存在两类托运人。
中国:《海商法》第42条规定:“托运人”,是指:1、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2、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两类托运人之间没有任何连词,通常认为,《海商法》中有关“托运人”的两个句子为选择关系,即只需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即可视为《海商法》下的托运人[13]。
3、选择式
《汉堡规则》、《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即采用这种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也规定了两类托运人,但这两类托运人不能并存,非此即彼。
《汉堡规则》第1条定义中的第3项规定:“托运人”,是指由其本人或以其名义或代其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契约的任何人,或是由其本人或以其名义或代其将海上货物运输契约所载货物实际提交承运人的任何人。对比我国《海商法》和《汉堡规则》中托运人的定义,二者的区别仅在一个“或”字。日本研究《汉堡规则》的知名专家樱井玲二认为:“本公约中,‘托运人’一词,根据情况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被使用的。在提单实务中,托运人是信用证中的受益人,通常即贸易合同中的卖方。因此,在装货港其与把货物交给承运人的人相一致。另一方面,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人,在以CIF条件为基础的贸易合同的情况下,无疑是卖方,而在以FOB条件为基础的贸易合同的情况下,便会产生这个人是不是买方的疑问,即这个人是不是在卸货港从承运人那里提取货物的人。结果,在具体的事例中,究竟谁相当于托运人,这除非是在规定托运人责任的条文中(例如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由他们的解释来决定,再无其他办法。”[14]也就是说,这一“或”字,表明了两种托运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一项具体的义务,仅存在一个相应的托运人,而具体这一托运人到底是谁,则要结合《汉堡规则》的其他条款来识别。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公约》第I部分,第1条定义中规定:“发货人”是指其本人、或以其名义、或其代表同多式联运经营人订立多式联运合同的任何人,或指其本人、或以其名义、或其代表将货物交给多式联运经营人的任何人。尽管采用的术语是“发货人”,但此定义基本与《汉堡规则》中“托运人”定义如出一辙。
4、分立式
《瑞典1994年海商法》和《芬兰海商法》采用了这种模式。这种立法模式将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与将货物交付承运人的人分别定义,并明确了各自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瑞典1994年海商法》在第四部分运输合同第13章件杂货运输的介绍性条文第1条中规定:托运人(sender):指与承运人订立海上杂货运输合同的人;发货人(shipper):指将货物交付运输的人。第14章租船一般规定第1条定义:发货人(shipper):将货物交付装运的人。首创将《汉堡规则》规定的两种托运人分别定义的立法例,权利义务比较清晰,值得借鉴。《芬兰海商法》将《汉堡规则》中的两种托运人分别命名为“合同托运人”和“实际托运人”,并将前者定义为“为海上运输货物与承运人订立合同的任何人”,将后者定义为“提交运输货物的任何人”。《芬兰海商法》的做法与瑞典基本一致。
四、 建议及结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海事立法又趋于活跃。中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瑞典和我国台湾地区都通过了或修订了本国或本地区的《海商法》或《海上货物运输法》。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在1999年9月24日向参议院提交了《美国1999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而受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委托,国际海事委员会也于1998年2月提交了《CMI运输法(草案)》以供各国海商法协会讨论,并且几易其稿,在2002年1月8日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与国际海事委员会的联合名义推出了《UNCITRAL/CMI运输法最终框架文件》。
CMI运输法草案第一稿第1.5条规定:托运人,指契约托运人或发货人;第1.6条规定:契约托运人,指和契约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第1.7条规定:发货人,指承运人从其手中接受货物的人。即在第一稿中,采取了用托运人概念涵盖了《汉堡规则》所规定的两种情况,然后分别定义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在二者权利义务相同的情况下,用托运人替代,在二者权利义务不同的地方分别定义。无疑,这一立法例对于明晰两种托运人各自的权利义务很有好处,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在CMI运输法的第二稿第1.4条中,却将托运人仅限定为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而没有定义将货物交给承运人的人即发货人的法律地位。更富戏剧性的是在CMI运输法最终稿中又分别定义了发货人(consignor)和托运(shipper)。最终稿第1.3条规定:发货人指将货物交给承运人运输的人;第1.19条规定:托运人指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第7.7条规定:在一方虽不是第1.19条所称之托运人但为合同条款识别为托运人的情况,如果他接受了运输单证或电子记录,则此人(a)承担本章和第11.5条规定的托运人的义务与责任,并且(b)有权享受本章和第13章规定的托运人的权利和免责。并且在最终稿条文的说明中,还认为发货人可能包含托运人。从CMI运输法草案三稿的变化来看,尽管要将托运人与发货人各自的权利义务区分开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CMI运输法委员会还是倾向于将《汉堡规则》所定义的两种托运人分别定义,区分其各自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美国1936年COGSA》没有明确规定托运人的含义,但一般认为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人为托运人[15]。《1999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在第2条定义中的第(9)项规定:“托运人”,是指:(A)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契约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人;和(B)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付给运输合同项下的承运人的人。美国99年COGSA(草案)的规定扩大了托运人的含义,而且该定义的解释与我国《海商法》之相关规定一致,但不同于《汉堡规则》关于托运人之相关规定[16]。
值得注意的是,《CMI运输法最终框架文件》的合作起草者Michael Sturley教授也正是《美国1999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的主要起草者。《CMI运输法框架文件》在托运人定义的问题上几经周折,最终却采用了将合同托运人与发货人分别定义的方式,这也必将对《美国1999年海上货物运输法(草案)》的讨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托运人定义上采用分立式是未来海商法的发展趋势,将托运人区分为“合同托运人”与“实际托运人”是适当的,这样规定能够更好地弥补因《汉堡规则》规定不完善带来的困境,故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修改我国《海商法》时,可以借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海商法与CMI运输法最终框架文件的做法,将我国《海商法》中明确规定“合同托运人”与“实际托运人”的概念,并在具体条文中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1] 参见郭春风:《论对中国海商法托运人定义及相关条款的修改》,《中国海商法年刊》1997年。
[2] 参见傅旭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P74,人民交通出版社;姚红秀等:论我国《海商法》下“托运人”的认定,《中国海商法年刊1996》P35;另郭春风认为在FOB价格条件下,根据《海商法》就同时出现了两个托运人,可以推出他也认为有关“托运人”的两个句子为选择关系,参见郭春风:论对《中国海商法》托运人定义及其相关条款的修改,《中国海商法年刊1998》P13。
[3] 从傅旭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第74-75页的写法来看,似乎“委托他人为本人”仅限于直接和《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情况。
[4]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合同,同时第三人又知道关系的存在,这实际上就构成了隐名”,参见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第34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 《合同法》第402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与第三人的除外”。
[6] 《民法通则》第63条:“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7] 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第34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8] 《合同法》第414条:“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9] 1994年7月版,当时《合同法》还没出台,《民法通则》对的规定仅限于直接,即最高院草案的规定已经突破了《民法通则》关于的规定。
[10] 此处取广义上的含义。
[11] 参见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P338-339,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 参见杨良宜著:《提单及其付运单证》第687-68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3] 参见傅旭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诠释》P74,人民交通出版社;姚红秀等:论我国《海商法》下“托运人”的认定,《中国海商法年刊1996》P35;另郭春风认为在FOB价格条件下,根据《海商法》就同时出现了两个托运人,可以推出他也认为有关“托运人”的两个句子为选择关系,参见郭春风:论对《中国海商法》托运人定义及其相关条款的修改,《中国海商法年刊1998》P13。
[14]樱井玲二认为,应结合《汉堡规则》第13条和第17条关于托运人的责任的规定来识别在具体的事例中,究竟谁相当于托运人。参见樱井玲二著《汉堡规则的成立及其条款的解释》p268,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法律规则定义范文5
(一)时际法不是“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同义语
《国际公法百科全书》中“国际法,时际法问题”这一条目的释义为,“国际法中法律规则不溯及既往的原则,通常被称为时际法法理。”[3]根据该释义,所谓“时际法”的全部内涵仅限于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而时际法亦就成为了这一原则的同义语。对此,笔者认为,该释义实则是对时际法概念和原则的混淆;而若要对时际法概念作出正确、周全的定义就应当以分析和消解得出这一释义的理论误区为基础。如前所述,国际法上的时际法首先出现在胡伯对帕尔马斯岛案所作的仲裁裁决中。胡伯在其裁决中首先陈述了这样的观点:“……一个法律事实必须依照与之同时的法律,而不是依照因该事实发生争端时或解决该争端时的法律进行判断……。”随后又进一步分析指出,“至于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在先后继续的不同时期所实行的几个法律体系中应当适用哪一个的问题,应当在权利的创设和权利的存续之间作出区别。创设一个权利的行为受该权利创设时的有效的法律支配,依照这同一个原则,该权利的存续,换句话说,该权利的继续表现,也应当遵循法律的发展所要求的条件。”[4]据此,胡伯实则从两个不同的层面论及了时际法。
其一,是时际法的概念,体现在“至于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在先后继续的不同时期所实行的几个法律体系中应当适用哪一个的问题”这句话中。这句话说明的是“什么是时际法问题”,实则就是给时际法概念作出定义。依据这句话,所谓“时际法问题”即是“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在先后继续的不同时期所实行的几个法律体系中应当适用哪一个的问题”,亦即是法律在时间上的冲突问题或者说法律的时际冲突问题,而时际法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律。此外,在该裁决的另一处,胡伯对时际法的概念或者说功能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表述,“(时际法决定)在先后继续的不同时期所实行的几个法律体系中应该适用哪些规则。”[5]由此可见,所谓时际法,就是这样一类法律规则或原则,其功能是决定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在先后继续的不同时期所实行的诸种法律体系中应该适用哪一个法律体系,或者说在旧法和新法中应当选择何者予以适用;而只要具有这一功能的法律规范就都是时际法规范,无论其决定应当适用旧法还是新法。[6]
其二,是时际法的原则,即“一个法律事实必须依照与之同时的法律,而不是依照因该事实发生争端时或解决该争端时的法律进行判断。”这句话表明,胡伯认为应当据以判断事实的法律只有一个,即该事实发生时正在实行的法律;而该法律必然是确立于作为其判断对象的事实发生以前,并且在该事实发生时仍旧有效的法律。据此,该国际法上的时际法原则与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在其命令中规定的时际法原则,虽然文字表述不同,但精神却是一致的,其精髓亦即是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7]然而,必须着重强调的是,胡伯的这句话并非是对时际法概念的阐释,其说明的并不是“什么是时际法”或者“什么不是时际法”的问题,而是确立了一项具体的时际法原则;至于完整的时际法的内涵则应当是包括但并不限于这一项原则的。由此,罗奇在其专著《明基埃群岛与埃克里荷群岛案》中针对胡伯的这句话及其之后进一步的分析(即“创设一个权利的行为受该权利创设时的有效的法律支配,依照这同一个原则,该权利的存续,换句话说,该权利的继续表现,也应当遵循法律的发展所要求的条件”)所作的总结,“因此时际法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原则是行为必须按照与它们创设时同时的法律来判断;第二个是,依照与它们创设时同时的法律有效地取得了的权利可能丧失掉它们的效力,如果没有按照国际法带来的发展加以维持的话。”[8]虽然正确地将胡伯所确立的时际法原则划分为两个部分,但却并没有区别该原则与胡伯所述的时际法概念之间的界限,而是简单地认为所谓时际法就全然包含在了上述时际法原则之中,其观点显然是以偏概全的,并且混淆了时际法的概念和时际法的具体原则。故笔者认为,尽管法律“不溯及既往”作为时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中并无二致,但其终究只是时际法在解决法律于时间上的冲突问题时的一种精神的体现,而不是时际法内涵的全部。因此,时际法的概念不能与这项时际法的具体原则划上等号,时际法并非是法律(国际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同义语。
(二)时际法是规定国际法规范在时间上适用范围的法律总称
如前所述,就胡伯对时际法的概念所作的陈述而言,其认为,所谓“时际法问题”就是法律在时间上的冲突问题或者说法律的时际冲突问题;而所谓“时际法”则是决定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在先后继续的不同时期所实行的诸种法律体系中应该适用哪一个法律体系的一类法律规则或原则。事实上,在国际法学界,与之相同的观点不在少数:法语版《国际法术语词典》将“时际法”解释为,“为了指示那些可以决定在时间上相互连续的复数的法律规则中,对于某一特定案件应当适用的规则的诸原则而经常使用的术语。”[9]德国学者施瓦曾伯格对“时际国际法”的解释为,“对于特定的案件,先后继续的不同时期所实行的各种国际法规则的适用的决定。”[10]荷兰国际法学家弗兹尔同样将时际法问题看作是法律在时间上的冲突问题,其对“时际法”的理解为,“时际法,法律在时间上的冲突的重要问题。”[11]纵观胡伯与上述各家的观点,尽管在文字表达上略有不同,但其实质内容基本一致,即“时际法”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类法律原则或规则,其功能是决定在存在着法律在时间上的冲突的情况下,对于某一特定案件应当适用哪些或哪一法律;亦即是说,时际法就是解决法律在时间上的冲突的法律。可见,这一时际法概念的核心在于“法律冲突”;而倘若将“法律冲突”的定义与时际法在国际法上的实践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的话,则会发现这一概念仍然是并不周全的。法律冲突是一种广泛存在的法律现象,其可以被定义为“广义上是指至少两个法律互相歧异的(即不一致的)事实”,或者“为解决某一问题的法律规范复数并存、呈现出相互歧异的外观状况”。[12]由此,倘若将时际法定义为“解决法律在时间上的冲突的法律”,那么时际法就只有在“存在时间上相互连续的复数的法律”的情况下方能成立。然而,国际法实践中往往存在与之相反的情况,即在只有一个国际法规范的情况下同样会发生如何确定其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的问题。举例而言,在多个国家首次缔结有关劫机或海盗问题的条约之前,各缔约国中可能已经出现过劫机或海盗事件,而在这些事件发生后方生效的国际条约能否适用于其生效前已发生的事实,同样是一个国际法上的时际法问题。在上述情况中,只存在一个新生效的国际法规范,而不存在复数个国际法规范在时间上的冲突问题,即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法律冲突”;故倘若将时际法定义为“解决法律在时间上的冲突的法律”则不能包括上述情况,就与时际法在国际法上的实践情况产生了出入。因此,所谓“解决法律在时间上的冲突”应当是指时际法的功能,而不能以此作为时际法概念的完整定义。法律在时间上的冲突在国际法上的体现,即是国际法在时间适用范围内的冲突,包括积极冲突(在一个法律事实发生和存续的不同阶段存在着复数个国际法规范竞相对其进行调整,应当选择何者予以适用)和消极冲突(在一个法律事实发生的当时并无与之同时的国际法规范可以予以调整,而在其发生之后方开始生效的国际法规范能否适用于在其生效前已发生的该法律事实)。至于国际法上的时际法概念,笔者认为应当将其定义为,规定国际法规范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的法律的总称,既包括划定复数个相互连续的国际法规范分别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的法律,也包括确定一个单独的国际法规范在时间上的适用范围的法律。
二、国际法上的时际法规则
既然时际法的功能是解决法律在时间上的冲突,那么时际法的规则亦就是时际法解决法律的时际冲突的方法。如前所述,国际法在时间范围内的冲突包括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两种情形,因此,亦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形确立与之相对应的时际法规则。
(一)适用事实发生时正在实行的法律解决积极冲突
国际法在时间范围内的积极冲突的定义在前文中已作阐明,而解决这一冲突的时际法规则实则就是胡伯在帕尔马斯岛案的仲裁裁决中首先陈述的观点,即“一个法律事实必须依照与之同时的法律,而不是依照因该事实发生争端时或解决该争端时的法律进行判断。”在此有必要指出,尽管前文提及,李浩培先生认为胡伯所作的这一时际法规则实则是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同义表达,但笔者认为,胡伯的这句话所要说明的是,当存在时间上相互连续的复数的法律时,应当选择何者予以适用的问题,而并不是要说明因事实发生争端时的法律或解决该争端时的法律对该事实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因此,仅就胡伯这句话的文义而言,其旨在确立在复数个法律竞相对事实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应当依照事实发生时的法律对其进行判断的时际法规则,而并没有直接表达一项单独的法律对于在其生效前发生的事实不具有溯及力的含义。故胡伯的这一观点应当是解决国际法在时间范围内的积极冲突的时际法规则,而并不当然地等同于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依据上述胡伯所作的时际法规则,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一个法律事实会涉及到三个不同时期的法律:法律事实发生时正在实行的法律,因该事实发生争端时正在实行的法律,以及解决该争端时正在实行的法律。当这三个不同时期的法律竞相对同一个法律事实进行调整时,胡伯的观点是,用以判断一个法律事实的法律应当是与该事实同时的法律,即该事实发生时正在实行的法律,而非之后方实行的法律。至于如何解决法律的变化和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胡伯在裁决中进一步分析指出,“……应当在权利的创设和权利的存续之间作出区别。创设一个权利的行为受该权利创设时的有效的法律支配,依照这同一个原则,该权利的存续,换句话说,该权利的继续表现,也应当遵循法律的发展所要求的条件。”如前所述,罗奇根据胡伯的这一分析将上述时际法规则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行为必须按照与它们创设时同时的法律来判断。这一点得到了国际法学界的普遍接受;其二是,已经有效地取得了的权利,其继续存在尚需符合此后演进的国际法的要求。而这一点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在权利产生和继续存在之间作出区别,是对许多国际法学家在这一问题上所表述的观点的明显背离”,[13]引起了学界广泛的争论,因为倘若严格适用这一时际法规则,就可能导致国家已取得的权利在将来永远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从而破坏国际秩序的稳定性。针对这一点,杰塞普曾尖锐地指出,“每个国家将总是有必要检查对其领土各部分的领土所有权,以便确定法律的变化是否要求,正如(裁决)所表明的,重新取得……结果将是混乱的。”[14]
然而,在笔者看来,胡伯对其所作的时际法规则进行的进一步分析,以及罗奇基于胡伯的分析对该时际法规则所作的划分,是具有合理性的,应当作为解决国际法在时间范围内的积极冲突的时际法规则在实践中具体操作的依据。首先,从权利产生到出现争端再到争端解决的这一权利持续存在的漫长时间里,由于法律是不断演进的,因此依照权利产生时的法律所取得的权利在其持续存在的过程中必然会进入到在其产生之后方实行的新法的时间适用范围内;而依照法律事实必须根据与之同时的法律进行判断的时际法规则(即罗奇指出的时际法规则的第一部分内容),进入到新法的时间适用范围内的权利应当根据该新法进行判断,因为在此时,新法已经代替了权利产生时的法律,成为了与权利的持续存在期间同时的法律;当然,同样依照法律事实必须根据与之同时的法律进行判断的时际法规则,根据新法进行判断即适用新法,并不意味着新法将一概追溯地使权利自始无效或重新取得。因此,在权利持续存在期间,对其适用相应时期内演进中的国际法,是符合法律事实必须根据与之同时的法律进行判断的时际法规则的。其次,从设立时际法的目的来看,时际法的价值一方面在于保障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现状,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则在于使最初取得的权利能够同样符合演进中的法律的要求,继而接受已经演变了的法律的调整。这正如格罗斯在明基埃群岛与埃克里荷群岛案中的口头辩论中所阐述的,区分权利产生时的法律与权利存续时的法律,意在调和“法律的两个基本需要:稳定和变革。稳定,意在避免使根据以前的法律体系所取得的有效权利归于无效;变革,意在要求古老的权利适应新法。”[15]因此,只有在法律的稳定和变革的冲突之间找到相对的平衡,才能正确地理解和适用时际法规则。而经罗奇划分的胡伯的时际法规则的第一部分(行为必须按照与它们创设时同时的法律来判断)即是时际法保障法律稳定的价值体现,而第二部分(已经有效地取得了的权利,其继续存在尚需符合此后演进的国际法的要求)体现的则是时际法迎合法律变革的需要。故胡伯所作的时际法规则的这两部分是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其在时际法具体解决国际法在时间范围内的积极冲突的过程中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综上所述,解决国际法在时间范围内的积极冲突的时际法规则应当为,适用与所调整的法律事实同时的国际法规范,即该事实发生时正在实行的国际法规范;同时,还应当对因该事实所引起的权利的产生和存续作出区别,在权利产生时适用与之同时的最初的国际法规范,而在权利存续期间适用同样与之同时的、演进中的新的国际法规范,或至少使该权利的继续存在符合演进的国际法的要求。
(二)以法律“不溯及既往”作为解决消极冲突的原则
国际法在时间范围内的消极冲突指的是这样一种时际法问题,即在一个法律事实发生的当时并无与之同时的国际法规范可以予以调整,只有在其发生之后方生效的新的国际法规范,而该国际法规范能否适用于在其生效前就已发生的法律事实,即对该法律事实是否具有溯及力的问题。故解决这一冲突的时际法规则,其目的就是要确定一个单独的国际法规范的时间适用范围,易言之,就是要确定一个国际法规范是否具有溯及力。如前所述,法律“不溯及既往”作为时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中并无二致。因此,解决国际法在时间范围内的消极冲突的时际法规则仍应以此作为原则,即在通常情况下,国际法规范不具有溯及力,其不能适用于在其生效或正式实行前就已发生的法律事实。这一时际法规则当以在国际条约法中的体现最为典型。在国际法上,条约法较之习惯法更容易发生时际法问题,因为习惯法的形成一般需要长时间的过程,而自近代以来,条约的缔结则与日俱增。[16]对此,《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8条以“条约不溯及既往”为标题,明确规定:“除该条约显示或另经确定有不同的意思外,关于该条约对一个当事国生效日以前所发生的任何行为或事实或已经停止存在的任何局面,该条约的规定对该当事国无拘束力。”由此确立了条约“不溯及既往”的条约法上的时际法规则。并且,这一时际法规则还得到了国际法判例的支持———在对阿姆巴蒂洛斯案的判决中,国际法院支持了英国政府提出的希英两国于1926年签订的《希英商务航行条约》不能适用于希腊政府据以提出债权要求的于1922年和1923年所发生的事实,指出条约在原则上不具有溯及力。据此,以法律“不溯及既往”作为解决国际法在时间范围内的消极冲突的时际法原则在理论上和国际法实践中都得以确立。当然,以法律“不溯及既往”作为解决国际法在时间范围内的消极冲突的时际法原则亦存在例外情形,即在特定情形下,国际法规范可以具有溯及力,可以适用于在其生效或正式实行前发生的法律事实。这一点同样可以在理论上和国际法实践中找到依据。首先,仍以国际条约法为例。《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8条尽管以“条约不溯及既往”为标题,但其首句“除该条约显示或另经确定有不同的意思外”同时又表明条约不溯及既往并非是强行法的原则,即一个条约究竟是否可以溯及既往,以及溯及既往到怎样的程度,完全取决于缔约各方的共同意思;而这种共同意思可以显示于条约的明文规定,亦可以从条约谈判时的准备资料中寻求,甚至可以通过条约的目的进行确定。此外,《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2条规定:“违反《联合国》中所包含的国际法原则以武力的威胁或使用而获得缔结的条约无效。”
尽管国际法委员会在对该条内容的释义中指出,该条本无追溯力,并不使在禁止武力的威胁或使用的现代国际法确立以前由于强迫而缔结的媾和条约或其他条约自始无效;但其同时强调,大多数国际法学家毫不迟疑地认为《联合国》第2条第4项及其他规定权威性地宣告了关于禁止武力的威胁或适用的现代国际法,所以该条(《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2条)含蓄地承认其包含的规则至少适用于从《联合国》后所缔结的一切条约。也就是说,于1969年生效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的第52条的规定可以追溯地适用于自《联合国》生效后二十多年间的一切条约。因此,条约“不溯及既往”原则并非一概而论,即便是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亦有例外的规定。此外,在国际法实践中,同样有法律“不溯及既往”的例外情形。例如,1945年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对德国战争罪犯的审判实践,以及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实践,对于国际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一系列国际刑事诉讼的原则,其中就包括不适用国内刑法中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和“不溯及既往”原则。[17]至于在国际法实践中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例外情形,笔者认为,其仍旧是国际法上的时际法在对法律的稳定和变革进行权衡后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说明时际法重在保障法律的稳定,因为倘若过分追求变革,就会导致按照旧法是合法有效的行为必须按照新法一概被认为是非法无效、甚至需要受到刑罚的制裁,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无秩序和不稳定的状态;但时际法对稳定的重视亦不影响其同时兼顾变革,因为忽视变革同样会损害法律的公正性和时代性,亦无助于社会的进步。因此,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上的时际法,都会在以法律“不溯及既往”作为原则的同时作出特定情形下的例外规定。①当然,在确定何种情形可以适用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例外规定时必须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否则极有可能使时际法对变革的追求走向负面的极端,故对可以适用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例外规定的特定情形的范围进行界定是十分必要的。对此,笔者仅能提出初步的建议,即根据现有的国际刑法规范,涉及国际犯罪的情形,包括破坏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犯罪、危害国际秩序与安全的犯罪以及危害人类生存与健康的犯罪,应当被视为可以适用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例外规定的特定情形,在上述涉及国际犯罪的法律事实发生后方生效或正式实行的国际法规范可以追溯地适用于该事实。这是因为涉及国际犯罪的行为具有相当严重的国际危害性,应当被追究国际刑事责任;而倘若因为在上述行为发生时并没有与之同时的国际法规范对其进行调整,使得这些行为基于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得以免于应受的惩处,那么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对国际法的公正性和其惩前毖后的法律作用的极大损害,也是难容于现代国际法演进的主流的。这一点从前文提及的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在对二战战犯的审判实践中提出了不适用“不溯及既往”的国际刑事诉讼原则的做法中可窥一斑。因此,解决国际法在时间范围内的消极冲突的时际法规则应当以法律“不溯及既往”为原则,同时在至少包括国际犯罪行为的特定情形下做出例外的规定,即相关的国际法规范可以追溯地适用于发生在其生效或正式实行前的、至少包括国际犯罪在内的法律事实。
法律规则定义范文6
[关键词]禁反言规则 基于信赖之禁反言规则 英美法
一、禁反言规则的概念
禁反言一词来源于法语单词estoupe和英语单词stop(停止)。最早对禁反言这一术语概括定义的可能要算柯克勋爵,早在16世纪柯克在其著作中写道:“禁反言(estoppe)来源于法语单词“受阻”(estoupe)和现在通常所说的英语单词“停止”(stopped):之所以称为禁反言或定论(conclusion)是因为一个人自身的行为或认同使他自缄其口而不能再主张某种事实……”丹宁勋爵在20世纪70年代也曾对禁反言作出定义,即:“禁反言……是一项审判原则和衡平法的原则。它是这样的:当一个人通过其言语或行为导致另一个人相信了某种特定的事实状态时,如果他他的言语或行为会产生不公正或不公平的话,那么他将不被允许那样做。”有许多学者和法官在著述或案件判决中都曾对禁反言的含义提出自己的见解,以上所列举的两种定义只是其中比较著名和有代表性的。一般而言,禁反言是指:禁止一方当事人否认法律已经做出判决的事项,或者禁止一方当事人通过言语(表述或沉默)或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做出与其之前所表述的(过去的或将来的)事实或主张的权利不一致的表示,尤其是当另一方当事人对之前的表示已经给予信赖并依此行事的时候。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禁反言规则大致分为两支,一支是在法庭审理案件过程中,涉及审判事项的禁反言,也就是说为确保法院判决的既判力,禁止诉讼当事人就法院已决事项或争议表示反对或再次提讼,其实质就是“一事不再理”,包括记录禁反言(estoppel by record)、既判争点禁反言(issue estoppel /collateral estoppel)等等。另一支是在法庭之外的日常生活中,由一方当事人的言语或行为或者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契据或协议引起的禁反言,这其中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仅凭当事人之间的书面文件即可禁止一方当事人反悔的禁反言,包括契据禁反言(estoppel by deed)和协议禁反言(estoppel by convention/estoppel by agreement)等;另一类是当一方当事人因信赖另一方当事人之前的陈述行事而导致损害时禁止另一方当事人反悔的禁反言规则,这种禁反言规则又被称为基于信赖之禁反言(reliance-based estoppel)。包括陈述禁反言(estoppel by representation(of fact)/estoppel in pais)、允诺禁反言(promissory estoppel)和财产禁反言(proprietary estoppel)。下面将着重阐述基于信赖之禁反言的概念。
二、基于信赖之禁反言的概念
基于信赖之禁反言规则是指当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作出某中对既存事实的陈述(representation of existing fact)或者是对将来意图的允诺(promise of future)并且诱使另一方当事人相信了这一陈述或允诺时,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因信赖这一陈述或允诺行事而导致损害,那么法律会禁止做出陈述或允诺的一方当事人否认或改变其陈述或允诺。其中,确认基于信赖之禁反言规则的核心是“不正当性”(unconscionability)与“损害性信赖”(detrimental reliance)。“不正当性”是针对陈述人或允诺人(reprensentor / promisor)而言的,指其改变先前的陈述或允诺会产生不公正的结果(inequity),“损害性信赖”是针对受陈述人或受允诺人(representee / promisee)而言的,指其因信赖陈述或允诺所作出的行为会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loss or detriment)。
具体而言,基于信赖的禁反言包括陈述禁反言、允诺禁反言和财产禁反言。
陈述禁反言(estoppel by representation)又称为事实陈述禁反言(estoppel by representation of fact),是指当受陈述人按照陈述人的事实陈述行事时,禁止陈述人否认或改变其先前的事实陈述从而对受陈述人造成损害。在英国,陈述禁反言与事实禁反言(estoppel in pais)是可以互换的,而有时单独使用“禁反言”一词是陈述禁反言的缩略语。按照言语或行为、作为与不作为的陈述方式不同,在具体案件中陈述禁反言又分为沉默禁反言(by silence)、默许禁反言(by acquiescence)、言词禁反言(by words/statement)和行为禁反言(by conduct)等。
允诺禁反言(promissory estoppel)是指当没有提供任何约因的受诺人因信赖允诺人的允诺而行事时,禁止允诺人否认或改变其允诺从而对受诺人造成损害。也就是说这一无约因的允诺(bare promise)具有强制执行力(enforceable)。
财产禁反言(proprietary estoppel)产生于涉及土地权利(title to land)的交易。指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声称他将来会把自己所有的土地或土地权益转让给另一方,但事实上这一声明并未发生法律效力,另一方当事人因信赖这一声明并耗费大量财力从而导致损害的发生,此时法律将禁止土地所有人改变或否认其转让声明并使此声明具有强制执行力。
在这里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陈述禁反言与允诺禁反言的区别首先在于前者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陈述而后者是对将来意图的陈述;第二点是在英国法、美国法与澳大利亚法中对这三类禁反言与衡平禁反言(equitable estoppel)的关系理解不同。衡平禁反言是指当一方当事人因信赖另一方当事人所做的陈述而行事时,如果允许另一方当事人改变或否认其先前做出的陈述会给一方当事人带来不公正的损害,那么法律将禁止当事人这样做。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衡平禁反言的实质与基于信赖之禁反言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也具备两个核心因素及“不正当性”和“信赖损害”。之所以会称为衡平禁反言是为了与普通法的禁反言相区别,但是应当说在英美法系各国的司法实践界与法学理论界这一概念是极具争议的。因为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主流观点是衡平禁反言包括允诺禁反言和财产禁反言,而陈述禁反言则被认为是一种证据规则而归于普通法禁反言的范围之内,而在美国衡平禁反言与英国的陈述禁反言是同义词,也就是说二者可以互换。所以,在英国和澳大利亚衡平禁反言与陈述禁反言是并列的,而在美国衡平禁反言与允诺禁反言是并列的。
参考文献:
[1]Moorgate Mercantile Co. Ltd. v. Twitchings,1976.225.
[2]See Elizabeth Cooke.The Modern Law of Estoppel.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84-111.
[3][美]加纳(Garner,B.A.).牛津现代法律用语词典(影印本).法律出版社,2002.328-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