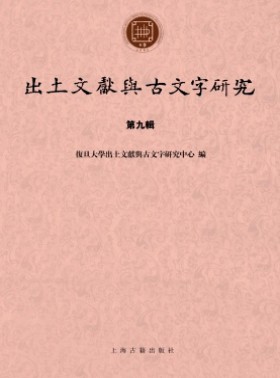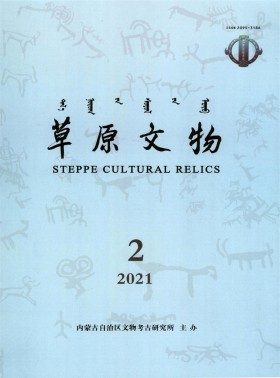【摘要】古文这一字体的名实历来存在争议,自王国维先生提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后,诸多学者均对“古文”字体有所论及,启功先生从文字书写的角度出发,结合当时所出实物资料,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提出“古文”是“篆类手写体”的看法。本文通过分析归纳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近年来新出的战国文字材料,以书写研究为核心,对“古文”字体重新定位,并对其“名实”“体用”“源流”做出新的解释。
【关键词】古文;名实;字体;笔形弁言
自20世纪中叶以来,古文字学家对于文字的研究重点由其形、音、义的考释转向了字体的构形层面[1],这一意义重大的转换,不仅使得原有的理论成果得到了重新审视,而且将一些原来隐而不显的问题也纳入学术研究的课题中来。此前,清乾嘉以来的学者对于古文字的考证日益精密,文字字体的研究深受小学的影响,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常集中在文字训诂上,而较少的关注字体的名实与演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地下发现的古文字资料日益增多,学者们以更广阔的视野来重新审视汉字的构形,字体的名实与体用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自王国维先生根据当时地下所出文字材料,提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2]之说后,容庚、启功、陈梦家、张政烺等诸多学者均对“古文”字体有所论述,然而分歧较大。这些对于字体名实探索的努力值得敬佩。就具体对“古文”这一字体的名实作探索推进时,我们不得不回答以下这些问题:历史文献记载的“古文”字体名称和实物中的字体形状,往往分歧较多,是否有明确的指向?“古文”的笔形特征为何?造成“古文”字体独特的笔形特征的原因是什么?实物上所体现的笔形样态在各个时期是否有承递关系?文献所载“古文”与实物上的“古文”有何差异?“古文”字体的“源”与“流”能否厘清?本文试图通过对“古文”字体的名与实的详细考察来回答上述问题。笔者将历史文献所载“古文”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做一番梳理,并将带有“古文”笔形特征的实物字样按时代先后顺序进行整合。在研究“古文”字体的名实的关系时,站在文字书写的角度上,结合新出简帛实物材料,通过对带有“古文”笔形特征的各个时期字样的书写载体和书写方式的客观阐述,来探讨“古文”的“名”与“实”,“体”与“用”,“源”与“流”,以及“正体”与“俗体”[3]的转捩。
一、“古文”字体研究简述
清代学者论及“古文”,多是依许慎《说文》中所录重文(古文、籀文)字体而推衍,孙星衍《孙氏重刊宋本说文序》[4]说:唐虞三代五经文字,毁于暴秦,而存《说文》。《说文》不作,几于不知六义;六义不通,唐虞三代文字不可复识,五经不得其解。《说文》未作已前,西汉诸儒得壁中古文书不能读,谓之逸十六篇。孙氏是站在“证经”的立场来谈《说文》,其研究不脱“小学”藩篱,从序中所言“西汉诸儒得壁中古文书不能读,谓之逸十六篇。”可说明这里所提及的“古文”是指“壁中古文书”,即先秦古籍,当然,也是指先秦所用字体,因为其书“不可读”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字“不复识”,接着,古文究竟为何种字体,孙氏论述说:叙篆文合以古籀,即并《仓颉》《爰历》《博学》《凡将》《急就》以成书,又以壁经鼎彝古文为佐证……其云古文、籀文者,明本字篆文……世人以《说文》为大小篆,非也。在孙氏看来,古文、籀文即是说小篆前身,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可惜的是,就其“古文”从何而来,成于何时,作何之用,孙氏并未进一步阐明。近代以来,考古发掘甚为发达,甲骨、金石、简牍等大量古文字实物书写材料的出土,给古代字体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帮助。运用“地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考据方法,是由王国维最先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5]王国维提出:“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并认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主张东西土文字不同之说。张政烺提出:“籀文行于秦可考而信,古文经出于邹鲁儒生之手,流传于东方,也是事实。但是说有‘六国古文’则未免武断。”[6]他认为战国时政治上没有统一的政权,经济上没有统一的市场,不可能有六国共同使用的文字。并举近代出土的诸如长沙缯书、侯马盟书、温县盟书、平山县中山国铜器、江陵信阳长沙简策等战国文字资料,以说明与邹鲁儒生习用的古文有所差别。但“古文”究竟是何种性质的字体,张政烺并未展开论述。王国维受当时所出战国文字资料的限制,据汉时文献以及秦时古器物上的铭文,提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这是强调秦国与六国文字使用的差异,张政烺则强调六国之间,文字使用亦有差别,不能一概而论。陈梦家认为“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是不能成立的,提出《史籀篇》是西周晚期的文字,并非秦人所独创独用,所以籀文不但合于甲文和西周金文,有些也合于东周的东土(齐、陈、邾)金文。他认为秦的金文和东土诸国金文,共同点大于异同点,又从反面论证,提出战国时的陶器文、玺印文、兵器文、货币文和《说文》古文自成一系,与西土的秦金文不同,和东土的六国金文也不同。一正一反论证,说明并非仅秦用籀文,也说明六国并非仅用古文。接着就“古文”究竟是何种字体,做出进一步推论,与作为官书的史籀篇、两周金文相比有异,故确定其性质,与六国时陶器文、货币文、玺印文、兵器文相合,遂证其时代,得出“古文者乃战国时(甚至于是晚期)的一种民间书”的结论。容庚则认为时代比较久远的,凡是殷商的文字统属于古文,又举例说:“近代所出甲骨文字,为商代之物,信而有征,亦古文也。”这是广义上的理解,其时期很难准确划分,字体样态也难区别。启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明确提出:“字体名称和形状的变化,因素很多,必须从实物和文献互证,才能得到比较可靠的真象。”[7]这是继承前贤“二重证据法”,即采用“综合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科学方法”来考察中国古代字体,就“古文”而言,启功先生从“古文”的论述从其广狭二义展开,提出广义的“古文”是小篆以前的文字皆可称之,与容庚看法大体一致;而狭义的,则是“指秦以前写本的书籍中的字,特别是秦以前所写的经书的字”[9],启功先生接着就对其狭义的“古文”究竟是什么时候的字体论述道:孔壁中古文经的抄写时代,固然不能知道,但往上不会早于孔子生存的时间……下限都不会晚于秦始皇三十四年,自然可以说它大致是六国时的写本。接着就“古文”与“籀文”谁先谁后的问题提道:西土的秦国曾用籀文是事实,但难说秦末有过广狭二义的古文,只是未把籀文之前和籀文之外的古文算是“正体”来承认和使用罢了。东土的各国曾否行过籀文未见明文,而所谓“左右均一,规旋矩折”一类情形的字体,东方各国并非没有出现过。启功从书写的角度出发,以字体发展的眼光辩证的分析问题,这种独特的视角和研究方法,消除传统对于字体概念的“偏见和谬误”,建构出更为真实的字体演进图景,并提出“古文”是古代的一种手写体。[10]对古文字体的名实体用予以论述的学者众多,这里不再一一孴录,就其体用而言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看法:篆类手写体;民间俗写体;标准或应用[11]文字(无正俗之分);就其使用年代而言大体有以下三种观点:先秦时期;六国晚期;春秋末期至战国末期。
二、两汉文献所见“古文”之名
“古文”之名大抵起于汉代,后世继续沿用,泛指与今文字体系相对应的古文字体系,时间地域并无限制,也没有确定的字形;狭义的“古文”则多是指秦以前经书写本中的文字。广义上的古文概念过于宽泛,其涵盖了除今文字之外的所有字体;而狭义的古文字体概念则又过于绝对,常常出现字体的同名异实的现象,字体名实产生混淆,对字体的研究造成了很多麻烦,这就需要对古文的名称与实际有一个明晰的划分。“古文”这一字体名称,其所指的意义前后汉有所差异,我们据前汉时《史记》文献中“古文”之名做一番辑录:往往称皇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古文,谓《帝德》《帝系》二书也。(唐司马贞《史记索隐》)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弟子籍》出于孔氏古文,近是。(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上举文献中所提及“古文”的名称,从《帝德》《帝系》《弟子籍》以及“诵古文”等可以看出,“古文”并非是指字体,而是指先秦写本旧籍而言,除此之外,诸如《尚书》《毛诗》《礼经》《春秋经》《孝经》等旧籍,皆称之为“古文”,而所书旧籍的字体,汉时已不用,但前汉时人仍能认识。后汉时人所论及“古文”,则又多是专指字体而言,下举几例:张敞好古文字。(班固《汉书•郊祀志》)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许慎《说文解字叙》)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许慎《说文解字叙》)鲁恭王得百篇《尚书》于屋壁中,使使者取之,莫能读者。(王充《论衡•正说篇》)汉武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卫恒《四体书势》)许慎是后汉晚期时人,《说文叙》提及“古文”多达十次,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如“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以古文为古代的文字,与今文相对应。另一类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孔壁书者,鲁恭王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古文,孔子壁中书也”,其“古文”是专指孔氏壁中书的字体。“古文”之名,可以泛指一切古代文字,也可以专指古代的某一种字体,梳理历史文献,“古文”传统之义,可以划分为三类,即:类指,先秦旧籍;泛指,与今文字体相对的皆称“古文”,是相对的概念;专指,“孔子壁中书”(文字字体)。
三、从出土实物资料看“古文”之实
“古文”就专指“字体”的“孔子壁中书”而言,其“体用”与“源流”为何?需从对“孔子壁中书”有直接记载并孴录其字体的《说文》着手。从“古文”字体异体字的数量来看,《说文》所出“古文”共计510字,同一字有三种构形的字有6字,同一字有两种构形的达44字;《说文》所出“籀文”共225字,其中只有“其”和“墙”二字有两种不同的构造,籀文在构形上趋于一致,不像古文那么多样。由此可以推测,出于《史籀篇》的籀文,其字体的构形规范严格,更符合“正体”要求,而古文同字异形的字较多,符合“俗体”概念。从笔形[12]样态来看,《说文》所出“古文”多呈“蝌蚪”之形,“科斗”亦称“蝌蚪”,汉末时用于书体之名,郑康成《尚书赞》云:“书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蝌蚪书。”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指汲冢书为“科斗”。又说:“科斗文者,周时古文也。其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焉。”用毛笔在不同的书写材质书写,因毛笔具有弹性,起收笔书写出尖,中间偏前部分略粗,这是毛笔书写的特性以及右手书写习惯使然,符合“手写体”概念,侯马盟书[13](图1)即属此例。选择从不同时期不同书写载体分析(表1),使得一脉相承的“古文”笔形特征及笔形样态更加明了从笔形特征上看,自《说文》中古文以下,历数《正始石经》、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吕大临、王楚、王俅、薛尚功等摹三代彝器,赵孟頫六体古文,乃至清代的《西清古鉴》,其皆有“两头尖”笔形特征。同样的,自《说文》中古文上溯唐维寺126号楚墓简牍、王家咀798号战国楚墓出土竹简《孔子曰》、信阳楚简、长沙仰天湖楚简、子弹库帛书、诅楚文、侯马盟书、春秋错金宋公栾戈、四祀邲其卣、作册般甗、宰甫卣铭、干支表骨刻辞(表2),也都是有“两头尖”的笔形特征。可见,自汉以降,“古文”字体的书写的“两头尖”的特征并非杜撰,而是有“源”有“流”的。上述仅是对于《说文》中“古文”,也即专指“字体”的“孔子壁中书”的静态分析,得出其符合“手写体”“俗体”的概念。然而,诸如盟书文字、楚王酓悍鼎铭等明显带有“古文”特征笔形的字体,其使用的场合不可谓不正式,故不能说“古文”字体就是俗体文字,只能说“古文”的“笔形特征”来源于俗体书写。“同时代并行的两种字体的对立统一、两种字体的地位转换是我们了解字体及其发展演变的关键所在,标准体体现文字规范,应用体体现文字方向。”[15]“古文”与“籀文”也是如此,并非仅秦用籀文,亦非仅六国用古文,盖一字体,因时而传,不能凭空产生,六国之古文,实源于周之俗体,“礼崩乐坏,文字异形”,六国不以周代正体为尊,秦国地处西北,文字传用正体,故秦之“籀文”,实周时之“正体”,“古文”古之即有,正俗之变,因时而易,譬如“隶书”,秦时为俗体,汉时为正体,秦时“古隶”经规范美化之后而成“八分”作正体之用同理。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从殷商至魏晋。“古文”这一字体是“同名”而“异实”的,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书写材料上的“古文”笔形“两头尖”的特征一脉相承而结构差别较大。魏晋以降,“古文”的书写只强调其笔形特征,加之以规范美化,即成带有“两头尖”点画特征的程式化书体。
2.《说文》中“古文”。与六国时的陶文、货币文字、玺印文、兵器文多相合,故可证其使用年代当属战国中晚期,而带有“两头尖”笔形特征的“古文”,从侯马盟书来看,其使用年代上溯至春秋晚期乃至殷商时期(甲骨朱书文字)。
3.“古文”就专指字体的“孔子壁中书”而言。其字体是战国时六国“手写体”,而并非“俗体”“民间体”。“古文”的笔形特征来源于书写性简化,遵从“反逆性”[19]原则。
结语
从文字书写角度出发对“古文”字体的名实研究的意义在于两点:首先,详细的描述与界定“古文”字体的名称与实际的运用,是对于前人“古文”字体研究的延伸。其次,运用成熟的字体研究方法和系统性的视角,从文献到实物,从微观观照到宏观梳理,解构以往的字体划分,重构现代视域下的字体框架,进而更新字体系统的概念。近年来简帛材料出土即多,尤其是战国楚简的整理面世,为“古文”字体研究提供的大量的实物资料。以往字体的“名实”与“体用”争议较多的问题,也因为新材料的出土而获得解决,本文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以及对新出先秦文字材料的笔形考察,对“古文”字体的“名实”与“体用”做出新的解释。就“古文”字体的历代承袭与演变的脉络而言,有待进一步的梳理研究。
作者:王金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