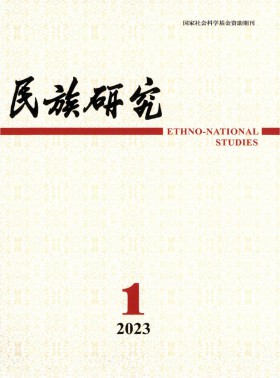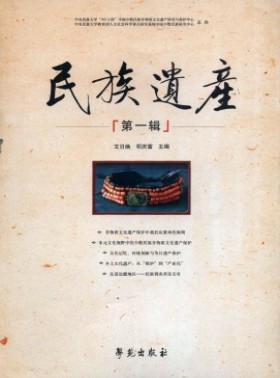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民族历史名著英译思路,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本文作者:邢力 单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13世纪的蒙元王朝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千古奇书─—《蒙古秘史》。它是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兴衰过程为中心,记述蒙古族从神话传说起源到13世纪40年代五百多年历史演进的一部“敕修”官方史书,同时也是一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永久价值的文学经典。它虽然以一定的史实为依据,但糅入了一些神话传说来解释英雄人物的诞生和历史事件的关系,同时在写作和叙事方式上形象生动,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因此可以说,《蒙古秘史》在对蒙古帝国创业史的记述中表现出很强的文学传说和历史色彩,是一部历史文学著作和重要的文化典籍。杨义在《〈蒙古秘史〉:七百六十年祭》一文中称赞此书“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而且在整个中华文学史上是一部掷地有声的奇书”①,此誉绝不为过。从内容来讲,《蒙古秘史》包罗万象,涉及13世纪中叶前蒙古族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语言等多方面的珍贵材料,堪称反映古代蒙古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就文本而言,《蒙古秘史》的畏吾体蒙文原文早佚,流传至今的最早形态是14世纪末出自明朝翰林院的汉字音写本,即以当时的汉字拼写原书蒙古文发音并附有旁译和总译的一个特殊读本,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价值。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魅力和价值,《蒙古秘史》引起了中外众多学者的高度重视。六百多年来,它的流传和研究遍及多种文字。目前,关于《蒙古秘史》的研究甚至引发造就了一门风靡世界的专门学科———“秘史学”。不言而喻,在《蒙古秘史》走向国际的过程中,翻译尤其是英译(有鉴于英语作为目前使用范围最广的国际交流语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国内翻译界对于有关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更没有联系到典籍翻译和翻译学的建设进行专门研究。另一方面,长久以来,我国民族学界对这部民族文史经典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史学、文学和蒙古文献学领域,对于其翻译研究价值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秘史》的英译研究更是从未有人问津。考虑到秘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所要求的扎实框架和这当中英译研究的空白现状,本文拟对《蒙古秘史》的英译史进行纵向梳理,对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柯立甫译本展开微观评析,并对其英译的总体趋势进行分析和评判,以期从民族文学外翻的角度为秘史学甚而整个民族文学、翻译学建设提供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视角。
一、《蒙古秘史》及其英译史
1、《蒙古秘史》简介
《蒙古秘史》(Mongqol-unniucatobcaan),意即“蒙古的秘密历史”,是蒙古文人史官记载成吉思汗孛尔只斤黄金家族出身和家谱的古书。多数学者认为其原文为畏兀体蒙古文,约成书于13世纪,成书地点在蒙古高原的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流域,作者佚名。《蒙古秘史》成书后,身为统治者的黄金家族将之视作“祖传家训”秘籍,“事关外禁,非可令外人传写”②。直到元亡明兴,此书落入朱明王朝手中,明太祖朱元璋为培养通达蒙古民情、军情之人以扫除漠北残余的北元势力,命翰林编修火原洁和马沙亦黑等以汉字音写其蒙古文并附有旁译、总译,以供学习蒙语蒙文之用,世人才有幸一睹它的奇书概貌。然而,遗憾的是,这部奇书其后只有汉字音写本传世,蒙文原本自汉译后迄今下落不明。也正由于此,《蒙古秘史》成为一部充满悬疑的“谜”书,有关的众多问题,如成书年代、原文形式、书名作者等,一直困扰和吸引着众多的蒙古族专家和文史学者。由于《蒙古秘史》的畏吾体蒙文原本早佚,“现存的《元朝秘史》,则是以六百余年前河北地域的汉字方音,译写《蒙古秘史》原文(当时尚存)的古蒙古语音而成者。”③换言之,目前对我们而言,《蒙古秘史》的存在源头就是一个包含了音译以及简单意译的汉译本,它在文献学上的地位堪比原著,其价值不言而喻。这个汉译本大约在明朝洪武初年(约1382年左右,有争议)形成,后有12卷本(正文十卷,续集二卷)和15卷本(明永乐年间收入《永乐大典》)分别传世。这两种本子在内容上完全相同,只是分卷有差别。
目前行世的主要有三种版本:15卷《永乐大典》本、12卷顾广圻本和12卷叶氏观古堂刻本。学术界研究和译注一般都是以错误相对较少的12卷“顾广圻本”或“叶德辉本”为底本的。1980年,额而登泰、乌云达赉两位《蒙古秘史》专家以上述三种版本中错讹较少的顾广圻本为底本,参照另两种本子进行校勘,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蒙古秘史校勘本》,这是目前比较权威的一个通行版本。现存的《秘史》由三部分组成:正文、旁译和总译。正文大字是用汉字音写的蒙语原文;旁译是附在正文每个词语旁的逐词训沽解释;总译则是指正文后面直译大义的汉译文。学术界为了研究方便,将明译正文段落(不一定是蒙文原文的自然段落)顺编序号,约定俗成,遂有了《蒙古秘史》共有282节之说。需要指出的是,《蒙古秘史》因翻译而衍生出了《元朝秘史》之名。《蒙古秘史》是原书名,而《元朝秘史》则是明廷译官在翻译后加上的题名。本文一般使用前者,只有在尊重史料引述原貌时,才采用后者。
2、《蒙古秘史》英译史
作为一部稀世奇书,《蒙古秘史》很早就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自从1866年帕拉基•卡法罗夫主教(Palladiǐ.I.Kafarov)第一次向西方译介《蒙古秘史》起,它的俄译本、日译本、德译本、法译本和其他语言译本迅速涌现,很快形成了《秘史》译介和传播的高潮。然而,在《蒙古秘史》的多个语种对外翻译中,最为典型的还是它的英语翻译和研究。虽然起步稍晚,但英译本数量众多,近些年来更是成果显著。从上世纪50年代起,《蒙古秘史》的英文译本先后涌现,逐渐成为该著作译本最多的西方语种。早期的《秘史》翻译主要属于节译和改写。最早出版的英译本就是由印度的孙维贵(WeiKweiSun)于1957年节译完成的。它未参照蒙文,是针对汉语总译(除第278节外)的一个全译本,起初发表在《中世纪印度季刊》上,后由印度阿利加尔(Aligarh)大学历史系出版成书。另外,美国的包国义(ünensecen)也在1965年发表于《乌拉尔———阿尔泰丛书》第58卷的《〈蒙古秘史〉研究》一文中对《秘史》卷九进行了拉丁转写和英译。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节译改写本是阿瑟•韦利(ArthurWaley)的译本。韦利是著名的翻译家和汉学家,曾经英译过《诗经》等许多中国典籍。1963年,他根据汉语总译翻译了《蒙古秘史》的故事部分,并将译文收入《蒙古秘史及其他》(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andOtherPieces)一书,由GeorgeAllen&Vnwin出版社出版。韦利文学修养很高,加之将译文读者定位为普通读者(manywhodonothaveaccesstolearnedpublications④),故译文流畅简单,故事性强。罗依果先生在谈到其译文时称“就汉语总译的翻译而言……韦利的译本毫无疑问是最具可读性的”⑤。这个译本全文除用方括号标出必要解释外无任何脚注,基本上属于改写。#p#分页标题#e#
作为一部蒙古民族古代的文史巨著,《蒙古秘史》的翻译要求译者具备极高的文学、史学、历史语文学等多方面学术素养,这种基础显然非短期积累可成,因此《秘史》的英译以节译和改写开始既在情理之中,又符合典籍译介由简到繁的自然过程和目的与读者由浅入深的认知期待。但在节译的同时,英文全译的工作也逐渐展开了。就全译本而言,最早的当属柯立甫(F.W.Cleaves)译本了。该译本虽然由于某些原因一直耽搁至1982年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面世,但早在1956年即已完成,1957年已附印。而且据保罗•卡恩研究,“尽管其出版推迟了几个世纪,但早在20世纪40年代,柯立甫译本的抄本就已经在诸如H•戴斯蒙德•马丁和约翰•A•鲍埃勒等多个东方学家和历史学家中流传并被引为出处”⑥。这是一个纯学术性译本。七八十年代是全译本相继问世的时期。1971至1985年,澳大利亚的蒙古学家罗依果(IgordeRachewiltz)在澳洲的学术期刊“远东历史论文”(PapersonFarEasternHistory)上陆续发表了散韵结合的《蒙古秘史》英译文。这个译文已在修订后于2004年由Brill出版社最新出版,名为《蒙古秘史:13世纪的蒙古史诗编年史》(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AMongolianEpicChronicleoftheThirteenthCentury)。1990年,俄岗各•奥侬(UrgungeOnon)也编译了他的《成吉思汗的历史和生活(蒙古秘史)》(TheHistoryandLifeofChinggisKhan(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一书,由Leidon出版社出版。该译本在经过修订后题名为《蒙古秘史:成吉思汗的生活和时代》(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TheLifeandTimesofChinggisKhan),于2001年由Curzon出版社再次出版。这是较新的一个译本,应进一步受到关注。
二、柯立甫译本评析
在《秘史》的众多英译本中,目前为止最有影响、最值得关注的是哈佛大学出版的柯立甫译本。柯立甫是美国资深蒙古学家,他的这个译本以学术性见长,富含了大量的注释、脚注和评论,不仅是翻译而且也是一部珍贵的学术专著,对《秘史》的翻译和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罗依果所言,“田清波和柯立甫的心血之作(按:柯立甫在翻译过程中曾接受了田清波大量指导性建议)为所有目前和将来的译作奠定了基础,是一部具有永恒价值的里程碑式巨作,所有1982年后有关这部蒙古史诗性编年史的译本和版本都极大地受惠于它。”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经典译本给予重点关照,以下试就其总体特点做综合评析。
1.纯粹学术性译本的认知定位
柯立甫译本原计划包含两卷,卷一为翻译,卷二为评论;但实际上只有卷一译本问世。译本包括有发音列表、序言、导言、正文(12章282节)和两个索引。
1)长篇学术导言
柯立甫译本在正文之前包含了一篇长达近50页的导言,回顾了《秘史》在中国经孙承泽、万光泰、钱大昕等学者之手的流传和研究情况以及西方学者的早期研究,列出了《蒙古秘史》的各种流传版本,同时对秘史学研究中诸多富有争论的问题都有涉及或自己观点的提出,如《蒙古秘史》的汉译时间、成书年代、《蒙古秘史》与《华夷译语》的关系等,不啻为一篇史论结合的学术论文,极具参考价值。可以说,这个长篇导言在译本的开篇即设定了其以追求学术高度为目标的基调。学术上的认识与研究渗透到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当中,使得译本具有浓厚的认知特征。
2)学术注释和索引
由于意识到“如果不给出一些评论以作为即时的导引,许多东西不仅注定不能为普通读者所理解,而且也会令专家不解”⑧,柯立甫译本在导言和译文中都广泛使用了脚注,其中导言注释381条,正文注释116条。区别于一般译本注释主要补充解释译文对原文无法对等的非足额翻译,该译本脚注范围很广,既包括对文中个别词句的语文学溯源和解释,也涵盖了内容上的互文见义,同时还有参考文献的拓展延伸等,可以说具备极高的学术价值。即便如此,柯氏仍然认为其不过是介于无注释和专家所要求的尽可能多的翻译注释两个极端之间的一种妥协,详细解释按原计划需见诸卷二更为丰富的评论,然而卷二始终未出也将不再出版。因为在1992年1月27日写给罗依果的一封信中,译者柯立甫明确表示“我实际上已经决定不再竭力去完成我的《秘史》翻译的第二卷……有太多的材料要处理─—我手头有数十个关于已出版材料的文件夹,因此要花费的时间远多于我所能腾出的时间。”⑨具有详尽材料和说明的柯立甫译本卷二因隔时多年大量新出现材料不好整理和作者学术时间紧迫而不得问世了,我们因此对很多学术性的讨论和柯立甫对译文内容的一些解释将无缘得见,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柯氏译本最后附有两个索引─—名称索引和短语索引。名称索引标注了该名称出现的章节和在该章节中出现的次数,同时给出了称谓、称号和表诸自然特征的术语的英文翻译,对其中人名进行了简单的身份认定。短语索引则以同样方式对所有文中保留原文音译形式未进行英译的词汇短语标注出现的章节和在该章节中出现的次数,同时附有各词条中文旁译训诂的英译文。这两个索引皆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不仅方法科学便于读者查询,而且也充分反映出英译本建立在译者对原文详尽细致的研究基础之上,更添译著的学术性分量。
2.以忠实为要义的翻译策略
柯立甫在自序的一开始即点明了泰特勒著名的翻译三原则,并以之为自己的翻译标准。这三原则即:一、译作应完整地再现原作的思想;二、译作的风格与笔调应具有与原作同样的特征;三、译作的行文应和原作一样流畅自然。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柯立甫在译文中诉诸于不同的翻译方法。
1)字比句次的严格对译
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再现原作的思想,柯立甫遵循严格的对译。一方面,他用方括号将所有添加之词(冠词、第三人称代词、表示所有格的介词以及may、might、shall等各助动词除外)标出,力求与原文相比一字不可多。另一方面,柯氏在英译文中力图保留原蒙语句式句序。“蒙语句子成分的一般配列程序,主要成分表现为‘Su[主语]—O[宾语]—V[谓语]’格局,次要成分定语置于主语和宾语之前,状语处于谓语之前。”⑩为了保留这种蒙语句构特征,柯立甫在翻译中往往舍弃英语常用的句式,尽可能地保留原语的句型和句序。对比原文与译文,明显可以看出,除英语和蒙语中动词位置差距太大无法保留外,译者基本上完全沿用了原文的句型和顺序。正如保罗•卡恩所言,“为了尽可能地直译,他(柯立甫)牺牲了常用的英文句法,重构了蒙语原文的语法结构。”○11字对字的翻译久为译界诟病。译者过于刻板的对译确实使译文在很多地方表现出了不堪卒读和令人费解的必然后果。然而,考虑到《秘史》作为一部文史巨著的特殊存在形式和史学价值,我们应该承认译者本着学术译本观力图精确再现其原貌的良苦用心和实际效果。#p#分页标题#e#
2)古体风格的有争议再现
柯立甫在序言中表明“由于意识到‘译作的风格与笔调应具有与原作同样的特征’并有意保持原文的古味,除拼字法以外,在自己看来可行的范围内,我都使译文参照《钦定本圣经》的语言模式,因为我认为它的词汇和风格是唯一与蒙语原文一致相符的”○12。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柯氏译文表现出诸多的钦定圣经式语体风格:①古雅词汇和习惯用法的使用。如you的主格选用古体单复数形式ye和thou,you的宾格、与格和属格则用thy、thee、thine,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时动词变位以th结尾(cometh,drinkth,departeth等),动词过去式变化根据古英语而非现代英语习惯(spake而非spoke,brake而非broke等)……②连接词“and”和介词的广泛使用,使译文产生庄重典雅的古典风味。③平行对仗结构多见,句式匀称,节奏感强,一如《钦定本圣经》般凸现对句法结构的重视。④否定式采用动词原形加not的古用法,不用现代英语助动词加not的形式。问题在于,《蒙古秘史》的语言风格可否和《钦定圣经本》进行类比?后者的语体行文方式是否契合《秘史》的风格?《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源出于希伯来犹太文化;而《蒙古秘史》作为蒙古民族的创业史“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民族文化精神”○13,二者从文化起源和精神气质上是迥然不同的。另一方面,《钦定本圣经》是1611年在英王詹姆士一世治下由47名学者联手译成,以古朴庄严而著称。而《蒙古秘史》虽在1240年成书,古则古矣,语言风格上则更多地以纯朴自然、浑然天成为特征。正如郑振铎所说,其“天真自然的叙述,不知要高出恹恹无生气的古文多少倍!我们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纪》等叙同一的事迹的几段来对读,便立刻可以看出这浑朴天真的白话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来了”。○13从这个意义上对比来说,《钦定本圣经》的语体文风与《秘史》还是有差距的,因而以其语言模式来再现《秘史》的古味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实际上,评论界对柯氏译本的批评也主要集中在此。柯立甫因此在1990年12月18日给罗依果的一封信中抱怨道:“你一定已经注意到,几篇评论中没有一篇是肯定的,它们中没有任何一篇从整体上对我在文中所处理的无数问题给予些微注意,而只是一味痛惜我仅仅因为原文语言本身古老就选用了一种有些古老的英文来作为翻译载体。”○14
3)流畅度、可读性的欠缺
虽然有泰特勒关于流畅自然的翻译原则指导,然而柯氏为追求再现原文语法句法所采取的字比句次对译必然导致译文在流畅度和可读性上大大受损,“很多时候对于一般读者而言甚至困难到晦涩难解的程度”○14。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从精确再现的学术追求角度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其过度操作也在某些时候导致了译文的不可解颐。事实上,作为对柯氏译本古奥难懂的反拨与补偿,1984年保罗•卡恩(PaulKahn)以柯氏译本为底本进行了改写,改写后的语言通俗流畅,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受到普遍欢迎。
3.民族文化解释的残缺不足
作为“蒙古族这个狩猎游牧民族的‘创世纪’”○15,《蒙古秘史》的民族文化特色是鲜明的。作为蒙古学专家,柯立甫对这种文化特征的基本把握是准确的。比如“腾格里”一词,在原文里指“天神”、“上天”、“苍天”,但若随意将其译作God或Lord,必然造成民族宗教概念的偏离,因为这两个词源出于基督教的救世主,而古代蒙古族信仰的是崇拜自然的萨满教,这种替换会造成宗教概念的混淆不清。因此柯立甫选用了兼具自然和神含义的“Heaven”一词,这样的处理是极其到位的。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原文中更多反映民族文化的民俗、民谚等词条,柯立甫或以只言片语简单脚注或者干脆不予注释,造成民族文化解释力度的不足。度其原因,可能有二:柯氏作为蒙古学的大家,对许多蒙古文化特征早已引为当然、不以为异,且作为对定位为学术性译本的读者预想亦认为无需过多解释,此其一;柯立甫译本原计划出二卷,详细解释及评论均欲归入卷二,惜终不面世,成为不完整的译本,注释亦残缺,此其二。总观柯立甫译本,作为一个学术型译本基本实现了译者严格准确再现原貌的翻译目的,译者所采取的一些翻译策略因此应当视为服务于目的的有效途径,但译本在风格上有所偏离原作,文化性、可读性有待加强。
三、《蒙古秘史》的英译趋势
作为一部旷世奇书,《蒙古秘史》本身的复杂情况决定了随着研究的深入新译本的不断涌现成为必然。继柯立甫之后,又分别有罗依果、奥侬两人先后对全文进行了英译。同柯氏译本相比,历时地看,他们的译文逐渐表现出以下趋势来:
1、通俗化
不同于柯译本的学术定位,罗依果在其译文前言的一开始即言明“我进行此项翻译的原因,就是要在F.W.柯立甫的巨著出版之前(按:柯立甫译本1956年即已完成付梓,却迟至1982年才出版面世),为学生和非专业读者提供一个现代英语译本”○16。基于此,罗依果译文摒弃了柯氏的16世纪《圣经》语汇,改用浅近易懂的现代语言;同时,也不再固守原文的语法语序,而是按照现代英语习惯重新整合组织语言,添加部分不用方括号改用斜体,从而使得译文减少阅读阻碍感,更加通俗流畅。另一方面,罗氏译文保留了脚注形式,给出了必要的直译和歧义解释,体现了译者的学术严谨。更为难得的是,译文后附有宏富的评论,从语文学和历史学角度展开阐释,篇幅占到整个译本的三分之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因此,可以说罗依果译本是一个介于学术和通俗之间的中间译本,充分体现了译者在这两方面的着力和用心。及至奥侬的译本,这种通俗化的倾向表现得更为明晰。译者采用了松散的意译法,除不得以外很少用方括号标出添加成分,而且拓展和释意直接以译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出现,保证译本的流畅易懂。总体看来,《秘史》英译所表现出的这种通俗化倾向恐怕与《蒙古秘史》传播推广的客观趋势以及译本越来越针对大众的交际要求不无关系。
2、文化化
作为一部少数民族典籍,《蒙古秘史》所富含的民族文化内涵极其深广,内容涉及宗教、民俗、民谚、制度等方方面面。因此,在翻译中文化内容的准确传递和适当解释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柯立甫的不完整译本无疑是薄弱的,其后的罗依果译本虽然文化解释有所增强但仍显不足,这种情况直至奥侬译本才有了显著改善。这一方面与译者主体(作为不同于以往的达斡尔蒙古人)民族文化意识大大增强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与“秘史学”的研究进展相关─—奥侬教授在翻译中就大量参考了我国和蒙古国学者如额尔登泰、乌云达赉、阿萨拉图、策•达木丁苏荣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表现形式上,奥侬译本的前言除对《秘史》的成书年代、作者、翻译中的问题等学术问题进行探讨外,最主要的是在开篇即回顾了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带领下的勃兴史,并把成吉思汗称之为与释迦牟尼、孔子并列的“东方三大伟人”之一。译本正文后的附录则是别出心裁的“成吉思汗战争艺术”,罗列了成吉思汗的十六大军事策略。这样从译本的总体定位上即凸现出其民族文化读本的基调来。在正文中,奥侬教授用大量脚注对当时的婚俗(如第18节“娶寡嫂制”)、狩猎(如第13节“猎物被放上马之前别人有权提出分享”)、宗教(如第43节的“主格黎”仪式)等多方面的文化内容进行解释,从而使得这个译本的文化价值、文化意义大大加强。而《蒙古秘史》作为一部少数民族典籍的性质也必将使其文化化倾向在未来的译本中会得以传承和发扬。对于这部“谜”一般的典籍,它的英译工作不可能停留止步于现有阶段,新的译文会随着“秘史学”的研究进展而层出不穷,这是因为诚如柯立甫教授所言“由于它(《秘史》)作为一个早期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在数代学者致力于对它的研究之前,不可能有确定的译文出现”○17。随着译者主体的变化和诠释角度的丰富,《秘史》的英译势必呈现更为开放多元的局面。#p#分页标题#e#
结语
《蒙古秘史》的英译研究在本质上隶属于中国民族典籍翻译研究。这是一个横跨民族学与翻译学两大学科、身兼二任的交叉研究领域,也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边缘学术地带。这是因为,一方面,目前我国的民族学研究主要聚焦于民族研究与文献研究两大块,忽视了翻译研究作为其另外一个下属分支的应有价值。事实上,翻译作为不可或缺的一环直接参与很多民族文献的流传和研究,为民族学研究提供新的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信息,从这个角度所进行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因此无可争议地隶属于整个民族学研究的大框架、大学科、大领域。另一方面,当我们设想正在建设中的中国翻译学框架,指出它应当涵盖理论翻译学(翻译理论)、翻译史(包括翻译批评史)和典籍翻译研究三个分支时,又往往遗忘了其中的中国典籍翻译研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汉语典籍文献及其翻译(汉籍外译)。“民族文学,这里专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主流和汉族主流文化的重要补充和中国文学文化全景的重要组成部分,舍此则中国文学是残缺不全的。”○18民族典籍翻译因此是翻译学中典籍翻译研究的重要的构成部分,舍此则中国典籍翻译研究是不完整的。本文选择对《蒙古秘史》的英译情况展开初步研究,正是鉴于代表性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在目前学术领域中的空白现状和课题自身所包含的深远意义的考虑。由于民族典籍翻译的跨学科性质使然,更由于《蒙古秘史》本身的包罗万象所致,《秘史》的英译研究与生俱来要求在方法上跨涉民族学、文献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多个学科,因而需要各领域的学界同仁以跨学科的姿态共同瞩目参与其中。但愿本文不揣浅陋,能够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可以引起更多学人对于我国民族文学、文化典籍翻译研究尤其是外翻研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