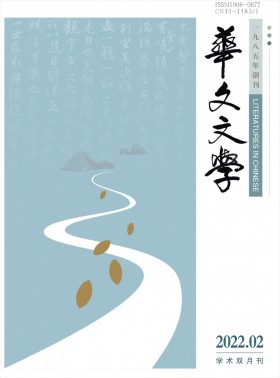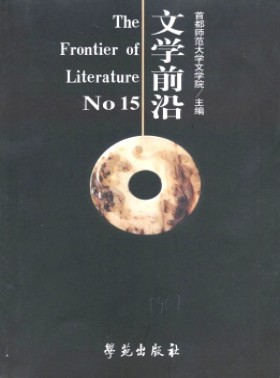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张炜文学的生态观,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生态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种在对环境负责的精神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1)。生态的原意为生命体的生存状态。从人文视野出发,其内涵为:“人适应环境的方式,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处的生存状态,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等层面。”(2)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揭示自然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背后隐藏的精神生态危机。 张炜作为当代文学史上创造力旺盛且成绩卓著的重要作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至今,共创作了《我的田园》(1990—1991)、《九月寓言》(1992)、《柏慧》(1994)、《家族》(1994—1995)、《外省书》(2000年)、《能不忆蜀葵》(2001年)、《丑行或浪漫》(2003)、《你在高原》(2010)等系列重要长篇小说。上述作品执著于对人生存状态的思考,赋予其作品崇尚自然、企慕和谐的生态整体观,表现了对生态危机的反省与批判,展示了对精神生态家园的皈依与守望,体现了作家对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社会发展与环境关系的审美反思,显现出“融入野地”的生态理想。张炜“融入野地”的生存理想不仅仅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精神道德化的问题,更指向人类如何通过维护个体与自然的平衡来维系内心世界平衡的问题,最终形成一个内(人与自我)外(人与自然、人与人)同构的平衡生态世界,以达至“自然”而“自由”的诗意生存之境。 一、生态整体观的书写 张炜对自然深深地迷恋,神奇美丽的自然不仅是他歌颂和倾慕的对象,更成为他思想的源泉、艺术的灵感,甚至是精神的依托、生命的依靠。“我深深地迷恋着这片原野,迷恋着原野上的一切。我觉得自己真的离不开它,即使偶有脱离,也是深深地思念和盼望。我发现大自然教导了我热爱艺术,而艺术与大自然又如此密不可分。”(3)作家不仅在“出奇的美丽,也出奇的富庶”的芦青河边度过难忘的童年,更在野地的小屋中避开喧哗和浮躁写下了众多关于人与自然的诗篇。长期在自然之中浸染,使张炜葆有一颗自然之心。直到现在,他大部分时间仍然居住在胶东半岛的万松浦书院,那里不仅有美丽神奇的大海,还有万亩松林,及松林中的众多动物,无论白天黑夜都能听到大海的涛声,有时还会听到林涛的呼鸣正是大自然的美丽与神圣铸就了作家张炜。在《大自然使我们真正地激动》中,作者写道:“一个诗人如果不能与那(自然)一切相通相连,那么他就是可有可无的。他可以嗅到风、云、河流、树木、太阳等等一切的气味,感到它们的脉动。他的喃喃叙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4)“我每一次走进原野都觉得自己接近了艺术。相反,有时动手写作和阅读的时候,反而觉得离开了艺术。”(5)自然、野地是张炜一生追寻的诗意的栖居地。而与自然相对照,“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最终将告别它市声如潮,淹没了一切,我想浮出来看一眼原野、山峦,看一眼丛林、青纱帐。我寻找了,看到了,挽回的只是没完没了的默想。”(6)这种源于作家内心深处对人与自然密不可分关系的摹写,为生态整体观的建构准备了条件。 生态整体观认为人类与自然世界是一个整体,人不是世界的中心和万物存在的目的,而仅仅是世界的一个特殊成员。因此,所谓“生态危机”,不仅指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威胁,更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指引下,人类对生态整体关系的破坏。张炜深知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现代人为满足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恣意地破坏生态共同体的整体性联系所导致的。对此,他说:“只有土地才会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性质,并且会一直左右我们。我们应该懂得从土地上寻找安慰、寻找智慧和灵感。我这不是一种虚指,而是说要到真实的泥土上去,到大自然中去。当你烦躁不宁时,你会想起田野和丛林。无数的草和花、树木,不知名的小生物,都会与你无言地交流,给你宽慰。”(7)这种全新的生命整体伦理要求现代人放弃与大自然隔绝甚至为敌的欲望,从自然中去寻找新的生命智慧,融入那种生生不息的大化生命之流,体味人与自然契合的激动。自然是张炜小说中一个永恒的主题。作家不仅充满激情地直接对大自然进行描绘与赞颂,更在描写自然美好风物的同时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如何,你应该是大自然的歌者,它孕育了你,使你会歌唱会描叙,你等于是它的一个器官,是感受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和神秘的一支竹笛、一把有生命的琴。”(8)人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用心体会“你才觉得自己不是多余的,你与周围的世界连成了一体、一块,是渺小的一部分,是一棵大树上的小小枝杈,是一条大河上的一涓细流。你与大自然的深长呼吸在慢慢接通,你觉得母亲在微笑,无数的兄弟姊妹都在身旁。连小鸟的啼叫、小草的细语,也都变得这么可亲可爱。你这时候才是真正无私无畏,才是真正宽容的一个人!”(9)张炜把人当作自然的“一个器官”,认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的其他组成部分处于同等地位,共同组成生态整体的观点与美国学者利奥波德(AldoLeopold,1887—1948)《沙乡年鉴》中提出的“大地伦理学”思想有共通之处。大地伦理学认为:人只是土地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明确提出了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本价值判断的标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10)与此相一致,在《融入野地》中,张炜告诫人类:“我所提醒人们注意的只是一些最普通的东西,因为它们之中蕴含的因素使人惊讶,最终将被牢记。我关注的不仅仅是人,而是与人不可分剥的所有事物。”“我的声音混同于草响虫鸣,与原野的喧声整齐划一。这儿不需要一位独立于世的歌手;事实上也做不到。我竭尽全力只能仿个真,以获取在它们身侧同唱的资格。”(11)人类必须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怀着“敬畏生命”的心态,以自然为依托,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才能平安、快乐地生存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远离自然的人,不仅不会有任何真实情感,更会因失去与自然的整体联系而走向毁灭,自然生态的整体性、联系性及人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也由此得以生动体现。#p#分页标题#e# 二、生态危机的反省与批判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由融合到疏离的演变史。现代化进程对自然资源的无穷掠取,不仅使人类日益远离诗意栖居的自然家园,更由于金钱与权势、物质与欲望的膨胀导致日益严重的道德危机,使人类失去了抚慰心灵的精神家园。可悲的是,人类不仅不为自己对自然的肆意蹂躏而反省,相反还为自己的愚妄的举动而沾沾自喜。在张炜笔下,诗意自然被现代工业文明破坏的惨景随处可见。《柏慧》中,白杨林松林和青冈木已被一处处起伏的沙丘链所埋葬。美丽海滩涌入许多外地人,修建了一条条乌黑的柏油路,一辆辆卡车给大海滩上留下了一片片坑穴。野心勃勃的外地人要把这里全部的宝藏挖掘一空:水源、矿藏、果子、沃土。现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制掠夺,不仅使海水一片油污,看不清颜色,更导致地表下陷《刺猬歌》中的唐老驼近乎疯狂地砍伐森林。“一口气砍了九年大树镇上人与林中野物唇齿相依,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日子,从此一去不再复返。”(12)对此,作者曾说:“我亲眼见到有些人狠狠地刨倒了一棵开满鲜花的槐树,双脚把花朵踩到土里时的那种微笑,那是掩饰不住的快感。连续五天的围垦,树林没有了,留下来的是一片焦土”(13)毁灭性的开发使最初无边的密林变成了不毛之地。不仅是自然环境,各种野生动物也面临着灭顶之灾。现代科学技术导致人类自我意识急剧膨胀,人类以自然的主人和征服者自居,傲慢地认为,其他物种的存在意义只是满足人类的需要,除此之外,不再有任何独立的价值与属性。人性的贪欲导致人性的变异,而人性的丧失,往往是从残害动物开始的。在《能不忆蜀葵》中,张炜借主人公淳于阳立之口发出感慨:“现在的人多愚蠢啊,多么不善良,如果找找原因,其中一条就是不能经常与可爱的动物们交换一下眼神!”(14)人类创造了引以为傲的工业文明,创造了繁华的都市,但却日益给自己套上了枷锁。田园牧歌在汽车的轰鸣中消失,都市人在拥挤的格子间呼吸着污染的空气,忍受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迫害,不仅生命力渐趋枯萎,更缺乏生活的诗意。“又破又响的汽车轰隆隆地跑在街上,让人白天晚上不得安宁,冒出的油烟半天也散不开。各种宣传车来来往往,无数大喇叭吵翻了天,野蛮无理地强行掠夺你的宁静。”(15)正如作者所说,大地变得如此拥挤、嘈杂、混浊,人的心情变得烦躁、恶劣,这一切就像一张讨厌的网,罩住了美好的天地。恩格斯曾告诫人类:“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16)人类永远不能够征服大自然,人类永远不应当与自然为敌,从长远看,人对自然的征服、控制和改造绝对不可能获得胜利。但更多的时候,人们忘记了恩格斯的告诫,陶醉于对自然的短暂胜利,妄图以征服自然来张扬自己的力量,不仅导致自然生态危机,更造成人类精神生态的变异。 现代文明在给自然生态带来深重的灾难的同时,更使素朴、纯净的乡村在异化中走向毁灭。《九月寓言》以神话的方式宣告了现代文明侵袭下一个诗意栖居村落的覆灭。矿区大量地开采,导致小村的根基被掏空,小村人最后只能被迫迁移,只留下一片荒草和一些断墙瓦砾。“那个缠绵的村庄啊,如今何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沉寂和悲凉。”(17)现代文明正在侵袭着最后一块“野地”,工区里的许多事物都让小村人羡慕:黑面肉饼,澡堂,胶筒皮靴。矿区给小村带来了文明,但也带来了难以预料的灾难。城市文明是诱惑人的,它使小村的女人频繁地到矿区澡堂洗澡,它能使女人们变得更白更美,但诱人外表下潜隐着的巨大的人性变异,不仅使洗澡后的小豆被矿工小驴强奸了,更使村民龙眼、憨人等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自愿做了矿工他们虽然吃到了黑面肉饼,但龙眼却为此死于矿山事故。连村里最俊俏的女人赶鹦,竟然也受到了四十多岁秃顶工程师的诱惑,二兰子更是被语言学家欺骗,忍受着堕胎的痛苦令作者痛惜的不仅仅是毁灭乡村的自然生态危机,更是自然生态危机导致的乡村人自然本性的失落、人精神的异化。 张炜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犀利而深刻的。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在19世纪和20世纪所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就是追求物质的欲望不可遏制,一再地毁坏大地。更不可饶恕的是毁坏世道人心。单纯地发展经济、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的思想,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思想。这是人类最没有出息的表现。”(18)推动现代文明的根本力量无疑是现代科技,对此张炜批判道:“现代科技的发展有一个积累和突破的过程:这个过程终于有一天突破了一个度,伤及人性的朴素和自然的属性,而且难以换回。这将是当代人类诸多难题和困境、导致未来灾难的总根源。”(19)的确,现代文明如张炜所说把人的欲望充分调动起来,使人与大自然处于敌对状态。因此,逃离城市返回乡野不仅成为作家张炜的文化批判立场,更是精神归宿的选择。《柏慧》中,主人公逃离了都市,返回乡野繁茂的葡萄园;《外省书》中的史珂从首都逃到济南,再逃到胶东半岛;《怀念与追记》中,主人公老宁一直不停地逃离都市;而《远河远山》中那个热爱写作的主人公更是对城市避之唯恐不及。与之相对立,那些信奉并享受着现代文明的人物,在张炜小说中多为道德沦落、心灵扭曲、肤浅庸俗的人,《九月寓言》中的秃脑工程师,《柏慧》中杂志社中的大部分人,《外省书》中的史铭和史东宾父子等均为代表。现代科技带给人们的既是一种进步,在某些方面又是一种退化。在张炜小说中它更是作为异己的、毁灭的力量而呈现,从而给人类生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把人类与生态环境分成主观和客观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但是张炜作品中所展现的现实却十分明显地否定了人与生态环境的独立性。作品清楚地表明:外部生态环境的破坏可以导致人类“内部自然”——“精神生态”的失衡。作家因此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竭泽而渔式的现代化和工业文明,作品对生态现实的批判和哲学反思达到了相当的深度。#p#分页标题#e# 三、精神生态家园的皈依与守望 张炜笔下乡野自然美丽得像是童话中的王国:大海滩满是野草、野枣、花儿;庄稼地里蚂蚱在草窠间蹦跳,起飞,草又嫩又绿;河里面有鱼有鳖有螃蟹,还有一片片的苇子张炜描绘自然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自然美,更是为表现人在自然中和谐快乐自在地生活。在他看来:“人直接就是自然的稚童,无论他愿意不愿意,也只是一个稚童而已。对自己和自然的关系稍有觉悟者,就会对大自然产生一些莫名的敬畏。人的社会活动,都是处于自然的背景之下、前提之下的。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现代人对自然虽然不能完全是依从和服从的关系,但也差不太多。人力不可能胜天,人只能在大自然的允诺下获得一定程度自由。”(20)张炜作品中生态意识的核心就是构筑一种倡导万物之间和谐与互爱的生态伦理,其关键无疑是重新理解人在大自然中的位置,反叛在控制与征服自然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地位的无限制扩张,进而表现人作为大自然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如何在与自然的诗意栖居中走向绿色生态家园的。 短篇小说《三想》是现代化背景下倡导生态意识,表达生态理想的重要作品。在生态意识指引下,小说中的动植物与人一样,都是有灵性、会思考的物种,它们原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因同处生态危机的现实,进而回顾经历,反思根源。《三想》并置了一个在大自然中流连忘返的“奇怪的城里人”(人)、一只遭受人类伤害的母狼(动物)、一棵阅尽大山荣辱兴衰的百年老树(植物)的所想所思,三种生命形式并举,共同反省人类对自然的历史与现实。“令我无比震惊的事实”是大自然的瑰丽生机竟存在于这样一个军事封锁区。这里花草繁盛,森林茂密,野物会聚“这个世界恰恰是因为拒绝了人、依靠着大自然的汤水慢慢调养,才滋润成今天这个样子。”饱经忧患的母狼呣呣望着倾盆大雨,对人类的至高无上发出质疑“:人如果真是至高无上的,就除非没有太阳和土地。”而崖下那株历尽沧桑的老白果树,则为人类对自然的肆意妄为感慨不已。通过母狼呣呣的自述,作家阐明了现代人自绝根脉的疯狂与愚蠢;而崖下的老白果树更是看清了人类几百年来与绿色为敌的狂妄与目光短浅老白果树喜欢与任何形式的生命亲近、母狼呣呣虽然备受人类迫害,连最亲爱的儿子也被人类打死,却仍不忘呼喊:“让我们这些做母亲的达成新的谅解吧,我们有权利让后一代和气地相处。”(21)面对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倾听动植物对人类粗暴对待自然的控诉,城里人对现代人与自然失衡的现状进行了反思:“人只有走到大自然中才会知道自己是多么渺小,多么孤单。要解除这些心理障碍,也只有和周围的一切平等相处”(22),体现了作家对生命平等,和谐共存生态理想的执著守望。 张炜对大自然的挚爱,不仅表现为对自然的贴近,更把自然作为他精神理想的主要寄托对象,通过自然万物的呈现,展示其对生态理想的憧憬与想象。张炜曾说:“我反对很狭窄地理解‘大自然’这个概念。当你的感觉与之接通的时刻这一切才和艺术的发条连在一起,并且从那时开始拧紧,我有动力做出关于日月星辰的运动即时间的表述。”(23)大自然既是张炜生命的体现,更是其艺术生命的寄托。他的艺术在广阔的大自然中自由驰骋,构筑了一个恬静和谐的自然生命与自我生命同一的精神生态家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表达了对“诗意栖居”理想的渴望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