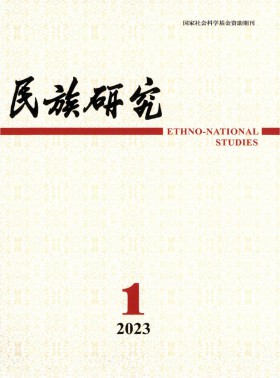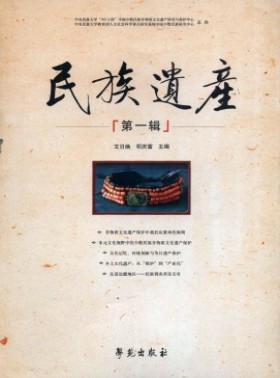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民族谴责与艺术探讨,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台湾少数民族,大陆总称为高山族,族人现在自称原住民,一般分为九族,内部文化有相当大的歧异。但由于九族在当代社会经济变迁中有共同的遭遇,因此本文将其作一个整体看待。台湾少数民族当代社会文化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艺术实践的丰富性和多意义特征为我们理解艺术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个例。由于歌舞对台湾少数民族有特殊意义,并且相对于其它台湾少数民族艺术来说,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对创顷注了特别的关心。 一、理论:艺术、族性与社会力量 珍妮特•沃尔夫(Janetwo盯)认为:艺术并非超乎存在、社会和时代之上的“天才的创造”,而是“包含大量现实的、历史的因素的相当复杂的建构。”“艺术和文学应该被视作历史的,被环境决定了的,和生产性的。”①豪泽尔(AnloldHauser)也说:“世界上只有无艺术的社会,而没有无社会的艺术,艺术家总是处于社会的影响之中,甚至当他企图影响社会时也是如此。’,②两位理论家的共同信念是:永远没有超脱于社会力量的艺术。对于少数民族艺术而言,这一信念的直接理论后果是:少数民族艺术及其实践必然受制于并表达民族自身社会、文化、历史所赋予的,与他人有区别意义的特征,即族性(ethnici-ty)。 不过,根据吉尔兹(《3搜rtz)的主张,族性其实是一个历史过程:族性的维持有赖于族群认同(ethnicgro叩identity)的建构,这种建构需从族群共同体的“原生纽带”(primordlalties:指族群共享的先赋特征,如族源、体质、共同语言、共享文化等)所赋予的文化特质中寻找资源;但族群认同的唤起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至少两个不同族群在同一社会环境中的分立和互动;“原生纽带”的自我表现也在历史中不断变化。因此,吉尔兹认为:应当将族性放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oontext)中去考察,才可能理解族性的双重政治文化意义:它既是变动不居的社会结构的决定因素,也是这种结构的产物。’,③这样,少数民族艺术就不能不反应族群关系及其所发生的社会语境,这就是说,它要反映族群互动的具体历史以及互动所依据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历程。 就如豪泽尔所强调的:“当我们考虑艺术和文化发展的地方因素时,我们仍发现,社会关系的作用比种族和民族因素大得多。”④因此,对于少数民族而言,“艺术无法超脱社会力量制约”这一命题就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它还受制于并表达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结构。这篇文章关心得更多的也正是这个方面。 二、台湾少数民族当代社会变迁及变迁中的歌舞艺术实践 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变迁是台湾地区二战后现代化变迁的一部分,它有一种阶段性特征:40年代末一50年代末:这期间,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变迁整体上不明显,由于“山地保护政策”的实施,其固有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未遭遇异文化的强烈冲击。⑤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歌舞艺术处于其原生状态,即与其生活融为一体的状态,换句话说,少数民族主位并没有艺术这一分类,逞论歌舞艺术。不过,就局外人观之,其能歌善舞的特质是相当引人注目的。⑥60年代初一80年代初: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增长,在经济力量带动下,市场经济通过行政力量扩张至山地社会,造成山地传统社会结构的改组乃至崩解。⑦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压力强化了主流社会(本文指台湾汉族社会)的“同化”企图,沉重的同化压力给少数民族社会带来重大的社会文化后果,也因此给台湾社会带来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山地雏妓”问题,对山地籍童工及船员的超经济剥削等,限于篇幅,不作详述。这一阶段,台湾少数民族歌舞因经济压力而从生活整体中剥离,这就是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山地“观光秀”歌舞表演的大量出现。但经济驱动并未促使山地歌舞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独立艺术门类:观者不以审美,而以猎奇为目的,表演者不以传达民族审美意识,而以获得现金为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原本质朴的山地歌舞媚俗化。 80年代初一卯年代:前期积累在少数民族群体内的同化压力造成的紧张情绪急需得到纤解,而台湾地区政治集团的结构调整为这种纤解提供了可能—“原住民族群认同运动’,⑧蔚然形成。这意味着少数民族不甘于变迁中的受动地位,意图起而成为变迁的主导力量之一。该运动始终以为弱势民族要求各种权力为目的,但取向上前后有差别:90年代以前,主要倾向是抗争,⑨90年代后,主要诉求是重建和对话。⑩少数民族歌舞也适应族群运动的需要,特别在90年代,少数民族利用歌舞艺术的符号象征特征,重建民族认同,并以之与主流社会对话。“原住民乐舞系列”和“原舞者”表演是实现上述目的的具体努力。。 三、社会力量格局、族群运动和民族艺术实践 (一)力,格局中的族群运动 反观台湾少数民族变迁史,有两个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第一,是变迁中有一个一直起作用的结构性力量存在,即台湾主流社会与少数民族社会在社会历史文化力量对比中的一强一弱的格局,这一格局即使在今天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第二,在变迁压力下,少数民族的族群认同表现出相当强的韧性。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可以概括为:“强一弱”力量格局赋予主流社会主导变迁的权力,这种权力在6任一80年代强加给少数民族巨大的同化压力;少数民族认同的韧性使之在同化压力下面维护了地区中族群文化多元性的存在,并使主流社会无法支付一体化的成本,转而考虑将多元文化的冲突制度化,以维护地区性社会的整合。 不过,总体来看,“强一弱”力量格局仍是更基本的起作用因素:族群运动的价值。正因此,它可以视为少数民族在舞台上展示民族意识的最初尝试,这种尝试提供了一种主流社会人群可以理解的对话方式(之所以可理解,乃由于它已归于主流社会的分类),因此在族群运动后来的“对话诉求”中有重要意义。#p#分页标题#e# (二)歌舞艺术与族群政治%年代初“原住民族群认同运动”的特色之一,就是它表现为一系列的文化展示,除了“原住民乐舞系列”和“原舞者”表演外,还推出了哈古(卑南)的雕塑,拓拔斯(布农)的小说,莫那能(排湾)的诗集等。。这种文化展示实际上代表“原住民运动”由抗争诉求向对话诉求的转型。这阶段的歌舞艺术实践,带有强烈的艺术外目的,这种目的同族群政治密切相关:第一,它是认同的符号建设,第二,它是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对话的手段。 许多族群理论家认为:“族群认同的维持,系仰赖由成员们所操控(~iPu-Iate)的一些文化特质的作用过程……这些人将宗教、族称、地域性或美学形式等文化特质组织起来,成为一组用来识别族群的表征。’,。“原住民乐舞系列”和“原舞者”表演无疑都有认同重建的意义,都希望“借着在国家剧院的表演,……使族人对自己的文化再肯定,更珍视。”⑩它还具有对在变迁中疏离了自己本文化的族人进行“传统教育”的意图。 两种“原舞”表演还意味着台湾少数民族在文化领域争夺表达权力,通过艺术符号的展示,一再地宣称并强调自己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有与主流社会平等对话的基本权利。 当然,平等权利的实际获得,有赖于对话实践过程的有效性,即发言必须为对方所理解。这实际上需要对话双方的共同努力,但少数民族的对话对象并非都是经过人类学训练的热心人,而是对本文化完全“自以为是”的主流社会大众,这注定了少数民族发言人为实现沟通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包括为适应主流社会大众的理解方式而冒误读本文化的危险。 (三)对话与沟通的困境 前文曾谈及“观光秀”的客位分类意义,而%年代的两种“原舞”实践作为申张族性的努力,并未让歌舞重新回到生活整体,而依然采取舞台表演的形式,这样做是必须的,因为这才是主流社会可以理解的方式。然而,这也使少数民族表演者陷人陌生的语言—舞台语言的环境中。应该说,两种“原舞”实践相当有创造性,为了用舞台语言表述民族意识,表演者下了很大的人类学工夫:表演者尽量采用少数民族成员,表演内容与部落实际一致,“进场速度、灯光语法,也要依其乐舞本来的情绪起伏来表现。因此……要求全部工作人员,包括舞台灯光设计等都到部落去了解这乐舞背后的意义。至于本质,则完全由他们(少数民族演员)来呈现,音乐上尊重原音,舞蹈上不加编排”。⑩这种跨越认知障碍的艺术实践十分可贵,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不过,毕竟是两种差异很大的语言,因此,沟通与对话中的误读在所难免。仅是舞台,就已经对少数民族歌舞所由发生的时空制度进行了改造。比如阿美族丰年祭中的集体舞,舞步复沓且持续时间之长(动辄数小时),根本无法在舞台上复现,但恰是这种复沓和漫长才充分融人了部民的企愿和追求,对真正的欣赏者来说,观此舞所受的心灵震撼与观舞台表演的感受大不相同。 在两种“原舞”的编排中,许多认知障碍也是无法单方面克服的。“原住民乐舞系列”要依赖汉族民族学者明立国的舞台演绎经验,“原舞者”要依赖汉族民族学者胡台丽的“研究成果和人际网络”,乃至“文建会”的经济支持。⑩—在对话过程中,少数民族必须面对主流社会无所不在的话语特权,这是由其在社会力量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决定的。 下面三个例子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云门舞集”表演后出了邹族歌曲VCD和录音带,这成了邹族青年学习的范本,但在“邹族传统中,有些特定的祭歌只能在战祭前几天才能学唱,并只能由头目等少数人教导演唱。现在不论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吟唱,(族中)长老们害怕这样会触怒天神,使族人催涡。”“原舞者”表演赛夏族“矮灵祭”舞,由于各种原因,基本采用大隘部(北赛夏)的形式。演出后,遭到向天湖部(南赛夏)的抗议,认为这并非赛夏祭舞的正统。 “原住民乐舞系列—卑南篇”成员到卑南族各部落作田野调查,希望找出最能代表卑南族的乐舞或祭仪,不料卑南八部各有主见,都觉得自己推出的节目最能代表卑南族,结果在各部间产生嫌隙。’,。 少数民族在对话中的困境实际上就是他们对本文化进行连释的困境,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主流语言和本民族语言间争夺侄释优先权形成的紧张关系,主流语言已因主流社会之强势而渗人少数民族社会,因此两者的冲突多少表现为少数民族成员的内心冲突,其具体表现就是:少数民族很难在自我诊释的“策略取向”和“民粹取向”上作出抉择。这不仅是民族艺术,也是整个族群运动的难题之一。“民粹取向”借口沟通的不可能性而放弃对话,固然不可取,但单纯策略性取向也易导致对主流语言的屈从和牵就,两种极端都无法完成族性的准确传达,这不仅是少数民族自己的损失,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一种有益的价值参照的失落。或许,历史的最终结果由两种取向的合力决定。 其实,族群运动本身的建构性已经决定了它的策略性,特别是在“强一弱”力量格局客观存在的多元社会,主流话语要素进人弱势民族历史几乎不可避免,台湾少数民族歌舞艺术的舞台化就充满了策略性考虑。毕竟,族群运动的目的并非将本民族文化要素纯粹而全面地保有,而是不断唤醒和建构认同,以证明自己是一个有区别意义的存在;另一方面,这一证明,又确实必须在本民族的独特历史文化中寻找资源—这大概就是吉尔兹所谓“族性既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又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产物”的含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