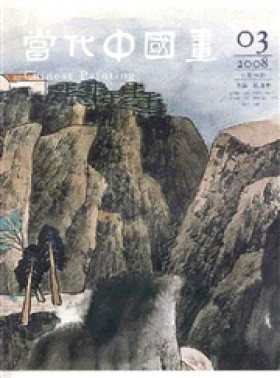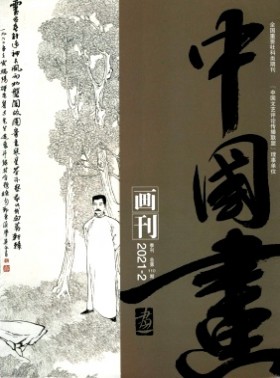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中国画创作与浪漫主义情怀,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就20世纪中国画发展史而言,中国画与浪漫主义艺术思潮结缘颇深。1912年11月刘海粟与乌始光、张聿光在上海创办现代中国第一所美术学校,任“上海国画美术学院”校长,首创男女同校,采用人体模特儿和旅行写生。他与蔡元培等学者一起借助感伤忧愤的立意,传奇的情节,让中国早期的中国画激荡着追求个性解放的自由呼声,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也埋下了中国画创作的浪漫主义情结,虽然时代浪潮跌宕起伏中的浪漫主义,更多地演化成一种审美态度,创作姿态,但其核心要义依然离不开创作主体对理想、激情及个性自由的渴望及追求。当我们从这一视点切入中国画新时期文本时,还是能从中清晰分辨出那些浪漫主义先行者的步伐姿态,并以此为线索追求后来者探求社会人生真谛的心理轨迹。
以历史人物或事件为题材的中国画作者常常采取一种凭借想象追溯历史场景的构思方式,而这种充满艺术想象因子的回望式作画姿态令历史画卷天然富含浪漫气质。中国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认为“诗人的责任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艺术家更富于哲学意味、更高。诗人出身的艺术家刘海粟的艺术观显然有自由主义的味道,而且富有浪漫主义气质。20世纪上半叶,在刘海粟的浪漫主义自由化的推动下,曾催生出了《巴黎秋天》、《关汉卿》等一批极具浪板主义审美品格的经典作品,使中国画成为现代浪漫主义艺术实践最为集中和突出的一个领域。而艺术创作选取的人物原型,或是心怀天下的思想巨匠,或是为改革献身的政治家、或是领一代风骚的大诗人,无不颇具精神高度和强度,本身就富有传奇色彩。同时,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又无一例外地设置节奏紧凑的情节,歌颂、赞美并随情境辅以饱含深情的抒情画面,以烘托人物的超越世俗的博大胸怀与高尚品格。塑造拥有崇高情怀的传奇人物曾是传统浪漫主义作品的突出特点,虽然,浪漫主义作品在新时期似乎已很少被提及,可是由个别艺术作品艺术特色,及截取历史人物生平中最艰难、困顿的人生时刻,于紧张的外部冲突中浓墨重彩地展示人物灵魂,凸现其为理想献身的强悍意志,我们不难看出,新时期的艺术创作在精心选择和塑造人物的画面构思中依然承袭着浪漫主义的精神传奇。
隔开久远的历史时空,拂去岁月沧桑的尘烟,将浪漫主义精髓复现于现实生活的有限时空中,艺术家的创作一般都不会拘泥于“形似”——平铺直叙一个人物的生平经历,而求“神似”——借助浪漫主义艺术表现手法定格放大这些著名历史人物身上的精、气、神,以求对现实有所辐射,这显然是新时期艺术作品富于浪漫主义气质的审美诉求。
军旅生活一直是当代艺术创作的热门题材。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美学倾向整体的“向内转”,军旅题材范围由相对集中的军营向更为开放的社会拓展,军人形象的刻画也突破了英雄主义模式,实现了向社会化、心灵化的转移。和平时期军旅生涯的内涵价值何在,社会转型期何以保持军人本色及品格,成为新时期军旅文学的一道严肃的审美命题。于是,我们看到了理想,一直以及感情等精神因素在新时期军旅题材创作中再度活跃,并为其平添了许多浪漫色彩。
拉开时空距离,追忆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岁月中的人情往事,从中凝练军旅之魂,是新时期军旅题材作品的一个重要表现。如解放军艺术学院创作的作品《南昌起义》开启了当代叙述者的追忆:惨烈的湘江战役、艰苦卓绝的爬雪山过草地,众多艺术家作品中的人物 克服千难万险,舍生忘死履行着鼓舞士气的宣传职责。女兵们用朴素的竹板、伤痕累累的留声机,更用青春的热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来自万里长征的美丽画卷。追忆中的场景与叙述者的心灵空间中交织延展。展览中,观众被深深震撼,因为“看懂了”那幅来自军人心灵的美丽画卷。刻画和平年代的军营或军人家庭生活,挖掘展示他们炽热而丰富的内心世界是新时期军旅题材艺术表现的另一个突出主题。
与新中国成立30年的革命战争题材作品相比,上述作品不像传统作品那样将军人性格置于激烈的战争冲突中加以聚焦式的刻画,以求塑造高度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借助时空产生的心理距离对老一代优秀军人的内心做探寻式的凝视特写,更注重在当下视角与历史视角的扭结交织中透视军人的内心世界,提炼军旅精神之魂魄。由此,虽然就美学境界而言,新时期军旅作品对军旅铁血深情的书写抒发缺了几分传统文本的壮怀激烈,却常因对军人执著于理想而曲折回环的内心真实情态的揣摩刻写而让人产生一种意味绵长的思索回味,并在这思索回味中加强了对人性崇高美的体验和感受,这也正是新时期军旅题材作品最具浪漫主义特色的所在。一切视觉艺术都是看与思的问题,风景画写生也不例外。 罗丹在谈到艺术家的眼睛的时候时说道:“艺术家所见到的自然,不同于普通人见到的自然,因为艺术家的感受,能在事物的外表之下体会内在的真实。艺术上的唯一原则,是把看见的东西抄录下来。问题在于见与不见。……一个低能的人只会抄写自然,而永远不会成为艺术品……艺术家看见的是通过他的与心相应的眼睛深深理解自然的内部。”在风景画写生中,破旧的茅屋,残败的围墙,泥泞的道路都可以成为画面的主题。在自然中一般人认为所谓“丑”的,在艺术中能变得非常美。破旧的茅屋,残败的围墙,泥泞的道路与普通的景物没有什么不同,但当破旧的茅屋,残败的围墙,泥泞的道路变成风景画的主题,它们就与一般的景物有了区别,它们的存在方式有了变化,艺术家不但赋予了这些景物以一定的形式,而且赋予了形式以一定的内容,艺术家与常人不同的是,艺术家不仅看到事物的功用,而且看到了事物中所蕴涵的美。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谈到:“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是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风景画写生能够训练感受形式美的眼睛。它能够改变我们视觉的态度,使我们超越实用的目的,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法国印象主义画家修拉用色点混合的方法来看待我们的世界,塞尚用圆柱体、圆锥体和圆球体来看待自然界的一切,马蒂斯要用儿童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活。艺术家都有自己看事物的独特方式,这是一种与常人不同的眼睛。#p#分页标题#e#
从审美角度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对于知识青年群体而言不谛是一次浪漫的注意意识拓荒体验。称其浪漫是因为,偶然的历史机缘改变了知青的生活轨迹,让他们在戈壁、丛林和荒滩上抒写下一段别样的青春成长史,经历过磨难,深思过生存,同时也意味着完成了一次对主体人格精神的强力锻铸。暮然回首荒原里青春生命的鲜活印痕令新时期的知青题材文学整体充满了浓郁的感伤抒情,有关青春、理想与命运的混声交响仍然回旋于20世纪80、90年代的艺术界。
青春是浪漫主义文艺最擅长表现的主题之一。青春主题曾经与革命主题结合在美术创作上表现出不少红色浪漫的华彩篇章。相比之下,新时期艺术作品的青春主题突出展现于知青题材中,其负荷的浪漫主义审美意蕴虽不乏激扬壮丽,却也因掺合着源自“”政治劫难的迷惘困惑,笼罩上了几分现代主义阴郁冷峻的色调,风貌色彩显得有些斑驳陆离。
无论浪漫主义思潮的内涵随时代社会变迁如何演变,自然乡土,永远是浪漫主义艺术无比钟情的精神家园。回归自然乡土的呼声里凝结着浪漫主义对现代文明的深邃思索与对理想人性的完美预设。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由文化寻根思潮的激励促发,新时期艺术对人类主体意识的美学探查出现了明显的生态人文审美转向,兼具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色彩的寻根题材作品的诞生。
徐悲鸿、张大千、刘海粟等艺术家们的艺术触觉是敏锐的,他们或在中国乡村与美国城市这样本土与西方文化的碰撞点上,或在原始山林这样现代与远古的交汇处展开深刻的自然人性艺术探查,其视野已逐渐超越现实的局限而跃向自然人文更深广辽远的时空之域。
因为裹挟着对主体意识的强烈求索与确证诉求,20世纪80、90年代影响深远的寻根文学曾被称为一次浪漫的精神还乡之旅。不难看出,新时期艺术创作也和小说、诗歌创作一起深度介入了这一特殊的旅程。与寻根文学一些过度渲染乡土文明原生态并流露出复古意识的作品相比,吴冠中先生常借鉴运用现代主义观念与技法,传达出对自然乡土审美价值的复杂体验,与此同时,也并未完全放弃源自内心的浪漫主义诗意情怀,并借此完成了充满困惑迷惘的精神还乡途中的对理想信念的一种的审美坚守。
当由浪漫主义审美对心时期作品进行了一番定点扫描后,我们发现,虽然新时期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创作观念之争及其艺术实践探索,但众多艺术家依然难以完全割舍那缕源自心灵深处的浪漫主义情愫,或许正如当代著名女作家王安忆所言,“‘浪漫主义’已成为一句俗语,人们将它当作一种与‘现实主义’的相对面而提,只是一个品种似的,岂不知它是一切艺术活动的起源与根本”,不论是否被遮挡在别样的艺术风姿下,这份都融注于深层创作动机中的浪漫主义情怀都推动着新时期艺术家们关于人性的探险求索,并造就艺术创作持久、强烈的美感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