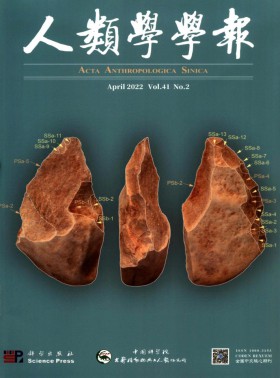作者:张海超 徐敏 单位: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对于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在云南的传播,相关讨论已经很多,蓝吉富、李玉珉、侯冲、张锡禄、李东红等的研究都不乏真知灼见,但另外不能忽视的是显宗诸家在大理的承传也未曾中断,正是显密两宗的融合使大理佛教信仰显示出独特的面貌。本文借用人类学的理论,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阿吒力教派进行民族志式的解剖,从僧迦制度、寺院建设、民间转向等细节展开讨论,此类“横截面式”的描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密宗阿吒力教派及显宗各家在大理的传承情况,由此而上,力图对南诏大理国佛教信仰的发展情况形成总体性的认识。
一、佛教显宗的传入与发展
一般认为,大理国时期洱海区域的宗教信仰基本以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为代表,但除崇信密宗之外,很早便从汉地传入的显宗在大理地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扬。以往的研究对南诏大理密宗的传播情况讨论已多,关于显宗诸家在大理地区的传播情况的专门探索则不多见,至今仍有不少的难题等待解开。云南佛教传入的确切文字记录最早出现在元初李京的《云南志略》中,“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1](P127)。此时正是密宗从印度开始外传的时期,两年之后的开元四年始有天竺僧人善无畏携《大日经》和《苏悉地经》来唐,因此,最初由唐传入的应该是密宗之外的其它宗派。所以,如果大理佛法以从唐朝传入为主的说法成立,其便绝不可能只有密宗。作为中国佛教成熟标志的禅宗和其它教派也应该一起进入了大理。有学者认为“显教各派……在云南很难开门立户”,南诏和大理国的禅派“虽然有几代大师的惨淡经营……最后又都淹没在阿吒力的大海中”[2](P195)。笔者认为,如此轻易抹杀显宗的传播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从1978年在维修大理三塔时发现的塔藏文物来分析,除发现大量密宗的佛像和法器外,也有反映内地华严宗、禅宗等汉传佛教的内容”[3](P245)。此外,凤仪阿吒力世家董氏法藏寺中发现的大理国时期的经卷中大部分都是从内地输入的显宗各派经文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4](P11~60)。现藏台北故宫、创作于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为禅宗诸祖留足了位置,对西土初祖的迦叶、阿难,到从达摩至慧能的中原六祖,一直到和尚张惟忠、贤者买纯嵯、纯陀、法光和尚等禅宗在云南的传灯图录记载详确;结合祥云水目山大理国《皎渊塔之碑铭并序》的记载,“利贞皇叔”曾有“达摩西来之,祖祖相传,灯灯起焰,自汉暨于南国,幸不失人”的提法,可见禅宗在云南曾经地位显赫。许多学者根据《中峰道行碑》称禅师的云南弟子玄鉴“兴立禅宗”、并被奉为“南诏第一祖”的说法而简单推定南诏大理国时禅宗完全没有传播或者极度微弱是筛除了一些关键性信息后做出的判断。
根据昆明玉案山筇竹寺的历代碑铭,大理国灭后,云南出现了一次禅宗重新传入的潮流,洪镜雄辩、玄坚雪庵等还开启了用?语讲经的潮流,但既然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禅宗已经获得了很大发展,为何元代昆明的佛教界还会认为此时才是禅宗初传呢?这种论述的出现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禅宗在云南最初几代的传播都集中在大理崇圣寺和祥云水目山,昆明不是禅宗的流布中心,此地的学者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其它地方的情况。此外,和中原禅宗呵佛骂祖、参话头、斗机锋等活泼生动的传布方式不同,大理的禅行实践似乎很快就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比如身居名刹崇圣寺的道悟国师“以定慧为禅家所宗”,玄凝则整日写经“,坐化之日,计其平生手书藏经多至万卷”[5](P20)。在禅学的另一中心———相国高氏掌握下的水目山,禅宗在数传之后也出现了新的气象,《水目寺诸祖缘起碑》记载:皎渊智元“昼则精研经论,夜则达旦跏趺。衣钵之外,分寸无余”,其修法方式颇类早期的苦行禅法;被奉为水目四祖的阿标头陀则是以长于神通的面貌为世人所仰慕:“虽去二百里者,食顷便回”,这些情况和中原禅法的发展不尽相同。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为贴近的禅宗表现出强烈的门派观念,从画卷看,位列六祖之后是神会的像,大理禅宗似乎接受的是菏泽神会的法嗣。神会和尚为南宗禅的大兴天下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但中原禅宗在以后的传承中却以清原行思和南岳怀让的影响更大,他们二位分别被后世门人推为“七祖”,神会一系的传承则很快走向衰弱。禅宗在慧能的弟子们分别发展成“五家”之后,又以南岳怀让系成为临济正宗,此宗大兴天下成为禅宗主流,几乎垄断了教内的话语权。元代云南僧玄鉴得到中峰的印可,成为临济正宗第二十代传人,当时人称他为云南初祖,似乎是在临济宗内的考虑。而临济的后传弟子有意不承认神会系之前在云南的传播可能是出于门派之见。后来许多学者根据元碑的说法认为南诏大理国只流行密宗、元代才是禅宗第一次在云南扎根是对此教内提法的误解。
华严宗兴盛于唐代,其独特的判教思想和认识论体系影响深远,儒家后起的程朱理学也深受其影响。华严宗在云南的传播至今仍有较多的实物证据。昆明郊区安宁曹溪寺大殿经梁思成先生考证为宋代(大理国)的建筑,而寺内供奉的木雕华严三圣也被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的周叔伽先生鉴定为大理国时期的珍贵文物。另一组传世的木雕像是由费孝通等人发现于凤仪北汤天村的文殊与普贤像,这两组古老的木雕佛像反应的内容均与华严信仰相关。此外,在被誉为“南天瑰宝”的剑川石窟中华严三圣的形象也很突出。它们的存在反映了当时华严宗的神学思想在当地社会被普遍接受。华严三圣在常见的显宗佛教造像组合中神秘色彩最为浓郁,三尊中间的佛祖显示法身为毗卢遮那佛,但这些造像毕竟都属显宗,并不是密宗的多头、多臂、面目狰狞的形象。参考现存云南省图书馆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保存的大理国写经中与华严信仰有关的多幅经卷,当时华严宗在大理流传广泛的情况可以基本明晰。
明代之前的云南佛教界有很多大德都有关于华严思想的著述[6](P237~246),尽管该宗详尽的法系脉络一时仍无法考证,但它在南诏大理国一直流行是毫无疑问的。由此观之,昆明西北筇竹寺古碑《重修玉案山记》中“滇人所奉皆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的说法并不实,应为夸大雄辩等人功绩、并配合元地方政府大兴土木扩充显教寺院而言的。此外,禅宗在中原的兴盛是各山高僧在全国范围内到处参学、不断交流的基础上实现的,保持相对独立的大理国并不具备此条件,当地的佛教徒显然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候冲先生曾考证天台、华严诸“教宗在云南可能没有具体分派”[7](P263),此类哲学基础深厚、思辨色彩强烈的宗派确实可能很快便走上合流的道路,各家在戒律和修行方法方面和密宗保持区别,但显宗内部各宗派已经不再泾渭分明,所有的修行者都被称为“得道者”或“净戒”,而与着重仪式、习瑜伽“密教”的僧侣相对。总之,对佛学理论的接受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可能会各有重点,大理佛学理论承传和修行方式有自己的特点,而与中原地区不见得步调一致,这可能也是给撰写者造成无“禅”、“讲”传承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p#分页标题#e#
二、显密僧侣之间的差异
元初段氏失政未久,当地在宗教方面还不可能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段氏更是在洱海区域保住了高度自治的地位,与前代相比,各方面制度变化可能不大,因此基本可以依据元代的史料粗略分析大理国佛教信仰的情况。“(大理)佛教甚盛,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1](P127),在一个佛教兴盛的地区,民众生活自然也能体现佛教徒的某些行为特点,以至于“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让我们继续对这则史料进行分析:虽然对于“荤”的界定在不同佛学体系中有差异,如果普通民众都不茹荤腥,则其崇奉的僧侣必然持戒更严,但根据下文将引用的材料,当地似乎并非所有的僧侣都“戒行精严”。明代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云南府•风俗》对僧侣有如下记载:“居山寺者曰净戒,居家室者曰阿吒力。”[8](P4)因为本条记录是因循“旧志书云”,并非只是明朝才出现的情况,由此笔者认为当地在明代以前“僧有二种”。根据他们修行的场所不同,笔者对僧侣群体进行了分类:结合元初的记录“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皆有得道者居之”,远离尘世生活是显教僧侣的一个重要特点,上文引述的这种情况的存在可以间接证明显教的兴盛。作者另外提到了“家无贫富,皆有佛堂”,现在藏区的佛堂往往是出家僧回家后的居所,在古代的大理,这些佛堂可能也会发挥同样的作用,而在家修行者在家庭内应该主要就在住宅附属的佛堂内进行修行活动。修行场所的差别使两类群体看来泾渭分明。从戒律角度看,(得道者)“非师僧之比”,他们“戒行精严,日中一食,所诵经律,一如中国”[9](P136)。由此看来,遵从汉地经律的僧侣和不重经律讲究秘密传承的密僧之间的区别也十分显著。因为两者在修行方式和修行场所上的巨大差异,当地人自觉地将他们进行了区分。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也看到了这种差别,但总是默认“得道者”与“师僧”同为密宗僧侣。无论如何,与其认为存在明显区别的这两种僧人是密宗内部的分化,还不如说他们是分别信仰汉传佛教显宗和当地密宗的信徒。综合各种文献资料的说法,我们可以以下表进一步说明两者的差异。
三、宗教实践中的显密结合
大理国时代留存的文物在数量上毕竟要多于南诏,我们可以借助这些实物对当时该地的信仰状况做进一步的分析。《文殊问疾维摩诘》是大理国时期的珍宝《张胜温画卷》上一个重点表现的场面,还有现存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的作为大理国赠给宋朝官方礼物的金粉书写的《维摩诘经》。此外,在剑川石宝山石窟中,民间俗称“愁面观音”的石像刻画的正是作病态的维摩诘菩萨。以上3例文物的存在说明与此相关的思想在大理很流行。众所周知,《维摩经》因为暗示在家修行可以获得高级果位,因此在唐宋时受到大批在家学佛的居士们的追捧。同理,它在大理历史上广泛传播说明当地在家修行信徒的数量可能十分巨大。笔者同时还注意到监造制经的是“佛顶寺主僧尹运富”,该僧并不以释为姓,可能正是在家修行的僧人,作为制作国礼的监督者,其地位和学识显然并不会低。而在《张胜温画卷》上有大理国“盛德五年”的题注,题注人为释妙光,此人可能是出家持戒的僧人,能目睹这副完成仅数年的国宝级图卷并在其上题注,其地位想来也非比寻常。存世图经上的两种签名可以提供直接的证据说明大理国时期是显密并重的,佛教传承存在两个各有侧重的系统。
尽管如此,笔者也不认为显密之间存在壁垒分明的界限,显密同属佛教,它们共同组成大理整体的佛教信仰体系。从中国古代的经验来看,教门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一身同时继承两家甚至更多家教法的僧侣大有人在。自古法门相通,它们绝非互不交涉,大理显密兼修者应该不在少数,因为材料有限,我们只能在记载墓主行状的古代墓碑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出土于大理五华楼遗址,作于元至正二十五年的《故神功梵德大阿左梨赵道宗墓碑》中记载,有一位曾为僧官的大阿左梨“退□辞荣,山居乐□,受具戒而修头?行,释名圆悟。二十九年三月,化寂于大悲兰若之庵”[10](P123),此人似乎是由密入显,最后归为净戒一类。碑文随即显示其后裔“造佛宇于家园,经像交辉”,而且“终于家堂”,显然仍是在家修行的师僧之属。个人修行可能由密入显,同一家庭内修行显密也可以互不妨碍。这种情况说明显密之间的界限可能很早就被打破,所以有很多僧侣作为政府册封的密宗大师,同时也正式剃发出家并拥有释名。
在凤仪北汤天发现的古老写经《护国司南抄》完成于大长和国安国六年,重抄于大理国保安八年,除引用了多种佛经及其注疏外,儒、道两家著述的传统文献也被大量征引。可见博学的作者不仅熟悉佛家内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掌握也十分精熟。法名玄鉴的作者身为“内供奉僧、崇圣寺主”,同时也是国家的“义学教主”,一般说来,义学僧是唐时设立的专门精研佛教汉文经典的僧人,玄鉴大和尚手下极可能集中了一大批义学僧人,崇圣寺可能也是当时汉语佛学经典研究的一个中心,而并非如近代的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一所纯粹的密宗寺院。居于其内的大德高僧除了有丰富的佛学知识外,对汉文献的其他内容可能也是触类旁通。作为一个知识群体,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僧人们学识渊博,不仅长于密术,而且精通显宗各派的经典,儒道两家的相关著述和思想他们也很熟悉,所以并不能将其视为单一的密宗信仰的实践者,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显然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与显宗僧团成员一起生活、互相辩难交流的学习方式不同,密宗坚持秘密传承,僧人的修行也以个体活动为主。印度、中原之所以有大规模的密宗寺院出现是因为其传承多由僧团形式进行,僧团规模不断扩大所致。而大理密宗在家修行和父子传承的双重特征决定社会不需动用太多财富建立寺院,除修持的坛场外,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密宗寺院应该多是礼仪性的,一般只是作为王国重大宗教仪式活动的举办地,所以在数量上应该不会太多。至于大理地区流传的《南诏野史》、《白古通记》等野史中记载的大规模建寺、铸佛活动,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针对民间小型修行场所而言的,这些举动可以视为政府对他们的资助,而且受惠的显然也包括显宗寺院。#p#分页标题#e#
四、僧侣的社会角色与南诏大理国佛教信仰的特征
一般认为,大理阿吒力教实行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父子世代宗业相承的血亲继嗣方法为主的传承方式”[11](P62~P63),但这在密宗的传承中并非偶见。在信仰密宗的藏区,其成熟的僧伽制度一直要到格鲁派出现后才最终确立,在此之前,佛教的传播主要也是靠父子、兄弟、叔侄等血缘关系维系。西藏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著名的弘法家族,尤其是在9世纪朗达玛灭佛后,佛教公开传播被禁止,密宗修法主要由家族世代相传。迟至元代,地位显赫的萨迦派五祖和四大拉章均属血缘继承,“法位以家族相传的形式继任,其政教两权都集中在昆氏家族手中”[12](P371)。大理密宗与西藏特定时间段内的传承方式没有本质区别。南诏大理国时期,一些佛教世家和王权之间发展出密切的联盟关系,如凤仪董家连续很多代都有享受王国封赐的杰出僧人。
密教传统上就和统治核心关系密切,它的兴盛多与皇室和贵族阶层的崇信有关。密宗最初多以秘密仪式和符咒为统治者祈福禳灾,很容易被视为贵族的禁脔。唐、宋、辽、金以及吐蕃、南诏、大理的统治者都曾不同程度上崇信密宗,从而使这种信仰最初为上层阶级把持,一般的民众可能无法浸润福泽。比如,在唐代密宗流行的时期,《仁王经》被认为有助于国家军事上的成功以及朝廷统治的稳定而多被信奉,在大理发现的写经《护国司南抄》就是对《仁王经注疏》的再诠释,《仁王经》的流传显示大理国时期的阿吒力僧人也在积极为王室事业服务,而密宗僧人直接出现在战场以襄助战事的做法更是常见。
宋朝官方似乎对与大理的联系和贸易不是特别积极,官方纪录下来的两地之间的交流并不多,但在有限的几种文献上大理国人到广西市马买书的事例屡次被提及,这批书目涉及儒、医、佛三家,而以儒家书籍最多,如《春秋后语》、《五经广注》等[13](P257)。应该说,两地的交往以民间交流为主,而且应该比记载的更普遍,只不过以重大历史事件和官方活动为纲目的正史在这方面的记载往往有所欠缺。这一时期虽然东南亚文化在大理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但中原文化的影响显然也并未中断。很多古籍资料证明至迟在大理国时期,当地的佛教徒普遍学习儒学经典。“师僧有妻子,然往往读儒书”,不断从中原输入的典籍,必然要对当地的知识界产生影响。因为缺少士人阶层,僧侣可能是这些书籍主要的阅读者和相关知识的传播者,虽然不一定每一位师僧都要“读儒书”,但作为当地的知识分子并参与政事的一部分阿吒力确实可能需要借鉴儒家的智慧。“释儒”或“儒释”称谓在大理的出现无疑也表明僧侣的另一重要角色,中原典籍在大理的传播使他们接近于汉地的居士学佛和兼通儒学的僧侣。“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辈”[1](P127~128),这些阿吒力僧人身上带有明显的知识精英色彩,这一情形的出现实际也显示密宗仪式的重要性总体有所减弱,而与显宗有关的读写技能成为不可或缺的训练。当然,此时他们的知识范围已经逐渐突破了佛教领域的局限。
一般说来,僧侣在南诏大理国时期都保持着很高的政治地位,除了为王室提供宗教服务,他们有时也直接参加王国的政治和军事决策。不过,随着职业僧侣数量的扩大,佛教的民间转向也在所难免。除了少数人在一定时段内因袭国师尊号或者考取政府职位外,很多阿吒力僧直接为民众生活服务。于是,大理历史上的阿吒力教逐渐演变为一种佛教的民间形式,至少将其侧重点转向民间的仪式性活动,比如超荐亡灵等。方国瑜先生曾推测古籍中“师僧”提法的来源“:盖阿吒力接缘应赴,故以师僧呼之。”[14](P530)另一方面,号称“释儒”或者“儒释”的阿吒力并非只是仪式专家,显宗的学习使其同时拥有书写和阅读的特殊技能,僧侣的民间转向使其能够作为知识的掌握者继续在民众中发挥影响,直到明代,他们仍然被延请作为民间碑文的撰写者,受尊重的宗教专家们逐渐也会将其掌握的包括儒家在内的知识带入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