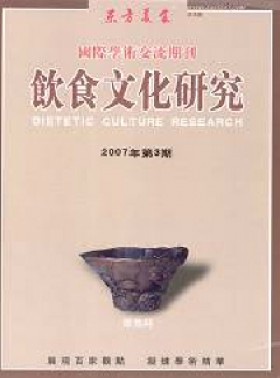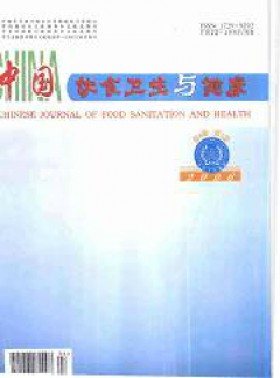作者:张敦福 单位: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地被称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除了马克思对“社会学家”的标签不感兴趣外,他们更极少被成为人类学家。然而,马克思与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通信,马克思描述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形态的《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都进入过人类学文献。《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实际上是建立在马克思有关笔记的基础之上———是马克思计划写而未能去写的著作,事实上他的逝世使他壮志难酬;马克思对人类学的关注,成为他学术研究的中心,直到他生命的终结①。人类学历史上,怀特(Leslie White)写了一系列文章,与博厄斯为首的历史特殊主义论争,认为社会演化有其普遍规律。怀特还复活了摩尔根的进化论类型学。尽管怀特没有提到马克思的名字,但一般认为,怀特理论的调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强调劳动力和生产资源,怀特则以对能量的控制取而代之,认为后者是人类演化的决定力量②。人类学家阅读和讨论马克思、恩格斯似乎言之有据。国内学者对这一点也有所认识。陈庆德指出,马克思理论体系不仅对经济人类学有认识论上的启示意义,而且其经济分析也直接为经济人类学开辟了学科道路③。陈建宪也注意到,马克思放弃《资本论》的写作,转而阅读大量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从政治经济学转向了文化人类学研究④。罗力群也对文化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理论原则做了缜密梳理⑤。通过回顾和检视近百年来的相关重要文献,笔者试图突显和强化以下看法:“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不认为自己是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他们转向人类学和历史,与其说是要关心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本身,不如说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他们往人类学那里绕一下弯,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些概念的灵活性、暂时性和相对性。”①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认识论是人类学唯物主义传统的理论源泉,尤其是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知识与智力的来源,从而成就了在人类饮食研究领域别具一格的研究策略。
一、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立场到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策略
哈里斯研究工作的理论前提是,“人类生活是对其生存实际困境和难题的反应”;他也名副其实地宣称,“尽管不是我发明创造了‘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但确是我给这个概念赋予了意义”②。他认为,范式(paradigm)是一个容易引起分歧的概念,他主张以研究策略(re-search strategy)取而代之,而这种研究策略有其唯物主义依据。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着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③如果说文化唯物主义有一套相互关联的理论原则,哈里斯认为,马克思的这段话富有先见地阐明了这些原则的核心;这一伟大原则是人类知识史上的一个重大进展,其意义和价值与同时代华莱士和达尔文表述的自然选择原理不相上下。但从现代人类学的角度看,“生产方式”用语具有认识论上的模糊性,对“再生产方式”的疏忽,以及缺乏对主位与客位、行为与思想的区分,都极需要重新给予阐明④。对人口再生产方式中技术和手段的忽略,“未能赋予人口控制的技术发展在文化演化中以中心作用,极大地伤害了经典和新潮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理论的可信性”⑤。对文化唯物主义研究策略的理论阐明始于客位、主位之分。在哈里斯看来,每一社会必须解决生产问题———在行为上满足最低限度的生计需要;因此必须有一种客位(etic)行为的生产方式。
其次,每一社会必须在行为上解决再生产问题———避免人口出现破坏性的增长或减少,因此必须有一种客位行为的再生产方式。再其次,每个社会必须处理好一个必要问题,即保证组成社会的各个团体之间、与其他社会之间安全、有序的行为关系……行为的上层建筑是这种普遍反复出现的客位方面的合适标志⑥。主要的客位行为包括以下类别:(1)生产方式:用于扩大或限制基本生计生产的技能和实践活动,特别是食物和其他形式的能的生产,假使特定的技能与特定的居住地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限制和机会。具体包括生计技能,技术与环境的关系,生态系统,工作模式。(2)再生产方式:用于扩大、限制或保持人口数量的技能和实践活动。具体包括人口统计及其模式的医学控制,配偶方式,生育力、出生率、死亡率,育婴,避孕、堕胎、溺婴。(3)家庭经济:在宿营地、住宅和公寓或其他家庭住地内组织的基本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再生产。包括家庭结构、家庭分工、家庭社会化、家庭纪律与性角色等⑦。其中,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归入基础结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归入结构。(4)政治经济:在群体、村落、酋帮、国家之间的生产、交换、消费和再生产。艺术、音乐、舞蹈、文学、仪式、户外活动、游戏、业余爱好等被列入行为的上层建筑。
这样便得到了基础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的三重方案。与这些客位行为大致相应的一套思想则分别是:(1)生计知识、民族动物学与植物学;(2)亲属关系、种族关系;(3)象征、神话、审美与哲学等①。文化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原则的理论表述可以概括为:客位行为的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盖然地决定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又盖然地决定行为和思想的主位(emic)上层建筑。可以简洁地称之为基础结构决定论原则②。把再生产方式标入基础结构,就能阐明一套有创见的、首尾一致的可检验的重要理论③。文化唯物主义策略还基于扎实的实证研究。自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哈里斯就“对主张多实地调查、少闭门造车的研究方法极感兴趣”④。他曾在巴西、莫桑比克、印度、厄瓜多尔和纽约等地从事田野工作,以充分的经验资料和社会事实为依据,证实了他的发现。哈里斯从人口、技术、环境、生育控制等因素着手,检视了采集狩猎社会前后的社会变迁,其严密的论证和有力的事实证实了马克思的以下两个著名论断⑤:“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⑦哈里斯反对那种把文化视为纯粹主位现象和个体精神、思想活动的看法。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哈里斯认为这是一套研究思想、上层建筑的原理,虽然是西欧影响最大的人类学研究策略,但它是反实证的、反辩证的、唯心的和无视历史的⑧。包括本尼迪克特在内的心理人类学家先驱们提出,人格构型是社会生活中稳定的、经久不变的核心。而文化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则是,基础结构和结构的根本改变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导致人格构型的彻底逆转⑨。认知主义则在主位规则的知识基础上预测客位行为瑏?瑠,而文化唯物主义的选择也比弗洛伊德的选择更为可取?瑏瑡。重要的是,哈里斯通过在各地开展的扎实的田野工作,证实了文化唯物主义策略的说服力,展示了其在多种研究策略中的优势。#p#分页标题#e#
二、饮食的奇风异俗:猪肉、昆虫及其他
人类社会的饮食现象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奇特习俗和传统。Robert Rowie喜欢收集此类资料,并称之为人类饮食习惯中“变化无常的非理性事件”。饮食人类学展示给人们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民族中,吃什么,不吃什么,怎么吃,人们饮食偏好背后的规范和机制。比如,存在这些饮食禁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不吃猪肉,印度教不吃牛肉,美国人不吃马肉、山羊肉和狗肉;也有看似怪异的饮食偏好,马肉是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的美味,大多数地中海沿岸居民喜欢吃山羊肉,蛆虫和蚱蜢在更多的社会里被当做美食①。问题是,这些饮食的背后有多少营养学的因素?多少遗传学的因素?多少消化生理学的因素?多少环境生态学的因素?多少区域人口学的因素?多少历史文化传统的因素?这些因素又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面对差异迥然的饮食习俗,哈里斯赞同“谈到口味无争辩”的文化相对论主张,不应当责难或讥笑不同的饮食习惯和风俗。但依然留下许多值得讨论和深思的问题。哈里斯关心的问题是,人类的饮食方式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差异?人类学家能否解释为什么在这种文化而不是别的文化中发现了某些食物的禁忌和偏爱?
哈里斯指出,人类学存在三种解读方法:文化唯心主义、折中主义和唯物主义。有学者主张,不应当到食物的项目性质中去寻找,而是到人们的基本思维模式中寻找。文化唯心主义者,如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自然物种被选择,不是因为它们是“好吃的”,而是因为它们是“好想的”,另外一些食物则是“不好想的”②。“在道格拉斯看来,人类学家研究饮食方式的主要任务是解码它们所包含的神秘信息。对古代以色列人的猪禁忌,不必研究自然史、考古学、生态学、猪的营养价值和生产猪的经济学。折中主义表面上站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立场之间,实际上有这样的强烈倾向:对具体的饮食方式个案做唯心主义的解释。”③。法国人类学家Fischler表达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当我们观察与人类饮食习惯相关的象征和文化表现时,只能接受如下事实:其持久性和顽固性是任意的原因造成,其中大部分很难讲出什么道理来。”④这种论点则显然流于不可知论。哈里斯的视野总是同更加广阔的经济、人口、环境、生态、地理等因素联系在一起,揭示了饮食禁忌与偏好的“文化之谜”,认为“食物是否有益于思考取决于它们有利于吃或不利于吃。食物必先填饱群体的肚子,然后才充实其精神”⑤。
犹太教《旧约》借上帝之口规定不可吃猪肉。1859年医学发现旋毛病与烹煮不够的猪肉之间的临床关联,被神学家用来为《旧约》食物禁忌辩护。哈里斯把禁忌产生和发生作用的生态环境、自然地理状况作为考察的重点,得出这样的结论:中东地区的气候和生态环境不适合家猪饲养而有利于反刍动物(牛、羊)饲养,古代以色列人迫于成本和收益比较的生存压力和人口压力,不得不放弃曾有的养猪生产。现代的欧美人不吃昆虫,认为它们有细菌、肮脏、令人生厌。事实上,人类的祖先是吃昆虫的。中世纪以来,欧洲人也吃昆虫。哈里斯指出,从营养学的角度说,昆虫几乎和红肉、家禽一样有营养。昆虫携带的细菌可以通过烹煮杀死。回答现代欧美人为什么不吃昆虫的问题,必须检验吃昆虫或其他小东西的比较成本和效益。他以生态学的最优化觅食理论预测:狩猎者和采集者将只寻觅和收获相对于“处置时间”(追寻、杀死、运载、烹煮等)能得到最多卡路里回报的物种;只要新项目增加了觅食活动的总效率,该项目就会被添加到他们的食谱中。哈里斯说,欧美人有足够的牛肉、羊肉、禽类和鱼肉,连马肉都看不上,怎么会需要昆虫呢?
三、印度圣牛之谜
印度拥有十亿人口,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和热量来维系如此众多民众的生命和健康。因为食物不足,印度人口曾普遍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①。但同时,印度大量的活牛或将死的牛不被人宰杀为食。吃惯了牛肉的欧美人可能大惑不解,因为看似非常不合理性的情景确实存在:印度人禁止宰杀牛作食物吃掉。国家政策的指导性条文第48款规定:“禁止屠杀母牛和牛犊,以及其他产奶和驼物的动物。”印度有两个邦通过了“牛保护”法案。因为没有人宰杀牛肉吃,印度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家畜,即大约1亿8千万头牛;也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游走于田野、公路、街道上的老弱病残之牛②。
印度人为何如此保护牛、回避吃牛肉、饲养大量无用的家畜?一个重要的解释把它归结为宗教狂热:这里的主流宗教印度教的核心教义是牛崇拜和牛保护。印度人崇拜他们的母牛(和公牛)为神灵,在家中饲养它们,给它们起名字,同它们说话,用花环和绶带装饰它们,容许它们在繁忙的大马路上信步游走③。母牛还成为政治的象征,母牛和牛犊的图画曾被国大党当作国家的标志④。但是,无论是宗教还是政治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杀牛和食用牛肉成为首选的象征?为什么是牛,而不是猪、马、骆驼或别的动物?哈里斯指出:“我不怀疑神圣母牛的象征性力量。我所怀疑的是,在一种特殊的动物种类和一种特殊的肉类的象征力量之认定,是出于任意的、随机的精神选择,而不是出于一种确定的实际限制。”⑤通过对印度宗教争斗、农民生活、人口变迁等方面历史的细致考察,哈里斯发现:印度农业体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为了吃肉而屠杀了在能量和营养上更有用的动物,而禁止杀、吃牛肉的宗教戒律则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圣牛(sacred cow)”的宗教及其信仰和观念毕竟是一定基础结构(人口压力、自然环境压力和技术发展水平等)之上的实现最优化要求而产生、兴盛的。由于这种基于历史资料的研究,哈里斯也显现出浓厚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旨趣。正如罗力群所说,对圣牛个案的分析,颇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味道,校正了“好吃”的偏颇、谬误和浅薄⑥。
具体而言,哈里斯所看到的,婆罗门信徒们选择了一种更富于生产力的农耕体制:强壮有力、肩背上有瘤的大牛能够在炎热、干旱和其他不利条件下充当拉犁动物,而它们消耗的饲料很少。由于这些牛很少(像欧美那样)在人工种植的草场上放牧,也不在人类生产粮食的田地中放牧,所以,几乎不可能在资源方面与人形成竞争。这些家畜在工作之前处于半饥饿状态,在犁地的间歇期吃植物的主茎、谷壳、树叶和家庭的剩饭剩菜。耕作期间,它们吃人类吃不动的棉花籽儿、黄豆和椰子的残渣压制的油饼。在印度的大多数地区,用家畜从事粮食生产,每单位的成本收益要比使用(像美国情境下)拖拉机更高一些。它们可以在抗病力强、耐力佳的状态下工作12年之久。牛粪是印度最大的有机肥料,也是清洁、可靠、无气味的热源,缺乏木质和化石燃料的千万家庭就靠它烧火做饭。母牛比公牛还有清道夫的优势:麦秆、谷壳、路边杂草、树叶和人类不能消化的其他东西都被它吃掉,更不用说它的奶是有价值的副产品了⑦。总之,活牛在印度人的生态环境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母牛和公牛是一种成本很低的耕作工具,可以在很多方面替代拖拉机;牛的粪便既可以当作肥料,也可以作燃料;印度的牛以草为饲料,它们不像在美国那样与人争夺粮食,这样它们提供的肥料和燃料就是免费的,而美国则不缺乏木材、石油和煤炭。更为重要的是,只需少量饲料和水,牛就能够在印度那样燥热的气候条件下存活很长时间。如果为了饥饿的缘故就杀牛,在印度人看来是很不合算、不应该的,因此自然产生了一种“爱牛情结”。总之,印度教的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服从于由生态、政治、经济和其他的行为和客位的条件所加的种种限制①。#p#分页标题#e#
四、结语与讨论:饮食领域的变迁与挑战
作为饮食研究的策略之一,文化唯物主义并不讳言自己的缺陷。哈里斯坦诚,文化唯物主义关于新石器生产方式起源的理论仍然是尝试性的、不完善的。例如,结构主义在这个题目上实际上没什么可说的,而辩证唯物主义则受害于其“内部矛盾”概念,不亚于文化唯心主义对伟大思想的依赖。马克思提出的“生产上的束缚”,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并没有阐明狩猎采集者的转变。自然和技术,而不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狩猎采集者的生产能力②。在布洛克看来,其一,哈里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和内容;其二,哈里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持有异议,这点令人困惑不解③。结果,人们只能认为,哈里斯的理论根本谈不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④。也就是说,文化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有争议的。但在笔者看来,正如上文展现出来的,哈里斯正是有鉴别、有批评地继承和发展了唯物主义,而不是机械地照搬和模仿。这种创造性开拓,正是学术进步的源泉。如同《马克思的外套》一文结语所感慨的,“事物就是人们用来建构生活的用品,如衣服、寝具、家具等补给品,没有它们就等于毁灭自我。我们何德何能可以藐视物品?谁又有本事藐视得起物品?”⑤回顾和环顾饮食习俗变迁的历史和当今实际,我们仍然很容易看到,活生生的社会事实是如何支持文化唯物主义的研究策略的。正如已故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所确信的:“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⑥;中国人的“饭(grain foods)”和“菜(dishes)”之分,就与其农业生产、生活传统密切相关。安德森在《中国食物》开篇就谈到,中国五大区域(华北、东北、华南、西藏、中东部)在饮食内容、方法乃至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就受制于土壤、气候、地理环境等难以改变的基础结构⑦。湘菜、鲁菜、川菜、淮扬菜、东北菜等菜系的分野背后,也有着自然环境因素的力量。韩国人在衣着饮食方面崇尚身土不二,绝非后天观念使然。在这一点上,观点各异的食物研究者们也颇有共识:“我们是什么人取决于我们选择什么食物。”⑧饮食研究中文化唯物主义与其他研究视角之间的分野绝非就此消失。哈里斯明确地坚持认为,人类学是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科学就必须基于一般规律,而一般规律来自基础结构。但人类学也有其他发展方向。在普里查德看来,人类学是门人文学科,而不是社会科学。格尔茨则提出,人类学不是实验科学,而是探寻和解释意义⑨。不是所有的学者对探寻一般规律感兴趣,饮食人类学研究有着多种多样的研究策略、研究视角、兴趣领域和发展方向。笔者在华琛的课堂上,极少听到哈里斯的大名①。华琛注意到,当今的饮食领域,出现了许多有待研究的新议题:比如1990年代前吃肥肉,1990年代后瘦肉取代了肥肉的地位,蔬菜取代了肉食的地位;30多年前,人们把发胖看作是展示生活富裕、身体健康、家境富有的标志,消瘦被看作是倒霉、疾病和早死的征象,唯恐避之不及②。进入新世纪后,肥胖成为一种病症,减肥成为时尚。我们也看到,麦当劳、肯德基、可口可乐等世界大牌食品几乎不受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因素的制约而向全球扩张。而且,在一个世俗化的、祛魅的当下时代,即便是有些本土特色的食品,也被“文化人”建构出来,文化经济(cul-trual economy)由此成为当前经济活动的重要景观。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发生的一个转向,是关注“文化中介者”在各种各样消费品形象、消费经验、消费认同和生活风格形塑过程中的作用和机制③。像葡萄酒那样的商品,酿造人、营销人员、公关人员、调酒师、分销商和撰稿人,在酒的出处(provenance)问题上、进而在酒的消费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建构作用④。在中国方兴未艾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中,或真或假的“起源故事”、“古代传说”在地方小吃、地方酒、土特产品的塑造和营销中,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日益凸显。无论我们秉持什么观点,食物是探知分析文化特性的一个重要视角⑤。在这个领域里,有待我们探寻的问题远比我们已经获知的知识和观点要多得多。作为一种研究策略,文化唯物主义依然具有科学认识价值,同时也面临着全球范围内饮食变迁新景观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