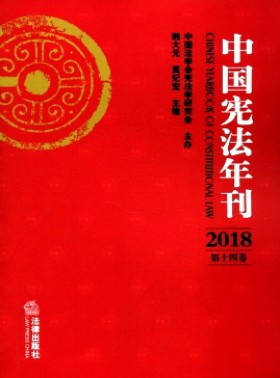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宪法的定义思考,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宪法究竟是什么?对此百家争鸣的局面有利于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提供多样化的丰富知识; 但没有一个较为共识的界定,缺乏较为公共的交流地基与平台也造成了对有效沟通的阻碍,使大量资源在非针对性争吵中无谓消耗。宪法在形式与实质之间的漂动无疑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形式宪法与实质宪法的划分是学界的流行手法,其中形式的宪法是近现代的产物,或者说近现代特别是1787年之后才获得公认的确定涵义,它是一个庄严的文件,有“宪法”或者类似的名称,一般还都有严格的修改程序,并宣称自己的最高法律地位(不管这种地位是真的、假的或者真到什么程度)。这些很少有人质疑,可是什么是实质的宪法呢?似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的角度、立场、方法、视野皆导致不同的结论,而这些实质宪法的界定又必然要和形式宪法协调彼此关系,因而又横生枝节。宪法在实质与形式之间徘徊踌躇。 本文试图从纯粹法学、政治法学、纯粹政治学三个角度来探讨实质宪法的界定及其与形式宪法的关系。 一、纯粹法学宪法 纯粹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凯尔森力图去除法学中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判断,把法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就好象法律是在一个封闭的容器中一般”。 [1](P136)故而他的目的是要构建一个自足的规范等级体系,其中每个规范效力的理由都来源于更高的规范,根据更高规范而创制,而整个体系归结为一个原点,即自名的基础规范。他的宪法概念是从这个自足的规范等级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过程来界定的,下级规范的创制同时又是上级规范的适用。基础规范不是由造法机关按法律程序创造的,因为在它之前根本没有法律,它是一个预设为有效的规范:赋予宪法“缔造者”及宪法权威的规范,而这种权威只按照实效性原则授予。于是,宪法处于法律体系的第二个位阶或步骤或阶段上,通过与一般规范的对比而获得自己的含义,即宪法(实质的)是“由调整一般法律规范的创造,尤其是创造法律的那些规则所构成。”[2](P196)它规范一般规范的创造机关、程序乃至部分决定未来一般规范的内容,包括消极禁止和积极要求。相应地,一般规范决定法律适用的机关、程序和创造个别规范的行为内容。 这样就可以发现实质宪法是每个法律秩序都必不可少的主要因素和必经阶段。每个国家即使是专制国家都有宪法。而形式宪法则不是必不可少的,许多时期、许多国家都没有。即使在有形式宪法的地方,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形式宪法仅仅意味着一种特殊形式、特殊程序(有时程序也不特殊),通过这种程序,任何东西,包括内容上与实质宪法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东西都可装进这种形式,然后美其名曰:这是宪法。同时,在很多情况下,实质宪法规范都遗漏在形式宪法之外。下面具体谈一些特殊情况: (1)习惯法与判例法 习惯法与判例法如同立法一样都是一般规范,它们都决定个别规范的创制,因而习惯法、判例法的创制必须是一项宪法制度,是由实质宪法所规范的,这一点形式宪法当然可以明文规定,但目前绝大多数情况下,关于习惯法、判例法创制的宪法规范都不在形式宪法之中,也就是说它们本身作为习惯法而存在(宪法层面的习惯法)。另外,某些判例法本身对立法具有拘束力,即宪法规范也可以以习判例法形式存在(宪法层面的判例法)。 (2)直接适用的宪法条文 有的宪法条文是可以为行政、司法机关直接适用的,如美国宪法第七修正案“根据普通法进行的诉讼,如果争执价额超过20美元,由陪审团审理的权利应予保护。”有些国家宪法明确规定自己的直接适用性,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国内学者如王磊等不遗余力要求宪法司法化(即直接适用),但按凯尔森的概念,实质宪法规范不可能直接创造个别规范,必须有一般规范为中介,也就是说宪法规范只能立法适用,不能行政、司法适用,那些可以直接适用的宪法条文规定并不是宪法规范,而是特殊形式下的一般规范。但凯尔森也承认“它们只有在也决定对今后法律某种内容的立法这一范围内,才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宪法。”[3](P291)这其实导出了双重性问题,例如美国宪法第三修正案:“未经宅主允许,平时不得在任何住宅驻扎军队。除以法律规定的方式外,战时也不得驻扎。”可以分解为“平时,法律不得授权行政机关在任何住宅驻军,战时可以。 未经宅主允许,行政机关不得在任何住宅驻扎军队。战时法律另有规定除外。”前一句作为对立法内容的要求,体现了对一般规范创制的约束,防止立法的滥用与懈怠;后一句则是约束行政的一般规范,因此本条款可以说既是宪法规范又是一般规范,具有双重属性。 (3)国家机关的创制 宪法规范只调整立法机关的组织和程序,而行政、司法机关的组织和程序由一般规范规定,但许多宪法条文规定了许多其他机关的创制,如何定性?应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其他机关作为立法机关。如总统颁布法律,故而是法律颁布机关;内阁提出法律案,故而是法律提案机关;宪法委员会、宪法法院或有权普通法院在事前或事后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撤消违反宪法的法律法案,可以说是消极立法机关。所以这些规定都是宪法规范。第二,其他机关不作为立法机关时,如乡镇政府,则是一般规范。但再次考虑双重属性问题时,又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相对于决定下级一般规范(如组织法)的内容时,它是宪法规范,而无须中介直接构建个别规范创制机关时,它就是一般规范。 (4)层级立法相对于早期立法局限于议会法律那种简单形式而言,目前立法层级日益庞大,比如中国构成了“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的多级立法层次,这种情况下如何定性?假如:《宪法》规定:“规章可制定罚款,其数额由法律限定”;《立法法》规定:“规章可制定罚款,其数额不超过2000元,法规可进一步限定”;《条例》规定:“规章可制定罚款,其数额不超过1500元”;《规章》规定:“随地吐痰,罚款500-1000元;情节严重的罚款1000-1500元”。#p#分页标题#e# 在此情形下,由于仅有规章可以创制个别规范,因而只有规章是一般规范,其上三级规定都是宪法规范,这样宪法规范的内容就出现了多个层次。而且如果上三级规定在决定下级规范同时又能直接适用,则根据双重属性原理,它们都是宪法规范(相对于下级一般规范),又是一般规范(相对于个别规范)。 凯尔森的实质宪法似乎可以大概地称为立法法,他根据法律运行阶段的划分标准独具特色,同时其对形式宪法和实质宪法的区分给我们有益的启示。但他的实质宪法有泛庞大化的倾向,因为立法者选举的细节、各种提案主体的组织和程序、议会组织的细节、多层级立法及双重属性问题使整个实质宪法范畴过于庞大,似乎不得不区分其中的高级部分(如宪法作为宪法)与低级部分(如条例作为宪法)、核心部分(如议会三读程序框架)与外围部分(如议会委员会小组会议发言顺序)、单纯部分(只能作为宪法)与重叠部分(同时又是一般规范)。 二、政治法学宪法 如果说凯尔森基于自己的界定明确指出实质宪法与形式宪法的区分,并指出形式宪法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话,作为凯尔森主要论战对手的政治法学①代表人物的施米特则基于自己的界定对形式主义宪法的弊端提出了更为尖锐的批评。 施米特首先区分了宪法与宪法律、绝对意义的宪法和相对意义的宪法,政治统一体是预定存在的,而一切存在都有一道被给定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的整体状态就是绝对意义的宪法,但这时未必通过有意识的行为来自我决定这种政治存在的形式。当国家-民族已经觉醒,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行动能力和主体身份,希望决定自己的命运、维护自己的存在,就有意识地通过一次性决断,自己为自己决定整体上政治统一体的类型和形式,这也是绝对意义的宪法,是施米特重点论述的对象,也称为实定的宪法(实质宪法);形式宪法被施米特称为宪法律。政治决断决不是法律,也不是宣言,而是更高的、一切法律(包括宪法律)的基础。宪法律是为了实施宪法(根本政治决断)而制定的,借助其易标识性、严格程序及更大稳定性,使宪法能够得到外在化、明确化,并防止变动不居的议会简单多数的影响。但制定者的理性有限,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情况下,各政党基于政治利益上的考量与各种偶然事件,使众多宪法律缺乏系统脉络,相互之间亦多有矛盾、冲突、不一致,而且大量非根本的东西都塞进宪法律之中。并且正是宪法律的这种可证实的标记性使之抢占了人们的观念领地、喧宾夺主,使人们混淆了宪法与宪法律的区别,突显了各个条款间形式上的相同,使内容实质上的区别荡然无存,也就是说“真正的根本规定被强行降到宪法律细则水平上”。 [4](P16)统一的根本决断被分解为大量的混乱的宪法律,被相对化了而这些宪法律又与繁难的修改程序画上等号,“于是宪法不过是一种权益之计,实际上只是一部空白法律,必须不时地按宪法修改的规定来加以填充。”[5](P23)这样就使形式掩盖了内容,程序掩盖了本质,为了实施宪法而制定的宪法律反而破坏了宪法的统一。施米特的批判并未到此止步,他进一步指出,宪法律顶替了宪法的位置,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成了宣誓效忠和叛逆罪保护的对象,这样一个个单独的宪法律束缚了维护宪法根本决断的非常措施的手脚,真真地给了敌人在宪法律的掩护之下攻击宪法的可乘之机,对国家的自我防卫构成障碍。于是宪法不仅被宪法律分散化,而且为其所累所害、乃至降到其下。其结果是“为了捍卫形式和相对意义上的宪法而不去捍卫实定和实质意义上的宪法”。 [6](P126)施米特谈的问题十分类似“宪法精神—宪法原则—宪法规则”的关系问题,没有宪法精神的统领,成百的宪法规范都是毫无内在逻辑的一样表象,单单把握宪法规范而不领悟宪法精神无疑是本末倒置,常常会干出以护宪之名行违宪之事的闹剧。 比较一下施米特和凯尔森思想的对立也许有利于理解各自的实质宪法:首先在出发点上,主体存在:规范存在。施米特预设了政治统一体的先在性,一个具有政治统一性的民族的具体存在优先于一切规范,国家—民族统一体存在着,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存在提供根据,制宪权本身永远不能凭借宪法律来设立,民族始终是一切政治事件的根源,是常新的、能动的力量。而凯尔森认为国家只是国内法律秩序的拟人化,国家和法律是两个对立实体的二元论是站不住脚的,若干人之所以组成一个共同体,只是一个规范性秩序调整着他们的相互行为,共同体不过是法律秩序的同义语,所以只能预设规范存在,而不能预设主体先在。 其次在规范效力来源上,强调主体意志的能动性:强调规范系统的完整性。施米特认为规范本身不能为任何事情提供理由,规范的效力凭借的是一种实在的意志,一项规范从来不能自己把自己制定出来,统一体和国家秩序在于国家—民族的政治存在,而不在于规范。凯尔森认为断言所有人民具有共同的意志是明显的虚构,只是形象化和人格化的说法,具有意识形态的目的。规范效力的理由始终是另一个规范,同一法律秩序中的规范效力全都可追述到第一个宪法。说人创造法律其实是规范以人作为机关创造了下位规范。第三是国家主权观:国际一元论。施米特认为主权概念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国家要维持其存在就必须有自决权,能自己为自己制宪,人民制宪权的有效性根据仅仅在于其政治存在,一个国家的人民应以充分的意识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手中,规范神话造成的唯一结果是谁也不去追求主权这一根本问题,国际法共同体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而只是反映了一批独立政治统一体彼此共存的状况,即使宪法律纳入一个国际法协定义务,那也只是一种技术手段,未尝减少政治独立性。凯尔森认为国家的法学定义是相对集权的强制秩序,其属人、属地、属时效力范围均由国际法决定,而属事效力范围则受国际法限制。国际共同体利用各国作为它的机关创造了国际法,国内法律秩序是同国际法律秩序有机的联系着的,汇合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国内法的效力最终理由归结到国际法的基础规范上去。最后在国家的连续性问题上,施米特认为决不能在国内法或国际法层面上提出,只能从人民统一体的存在的连续性上提出,宪法即使改变,先前的法律因政治存在的连续而直接继续有效,不需特殊手续。凯尔森认为国家的连续性从国内法上看是法律秩序的连续性,如果革命或政变废弃了旧宪法,则只能从国际法上去以领土为主要标准来衡量,宪法改变则原有的法规只是因新宪法的明示或默示赋予其效力才能“继续”存在,只是立法的省略技术。#p#分页标题#e# 凯尔森反对拟人化,但其困难是总体上有机械化、静态化、缺乏能动性的倾向;而施米特采用拟人化手法,富有能动性,但其统一意志论在如何协调实际上分散、对立的意向上必定有假设成分。凯尔森主张较为理想化的规则(技术)统治,而施米特要用魅力专权来打破之,用实质正当性对抗形式合法性。似乎反映了在社会学角度上的功能论和对抗论的不同。 但同时施米特认为人民制宪意志只能靠行动证明而不能受任何规范、程序的束缚,人民没有表达其特殊意志恰表明依然同意现行宪法,而在关键时刻,人民“否”的简单作为自动表达了相反的意志。而凯尔森也承认成功的革命、政变的新宪法不从属于前一部宪法,现实的重大变局无论如何是不能用规范祛除的。凯尔森以实效性原则为核心的基础规范实际上是与施米特的人民存在、人民行动大致处于同一位阶上的,其暗合之处都在于最终都服从于现实,反映了理论构架无论如何都不能跳出现实的掌心。 三、纯粹政治学宪法 施米特曾指出绝对意义的宪法可以指政治统一体一道被给定的具体生存方式,包括其观念的整体和动态的过程,但他没有具体分析;而且在另一种绝对意义的宪法(实定宪法)即总决断中,他也只是提到民主、君主、联邦、单一、代议、法治等基本属性,因为决断是“是”或“否”,越简单越好。而对这种实存的人类行为模式进行精密严谨的经验性观察研究,正是伊斯顿所谓“纯粹的政治学”②的关怀所在。伊斯顿认为,只有政治系统论才是一般的理论,而其他政治理论“研究和阐明的是政治系统的某些特殊部分和侧面。”[7](P516)故而,宪法(实质上的)就是政治系统的存在方式,系统成员在社会生活中不满现状而向政治系统提出要求,并提供支持,系统当局将输入经处理后对社会价值作出权威性分配,当政策输出产生结果后,系统成员作出反应重新提出要求和支持反馈给政治系统,开始新一轮的沟通。在政治系统中,输入、输出的类型与范围是变化的,并不是人们所有的期望都作为正式要求向政治系统提出,比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成员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主要是安全、自由、秩序,而20世纪则更多地提出福利、环境、教育、发展等要求;输出的类型也经历了巫卜、部落决议、神明裁判、长老意见、首领命令到现代的法律规范、司法判决等不同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政治系统与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等不是分裂对立的实体,输入输出并不是象在大厦的许多房间里穿梭进出,这种形象的比喻只是说明人们在各种领域中获得一些经验,然后提出政治要求。政治角色与非政治角色统一于成员本身。古典的关于市民社会于政治社会的分离只是表明在那种环境下系统成员对政治系统的要求较为狭窄,而当系统输出超过一定范围,则会导致支持输入的下降以及反向要求的增加,这种反馈导致系统调整输出,从而形成一定的模式;但这种模式不能绝对化,更不能因此否定政治系统的存在及其价值,政治系统是人类群体生活的必要条件。③ 在不同环境下,当新的要求产生时,政治输出就会进入这些新的领域。特别是在20世纪,政治系统在提取社会资源、分配价值物、进行行为管制的输出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政治系统运行必须依靠一定的结构,结构就是人们政治角色的组合模式,如要求输入的过程(即利益表达和综合的过程)有的是小型的面对面的沟通,有的经过大众性的利益集团和政党,有的经过公共舆论,有的是在普遍压制下仅允许少数特权集团的表达并经过自上而下的刺探,有的经过依附性的人身关系;输出(即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有的经过固定的规则程序,有的非常随意,有的集中、有的分散;政治角色之间的自主或控制程度,政治沟通的范围与方式,政治录用特别是当局人物的录用方式等各不相同,正是从这些不同之中,我们才能够进行民主、专制等类别的判断。一般而言,当要求大量增加时,就需要专业化规模化的结构吸收、整合、分析、处理,否则就必须发展出更多的管制输出结构准备压制,以应对支持的降低。 政治系统的运行也离不开一定的政治观念文化,包括态度、信仰、价值观等,正是这些政治观念文化影响和制约这系统的结构和运行模式。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世俗化和政治结构分化是衡量各种政治系统发展程度的标准,世俗化“代表性地意味着以习惯和超凡魅力为基础的合法性标志的削弱,而政府实际作为的重要性日益成为合法性基础。”[8](P58)世俗化还使人们日益有较强的意识改变个人的命运,不但基于慎重考虑,按所需方式控制社会和经济环境。使政治系统和系统成员之间的积极关涉增加,扩大了政治输入输出的范围,并促进了政治结构的分化。 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产生了作为一种特殊输出类型的形式宪法,它以输入类型由褚法合体转变为诸法分离为基础,是政治系统日益全面自觉对于自身存在方式进行梳理、分析、比较、鉴别从而决定维护或变革的高级表现形式,是政治系统输出方式的一次变革、飞跃,由原先局部、分散的输出转变为一次性系统化的输出。在这个角度上看,形式宪法是全面性地(至少是大规模地)维护或变革实质宪法的政治决策输出。在维护部分,由于它是对政治系统存在方式的模拟、反映或影射,自然是不精确的,常常存在误差的,同时系统存在方式的哪些部分写入形式宪法必然没有统一的认识。在变革部分,其经过实施后取得成效或失败再反馈到政治系统进行新一轮输出。大规模变革若要成功,必须有足量的支持与要求的输入,阿克曼区分“立宪政治”(许多人在公民角色方面投入很多)与“常规政治”(不关心和不注意政治),[9](P196)指的就是这一点。 所以在纯粹政治学的意义上,实质宪法是政治系统的存在方式,包括其运作模式、体系结构和文化观念,三个部分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结为一体。形式宪法是实质宪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同一般法律一样,都是系统输出的政治产品。从这个角度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话“法律实际是也应该是根据政体(宪法)来制定,当然不能叫政体来适应法律。”[10](P310)似乎恰当些,毕竟是生产线决定产品,而非相反。#p#分页标题#e# 四、结语 形式宪法的出现是进步,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标志,但另一方面它的多面性又使人们认识实质宪法困难重重。纯粹法学的立法规范论使我们看清楚了法律系统自我运作的逻辑层次,并指出实质宪法和形式宪法是交叉关系,其他的规范都可以塞进形式宪法,而大量的实质宪法规范遗落在形式宪法之外;而政治法学的决断论则集中力量揭示形式宪法的政治局限性,甚至说危害性,指出它分化、阻碍、掩盖乃至压倒了实质宪法;④纯粹政治学的系统形态论使我们认识到形式宪法作为政治输出的一种形式,是政治系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实质宪法相对成熟的标准,从这个角度看,也许能适度缓解政治法学的焦虑。三种解读的共同点在于都认为实质宪法是普遍存在的,抽去了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价值判断,这种解读并不是目前最流行的,所以本文从此切入,而当讨论完这三种解读,我们发现形式宪法的多面性就在于它要承担许多不同的任务,如它要调整一般立法,要外化并实施根本决断,要进行一次性系统化的输出,不同的形式宪法还要肩挑许多不同的价值判断,这些任务往往又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兼容性,而形式宪法不能面面俱到,便各有取舍,是一种各种性质都有但不纯粹的混杂体,而一些好的实质宪法的解读就是关注形式宪法所具有性质的某一方面,把它提取出来加以理想化或极端化,这也是本文三种解读的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