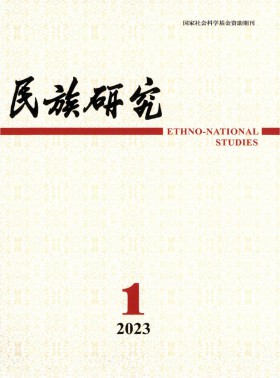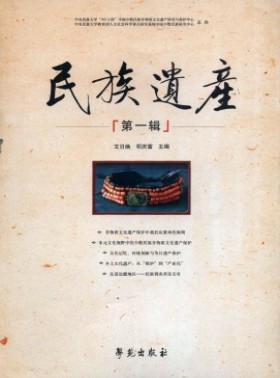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民族文学翻译的美学探讨,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民族文学承载着民族思想、道德文化,是民族艺术和价值的展现。从美学角度出发,探寻翻译理论与民族文学之间的联姻,以翻译为媒介实现民族语言向汉语、英语等其它语言的转变,再现民族文学之美,促进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民族文学的翻译不仅要关注“文化失真”和译者的主体性,还应从形式美、模糊美和民族性等方面进行美学重构,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美,挖掘到民族文学的价值,帮助读者领悟其美学思想,尽量实现民族间跨语际审美价值的传递。
关键词:民族文学;翻译;审美价值;美学重构
民族文学是漫长民族长河的历史生活的展现和精神世界绚丽之花的绽放。大多以文学传记和史诗、民谣的方式来体现民族的道德情感、人文风情和审美情趣,是民族艺术和价值的展现,具有独特的魅力和韵味,深深地烙印着民族的印记,反映了民族的传统和生活,与汉族文学相铺相成,对中国文学的时代风貌和内在气质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极大地推动和拓展了中国文学前行的轨迹。其悠悠历史,独特的人文自然环境、美妙的风土人情和强悍的生命力,造就了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与众不同的美学风貌。如北方民族粗犷剽悍,相对其文学艺术风貌则质朴刚健;南方民族细腻温婉,其文学艺术格调则婉转绵长。民族文学随着民族交流的深入和文化的融合,如何再现原生态民族作品,挖掘原生态的民族文学价值,传递民族灵魂至关重要。
一翻译美学与民族文学的联姻
20世纪30年代国外就开始关注翻译美学的研究,泰特勒倡导“翻译三原则”,译论家阿诺德主张,译者对文学作品真挚的审美感知影响其翻译技能的好坏。西塞罗、贺拉斯等译论家,也指出翻译语言应蕴含民族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之美。雪莉和斯特德编撰的《翻译美学研究》更是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翻译美学,从而巩固了翻译美学的地位,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国内翻译与美学的联姻细水绵长,底蕴深厚,可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佛经翻译,从东汉支谦的“文质说”,近代严复的“信达雅”,到现代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许渊冲的“三美”论等。这些学说无不体现了翻译美学的精髓,主张再现原文的意境、神韵和境界。正如毛荣贵所说“美学与翻译的融合有如珠联璧合,相得益彰”[1]。这些美学理论渗透着对“美”的关注与诠释。总之,翻译美学应用美学原理,解决不同语码和不同文本之间转换的美学问题,从美学角度来传播民族文化和特质。民族文学的传播与推广需要以翻译为介质,实现其向汉语、英语等其他语言的转变和不同民族思维的对接,打破族际、国界的障碍,才能挖掘到民族的文学价值,实现民族的还原,推动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茅盾曾指出,“文学翻译通过语言的转码来传达原作的艺术意境,感受到原作的美,启迪读者的思维。”这段话言简意赅,彰显了文学翻译的主要性质和任务。因此,还原原生态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的时代背景和艺术过程,就是对文学作品民族性和审美价值的还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文学之工整,视其意境之深浅。”[2]美学与翻译的联姻,帮助我们挖掘到独特的民族异质与内涵,领略民族文学的美和奇特的风情面貌,感知不同民族间迥异的风土人情。
二民族文学翻译应注重的两个因素
(一)关注文化“失真”,还原民族的特质
翻译失真往往是指受到诸多因素如语言文化、译者与读者等的影响,原文本的文化信息无法彻底还原,译者创造性的叛逆,形成了新的文化信息,丧失了原文本的原汁原味。文化“失真”涉及到译者和读者两个方面。译者如果对原文本的认知语境产生偏差,就容易误解了其民族文化,文化出现“空缺”或“失真”。同时,目的语读者和源语言民族的思维方式迥异,语言和内容理解会产生分歧,文化理解方面又产生“失真”,从而无法传递独特的少数民族信息。因此,关注文化“失真”现象,提高译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审美鉴别能力及文学素养,从而保证优秀作品的等值翻译。如古代匈奴人崇拜狼,以狼为图腾,匈奴王自称“狼主”。倘若译者不具备该语段的文化背景,只是单纯地把“狼主”译为“Wolflord”,导致文化“失真”,读者无法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其中的文化语境,难以把握文化语境的差别而迷茫。若转译为“Attila”,“kingofHun”,读者一下子便豁然开朗,也可传神地传达其民族如狼般骁勇善战、勇猛凶悍[3]。民族性则是民族文学内在的个体性、独特性,它演绎了民族文化和精神面貌独特的灵魂,呈现不同民族特有的形态。只有保留作品的民族性,民族文学才能独具韵味。突出民族性是民族作品翻译成功的关键。许多优秀的民族作品如果翻译不当,则味同嚼蜡,丧失了民族的特质。蒙古族诗人阿尔泰的作品享誉本民族,尤其是其作品《醒来吧,我的诗》为蒙古族人民争相传颂,结果因为翻译欠妥,该作品的民族韵味大大减弱,蒙古族的彪悍与柔情无法传递,文学魅力也荡然无存,无法打动读者的心弦。蒙古族作家郭雪波形象地描述此种现象为“蒙文诗让人泪水涟涟,而译本只能湿润眼眶。”因此,关注文化“失真”,还原民族的特质刻不容缓。
(二)发挥译者的主体性,提升其文学素养
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得忠实于原作的客观环境,以此为基础,从语言风格、审美观念和文化修养等方面再现原作的内容和思想,把握原作的风格和特色,也体现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翻译的过程是源语言和目标语的转换过程,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是不同语码转换的桥梁和枢纽。就翻译而言,审美主体肩负着双重任务:对源语言的理解和欣赏及对源语言的美的介质的还原与再现。刘宓庆指出:“原语形式美的可译度、文化差异及文学鉴赏的迥异钳制了译者水平的发挥。”[4]因此,译者必须掌握精湛的的书面表达能力和审美鉴别能力,只有优秀的译者能够再现原作的生命力,通过对原作的语言、文化及审美等方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为作品注入活力与生机。此外,译者的水平与风格包涵着对民族经验性内容的顺应,没有民族经验性内容的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是没有水平与风格可言的。由于翻译人员的审美理念不同,对“美”的鉴赏差异很容易引向脱离民族经验的个体风格。因此提高译者文学素养也很重要,文学素养和语言功底直接制约着民族文学的翻译。不了解民族知识和风俗,就无法还原原作的风貌和格调。如柯立甫在翻译《蒙古秘史》的过程中对文本进行了大量的注释,再现原文的古体风格,以期其译作能为读者或专家理解,但是柯译本的译本依然饱受争议,尤其是古体风格和文本的流畅非议最多。柯立甫对本民族文学造诣高深,并能娴熟地应用蒙古语和英语两种语言,而《蒙古秘史》的译本还是责难颇多[5]。译者只有博览群书,提升个人素养,了解各民族的历史宗教和风土人情等知识,才能更好地翻译民族文学的作品。
三民族文学翻译的美学研究
(一)把握形式美,注重音韵美
形式美就是作品的外在美,通常指语言的表现手段和表现方法,包括音韵美,结构美及词汇美等方面,即是原作的语言风格。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尽量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仅要重述原文的内容,而且要着力表现原文的风格特征,尽量寻求替代性的语言形式,让读者身临其境,品味到原作的风格和韵味。《越人歌》是古代春秋时期壮侗族的古老民歌,全文对仗工整,结构类似,音韵优美,抑扬顿挫,讴歌了跨阶级的爱情。其中两句诗词是“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众人皆知,翻译除了要传达原诗的形美和意境之外,还要按照译语的特点创造新的音步和韵脚,特别是这句诗词里面有双关,到了英语里面就很难传达了。“枝”和“知”谐音,以“枝”比喻“知”。树上有枝人人皆知;爱慕君心、情深款款却只能自知。暗含意思就是:木尚有知(枝),而君心尚不如木枝(知)。在英语中难以找到既可以意译又可以双关的同音词。译者运用词汇衔接手段,在最后一行用了一个“grow-ing”,把前后两句衔接起来,保持了形式和意义的统一,让树木的生长和感情的增长意义上保持连贯,并且用“tree”和“thee”押尾韵,尽可能地保存原诗形式美、并创造译诗的“三美”。音美是指译诗的节奏及韵律与原诗的对应程度。一些民族民谣和诗歌注重韵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尽量言简意赅,接近原文风貌,体现原作音韵美,以取得翻译的最大等值。以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民歌《木兰诗》前两句为例,“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译者巧妙地译为,“Rattle,rattle,onandon.AndMulanwoveatthedoor”。原诗和译作韵律均整齐有序。译诗使用拟声词rattle,使译作读起来朗朗上口、抑扬顿挫,使人身临其境听到了织布机唧唧的沉闷声,再现了原诗的效果和风格,取得了与原语最大程度的等值。
(二)出神入化,再现民族文学的模糊美
“花非花,雾非雾”,文学作品多有朦胧隐约,扑朔迷离之感。模糊美学也是美学的一大课题。模糊语具备更高的艺术研究价值,它包含暗示性、意蕴性、简洁性、朦胧感等特征。文学作品常借助于模糊语,它是艺术和作者情志的升华,体现了作者深邃的情感和抽象的意象,也是作品的一种审美手段。模糊语的美学特质决定了其对译者的文学素养和内在气质要求更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正确处理好模糊语,尽量再现原作的美学意蕴,让读者领略到“不见庐山真面目”的模糊美。同时,译者应关注民族文化和生活风俗的差异,挖掘不同语言的模糊美的异曲同工之处,捕捉“欲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感,它虚实相生、意蕴无穷,犹如花间的蝴蝶忽而飘忽不定,忽而驻足停留,言虽尽而意无穷,给读者留下思索的余地。译者通过审美主体的知觉活动把握文学作品的性质,了解作者创作的心境及时代背景,再现原文的时代风貌和艺术场景,用译语勾勒出这种模糊性。如南北朝民歌《诗经•关雎》题目译为“wooingandwedding”。拟声词“关关”表示雌雄鸟的和鸣声。相传这种水鸟“雎鸠”成双成伴,忠贞不渝,同声同死,一般用来比喻男女之间的恋情。作者采用意译,而是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和发散的审美空间,表达了恋人内心的欢愉和恋情。Wooing和wedding,节奏和韵律感更强,读起来朗朗上口。其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句,译者将“淑女”译作了“amaidenfair”,而不用“lady”和“girl”;将“君子”译为“ayoungman”,而不用“gentleman”,前者词语更为贴切,符合民歌风味;后者用词有些过于典雅,不符合语境。
(三)还原民族美,展现文化美和个性美
文化是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结晶和历史底蕴的沉淀,凝结着民族的智慧,潜藏着民族的特质。正如评论者所指:“文化是外部世界对文学影响最丰富的中介系统。它涉及到主体与客体相互制约、共同构建文学的过程,文化在构建中并不断演化。”因此文化介入到文学中,反映了作家以更敏锐的觉察力体味人间百态,重塑沉淀的千年文化和传达民族心理,以理性的方式憧憬未来的景象。文化翻译则是译者借助各种翻译方式如归化和异化手段来展现不同的文化意识,分析原作与译作之间文化差异的因素,独具慧眼传达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之美和异域风采借以实现作品的审美价值,发现文化美的真谛,可尽情领略异乡情调从而拓展自己的视野。如《招魂》(选自《虎迹》)中,马克•本德尔将其翻译为“CallingBacktheSoulofZhygeAlu”.文末译者就彝族文化中的意象支格阿鲁进行了详细阐述。利用注解,读者可以对支格阿鲁有一个大致了解:他是彝族神话故事里的一个传奇人物。“毕摩”是彝族社会集智慧、信仰于一体的文化符号,这个词汇所代表的文化意象以及相关联想难以通过直译“毕摩”来产生[7]。民族文学中的文化意象传递常常出现信息的失落。译者无法找到对等的文化信息来替代,这时通常采用“音译+注释”的方法来规避文化信息的混淆,译为“Bimo,thepriestinthetraditionalanimistreligioninYinationality”。民族个性就指民族内部历经时代变迁多数成员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共有的心理倾向、心理特征及其所反映的社会行为方式的总和。也就是说民族个性是多数民族成员历经共同的社会化的过程,形成稳定的内在化的文化价值和特定民族心理的结果。民族的个性反映了民族的差异,其传统文化价值观特别是宗教信仰促进和推动着民族个性的发展。例如藏族的佛教,新疆的伊斯兰教等对民族个性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促进了民族个性的飞跃。如蒙古族“腾格里”在蒙古语中是指“天神”、“上天”,如若不考虑民族宗教,一味译为“God”或“Lord”,必然造成文化的曲解。西方基督教的救世主一般称为“God”或“Lord”,而古代蒙古族崇拜自然,信仰萨满教,因而翻译为“Heaven”更为适切,该词兼备自然和神灵的含义,彰显了民族独特的个性和宗教信仰。又如《指路经》中描述的“下界”,“下界”不能用西方文化中的“hell”(地狱)来翻译[8]。“西方文化中的‘地狱’是恶魔与邪恶的人死后居住的地方”,而彝族毕摩文化中的“下界”则是除了英雄以外的大多数人死后居住的地方,没有任何善恶意义的划分。同时,民族的地域环境、生活方式及传统习俗等因素也会对民族个性的形成造成一定或主要的影响。如青藏高原和广袤的草原赋予藏族人民豪迈、爽朗的个性。险峻而恶劣的山峦造就了土家族人直爽、强悍的个性。这些都表现了他们独特的审美心理和民族个性。
(四)民族文学翻译教学中的再创造美
许渊冲的“再创造美”理论认为,文学翻译犹如艺术,它研究原文本的“美”,而“美”的传递是译介的高准则。因此他指出要再现原作的各种“美”,如意蕴美、内涵美等,把民族之美转化为世界之美。如彝族文化中的“祖先神”,宁可用“Theancestorsofthesoul”也不随便使用“god”一词,因此“god”会让西方读者产生基督文化的联想,引起对文化意象的误解。再如,“Ihavenoideaifitisreasonable,butheisindeedmyhallelujah.”若直译为“我不知道这是否符合情理,但是他确实是我的哈利努亚”。由于不了解异域文化和习俗,中国读者对“哈利努亚”的含义一头雾水,无法领会其含义,更别提语言美了,若改译为“你是我的救世主”,读者则豁然清楚。再如壮族民歌,“布匹要剪就快剪,衣带要浆就快浆。”Cuttheclothaspossibleasquickly,starchclothesinnotime.如果不了解壮族文化和传统,读者可能会将“浆洗”理解为“洗衣服”,而直接翻译为“washclothes”[9]。但是古代壮族妇女会涂抹一些米浆来清洗衣物后,这样衣服穿着舒适而闻起来芳香。译者把握了其民族文化,直接转译为“starchclothes”,对翻译进行再创造,让人一目了然。许渊冲这种自由独特的创作手法,跨越了不同种族的障碍,实现了原作和译作内涵的秀勇和意蕴的完美。
四结语
民族文学承载着民族思想、文化、感情等内涵,反映其民族的独特文化和思维。民族文学的翻译实际上是不同民族间语言文化的互动,也就是民族文化输出的过程。不同民族间的语言和思维差异巨大,为民族文学的传播设置了双重门槛。翻译美学与民族文学的联姻,促进了民族文学走向世界。透过美学研究民族文学,不仅要关注文化的“失真”和译者的水平,对文学进行再创造,还需要译者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学的形式美,再现其模糊美,演绎其民族美,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语美,保留了浓厚的民族气息,向世界传递着风格迥异的民俗与文化。
参考文献
[1]傅仲选.实用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
[2]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台北:书林出版社,1995.
[3]姜秋霞.文学翻译中的审美过程:格式塔意象再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沈国荣.基于许渊冲“三美论”拓展民族文学翻译空间[J].贵州民族研究,2015(1):72-76.
[5]韩广富.探寻蒙古族萨满教文化发展的轨迹[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5):65-68.
[6]王丽萍.许渊冲翻译美学思想探微———从“三美”角度分析《诗经》英译本[J].海外英语,2011(7):89-91.
[7]陈鸿.彝族毕摩经典译注[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3):45-47.
[8]色音.元代蒙古族萨满教探析[J].西北民族研究,2010(6):21-25.
[9]胡燕琴.翻译美学视阈下民族文学翻译之意蕴[J].贵州民族研究,2016(7):58-62
作者:胡燕琴 祝琦 单位:上饶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