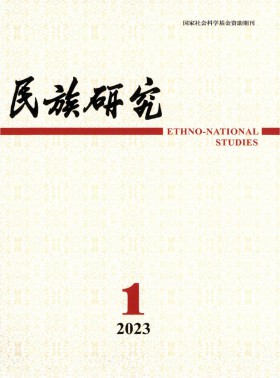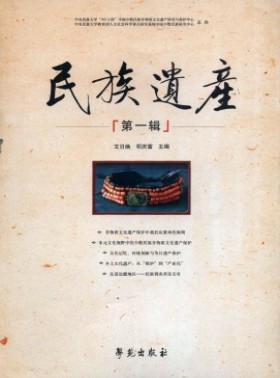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民族文学创作与民族文化传承,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摘要: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寓言化追求一直存在,主要表现为通过寓言模式的建立来显示潜藏于民族内部的集体主义经验,基于描绘最具民族意义的局部意象来求得对民族过去和未来发展的整体把握。基于此,依据詹姆逊文学寓言观,通过对少数民族文学寓言化创作的审视以及对民族寓言背后所折射的民族叙事方式的分析,探讨现代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寓言手段与民族文化传承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詹姆逊;民族寓言;集体经验;文学创作;文化意象
一、民族文学的历史寓言方式与民族语言符号保护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历史寓言是最早也是最常见的寓言手段,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少数民族语言符号与历史的关系,詹姆逊文学寓言思想指出:“民族语言符号是文本意识形态的显现”,[1]无论历史叙事宏大与否,民族语言的表现形式都是稳定的,而历史的寓言化便是出现在这些稳定的民族语言结构之中。以土家族历史小说《最后的巫歌》为例,文中的第一条线索是明写土家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民族历史变迁,第二条暗线刻画土家族人的精神与灵魂发展历程,两条线索一明一暗需要互相配合,暗线怎么配合明线呢,即是通过寓言的方式。在《最后的巫歌》中作者以一头白虎的命运为叙述对象,讲述白虎对后裔的庇护,与巨岩中象征灾难和潜在危害的孽龙作战,白虎身上的兽性和神性隐喻了土家族祖先从混沌不开化的原始力量中跳脱出来,征战杀伐、生离死别,最终建立山地文明的历史命运,这种隐射、暗喻交织的双线索历史叙事法正是少数民族历史寓言的标志,其中以少数民族礼仪仪式和巫文朗诵为代表的语言符号系统不断强化着民族身份、民族记忆以及文化认同,而在当今社会此类少数民族语言符号特质正在消亡,甚至已经消亡,避免这种符号特质消亡的有效手段便是借助产生于稳定民族语言结构之中的寓言化文本。詹姆逊文学寓言理论认为神话、传说所代表的专有语言系统在民族口耳相传的层位上处于优先地位,容易造成民族历史叙事的文学体裁被固化,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一种民族语言系统可能被另一个语言系统所取代,但民族历史却并不会出现全然的断层和散佚”,[2]对语言形式的改变可以借助文学载体的革新来突破,从而发展出新的寓言面貌。那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临的崭新文学载体是什么呢,怎样去筛选适宜少数民族历史寓言化创作的文学载体?以少数民族历史诗歌的转型为例,中国现代“游仙诗”和“剧诗”都是历史叙事的新型体裁,但并非都适合少数民族历史寓言方式的转型。首先是“游仙诗”,现代“游仙诗”有点类似于早期的“乌托邦”,但从渲染返璞归真的原始情怀变为强调对现实的“超脱”理想,然而使用现代语言系统“借古喻今”的可能性要参考文体特征、精神内涵是否具有少数民族整体社会生活的相通性,詹姆逊将文学寓言定位于“从不同层面和广度显现集体性经验”,[3]从这一角度来看“游仙诗”体裁更适合少数民族“寻根文学”而不是历史寓言,“剧诗”体裁反而展示出了自身的优势。“张松如、苏国荣等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家将剧诗归位为中国传统戏曲”,[4]简而言之即是戏剧装进了诗的词句之中,而少数民族历史叙事中最常见的便是以神话剧情为主线的英雄史诗,剧诗与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有着良好的姻盟关系,而从思想内涵来看,剧诗的戏剧主旨集中表现为“载道”意识,有利于反映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塑造与神话故事演绎的信仰系统,促使民族寓言超越个体意识上升为历史集体意义的大群体叙述观。詹姆逊文学寓言思想将民族寓言文本划分为三个层面:“直译的文本指涉、道德的心理解读以及寓言的阐释符码”,[5]其中直译的文本指涉和道德的心理解读都是随着时代价值的转变而变化的,但民族寓言的阐释途径却是防御式的模式,少数民族历史叙事要从现代实践中去挖掘那些逝去却有时代启迪价值的东西,而不是为了守卫传统而存在,詹姆逊文学寓言观不鼓励回归民族寓言的古老形态,提倡“把民族历史看作是我们需要颠覆的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活跃因素”,[6]例如,莫言《生死疲劳》通过动物变形来打破历史的线性压制,文中以驴变牛、猪变狗的戏谑刻画隐射荒诞的民族历史转折点。“透露着一种新鲜时代含义的世界文学观念”。[7]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寓言方式与民族文化内涵拓展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寓言方式是借助寓言的张力去引申和发展民族文化内涵。寓言是一种表达性的力量,可以表达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意蕴,对此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因素存在语音、字、词、句、语法、故事、场景、形象等各个层面,寓言的突出功能在于推动叙述行为和叙述过程最终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文化意象。例如“神农架位于鄂西北与川陕接界处”,[8]神龙文化一直是当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彝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玛庵梦》中的“九头鸟”“蛤蟆龙”“棺材兽”“野人”等奇异、诡秘的原始文化想象如果被单独呈现,并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神龙架山区建立对应关系,好比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文学中虚拟元素所代表的“另一个世界”要与现实生活中的“这一个世界”融合贯通,彝族小说《玛庵梦》以玛庵山上的氏族首领“奥博申申”横跨阴阳两界的战斗经历来暗示以“人”为中心的物质循环状态,立足于对彝族真实地理空间的勘探来复活久远的神龙文化,其时间的寓言性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詹姆逊文学寓言观反复论述了这种运用时间两端相接来反映民族文化本质的寓言方式,指出时间的相互对立和依存为寓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民族寓言表达的现代困境在于如果时间距离感消失,那么便很难从时间距离中抽取自足的文化意象,因此现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如果能凭借“魔幻现实主义”以外的题材去构建民族文化的寓言文本是突破时间困境的出口。例如《绝地逢生》讲述了“云贵高原乌蒙山脉中一群少数民族村民居住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绝地”,[9]这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绝地”显然是作者创作出来的生态文化意象,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出生在那里,这个绝望之地如何会诞生一座村庄,小说并没有去交代,没有“过去的时间”,作家只告诉读者,人们要往外搬迁,整个小说的时间状态都是当下的时间状态,解决向哪里搬迁、如何搬迁的生存难题,但“绝地”的生态文化意象以及对这种生态文化的无边想象却一直凌驾在“搬迁”之上,叙述者叙述着现在时间中发生的事情,读者却想象着过去时间的景象,“绝地”寓言的高度概括性促使作者的生态文化叙述充满对世界生命无常的象征意味,小说中的人们越是顽强抗争,“绝地”的意象魔咒就越发深刻、沉重,即使最后人们终于走进城市完成了自救,也没有化解“绝地”随时可能再现的危机感,自然意象系统、人物意象系统之间的张力关系成就了该篇的生态文化寓言主题。可见,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寓言形象与时间息息相关,但却可以运用脱离时间的方式去表现时间,这便是詹姆逊文学寓言观所强调的“陌生化”戏剧张力的重要性,少数民族惯常使用“陌生化”来创造一种强悍有力的形象,这种形象的在场与不在场都无关紧要,因为被寓言化的形象让人们想起的不是形象本身而是触动人们心灵记忆的真实感受,它时时刻刻都在场,刺激着读者的感官神经。应用“陌生化”叙述来引发读者对时间的“通感”是现代少数民族文化寓言追求的艺术效果,但创作的关键并不在于对“陌生化”意象的直接性营造,詹姆逊文学寓言观认为,文化意象的寓言化冲击仅仅发生在“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距离之中,是它们之间的距离带来了“陌生化”效果,而不是现实本身就存在一个“陌生化”意象。例如《豹子最后的舞蹈》中,“斧头”回忆森林火灾时形容“天空通红,烈焰腾空,烧得星星砰砰下坠,美轮美奂,有几百只豹子跳了崖……”,[10]这种陌生化意象带给读者的精神刺激是来自场面的壮丽(本体)吗?不是,是对豹子跳崖这一模糊物象的省略,真正的喻体存在于读者的想象之中。
三、民族文学的伦理寓言方式与民族价值观传播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作家主体身兼知识分子与族群发言人的双重身份,这使少数民族文学的伦理表达交织着身份认同的矛盾感,詹姆逊文学寓言观指出:“在民族规范之内,作家需要的是‘扩张’,但在民族规范之外,作家需要的则是‘根’”,[11]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面对的是世界文化、资本、政治以及宗教的全球一体化背景,他们有对民族未来的焦虑,也有对民族迷人的古老传统的担忧,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伦理寓言创作急切地呈现出新旧伦理互动的力量交锋。例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风马之耀》都是以寓言的方式描绘藏族传统伦理生活,使用了大量的先锋技巧,显示作家受到西方文学思潮的巨大影响,但从文学内容上看却充满了“外部人”的窥视视角,在扎西达娃的小说中总是存在着一个强悍的闯入者形象,热衷于让“闯入者”们打破藏区的寂静和平和,这种寓言现代文明冲击的闯入者意象是少数民族文学适应全球多元文化格局的必然产物,正如詹姆逊所言:“民族寓言的现代化之路表现且必然表现为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地区的情感文化流变”,[12]可以预见未来少数民族文学的伦理寓言手段只能采取“跨民族”的审视方式来完成,区别在于作家实现自身与家园的联系是通过流动的混合身份认同,还是站在一个地方就代表一个地方的单一化民族身份认同。对此,单一化的民族身份认同已无法适应少数民族伦理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少数民族集体文化意识的“想象的共同体”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裂变,八十年代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致力于描写民族起源、故乡、母语与信仰之间的多边关系,在九十年代的少数民族小说中作家则不停地解释着失去故乡和失去母语的民族生存状态,而当代少数民族伦理文化的“流散”视角已形成,基本看不到血缘在族群关系确认中的地位,早期作品中的浓郁民族特色正被不断淡化,对主要人物的塑造表现出民族身份的含混性,这反而意味着民族伦理的寓言化方式将越来越重要。詹姆逊文学寓言观在对民族伦理身份认同的阐释中提到了“模糊”二字,民族身份本身的模糊化表现为不刻意描绘人物身份的民族性特征,而是通过寓言化的方式来间接传递。例如我国著名少数民族作家老舍的文化个性中流露出鲜明的满汉混合意象,《龙须沟》中的“程疯子”,无论是从服饰打扮、语言风格还是饮食习惯都已看不出该人物的满族身份,作者只淡淡地叙述他在谋生技能上一无所长,在社会交际中屡屡碰壁,将笔墨都花在“程疯子”的“疯”上,详尽地描写他见人就作揖,“多礼”得让人讨厌,他真的疯了吗?那是这个人物在所处伦理文化关系中表现出的“不合时宜”,这种独特的身份寓言方式展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民族伦理交互现象。詹姆逊文学寓言思想认为民族身份建构存在两种文本,一种是写实的文本,另一种是写虚的文本,写实的文本指向单一化民族身份认同,而写虚的文本则在于创造自己的“他者”,《龙须沟》中的“程疯子”便是自己的“他者”,是他在其他族群中的“他”的形象。可见,少数民族伦理寓言化创作并不是为了建立民族身份的对应关系,反而充满了作家对待民族历史和现实、虚构和纪实、文学性与社会性的对立视野,民族身份显现在价值判断与自身定位的两难局面中,当前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城乡文化冲突、阶层分化、文化隔膜都包含着这一寓言逻辑,但文学创作对它们的表达却并不是简单的呈现二元对立的叙述框架,詹姆逊文学寓言观给出了“写虚”文本的寓言定义,即是“‘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弦外之音’的妙境”。[13]例如《云彩擦过悬崖》中“吴三桂”作为来自蛮荒神农山区的唯一外来者,他在大城市的生活状态很少表现出倔强或反抗,更多的是应对异质环境时的柔韧灵活,但作家却偏偏数次写他做梦梦见有一个油锯在割锯他的身体,将他剁成三截的噩梦,以高度抽象的梦境间接地隐喻了主人翁在异质环境中的身份认同焦虑。
作者:章晓宇 单位:湖南女子学院
参考文献:
[1]王莹莹.新历史小说的寓言化叙事倾向[D].辽宁大学,2012.
[2]牛婉若.寻根文学:民族寓言的现代性叙事[J].文艺研究,2013,(12).
[3]申霞艳.寓言叙事及其民族国家想象[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
[4]王逢振.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的寓言”[J].民族学刊,2011,(10).
[5]吴铀生.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与族性文化、民族主义[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6]张掮中.寓言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当代形态[J].中国民族,2012,(12).
[7]李元乔,黄勇.进入中国文艺批评理论的詹姆逊民族寓言思想[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3,(5).
[8]朱全国.寓言的形成及其意义理解[J].文学遗产,2012,(1).
[9]韦良时.想象的困境———论詹姆逊的乌托邦文学观[D].内蒙古大学,2013.
[10]蔡同庆.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J].青海民族研究,2011,(7).
[11]禹建湘.乡土想象中的民族寓言[J].理论与创作,2012,(5).
[12]李长中.城市空间的寓言性想象与“反城市”书写———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心的考察[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13]李忠伟.少数民族伦理道德民族性的多维度阐释———以蒙古族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