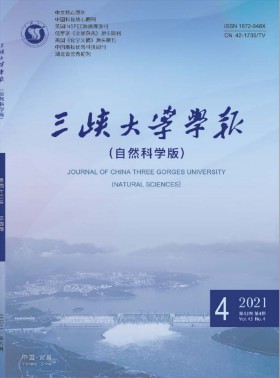三字经全文及解释范文1
[关键词]:《论语正义》《说文解字》
中图分类号:G62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9-0064-02
《论语正义》(后简称《正义》)是《论语》旧注中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共二十四卷,是刘宝楠父子竭尽毕生精力所作。《正义》一书大量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网罗众家之长,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古代字书、辞书和文献解释字义,尤其以引用《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居多。刘宝楠在《问经图序》中说过:“欲治圣经,先通小学。世有薄小学为不足道者,非真能治经者也。”由此可见其对小学和《说文》的重视。《正义》全书引用《说文》约七百八十条,其引用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引用方式多样
《正义》引用《说文》约780条,根据其疏经解义的需要,主要采用了四种引用方式,从引用内容角度来说,主要分为全引和节引两种方式;从形式上讲,主要分为叙引、连引两种方式。多种方式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刘宝楠陪当地引用《说文》,既使字义得到准确疏证,文字内容又不显繁冗。
(一)全引
是指《正义》将《说文》中许慎所作内容全部引用过来,对于徐铉所增注释以及反切注音部分刘宝楠均不予引用。如:
《雍也》:“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正义曰:“《说文》:‘牖,穿壁也,以木为交窗也,从片户甫,谭长以为甫上日也,非户也,牖所以见日。”
《乡党》:“君召使摈。”正义曰:“《说文》:“傧,导也,从人宾声。摈,傧或从手。”
按,“牖”,《说文》:“穿壁也,以木为交窗也,从、片、户、甫,谭长以为:甫上日也,非户也,牖所以见日。”。《说文》,“傧,导也,从人宾声,摈,傧或从手。”两注《正义》均采用了全引的方式使释义具体、完备。全引这种情况在《正义》中比较少见,运用全引方式引用《说文》的字大多是字义或字形上不易理解的字。
(二)节引
《正义》对《说文》的引用绝大部分采用了节引的方式,即只引用《说文》中的部分内容:或只引用解释字义部分;或只引用“一El"部分,或只引用说明异体字形部分;或只引用“读若”部分;或释义和释形都引用等等。节引方式的运用,使刘宝楠在引《说文》时,能够节其所需,从而使释义既简捷又准确。如:
《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正义曰:“《说文》云:‘畏,恶也。”
按,《说文》:“畏,恶也。从,虎省。鬼头而虎爪,可畏也。”《正义》只引用了文中释义部分。
《微子》:“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包曰:“伦,道理也”。正义曰:“《说文》:‘伦,一曰道也。’
按,“伦”,《说文》:“辈也。从人仑声。一曰道也。”《正义》根据《论语》原文内容,节取了“一曰”部分,舍弃了“辈也”这一意义,使字义得到准确解释。
《宪问》:“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正义曰:“《说文》:‘臾,古文蒉,论语有何臾,则许所见壁中文也。”
按,《说文》:“蒉,卿器也,从,贵声,臾,古文蒉,象形,《论语》曰:‘有荷臾而过孔氏之门。”’《正义》引用了《说文》“臾,古文蒉”部分,说明“臾”是“蒉”的异体字,并指出《说文》所引《论语》出自古论。许慎在其《说文解字?叙》中曾表明:“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可见,刘宝楠对“臾”的分析可能出自于此。
《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正义曰:“参者,曾子名,《说文》森字,读若曾参之参。’
按,《说文》:“森,木多貌,从林,从木,读若曾参之参,。”《正义》节引了《说文》“读若”部分,说明“参”字读音与“森”字读音相同,从而明确了“参”字读音。
《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正义曰:“《说文》:‘交,胫也,从大象交形。”
按,《说文》:“交,交胫也,从大象交形,凡交之属皆从交。”《正义》节取引用了《说文》释义和分析字形部分。
(三)叙引
叙引在这里是指作者将《说文》内容用自己的语言转述到正义中去,而不是直接将《说文》内容原封不动引用上去。我们把这种引用方式称为叙引。如:
《公冶长》:“予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正义曰:“浮者,《说文》云汜也。’
《尧日》:“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正义曰:“《说文》训慢为惰,凡怠惰,则致缓也。’
两例中,刘宝楠均采用了叙引的方式将《说文》内容转述到正义内容中去。
(四)连引
《正义》在引用《说文》解释字义时,往往会在后面对与其相关的字继续追加引用《说文》进行注解,但是没有标注“说文”或“说文云”等注语,我们把这种引用方式称为连引。运用连引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有的是一个双音节词,有的是几个字之间有字义或字体上的关系,刘宝楠为了使疏证内容清晰明了,并保持疏证内容的完整性,有时会采用连引的方式。如:
《子罕》:“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一正义曰:“《说文》:‘瞽,目但有联也。联,目精也,今谓之眼珠,又言,目无牟子也……”
按,《正义》在引用《说文》解释瞽的同时,对“目但有联也”中的“联”字又追加引用《说文》进行解释,使以对“瞽”的解释更加具体、准确。如果对“联”字解释不明了,那么“瞽”字的解释也会显得晦涩难懂。
《乡党》;“君在,如也,与与如也。”正义曰:“《说文》:‘,行平易也,躇,长胫行也,一曰。’”
按,“”是一个双音节词,使用连引的方式不仅使释义简捷明了,而且使释义内容具有完整性。
《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正义曰:“犹争也,《说文》:‘,两士相对,兵杖在后,象之形,,遇也,从、断’。二字义微别,今经典通作。’
按,“”、“”两个字之间既有字义上的差别,又是通用与非通用字的关系,连引方式的运用突显了释义内容的整体性,使释义一气呵成。
二、引文用字具有随意性
通过与《说文》大徐本对比,《正义》所引《说文》内容基本
与《说文》一致。但是,在一些引文用字方面与《说文》用字存在差别。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增字,减字,换字三方面。增字、减字和换字的情况是《正义》在不与《说文》原意背离的前提下进行的。
(一)增宇
是指《正义》所引《说文》内容与《说文》相比,增加了个别字词,这种情况情况主要是指增加了实词,个别虚词的增加(如“也”字)不包括在内。如:
《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正义曰:“《说文》:习,鸟数飞也。”
按,《说文》:“习,数飞也……”《正义》增“鸟”字。
《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孔曰:“不疑惑”。正义曰:“《说文》:“疑作疑惑也。”
按,《说文》:“疑,惑也,从子止匕矢声。”《正义》增“疑”字。
(二)减字
是指《正义》所引内容比《说文》原文减少了个别字词,这种情况也不包括虚词。如:
《述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正义曰:“盈者,《说文》云:‘满’也。”
按,《说文》:“盈,满器也。”《正义》减“器”字。
《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正义曰:“《说文》:贵,不贱也。
按,《说文》:“贵,物不贱也……”《正义》减“物”字。
(三)换字
是指《正义》引文中个别用字与《说文》用字不同,这种情况在《正义》中比较普遍。如:
《泰伯》:“边豆之事,则有司存。”正义曰:“《说文》:‘木器谓之桓,从木、豆。’”
按,《说文》:“桓,木豆谓之桓。”《正义》将“豆”替换为“器”,《说文》:“豆,古食肉器也。”‘器”,《说文》:“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器,皿部日,皿,饭食之用器也,然则皿专谓食器,器乃凡器统称,器下云皿也者,散文则不别也……”依据《说文》和《段注》,我们可以知道,“豆”和“器”二字意义相近,都有表示“器皿”之义,只是“器”所表示的意义范围大于“豆”。
《乡党》:“君子不以绀鲰饰。”正义曰:“《说文》无鲰字,下云帛爵头色也……”
按,《说文》:“,帛雀头色……”刘氏将《说文》“雀”字替换为“爵”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今经典鲰字许无,即鲰字也。”《考工记》‘三人为,五人为,七人为缁’,注:‘染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则为,,今礼俗文作爵,言如爵头色也,又复再染以黑乃成缁矣。’士冠礼‘爵弁服’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头然,或谓之。’依郑则爵、、三字一也,三字双声。《巾车》‘雀饰’注曰:‘雀黑多赤少之色。’玉裁按今日验雀头色赤而微黑。”依《段注》所引内容。我们可以知道,刘氏所引《说文》对“”字的解释与《考工记》郑注“”字义合,而且“爵”与“雀”都有“赤而微黑”之义。可见,刘氏用“爵”代替“雀”绝非妄加引用,必有其所据。
三、引用《说文》又不拘泥于《说文》
《正义》在引用《说文》时,并没有一味遵循拘泥于《说文》。为了使疏证更加准确,《正义》还常引用《尔雅》、《方言》、《释名》、《玉篇》、《广雅》、《类篇》等辞书和其他一些文献与《说文》参证、互证。对于《说文》的缺失和不足之处,刘宝楠没有盲从,或指出存疑之处,或作出校订。这些都反映了刘宝楠严谨、务实的学术态度,体现了我国训诂学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如:
《八佾》:“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宦,何谓也?”’正义曰:“《尔雅释宫》云:‘西南隅谓之奥。’《说文》:‘奥,宛也,室之西南隅。’《释名・释宫》云:‘室中西南隅日奥,不见户,明所在秘奥也。”此注先引《尔雅》后引《释名》与《说文》释义参证互证。
《先进》:“冉有,子贡,侃侃如也。”正义曰:“《说文》侃下引子路侃侃如也,疑作子贡,或许氏误记。’
按,《说文》“侃,刚直也,从佃,佃,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昼夜,论语曰:‘子路侃侃如也’。”《论语》作“子贡”,《说文》引作“子路”,对于二者的不同,刘宝楠在没有确凿的证据情况下,没有妄加评判是非,而是以存疑的态度指出“疑作子贡,或许氏误记”。
三字经全文及解释范文2
摘要:汉代是我国训诂学研究的鼎盛时期,汉代注释声训的原则以及推求语源的训诂实践在训诂学史以及语源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拟对汉代声训研究做一概述,主要分为两方面来论述,为政治服务的声训和语言学上的声训,前者选取《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义》,后者选取《说文解字》和《释名》为代表,分别进行系统比较,分析其异同点,并进一步看到它们的贡献及不足。
关键词:汉代;声训;分类;特点
中图分类号:H1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6-0124-04
声训是相对于“形训”和“义训”而言的,其主要原理被认为是“声义同源”,是古代训诂学家的一种认知和解释。中国的声训之学早在先秦时代就已产生,最早的声训材料在《周易》中发现,“乾,健也;离,丽也;需,须也”,先秦诸子散文中也有所出现,《论语・颜渊》:“政者,正也”,《孟子》:“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先秦典籍中出现的声训虽然有限,但却奠定了声训发展的基础。汉代是声训发展的高峰时期,训诂学家在注释中大量运用“以声说义”的方法,郑玄遍注群经,并提出“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的训诂主张,其弟子刘熙的《释名》更是这一时期的集大成之作,《说文》中部分说解条例也涉及了声训。虽然《春秋繁露》《白虎通义》也大量运用了声训,但并不是声训学专著,因为其说解完全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宋代以王圣美等人提出的“右文说”为代表,清代以段玉裁、王念孙等人主张的“声近义通”说为主流,但是声训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有所衰微,不再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只是在考释训诂中,学者们才有所研究。而真正要了解声训的价值及作用,还需要深入挖掘。
一、声训的定义及性质
目前训诂学界对声训的定义有三种,一声训是用音同或音近的词来说明被释词的来源,以词的语音关系来说明词语之间的语源关系。二简单认为声训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训释字义。三则是段玉裁、王念孙等人主张的“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1]前两者是狭义与广义的区分,狭义考虑的是词源问题,广义不仅探究词源,还包括了其他文字假借现象。而“因声求义”这一说法就是基于声训的表面形式,把“读如、读若”之例都视为声训,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慎重的。[2](P77~80)
关于声训的性质,孙雍长先生《论声训的性质》一文中提道:“声训旨在揭示语源,所以用来训释的字必定与被训释的字具有古音相同或相近的关系,训释字所代表的词与被训释字所代表的词也就具有本枝源流的关系,这才是声训的本质属性所在。”[3](P52~55)所以,不能把一切音同或音近训释的训诂材料都视为声训,声训旨在揭示语源,阐明声义同源规律,即揭示词语最初的命名之义,刘熙在其《释名・叙》中说道:“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之称,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意在探求事物命名的“所以然之意”,大量运用声训来解释词义,探索语源。黎千驹先生在其《论汉代声训的功用与性质》中也说道:“所谓声训,是指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的命名之意的一种训诂方式,其目的在于探求词的语源,而不是像义训那样在于揭示词的所指义,也可用来指明古籍中的假借现象。”[4](P48~51)综上所述,声训的性质旨在揭示词的命名立意之义,即探求语源。
二、声训分类比较
汉代产生的大量声训,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并没有真正做到以音义关系推源,而是为古今文学家阐述其哲学观点、政治学说及道德说教服务的,此类声训的主要代表是《春秋繁露》《白虎通义》。而以《说文》《释名》为代表的训诂学专著广泛运用声训的方法说解词义,保留了很多有价值的声训材料,为词语推源提供了参证。因其目的、价值的不同,将汉代声训研究分为两部分来论述,比较分析后看到它们的贡献和不足。
(一)政治声训
这类声训的主要代表是董仲舒《春秋繁露》和班固所撰《白虎通义》,二者从内容上讲是把儒家经学和阴阳谶纬思想相融合,为封建统治服务,达到用儒家伦理道德说教的目的。从形式上来说,对词义的说解主要采用声训的方式。下面将二者做一初步的比较,从而凸显其特点。
1相同之处
其一,声训的目的相同,都具有很强的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目的和神学色彩。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主张为政“必正乎名”,通过对天道观、阴阳五行思想的解说,提出“天人感应”理论,进一步把儒家伦理道德作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如“君者,元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君人者,国之元也”,[5](P62~68)把君主置于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汉章帝召开白虎关会议,由班固等整理成《白虎通义》,目的就是建立统一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系,训释的主要内容是礼仪制度,承袭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及阴阳谶纬思想,想方设法宣扬封建道德观念,“君,群者,群下之所归心也;臣者,坚也,励志自坚固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6]把“君、臣、父、妇”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训释得很清楚。
其二,声训的表达方式基本相同,都采用“…者,…也”、“…,…也”或“…之为言…”的形式。如:王者,皇也;王者;匡也;王者;方也;王者,黄也;王者,往也(《春秋繁露》)。士者,事也;教者,效也;亥者,也;仲,中也(《白虎通义》)。恭,敬也;意,心之所向也(《春秋繁露》)。伯,白也;天子,爵称也(《白虎通义》)。名,名之为言真也;寿,寿之为言雠也(《春秋繁露》)。蓍,蓍之为言耆也;火,火之为言化也(《白虎通义》)。以上简单列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两者所含声训在表达方式上的相同之处。
其三,在训释词之后,经常带有训释语做进一步的说明。武者,伐也。文王之时,民乐其与师征伐也,故曰“武”。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谓也(《春秋繁露》)。木之言触也。阳气动跃触也而出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禀六气以生者也(《白虎通义》)[7]。在训释的基础上,加了一段对训释词的解释,进一步说明其含义。
2不同之处
其一,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白虎通义》的声训要远远多于《春秋繁露》,数量明显增多,而且相对集中。《春秋繁露》主要出现在其“深察名号”篇中,《白虎通义》全书四十三篇,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伦理道德、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涉及的词语解释,几乎都采用了声训的方式,运用相当普遍。
其二,与《春秋繁露》相比之下,《白虎通义》的训释体例较为完备,已成一定体系,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主要体现在训释方式的增加和解说的综合性。如“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无所不知也;宫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时者也”[8](P120~123),在这种表达方式中,被训释词与第一个训释词构成声训,而第二个训释词做进一步解释,但并不一定与被训释词存在音同或音近的关系。《白虎通义》在继承了《春秋繁露》思想的基础之上,为统一五经经义异同而作,吸收了先秦时期的各家观点,如叶方石、王丽俊《声训的特点》一文中提到的关于“礼”的解释,“‘礼之为言履也。可履践而行’,就吸收了先秦典籍中对礼的阐释,《礼记》:‘礼者,履此者也’,《荀子》:‘礼者,人所履也’,《尔雅》:‘履,礼也,注:礼可以履行’”[9](P38~39),由此可看出《白虎通义》内容的旁征博引。
这类声训主观性太强,本着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没有从语言实际出发,凭着自己的主观想象和臆测把音同或音近的字拿来训释,将儒学神学化,其中还深深打上了阴阳思想的烙印,糟粕颇多。但并不否认其中也包含了某些正确的解说,保存了丰富的古文献资料,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其贡献与不足。
(二)语言学声训
《说文解字》《释名》的出现,标志着声训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不再单纯地为宣扬政治目的、阐明学术观点服务,而是成为训诂学研究中的一种词义训释方式。《说文》是我国第一部成书的字典,综合分析字的形、音、义,以形训为主,但声训也占有一定比例。而《释名》是声训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刘熙已注重从义类出发,探求事物的命名之由,开词源研究之先河。[10](P82~87)《说文》成书早于《释名》,因此《释名》的创作也可能受到了《说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有所继承和创新,形成自己的特点。这部分内容将二者进行综合比较,深入认识其语言学研究方面的价值。
1相同之处
《说文》和《释名》同是汉代这个特定时期训诂研究的产物,都广泛采用声训的方法来说解词义,至此汉代的声训才算真正的定型。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声训中多有穿凿附会之说,受《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的影响,夹杂了阴阳五行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深深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如《说文・一部》:“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释名・释长幼》:“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摆脱时代思想对语言研究的影响。
2不同之处
《说文》是以分析字的形、音、义为主,所以声训还只是解释字义的一种辅助方法,与其他训诂方法相辅相成,[11](P188~194)而《释名》的释义却是以声训为主,著书目的是把“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之意叙论指归”,所以两者存在较大的不同。
首先,声训所占的数量不同。《释名》完全是从声训出发,全书释1502词,可以说声训所占比例在90%以上。《说文》中的声训,参考黄宇鸿先生所统计的数据,“声训共有706例,占全书总字数的8%”,[12](P30~35)可见在二者中声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其次,声训的立足点不同。《说文》全书以“六书”贯之,释义以形为主,因形说义,声训往往与汉字的形体紧密联系,以说明文字形义的关系。许慎是一位古文经学家,故《说文》多引经据典,释义往往比《释名》可靠。刘熙著《释名》重在以声立训,探求文字声义同源规律,追溯词源,以明事物命名之旨,相比之下,其声训具有随意性和灵活性。如《说文・月部》:“朔,月一日始苏也。从月,声”,《释名・释天》:“朔,月初之名也。朔,苏也。月死后苏生也”,可看出《说文》在声训之后多表明字形结构,《释名》在声训之后进一步说明事物命名的依据。
第三,声训表达方式的不同。严格来说,《释名》的表达方式要比《说文》复杂得多,体例也相对完备。《说文》的声训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明字词得义之由,如《说文・仓部》:“仓,谷藏也,谷黄取而藏之,故谓之仓”,《说文・韭部》:“韭,菜名。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说文・麦部》:“麦,芒谷,秋种厚埋,故谓之麦”。二直接用声训词来做训释,《说文・门部》:“门,闻也”,《说文・户部》:“户,护也”,《说文・月部》:“月,阙也”,三在训释词中隐含声训词,《说文・一部》:“吏,治人者也”,《说文・示部》:“,烧柴燎以祭天神”,《说文・土部》:“土,地之吐生万物也”。[13]
《释名》的声训方式繁多,清人顾广圻将其归纳为10例:“曰本字,曰叠本字,曰本字而易字,曰易字,曰叠易字,曰再易字,曰转易字,曰省易字,曰省叠易字,曰易双字”,[14](P199~203)近人杨树达等不满顾氏的分类,又将其分为“一曰同音,二曰双声,三曰叠韵”,主要是从语音角度来分析。从前人的研究就可看出《释名》的声训体例之复杂。本文主要从表述方式上将其分为三类,一是用音同或音近字训释,这在《释名》中占绝大多数,《释名・释言语》:“密,蜜也,如蜜所,无不满也”,《释名・释饮食》:“饵,而也,相黏而也”,二是用本字作训释,《释名・释州国》:“齐,齐也,地在渤海之南,勃其之中也”,《释名・释书契》:“籍,籍也,所以籍疏人名户口也”,三是一词多释,《释名・释天》:“天,显也,在上高显也;天,坦也,坦然高而远也”,《释名・释形体》:“毛,貌也,冒也。在表所以别形貌,且以自覆冒也”。[14](P199~203)
《说文》与《释名》各自的特点十分显著,《说文》对声训的运用比不上《释名》,可信度却比《释名》要高。虽然都被其时代所限制,但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这类研究确立了声训的基本形式,奠定了声训的地位,使其系统化和理论化。
三、贡献及不足
从上述的声训研究分析可知,理解古人的声训不能简单认为词义说解正确与否,而应结合作者当时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来深入理解,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思考、研究。
以《春秋繁露》《白虎通义》为代表的这类政治声训,尽管是为政治服务的,用来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制约、禁锢人们的思想,但是也应看到它存在的合理之处。(1)其中的声训材料为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虽然不能概括上古音韵系统的全貌,但有利于考察汉代的语音情况。(2)在追溯语源方面,对后人的创作具有启示作用,如《释名》从事物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究其由来,就是以当时的神权法典《白虎通义》为标准。(3)对后代训诂学著作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们出现在《说文》《释名》之前,虽然推求词源方面并不一定正确,但其声训实践为《释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这类声训在训诂学研究中地位并不高,词语训释仅凭主观的猜测,没有从语言实际出发,是最遭人诟病的。其弊端主要在于缺乏科学性、合理性,多随意附会之说,封建神学色彩浓厚,不能从词固有的音义关系出发,只要符合阐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就随意联系,强加比附,无法与后来《说文》《释名》等语言学上的声训相比。
《说文》主要从文字学的角度说明声训,《释名》则从语言学出发,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声训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贡献:(1)运用声训来推求语源,推导事物命名的理据,系联了一大批同源词,推动了汉语语源学的产生和发展;(2)使声训的发展不断系统化、科学化和理论化,注重从语音着手探求词义关系;(3)涉及语音的分析和描写,为古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具有特殊的科学价值;(4)是声训的奠基之作,理论和实践都产生深远影响,在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5)有助于分析古书中的假借现象,假借的前提也是假借字与被假借字具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可根据声训材料判定是否具有通假关系,便于读懂古书。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尚难摆脱经学的影响,其中也免不了有牵强附会之处,夹杂阴阳谶纬、儒家男尊女卑、礼乐教化的观念,如《说文》中对天干地支字、数字的阐释,明显受到董仲舒等人的影响,“《释名》还多采用《白虎通义》的一些说法,神秘色彩颇浓,有时滥用声训,强用音同音近字解释事物名称”。[15](P30~33)
综上所述,对汉代声训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研究,比较了它们的异同,总结其贡献与不足,它们之间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春秋繁露》《白虎通义》《说文》《释名》都是声训研究的重要史料,为上古音韵研究提供参证,有利于梳理汉语语音的发展源流及脉络;有助于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历史角度出发,探索语源,可深入挖掘汉代人的思维特征;结合当今的时代背景来看,对外汉语教学中,在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发音、熟悉字义方面,声训可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是要辩证地看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国良.两汉声训研究及汇纂[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2]段雪璐.训诂方式与训诂方法的区分――以“声训”和“因声求义”为例[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
[3]孙雍长.论声训的性质[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2).
[4]黎千驹.论汉代声训的功用与性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9,(2).
[5]宋锡同.汉代经学走向管窥――以《春秋繁露》与《白虎通》的对比分析为视角[J].河北大学学报, 2008,(1).
[6]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3.
[7]王丽俊.《白虎通义》声训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
[8] 叶方石,王丽俊.《白虎通义》声训的价值与不足[J].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2).
[9]叶方石,王丽俊.《白虎通义》声训的特点[J].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3).
[10]魏宇文.《释名》研究综述[J].嘉应大学学报, 2000,(5).
[11]朱惠仙.《说文解字》声训研究述论[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2).
[12]黄宇鸿.《说文》与《释名》声训之比较研究[J].武汉教育学院学报, 1996,(2).
[13]汤可敬.说文解字今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7.
[14]蔡英杰.中国古代语言学文献教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15]褚群武,赵拴牢,杜红梅.论《释名》声训的贡献及阙失[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2012,(5).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nunciation-based
Word Interpretation (Sheng Xun) in Han Dynasty
ZHANG Jie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三字经全文及解释范文3
《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中有关虚词的部分,继承了《释词》以及其他诸如袁仁林《虚字说》、刘淇《助字辨略》等的学术成就,但在同时,对前人一些不尽妥当或者至少马建忠本人认为是不妥当的虚词解释直接予以批评。其中《文通》对《释词》的批评据笔者统计,涉及到的古汉语虚词有二十一个,如“之”、“所”、“焉”、“也”等,这种批评在《文通》全书中共约二十五处之多。书中“高邮王氏”、“王氏”等所指不言自喻,而那些“经生家”、“经学家”等字样也多是指王念孙父子或《释词》而言。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观察分析《文通》对《释词》的批评,那么可以看到,“在大多数情况,他(马建忠)的批驳是有说服力的”[1],是言之成理的、正确的;而有些是批错了的;有些则属王、马皆有所申说,但我们却都不敢苟从的。
举例如下:
一、《文通》正确的:
(1)……又僖公二十三年云:“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经生家皆谓所引传语各节,首句皆间“之”字,而下以“若”字对之,故“之”与“若”互文耳。不知凡起词坐动有“之”字为间者,皆读也。而凡读挺接上文者,时有假设之意,不必以“之”字泥解为“若”字也[2]。
《释词》卷九:之,犹“若”也。
我们今天一般看法是:“之”助词,插在主谓之间,使这个主谓词组不构成句子而构成分句,表示语义未完。这一认识同于《文通》,不同于《释词》。
(2)“与”字于助动后,无司词者常也。
论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可与共学”者,言“可与之共学”也。“之”者,以指“可与共学”之人,下同。“可”,助动也。此等句法,动字往往解为受动。……有谓礼中庸云:“可与入德矣。”论语阳货云:“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易系辞云:“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史记袁盎列传云:“妾主岂可与同坐哉!”诸“与”字作“以”字解,而引史记货殖传云:“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与汉书杨雄传云:“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为朋”诸句,以“与”、“以”两字互文为证。不知古人用字不苟,其异用者正各有其义耳。况助动后“与”实有本解。如汉书陆贾传云:“越中无足与语。”若云“无足以语”,则不词矣。书籍中“与”字往往有不可解之处,释词所拟之解,颇可释疑,然不敢据为定论也[3]。
《释词》卷一:与,犹“以”也。
很明显,《文通》的说解优于《释词》。
(3)古人用字,各有其义,不可牵混。且假设之词,有不必书明而辞气已隐寓者。如释词引吕氏春秋知士篇剂貌辩答宣王曰:“王方为太子之时,辨谓静郭君曰:‘太子之不仁,过删涿视,不若革太子,更立卫姬婴儿校师。’静郭君泫而曰:‘不可,吾弗忍为也。’且静郭君听辨而为之也,必无今日之患也。”又去尤篇曰:“邾之故法,为甲裳以帛,公息忌谓邾君曰:‘不若以组。凡甲之所以为固者,以满窍也。今窍满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组则不然,窍满则尽任力矣。’”两节,谓“且静郭君”云者,齐策“且”作“若”,而“且组则不然”者,亦与“若”同义。不知“且静郭君”一句,原是假设之事,而“且组则不然”者,申明事理,并无假设之意,何以强解为哉[4]!
《释词》卷八:且,犹“若”也。
在此,《文通》的驳正是有理有力的。
(4)又孟子万章下云:“而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一节,经生家以“而”字作“如”字解。左传襄公三十年云:“子产而死”一句,则以“而”字解作“若”字,又杂引他句,“而”字解作“乃”字。不知“而”字之解“若”、“如”等字者,非其本字,乃上下截之辞气使然耳[5]。
对于这个问题,《文通》还有论述:
(5)夫“而”字解如“若”字之义亦通,然将两上截重读,接以“而”字,其虚神仍在。
……论语述而云:“富而可求也”句,必将“富”字重顿,而云“富之为富而可求也”,则下句“虽”字已跃然矣。左传宣公十二年云:“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犹云“且为一国之君而逃臣”云,如是上截顿足,则下截跌进更有力。若惟云“君若逃臣”云云者,则无余音矣[6]。
《释词》卷七:而,犹“如”也。而,犹“若”也。
《文通》或从“辞气”角度,或从修辞角度来说明问题,胜于《释词》之泥解。
二、《文通》批错了的:
(6)经生家皆以“何则”二字连读,愚谓“何则”二字,亦犹“然而”两字,当析读,则“则”字方有着落。且“则”字所以直接上文,必置句读之首,何独于此而变其例哉[7]?
《释词》卷八:何则,“何也”也。《墨子·尚贤》篇曰:“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失损其国家,倾覆其社稷者,巳此故也。何则?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荀子·宥坐》篇曰:“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
上下比较,《释词》所解更为文通字顺,而《文通》则有点胶柱鼓瑟。
(7)惟史籍中有时“唯”字与“即”字同解,而经生家以“唯”、“虽”两字同韵,往往以“虽”字解“唯”字,拘矣[8]。
《释词》卷三:惟,独也,常语也。或作“唯”、“维”。家大人曰:亦作“虽”。
古汉语中表示让步假设,用“唯”、“虽”或“即”,意义相同,《释词》所解无误。杨伯峻《古汉语虚词》同《释词》。王力评价《释词》此解“确不可拔”[9]。
三、王、马所解都不能令人满意的:
(8)经生家谓经籍内有“也”、“矣”两字互相代用者。论语先进云:“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以为“也”代“矣”字。论语里仁云:“其为仁矣。”又以为“矣”代“也”字之证。蒙谓“皆不及门也”者,决言同时之事,“也”字为宜。至“其为仁矣”之读,夫子自叹未见好仁者之真恶不仁者,故追忆真恶不仁者之曾已为仁之时,直使不仁者不得加乎其身云。此似追记已事,助“矣”字为宜。夫“矣”“也”两字皆决辞,有时所别甚微。若非细玩上下文义,徒以一时读之顺口,即据为定论,此经生家未曾梦见文通者,亦何怪其尔也[10]。
《释词》卷四:矣,犹“也”也。“也”“矣”一声之转,故“也”可训为“矣”,“矣”亦可训为“也”。
《文通》的说解虽然费力不少,但大多只是臆测之辞,不能说服人,而言辞上还有点盛气凌人;《释词》只从语音上推敲,也有缺漏。其实,就一般情况而论,“也”用于判断句,“矣”用于叙述句,它们各有适用范围;这两个字有时混用,但这是少数情况(参看王力《古代汉语》第一册和杨伯峻《古汉语虚词》)。此种混用情况,笔者以为,是由于古书传写时不同的人用字规范与否的原因造成的,或许也是上古语法发展演变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反映(它们均不见于甲骨文和西周金文,而是在这之后才出现并使用起来的)。
(9)列子力命:“仲父之病疾矣,不可讳,云至于大病,则寡人恶乎属国而可?”“云至于大病”者,谓或至于大病也。“云”者谓也。此句有“则”字为承,有假设之辞,不必以“云”字强解“如”字也,盖假设辞气,可不言而喻。而释词注引礼檀弓:“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则如之何”之句,以证“云”作“如”字之解,究属牵合[11]。
《释词》卷三,家大人曰:云,犹“如”也。
《文通》与《释词》各言其是,各有所据,然孰是孰非,一时难以确定。
杨伯峻《古汉语虚词》有解“云”为“如”,同意《释词》,但同时又说:“‘云’作假设连词,极罕见”。可见这亦非通例。
《文通》对《释词》的批评,多数颇有道理,起码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其中也不乏精采之处。如:
(10)礼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云云,“能尽其性”者,犹云“设如能尽其性”也,经生家即以“能”字有假设之意。不知凡挺接之句,或重叠其文,如“能尽其性”之类,皆寓有假设之语气,不必以用“能”字为然也[12]。
《释词》卷六:“能,犹‘而’也。……《韩诗外传》:‘贵而下贱,则众弗恶也;富能分贫,则穷士弗恶也;智而教愚,则童蒙者弗恶也。’”
在实际语言环境中,表示假设关系等语义关系,可用关联词语,也可采用“意合法”,现代汉语如此,古代汉语亦如此。《文通》的作者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王引之《释词》颇可破解古文之疑惑,然在此却忽视了汉语语义连接方式的多样性特征。
诸如例(10)这样的论述,我们还可找到一些。
《马氏文通》之所以可以在前人虚字训释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开拓和进展,从而廓清《经传释词》虚词解说在客观上所造成的一些迷惑,原因在于:
第一、马氏具有更具科学性的头脑,他在先进的语言理论的指导下,把对虚词的认识纳入语言的整个系统中来进行。
首先,他分析研究古汉语虚词,注意从系统的角度来观察,即不但从语音方面,从词汇方面,而且还能从语法的组合和聚合两方面来考虑问题,认识虚词——当然这yì①不等于说彼时的马建忠已经具备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这样较之单纯地从语音,或者仅从语音、词汇角度去认识分析虚词,其视野会更加开阔,其结论也会更加准确。
郭绍虞先生曾对《释词》作过一个概括而中肯的评论:“《经传释词》虽则是研究重在配置意义的虚字的书,但是称之曰‘释’,可见只是训诂学方面的著作,称之曰‘经传’,更可见得此书是重在解释经传之词,为读古书服务,亦不是为写作服务的。所以对虚字的解释也只是求它的个别意义,亦不重在求它的配置意义。尽管他的方法,是归纳了很多同类的句型再去推求它的意义,但是目标所在,只是这个虚字在语句的组织配置中的个别意义,亦不重在配置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别[13]。”
从体系的角度说,《马氏文通》是我国汉语虚词研究进入现代语言学阶段的一个标志,而在它之前的有关虚词研究的著作,包括《经传释词》都仍属于传统训诂学的范围(某些词,《释词》归之于“词”〔虚词〕,而《文通》则归之于实词,其原因也在此)。在这方面,《文通》表现出迥异于前人著作的风格,表现出一种时代的高度。今天的人们评论《文通》,说它模仿拉丁语法也好,说它尚有许多自相矛盾、不严密的地方,因而不够成熟也好,却都无法否定《文通》的时代意义与开创之功。
其次,在具体批评《释词》过程中,马建忠非常注意从虚词的语法特征角度来阐述自己的意见。他所选取的角度与我们分析研究虚词的角度基本一致,他批评《释词》往往是从虚词的语法位置、句法功能以及语法类别等方面入手,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举其中的“焉”字为例。
《文通》曾在五个地方对高邮王氏父子有关“焉”字的解说进行了批评:
(11)—Ⅰ:礼月令:“天子焉始乘舟。”犹云“天子于是始乘舟也。”……惟高邮王氏必以“焉始”两字连续,似牵合耳[14]。
(11)—Ⅱ:古书多有叠用两字同意者,高邮以“焉虑”连续,解作“亡虑”者,未免牵合。……而“大抵”“大要”“大归”亦寝用矣[15]。
(11)—Ⅲ:高邮王氏引吕氏春秋季春篇云:……不亦固哉![16]
(11)—Ⅳ:“焉”字助字,与助读同。……而始有其意存焉也[17]。
(11)—Ⅴ:统考所引,无论为读……故统谓之助字者近是[18]。
在这里,例Ⅰ、Ⅱ是从虚词的位置与组合角度来讨论问题,例Ⅲ是从虚词的作用、位置方面阐发己见,批评《文通》的错误,例Ⅳ、Ⅴ则是对虚词语法功能或语法意义进行总结,同时指出《释词》的错误及其根源。经过这番阐述,人们对于虚词及其语法特征便会有一个相当全面的理解。
《文通》特别注意结合句法功能来审订前人对虚词的解释,而不单单局限于语义的贯通。如:
(12)“不”字有代“无”字者。汉武五子传赞:“不一日而无兵”。又枚皋传:“凡可读者不二十篇”。诗王风:“不日不月。”周官大司马:“若师不功,则厌而奉主车。”诸“不”皆可解作“无”字,以其先乎名字故也。故释词谓论语先进“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句,“不间”当作“非间”者,失之矣。以“间”字为动字故也[19]。
《文通》注意抓住每一类虚词的句法特征来说明问题。这是其对《释词》之批评本身的特点之一。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指出:“从马氏对助字的解释来看,他提出助字有‘济夫动字不变之穷’的作用,这是前人没有说到的,是他的创新。”[20]“马氏能指出汉文介字这种济实字之穷的重要作用,是他比较汉文西文,亦能联系汉语实际的结果。”[21]在《文通》中,马建忠对虚词的语法意义作了相当精确的概括,这种概括构成了其虚词说解的基础,同时也成为马氏批评《释词》的根本依据。
从细小的方面来说,比如对某些助字,马氏很注意从语用角度来分析,如上面对“也”、“矣”的解释,这种解释本身正误暂且不提,至少他的研究方向是值得借鉴的。对某些连字,他又能不囿于句子或词组的范围,从句群的角度来研究,如前述对“且”的说解。
所以,《文通》把虚词纳入整个语法乃至整个语言系统之中进行分析与研究,从语法功能角度对虚词进行分类,而后在虚词“类意义”的统摄下,再对各个虚词进行横向的比较,寻找甄别其异同,这就避免了以往虚词说解上存在的头绪不清、几呈散沙一盘情况的再现,同时使自己对《释词》的批评更具有理论高度,更能切中要害,更富于条理性,也更为有力。我们今天分析虚词,其依据最主要还是虚词的组合功能与虚词在语句中所表现出的一定的语法意义,这一点与《文通》是基本相同的。因此,两相比较,假如我们再考虑到马建忠当时尚处在封闭落后的封建社会,考虑到在他之前尚没有谁对汉语虚词进行过真正意义的语法研究,那么我们就不能不佩服马建忠的远见卓识了。
其三、马氏有一个信念,他认为,“古人用字不苟”,“古人用字,各有其义,不可牵混”(见例(2)、(3)),因此,只要从字面上可以讲通,就不向通假或其他方向去理解。在具体说解时,他非常坚定甚至有时近乎固执地抓住虚词各个不同用法之间在意义上的联系不放,对各个虚词的或复杂或简单的不同用法,他都试图从字面上寻求最为合理的解释。他用这个作武器来反对王引之等在语音上随意穿凿联缀,这是他的优点,然而也是造成其某些错误的根源。反过来看,王引之精通音韵,触类旁通,能依声破字,不过这一乾嘉学派的法宝用于古汉语的虚词研究,其效用远远比不上对实词的研究,因为虚词问题主要还是语法问题,而非词汇问题。
第二,《文通》在阐述虚词意义时,还注意从修辞角度来考虑问题,为我们研究虚词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如上例(5)即如此。再如:
(13)礼文王世子:“故父在斯为子,君在斯谓之臣。”释词谓两句内“为”与“谓”互文同解。照注内云,“为”下当有“之”字脱去。愚以为两句内“为”、“谓”两字当作原解,于意更顺。盖爷子天纲,凡父在不能不得其子,故“为”字作断词解。至君臣之伦,不若父子之重,故云君在而后称之曰臣,则词义稍缓。“谓”字仍作“称谓”之意,而“为”后“之”字非脱落明矣[22]。
类似的说解,《文通》中还有不少。虚词既是语法学所要关注的对象,同时又是修辞学所应该涉及的问题。马建忠注意结合修辞来讨论问题亦批评《释词》,表现出其过人的识见,显示出其开阔的视野与活跃的思维,而这一点恰也是王引之等人所忽视了的,并且是导致其错误说解的原因之一。
第三,《马氏文通》超越前人的地方还在于,它能广罗例证,以丰富的材料为基础来说明道理。其所罗列的例句多达七八千个,其中有关虚词的例句约占一半,在其前后几乎没有哪本语法学著作能够收集亦分析如此之多的例子。《文通》一方面广泛占有材料,另一方面,它既注重一般意义的归纳,又注重特殊意义的分析,因而得出的结论更为全面,更有说服力。较之《文通》,《释词》更多地注重难解词语的训释,对于虚词的一般语法意义,则常常以“常语也”而一笔带过。这固然与其书体例有关,但也给人一种各个义项互不关联的印象,客观上影响我们对各个虚词语法意义的全面认识。
对于《文通》的其他方面,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言。王力先生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建忠的著作算是杰出的。”[23]这个评价一点也不算过分。《马氏文通》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它在中国语法学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注释:
(1)《吕叔湘文集》第三卷456页,商务印书馆92年7月版。
(2)《马氏文通》249页,商务印书馆83年9月新一版(以下只标书名和页码)。
(3)《马氏文通》271页。
(4)《马氏文通》279页。
(5)《马氏文通》295页。
(6)《马氏文通》289页。
(7)《马氏文通》74页。
(8)《马氏文通》317页。
(9)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64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第1版。
(10)《马氏文通》347页。
(11)《马氏文通》156页。
(12)《马氏文通》184页。
(13)郭绍虞《从〈马氏文通〉所想起的一些问题》,见《复旦学报》1959年3期。
(14)《马氏文通》55页。由于篇幅所限,此处及以下4例只作略引。请详参原文。
(15)《马氏文通》87页。
(16)《马氏文通》357页。
(17)《马氏文通》358页。
(18)《马氏文通》360页。
(19)《马氏文通》239页。
(20)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第一版466页。
(21)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466页。
三字经全文及解释范文4
关键词:杨慎;《升庵全集》;字词;考据
杨慎《升庵全集》中收录了杨慎一生的要著,是他学术成果的精华。其中,字词考据成就更是功不可没。本文就杨慎《升庵全集》有关字词方面的考据列举数例并作粗浅探索,以期抛砖引玉。
杨慎博学多识,对于典籍著作中字词的意思总能加以自己的理解训释出和前人不同的意思,其中不少都很有价值。例如:
一、释“”
《升庵全集》卷五十九“来”条对“”在《楚辞》“车既驾兮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的意思提出不同看法。旧注这句当中的“”为“去也”。《说文》“,去也。”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云:“,丘杰切,去也。”《康熙字典》亦将其训为“去”并举《楚辞》此例。看来,“”训“去”似成定论。但杨慎对此提出质疑:又按《吕氏春秋》“胶鬲见武王于鲔水,曰:‘西伯来?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伐殷也。’胶鬲曰:‘至?’武王曰:‘将以甲子日至。’”注:“,何也。”若然,则“”之为言“盍”也。无疑,在《吕氏春秋》当中的“”解作“何也”是恰当的。杨慎指出如果以“何也”的解释去解《楚辞》,那么“则谓‘车既驾矣,盍而归乎’,以不得见而心伤悲也,意尤婉至。”这样的解法放入文中似乎更能体现那种不舍、悲切的情怀。而且,《正字通・曰部》“,与曷通”。又《辞源》“通盍。”杨树达《词诠》当中认为“”是疑问代名词,“何也”的意思,举《吕氏春秋》当中的例子证之。因此,杨慎这么解也是说得通的。最后杨慎又举两例以证其说:“则今文所袭用‘来’者,亦谓‘盍来’也,非是发语之辞矣。《文选》注刘向七言曰:‘来归耕永自疏’,颜延年《秋胡妻》诗曰:‘来空复辞’,皆谓‘盍’字始通。”《辞源》当中也举《秋胡妻》一诗认为“来”应为“何来”之意。杨慎其说未必精确,但却从另一个角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二、释“爱”
《升庵全集》卷六十三“字义”条,杨慎在这条中不但解释了“”的字义,也用有力的论据驳正了许多学者的解释,并阐发了语音与词义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现在科学的训诂学所用的“因声求义”的方法。虽然没达到理论高度,但有明一代,是非常难得的。他指出:班固《终南山赋》“霭,若鬼若神。”注:“,音爱逮,吐吞,障蔽天日,变化殊形也。”《韵会》“,不明貌,一作。”杨慎由对“”的解释拓展到《诗经・邶风・静女》当中的“而不,搔首踯躅。”一句,这句诗在郑玄《毛诗笺》以及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当中对“爱”的解释都是“喜爱,悦爱”之义。然而,杨慎能够大胆怀疑经典,他指出:“毛苌云:‘爱,蔽也。’《文》从人作‘’,《方言》从草作‘’,字书或从‘’作‘’,或从‘日’作‘’,皆‘蔽而不’之意,今文但作‘爱’。将“爱”解释成“蔽”虽然古已有之,但是他从古音学的角度将声音相同但形体不同的“、、、”联系在一起,这样意思就更加清晰了。最后他补述道:“宋玉《高唐赋》:‘兮若姣姬,扬袂障日,而望所思。’以‘扬袂障日’解‘’字,尤明白。韩文,云阴解,日光穿漏移以解。与字亦切。从人,蔽从草,从日,从。”他博雅的学术作风,并且能够较好的注意到语音、词汇之间的密切关联,在明代是极为难能可贵,值得称颂的。
三、释“查”
卷六十二“查字考”杨慎排比列举了12个用“查”的例子,以证“查”与“槎”的关系,其云:
《说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诧,邪斫也。《国语》“山不槎蘖”是也。今世混用莫知其非,略证数条于此。王子年《拾遗纪》“尧时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贯月查,一曰挂星查。”《道藏歌》诗“扶桑不为查。”王勃诗“涩路拥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犹对仙家,坐菊之宾,尚临清赏。”骆宾王有《浮查诗》,刘道友有《浮查砚赋》,《水经注》“临海江边有查浦”,字并作“查”,至唐人犹然。任希古诗“泛查分写汉。”孟浩然诗“试垂竹竿钓,果得查头鳊。”又云:“土风无缟,乡味有查头。”又云:“桥崩卧查拥,路险垂藤接。”皆用正字,不从俗体。此公匪惟诗律妙,字学亦超矣。杜工部诗:“查上觅张骞”,又“沧海有灵查”。惟七言绝“空爱槎头缩项鳊”、七言律“奉使虚随八月槎”,古体近体不应用字顿殊。盖七言绝与律乃俗夫竞玩,遂肆笔妄改,古体则视为冷局,俗目不击,幸存旧文耳。①
杨慎所运用的排比归纳的方法,为清代这种训诂方法运用的普遍运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肯定杨慎旁征博引的基础上,也应看出杨慎认为“槎”为“查”的俗体,从而境界顿殊,并认为七言绝句与七言律诗都是“俗夫竞玩”的东西,但实际上俗体字对于文字的发展亦有重大的价值。杨慎一类的文人对俗文化往往表现出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但不仅是汉字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智慧对中国文化、思想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总是大于少数精英文人的作用。
四、释“三思”
杨慎的训诂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关键就在于他能够大胆怀疑所谓权威。比如《论语・公冶长》篇的季文子三思一条,杨慎《升庵全集》在卷四十五中,反驳权威,提出“三思”之义,慎云:
季文子相三君,其卒也无衣帛之妾。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左氏侈然称之。黄东发曰:“行父怨归父之谋去三家,至扫四大夫之兵以攻齐。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行父不能讨,反为之再如齐纳赂焉。又帅师城莒之诸郓二邑,以自封植,其为妾马金玉也多矣。是亦公孙弘之布被,王莽之谦恭也。然则小廉乃大不忠之乎,时人皆信之。故曰:“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不然之,曰:“再、斯可矣。”此言微婉。盖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党而纳赂。专权而兴兵,封植以肥己矣”。不得其解者,乃云:“思至于三,则私意起而反惑。”诚如其言,《中庸》所谓“思之不得弗措也。”《管子》所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吴臣劝诸葛恪十思者,皆非矣。然则以三思称季文子者,亦左氏之流也夫。②
在杨慎之前,何晏《论语集解》曾提到“郑曰,文子忠而有贤行。其举事寡过,不必及三思也。”朱熹《论语集注》“程子曰: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讥之。”这两种说法,尤其是朱熹的思想在当时被当作正统思想传播,可以算的上是权威。但是杨慎引《中庸》、《管子》反驳这种正统权威。根据《论语》原文看,郑说,程说不免胶瑟。相比之下,杨慎的有力地反驳更贴近夫子本意。后李贽《火焚》、张燧《千百年眼》都因袭杨慎之观点,李炳南《论语讲要》也认为杨慎此说可从,这是不无道理的。
总之,杨慎《升庵全集》对典籍著作中的字词的训释多能作出较为清晰的解释,且能利用科学的排比归纳的考据方法,这些对具体词义的考据和训诂考据学的发展都是意义非凡的。
参考文献
[1] 杨慎.升庵全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2]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乔立智,常青.杨慎《升庵集》对杜诗的考据探论[J].2013,(4)
[4] 杨树达.词诠[M].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二版
[5] 郭在贻.训诂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 李炳南.论语讲要[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注解:
三字经全文及解释范文5
【关键词】初中语文;文言文;“通”“同”; 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2)01-0068-01
在初中语文(2007年苏教版)教材中,用“通”、“同”是等来解释文言文中的用字现象,涉及假借字、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通用字等文字学概念。但每一个术语没有定指,比如“通”有时候指假借,有时候指通假:这无疑给初中的文言文教学增添了一定的困难。如何将这些术语所涉及的字既比较准确又能照顾到初中生的特点讲解出来,做到“深入而浅出”,这是本文讨论的焦点。
要深入浅出地讲解这些文字现象进而通释相关全句句义,首先在教师的心目中对以上提到的文字学概念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假借字指语言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词,但没有文字来记录,于是借用一个和这个词读音相近的字来记录这个词,被借用的字称为假借字。通假字指古人临时写的同音别字。古今字一般指出现有先后、在形体上有相承关系、意义上有内在联系的一组字,先出现的为古字,后出现的为今字。异体字指形体结构不同而意义和读音都相同的字。通用字指在同一个时代里,读音相近、意义相通、而且在当时可以通用的一组字。
其次,要认真分析“通”“同”等术语指的是哪一种文字现象。因为“通”“同”等注释术语并不定指某种文字现象,所以有必要运用文字学的知识,查找文献用例,重新分清这些文字的性质,进而对文义予以确解。本文初步探索了这些用例中的文字现象,也尝试作了一番解释,当然每位老师可以据此再进行考察,以便心中有矩。
下面主要结合初中语文(2007年苏教版)三年级教材,分别从教师备课的角度——深入分析和讲课的角度——浅显讲解两个方面,说说如何讲解初中语文文言文注释中与“通”“同”等有关的用字现象。
一、通假字例
“入则无法家拂士。”拂,同“弼”,辅佐。(九年级下册《孟子二章》) 分析:“拂”本义指拍打而过;“弼”本来有辅正的意思,二字没有意义联系。辅正一义有“弼”字表示,“弼”“拂”同为质部蓝纽字,音同。可见这里“同”指通假。讲解:拂,通假字.本字是“弼”,辅正的意思。另如“具”和“俱”(《岳阳楼记》)、“与”和“欤”(《孟子二章》)、“被”和“披”(《陈涉世家》)都是本字和通假字关系。
二、假借字例
“层层指数,楼愈高,则明愈少;数至八层.裁如星点。”裁,通“才”,仅仅。(苏教版8年级下册诵读欣赏《山市》)分析:“仅仅”一义在古代可以用缦、裁、财、才等字表示,而且这些例子一般均在汉代以来的文献中出现,说明在先秦时代没有文字记录读音与“裁”或“才”相近、意思和仅仅相同的词,后来以音近为原则,借用“裁”“才”等字来表示该意义,这里“通”实指假借。讲解:裁,假借字,借来表示仅仅的意思,后来借用“才”字表示。假借字指语言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词,但没有文字来记录,于是借用一个和这个词读音相近的字来记录这个词,被借用的字称为假借字,如“仅仅”一义本来没有字记录,借用一个读音相同的字“裁”来记录。
三、古今字例
“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益,增加。曾,同“增”。(苏教版九年级下册《孟子二章》) 分析:“曾”的本义指口气上出,穿过透气天窗而散越,所以有增加的意思;“增”本义指增加,二字有内在意义联系。先秦多用“曾”字表示增加的意思,后来则用“增”表示。这里“同”实指古今字关系。讲解:曾,增加的意思,后来用“增”字来表示,“曾”和“增”是古今字关系。另如“属”和“嘱”(《岳阳楼记》)也是古今字关系。
四、异体字例
“小惠末徧,民弗从也。”徧,同“遍”,遍及,普遍。(苏教版九年级下册《曹刿论战》) 分析:“徧”本义指到处,普遍;《广韵》认为“遍”字是“口”的俗字,所以这里的“同”是异体字关系。讲解:徧,遍及、普遍的意思。后来用俗字“遍”表示,二字是异体字关系。
五、通用字例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畔,通“叛”。(苏教版九年级下册《孟子二章》) 分析:“畔”的本义指田界,田界是判分田地的;“叛”本义指闹分裂,二字意义有联系,都是“判”的派生词。二字都从“半”得声,音形皆近。表示“闹分裂”的意思先秦多用“畔”表示,也有用“叛”的例子,所以通用。这里“通”实指同源通用字关系。讲解:畔,和“叛”都有闹分裂、背离的意思,二字属于通用字关系。通用字指读音相近、意义相通、而且在当时可以通用的一组字,如“强(疆)”和“僵”形体、读音相近,在僵硬这一意思上古代可以通用,所以是通用字。另如“辟”和“避” (《鱼我所欲也》)、“辨”和“辩”( 《鱼我所欲也》)都是通用字关系。
【参考文献】
[l]许 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
[2]余遁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3]刘兴均,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三字”问题.中国训诂学研究
会2004年会提交论文。
[4]汉语大字典编纂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1—8卷,四川辞
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1990年。
[5]苏教版初中语文八、九年级课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
【摘 要】在初中语文(2007年苏教版)教材中,用“通”、“同”等来解释文言文中的用字现象,涉及假借字、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通用字等文字学概念。要深入浅出地讲解这些文字现象进而通释相关全句句义,首先在教师的心目中对以上提到的文字学概念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其次,要认真分析“通”“同”等术语指的是哪一种文字现象。第三,要将这些术语所涉及的文字现象及词语意思用浅显易懂的话语讲解出来。
【关键词】初中语文;文言文;“通”“同”; 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2)01-0068-01
在初中语文(2007年苏教版)教材中,用“通”、“同”是等来解释文言文中的用字现象,涉及假借字、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通用字等文字学概念。但每一个术语没有定指,比如“通”有时候指假借,有时候指通假:这无疑给初中的文言文教学增添了一定的困难。如何将这些术语所涉及的字既比较准确又能照顾到初中生的特点讲解出来,做到“深入而浅出”,这是本文讨论的焦点。
要深入浅出地讲解这些文字现象进而通释相关全句句义,首先在教师的心目中对以上提到的文字学概念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假借字指语言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词,但没有文字来记录,于是借用一个和这个词读音相近的字来记录这个词,被借用的字称为假借字。通假字指古人临时写的同音别字。古今字一般指出现有先后、在形体上有相承关系、意义上有内在联系的一组字,先出现的为古字,后出现的为今字。异体字指形体结构不同而意义和读音都相同的字。通用字指在同一个时代里,读音相近、意义相通、而且在当时可以通用的一组字。
其次,要认真分析“通”“同”等术语指的是哪一种文字现象。因为“通”“同”等注释术语并不定指某种文字现象,所以有必要运用文字学的知识,查找文献用例,重新分清这些文字的性质,进而对文义予以确解。本文初步探索了这些用例中的文字现象,也尝试作了一番解释,当然每位老师可以据此再进行考察,以便心中有矩。
下面主要结合初中语文(2007年苏教版)三年级教材,分别从教师备课的角度——深入分析和讲课的角度——浅显讲解两个方面,说说如何讲解初中语文文言文注释中与“通”“同”等有关的用字现象。
一、通假字例
“入则无法家拂士。”拂,同“弼”,辅佐。(九年级下册《孟子二章》) 分析:“拂”本义指拍打而过;“弼”本来有辅正的意思,二字没有意义联系。辅正一义有“弼”字表示,“弼”“拂”同为质部蓝纽字,音同。可见这里“同”指通假。讲解:拂,通假字.本字是“弼”,辅正的意思。另如“具”和“俱”(《岳阳楼记》)、“与”和“欤”(《孟子二章》)、“被”和“披”(《陈涉世家》)都是本字和通假字关系。
二、假借字例
“层层指数,楼愈高,则明愈少;数至八层.裁如星点。”裁,通“才”,仅仅。(苏教版8年级下册诵读欣赏《山市》)分析:“仅仅”一义在古代可以用缦、裁、财、才等字表示,而且这些例子一般均在汉代以来的文献中出现,说明在先秦时代没有文字记录读音与“裁”或“才”相近、意思和仅仅相同的词,后来以音近为原则,借用“裁”“才”等字来表示该意义,这里“通”实指假借。讲解:裁,假借字,借来表示仅仅的意思,后来借用“才”字表示。假借字指语言中已经出现了一个词,但没有文字来记录,于是借用一个和这个词读音相近的字来记录这个词,被借用的字称为假借字,如“仅仅”一义本来没有字记录,借用一个读音相同的字“裁”来记录。
三、古今字例
“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益,增加。曾,同“增”。(苏教版九年级下册《孟子二章》) 分析:“曾”的本义指口气上出,穿过透气天窗而散越,所以有增加的意思;“增”本义指增加,二字有内在意义联系。先秦多用“曾”字表示增加的意思,后来则用“增”表示。这里“同”实指古今字关系。讲解:曾,增加的意思,后来用“增”字来表示,“曾”和“增”是古今字关系。另如“属”和“嘱”(《岳阳楼记》)也是古今字关系。
四、异体字例
“小惠末徧,民弗从也。”徧,同“遍”,遍及,普遍。(苏教版九年级下册《曹刿论战》) 分析:“徧”本义指到处,普遍;《广韵》认为“遍”字是“口”的俗字,所以这里的“同”是异体字关系。讲解:徧,遍及、普遍的意思。后来用俗字“遍”表示,二字是异体字关系。
五、通用字例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畔,通“叛”。(苏教版九年级下册《孟子二章》) 分析:“畔”的本义指田界,田界是判分田地的;“叛”本义指闹分裂,二字意义有联系,都是“判”的派生词。二字都从“半”得声,音形皆近。表示“闹分裂”的意思先秦多用“畔”表示,也有用“叛”的例子,所以通用。这里“通”实指同源通用字关系。讲解:畔,和“叛”都有闹分裂、背离的意思,二字属于通用字关系。通用字指读音相近、意义相通、而且在当时可以通用的一组字,如“强(疆)”和“僵”形体、读音相近,在僵硬这一意思上古代可以通用,所以是通用字。另如“辟”和“避” (《鱼我所欲也》)、“辨”和“辩”( 《鱼我所欲也》)都是通用字关系。
【参考文献】
[l]许 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
[2]余遁永,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3]刘兴均,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三字”问题.中国训诂学研究
会2004年会提交论文。
[4]汉语大字典编纂委员会,汉语大字典.第1—8卷,四川辞
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1990年。
三字经全文及解释范文6
【英文摘要】The supreme judicial organ held to westernization when confliction arose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law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But, traditional rules were still kept partly, because they were accorded with western law, and that the supreme judicial organ compromised to Li and reality reasons was more unimportant. The fact of common principle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law suggested that researching the reasonable ingredient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ranslating western law extremely to leg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关键词】法律冲突;定婚;解释例;民初;大理院
【正文】
在清末修律的浪潮中,西方法制被大规模的引进,由此开启了中国法律转型的进程。如果我们对这一法律移植的过程采取与当事者同样的视角,则我们的研究很难具有反思意识。本文拟对民初大理院处理新旧法律冲突的法律解释过程进行解析,[1]希望能够超越以往法律移植的理论模式,对大理院处理中西法律冲突的解释逻辑及其背后的根由进行重新认识。
一、民初的司法背景与大理院解释例
民国元年(1912年),参议院并未批准援用参酌西方法制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而是确定“嗣后凡有关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律中规定各条办理”,[2]即适用所谓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现行律”即《大清现行刑律》,它是清末修律过程中的一部过渡法,只是对《大清刑律》作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并未改变“旧法”的立法精神。[3]民初的中国社会,“在西潮的冲击下,一方面,法律制度既早在新旧嬗蜕的时期中,整个司法界的人员结构已流动变迁;而在他方面,社会种种制度与人们思想,又方在剧烈的发酵时期内。”[4]可以说,民初新旧法律的冲突已不可避免,只是一部民事“旧”法在“新”时期的援用,更加凸显了此种法律冲突。
在政治紊乱的民国初年,立法机关很少在实际意义上存在,更遑论有效地发挥作用,惟有“司法机关比较特殊,从上到下的联系相当紧密,直接受到政潮的影响很小”。[5]所以,尽管民初法律冲突的处理在立法上不能有效地进行,仍可依赖于司法机制。民国之初,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院长有权对于统一解释法令作出必应的处置”。[6]于是,大理院因法律解释之责首当其冲地面对实际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法律冲突问题。由于1928-1929年仿照德国民法典的正式民法颁布后,民国时期的法律冲突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文仅把讨论的时间限定在民初,即1912-1927年。
在当时的新旧法律冲突中,最为典型的是婚姻领域。因为传统律条和习俗在婚姻领域的影响非常坚韧,本土色彩浓厚的定婚制度尤其如此。在中西法律交汇的当口,法律冲突在定婚制度中的表现值得我们深究。民国时期的解释例反映了当时法律生活的生动场景,材料保留也相当完整,但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7]民国时代的法律家郭卫曾将1912-1946年所有的解释例进行汇编,其中1912-1927年的解释例编为《大理院解释例全文》(全一册),收录民国元年到民国十六年的大理院全部解释例(惟缺漏统字第1888号),由统字第1号至统字第2012号止。[8]“现行律”虽然是一部旧律,但的确是当时办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渊源。下面以“现行律”为,通过分析大理院众推事对其的遵循或背离,来观察民初司法当局对新旧法律冲突(或曰中西法律冲突)的立场,以及大理院解释立场背后的理论意义。
二、解释例中的定婚问题
大理院涉及定婚问题的解释例,大致可分为婚约、犯奸盗悔婚、无故悔婚、患疾悔婚和再许他人五个问题,下文将对它们进行分类解析。[9]
(一)婚约问题
关于婚约问题,“现行律”并无明确规定。依照“现行律”《男女婚姻》条:“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谓先已知夫身残疾、老幼、庶出之类。)而辄悔者,(女家主婚人)处五等罚;(其女归本夫。)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10]仅就律文观之,婚书和聘财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辄悔;律文并未明言凡结婚者须先定婚。然而,结婚在儒家礼义中须遵循“六礼”始能算完备,至少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11]否则便“名不正,言不顺”。而“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就是定婚的核心内容,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就是婚书和聘财。
应该说,在民国以前,关于婚约的问题并无疑义。惟民国以后,西风东渐,婚约似乎成了“不合时宜”的产物。统字第1353号解释例有案:某男走失多年,其未婚之妻后来为了避乱,移住其家近十年,除所住房屋外,衣食皆由母家供给。未婚夫无父母,与弟早分炊,临走时口头嘱托他人代管家产。该女不愿改嫁,盼未婚夫归家成婚或为其守志立嗣,请求兼管遗产被拒绝而涉诉。大理院答复:其既定有正式婚约,移住夫家后又愿为守志之妇,自应准其为夫择继,并代夫或其嗣子保管遗产。[12]又有统字第1900号解释例也称:“民诉条例所称‘婚姻’应包括婚约在内。”[13]很明显,这两条解释例是依照“现行律”所作的历史解释。因为在儒家礼义中,定婚(或婚约)当然属于婚姻的范畴,而且结婚必须先定婚。这是无须明言的题中之义,所以律文没有言明。此外,统字第1357号解释例中,大理院复司法部有关结婚法律:婚姻须先有定婚契约(但以妾改正为妻者不在此限),定婚以交换婚书或依礼交纳聘财为要件,但婚书与聘财并不拘形式及种类。[14]这除了对婚约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外,还赋予相关婚俗以广泛的生存空间和法律效力。
(二)犯奸盗悔婚问题
“现行律”禁止悔婚,但规定:“其未成婚男女,有犯奸盗者,(男子有犯,听女别嫁。女子有犯,听男别娶。如定婚未曾过门私下奸通,男女各处十等罚,免其离异。)不用此律。”[15]很明显,犯奸盗悔婚,律有明文,本无疑义,也属民国时代的“新问题”。
解释例所涉案情,也基本在律文规定的范围之内。比如,统字第483号解释例:有未成婚男子犯窃盗被处刑,女家悔婚另嫁被诉,问应如何办理。大理院答复:现行律“男女婚姻”条本有禁止悔婚明文,但未成婚男子犯奸盗听女别嫁。此案应准许悔婚。[16]很明显,第483号解释例依据“现行律”直接适用。又有统字第1744号解释例:未婚男子犯杀人罪被处徒刑,女方因刑期极长不能久待,请求解除婚约,问是否合法。大理院答复:现行律载,未成婚男女犯奸盗者,男子有犯听女别嫁,女子有犯听男别娶;又期约五年无过不娶及夫逃亡三年不还者,听经官给照别行改嫁。凡有破廉耻之罪与奸盗相似或被处刑三年以上依类推解释,均应许一造请求解除婚约。[17]此案中虽是未婚男子犯罪,但并非奸盗,而是杀人罪,“现行律”并无直接条款可以适用。从解释例来看,大理院并没有直接依照犯奸盗律文类推,而是将犯杀人罪并刑期极长两种因素都考虑进来,犯杀人罪比照犯奸盗,紧扣该条之立法精神——“破廉耻”,将刑期极长比照定婚男子过期不娶和夫逃亡三年不还,也甚符合“现行律”救济受不实夫妻名分拖累之女子的立法本意。
(三)无故悔婚问题
无故悔婚,“现行律”也有明文:“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谓先已知夫身残疾、老幼、庶养之类。)而辄悔者,(女家主婚人)处五等罚;(其女归本夫。)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18]女子定婚而悔,除女家主婚人受刑罚之外,仍要强制结婚——“其女归本夫”。
统字第510号解释例涉及定婚之女以死抗婚,请求裁决。大理院答复:既定婚则有结婚之义务,惟外国法理认为此种义务不能强制履行,即使强制执行亦未必能达判决之目的,我国国情虽有不同而事理则不无一致。现行律婚姻条虽然有效但刑罚条文已经失效,所以只能和平劝谕,别无他法。[19]统字第723号解释例也表示,无故悔婚虽然不法,但婚姻不得强制执行。[20]这两条解释例所反映的问题依当时当然的民事规则——“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明显有法可循。大理院在处理此案时,一方面确认定婚便有“结婚之义务”,另一方面却援引外国法理认为此种义务“不能强制履行”。
又有统字第1934号解释例:未婚夫以聘妻之父为被告(声明不告聘妻),以婚约成立为理由诉令被告履行婚约,高等法院请示是否准理。大理院答复可以审理。[21]此解释例问及聘妻之父可否为履行婚约之诉的被告,这大致包含三个问题:甲、聘妻之父可否为被告;乙、履行婚约之责任人是否在聘妻之父;丙、履行婚约可否被诉。关于甲问题,告聘妻之父属儒家之干名犯义,今大理院准许以聘妻之父为被告,乃有以西方平等之风修正儒家“尊尊”之意。再说乙问题,“现行律”《男女婚姻》条规定,如果无故悔婚,女家主婚人要受责罚,由此而论,此案中聘妻之父负有履行婚姻之责任。再说丙问题,履行婚约可否被诉在古代似乎不成其为问题,一是因悔婚涉诉并不鲜见,且律有明文;二是因为古代婚姻履行可强制执行,诉讼可以有补于实际。但是民国以来,大理院已经确认定婚虽有结婚之义务,但婚姻履行不可强制执行。那么,此时(民国十四年)是否仍然可诉?大理院仍准许审理。这其中的逻辑应该是聘妻之父负有履行婚约之义务,虽婚姻履行不能强制执行,但其应当为此承担民事责任。
(四)患疾悔婚问题
患疾悔婚,“现行律”《男女婚姻》条有文:“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或)有残(或废)、疾(病)、老、幼、庶出、过房(同宗)、乞养(异姓)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不愿即止,愿者同媒妁)写立婚书,依礼聘嫁。”[22]同时亦有:“若为婚而女家枉冒者,(主婚人)处八等罚,(谓如女残疾,却令姊妹相见,后却以残疾女成婚之类。)追还财礼。男家枉冒者,加一等,(谓如与亲男定婚,却与义男成婚。又如男有残疾,却令兄弟枉冒相见,后却以残疾男成婚之类。)不追财礼。未成婚者,仍依原定。(所枉冒相见之无疾兄弟、姊妹及亲生子为婚,如枉冒相见男女先已聘许他人,或已经配有家室者,不在仍依原定之限。)已成婚者,离异。”[23]根据律文可知,定婚时若男女患疾必须明白通知,各从所愿,隐瞒实情枉冒为婚,应予离异。但对定婚后患疾并无规定。
先说定婚时患疾。统字第232号解释例,某男系天阉,某女不知与其结婚,发现后得请离异否。大理院答复:依现行律男女定婚,若有残疾务必明白通知,枉冒已成婚者,应准离异。[24]类似的解释例还有一条,统字第1031号解释例,定婚后,得知男为天阉,女方欲悔婚。大理院答复:此情形为残废,按现行律“男女婚姻”各条办理。[25]这两条解释例皆是一方在定婚时隐瞒患疾事实,大理院依照“现行律”进行处理。
定婚后患疾的解释例有三条。统字第588号解释例问及:定婚后,女子患癫痫屡医不治,未婚夫能否据以撤销婚约。大理院答复:查癫痫程度如系重大可撤销。[26]另有统字第1248号解释例,提请解释者二:一是“现行律”《男女婚姻》条载,“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其女归本服”,文中“及”作“并”字解抑作“或”字解。二是定婚后若一方出现残疾是否允许悔婚。大理院答复:查定婚需凭媒妁,写立婚书或依礼收受聘财始为有效,不得仅有私约。律文所言私约是指对于特别事项之约定而言,即残疾老幼庶养之类须特别告之,经双方合意并立婚书或受聘财之后不许翻悔。若事故在前,定婚时未经特别告知经其同意,则虽已立婚书交聘财并已成婚亦准撤销;若定婚后成婚前一造身体确已发生重大变故,应令其再行通知,如有不愿应准解除婚约;若已成婚则应适用一般无效撤销及离婚之法则。[27]类似的解释例还有统字第1584号解释例:定婚后,男患疯癫程度颇重,并未通知相对人,相对人闻知后将女另许被诉。大理院答复:查男女一造于定婚后若罹残疾,当各从相对人所愿,不得强令继续。来函罹疾一造既违背通知之义务,自不能以他造未经声明解除仍请履行婚约而禁其别字。[28]
以上三条解释例都涉及定婚后患疾的问题,此种情形“现行律”并无明确规定。大理院认为若定婚后成婚前一造身体确已发生重大变故,应令其再行通知,如有不愿应准解除婚约;若已成婚则应适用一般无效撤销及离婚之法则。这种解释背后的逻辑应当是体察“现行律”相关律文的立法本意,认为是否愿意同已知患疾之人为婚应尊重男女两家的意愿。因此,即使定婚后患疾,亦应与定婚之前相同,使对方明白易知。大理院引入西方法学话语,以“通知之义务”表述此种行为,相当贴切。
(五)再许他人问题
再许他人,“现行律”有明文规定:“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女家主婚人)处七等罚;已成婚者处八等罚。后定娶者(男家)知情,(主婚人)与(女家)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给后定娶之人。)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而再聘)者,罪亦如之,(仍令娶前女,后聘听其别嫁。)不追财礼。”[29]由此看来,再许他人也本不成为问题。
有关再许他人的解释例共有五条,其中有两条涉及抢婚。比如统字第471号解释例:一女两聘,男方率众抢回完娶,他日该女之父抢女未果,为泄愤率众烧毁柴薪被诉。大理院答复:男方抢婚不得谓无罪,以略诱论。女家之父仅负民事责任。[30]又有统字第906号解释例,某童养媳不堪虐待而逃,未婚夫家长自愿退婚。该女改聘待嫁之际,前夫归家反对其父先前退婚主张而抢婚,后夫闻讯也退婚,问前婚是否有效。大理院答复:子若成年,其父母之退婚未得其同意者,其退婚不为有效。抢婚虽有干禁例,但依律尚难据为撤销婚约之原因;若有强奸行为,应准离异。[31]这两条解释例,前一条解释例并未讨论抢婚对婚姻效力的影响,后一条解释例则认为抢婚虽有干禁例,“但依律尚难据为撤销婚约之原因”。很明显,这一解释是严格依照现行律作出的。
再来看其余三条有关再许他人的解释例。统字第914号,某人外出,其童养之妻被另聘他人,已成婚十月,前夫归家后控诉到案。由于前夫坚持追还完聚,而该妇成婚既久,恐强制执行有意外之虞,问如何处断。大理院答复:女子再许他人,按律应归前夫。然该女愿归后夫,因婚姻案件不能强制执行,若劝谕前夫不成,可倍追财礼,令女从后夫。[32]另有统字第986号,某父悔婚,败诉后为聘财将女另嫁,是否构成欺诈罪,维持前婚约之判决是否有效。大理院答复:父悔婚将女另嫁,虽志在得财,但不得为诈欺罪;婚姻案件虽不得强制执行,但效力尤在。受确定判决之人本得对于违背判决另定之婚约,请求撤销或另求赔偿以代原约之履行。如果提起撤销重定婚约之诉,审判衙门可适用现行律“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归后夫”条妥善办理。[33]还有统字第1188号,祖父将孙女两聘,先聘之夫兼祧三房已娶两房,问如何处断。大理院答复:先聘之夫既不能重为婚姻,应准撤销,将女断归后夫,其给付之聘金依不法给付原则不能请求返还。若女初愿为妾,可认为前约为聘妾之约并非定婚,尚属有效;若后聘之婚并未征得该女同意,亦准其撤销。[34]
第1188号解释例虽涉及再许他人,但先聘之夫兼祧三房已娶两房,大理院以不能重为婚姻为由否定其定婚效力,同时认为后聘之婚未经该女自愿亦可撤销。同样,第914号和第986号解释例也依据“现行律”认为,再许他人,女归前夫。但是,按照西法认为婚姻案件不能强制执行,惟有劝谕前夫依现行律追偿,只是后例解释更为详细。大理院在第986号解释例的处理中,认可了“婚姻案件不能强制执行”的西方法理,在这个问题上修正了“现行律”的立场。大理院沿着西方法的逻辑,认为该案件虽不能强制执行,但是判决依然具有效力,“受确定判决之人,本得对于违背判决另定之婚约请求撤销,或另求赔偿以代原约履行”。前夫可以请求撤销后婚,也可以另求赔偿以代原约履,这实际上是“现行律”对再许他人问题的处理。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五类定婚问题中,“现行律”除了对婚约问题无需规定,且对犯疾悔婚中定婚后犯疾这一情形并未明确之外,对于其余问题基本上都有法律明文。大理院在作出解释的过程中,不仅承认婚约的效力,而且对各类悔婚问题都依照“现行律”予以禁止,惟依据西方法理认为婚姻义务“不能强制履行”。
三、会通中西——立场折衷还是法意使然?
前文梳理了有关定婚问题的所有解释例,对大理院如何处理定婚有了基本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描述大理院面对中西法律冲突时的基本立场,并试图对大理院处理中西法律冲突背后的根由进行重新认识。
先看大理院的基本立场。如前所述,本文所涉定婚问题中,“现行律” 除了对婚约问题无需规定,且对犯疾悔婚中定婚后犯疾这一情形并未明确之外,对于其余问题基本上都有明确规定。既然这些问题大多在传统礼法上并无疑义,却仍然被提请解释,大理院也并没有驳回,这本身就说明传统礼法在民国建立以后遭到了司法阶层的普遍质疑。在大理院的解释过程中,西方法被大量的接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在用语方面,“义务”、“强制履行”、“不法给付”、“无效撤销”等西方法学术语被陆续引入,逐渐替代传统判语,显示出西方法渗透的明显表征。其二,西方法的原则被直接引入作为大理院解释的理论前提。在处理悔婚问题时大理院解释说,既定婚则有“结婚之义务”,惟外国法理认为此种义务“不能强制履行”。这条西方法律原则成为处理传统定婚案件的重要法律依据。不难想象,在革旧鼎新的民国初年,中国旧法早已成为众矢之的,而大理院诸君大多游学国外,浸润西法,站在时代潮流的当口,他们以缔造新法的热忱,引进西方法的术语和原则改造中国传统礼法的行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35]
虽然大理院力图用新法改造旧法,但是,大理院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实际上保留了大部分传统礼法。在无故悔婚和再许他人的问题上,大理院认为“现行律”有禁止悔婚明文,认为既定婚则有结婚之义务;在犯奸盗悔婚问题上,大理院依照“现行律”准许犯奸盗的相对方悔婚;在患疾悔婚问题上,大理院依照“现行律”明白通知,各从所愿的法意,准许隐瞒患疾的相对方离异。虽然在悔婚问题上,大理院始终坚持婚姻案件不能强制执行的西法原则,但在个案中也明确表示原约“效力尤在”,“受确定判决之人,本得对于违背判决另定之婚约请求撤销,或另求赔偿以代原约履行”。可以说,在定婚问题上,大理院的处理与现行律的规定差别不大。
一方面,西方的法律术语和法律原则广泛渗透到大理院的解释之中。而另一方面,大理院处理定婚问题时却保留了大部分旧法。为何会如此?当我们回头检视与大理院处理结果基本一致的“现行律”条文,或许会趋近事实本身。“现行律”《男女婚姻》条有文:“凡男女定婚之初,若(或)有残(或废)、疾(病)、老幼、庶出、过房(同宗)、乞养(异姓)者,务要两家明白通知,各从所愿,(不愿即止,愿者同媒妁)写立婚书,依礼聘嫁。若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谓先已知夫身残疾、老幼、庶养之类)而辄悔者,(女家主婚人)处五等罚,(其女归本夫);虽无婚书但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女家主婚人)处七等罚;已成婚者处八等罚。后定娶者(男家)知情,(主婚人)与(女家)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给后定娶之人。)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而再聘)者,罪亦如之,(仍令娶前女,后聘听其别嫁。)不追财礼。”“其未成婚男女有犯奸盗者,(男子有犯,听女别嫁。女子有犯,听男别娶。如定婚未曾过门私下奸通,男女各处十等罚,免其离异。)不用此律。”细绎律文,我们发现,在定婚之初,“现行律”奉行的原则是明白通知,各从所愿——西方法可以表述为诚实信用原则和自愿原则;对辄悔和再许他人者进行处罚,对知情而娶者财礼入官,不知者追还财礼则是出于朴素的报偿观念——西方法可以表述为过错责任原则;对于女归前夫而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这与大理院准许另求赔偿的西式处理更是如出一辙,可以理解为公平原则。如此看来,大理院在定婚问题上保留部分旧法,与其说是基于礼俗和现实而采取的立场折衷,还不如说是基于西方法而做出的价值选择。
以西方法作为参照系来审视中国固有法是百年来我们一直在走的路,甚至大理院的法律解释也是这种思维模式下的产物。倘若我们换一种视角,当我们在讨论中国法律转型问题中的西方因素时,去思考“一方如何使另一方显得更清楚,而不是假定(无论多么含蓄)此方或彼方的优越性,或试图坚持他们完全等同。”[36]仅仅将西方法视为一个相对的他者,或许我们更能有所收获。尽管大理院的选择是以西方法作为参照系的,但是如果我们放弃立场倾向而作一种冷静的考察,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法并非像遵循“类型学”路径的学者认为的那样简单和程式化,[37]仅仅用“等级”、“伦理”、“血缘”、“宗法”等化约语汇并不能恰当地描述它们。传统中国社会确实缺乏自由价值足够的空间,但是,作为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社会组织,秩序始终是其最重要的考量。从孔子的“言必信,行必果”到商君的“徙木立信”,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到法家的“罚当其罪”、到儒家的“投桃报李”以及佛家的“因果报应”,诚信、报偿和公平等观念在传统中国社会一再地被宣扬。尽管中国古代社会的确等级分明,但是同阶层之人的交互行为仍然是全部社会行为中的大部分,在同等人之间,社会行为的等级因素相对淡化,而规则的作用则被凸显。虽然“血缘”、“宗法”和“伦理”一直被视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规则之元,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人们长期处在一种“水淹至颈”的生存状态之中,[38]血缘亲情与宗法伦理可能并不一定比公平交易的生存规则更为重要。当我们以一种微观的视角去考察固有中国法时,我们会发现经由华夏先民几千年生活经验沉淀下来的法则本身具有深刻的合理性——不仅具有“经验合理性”而且具有“价值合理性”。[39]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法律而言,挖掘传统规则中的合理性因素可能比进行法律移植更为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模范西方”,最终可能只是落个“得形忘意”的尴尬下场。[40]
【注释】
[1] 法律冲突本为国际私法上的概念,原指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由于不同国家对同一问题的规则不同,因而产生的有关国家对同一民商事问题的法律规则之间相互冲突。但在当前的法学界中,“法律冲突”这个概念经常被用来讨论同一国家内部不同规则之间的相互冲突。如蔡定剑:《法律冲突及其解决的途径》,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范忠信、侯猛:《法律冲突问题的法理认识》,载《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本文的“法律冲突”是从中西法律整体上的异质而言的,并不意味着中西法律之间所有具体制度的对立和矛盾。另外,本文所称“新法”指的是清末以来力图引入的西方法;“旧法”指的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法律。“新法”、“旧法”与“西法”、“中法”意义相同,可以互换。“新”、“旧”仅指称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并不包含价值上的优劣。
[2] 罗志渊:《近代中国法制演变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252页。
[3] “现行律”的旧法性质,学界一再申说,江庸先生曾一语道破:“是书仅删繁就简,除消除六曹旧目而外,与《大清律》根本主义无甚出入”,见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2页。
[4] 黄源盛:《民初大理院(1912-1928)》,载《政大法学评论》第六十期, 第139页。
[5]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版,上册“例言”。
[6] 详见民国四年六月公布的《修正法院编制法》第三十三条,载《大清法规大全》,“法律部”,卷4,宪政编查馆辑。
[7] 目前学界尚无以解释例为主要材料的研究,台湾学者黄源盛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最为充分,代表成果参见《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1912-1928),(台北)政治大学法学丛书编辑委员会2000年版;引用少量解释例为材料的研究有黄宗智:《法典 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卢静仪:《民初立嗣问题的法律与裁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张生:《民国初期民法的近代化——以固有法与继受法的整合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李卫东:《民初民法中的民事习惯与习惯法——观念 文本和实践》,中国知网“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赵晓耕、马晓莉:《于激变中求稳实之法——民国最高法院关于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解释例研究》,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5年5月。
[8] 郭氏毕业于北洋大学法科,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大理院推事。郭氏所编解释例由上海法学编译社分次出版,会文堂新记书局发行。本文所据之解释例皆引自此《大理院解释例全文》(民国二十一年七月版)。
[9] 文中所据之材料皆为笔者对原文的整理,但在用语上力求保持原貌。由于实际案件复杂多样,为了分析的方便,案件分类并不遵循严格的逻辑,各子类可能并不构成周延的总类。
[10] 《大清现行刑律按语》,“婚姻门”,第3页。本文所据“现行律”律文皆出自《大清现行刑律按语》,《按语》为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版本,无著者、出版地和出版日期。
[11] 语出《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后成为中国婚姻相沿数千年之礼俗。
[12]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195页。
[13]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1100页。
[14]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797-798页。
[15] 同前引《大清现行刑律按语》。
[16]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271页。
[17]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1007-1008页。
[18] 同前引《大清现行刑律按语》。
[19]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285-286页。
[20]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397页。
[21]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1123-1124页。
[22] 见前引《大清现行刑律按语》。
[23] 同前引《大清现行刑律按语》。
[24]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152-153页。
[25]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584页。
[26]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326页。
[27]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722页。
[28]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920-921页。
[29] 同前引《大清现行刑律按语》。
[30]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264-265页。
[31]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498-499页。
[32]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506-507页。
[33]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550-551页。
[34] 《大理院解释例全文》,第679-680页。
[35] 从黄源盛先生整理的《民国大理院历任院长及推事略历一览表》可以看到,在有学历记录的49人之中,就有38人有过留学的经历,大理院推事的西学背景可见一斑。该表为前引黄源盛文所附,数据为笔者统计。
[36] 同前引黄宗智著,“导论”。
[37] 对马克斯·韦伯“类型学”方法的反思,参见陈景良:《反思法律史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载《法商研究》2004年第5期。
[38] 斯格特在《农民的伦理经济》一书中将小农经济下农民的生存状态描述为“水淹至颈”,即“像一个男子不得不长久地站在深至脖颈的水中,即使只是小小的风浪也可能使他溺死。”参见J·C·Scott ,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