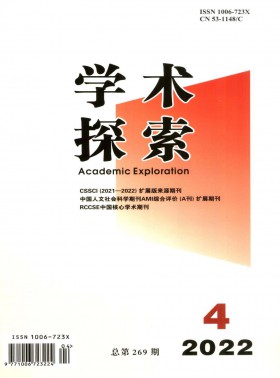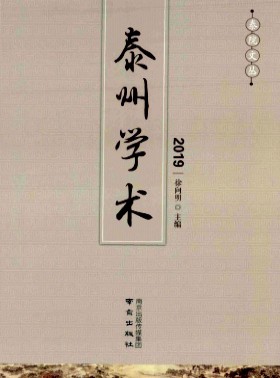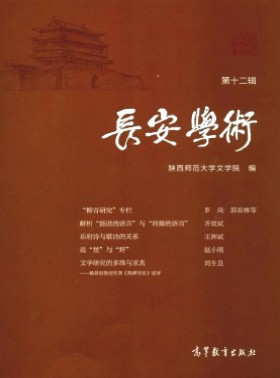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刘秉忠学术对文学思想的重要性,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尹红霞 单位:邢台学院中文系
一个时代的文化思想和时代精神常常濡染甚至决定该时代的文学思想及创作的风貌与走向,这恐怕是不争的事实。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状况不可不涉及其学术思潮,同理,研究一个作家,尤其是兼为学者的作家,其学术思想对其文学思想甚至有导向性的影响,因此,研究刘秉忠的文学,我们亦不能不论及其学术及其学术于文学的影响。
刘秉忠学术多承邵雍之学,关于邵雍《皇极经世书》,邵伯温有云:“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焉。”它是一种依托于《易》而作自圆之发挥的象数思想体系,是邵雍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刘秉忠思想受邵氏哲学思想影响之处,主要在于其认识论。邵雍提出了“以物观物”的认识方法,其于《皇极经世一观物内篇》中认为,一般人观物方式是“以我观物”,不免“溺于情好”,而圣人观物:“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而观之以理也”,“物”与“我”应是“两不相伤”:“观物之乐,复有万万者焉。虽生死荣辱转战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则何异四时风花雪月一过乎眼也。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耳一如盆之应形,如钟之应声一因静照物一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伊川击壤集》自序)于认识论意义上,便是保证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这两体各自的独立不受侵伤。这种认识方式也代表了北宋以来受科技水平发展的影响而形成的一股认识的理性思潮,这种理性包含有两点一是造物有不变之理的客观理性,一是反对“我自怀私”的主观理性。刘秉忠“闲来与物少相碍”、‘,险事若私先有碍”之语,亦是此意。
这种认识论影响到文学上,最重要的是于文学的审美观趋向的导向作用:邵雍虽然认为孔子删诗“盖垂训之道,善恶明著者存焉耳”,但同时又反对“时之否泰,出于爱憎”即以主观认识去评价社会,而提倡“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这实际上不窗在暗中消解了诗歌存“善恶”的精神和标准,对现实采取的是一种超脱的态度,这就显然流露出道、释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色彩。受邵雍影响甚深的朱熹文学观虽强调诗人主观动机要合于所谓“性情之正”,但朱熹实际上连所谓的“陈善闭邪”的诗亦不大主张作,而是偏爱吟咏性情之作,其在《清邃阁论诗》中明言“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其真味发溢,却又与寻常好吟者不同。”剥开其道学气之表层,其中对“适怀”的构思方式以及“平淡自摄”、“真味发溢”的艺术效果的津津乐道,显见道家“自然为真”艺术观的投影。至于陆学派,更是注重于“自然本心”、“天机自然”的体悟,其重要学者包恢就以“自然”为其文学观的核心,他所谓“冲漠有际,冥会无迹”,正是道家艺术观的阐说,而“真景在前”、“空中之音,相中之色”(《答傅当可论诗》)的特点,则又可见由佛教“取境”学说移植过来的意境论的表述。“皆因彼之自尔,而我无所与”的这种观点,当其显示在审美观照与艺术创作的领域时,必然就有了勿以主观相干扰的模仿美学意识。邵雍“观物”思想及其影响下的一些文学观念是和苏轼等人体察以传神的艺术思想是完全接轨的。不难看出,由邵雍认识论影响下的宋学家不约而同的于“自然”的认同趋向,刘秉忠文学邢台学院学报审美的最高理想亦是以“自然”为宗。
应当指出的是,刘秉忠受释道影响较深,没有受到程朱理学的熏陶,其文学就不曾笼罩那种浓浓的所谓的“道学气”,因而我们从他的文学作品绝少看到有关义理的说教,同时,这种“自然”与前朝历代诸如代表性作家陶渊明等所体现的艺术追求之“自然”亦不相同,其中,更多了一点哲人的理思,少了一点诗人体验下的“真趣”。这也是刘秉忠诗论虽以“自然”为宗,但具体诗歌的创作仍然缺少一份灵动的神韵,原因亦正在于此。这种理性意识影响到审美观照的对象,对象本身的形象特征便成为作家关注的次要点,而关注的焦点却在对象本身所寓含之理.如邵雍《题黄河》“谁言为利多于害,我谓长浑未始清。西至昆仑东至海,其间多少不平声。”此诗本为题咏黄河,却略去黄河本身,别出心机,寓以丰富的理性内涵,发人深思。影响到文学具体创作上,便使得文学创作取材多以直接或间接表达自然之理、人生之理为主,刘秉忠诗歌所包含的深厚的理性意蕴,正说明了这一点.其实,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论宗”,经魏晋玄言,隋唐道释,以理为诗的现象于中国诗史自有其发展之轨迹。邵雍即明以继承陶诗为己任“可怜六百余年外,复有闲人继后尘”,然而,邵雍诗歌并不同于陶诗,如果说陶诗之中所包含的还是一种艺术化的未以言明的“真意”的话,邵雍诗歌却是一种直抒胸臆的浅切表白,其“兴来如宿构,未始用雕镌”(《谈诗吟》)的创作亦不同于陶诗的“天然去雕饰”的诗作,而邵诗的理性更浓,艺术魅力却欠缺不少,哲人于诗,是把哲理诗化了,诗人作品中的哲思,却是真切体验下不自觉流露出的“真意”,因而更富艺术魅力。苏轼是难得的哲人和伟大诗人的结合,刘秉忠论诗于艺术上多承苏轼之论,也正因他并非如邵雍等那种特定意义上的“哲人”,诗作虽亦言理,然其亦注重艺术表现如语言表达上的锤炼等,这是其与邵雍不同之处。
可以说,刘秉忠于文学审美理想与审美观照上及至在具体文学创作中,都可见邵雍“观物”思想于其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影响,这正是我们探讨刘秉忠的文学,而又必须于其学术进行观照的一个原因。另外,邵雍之学中体现的文学价值观亦影响了刘秉忠于文学价值的认识。邢怒《伊力l击壤集后序》云:“以先天地为宗,以皇极经世为业,揭而为图,萃而成书。其论世尚友,乃直以尧舜之事而为师。其发为文章者,盖特先生之遗余,至于形于咏歌,声而成诗者,又其文章之余”,可见邵雍之学,视文章如“遗余”,而诗歌是“文章之余”,其地位更是等而下之了,邵雍之后的理学家们多承此意,这是与文士们不同的。#p#分页标题#e#
金末元初,苏学盛于北,北方文人是重文的,王悻《遗山先生口诲》中,作为北方宗师的元好问谈及文章功用说:“千金之贵莫逾于卿相,卿相者一时之权,文章千古事业,如日星昭回,经纬天度,不可少易。”这种观念在北方文人中深入人心,如刘因、郝经等即虽受程朱之学影响之人亦秉承此念。然而,刘秉忠却说“文艺属游泳,道义长推尊”、“吟写总为闲伎俩,且将消遣日长天”,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到文学的具体创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创作态度,在创作态度上提倡以逸驭劳,有道是:“晋宋间诗多闲淡,杜工部等诗常忙了,陶云:‘身有余劳,心有常闲’,乃《礼记》身劳而心闲则为之也”,非谓忙中偷闲,而是浑然全体之闲适自在,从容不迫、平心静气。表现于外者是平和闲雅,如秉忠所谓“自然闲雅贵天资”,精蕴于内者是闲淡虚静,又如秉忠所谓“谁信道人心似水,无时无节不澄清”。二是情感基调,由于其是“闲情以自适”,所吟咏抒发的是自己的闲情逸致,取材不涉及社会现实的揭露批判:“山有岚光水有声,得闲便是大功名。彼长然觉此为短,我圣未知人所轻。几树好花风乍静,一钩新月雨初晴。此心只合长无事,莫为人间宠辱惊。”其情感的抒发便纤徐闲适。我们欣赏刘秉忠文学作品时,会更加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总之,刘秉忠的学术于其文学观的重要方面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导向性作用。因此,我们探讨其文学的同时,于其学术也作观照,这样,我们就可以以一个更为全面的角度来审视和评论刘秉忠的文学,可以更正确地理解其作品及其于其时所表现出的独特特色。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刘秉忠的诗论重在艺术的角度,其表层更多体现的是于苏轼的某些文学观念的继承或释家论诗的一些主张,但是,其文学的总体精神的底蕴却离不开我们上文所言及的学术于其的这些影响。可以说,刘秉忠的诗论是将其文学审美理想付诸具体实施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