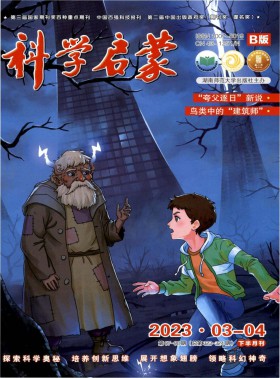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启蒙与文学的契合关系,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在广大中国人民的焦虑和探索中,启蒙并非以完全本色的面貌且多少有些匆忙的出场,在缺乏长久的铺垫和积蓄力量的境遇中,在中国的大地上留下一段并不长远的坎坷曲折的印迹。在中国特定历史和文化语境下,启蒙的遭遇启示我们需要深刻的思想力度与坚定的“生命回归”的守望,以澄清启蒙的源头及其指向。当真正廓清了启蒙的内涵与指向,诸如有关启蒙阐释过程中概念的偷换、固有思维模式的禁锢等等问题都会得到清晰的揭示,对于启蒙自然会得到更透彻和准确的审视与把握。 如果说启蒙存在一个终极的精神指向,那就是生命的自由。而鲁迅是真正领悟了启蒙实质精神的一位思想者,他从实现“自我启蒙”看见自身开始,义无反顾地走向生命的回归。鲁迅以他的文学印证了文学与启蒙精神的深度契合。但是鲁迅的文学也以它的丰富和特别,超出了仅仅“启蒙主义”这样粗略的概括和界定。在他文字的下面深深镌刻的是他不无悲痛的守望与愤然前行的背影。 在我们民族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漫漫启蒙之路后,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在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运行模式中,对启蒙的正本清源,及其与文学关系的深入把握,仍然十分有必要和有价值。具有深刻生命有限性体验的鲁迅和具有高度自省精神的鲁迅的文字,无疑是更可信的。 一 根据康德的阐释,启蒙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P1),即唤醒自我对自身蒙昧的自觉,从而走向“成熟状态”。换句话说,启蒙是源于自身并指向自身的。相对照之下,启蒙在中国的被解释被传达都与此有很大的差别。在惯性的思维逻辑下,启蒙一般被理解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教化式的知识传输和指导启发,这仍是落于封建统治思维模式的窠臼。 启蒙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作为不断重新审视世界、审视自己的生命自觉状态,是始终保持对固有思维模式的反思,从而维护生命本源性的自由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启蒙是一种回归:重新获得祛文化化的生命状态和思维视野,跳出一切桎梏的牢笼,还生命以澄明,反思自身被建构的历史。所以说启蒙不是一部分人针对另一部分人,不是从上到下,不是主流意识对民间意识,不是精英意识对大众意识;也不是针对某个历史阶段,或是某个特殊的群体……正如康德所说:“启蒙运动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1](P3) 启蒙不是要传输某种知识、某种主义,传播某种理论,而是回到生命的本初,自己把自己照亮。所谓知识分子先觉者的启蒙主体、人民大众作为启蒙对象等等这样的认识,本身就是对启蒙精神的庸俗化理解和把握,意识深层仍是对人类整体做出区别对待的固守。众多的限定性术语,如审美启蒙、革命启蒙、阶级启蒙、政治启蒙、民族启蒙、个人启蒙等等,如此繁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启蒙本身变得模糊,逐渐偏离了启蒙的根本性内涵,拆解了对启蒙的整体性把握、在特定领域的取舍,不可避免地造成某种误解或是遮蔽,始终不能脱离庸俗化的实用主义的思维逻辑,很有可能导致新的蒙昧,反而走向了启蒙的对立面。启蒙需要个体生命,突破内化为无意识的思维结构和范畴界定,以避免启蒙在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障碍面前搁浅。真正的启蒙只有一个,而且是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 二 在中国的思想史及文学史上,启蒙已经成为鲁迅及其文学的重要标签。然而对鲁迅及其文学与“启蒙主义”之间做一个直接的概括和界定,无疑会忽略或遮蔽其中许多丰富曲折的意蕴,这其中仍有许多情感、思想与矛盾需要去做细致的挖掘和思索。 虽有“无可措手”的寂寞与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2](P417),从这里我们看到了鲁迅的重大思想转折,对于“启蒙他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透视,他从这一刻起开始了“启蒙自我”、照亮自我的历程。鲁迅深入到了启蒙精神的内核,坚守了与康德相通的启蒙视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与民主作为中国启蒙树起的旗帜,它们的历史有限性和现实局限性,对生命及文化都有异常清醒透视的鲁迅,于此都保持了警惕性的深深质疑与反思。对于知识分子也没有因为同情而减弱对他们的批判,同时对自身坚持了惨烈的自剖与反省。 “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P31)不难看出,在否定了外在性“招牌”的国民性改造,在鲁迅的思维里是内向性的追问与指向。鲁迅所谓的改造国民性,在根本上就是要恢复人的本源性的生命状态,是在“自我启蒙”完成之后的生命回归之旅。“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就是诚与爱。”[4](P7)这即是鲁迅为启蒙呐喊、提倡改造国民性的源发点。也正是从这样的起点出发,鲁迅发出这样的祈愿:“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5](P125)。从个体生命到整体的人类群体,鲁迅始终给予现世最本真的观照。 著名的“铁屋子”的比喻,在出现于《呐喊•自序》之前,鲁迅已经沉默了十年。在“看见了自己之后”,沉潜于自己内心的悲观和虚无之中。面对启蒙理想的窘境,“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2](P419)。“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忘却的一部分,到现在变成了《呐喊》的来由。”[2](P415)纵然鲁迅内心有怎样凄惶的生命感触,有怎样曲折的矛盾与挣扎,有怎样苦痛的怀疑与反思,启蒙的梦是他始终不能忘却的,是他生命中不可磨灭的期望与憧憬,所以鲁迅始终坚持“立人”的主张,“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2](P419)。鲁迅以他的文字及自身的行为和遭遇,自始至终捍卫了启蒙的精神实质和个体生命自由的尊严。#p#分页标题#e# 从“启蒙他者”失败后的热情中走出来,到看到自己后的“自我启蒙”,鲁迅对启蒙始终有他“自己的确信”。在对科学与民主的热烈呼喊中,鲁迅保持了静观,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深思。然而令人可叹的是“人们巧妙地将鲁迅对现代民主之存在本身所提出的尖锐问题,弱化为他为民主政治之具体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在某种特定情况下的具体的不利状况的思想警觉。这样,人们就成功地为鲁迅保留了一种先知般的深刻性外观,但构成鲁迅之深刻的问题本身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回避掉了”[6](P68~78)。 作为民主最根本的理论建构基础———个体生命的自我实存,在民主的环境中常常不知不觉地被抽离、被遮蔽,甚至被遗忘,从而民主往往失之于技术性、工具性的社会运作方式。所以在充分肯定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历史进步与成就的同时,应当始终保持对它们清醒的关注与审视。社会的完善与建设不可能一劳永逸,民主与科学也不会是所有社会问题的“终结者”。“出于人的有限性本质,民主政体作为人的一种历史性选择的结果,其历史性本质决定了它并非某种至善,相反,它的合理性必定是有限度的。”[6](P68~78)民主与科学自身仍需要不断完善甚至被超越。鲁迅所作出的质疑与反思,其起点即是在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体生命,是旨在实现心灵的“生命回归”至本源状态所生发出的辩证思考。不难看出,鲁迅的思考早已超出了反封建的有限视野,他的超前与清醒也使得他少有与之同行的人。 似乎自然会成为启蒙承担者的知识分子,鲁迅同样给予批判,并揭示其悲剧的命运。孔乙己一样的旧知识分子仍未获得新生,需要拯救,“自我启蒙”根本就没有完成,如何可能走向“启蒙自我”,去求索生命的自由,他们早已忘却了生命“来时的路”。而新知识分子如涓生、吕纬甫、魏连殳等,对于他们的理想、激情、信仰,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选择抛弃,选择退守,在孤独与痛苦中承受灵魂的煎熬、凄凉的沉寂或死灭;他们身心的遭遇让我们看到生命个体启蒙的艰辛及惨痛的过程,以及蒙昧惯常的历史力量的强大与顽固,几个人的烛火终还是被黑暗吞噬。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不敢正视现实、无奈的逃避、容易陷入内心伤痛的沼泽难以自拔等等,都警示我们知识并不直接带来觉醒、抗争与坚持,知识分子同样是有限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依然被质疑与悬置。所谓由知识分子构成的精英阶层在何种意义上存在,他们是否拥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理,他们是否可以拥有更大的话语权,都是需要重新审视的。 在鲁迅所有的小说中,我们发现根本就没有启蒙成功的范例和方案,而只有启蒙与蒙昧之间的曲折复杂的爱憎和冲突的人生感悟。作为鲁迅呐喊第一声的《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狂人,当他意识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7](P432),就已宣告了觉醒者自身的悲剧与尴尬的境遇。《祝福》中祥林嫂的出场满含深意。作为见过世面的“我”对祥林嫂的描述与“我”自身形成了多重的反讽映照。“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她分明已经纯乎一个乞丐了。”“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8](P6)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拷问,见证了“我”的虚弱无力、彷徨失措;“我”却见证了祥林嫂的“改变”与造成她“改变”的几番积极努力背后的挣扎、苦痛、自责、悔恨、无奈,以致最终麻木的彻骨的凄凉。“我”通过祥林嫂看到了启蒙的沉重,也看到了自己的逃避和无能为力,而祥林嫂从“我”这里彻底走进了希望的覆灭。 自我既是启蒙的终点,也是启蒙的起点,自我就是启蒙自始至终的主线。启蒙也可以说是从发现自我的“自我启蒙”到完成“启蒙自我”的过程。而“他者启蒙”,本质上是教化式的主体对受体的对立思维的结果,是对启蒙基本要义的悖反,是无法真正实现启蒙的。“启蒙他者”是具有精英意识的人的文化想象,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存在,但是真正的“生命回归”仍需要靠每个人自己去实现。 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写道:“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情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确为自己玩玩,有时候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3](P79)“总而言之,我为自己和为他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3](P80)这就是鲁迅,勇于坦露自己内心异常苦痛的矛盾,承认自己对世界的不确知,而这样对自身的无情解剖,是让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作为“历史的中间物”[9](P285~286),无法完全割断因袭。“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9](P286)所以告诫自己,也告诫那些“偏爱他未熟的果实”的人,“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微末的欢喜”[9](P282)。因为有着这样深重的“自知之明”和“毫无把握”,他这里没有答案,“自我启蒙”的觉醒没有实现,启蒙是难以想象的。关于未来的路“连我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来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9](P284)。前行中鲁迅始终保持对自己思想的审视态度,也时刻提醒他人应有所质疑的对待。 #p#分页标题#e# 三 启蒙,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步是自我怀疑与自我发现,从而走向“自我启蒙”。这首先要突破的就是自我中心的“魔咒”。“自我中心是生命的必要条件,但是也是地球上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与生俱来的一种内在限制和缺陷,因此每一种生物实际上都处于终身的困境中。”[10](P12~13)的确,个体生命的自我肯定、自我相信的与生俱来性,使得自我怀疑异常困难,无异于宣告自我存在合理性的破产,从而导致生存失去根基。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层次来认识,第一个层次,从生命本体的意义来理解,生命的存在是需要肯定和认可的,需要珍惜和热爱的;第二个层次,生命在历史的进程中,经过漫长文化的洗礼,形成具有相对稳定的思想意识、情感结构、人格特征的历史性存在,这个层次是需要怀疑的,需要不断审视和检验的。 而人们通常的理解是把这两个层次混为一体,以致模糊不明;或是看不到第一个层次的生命的本初状态,直接把第二个层次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自身的根本性存在,从而陷入“历史的牢笼”,成为特定意识模式的囚徒,以致陷入终身困境中。这可以说是最根本的原因,造成启蒙异常的艰辛与坎坷。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鲁迅就是一位少有的穿透了历史的迷雾与“自我中心”困境的深刻自省的思想者。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一生所呕心沥血的就是旨在打破“自我神话”的迷梦,展现了自身完成“启蒙自我”的苦痛历程与悲壮的“生命回归”。 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倡导的家国意识,使得民族国家这些巨大的文化构成元素根深蒂固,占据着人们观念的主导地位。个人的一切都与家与国深深地、不容质疑地连在一起,以致在思想和精神的领域,个体生命本位总是处于被遮蔽或被压抑的缺失状态。一个人若只是生活在自我独立的精神世界中,便会遭到普遍的排斥与隔离。这种生命个体对自身精神的追求和守护与人类的群体性生存的历史文化凝聚和认同之间的冲突,是人类面对的一个时刻潜在的深远矛盾。在《彷徨》和《野草》的字里行间,同样透露出这个矛盾也是鲁迅所深深体验并难以释怀的生命情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先生“爱人比爱国更重要”的声音已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但需要申明的是启蒙并不是否定集体性的解放的。这其中的思辨关系,“五四”一代的先辈们已给出了极富启示性的思考。鲁迅有言:“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1](P56)胡适有言:“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12](P663)每个个体都是集体中的一员,都受集体的制约,但每个人都有自我独立思考与质疑的权力。当启蒙的个体生命本位遭到否定和遗弃,那启蒙也就失去了路径和根本的指向。在并不遥远的我国中,整个国家的民众对“革命”和个人崇拜的盲目迷信与狂热,其中的教训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和反省。 由此可见,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形式,有其自身存在的本源性的悖论和矛盾,加之各个人类群体不同的历史文化的原因,启蒙自有艰难曲折的深刻根源,在特定的时代和历史情境中与特定的民族背景下,启蒙也许会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祛蔽的过程中常常会形成新的遮蔽,以致造成或长时期或短时期的新的蒙昧。所以客观地讲,对于启蒙的现在与未来,我们在始终坚持永不放弃的基础上,不能急于看到一个启蒙的结果,也不能急于给出或悲观或乐观的判断和结论。“自我中心”的“魔咒”和历史文化的凝聚与认同的积淀力量的难以抗拒,牢牢地规约着每一个人,以致人被困为无意识的囚徒。暂不论由此衍生出的种种迷雾与阻碍,时间与生命自身的制约使得启蒙几乎无法避免的艰难与漫长,然而像鲁迅一样穿透并超越这些无形障碍的思想者本身,就是实现“生命回归”的启蒙指向的最好诠释。 四 启蒙作为一种生命精神的指向,是重要的思想资源。启蒙元素的融入对文学来说,是极大的推动和丰富。在启蒙精神和视野的拓展与提升下,文学展现出新的面貌。剥离种种主义、种种理论,以生命为根本指向,文学真正成为审视与表达生命情感和思考的园地,也真正出离于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或显在或潜在的影响和束缚,在原有的审美情趣及结构之外,不断开拓出新的审美天地。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启蒙对生命个体的审美心理与情感都产生影响与革新,从而产生新的审美期待,形成新的审美情趣与视野,进而促进文学的发展与创新。 关于启蒙与文学,鲁迅的文字对于加深我们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重要的研究和探索的价值。鲁迅的文学,尤其是小说,所表现与传达的复杂幽深的人生体验与生命况味,是难以用仅仅“启蒙主义”这样理论性的术语来概括和容纳的。作品人物的遭遇,心理的变化起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情感的波澜,日常生活中人情的冷暖薄厚,季节的生息交替,人生五味的细微描写与呈现,个体与群体、与社会、与国家之间繁复纠缠的情与理……鲁迅给我们展现了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的生存———由微观生活而直透宏观存在的本相。另外,鲁迅言明的在创作中运用的“曲笔”以及未曾都说出来的话,这些隐去的思索话语与体验,同样在向我们昭示着生命的生存更为难言的创痛、孤独与绝望。鲁迅小说创作的多重审视视角、多重注视的目光,是他一层层反思质疑的体现,是深厚思维力量透视与洞穿的体现。这样的艺术手法更适合于、也更深刻地展现出他思想的脉络和经纬。 鲁迅的文字简练、朴实、真挚,同时饱含感情,而这背后正是广博深刻的沉思与体验,在语言上凝练的结果。这样富含情感与思想的句子在鲁迅的作品中随处可见。《明天》里“单四嫂子终于朦朦胧胧的走入睡乡,全屋子都很静”[13](P456);在呐喊之前“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14](459~460);回乡的路上眺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15](P476);离乡时“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15](P485);对于生命“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的太滥,毁得太滥了”[16](P553);《祝福》的夜里“人们都在灯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静”[8](P10);童年的回忆里“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17](P564)。#p#分页标题#e# 对于逝去的岁月“待到孤身枯坐,回忆从前,这才觉得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18](P121)。痛心“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18](P128)。感伤于“依然是这样的破屋,这样的板床,这样的半枯的槐树和紫藤,但那时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18](P129)。当收回追忆的思绪,“我要向着新的生活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18](P130)这些文字隐去了纷繁复杂的思索和冲突,只是体验与思考深深融合在文字里留下的质感和重量,让我们所感触到的是一颗伟大的心灵无限的悲思与哀愁。 如若没能深刻体验启蒙精神的内核,无法内化于生命,以致真正的启蒙对某些创作者来说始终是外在性的。因此在自身未完成“自我启蒙”的情况下,创作者对启蒙的狭义理解和处理束缚于固有的思维框架内,从而在作品的呈现上不但会削弱了形象的深度和表现力,而且不能艺术化传达启蒙的真正内涵。艺术上的不足的根本原因不是启蒙与文学的关系出了问题,而是创作上的欠缺,对思想和艺术造成两方面的损伤。 文学的审美意识追求的是生命的真与善,是生命的丰富与心灵的自由,而启蒙所要实现的正是生命回归到本真,同样是指向生命的自由。“除了自由之外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的启蒙,与文学的天然契合,使得文学不会沦为庸俗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启蒙对人生命自由的不断拓展和澄明,为文学打开了更加广阔和自由的精神时空与生命情怀;文学会更好地展现透彻的启蒙理想与方向。启蒙有了文学的审美的承载,使得旨在“生命回归”的精神自由追求不至于显得虚无缥缈。也正是文学的审美化的传达,使得真正的启蒙不至于滑入新的蒙昧。虽然文学并不必然负载着启蒙的使命,文学也不是实现启蒙的绝对力量,但是启蒙与文学的契合是高度统一的。在艺术上把握这种统一,就需要广阔深厚的思维视野与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