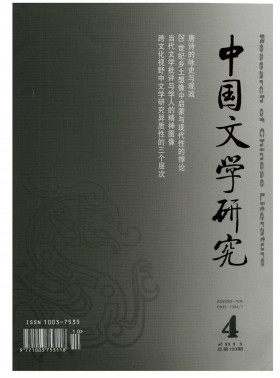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中国文学传统的生态内涵,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中国文学畅扬生命整体美并关注“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不仅接通艺术生命和宇宙生命有机谐和共振,而且展示了“生态文学”的古典形态。我们挖掘中国文学传统的“生态”内涵,既是一种对接,也是一种现代阐释;作为历史性机缘,更成为历史、现代与未来接续的必然。当继承、对话、扬弃、转型;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体用关系、共生共存等词语运用其研究,必然在现代境域中使之观念重构、价值重建、意义重生。我们环绕“生态”体验,力主拓展视野,对中国文学传统给予现代阐释,在多向转换及“对接”中,悟解“生态”对人之生存本然性构建的必然性。 一、“生态”接通中国传统话语系统 “生态”一词,产生于19世纪,繁盛于20世纪。1866年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最初使用“生态”时,其意义是指生物与其生存环境间的关系。至20世纪后半叶,“生态”与多种学科联姻而植生出无数学科;与多种文学艺术类型触发相似相同的体验方式,使多样的创作类型得以生长,也成就了多样的话语表达及阐释方式。“生态”还与多种地域及人的生活状况、文化生存方式续缘,使“生态”有机状况无限延展,成为转换人的文化存在方式的必然。“生态”之能量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无所不入,有着近乎无所不涉的领域,原因就在于“生态”的蕴含及根本所指。“生态”与中国话语接通,不论是历史、传统的,还是当下及文化整体风貌的,不仅都会凸显上述种种转换特性及条件,而且最重要的,或许是启悟我们去挖掘、修整、组合、再生中国古已有之且丰富的“生态”文化资源。 首先,“生态”作为概念的植生作用。“生态”既是一个现代含义的概念,也是一个膨胀指数极高的现实存在。但其丰富的内涵及明确的所指性却不拘于现代,而是接通着人类生成的始终,与人的生命、生存,以及人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建立多样并复杂的关系。我们之所以说中国文化传统满含“生态”之义,其意就在于此。在古代中国人那里,天地人三者始终是生态化地连接着,这种连接不是对象化的,而是“生命”的连接,是“生生”永续的,天地、阴阳交感而和合,化育化生万物。那种天地人和合、“并生”、“为一”、“本与体”且生生化育的同类话语表述众多,并且生成性及辐射现象也颇多。至王阳明,便有集大成的表述,《大学问》云:“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1]“生态”意涵与天地人和合,万物一体,生生化育等话语,尽管非产生于同代,但却异曲同工,其内涵也有相似相同性。这就创造了相互间对接、融合的必然条件。其条件既“自在”,即伴随自然与人的生态和合,并有亘古不变的本然状态,也“自为”,因为作为不同文化传统的交往与对接,是 历 史 性 与 过 程 性 的 现 实,也 是 未 来 的趋向。 其次,“生态”对于天地人关系的表现作用。中国思想史中诸多理论都强调人是自然宇宙生命大家庭的一员,人与自然是一体的,这就包含着较为深刻的生态思想。天地人朴素有机体的相合,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在此统摄之下,人们的思维没有把主客对立起来,没有将自然只看作是一个外在于人的认识对象,而是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有机且系统的统一整体,总是把外在自然转化为内在自然,成为人的内部存在;将自然既作为社会道德体验、精神活动的实有存在,又作为参照、尺度,来映衬人的品格、德性。尤其在文学体验中,自然的形貌总是含蕴始终,人们通过天地人一体的运行而感悟人生,且与人的自体性活动有机融入,进而构筑朴素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关系。文学活动始终表现对自然的那种浓郁的生态亲和性,其中较少认知性及理性、思辨性的话语阐释,却恪守“外师造化”式生态体验。即便是游记性文学体验,尽管也有对自然现象的客观及经验性阐释,但却与对自身生命、情感及审美悟解相融合。这时,人对自然的那种天然性的情谊、情感及亲和力往往超过了与自然相对立的认识性理解,其中满含着最适宜于艺术创造的生态智慧。 第三,“生态”对于话语层次的构造作用。对生命的理解及体验溶解在古代人的人生体验中,成为古人在构筑自身的生存环境时必须进行的现实与理性的选择。古人思维及话语表达更多的是直觉的,经验体验性的,他们对生命感的植入,对生命意识的经验性体味会成为他们生活及生存的选择。我们不可能确证这就是生态文学(创作与批评),但无疑是生态文学的前在雏形,或为相似性。这一方面得自于人类演化的历史过程中,生态体验的相似性,另一方面,源自中国特殊自然地理环境所生成的,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存在方式,以及由此铸就的天地人和合的体验方式。这多种因素成就古代中国人的生态体验的特殊性,也植生出文学现象的“生态”性韵味。“生态”在接通人们构造话语、范畴的支撑系统时,会植生带有极强的生命意识及生态关联性的话语表达。如:道、气、性、势;韵、味、悟、神;太极、生生、化生、化育;乾坤、阴阳、刚柔、中和;混沌、天籁、大象、大音;雄浑、含蓄、豪放、妙境等无以尽数的话语模型,既内蕴艺术体验及生成性的话语特点,也具有很强的生态意味。尽管我们不可能以“生态”重新组装这一系列概念及系统,但如果我们从生态意义上给予新的诠释,想必在挖掘其本有含义之时,必然会焕发其新意,体现其再生之意。 最后,“生态”与“生生”的统贯作用。“生态”与“生生”在指向生命有机性方面,含义相近,如存差别可有二:一是产生的语境及历史条件不同;一是“生态”更显关联性,“生生”则依循节律性。两者都具统贯性,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或许“生生”更具适应性。“生生”既是自然之生态存在的现实,是生命运演及个体生命生成及延续的表现,也是艺术审美生成及体验的本来状况及节律性展示。进入现代语境,“生生”亦可为“生态”的代名词,作为一个范畴,会有极大的辐射性及再生作用,并作为生命体验及艺术审美活动的最佳展示方式。古代中国人论述诗文中的声律、对偶、修辞诸问题,书画理论中的着色、骨法用笔、皴染及虚实等表现手法,戏剧中的结构、程式、虚拟等,总是以“生生”运行的生态节奏及韵律感印迹生命活动,汇聚审美体验。即便是对方法的运行,古代人也总是将其置入生命运行关系及“生生”的生态演化节律中,在生态化的、和谐性的关系视野中进行艺术操作。这丰富的表意系统,是现代境域中文学活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话语资源库。#p#分页标题#e# 二、“生态”作为中国文学体验的核心要素 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及文学体验活动中有一个无法割舍的情结,即神往“自然”,并且是带有明显生态特点及生命体验性的自然。这种“自然”,不仅是促动人的现实活动、道德守成及情感体验的重要标尺,而且成为文学活动的核心要素:其一,既成就天地、山水、花鸟,也是归位这一系列自然现象的内在机制;其二,主体融身自然,而来解困,记叙情意,调养精神;其三,作为主体自身性格品质的参照,将实在、物性的自然现象,转换为人性、德性、情性的“自然”。这种富含生态特性的“自然”,不单是静止的,实在的,其动态性及关联性,则是“生生”的,节律性的,也被“德性”提升。文学作为人师从自然、效法自然、诗化自然及提升自然且又回归自然的活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内在生态关联成为文学活动的基本载体和创作材质,并成就多重“道性”的合奏。自然与天的运行作为自然道性,必然推进至艺术之道,而艺术之道又需反馈,且和谐润化自然之道,进而提升人生、人性之道。 首先,“生态”与“艺道”的合奏。中国文学中的艺术之道是体“道”的中介,起到接通、融合的作用。宗白华说:“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2]人们期望自然与艺术之道性的和谐、圆融,而显示人生、人性之道,艺术之道又接通自然之道与人生、人性之道,使之有机融合,形成“天文”与“人文”的有机合成。刘勰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迭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原道》)刘勰将文学现象与天地之文相贯通,强调“心生”、“言立”对于“自然之道”的作用;从天地人相关联的总体范围思考文学问题,将其视为与自然之道并行的艺术之道。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虎豹虫鱼都是自然天地的生态杰作,它们构成了生机勃勃的自然之文,而人文则是对自然天地之文的仿效。尽管刘勰并不懂得所谓的生态理论及文艺活动的生态元素,但他从人与自然的生态一体性的关系出发,所绘制的自然“生态”状况,也内涵对人的活动的生态助推性作用。他的这种“自然”情结,似乎已经把“生态”作为文学的母体,其“艺道”也表明,离开自然之生态有机性的孕育,人就难以创出真正的文学艺术。 其次,“生态”与“人化”的合奏。古代中国人立足于人与自然生态有机性而认识文学,而不从唯理性角度看待艺术特性,这形成了文学活动本体论基础。文学艺术不是对自然之道的简单而直接的模仿,不是对其外在物质实在的复写及转换,或者说,自然生态给予人的不仅仅是物质外壳及质料组合,也不是自然生物躯体(包括动植物及人)的外在运动,不拘于丰富的色彩、奇特的形态,而是得自生命运演节律,其内蕴的生命能量转换及融合的境域而成就的内在生命力。生命作为自然生态最重要的特征,不仅成就了人的感性生命体的存在,更旨在延伸人的生命活动,促成“自然人化”的过程性及文化的累积,进而生成人的社会存在及精神———文化存在的生命力,使人的自然性的生命不断转换为文化的生命存在。文化、艺术实为“生态”与“生命”合奏的结果。生态关联性与生命、文艺对自然生态之滋养的多样性汲取方式,不论是心师、效法也好,诗意化体验也好,必然是中国古代艺术构成和审美价值的核心要素。 第三,“生态”与“人心”的合奏。人与自然关联,天人异质而同构且互相感应,构成了古代审美体验的发生基础。《周易》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材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周易•说卦》)这表明人与天的结构有相通的“生态”根源,其相通及相应就成为阴阳、刚柔转换以及物我、情景交相感应的基础。“生态”作为文学的基础与根本,其最直接的接通点是“情感”。在中国人的艺术体验中,“情感”往往与“心”(思想、观念)连接,早期的“心”与“情”有相通性,如《乐记》论情感产生时云:“音之 起,由 人 心 生 也。 人 心 之 动,物 使 之 然也。”[3]之后,“心”超越了“情”,成为规范或统领,“心统性情”就表现了这种作用。在真正的艺术体验中,“情”与“心”无法分离,是有机交融且一体化的“合奏”,其原因就在生命之体的运动及生命力的发射,其根基即为“生态”存在。当“生态”与“人心”合奏时,“心”则不虚空,而是有更丰富的内涵及所指。人感于自然生态中万物的阴阳转换、刚柔交错,悟解着生命的生长变化、生命的延续,内心产生情感的呼应,发之于管弦就成为动听的音乐。钱钟书就说:“夫艺也者,执心物两端而用厥中。兴象意境,心之事也;所资以驱遣而抒写兴象意境者,物之事也。物各有性: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其性有必不可逆,乃折吾心以应物。一艺之成,而三者具焉。”[4] 第四,“生态”与“情意”的合奏。文学有情有意且寻理。中国文学中满含着情意与情理,却不只流于主体心理及情感表现,不是单纯的感情发泄,在表现时往往会有三重附着物。这其中:一是天地、四季、四时、山水或诸多自然物;二是对“生”与“命”的体认,其中也包括身世、家事、国事的纠葛;三是对先人、圣人、神人的追思。前两者有时会纠结在一起,而使情意表达与自然、与生命呈多层次及多角度的交合。这里面不乏爱意,既有对诸多自然现象的爱意,有对生命的爱意,亦有自身之爱,其中,就满含“生态”与“情意”的合奏。李清照词《声声慢》中,既用连续的叠词表达情意,也将诸多的自然物与她的心情、心境相通,以其映衬,其中又深蕴身世、家事、国事,这种多重的纠葛,奏出了独特的生命和旋。四季的时序时节转换是自然生态运演的结果,其节律性更抚养着万物生命。中国文学传统中,人们曾极尽四季、时节地表达情意性,并紧扣生命、生机的活动特点,也富含深沉的志趣与志向。董仲舒云:“春爱志也,夏乐志也,秋严志也,冬哀志也。故爱而有严,乐而有哀,四时之则也。”“天乃有喜怒哀乐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气者,合类之谓也。”[5]“四季”与“四情”纠葛,情意体验性极为浓重,董仲舒用中国文化中“生态”意味极为浓重的“气”,来展示生命体验性的直接性。“气”的生命体征随着日月变化、时令及季候转换,促使人的情意发生相应的变化。刘勰云:“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龙•物色》)刘勰认为季候变化与人的情感存在感应的关系:春天万物复苏,人的情感也易于萌动;夏天热烈,人的情绪高昂;秋日萧索,悲情易生;而冬天万物肃杀,人的情志也深沉高远。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同样强调了自然对人的感发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云:“情者阴阳之几也,物者天地之产也。阴阳之几动于心,天地之产应于外。故外有其物,内可有其情矣;内有其情,外必有其物矣。”[6]这些论述都能够通过这种“生态”与“情意”合奏,促动自然环境与人的心灵之间的融会贯通。#p#分页标题#e# 三、“生态”承载文学的运思与体悟 古代中国人主张文学活动中主体的运思与融情,以求创生人与自然,情与自然事物之有机融会的至高境界。文学艺术秉承天地之气及精华,并在有机、和谐的关系中既将之发扬光大,又游于气运流行及生命活动的“生生不息”,使艺术充盈着鲜活的生气和无尽魅力。对生命的体悟并思接千载,情动心魄,全在于“生态”有机性的承载,而迸发生命力。 首先,“生态”与主体的感物生情、至性的天性。中国传统文学不仅将人与自然的“生态”感应作为艺术情感发生的基础,更强调艺术作为表征生命体验的特性。人与自然间的关系既呈现异质同构性,又基于和谐共振性,这作为“生态”化的有机关系,必然引发主体在文学体验的性情迸发,感物而生情,以至性显天性。张载云:“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7]这指出了人在与自然的“生态”之关系中,表现着心物同构、物我相通的特性,进而有机把握乾坤、天地、阴阳相转换的“天性”,通过尽情挥洒主体之情性,而凸显生命之美的魅力。事实上,天人之间本来就存在必然的交感、互动、共生性,并在人与万物的感应互动中运通,其呈现的“生态”有机关系恰成为文学活动表现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基础。 其次,“生态”与主体的“临春风思浩荡”。古代中国人往往将艺术视作一种生命体验的表征,认为人能够经由艺术与自然生命的交流,而洞悉生命的奥妙。人们借助艺术能够将心灵世界沉潜到自然生态之中,与自然万象融汇为一,并至深体验生命之“和”、之美。在生态有机关系中,人作为生命活动体,具有自然生态家族的成员身份,别离这种存在关系,人将不复存在,艺术与审美也将无从谈起。正是基于这种身份认同,才能够不断畅抒感物生情,进而确证知心、知性、知天的天性;人才能真切感知天地的生命精神,启悟且形成生态谐和共振,才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与天地自然的生态运行节律相应和,进而“应物斯感”,“有触则动”,“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正是山川大地,莺飞鱼跃,繁花似锦,宇宙自然的生命律动及生态“魅惑力”触动了主体存在之元气及淋漓的诗心,使情思飞扬、浩荡,主体便不断勃发着激情涌动的生命之流,去悟解“生态”及生命的美。 第三,“生态”与主体的“三竹”体验。中国传统文学的理论思维也建立在天地人生态合一及同构、共感、互动、共鸣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感物兴情”作用,既呈现其诗性、节律性,也使之具有“间性主体”活动特点。郑板桥著名的“三竹”说,就最佳地描绘了这种节律性体验特点。“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8]340“三竹”节律,除了是一种艺术体验方式外,其“本真更在于为我们呈现了一种生态性思维过程及节律。”郑板桥显然超越了人对自然、自然对人的“定则”,以表现浓重的生态之“趣”。“‘胸中之竹’之于‘眼中之竹’,‘手中之竹’之于‘胸无成竹’都是艺术生态再生性的逻辑关系,是超越性的生态再生,通过节律性转换在艺术审美化的情境中澄明人所应有的那种本真性的生态审美境界。”[9]这种基于生态有机性的体验,主体生命激情的涌动与外在之物、之象,交感互应,气脉流行,首先以万物之感性形式对主体的审美心灵产生感召,这同时也是自然之气、人身之气及人的精神之气的多样化构合。 第四,“生态”与主体的“物我一体”。“生态”有机与交融性关系贯通文学,必然推演着创作主体对自然事物及现象精心揣摩、心领神会,在情意促发中既体认“物”,更确证“我”,以达“物我一体”。郑板桥言:“日则凝视,夜则构思,身忘于衣,口忘于味,然后领梅之神,达梅之性,挹梅之韵,吐梅之情,梅亦俯首就范,入其剪裁刻划之中而不能出。”[8]359这是对李方膺画梅的主体感受,板桥体悟李方膺“痴情”于梅而现“物我一体”,又以此为中介,悟解自身的“物我一体”。其中,内涵李与梅、郑与梅、郑与李的多层次体验,具有“生态”之融合性、创生性。郑板桥的“物我一体”的多重体验,首先潜心于物而“日则凝视,夜则构思”,然后则悠然忘我,进而领悟神性及情韵。梅之神性及情韵即从“我”之心中、笔下自然涌出,“我”之性情及神韵亦从梅之花间、枝头上自然流露。这种多重流向合一,必然使主体在生命之流的涌动中潜心于物,身与物化,进而达到心与物、情与景、意与境的“生态”契合。这种契合会摆脱种种意念的局限、功利的约束、尘嚣琐事的缠绕,而使体验者能随触而应、随感而通。如此这般,主体以自由的心态面对生态有机的世界,便能够在气运流行中,接纳千姿百态的自然生命,且展示主体与天地自然之气、之物、之理的“生态”契合的境界。 四、“生态”标识着文学价值及人的生存 文学以精神体验凸显其价值。文学的“生态”既以自然价值为根,又不简单复写,其精神价值内存“生态”合成及“人化”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精神价值,总是用自然生态现象来映衬人的精神体验,意欲表达古代人融身于自然,且在“生态”融合中祈求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愿望。“生态”近乎成为标识,以凸显文学价值及人的精神活动。#p#分页标题#e# 首先,“生态”与精神的价值提升。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们总是将自然物作为人的生存与发展的价值支持物,既作为精神体验的载体,又作为精神价值及生命价值的提升物。人们崇尚“生态”之有机性及和谐性,期望在这种和谐状态下人与自然的多样化、多方位的交流。自然生态是人的衣食之源,不仅对人的躯体存在及物质生存是根本性的,同时还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最本真的皈依和依赖。古代人从事文学体验,自然事物及自然存在的生命现象作为体验自我的标识,成为构建人的道德品性及精神守望的支撑体。自然物性与人的道德及精神体验的有机合一,相互衬托及参照,在参天地之化育中,不论是山川河流、花草树木、飞禽猛兽,人们总能挖掘同人的德性与精神相同的物性特征,并在极尽地渲染中,在交感互生与生态构合中生发新义,升华至高深玄妙的审美境界。 其次,“生态”与自由的价值追寻。古代中国人将精神现象与宇宙之气相联系,将精神视为整个天地自然所共有的产物。人们总是视自然是“自由”的,潺潺的流水、水中的游鱼、高飞的雄鹰、驰骋的骏马等“逍遥”且自由。从一定意义上说,不论是有机还是无机,有生命还是无生命的自然物,人们在体验及“人化”中,在其德性与情感性转换及物性的映衬中,都蕴积着自由感。在文学活动及审美体验中,主体对自然物的物性把控,并不陷于尘嚣琐事的缠绕,较少功利性羁绊,或者说,不以功利价值获取为上,而通过对自然物的自由感的体悟,寻求对自身自由与精神的体认。人们选取多种多样的物性特征作为人性、德性及精神品质的参照,往往会感悟其中的自由,从中汲取的也是满含“生态”有机性意味的自由。 第三,“生态”与惠利的价值获取。人从自然中获利是为汲取物质与精神生存滋养。“生态”与惠利既一致,也是本根性的,有机性本就包含惠利性。多样的生存滋养作为价值存在,其“生态”化也是必然。在文学及审美体验中,惠利主要不是物质及利益的,也不只限于感性生命的呈现,而主要是精神性的,并由物性价值递升为精神价值,体现价值转换性惠利。一般意义上,惠利的获取状况及价值量的显示,往往会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一个尺度。从生态价值与人的精神价值的双重意义上看这种价值尺度,其价值量大小,往往不是以物质转换性价值显示,而是基于有机性及对人的精神、德性提升的存量。在传统的文学活动及审美体验中,“生态”与惠利的价值关系,总是呈现提升状态,主体融身于有机性体验中,悟解自然、物性及生命,合着生态有机节律的脉搏,合奏着“生生”的韵律,感悟自身,获取自由,以获得“生态”润化的惠利。在中国古代,人们对“生态”理论与现象的认识及理解,对人的生存的“生态”化体验,对“生态”的学理性及策略的掌握并不是主动的、有目的,甚至是模糊的、被动的,但作为朴素的价值寻求,作为对生命有机性的亘古体验,这一切都会在主动与非主动的交织中,成为艺术体验的必然。 第四,“生态”与真性的价值呈现。“生态”真性既为自然的本来状况,更呈关联性。真性依据是自然价值,或是自然的存在之真(自然存在的绝对意义)。自然之真是固有且实在的,但作为价值存在,则必须是关联的,有机的,是促进万物“生生”及转化生成的。文学与审美体验作为关系性存在,作为生命活动的特有方式,基于自然之真,而获得基础性条件,又依循“生态”的真性及关联性,进行精神价值创造。文学活动呈现“真性”价值,其精神价值、审美价值的显示,必须是自然价值、生态价值与生命价值的合奏。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表现及理论沉淀中,非常注重对这多重价值的体认及阐发,而合成的方式,是通过真性与善性、实性与虚性、物性与情性的多重交织,以有机的生态融合而表现。在中国文学活动中,一种技巧运用得好坏关键看它如何融合人与自然,心与物、情与景及意与境,或者是对自然、生命、精神之真性如何给予“生态”化的揭示,如何把控多重价值的有机呈现。 中国文学体验从“生态”一体化的宇宙观出发,通过心物感应,经由情与景、意与境的交融,产生动人的、生气充盈的审美意象;有限蕴积无限,且在超越有限的人生和自然之物的审美场域中,激活自由无碍的生命精神,去体验至高的“生态”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