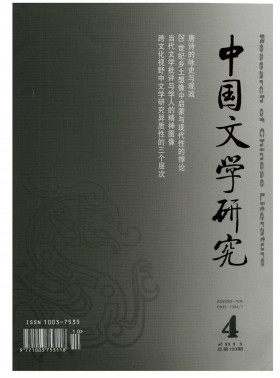1950、1960年代是现代文学史建构的重要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论”是其文学史书写的理论基础。而“”十年结束后,整个文学史书写处于徘徊状态,它主要表现在对1950、1960年代以来文学史书写的恢复,文学史书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比如,当时最为通行的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实际是对1960年代所确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的恢复,而其他各高校联合主编的现代文学史也莫不如此,整个文学史书写处于停滞徘徊状态!1980年代以降,随着历史转型,之前认可的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工具论”等开始受到质疑,文学独立意识、文学审美意识受到人们的推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产生于这一语境。作为1980年代中后期重要的文学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是对195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让文学史回归文学自身,它带来了文学史书写模式的飞跃,这在文学史建构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但站在21世纪的今天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充满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带来的文学史书写所具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 一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可从三层维度认识,即“二十世纪”这一独特时间维度;以“中国”为基体的空间性以及它进一步延伸而跨入“世界”的空间维度;而“文学”以及由此延及的“文学性”是这一文学观念的本体维度。这三层维度构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本文仅从时间维度观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这是一充满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于1985年5月,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之后,《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连同“三人谈”相继发表于《文学评论》、《读书》杂志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给学术界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反响,正如《文学评论》在《致读者》栏目所言,《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阐发的是一种相当新颖的“文学史观”,它从整体上把握时代、文学以及两者关系的思辨,这是对我们传统文学观念的一次有益突破。①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宏观的视野,试图跻身“世界文学”的行列,将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文学打通而形成完整统一的整体:“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人‘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②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磅礴的气势,冲击着1980年代以前的文学观,并带来了文学史书写模式的大改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包括以下内涵:“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③这种由主题、内容,以及审美内涵与形式等方面所带来的文学研究方法的改变,进而延及文学史书写模式的大改变,这显然是对由新旧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指称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文学在文学史书写模式上的重大突破与超越。 因此,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书写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这对1980年代以来,甚至将来的文学史书写产生深远影响,它一时成为人们阐释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书写文学史的重要话语。人们开始以这一新的观念来遴选,并确立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并以此观念来确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结构。 任何具有建设性的文学史模式的形成都是建筑在对旧有文学观念、旧有文学史模式的解构与超越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首先意味着对在此之前确立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文学史模式的解构,而其实质就是对二十世纪涵括的三阶段分别指涉的旧民主主义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时空解构,即对文学史书写依附,从属于中国近现代,以及当代“革命史”的文学史模式的解构。正如黄子平所言:“我们寻找文学史本身的整体性,而不是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这大概是产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的比较深层的原因。”④ 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间维度而言,它主要指称“二十世纪”这一具体的历史时期。“二十世纪”作为浩渺历史的一瞬间,它主要指称一个自然的、宇宙的时间段,它既与传统相承,它更开启二十一世纪的将来。但当“二十世纪”与“中国文学”组合在一起时,则形成一意识形态话语,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新的文学观念的出现,这使人们习以惯之的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时空结构发生了质的改变,正如提出者所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这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⑤ 这一文学史观的整体性,使之前形成的文学史模式发生了质的改变。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者之一的钱理群先生,他开始以此观念来书写文学史,比如把“改造民族灵魂”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题,并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入传统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纵横背景来考察。这使该时段的文学史时空结构发生了变化,其《序论》指出:“从戊戌政变前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二十年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新文学的酝酿、准备时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文学的发展,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上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则可以看作是它的‘下篇’。”⑥“戊戌政变”前后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起始点,同时,该文学史有还有意识地把1917年定位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式开始,这就改变了1950年代以来文学史叙述将1919年产生的“五四”运动作为现代文学起始点,这改变了由《新民主主义论》所确立的文学史时空结构。#p#分页标题#e# 这种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文学史时空结构改变更表现在“重写文学史”的具体实施中。最典型的是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该文学史在结构上分为上编、中编、下编三部分。上编主要叙述1898-1917的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起始确定在1898年的戊戌政变前后,在孔范今看来:“作为肇始于上世纪末,张大于本世纪初并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前提和构成部分,表现为‘工具革命’的白话文运动,早在这个时候就巳开始了。”⑦ 其明显表现就是1897年裘廷梁响亮地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之后的陈荣衮、梁启超等提倡的“言文合一”的“工具革命”,这与“文学革命”中的白话“工具革命”有着精神的类似性,这是该文学史把1898年定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起始的原因。因此,1898-1917年这段文学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上编。该文学史更在文学史时空结构中着眼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由于打破了以前文学史时间结构,这也带来了文学史空间结构的改变,最明显的就是台、港文学被写入文学史。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寻求自己生存立足之地的特殊世纪,但由于政治地理差异,这使得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成为分割散居状态。因此,以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只是“大陆”的文学史,这造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台、港文学的缺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打破了之前的文学史时空结构,因此,该文学史的中编、下编,在突出文学史时间性的同时,更突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空间整体性;因此,中编包括1917-1976的大陆文学,1949-1965的台湾文学;下编包括1976之后的大陆文学与1965之后的台、港文学。正如有学者指出,孔范今主编的文学史:打破了以社会历史分期作为文学史分期的传统,恢复了历史的整体面貌,回到了对象本体:从时间上恢复了一个世纪文学发展过程的完整性;从空间上全面呈现曾经生存于各种不同历史空间的文学对象的原貌;从关系上全面梳理各种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的制约,清理各种文学景观生成的来龙去脉,使一部文学史真正获得“史”的价值和品位。⑧ 这种文学史时间结构特征照样体现在其他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冠名的文学史中,如黄修己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现,真正打破了1980年代之前文学史所确定的时间观。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具重要的学术意义,孔范今先生在其主编的文学史中指出,作为一个新的文学史范畴,“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实质上是对文学发展过程在史学领域中的重新整合,其意义至少有三:第一,从根本上解脱了社会政治历史分期对文学史考察的教条式束缚,使文学相对独立的品格得到科学的尊重,并使其发展过程得到相对完整的体认;第二,对社会政治历史分期的疏离,意味着研究者主体学术观念的调整,意味着他们将从非文学的价值认知系统中超越出来,与对象进行科学的对话和沟通;第三,由于文学发展过程的完整展示,这一过程中许多深在而复杂的因果关系才会变得连贯而明晰,许多长期困惑人们的历史的症结,也便有了释解的可能。“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新文学史范畴的提出,必将预示着一个新的文学史研究局面的呈现和发展。⑨ 以上叙述,道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学术意义,其最重要的表现即是它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模式的反拔与突破。但在此要追问的是:这种反拔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其实质是否就是真正文学的表现?它在反拨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的同时,是否已堕入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观? 二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是对1980年代之前文学史模式政治意识形态的突破,有文学史回归文学自身的倾向,但这一文学史命题的时间性,亦照样建筑在意识形态上。 只要观察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名的文学史文本,其各个时间段的临界点,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内涵,亦深具意识形态。首先看孔范今主编的文学史各个时间段划分:第一个时期,即1898-1917,1898年“戊戌政变”前后成为该文学史起始点;其他时间段,即1917-1976这一时间段的大陆文学,1949-1965的台湾文学,1965年后的台、港文学,它们无不打上各个历史时期政治事件的烙印,文学史照样成了政治事件衍射的对象;而该文学史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学的叙述,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叙述。仅看该文学史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起始的描述即可窥见一斑:维新文学运动张帜并大兴于1898年戊戌交法失败以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中坚及其追随者痛定思痛,深省到文化思想启蒙的重要,决意开通民智维新自强,从事思想启蒙和文学革新运动。其主要代表人物除梁启超外,还有黄遵宪、夏曾佑、蒋智由等。他们大张西方“自由主义”的旗帜,主张文学应适应时代要求,反映现实和理想以改革政治、改革社会。从此,“译著东流,学术西化”,出现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和“戏剧改良”,促成了晚清文体的大解放,并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开辟了道路。⑩ 这是一段充满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史叙述,此时期的文学成了适应时代,改革政治、改革社会的工具。在时间划分上,1898-1917这段文学史以1906开始的“革命派文学”为界而分为两部分。对“文学革命”的背景叙述也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而对“文学革命”的叙述更打下了“五四”这一政治事件的烙印:“五四,这个划时代的历史符号,标志着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现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近代文学都以此为界,无不是因为在这个符号里涵盖了一场足以动摇传统中国思想文化根基的精神风暴。”#p#分页标题#e# 文学革命所建立的文学理所当然成了思想启蒙的工具,新文学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启蒙文学”;而以1925年为界,“社会思潮和文学观念却为之一变,启蒙被淡化,个性遭冷落,而社会解放、集体主义、阶级斗争、民族救亡成了当时文学的中心话语。”???该文学史描绘的革命文学、抗战文学、延安文学无不为意识形态所渗透。至于1949-1976年的大陆文学,1949-1965的台、港文学,也无不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该文学史的《导论》部分更叙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重要关联,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并没得到充分体现。以上叙述可看出,该文学史在突破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分期的同时,它亦照样堕入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漩流。 再看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与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他们似乎在尽力避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局限。首先看黄修己主编的文学史,在时间划分上力求1900-2000这一完整的“二十世纪”,他把1900-1916时间段的文学称为“前五四时期”的文学;1917-1949的时间段,他主要论述“五四”启蒙文学到共和国时期的文学;1949-1985时间段,他主要论述该大陆文学发展的艰难历程;1987-2000时间段,他主要叙述市场经济转型大陆文学的发展。 因此,文学分期照样没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同时,大陆文学的叙述构成该文学史主体,而通俗文学、少数民族的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等文学样式并没完整融合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它们只能以附体的形式给予叙述,而这正有悖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与合理性。再看严家炎先生主编的文学史,该文学史似乎尽力避免文学史分期带来的意识形态性,因此,文学史时间叙述较为模糊,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间的起止也不确定。该文学史把“跨入世界文学”的“现代性”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主题,以此为标准,他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源头应该“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算起。”由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步入“世界文学”的过程还远未完成,因此,有关该文学段下限在他看来还很难确定。 可以说,这既是该文学史相对于其他文学史的优点,也是其不可弥补的局限。事实上,以“现代性”为标准叙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照样深具意识形态,它会压抑排斥那些所谓不具备“现代性”但却属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样式,比如旧体文学、通俗文学等,这也违背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而以“现代性”维度带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矛盾与悖论,更会造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人为断裂,它会形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时间上限与下限临界点的模糊与尴尬???。 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叙述要打破近现代,以及当代文学的政治界限,极力保持文学的整体性时,汉学家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分期令人反思,他将1842-1911称为“现代前夜的中国文学”,即近代文学;而将1912-1949称为“民国时期文学”,即现代文学;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他称为当代文学,以“国家、个人和地域”,分别叙述了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 ?该文学史分期似乎又回归了之前近、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分期。以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文学史叙述说明,由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身与政治的纠缠,它很难以纯文学姿态呈现于文学史叙述中,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文学史叙述并非真正回归了文学自身,而仅以时间维度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身即是一带悖论的意识形态文学观。有学者曾以空间相比附而指出时间的特征:“除了它的一维性以外,时间概念的另外两个根本属性是它的指向性和过渡性。时间的指向性决定了事件的先后顺序是不可逆的,而其过渡性又使我们得以把过去、现在和将来加以区别。” 因此,作为历史的时间是一条绵延不断尽的河,它延续于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二十世纪”这一特定的历史段,它既承续于过去、横亘于现在,还延续于将来。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仅以时间这一维度而言,它的存在根据似乎并不稳固,它带来更多的是对这一概念科学性、准确性的怀疑与反思?作为文学的断代史,它要么将这段历史:1900-2000拦腰斩断独立出来而显示出文学史叙述的牵强;要么为寻求文学的合理性、合法性,它不得不依附于政治历史事件,而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起始点不断向前延伸,而其终点不断向后推延的尴尬,而最终失去这一概念的纯正性。正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者所言:“在我们的概念里,‘二十世纪’并不是一个物理时间,而是一个‘文学史时间’。要不为什么把上限定在的一八九八年而不是纯粹的一九00年?如果文学的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它的基本特点、性质还没有变,那么下限也不一定就到二000年为止。” ?这段话至少传达了两种信息:其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的牵强与尴尬;其二,作为文学史观念的意识形态性。因此,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提出不久,有人即指出:“预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时,应该充分注意它的历史惯性和封闭保守性,应该充分估计进程中的种种艰难挫折”,由此,他断定“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汇入世界文学的进程,其始点和终点都不在二十世纪内,也不在二十世纪的临界点上。这个进程所跨越的时间比二十世纪要大得多。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