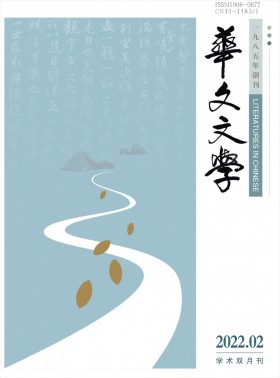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行过洛津文学解读,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本文作者:杜旭静 单位:装甲兵工程学院
一、故园记忆
施叔青出生的鹿港是台湾彰化县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古名洛津,曾为台湾重要港口,从清乾隆四十九年,清廷开放福建蚶江与鹿港通商后逐渐发达。鹿港港口在清末因为几次地震造成泥沙淤积,逐渐荒废,由繁华走向了没落。这样的小城,如同很多古老的小城一样,一代代传下来许多奇异的传说,施叔青就生长在这里,睁着惊奇的眼睛,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对于故乡和施叔青小说创作的联系已经有很多人研究,翁淑慧的硕士论文里就谈得很深入:“她的小说里经常出现许多乡野传说,在不断传述、操演的过程中,召唤出那个行将被现代化浪潮冲退的传统庶民世界。乡野传说的流通是透过口耳相传,在传统农业社会,群我关系相当紧密,'街谈巷议'是庶民重要的文化活动,而禁忌、怪谈是其中常见的交流话题,从中可以察见他们的人生观与宇宙观。在施叔青笔下,乡土给人相当复杂的感受,既是可以把'活活的世界写死?'的慑人记忆,也是她笔耕的土壤、创作的根源,不断地在书写过程中召唤她重新回返故乡的记忆。这样的双重性导致施叔青对民间宗教不采批判的态度,因为那是她从小习以为常的生活氛围,并转而为她独特的美感经验与创作材料。”[1](p53)
在她的《那些不毛的日子》里有一段描写“我”的二伯父因为一个锯木工厂老板的儿子被机器轧断一只手,就一口咬定是水鬼使的勾当,于是“率领一批没事干的闲人青睐神明三王爷庇护,带着一个油锅,夜里一大群浩浩荡荡来水井这里抓水鬼下锅。”[2](p8)“台湾三部曲”之三《寂寞云园》里也有黄得云的怪得让人记忆深刻的贴身女佣与鬼魂通灵把人魇死的描写,《行过洛津》里就更数不胜数,从无数的和鬼神相关的节日———天公生日、七月半迎神送鬼等等就可以看出,鹿港是个宗教气息相当浓厚的小镇。鬼神信仰深植在庶民的深层意识,面对特殊的人生际遇,庶民经常采用鬼神信仰的解释法则。这和知识分子从学校教育所学截然不同。因为它其中隐含的超自然力量能响应民众的心理需求,以及上千年来形成的集体无意识,这些民间禁忌、通灵法术才没有随着现代科技和教育的发展而消失,相反依旧在现代生活中发生着类似宗教的作用。在这里很难产生彻底的无神论者,人们对于鬼神,对于超自然力量,不是如外人般隔岸观火地观赏,而是毫无疑问的相信。这对施叔青远离原乡后的创作和人生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另外还有有一些反复出现的意象或形象,也大多与鹿港的氛围和传说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地牛翻身引起地震,“祖母说地底深处住着一只奇大无比的牛,它生气了,所以地会动”[2](p8)。除了这样直接介绍的句子,施叔青在很多小说中用来形容地震的都是“地牛翻身”,在《行过洛津》中形容许情遭遇地震时就说“他直觉地感觉到那是地牛翻身的声响”[3](p19)。可以看出,地牛翻身已经成了地震的代名词,如同“西施”和“美女”一样,在施叔青的头脑里比喻的这一步也省掉而变为直接联想了。
再比如“火车头”的传说,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讲的是镇上一个千年火车头成了精,开始渴望人世间的温情,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高大的古装绅士,穿着一袭华美的银白色长袍,夜夜探访娼寮里的姑娘。妓女们难以忍受火车精在她们身上开机器似的摧残而渐渐憔悴,变得不成人形时,聪明的老鸨教妓女在枕边暗暗放一把剪刀,偷偷剪去银白长袍的一角。第二天,小火车站的火车头,左上方凭空缺了一大块,像是被剪去了似的,老鸨的疑心果然被证实了……[3](p13)有研究者由这个故事生发开去,探讨施叔青笔下的男性群落,“这则看似不起眼的小故事,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作家的创作理念中,并形成了她最初的男性观。”[5)在这篇文章里,火车头被看成了男性形象,对它的冷漠自私的揭露和对它渴望人间温情而不得的怜悯被看成施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表现,她写出了男性世界的阴暗,但不一味地批判鞭挞,而是发掘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和人性原因。从这里可以看出施叔青的冷静和敏锐,也可发现故乡的传说在形塑她的情感结构时起到的作用。从中也可以看出,在施叔青的故乡,对妓女没有激烈的批判和厌恶,她们如同在沈从文笔下出现在边城里等待相好的水手归来的娼家一样,不管是在自己还是他人眼里,都自然而平静。施叔青的很多作品中都有妓女的形象,她们大多平实善良又不乏紧跟时代的能力,“香港三部曲”中的黄得云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这个女子打破了以往妓女既定的命运,在香港经济的腾飞浪潮中扮演了一个强手的角色,一跃成为一大房地产商。尽管用一个女子为主角来写香港的历史有着对于香港曾为殖民地的象征意味,用受尽屈辱的妓女隐喻香港的命运。但是构思出这样的传奇,和施叔青心里对妓女的没有恶感仍然有着一定的联系。小说不可避免的会渗入作者的情感,从而影响到作者笔下的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创造出这样一个曾为妓女又堪称时代骄子的黄得云,是作者对这一形象的社会地位内心不存芥蒂,也从某些方面折射出她对这些底层女子善意的期待。
在施叔青小说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海盗。在我们熟悉的文化中,海盗并不是一个光辉的形象,看到它,一个用一块黑布蒙了一只眼的凶神恶煞的莽汉就跃入脑际。可是在施叔青笔下,海盗往往承担了乱世枭雄的角色,是海上的霸主,是义气的化身。《行过洛津》中的海盗涂黑,在成书中是作为背景出现,可是在施叔青的一篇序言中曾提到,因为过于偏爱海盗这一部分,险些偏离主题:“在我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曾经被嘉庆年间滋扰东南沿海的海盗时间所深深吸引,特别是几年之内海盗船只先后六次在鹿港海面游弋,佯装来犯,最后却只是虚张声势……反观南部的府城北部的艋舺连番遭到海盗袭击杀戮,人人自危。种种疑点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发挥写作者的想象力,创造了一个人物检视这一段历史的奥秘,虎虎地写了好几章。重读初稿,发现这部分与整个情节不仅不连贯,显得很突兀,更严重的是对小说的肌理起了负面的作用。理性上明知如此,情感上却舍不得把它删去。”[3](p15-16)后来放下笔,跟随圣严法师打坐了数日才得以神思清明,回到主干。施叔青对海盗的偏爱由此可见一斑。有趣的是,在她的妹妹李昂的《迷园》中也出现了一个与涂黑颇为神似的海盗朱凤,他被描写成台湾商业最初的发起者,甚至被迷园中朱影红的父亲朱祖彦引为自己家族的先人。他说“海盗有大队所谓夷艇,有枪有炮,目标是往来海上的大商船,要抢的是货物”,“至于那些残害来台移民,将人赶到沙州淹死的,只能算是恶人,称不上海盗。”“我们要记住,是像朱凤这样惯于乘风破浪、不怕牺牲生命的硬骨汉,才能克服种种艰难,成为海外移民先驱,开辟了新航线,并且,繁荣了海上的贸易。”这么相似的对于海盗如此高的评价,应该是和姐妹俩共同濡染的童年传说分不开的。而李昂在《杀夫》中频频出现的“后车路”、“龙山寺”也在《行过洛津》中反复出现,不能不说这是家乡为她们打下的印记。#p#分页标题#e#
不可小觑这些传说的力量,儿童在其中长大,那些神怪诡异成为他们成长中的养分,不知不觉建构着他们的意识世界,给他们相似的好奇心,影响他们的兴趣走向,进而影响到未来的惯用语言和关注点。如徐复观所说:“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到了忘记他的土生土长,到了不能对他土生土长之地分给一滴感情,到了不能从他的土生土长中吸取一滴生命的泉水,则他将忘记一切,将是对一切无情,将从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真正的生命。”[4](p156)可能是看多了离开乡土就写不出东西的例子,施叔青非常珍视她的家乡给她带来的梦和惊诧,对原乡几乎有着病态的眷恋。于是她说“我是那种以写作为家的人,居无定所,写作是我的居住之地。”[5](p315)这片略带魔幻色彩的土地给施叔青一生的创作以滋养,成了她写作永远的原乡。
二、基于使命感的创作
20世纪以来,“历史”已经颠覆了我们千年来对它的信任。当然这里所说的历史特指“历史叙事”,而不是已经过去和正在过去的历史事实本身。新历史主义的发起者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与驱魔师》中曾说:“由于20世纪中期英美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崩溃,解构的出现于是成了一种解放性的挑战,它一方面友善地将文学文本还原到与其他文本一视同仁的状况,同时又对非文学中实证主义的肯定性,即历史事实这一特殊的领域发起攻击。历史不能脱离文本性,一切文本都不得不面对文学文本所揭示的不确定性的危机。”[6]历史与文学的混杂是20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发现,它由一时一地一人的偶然怀疑变成人们勇敢坚决的正视,进而成为共识。继人的主观书写的复杂性和语言的重要地位被发现和确立之后,如何书写历史这一问题也被重新思考。而为了补足传统历史书写中的漏洞,文学开始分担这个任务。许多历史故事被重写,用小说的形式,再现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和细致入微的人物感情,试图使平面的历史立体起来,重新发现历史大事记中的因果和不被记入的小人物。这是我们至今仍在经历的过程。台湾在1987年戒严令解除之后,文学开始解冻,许多以前不得碰触的话题得以浮出水面重新讨论,尤其在文学中开启了对“二二八”事件的回顾反思,引发了一个重建历史的大潮。
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很多,包括文学类和非文学类,比如《二二八台湾小说选》(1990)、《沉尸、流亡、二二八》(1991)、《二二八事件辑录》(1992)、《“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1994)等等。这一时期出现的重建历史的小说潮体现了政治宽松之后台湾知识者清算历史的愿望。这时施叔青不在台湾,但对台湾文坛的新动向也应该不至于无知,可是她并未因此写一部历史小说出来,只是在1999年重回台湾后写了部长篇小说《微醺彩妆》,以90年代末期盛行台湾的红酒风潮为切入点,借以展现世纪末台湾“粗糙却生猛”的消费文化。这或可以理解为施叔青没有一直呆在台湾,没有受到其重建历史的浓烈气氛的影响,也与她出生在风雨飘摇的岁月的尾巴并没有亲身经历那个血腥的时代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她一直以来的关注重心并不在政治或社会大事件,而是个人心理、情爱。诸如政党纷争带来的灾难、台湾人的国族认同、“二二八”、“美丽岛”等问题从来没能长久地吸引施叔青的注视和思考,她关注的是人,尤其是由于种种原因甚至是没有原因的怪异畸形的人。她的大姐施淑曾用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她的早期小说,指出施叔青的早期小说由于“在叙事结构和文字肌理间的冲突,以及她的小说世界的细节、情境之喧宾夺主,因此在解读时,似乎不能由这些大名词———也即前引刘登翰所说的现代病态感的观念入手,而应该由那最早时用以构成她的独白世界,稍后则以内在文本(innertext)的兴致介入小说之中的幻想、梦魇进行分析。”[7](p172)她指出对施叔青小说的解读不应从宏观把握,因为它们深具女性言谈的特征,比如流动性和感触性,没有固定的形式、形体和概念。由此可以反观出施叔青的关注重点,是个人化,而不是宏大叙事。但是在上世纪末,她有了写台湾三部曲的想法。施叔青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从最初的创作中就体现了充分的女性特质,被施淑评论为非常具有女性意识的女作家。而女性书写(假设它存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铺排情欲———或以此反抗传统,或以此作为一种隐喻。身体是女性主义者的一个战场,在此生发出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的战争。上世纪60年代走上文坛的施叔青就经常用这种方式表达她“惨绿少女时代”的惊诧和恐惧。
台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充分学习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时候,大至经济政治,小到生活方式都在全盘西化,文学领域也在努力“向西看”,各种西方文学、哲学思潮都以极快的速度传到台湾。一本台湾70年代出版的《文艺美学》中提到现代社会(当然指台湾)“跨进二十世纪,作为人们精神交通的各种工具,日益进步……我们一日之内所涉猎的见闻,有时竟比我们祖宗一辈子所闻见的总量还要多。这样非同小可的事实,若以心理上刺激反应的例子来说,少见必定多怪,见闻多了,则对于一切也渐趋于平淡了”,于是“沉淀在现代人心里的许多感触,渐渐在积聚酝酿,酿成了现代对于所谓世事的独特看法和与古不同的生活态度。人们的情感很僵硬,同时又很锐敏,面对着变动迅速的现实,由无从捉摸而进至怀疑的地步。”[8](p75)这是对60年代的台湾真实的写照,那种动荡的现实对作家心理的冲击使得“现代派”得以出现,年轻的施叔青也是其中的一份子。这里记录的“多怪”的现实正是施叔青初登文坛时所经历的,因此除了“被艳称保存着浓郁中原文化”的故乡鹿港梦魇魔幻气氛的影响,这个逐渐现代化的社会和欧风美雨也迎合着她的写作,使本来就关注个人情欲和情感世界的她得以在同样以此为标榜的社会土壤中得到力量,写作才华得到鼓励,于是自然而舒展地写下去。不过从她的“香港三部曲”开始,施叔青的关注有所转变,她开始“不甘心被冠以明摆着局限的女性作家称号”,“对自己过分投入笔下的女人,与她们没有距离的共同呼吸生息的写法感到无比腻烦”[9],开始走出女性作家纤细敏感的个人世界,想要为香港写一部历史了。“香港三部曲”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它以黄得云从一个妓女到在香港房地产界呼风唤雨的商业奇才的传奇经历,贯穿了香港百年的历史。对此研究已有很多,对它的价值作了充分的挖掘,不过简单来讲,这部小说仍然以女性身体作为殖民地的象征,以情欲作为书写的主线和香港与英国之间微妙复杂关系的隐喻。这样一部“大河小说”[10](p179/287)并没有改变作者一直以来有意无意的女性主义关照和写作倾向。#p#分页标题#e#
一般说来,一位写作者比较熟悉一种写作方式,常用的也只有一种文体,这种独特的方式和文体写作就是他自己的风格和言说方式。突如其来的转型必定来自作家身处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像施叔青这种在几个岛上不断漂移的人,其写作的转向是种必然,而“香港三部曲”就是这个过渡阶段的成果。1998年施叔青接受简瑛瑛等人的访谈,表示写完《两个芙烈达•卡罗》之后,想要写一本以台湾为主的长篇小说,她表示:“我可能就不会那么样地偏重男女情爱了,会比较从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的层面去看。”[11](p136)而这种转向除了和施叔青个人的际遇和思考相关之外还有一个社会背景。张瑞芬对此有一个梳理:“作为一种抵拒男性父权的声音,女性家族史的书写,就当代广义的华人文学而言,从美国华裔谭恩美《喜福会》、《接骨师的女儿》,到严君玲《落叶归根》,香港作家黄碧云的《烈女图》,大陆女作家张戎《鸿》、虹影《饥饿的女儿》与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在在体现了近年来女性书写主题从情欲到历史的过渡。”[12]大陆女作家对情欲的关注和台湾有一个大概30年左右的时间差,但从“情欲到历史”的过渡是她们所经历的一个相似的过程。对施叔青来说,在写了几十年的个人世界之后些许的厌倦、远离家乡多年之后对故乡的深深想念以及重建漂流中的自我的要求为她创作的转变做出了充分的铺垫,于是在朋友的鼓励下和对自身完满的追求中她拿起笔,为原乡立传。施叔青在2005年出版的《驱魔》中有这样一段话:“望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哥德式飞扶壁,线条构架凌空错综交叉,我不禁陷入沉思:米兰公爵挽住时代巨轮,建了这座哥德式教堂,难道他不知道这种火焰式的建筑形式在那时代已经烂熟到无新意了吗?……反观我自己,十多年来沉浸于历史,把自己掩埋在史籍文献堆里,终日与泛黄的旧照片为伍,孜孜不倦地苦写一本又一本的历史小说,其实文学和所有的艺术一样,无不是在反映时代、创造潮流。米兰公爵的盲点是他一厢情愿地认定信教虔诚的子民适合哥德式的教堂,而我自不量力地苦写历史小说,美其名曰是为了使命感。”[13](p30)
长时间写历史小说给施叔青带来身体上的疲惫和心灵上的困惑,甚至怀疑自己的努力也许是个不合时宜的笑话。但我们在体会到作者的辛苦和精疲力尽之时也能一窥她对“历史”的看法———她明白文学是在反映时代、创造潮流,即使冠名为历史小说也摆脱不了现代观念的纠结而真的回到历史。如罗伯•格里耶所说“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盛行一种小说形式,这种小说形式实际上说明了一种秩序,即一种思考和在世界上生活的特殊方式。”[14](p3)因此20世纪最主要的学术———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都化作一个个不经意的情节、人物、格调出现在她的这部“历史小说”中。这是无法避免的,清醒的施叔青也不曾刻意逃离它们以使自己的小说显得客观,而是选取了一种豁然的态度,由小说的需要出发,不管什么主义或方法,当用则用。而在“香港三部曲”中,施叔青有种使小说更加客观朴实的刻意,因此对黄得云的传奇经历轻描淡写,用一种并不很适宜的淡笔描画宏大磅礴的事件和起承转合中丰富的人物,用王德威的话来说就是有种不自然的刻意了:“黄自遇屈亚炳后,一心从良。施叔青也刻意以'平淡无奇的文字',来叙述黄的寻常百姓生活。从浓艳到质朴,施原是要以修辞风格的改换,凸显黄由绚烂到平凡的过程。但施忽略黄的大起大落原本就不平凡;就算她不操花柳生涯了,她的境遇依旧离奇。小说后半部写黄辗转受雇当铺,开始成为商界强人,是要让人侧目的。施力作谦虚抑的文辞,反而显得矫情。”[15](p286)而接下来回到台湾后创作的《微醺彩妆》就自如得多,这部《行过洛津》更是既充分展现了她的历史意识、又没有让历史意识淹没小说本身。米兰•昆德拉将小说视为对“被遗忘了的存在的探寻”,所谓被遗忘的存在就是或远或近的历史,施叔青建构了一个迄今为止尚不为人所知的存在,使她的小说提供了某种认知,并使之以此区别于故事。这既是从以往的创作经历中吸取经验的结果,更是辗转的生活给她的一份厚礼。
三、自我的建构和历史的建构
施叔青没有选择很多大河小说所采取的家族志的方式再现历史,而是选取了一系列底层小人物,通过描摹他们的生活轨迹,把洛津由盛到衰的历史刻画出来。这是所有看过她的小说的人有目共睹的,同时也为批评家所津津乐道。这种以小搏大的书写方式对于大河小说来说是一种突破,但是对于施叔青的写作特色和特长来说却是“吾道一以贯之”。以惯用的手法进入新的创作空间从而为施叔青带来了文本的极大丰富,这合情合理并且可以预料。而颠覆传统的历史叙事———大事记、大人物记———最简单易行而且效果显著的办法莫过于由女性来书写,这样女性可以用与生俱来(是与生俱来还是逐渐形成可以讨论)的细腻敏感倾听宏大历史空间之中的无声之处,那些曾经沉默的小人物的痛苦与挣扎得以再现、发声,历史才不再是平面。正如谢拉•罗伯森所说,打破沉寂之时,正是真正理解沉默之日。施叔青抓住历史中不曾发声的点,将那些一直被压抑而寂然无声的群体搬到纸上,还他们一个历史,也给自己寻到了一个根。
其实传统的历史叙事之外,关于伶人的传说和野史并不少见,他们因其暗含的香艳历来吸引人们的眼球,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生活佐料。可是如施叔青这样不带倾向性地使其成为小说的主人公,且让他们成为连接社会上层和下层的重要角色的写法却很少见。这用施叔青写作的女性特质解释已嫌不够,不得不引入她独特的人生经历了。施叔青辗转于三个岛上,台湾、香港、纽约曼哈顿,它们各有自己的文化标签。在不同的文化中生活,遭遇到心灵撞击自然不可避免。而且不止转换一次,仅就台湾来说,她几次离开又几次回来,每次回来都见到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过如此的起落,必定对于人生的漂泊和世事之无常心有戚戚,她后来情愿皈依宗教,多少有这样的原因。而自己的事业又每次都要从头来过,没有强悍的承受能力是难以度过的。也正因为此,在评论家笔下,施叔青是个不大容易归类的人物。她出生在台湾,显然应该是台湾作家;可是又嫁了个美国夫君,在纽约居住数年,因此可以算是流散作家;随丈夫在香港住了17年,又被称为香港作家。每种文化身份都是短暂的,不够确定,因此很多研究者都把她留待别处去谈。比如张诵圣《文学场域的变迁———当代台湾小说论》中,谈了袁琼琼、朱天文、王文兴,没有施叔青[16];刘亮雅《情色世纪末》中第一章是《世纪末台湾小说里的性别跨界与颓废》[17],这个题目和施叔青的创作何其贴合,可是她却以李昂、朱天文、邱妙津、成英姝为例,没有论及施叔青;肖薇的《异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海外华人女性写作比较研究》中写了聂华苓、严歌苓、谭恩美、汤婷婷,没有提到施叔青;蔡雅熏也是追随夫婿离开台湾来到美国,“我深深体会着,无论在国外多少年的华人,工作如何兢业勤奋地融入当地社会,口中如何褒贬中国或台湾,情感的故乡与历史的故乡,两者都令人魂牵梦萦,游子心中是如何也断不了中国的民族脐带。”[18](p8)#p#分页标题#e#
施叔青初到美国的感情其实和她是很像的,创作中也有所流露,可是在蔡雅熏的《从留学生到移民———台湾旅美作家之小说论析1966~1999》中,不管是六、七十年代还是八、九十年代,论及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朱秀娟、平路、李黎等,却也没有施叔青;范铭茹在《众里寻她———台湾女性小说纵论》中论述了50-90年代女性小说,讲到了李昂、朱天心、袁琼琼、苏伟贞、於梨华,写到了“嫁出国的女儿———海外女作家的母国情结”、“来来来,去去去———六、七十年代海外女性小说”等等,里面也都没有论及施叔青。范铭茹在题为“台湾现代主义女性小说”的一章里谈到了施叔青缺席的原因:“在现代主义影响下投身写作行列的三名女作家,施叔青、李昂与季季,也都因此时期创作时间不长或因后来的发展更出色,较少将她们纳入为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家”。[19](p79/80)可见,施叔青虽然是重要的作家,可是因为她的漂移使研究者难以归类,因此对她的研究多有空隙。除了专章的“施叔青研究”外,如同台湾女作家、香港女作家、流散女作家的框架是难以容下她的。是施叔青的变动不居造成了这种归类的困难,而变动不居的人最容易产生身份的不确定感。犹太人有他们的宗教,华人流散作家只能依靠他们的笔。因此失乡的人最需要建立自己的原乡,他们需要知道生存于这个世界上,时间上的位置是什么,空间上的位置又是什么。他们对此内在要求之迫切远甚于身份确定的作家。她和妹妹李昂,虽然同为台湾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家,但是姐妹俩不同的生活经历使她们对写作有了不同的取向。李昂也有赴美国学戏剧的经历,可是两年之后取得硕士学位就回到了台湾,她几乎没有机会感受施叔青所有的身份困惑和飘零之感,因此她就没有姐姐施叔青为台湾立传的渴望和内在要求。
在只能以写作为原乡的施叔青那里,寻找和重建自己心目中的原乡是必然的选择。她写洛津的历史,实际上是在建造自己的根。施叔青把为家乡和自己寻根的愿望结合在“台湾三部曲”的创作中,并在第一部就写了她的出生地———鹿港———最繁华的年代。这是她最熟悉的地方,也是孕育了她不曾改变的写作基调的地方。她花了很长时间阅读历史资料,把自己埋在泛黄的老照片之中,希望在心理上还原一个古老的由移民走向繁盛、又从繁盛走向衰落的洛津。王艳芳在对比了施叔青、严歌苓、虹影以及王安忆的跨越多元文化和多重时空背景的作品之后提出:“华文女性写作对史料的发掘、对日常生活的还原以及对性别关系的建构都是为了想象和重构女性历史,但最终目的却又不是为了女性历史的重构,它只不过是在女性历史的重新想象中寻找接近完整的自我。”[20](p131)对于施叔青来说,《行过洛津》是她继以女性历史建构香港历史之后的又一个自我完成的努力。由此可见施叔青是以寻找原乡、建构自我的内驱力为原乡立传,在以文学建构台湾历史的同时重新建构了立于传统中的自我,使身份漂移的自己不至于失根。外在的劝解和朋友的压力只是一种催化剂,作为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作家,施叔青以自己的香港、纽约经验建构台湾史是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