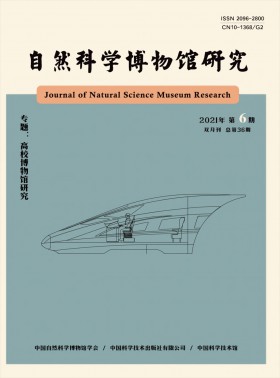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湘女的自然文学,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为一种旨在考察、表现自然与人之间关系,思考、探询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的文学类型,自然文学否定视人为万物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强调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万物的相互依存与密切联系。2011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推出了四卷本“湘女自然文学精品”丛书。在近27万字的精选篇幅里,作家湘女以她手中一支充满钟灵之气的笔,多元、生动、淋漓地宣扬着“万物一齐”观,也即倡导人与自然共生共荣。 一、美妙的篇章 “文学有个古今一贯的要求或道德,就是把一组文字,变成有魔术性与传染性的东西,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由‘争斗’求‘完美’一种理想”[1]。湘女所创作的文本极富潜移默化性,是熔铸了作家个性气质、情感倾向与美学追求的“言语”。 (一)同构于“水云”的文体湘女的自然文学系列,打破了文体间的藩篱,阅读时,读者无须刻意辨识哪是小说、哪是散文,这诸多作品的交集在于挥洒自如的结构。譬如《边寨童趣》起首:这里的山都很高,山之间是深深的谷。金水河就像个蛮乎乎的山野孩子,淘气地顺着山势左曲右拐,蹦蹦跳跳。这是条界河。河这边是中国的云南,对面是越南的莱州。两岸是一样的山,山上都有茶园和竹林;一样的稻田,田里都漾着明澈的水;一样的村寨,屋顶上炊烟袅袅……最有趣的是河两岸奔跑尖叫、大声呼应的男孩女孩,都是黝黑发亮的皮肤,都是浓厚茂密的黑发,都是顽皮可爱的笑脸,都是明亮清脆的嗓音…… 在这三个颇为散漫的段落之后,湘女用了吃芒果、采玉荷花、听水碓“唱歌”等场景而非依照时序来结构作品,将气力付诸一系列富于情致的片段上:傣族女孩制作出精美如小工艺品的芒果香包,以备在游戏中抛给自己心仪的人;走在文静、优雅得仿佛工笔画的玉荷花树林里,孩子们禁不住放轻了脚步;利用水碓碾米时,谷粒慢慢裂开,泛起一层金色的糠壳……这些温润、微馨的碎片并不增加故事的精彩程度,却让读者收获到一种深远的韵味。 再譬如《森林传奇》里写一个猎人因无法拔出被他追捕的雄鼷鹿钉在他胳膊上骨头里的一对小獠牙而再也无法持枪、用刀,文末以一句超越了情节内容的“只有孩子们在担忧,雄鼷鹿没有了那对小獠牙,怎么保护它的妻子和孩子呢?”留下缺口,引读者去联想、感受作品意义的延伸,让读者与淳朴、善良的童心相遇。湘女在她的诸篇作品中以从容、暇誉的笔墨成就了白云出岫、风行水上般的文体结构,而对此种结构的自觉应用,还源于作家的天赋才情与她出乎定法的实践。 文学作品的形式总是粘附于内容,作品结构体现了作家的认知图式与思维图式。湘女自然文学系列中自在的文本结构不尽然是技巧使然。刘禹锡的《送周鲁儒序》有“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语;湘女自己在《赶马人的城•前言》里回忆她“对老家湖南的印象是一片雨。那雨从我们出门就淅淅沥沥,飘个不停。天空雾蒙蒙的,地上一片泥泞。雨中,奶奶撑着一把红油纸伞,抱着我看湘江”[2];吴然《在儿童散文的路上》里说“我总觉得‘云南’这两个字弥漫着一种不可言喻的浪漫与芬芳”[3]……楚地圆美流转的柔波、潺潺不断的霖雨,云南变幻多姿的云霞、各具特色的自然地理与民俗风情共同培育了湘女的精神品格及创作心理。按照格式塔心理学的原则,当某种外部事物所体现出的力的物理样式与人类情感中所包含的力的样式结构相同、相近时,这种情感的式样形式、节奏或某种感性状态的完型结构便会通过艺术符号这一特殊的“肖像性符号”呈现出来。人类情感所具有的形体上无定性、性质上动而不静、发展时无定向之特点,与水、云流动、飘浮不居的物理特征相一致,决定了作家在寻求情感表现方式的过程中“规矩虚位,刻镂无形”[4]。于是,湘女的自然文学作品也便自然而然地生成了“初无定质,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5]的文体结构。 湘女行云流水的文本原不乏情节性与戏剧化,譬如《雪门坎》里年轻帅气的巴郎赶着马途经雪门坎,与一位姑娘两情相悦,在一次约会后巴郎送姑娘返家,眼见她推开栅栏门将入自家的木楞房,他才转身回了宿营地。次日,启程去西藏前巴郎想再见姑娘一面,骑马赶到姑娘家却得知姑娘一夜未归竟是被雪狼下了毒手。譬如《桫椤寨》中当年13岁的老山猫在随其父“下坝子”时因遭遇盗马贼而莫名入得桫椤寨,那里有长了怪眼的燃烧的树兜,有野蛮的人群,有恶心的汤水,有眼珠乌黑、嘴唇猩红、笑容粲然且浑身披挂五颜六色珠串、会仰头大笑的小姑娘月儿。在那里,伺机想要逃跑的老山猫被人发现之后又被月儿策马劫走,后来月儿勒住马拖着他跳下马背,咬牙切齿地逼问他想怎么死……不过,此类情节性与戏剧化时常在由段段文字交织而成的起伏的情感流程中得以情境化。《雪门坎》里,是一片世事无常的悲凉与巴郎对心上人的负疚与痴情;《桫椤寨》里,是一方诡异但神奇的“月亮上的寨子”的幻境……由是,湘女的作品实现了一种流动的平衡乃至意境的隽永。 (二)“陌生”而“熟悉”的修辞湘女笔下不时可见“陌生”而“熟悉”的遣词造句。它们,是作者生命情思外化而成的语言符号。所谓“陌生”,是说湘女避开“直寻”而创造了一种通过不平常的词语组合以供读者久久回味的语言效果;所谓“熟悉”,则指这些不乏奇崛的语句恰恰是源于“童心”的认知与想象叠加而出的世界的模样。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有一首《每当看见天上的彩虹》:每当看见天上的彩虹/我的心就激烈跳动/年幼时如此/成年后如此/愿年迈时依然如此/否则,不如让我死去/儿童乃成人的父亲/愿我的时日一天天地/都由天生的虔诚串起。[6] 儿童何以成了成人之父?答案在于以赤子之心观看彩虹或其他一切事物,方可保持对事物本初的真切印象。湘女笔下的《喊月亮》,有着一个“违背”了常识却同时也因为充盈着童心气息而让人叫绝的标题。通过记述一段“边疆大山上的月亮,是孩子们喊出来的”的故事,湘女用心、用情地为读者塑造了一个自然、自在的对象世界。它既是一个客观的边地自然空间,也是生活在那里的孩子们天真、朴拙的心灵世界。读毕全文,回头再看“喊月亮”这个奇妙组合的动宾结构短语,读者更不难体会到湘女运思的新鲜、别致。#p#分页标题#e# 再如《神秘的菌子山》开篇:“每年五月之后是云南的雨季,这时,天上的云变得又厚又重,像一只只鼓鼓囊囊的大包袱。包袱皮儿一散,掉出来的全是雨”。“鼓鼓囊囊的大包袱”这一喻体并不符合常规的“美”的标准,但因其直观、准确、饶有童趣而具有了别样的美,甚至于,一场陡然降落在云南这块神奇土地上的雨,也因此被写得犹如一次魔术。就这样,生动、“准确”的修辞展示了湘女作品语言的魅力。而类似例子在湘女的自然文学作品中俯拾皆是。 二、尊贵的主体 无论采用第一人称与否,湘女的自然文学作品中始终有一个怀揣人文关怀的审美主体。面对无数审美对象,或自然的一隅、或人间的景象,这一审美主体都能敞开自己,将一己幻化至其中,始终为着人类与自然结成的种种关系或欢欣,或疼痛。 “去看看一粒种子怎么变成大树,去听听花开花落的声音,去摸摸被露珠洗过的天空,去数数被夜色擦亮的星星……去和那些饱经磨难,却依然勇敢顽强、奔跑如飞、目光似水、童心像小鸟一样扑闪的山里孩子一起,围着篝火跳舞,迎着山风唱歌,站在山的最高处,大声呼唤月亮吧。你就会惊喜地发觉,人与自然的关系,突然间变得如此纯真透明、简单亲近……”[7]以“万物一齐”为核心主题的湘女的自然文学作品,歌吟大自然的伟力,感恩大自然赐予人类的无尽物质、精神财富,重拾流逝了的诗意生活,救赎迷失的人性,经过作家艺术审美的浸染与消化,字里行间显现出一种个性光华与人格力量,是谓“尊贵”。 湘女的自然文学大致两路: 其一,人天相契型。 “我有时逃开自我,俨然变成一棵植物,我觉得自己是草,是飞鸟,是树顶,是云,是流水,是天地相接的那一条水平线,觉得自己是这种颜色或是那种形体,瞬息万变,去来无碍。我时而走,时而飞,时而潜,时而吸露。我向着太阳开花,或栖在叶背安眠。天鹅飞举时我也飞举,蜥蜴跳跃时我也跳跃,莹花和星光闪耀时我也闪耀。总而言之,我所栖息的天地仿佛全是我自由伸张出来的。”[8]乔治•桑的“自由伸张”说同样适用于湘女的自然文学创作。在以“人天相契”为主题的一类作品中,主角几乎都是身居边疆、与自然共生的孩子以及童心未泯的成人,这些拥有“一双远离喧嚣的眼睛”、“一颗滤去杂质的心”的人们,能够“乘着风的翅膀,循着云的足迹,沿着一千条从天外飘来的小路”,在“高远的边疆大山”与“缥缈的云雾深处”同大自然里的一切生灵进行交流,不论刚刚冒尖的竹笋、豆豆花儿、南瓜、村野里的平凡植物,还是高傲的白鹇、聪敏的猎犬、“越狱”的懒猴、灵巧的鱼鹰、母性的狸猫、痴情的黑颈鹤,以及那些为“我”这个成人所珍视的黑蜜蜂、壁虎、萤火虫、袖珍青蛙…… 湘女将充分的活力与动人的意味赋予了自己笔下的世界,她总能发现并挖掘出蕴藏在拥有赤子之心者们身上人性的点点滴滴,欣赏、尊重他们纯洁、美丽的心灵世界,并力图用笔墨呵护这一个个心灵世界。同时,通过书写“从冰峰雪岭到深峡密林,从平坝河谷到山间田野,在马铃摇响的每个黎明,在篝火映亮的每个月夜,仰视着那一张张风雨磨砺过的面孔,体验着他们的艰辛、忧伤和快乐,你就会深深懂得生命的意义、活着的勇气”[9]。湘女还把这份呵护延伸成为一种对在工业社会里深感被“异化”了的人们所心驰神往的精神家园的守望。 其二,警醒告诫型。 作为一个坚定的“万物一齐”观的持有者,湘女在其自然文学作品中所探求的人与生灵的平等共生方式,并不限于人类单方面的行动与付出以维护自然与人的和谐。湘女笔下的动物、植物们,无不具有自己的生存智慧乃至区分善恶、辨别美丑的能力及标准。譬如在收入《猎人的故事》与《山狸猫金爪》的诸篇作品中,那一个个毫无敬畏之心、笃信“人类中心主义”的猎人、采菌人、摩托车手、采燕窝者、捕“江猪”者等,在对自然的无度索讨乃至残忍伤害时,他们未必都不能遂愿,但无论得手与否,贪婪与自大使得他们无一不在自然的伟力面前显得如此猥琐、丑陋、狼狈,注定因为自己的不义陷于惶恐、孤立。而那些倚仗自己的生存本性、生存智慧对付乃至严惩侵犯者的自然生灵,始终保持了自身的意志与尊严。面对它们,人必须省思该如何自我约束、主动节制,并有所敬畏。 屹立于湘女自然文学作品中的这个审美主体,时常以辽阔的眼光注目、审视包括人类在内的世间一切生命,于是,湘女的笔下生出了一种博大的美,且这份博大与她文中书写对象的巨细无关。从高山大川到一花一草,从庞然大象到“顶多就三个苹果那么重”的鼷鹿,均承载了湘女那份广阔的气度与坚定的信念:“我们难以逾越物种的生命形态,但我们拥有共同的生存空间。作为大自然的一员,我们在对待同是自然生命的生物时,任何践踏与轻视,只会带来无穷尽的懊悔与沮丧。大自然会以种种神秘的方式,传递着它的仁慈与温厚、威严与警示,让人类一点点收敛、省悟,一点点孕育出悲悯之情,培育出珍重之爱,树立起敬畏之心。”[10] 三、丰沛的文情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11]。刘勰把文情比作织机上的经线,视其为文章构成的命脉。对此,湘女尤其善于以形象为纬线、情感作经线,编织出极富美感的图景,她的笔下,沉潜着丰沛的情感。 (一)外化了的真切体验 日常阅读中不难遇到有写作者喜欢把自然化作恍若宋词元曲中的意象,发挥它们的抽象审美意义,仿佛因此,作者便可俨然以一副隐逸之士的面孔引领读者体验某种逍遥之美。殊不知,技术性抒情的背后只是一片空洞,借未及心灵抵达的书写对象来“急疏利锁、顿解名缰”很容易陷入虚妄。那样的文字里洋洋洒洒荡漾着的,不过是硅胶质地的情意。文学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湘女的创作也不例外。她笔下的场景营造、细节设置时见艺术虚构,但这些虚构皆因源自作者深厚的生活积累而真实、诚挚。#p#分页标题#e# “如果不是以活生生的人为依据,逐渐掺和或加上合适的成分,而是以观念为出发点,那么我是从来不敢‘塑造形象’的。我由于并没有多大的天地来自由想象,就总是需要一个立足点,以便由此迈开坚实的脚步。”[12]生活积累为创作奠定坚实基础,不仅对屠格涅夫如此,对一切作家都如此。湘女曾与少数民族孩子们同一间教室学习,曾在距国境线不远的村寨“插队落户”,曾赴有“夷方”之称的人迹罕至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生活。数十载里,她的足迹几乎遍及云南每一处角落。颠沛的生活成为馈赠,丰裕的阅历使得湘女与边疆的人、物、事、景建立起了息息相通的关系。作为一个具有灵敏感悟力的创作者,湘女擅长于从审美对象中捕捉到容易为常人所熟视无睹的光色、声响、味道、触感、形象、节奏,继而探幽、揽胜,独辟蹊径地从中提炼出富于审美价值的哲思意味。 譬如《绿色童话》里那条勐巴拉娜大森林里能够如向导般引人“曲里拐弯地绕遍”整座山林的最长的青藤,历经艰辛回到原来的家园(一棵大香树上)的经历,如同半部植物版的《奥德修纪》。这则童话所表达的“归乡”主题如此真切地写照了人类精神的浪迹,足以触动从孩童直到老者的广泛读者群。湘女笔下的自然天地,均具有成为令人不时眺望甚至企盼返身其间的“故乡”的本质。它们有着质朴且多姿的地域风情,它们有着清丽或神秘的山野韵味,它们以自己天光云影之下的开阔旷达、亲切坦荡频频召唤着一度倚仗所谓自身强势对自然野蛮相待,从而制造了统治和进步假象的人们。对于湘女,“故乡”并非一个单纯的词语,它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学、生理学、心理学、诗学、美学的意义。 (二)复调型的美学韵致 “复调”本为音乐术语,是多声部音乐的一种主要形式。“复调音乐”由两组以上同时进行的声部所组成。这些声部各自独立却又和谐地统一为一个整体,彼此形成和声关系。前苏联文艺学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将“复调”概念引入文学批评,用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描写出了生活的多种可能性与人性深处的矛盾,而非灌输一种绝对的、千篇一律的思想,从而使得他的小说既具有辩证的色彩,又包含开放的可能。可以说,衡量一部作品成熟、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便在于考量其文情的信息量,也即作品是否波澜层叠、明暗交织呈现出一派繁复的人性景观。德国作家米切尔•恩德曾说“据我们的经验,孩子原则上丝毫也不关心的主题,或是孩子完全不理解的主题,是不存在的。问题是你如何用心,用头脑来叙述那个主题”[13]。湘女从不因为自己在儿童文学的范畴内书写人与自然而浅化作品。她的文字,具有一种复调构织的美学韵致。 《大树杜鹃》、《无字的情书》皆写在边疆支教的青年女教师面对“离开,还是留下?这是一个问题”的故事。《无字的情书》里的“我”虽然没有因为由一串红豆所“写”成的特殊的情书就此留在小学校放弃回城,但也因此推迟了回城的行程而慨然去赴一场与一位陌生的倾慕者的约会,并在不畏风雨的赴约途中领略到了山岭在夜色中如诗如画的景象,眼前浮现出“我”所执教的宛如童话城堡般的小学校。而《大树杜鹃》结尾,“我”感念于乡民们的热情、朴实以及对知识的憧憬而决定留下,同时向着在远方念大学的恋人阿林发出一句“你真的不来了吗?”的问语。这个设问如此意味无穷,尽管儿童读者或许暂时还敏感不到湘女在这个句子里用了一个表示已然的时态助词“了”,但由此也拒绝了给这个故事缀上一个常见的灿烂、圆满的尾巴。 优秀的作品旨在激活读者的感悟,而非宣布某个一清二楚的结论。那位男友阿林他究竟来是不来,湘女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这种开放所产生的多义性,对于每一名实在地生活着的读者尤其是处于成长中的小读者来说愈加可贵。因为读者们由此得以随着自己人生不断的渐进而不断理解作品更多的面向,这些面向可以互为补充、修正甚至于取代。而这,才是人与世界真正的模样。唯此,故事里那位青年女教师得失选择的个性与她的价值观才愈加凸显,并春风化雨般予以读者影响。在礼赞自然的同时注重刻划立体人性,是湘女自然文学作品中尤其值得称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