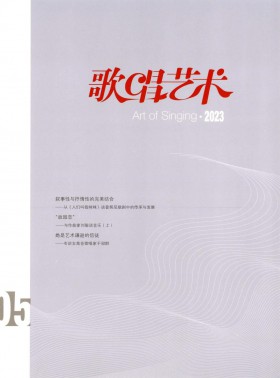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艺术理论与艺术体验的关联,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作者:简圣宇
建立起一整套理论体系,一直是理论家们执著的追求。甚至连德里达这样以反体系著称的学者,围绕“延异”概念而建构起解构主义理论,在其猛烈抨击和试图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实质上已明显呈现出建立“反体系的体系”的态势。艺术理论自当有其相对完整的体系性,因为一套自相矛盾、凌乱不堪的理论是难以让人信服的,更不消说用以观察和阐述自己所面对的艺术现实了。
我们不可片面否认体系化对建构一套完整的艺术理论的重要作用。但现实是,不少流派所创立的艺术理论往往为了追求其完整的体系性,一旦建构起一套体系之后就变得固步自封,拒绝面对不断涌现的纷繁复杂的审美问题。不少评论者也习惯于在展开批评之前,就预设好一套理论,不管遇到什么作品,不经过审慎、具体的文本细读就直接给出评判。他们文章的观点不是在文本细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是倒过来,以成规式的理论体系去框限、覆盖鲜活的具体文本,无论文本的思想内容如何,其分析过程都千篇一律,结论都是预先设定好了的。这就明显违背了学者们孜孜不倦地建构理论体系的初衷。
正如崔绪治所言,理论的价值在于它超出了一时一地的实践及实证经验的范围,而具有普遍范式的意义。它帮助、指导人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经验具有条理性、逻辑性。人们也总是利用自己所具有的理论,理解和整理各种经验,把符合自己的理论框架的经验看作可理解的,把不符合自己的理论框架的经验看作不可理解的。拘泥和保守的人们拒斥、摒弃后者;灵活和进取的人们则珍视后者,乃至收到启蒙思想、发展理论的效果。[1]在今日的艺术实践中,应该如何对待艺术理论与体验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关键是要立足于自身真切体验进行文本细读,同时兼顾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外部视野。只有秉持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相结合的研究原则,才能避免文艺评论沦为那种脱离个体生命实际体验的空泛话语堆砌,真正回归评论本有的审美品格。
一、艺术实践远比艺术理论丰富和复杂,应当警惕在进行艺术评论时,艺术理论凌驾于艺术实践之上。在运用艺术理论进行艺术评论时,应主要着眼于艺术实践(要特别关注艺术实践过程中激发作者创作的生命体验和欣赏者的审美体验),在实践的过程中针对实际存在的问题调整相应的理论。理论的建构应当是动态的,一旦固化的理论与具体实践脱节,那么首先应该反思和重构已有的理论。艺术理论是在艺术实践基础之上的总结,其最根本的作用在于总结艺术实践的经验,以指导新的艺术实践。假若将艺术理论置于艺术实践之上,必然导致理论役使实践的问题。
当下的艺术评论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一是完全脱离理论的指导,进行纯粹的技法分析。比如让评论者分析《步辇图》,他就论述该画的构图、色彩、人物造型,论者煞费苦心地描述画中的唐太宗面目如何、神情如何,来使和宫女又如何,虽认真详致,却没能通过自身的真切体验进入到艺术作品的丰厚意蕴之中。二是评论者大谈艺术理念抽象的“道”的层面,将目光过度聚焦在形而上的观念上,刻意回避、越过那些承载着“道”的“艺”的具体感性的层面,也越过自身的审美体验,甚至舍弃作品本身,有理而无据,流于空论,这其实是使艺术理论凌驾于艺术实践之上。甚至用抽象晦涩的理论,把劣质的艺术作品打扮为旷世佳作;或用道德批判替代艺术批评,等等。两种现象中的第一种,较容易被意识到,因为它往往是初学者容易犯的错误,也比较容易得到修正。但第二种情况就比较复杂,是各阶段的论者都容易犯的错误,其脱离艺术的感性维度、疏离个体生命体验的缺陷,极易被理论本身的抽象性、严整性、体系性所掩盖;不仅如此,艺术评论的这种“空谈”倾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艺术创作,致使观念先行,甚至是抛却了具体可感的艺术形式。
曾有学者在《中国嘉德2007秋季拍卖会:当代艺术》宣传册上提出:“艺术从根本上讲不是发明创造,而是一种表达,形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隐含的那种意愿。”这一观点实际上继承了康定斯基以降的蔑视绘画基本功的反传统观点,单纯就理论本身而言,在一定意义上有其道理。但着眼于具体的艺术作品时,就会发现它的偏颇。因为艺术如果抛弃了具体可感的形式,而只沦为观念或思想的传达,也就失去了作为艺术存在的价值。就我们的审美经验而言,对于那些抽象派的涂鸦式作品,如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杰克逊•波洛克那些在帆布上肆意地泼溅油漆、颜料完成的“画作”,无论是《蓝色无意识》(1949—1950年)、《黑与白•第5号》(1952年)、还是《集中》(1952年)、《气味》(1955年),即便作者真的在其中寄寓了什么伟大的思想感情,也因为缺乏可观可感的外在形式结构,使观者感到迷惑。更何况,艺术与哲学的区别就在于,哲学是理念,而艺术则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当代艺术抛开形式而成为一种观念表达,它其实不再是“艺术”而成为一种四不像的“类哲学”。这并非艺术之福,却标志着艺术之死。实际上,就连现代主义艺术家自己对此也颇为忧虑。1950年,艺术家瓦萨雷就曾感慨“:艺术家变得不受限制了。任何人都可以自称艺术家,甚至于自称天才。任何一点色彩、草图或
者线条,在神圣的主观感受的名义下,都可以算作是一件作品。冲动压倒了技巧。诚实的功夫本领被偶然奇想、临时凑合的东西所顶替。”[2]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许多琐事,此类琐事有时候只能成为些散落在新闻媒体的趣闻版块上的消息,谈不上与严肃的理论有什么瓜葛,可实际上它们往往潜藏着一种对权威化理论构成致命威胁的力量。比如,2009年,墨尔本一家著名画廊的负责人得到了一批署名为“安德烈”的作品,这批画作在澳大利亚艺术界引发轰动,得到的是一片溢美之词。然而后来画廊和评论家发现自己力捧的“画坛新星”安德烈,竟是一名牙牙学语的不满两岁的女童埃丽塔•安德鲁!这则新闻看似无关紧要,其实戳到了许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画家、理论家最致命的痛处:他们之所以声称那些谁都看不懂的涂抹之中寄托着深邃、复杂的伟大思想和感情,是因为太过仰赖康定斯基以降的那一套理论———在观赏具体艺术文本之前就已预设了固定的分析套路,用理论代替评论,用观念驾驭感受,其结果导致了艺术实践的衰微和艺术生命力的枯竭。#p#分页标题#e#
不少“画家”正是借此来糊弄他人的,他们搬弄些云山雾罩的绘画理论出来唬人,声称看不懂他们所倡导的艺术就等于不懂艺术,其本质是在掩饰自己连基本功都没打好就想一步登天当大师的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心态,而给他们唱赞歌的艺术评论家不是被忽悠了就是别有用心。其实评论者和欣赏者只需要将分析的立足点建立在个人的真切体验和真实感受上,就能知晓很多所谓“抽象派画作”中的“深邃、复杂”的思想感情,其实只是皇帝的新衣。无论是理论家、评论家,还是大众,在面对具体的艺术作品时,都应具有独立感知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具有独立的批判意识,不要被高高在上的理论吓到,也不要被貌似高深莫测的理论体系所蒙蔽。我们欣赏一幅具体的当代抽象派绘画,可以借助某个理论提供的特定视角去审视它,但不能因为理论而背离自己的真实体验。艺术理论是为艺术实践服务的,理论为实践提供指导性意见,并且随着实践的深入、变化而调整自身,其身段应当是柔软的,态度是谦虚的。艺术可以表达思想和观念,但绝不能脱离具体真切的感性形式和生命体验。理论凌驾于实践、理论驾驭甚至覆盖真切体验的问题,应引起艺术理论界的反思。
二、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面对具体的艺术作品时,往往套用既定的理论和结论,抽离了生命体验,审美维度缺失,造成对艺术的伤害。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拓展了新时代文艺现象的批评空间,将艺术文本作为社会文化研究的对象。但是,它在开拓研究视野的同时,日渐脱离了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相结合的研究原则,脱离实际的艺术体验。其与社会学、政治学等的联系愈加紧密,却与艺术欣赏中最根本的生命体验愈加疏离,漠视文艺作品感性表面背后的复杂脉络,解构和破坏艺术作品的整体性。文化研究多涉及性别、阶级、族群之间矛盾冲突的被遮蔽状态,为此其凭借的重要理论资源包括具有极强批判性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然而这些用以反击既往的话语霸权的理论资源,本身已日渐变为一套唯我独尊的霸权话语,以至于文化研究日益变成一种无所不包、全知全能的理论体系。它以独白替代对话,蛮横地企图把一切鲜活的现实问题都硬塞进自己预设的框架当中去阐述。阅读一些凭借文化研究理论分析影视作品的评论文章,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明显的弊病:在细读文本之前,他们就已经对作品预先设定好了评价的模式和结论。对于作品的优与劣,其评价参照的不是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其结论也不是来自于文本细读和审美体验,而是从文化研究的“政治正确原则”出发,套用大而空、僵而死的既成话语来对之进行审视。
比如作品中男性的戏份多了,就可以归类为“女性的被忽视状态,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和迫害”;而如果女性的戏份多了,也可以归类为“女性的被看状态,表现了女性的客体化和尤物身份”。又比如作品中还是使用既往拍摄手法,也可以归类为“走不出陈旧模式的窠臼”;借鉴了好莱坞的新模式,又可以归类为“对西方的献媚和精神上的被殖民状态”。总之,无论文本中发生了什么,这些理论都能在自己的体系内,对之加以“完美的、能够自圆其说的”阐释。评论家们甚至不需要去认真细读文本,只需要借助预设的理论体系,先造好一个批评框架,再按照这个框架去摘取文本的章节、镜头作为自己阐述的佐证,就大功告成了。就像清代政治斗争时所利用的“文字狱”资源,反正要收拾你的,先预先定好了罪名,再去寻章摘句、网罗编织罪行就行了。这些评论文章不是从文本走向理论,而是用理论框定文本。比如,对电影《金陵十三钗》的评论,就多是从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角度去分析、阐述的,这非常符合社会学、政治学批评对文本进行伦理层面等分析的传统套路。但在此类站在道德制高点或国族命运上进行的批评中,影片中具体人物角色的人性挣扎、荣辱悲欢都被忽视,只被当成评论中无足轻重的琐碎要素而已,所以最后只得了个“情色爱国主义”的评价。在艺术作品中,命运的偶然性是个言说不尽的母题。命中注定在某个时刻,有的人和事会把你灵魂的某部分带走,再注入新的,使你变成另一个人。人之命运的迷离难测,以及人的不甘和反抗,成为大多数文艺作品关注的核心,但这些生存性的经验与个体化的生命却往往被宏大叙事论者所漠视。赫拉克利特说“,在地狱里才嗅得到灵魂”[3]。《金陵十三钗》最闪光之处,即把各色人物置于一个地狱般的境遇当中,让他们各自现出自己的灵魂,以供观者思索。遗憾的是,在社会学、政治学的批判声中,这关键之处被屏蔽掉了。
这与之前的中国台湾电影《海角七号》在内地的反应有几分相似,影评人多是从家国情结出发,斥之为“隐藏着对日本殖民文化的怀念”。可实际上,这部电影最动人的,恰恰不是关于那些宏大的政治话语的内容,甚至也不是作为主线的摇滚乐团的艰难创立,而是穿插在影片中的作为个人叙事话语的写于60年前的《致友子的情书》。情书的片段极佳地表达了这种情绪:“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我只是个穷教师,我爱你,却必须放弃你。”感动观众的,是昔日那对恋人被时代的洪流挟裹着的绵绵苦痛,这种苦痛早已超越了时代和民族的范畴。我们在痛恨日本侵略者的同时,难道应该连被裹挟于其中的日本老百姓也要一并憎恨吗?把复杂得难以言说的内心情感,简单化地视为“媚日”,这种概念先行的评论,条条有理却又大而不当。再往前推,上世纪80年代电影《一个和八个》上映之后所遭遇到的,亦是此种宏大的政治话语覆盖个人情感的境遇。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如若把艺术喻为一只螃蟹,那么艺术创作实践和生命体验是蟹之身,而艺术理论则是蟹之壳。蟹壳的出现是为了保护蟹身,随着蟹身不断生长必然要褪去旧壳,长出新壳。正常的情况也当是蟹壳(艺术理论)适应蟹身(艺术实践和体验),而非反之。如果蟹壳非要桎梏蟹身,那么蟹身就难以得到发展,而蟹壳的作用则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当理论异化为“套路”,那么理论就开始走上其僵死之路,因为理论此后不再面对风云变幻的现实,亦不再面对纷繁复杂的个体生命体验,拒绝对自己独白的状态进行真诚而痛苦的反思。它面对任何问题,都像守旧者一般只管按照旧的模式来阐释,至于这个阐释对象是否是与之前旧物完全不同的新物,它统统不管。艺术评论如果过度仰仗理论的套路,将直接导致缺少个性和灵性,其中高深莫测、晦涩的词汇俯拾皆是,却鲜有那种令人耳目一新、为之击节的神韵。#p#分页标题#e#
三、艺术理论为艺术体验提供指引,但不能支配艺术体验。言说艺术的关键在于回归生命体验本身。艺术评论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层面,即评论者自己首先要以真切的生命体验切入作品的内在结构,再从这一体验出发,对作品进行审美评价。评论者给予的评价,必须源于自身体验,而非某个外在的理论体系。艺术作品乃是创作者凭借其特有的敏感性,捕捉自己内心所经历的那种极奇妙的生命体验,通过特定的言说方式表达出来的产物。因此为了真正理解和把握作品的内涵,必须将作品当作可亲可感的对话者,欣赏者在亲密、开放的对话中创造性地复现、观照创作者寄寓其中的内涵。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理论的过度阐释。好的艺术作品,能够为丰富我们的生命体验打开一扇门;优秀的艺术评论,能够指引我们洞悉自身、社会乃至宇宙世界。反之,糟糕的艺术作品和艺术评论,则导致我们的感受和视域愈加狭窄,走向封闭而难以提升。
诚如牛寒婷在《生命的感性之维》中所言:“生命感性经验的易逝与多变、丰富与细腻、偶然与神秘、活力与创造、挣扎与突围,是人的基本生命力量的体现,是艺术活力的真正源泉———就此而言,艺术的活力呼应的正是生命的活力。”[4]艺术作为一种对生命个体存在状态的审美观照,要表现的核心内容是对“存在”的感悟和反思,特别是对作为“此在”、即在世的个体生命自我存在状态的感悟、困惑和反思。在海德格尔看来,人的本质就在于他在“世界中的存在”。人的存在,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存在,每个人都无法脱离自己的族群、地域、文化等社会性属性。但人同时也是微妙独特的个体性存在,他拥有属于自己的个体世界,这个世界与一个个他人的世界构成了一个共在世界。个人世界离不开共在世界,但也不应被共在世界所遮蔽。对个体生命而言,世界首先表现为对他本人的独特呈现。外在的物质世界是纷乱复杂的,正是个人的真切体验把这个纷乱的外在世界在自己的思维中统摄起来,赋予其可亲可感的生命意义和审美意味。他所见的那个“世界”并非世界本身,而是本体世界在他脑海中的映射,他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就是如何在他那里呈现的。“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5]同样,对于一个对生活没有过深刻体会的人而言,这个世界在他的生命中是平淡乏味和缺少意义的。你不能指望一个市侩庸人在面对梅兰竹菊时,能够如同诗人、哲人那样产生思古之幽情。
艺术离不开美,但艺术本身要大于美,它包含着对个体存在和世界存在的深切思考。人们欣赏文艺作品时,在对其意境感怀动容之际,难以用富有逻辑性的理论语言将之表述清楚,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艺术理论难以概括、描述这种审美者在难言的意境中与对象融合无间的美妙状态,其阐释也往往会破坏这种兴会神到的妙境。艺术要展开言说的地方,恰恰是艺术理论所止步之处。纯理论论述追求严整的归纳和概括,而艺术作为一种内在生命体验的外在表达,其精神的丰富与复杂则难以被理论所框定。生命体验是帮助欣赏者感知、把握艺术作品的内在意蕴,藉此切近创作者的情思并与之进行精神沟通的关键途径。可以说,艺术的诞生就是源于人类把自己的生命体验表达出来、与他人分享和对话的冲动。
在艺术活动中,人们通过艺术作品这一中介来分享彼此对于存在的不同理解和表达。每个人的视界都有局限性,因而需要通过他人的理解和表达来丰富自己。借助他人对生命体验的独特理解和表达,我们的精神有机会在更广阔和深邃的视域重新审视自己、发现自己,进而在更深的层次上思考和体悟生命的真义。审美评价的关键是要立足于真切生命体验,而生命体验最重要的是个体生命面对艺术作品时那种独特、微妙的境遇性体验。每一个生命个体由于其视野和期待的不同,在具体艺术体验上有着极大的差异性,对同一幅绘画、同一部电影、同一句诗文,每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都会有自己的衡量和评判标准。对艺术作品的理论评价就像一部史诗,需要凝聚大多数人的认同感,需要不断对之进行明确的建构,但这一过程同时也遮蔽、覆盖了个体差异。而对艺术作品的个体体验则像一页日记,它是属于个人的,所有欢愉和哀伤都藏在幽微之处,情感、思想状态只有经历者自己才能最真切地了解,这种体验往往是难以转述、复现的,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面对艺术作品,艺术评论者应当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而非从他者或任何理论的视角出发,去判定和做出结论。不经个体生命体验而先验套用理论进行的评论,其描述、阐释和思考的那个“事实”,有可能只是涉及了广袤、深厚的土地表面之下薄薄的一层,而无视薄层下面巨大的生命奥秘和无限的艺术真谛,其结果就是只抓住表象,却忽略掉了最为真实、生动、深刻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