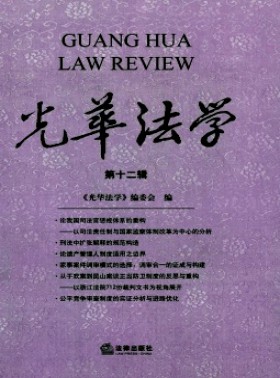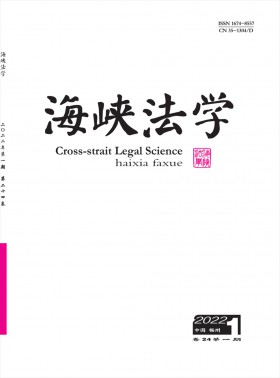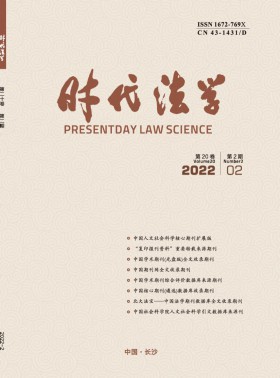从周到清近三千年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1〕。延宕千年的佛经翻译使佛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儒家思想最终共同构建了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深远的影响〔2〕。最近两次的西学翻译则开始西学东渐,开启了中国的近现代化〔3〕。对于清末以来中国的翻译,中国知名学者、学术翻译专家邓正来先生认为,从1862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时起到1989年,国人的西学东译运动,高潮有三次。“这些翻译工作对于造就中国的学术人才,沟通中西文化,建立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乃至推进中国的学术水平都发挥了积极作用。”〔4〕西方翻译史上古罗马对古希腊、欧洲各民族国家对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的继承与移植的巨大成就,显示翻译的不可替代的作用〔5〕。邓正来先生还认为,中国在没有自己的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情形下开展学术翻译工作,其最终目的在于构建并发展中国自己的学术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6〕。所以可以说,在当今中西学术格局强弱分明的情况下〔7〕,中国的法学翻译背负着发展学术汉语〔8〕、发展中国学术的使命。然而,在目前中国法学学术自生能力还较弱的学术体制下,虽然法学翻译的学术地位并不高,与法学翻译作品于中国法学界所展现的实际影响极不相称〔9〕,但法学翻译对中国发展自己的法学与培养中国法律学人所具有独特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10〕。虽然评价当今法学翻译于中国法学的影响,不是本文设定的主题,也已远远超出笔者的能力,惟不可否认,在法学翻译的学术地位并不高的情况下,译者为原文文本得以传递所进行的语际转换而付出了巨大的心力与财力,其精神与执着令人敬佩。2004年,中国知名法律学者苏力先生曾提出,当今存在着法学翻译热〔11〕。而书店里书架上的法学译著也是密密麻麻,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那么当今的法学翻译究竟如何?又如何应对存在的问题? 一、对当今法学翻译的调查与分析的理论基础与框架 古今中外传统的翻译论者大都以丰厚的翻译经验为基础〔12〕,当代的翻译研究或翻译学学者也很少翻译经验匮缺者〔13〕。笔者虽无高深的法学翻译造诣,但长久以来关注当今的法学翻译,并自觉的进行翻译训练与翻译论著的研读,故而根据翻译理论,对当今的法学翻译情况进行了考察,以大体确定当今的法学翻译状况;在翻译文体体系的参照下,甚至与文学翻译比较的基础上,笔者析清了何谓法学翻译;通过创建大体可具操作性的法学翻译的技术性构成系统作为考察与分析框架,并将当今的法学翻译与清末民国和西方翻译情况进行比较,对当今中国法学著作翻译展开描述性研究,试图去确定当今中国法学翻译的实际状况〔14〕。笔者创建的法学翻译的技术性构成系统,是指在法学翻译过程中,参与完成翻译的各项能力,其本身包括除去译者的法学翻译伦理精神与法学翻译观之外的语言文化涵养、学术研究、翻译技能等。法学翻译观,是指在总体上如何看待、理解法学翻译。语言文化涵养,可分为浅陋、一般、精通、高深四个档次;学术研究,可分为浅陋、一般、深入、高深四个档次;翻译技能分为朴拙、一般、娴熟、高超四个档次。此项调查与研究的主体部分,是一百多部各个不同时期的中外文译著〔15〕。考察统计的内容包括:译者译书时的学术背景、译书时的年龄、译者的语言文化底蕴、翻译的目的、翻译的时间跨度、翻译理论学习与翻译技能训练、译者言的类型〔16〕、是否有项目资金支持、参考资料与帮助人员、翻译组织、翻译策略或翻译观、译者注释等。以上这些项目,有的部分笔者进行了完整的数字统计,部分因资料付之阙如无法查知,抑或是由于查找太过于费力而尚未能给出统计数据,抑或有的项目并不能进行实证的调查,而是仅进行不是很严谨的印象式论断。本文的论述正是基于以上的考察统计与论述策略。 调查所进行分析研究的框架如下:译者按其学术身份区分为学者型与学生型〔17〕;翻译组织类型区分为独译型与合译型,合译型又区分为化一式合译、平等式合译与领携式合译〔18〕;序言分为研究性序言或批判性序言、概评性序言与译介型序言,其中概评性序言又分为浅显的概评性序言与深入的概评性序言〔19〕;翻译之动机类型分为名利型与学术型〔20〕;根据译文与原文的比较关系,把译文区分为质信型与归化型。学术翻译总类型〔21〕将之分为研究型翻译〔22〕、学习型翻译〔23〕、介绍型翻译与功利型翻译。香港知名翻译学学者张南锋先生曾指出,翻译研究涉及太广,又困难〔24〕,所以笔者的研究,或许只能得出欠缺严谨的偏颇肤浅之论。 二、法学翻译是什么? (一)当代中国法学译者的翻译观 西方翻译学界著名学者埃德温•根特勒尔宣称,大多数学者认为1976年在匈牙利召开的翻译大会上,翻译研究(translationstudies)作为独立科学而建立起来〔25〕。而西方翻译学界另一著名学者苏姗•巴斯尼特又宣称,到1991年翻译研究已不仅仅是科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严肃的学科〔26〕。翻译研究已经彻底摆脱以前只言片语的经验论说,而称为翻译学(Translatology)或翻译研究(TranslationStud-ies)。而我们的法学翻译者是如何看待翻译的?他们与西方的翻译论者,甚至与中国古代的翻译论者进行比较,结果将会如何?根据所调查的当今法学译著的译者言和某些法学学人已经发表的关于法学翻译的文章,笔者得到的总体性印象是:中国当今的法学译者,似乎大部分对翻译本身,包括翻译理论与翻译技能,了解不够;在进行翻译前,他们绝大部分,似乎没有进行过专门的翻译技能训练,也缺乏翻译理论的阅读;而与翻译直接关涉的语言文化涵养与对原著的研究,很多译者似乎难以达到学术翻译的基本要求。大多数法学译者的翻译观,实际上似乎是把翻译看作是懂点外语抱本词典就可以的事情。比如,最普遍的是,当今很多译者都宣称信奉“信、达、雅”,有的还基于自己的理解与经验对“信、达、雅”给出自己的寓意〔27〕,可是他们并不了解严几道先生本人的“信、达、雅”的意义,似乎也不知严先生为什么、又凭借什么而提出这三个字〔28〕。有些法学译者关于翻译的论断,虽然表现出他比较广博的知识与想象力,但从翻译研究的知识体系来看,却有闭门造车的嫌疑。中国著名翻译家劳陇先生曾对当时中国翻译提出严厉批评,用这一批评来评定当今中国的法学翻译,似乎也同样恰切:“实际情况是:一方面进行盲目的实践,另一方面则不断制造空洞的理论。”〔29〕那么,为何法学翻译界对包括翻译理论与翻译技艺的翻译知识,表现出的是这样的匮乏呢?笔者推测,部分原因是由于整个社会,也包括学术界,普遍缺少对翻译的深刻认识。正如张南峰先生所说,“都觉得翻译是雕虫小技,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30〕(二)法学翻译是什么法学翻译究竟为何?有位法学译者曾不断向笔者强调,法学翻译不同于文学翻译,法学翻译就是要“信”。可是其对于文学翻译是什么,翻译又是怎么回事不甚明了。翻译是什么?此问题,无论中西或古今,给出的答案多是:翻译是艺术〔31〕,或翻译是一门技术,同时又是一种艺术〔32〕,或翻译是科学〔33〕。#p#分页标题#e# 当今著名翻译学学者刘宓庆先生认为,翻译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其中科学性是翻译的基本属性,是第一位的,艺术性是第二位的属性。翻译具有科学性,其基础在于双语所指的同一,其实质是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涉及原语与译语在语义、语法、语音、逻辑等四个方面的转换过程。这一复杂的转换过程是科学的加工过程。刘宓庆先生的宏伟心愿是通过对比研究,最终找到汉英的对应矩阵。翻译的艺术性具有普遍性,因为翻译的全过程始终存在着艺术选择和加工以及艺术优化的任务。翻译者虽然要受原作“情、志、意”客体条件限制,但在语际转换中却需要变通,具有原创性,在此一限制和变通中收放有致又独运匠心,正是翻译艺术的真谛。翻译戏剧、诗歌是艺术,翻译法律文书、科技资料、宗教典籍也都是艺术〔34〕。笔者完全认同刘宓庆先生的观点。据此,法学翻译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在翻译理论上如何定位法学翻译?或法学翻译包括哪些构成要素?笔者认为,法学翻译是学术性、科学性与艺术性三位一体的统一。刘宓庆先生在翻译美学上进行研究,将文字性翻译分为文艺性翻译与非文艺性翻译〔35〕,因社会科学论著或学术论著的文体是论述文〔36〕,所以法学翻译属于非文艺性翻译。但刘宓庆先生同时强调“在翻译艺术特征的总体关照下,翻译原语非艺术作品与翻译原语艺术作品一样,都是科学运作和艺术运作的统一性语际转换过程:并无高低之分,只有层级之别。”〔37〕虽然从一般意义上讲,“非艺术作品要求的是基础层级的审美判断,要求运用基础层级的翻译艺术手段”,“而翻译艺术作品要求的则是综合层级的翻译审美判断,要求运用综合层级的翻译艺术手段”,〔38〕但很显然,这两种翻译在艺术性上是同质的,而在翻译技能上的同质性更是无庸赘言。况且有些学术论著的文学性,未必就低于普通的文艺作品〔39〕。而笔者考查的当今法学译者对此的看法,却显然将社科学术翻译与文学翻译彻底隔裂开,并未认识到二者在翻译艺术上的同质性〔40〕。其表现之一就是用“信”或诸如以“坚持以直译为原则”作为托辞,似乎为由于翻译技艺匮乏而硬译的阻滞重重、艰涩拗口的译文找借口。于是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学翻译有两个必然的平行问题,其一是对法学论著信息的准确把握,其二就是恰切的甚至高超的语际转换。社会科学论著的论述文体属性在于论说,因此法学翻译的首要或根本原则,就是传统译论上的忠实原则〔41〕,也就是寻求原文文本中的那个“确定的唯一”。而文学性问题的处理,根本就不是人云亦云的“雅”。对此的处理,现代翻译论者提出的处理哲学与方法,绝不是简单的“信”。〔42〕 然而,一部优秀著作所涵摄的信息量是如此的庞大与繁杂,译者如何能将著作翻译得忠实,那就得仰赖译者对原著具有精深的研究;如何在译文里能够再现原著,使其“穿上新装”并“被注入新生”,〔43〕此便是翻译技艺问题。所以,法学翻译要有精深的研究,要有相当的翻译技能,甚至高超的翻译技巧〔44〕。但是,笔者认为仍有必要根据刘宓庆先生的论断而再强调指出,从翻译本身来看,法学翻译本身并无什么独特之处,与其他翻译在翻译艺术性上是同质的。 三、法学翻译的技术性构成要素诸问题 (一)语言文化涵养要求 那么,技艺高超的译者会做什么呢?恰如18、19世纪的法国教士、诗人、翻译家雅克•德利尔所论,“他会研究两种语言的本质。”〔45〕清末语言学家马建忠对此有精妙的描述,可值全文录下:“…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滋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意,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析之所以然。……”〔46〕翻译对译者的原语言与译语言的本能的双语要求,是不言而喻的,而且翻译论史上,关于翻译的语言能力要求的论述数不胜数,已成为陈词滥调〔47〕。现代的翻译研究也已假定译者在语言能力上是胜任的。笔者在此要强调指出的是,译者要有对语言的深刻体察,尤其有对原语言与译语言差异的深刻认识,甚至深入的研究,而不是一点皮相性感想〔48〕。可是当今我们法学译者的中文与外语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到底是否达到可以翻译出基本合格译作的要求呢?马建忠先生于1896年对其以前与当时的翻译状况的评价,于当今的法学翻译似乎仍具有参考价值:“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语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达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达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乎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为天下识者所鄙夷而讪笑也。”〔49〕笔者认为,倘若没有能力用外文写出比较流畅地道的文章,那么也就不大可能达到理想翻译的外语水平要求。 可是我们现今庞大的译者群中,究竟有几人具有这种能力?关于当今译者的中西文化知识涵养,笔者以为与其语言文字涵养的情形是相同的。而文化涵养则为译书所必备,不可忽视。明末著名学术翻译家李之藻认为,“一般的翻译,只是传递普通信息的‘口舌之人’。思想概念、学问知识的翻译,是民族间的相互理解,还是深入本民族文化内部的重新诠释的创造。”〔50〕著名哲学家、翻译家贺麟先生曾研究严复的翻译,而认为严复“所选译的书,他均能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与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51〕,也正因为此,张君励先生认为严复的“物竞”“天择”“名学”“逻辑”是精妙的翻译创造〔52〕。笔者所调查的清末民国的31部法学论著译者,信息明确者16人,仅其译著能提供零星信息者9人,总共可知者20人,皆为学者;受过传统国学教育的,又有留学经历的,确定的有12人,估计留学经历的占全部译者的份额不会少于百分之80%;其他未查找到足够明确信息者未必就没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如序言里可知者强我、骆通、陈汝德等。而反观当今,我们的译者呈现出学生化的趋势〔53〕,即使他们的学术水平、语言文化涵养或许并不比有些教授、学者逊色,但依赖辞典翻译出版,正像林语堂、朱光潜等诸位学者所论,似乎很不够〔54〕。而我们1500年前的玄奘大师,其学力深厚,通彻华梵语文,能够自在运用文字融化原本义理,真堪称我们法学译者永远的楷模〔55〕。#p#分页标题#e# 传统的压制社会制度造成的思想与语言的贫乏〔56〕,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阙失与汉语本身的特点,都使现代汉语在表述精细的西方式学术时力不从心。古汉语是我们盲目丢失的本土资源〔57〕。而且古汉语具有凝练与深沉文雅的高贵气质,非常适合学术术语的创撰与学术高贵气质的表达〔58〕。这一点从对当今译作与清末民国译作的比较中分外明显。清末民国译著虽然大都倾向白话文〔59〕,但由于译者古汉语与国学的高深修养,其译文因大量使用古汉语而词汇丰富、深沉优雅,极富学术的高雅品味。德语史与德国学术史上也曾有过复兴古老德语的经历与成就〔60〕,况且由于新中国众所周知的原因,语言雅致的复兴勃发的学术曾被否弃,此一学术的继续发展之路亦曾被并阻断。通过翻译,取源古汉语语汇,创撰术语,改良句法,从而创建与发展能够表述精细事物与逻辑的汉语的法学语言,是中国法学进行自生发展的基础。 (二)法学翻译的学术研究要求 学术研究是进行法学翻译的本能要求,是前置性条件。那么这种研究应达到什么程度?理想目标就是“关于原著的全部知识”〔61〕,译者需取得原著者在译语界代言人地位,甚至超越原著者。笔者调查的西学基本经典的译者与已查明的20个清末民国时译者,他们都是学者,有些是某领域的权威;而现今中国的法学翻译虽然教授、学者为主导力量,但学生型译书却占很大一部分,且出现学生化趋势。考察的“外国法律文库”14本译著译者,都是学者,其中大部分是当今法学界的知名教授,可称为学者型的翻译丛书;考查的4部“博观译丛”的译者,都是学生;迄今规模最大、影响也很大的“美国法律文库”的情形如下: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可供图书目录》2006年第4期,美国法律文库已出版50部书,其中领携式合译为22部书,其中有一本普通的美国法律教科书的译者者除了一个人为教授外,其余全部都是学生,译者总数达26人。当然笔者承认,现今译书的翻译质量很可能与译者的学术职称与头衔并没有必然的正比关系。 西学基本经典的31部译书中,有研究性序言或批判性导读的18篇,最长的批判性导读长达52页,最短的也在10页;其中译者自己做批判性导读的16部书,占全部译书的百分之52%;清末民国时期译书的序言多为一二百字的译介型序言,其中雷宾南的《英宪精义》的序言为深入的概评性序言;“外国法律文库”的15本译书,研究性序言2篇,其余13部译书为译介型序言;考查的“美国法律文库”的11本译书,概评性序言6,译介型序言5;“博观译丛”的4部译书全部为译介型序言;苏力先生的译书与其主编的“波斯那文丛”,苏力先生都为其做了概评性序言;西方法哲学文库的5部书,有1部书为研究性序言,3部为深入的概评性序言,1部为译介型序言。邓正来先生的译书大部分都有研究性序言,严复先生的译书则有大量的按语。由此可以看出,西学译者更倾向于为译书附加研究性序言,而现今译书有研究性序言的则是凤毛麟角;西学译者对所翻译的原著都有精深的研究。调查还发现与民国与西方译著相比,我们现今的很多译者言,往往对原著者与原著动辄以“伟大”呼之,他们往往径直借用他人如西方论者或出版社、报刊评语做的“伟大”评语。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译者倘若未自己进行独立的、深入的研究〔62〕,如何发现原著者与原著的伟大?在西学译著里,译者对原著与原著者做的评价,往往暗隐的体现在他自己的批判性导言里,其评价只进行深入的学术分析与探微,而并不是动辄以“伟大”呼之。 (三)法学翻译的翻译理论与技能要求 那么,法学译者进行法学论著的翻译出版,是否应该进行翻译技艺的训练?90年代翻译学或翻译研究在欧美已成为独立的学科,翻译培训与翻译资格考试制度也正迅速发展,在有些领域已实现翻译资格准入制度〔63〕。而对于中国而言,即使社会普遍认为,翻译是抱本双语辞典就完事大吉的伎俩,但对法学界的译者而言,对翻译不知却是不可谅解的,因为无视其他学科的存在,不愿接受相关学术传统的教导与审查〔64〕,这也与学术原则与学术精神不是很切合。况且中国翻译史至今已有三千年,出现过许多成就卓著的翻译家,也留下了他们关于翻译的许多宝贵经验论说,对此我们不能拒绝无视。鲁迅先生曾讲,“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65〕林语堂先生曾明确提出翻译训练是翻译艺术的三大倚赖之一〔66〕。刘宓庆先生不但强调翻译技能,且其专著《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文体与翻译》等都直接或间接涉及翻译技能。西方论者彼德•纽马克也明确指出翻译的技能要求〔67〕。翻译恰如烹饪,翻译技艺恰如厨艺,即使各样原料与各式厨具一应俱全,但若无厨艺如何做出美食?中国知名学者梁治平先生曾讲到,对比先辈,我们的译者怎能不是胆大妄为,怎能“不愧死无地矣”。〔68〕 时光已远逝,可梁启超先生当年的愤怒之声仿佛尤绕耳畔,令人警醒:“……是对于著者读者两皆不忠,可谓译界之蟊贼也已。”此外,调查的译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初涉译事之作,况且学生型译著绝大部分属此种情形。为击退乱译,获得更好译本,鲁迅先生曾发出“非有复译不可”的呐喊〔69〕。而我们须知,中国的学术出版基本上还是完全的商业化运作的,再加上出版审批制度带来的经济负担,所以商业利润追求与出版成本的压制,使原著在同时期出现多个译本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对一般学人而言,其购买、借阅译著依据的往往是原著与原著者的学术声望,而不会太关注译者为何人。所以,译著往往就成为学界进行学术研究与讨论的重要依凭。所以我们的译者应该善待我们的读者,善待中国学术,尤其初涉译事者,而不应该让我们无辜却热切追求的学人,甚至让整个民族来承担我们翻译不能的责任。或许,就应像一位知名法律学者私下告诫学生时所说,(法学)翻译,你50岁以后再做吧!(四)法学翻译的译者组构与用工调查还发现,“西学基本经典”译书与清末民国译书大部分是独译的,而现今译书是合译占大部分,而独译占小部分。考查的“西学基本经典”31部译书中,独译25部,占百分之80%;化一式合译1部;平等式合译5部,但从其序言上来看,平等式合译者相互协调并寻求、接受广泛的指导,比较趋向于化一式合译;领携式合译为0。清末民国的31部译书中,独译23部,占百分之75%,化一式合译2部,平等式合译6部,占百分之20%,领携式合译0。考查的“外国法律文库”的15本译书,其中独译6部书,占百分之43%;平等式合译8部书,占百分之57%,领携式合译为0。考查的“西方法哲学文库”的3部译书都是独译。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可供图书目录》2006年第4期,“美国法律文库”至2006年底已出版50部译书,其中独译19部书,占百分之38%;平等式合译9部书,占百分之18%;领携式合译22部书,占百分之44%,合译总数41部书,占百分之62%。更为令人吃惊的是,现今中国的法学翻译,出现有史以来或许可能是世界上的独创:大规模的领携式合译。现今还有一独特现象,即有一些译者,他们往往习惯性的进行平等式合译,可是他们就是不曾独自翻译过一部书。笔者以为法学翻译之道在于独译,而且在笔者看来,除去原著本身是集合而成的编著之外,实在很难找到适合合译的法学论著。个中原因在于,法学翻译是由法学研究与语际转换两个平行的要素构成的,而这两个构成要素在本质上都具有个人独立性,除非两个或多个译者同时具备对原著与原著者相同的知识和相同的翻译处理。而这又是绝不可能的,否则《纯粹理性批判》的译者诺曼•肯普•史密斯(NormanKempSmith)就不会无奈的发现合译的不可行,否则西方更不会出现同一学术原著,有时竟会有多个译本的现象。。笔者也发现译者是否坚持独译,似乎与其学术精神、学术涵养与翻译能力有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翻译史和此次调查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p#分页标题#e# 与西学译著比较,现今中国法学译者的翻译用工基本上是少得可怜,长的往往一年,短的则数月,总体情况属于课余型而非专门翻译型,仓促应付型而非从容充分型。而西学基本经典译著的翻译用工则全部是比较长的,而且笔者获得的印象是,他们的翻译往往是伴随着相关研究而专门进行的,是从容的、时间充分的翻译。中国翻译史上的玄奘,专心翻译佛经19年,文学翻译家朱生豪几乎把终生付给了翻译。如此我们就会发现,舆论所批评的某些译著之所以错漏百出、质量低下的某些可能的原因了:用工不够,拼凑合译。造成这样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版社往往限定翻译期为一年。可是我们有些译者自身能逃脱干系吗?笔者不敢妄加推测。对于合译,苏力先生曾给出一个猜测性解释:译者可能能力欠缺,无法完成独译,与人合译壮大胆量,还可以推卸责任〔70〕。四、如何提升法学翻译?(一)中国翻译史的参照究竟如何对待法学翻译,倘若我们回顾中国自己的翻译史,就会深受触动,大受启发。笔者选择中国历史上成就最大、影响也最大的三个翻译家来作为我们考察、鉴赏的对象:其一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理论,钱钟书先生认为其开宗明义吾国翻译术〔71〕,主持译场取得巨大成就的东晋、前秦时高僧道安;其二是被誉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72〕,其翻译登峰造极的大唐高僧玄奘;最后是被奉为翻译圣人,其“信、达、雅”被奉为翻译金科玉律〔73〕,被胡适先生称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的严几道〔74〕。 道安虽佛学造诣高深,但其不懂梵文,更处于中国接受佛经与翻译佛经的初期,于是其翻译便自然的倾向于直译而求信,译文质而不过分追求华丽,所以其翻译是译介型的,译文是质信型的〔75〕。玄奘学力深厚,通彻华梵语文,能够自在运用文字融化原本义理,发挥自己信奉的一家之言,所以他的翻译是研究型的,译文是归化型的;又因“他还运用六代以来那种偶正奇变的文体,参酌梵文钩锁连环的方式,创成一种精严凝重的风格,用来表达特别着重结构的瑜伽学说,恰恰调和”〔76〕,所以他的翻译同时又是文学上的创造;他既勤恳又认真,且如此工作19年,再加上他天竺取经,本已声名显赫,便有唐太宗热情的出面资助,所以玄奘便自然成就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77〕。“严氏所选译的书都是他精心研究过的。不然,他做的案语,必不能旁征博引,解说详明,且有时加以纠正或批评”,〔78〕而且“严氏所选译的书,他均能悉该书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和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异同”,〔79〕所以严几道的翻译是研究型的;“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样阔气……”,为迎合士大夫的口味,“因此他遍铿锵一下子……”,〔80〕是可接受性的翻译,翻译策略上采取归化译法;又“因为他慎重翻译,‘一名之立,旬月踟躇’”,〔81〕所以他具有高度严谨的翻译精神〔82〕。中国翻译史上这三人都可供我们当今的法学译者品评、揣摩。 (二)法学翻译的命运与提升法学翻译进一步的设想 与原创相比,翻译难道真的是“雕虫小技”而非常容易?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令人敬仰的杰出学者,曾讲“据笔者个人的经验,译一本书比自己写一本要难得多”。 〔83〕郁达夫、苏福忠等等诸多文人、翻译家都明确做过几乎相同的表达〔84〕。按照苏力先生的说法,既然翻译艰难,又无大的利益,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有些已获得学术地位的博导、教授就不愿意去做〔85〕。或许这也是有些合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有些需要努力争取获得学术地位的年轻学人,翻译或许是其唯一的或不错的选择。而法学翻译会走多远?有论者曾这样讲,“也许法学著作的翻译在最多20年后甚至10年就会逐渐衰落”,其给出的理由是“法学著作其实都有地方性”,“法律同时又是一种相对保守的社会实践”,“法律学人的外语能力将普遍增强,他们可能更直接阅读外国的相关文献”。〔86〕 这三个理由其本身在消弭法学翻译热的自恰性上本文都是非常赞同的,但笔者以为,影响这一必然趋势的根本原因是中西法学的强弱对比关系〔87〕,中国法学是否已具备自生能力,并能茁壮发展起来,则是启动消弭翻译热的根本〔88〕。而这恐怕不是10年甚或20年就能解决的事情。况且当今中国法学研究掌握的外文资料还是不丰富、不充足,许多重要的西方经典论著,中国学人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此外,即使外语能力普遍提高,我们也很难期望中国的大多数法律学人能同时掌握英、德、法、意甚至拉丁文等法学强势语言〔89〕,同时,对中国法律学人来讲,翻译又是深入学习与研究的佳径。如上的缘由都支撑着法学翻译热的继续,虽然法学翻译较为远期的命运,笔者不敢妄断。当今这个大环境下,提升与确保法学论著翻译质量似乎绝不是个单一的、一蹴而就的工程,比如法学学术出版的非商业化,提升法学翻译的地位,真正的落实翻译校读制度,建立法学翻译论著出版的专家匿名审查制与法学翻译批评机制等等,这些似乎都是很难短期实现的。 鉴于中国当今大部分法学译者对翻译知识普遍缺乏,基本上又无专业性的翻译训练,所以法学译者自觉地进行翻译上的学习与训练,甚或考取翻译资格,意义非凡,或者法学翻译出版实施像国家法律职业资格制度那样的翻译资格准入制度〔90〕。这样一来,就保证了法学译者基本的翻译技能与翻译素养,提高了法学翻译的门槛,避免滥竽充数者浑水摸鱼。甚至出版社还可以与法学界建立统一的翻译人材资料库,网罗获得翻译资格证书,且热切追求学术、有深切学养的学人,这样就减少当今翻译出版熟人模式的运作,更可为全国各地有志于法学翻译的学人提供致力于法学翻译的便捷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