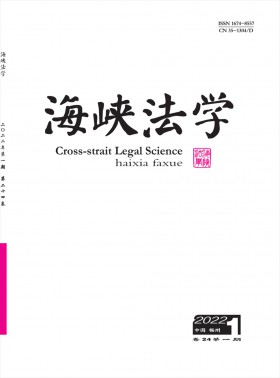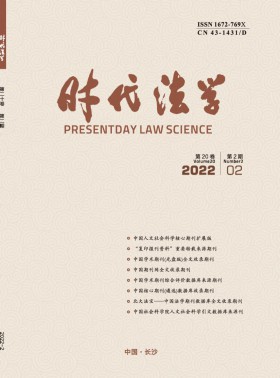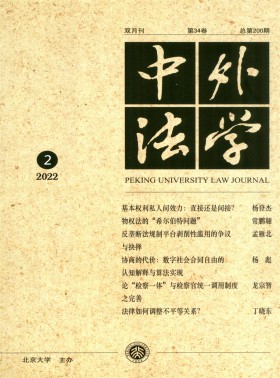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法学翻译的发展困境及方向,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法学翻译的命运 众所周知,当下法学翻译如火如荼,书店里书架上的法学译著也是密密麻麻,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有论者曾这样讲,“也许法学著作的翻译在最多20年后甚至10年就会逐渐衰落”,其给出的理由是“法学著作其实都有地方性”,“法律同时又是一种相对保守的社会实践”,“法律学人的外语能力将普遍增强,他们可能更直接阅读外国的相关文献”,〔4〕这三个理由其本身在消弭法学翻译热的自恰性上,笔者都是非常赞同的。但是该论者在论证法学翻译热必将消退时,还采用了事例论证,但其采用的事例在论证上并不妥切。比如该论者提到唐代的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并没有持续到今天,但对于佛经翻译热为何没有持续到今天,该论者并没有给出回答,也没有进行分析探讨,只是如中国古代论辩者一样,列举出一个事例,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其又提出“苏联著作和作品也并没有持续很久(尽管其中有政治的原因)”,除给出了部分解释是政治原因外,也未揭示学术上为何没有选择俄语。翻译史告诉我们,自东汉起至唐朝鼎盛再到元朝彻底衰竭的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因经常受历史偶然因素影响(也许这是集权专制社会的必然),也不是一直都在进行的,比如六世纪佛经翻译就中断过。〔5〕 知名学者陈康先生认为,“那些翻译大师过去以后,其他的人只敲着木鱼念经,不再想从原文中去研究佛经中的意义。”〔6〕 其实中国几千年以来学术也是如此,比如四书五经就曾被奉为圭臬。清朝的汉译满也未一直持续到今天,原因就是满人都被汉化了,清朝皇帝几乎都都舞文弄墨,写得绝好汉语诗,还翻译成满语干什么?的确,该论者论证说,任何事情都有始有终。其又根据这一论据,即法学是世俗应用学科,而称翻译热只会持续十年。 翻译研究多元系统论告诉我们,翻译的根本原因是文化的强弱对比关系决定的,一般就是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进行翻译。 据此,笔者以为,中国法学是否已具备自生能力是启动消弭翻译热的根本,西方翻译史即大体上拉丁语对古希腊语、各民族语言对拉丁语的翻译,表明当译语言界在被翻译的领域已具备自生能力甚至超越源语言界时,翻译就消停了。〔7〕 似乎毫无疑问的是,在法学上,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十年后还必然会处于弱势,或许几十年后还是。 其次,即使十年甚至几十年后,中国每个学子都能读懂英语原著,但处于优势的和极有研究价值的法学论著还有拉丁、德、法、意等法学著作,而我们也很难期望中国的大多数法律学人能同时掌握英、德、法、意甚至拉丁等法学强势语言。 况且我们的部门法学研究掌握的外文资料还非常的少,许多重要的论著都还没有能力翻译成中文,如民法上的许多拉丁、德语经典论著,十年内我们能将一些构筑我们法学传统所必须的外文原著都译完吗?更何况我们现今的法学翻译水平也令人堪忧。同时,对中国学人来讲,翻译又是深入学习与研究的佳径。如上的缘由都支撑着法学翻译热的继续,虽然法学翻译的较为远期的命运笔者不敢妄断。然而笔者以为,畅通与加大原版书的引进是消弭翻译热另一可能助因,且于中国学术是极为重要的事业,望学界、出版界等各界人士大力推进。 二、学术翻译的困境 在中国翻译史上造诣颇深的马祖毅先生曾作诗来刻画译者:舌人碌碌风尘里,青史无情不记名。近些年曾暴露了剽窃性翻译的事件,据说这也不过是整个中国实际情况的冰山一角。然而,译者对可能耗费其极大财力与心力的译作为何会署自己为著者呢?为何现今译者还出现了学生化的趋势呢?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学术翻译在中国当下的学术体制中地位很不高。与原创相比,译著在职称评定、为译者获得学术声名、获得项目资助、报酬等诸多方面上基本上都处于下风。恰如法学教授苏力先生所说,在学术界的观念中,也普遍认为学术翻译是技术化的学术工作。至今我们也没有设立学术翻译奖,奖给那些在学术翻译上取得巨大成绩者。如此,既无权又无势而且靠微薄的工资收入养家糊口的中国学术翻译者,如何有力量承担如此之重?对那些本来就靠贷款上学的学生译者来讲,微薄的报酬甚至无法支付搜集资料的费用。而所调查的西学译著,可以肯定的是,西译在为译者获得学术声名和获得项目资助上都与原创无区别。与原创相比,翻译难道真的是“雕虫小技”而非常容易吗?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学者,曾讲“据我个人的经验,译一本书比自己写一本要难得多”,〔8〕郁大夫、苏福忠等等诸多文人、学者都明确地做过几乎相同的表达。〔8〕 既然翻译艰难,又无大的利益,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某些已获得学术地位的博导、教授怎愿意去做呢?或许这也是拼凑式合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学术发展的经验尤其是中国翻译史上的后两次翻译高潮及至当今的学术翻译热所显示的是:翻译的影响远远大于原创。 三、法学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 既然法学译著在中国当下法学著作系统中事实上处于中心地位,学术体制就应该也给应给出一个与其中心地位相应的评价。若从学术研究的根本上来讲,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在现今学术评价体制还看不到根本改善的迹象时,尤其应使学术译著能够在职称评定、获得项目支持上与原创获得平等地位。欧美现在对于翻译也已经并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努力提高其地位。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笔者也坚信学在民间,但对于诸如优化选题讨论、开展翻译批评与研究、寻找与确定译者等诸多事务还需要大量的行政性辅助工作,更需要经费支持,所以有必要设立一个法律翻译研究机构,但考虑到设立于1982年的中国翻译协会已设立了作为译协下设的九大委员会之一的“社会科学翻译委员会”,所以设立法学翻译研究会应是求小规模高效率。 法学教授胡旭晟先生提出了另一方案,笔者认为也可行,那就是在中国法学会申请成立一个法律翻译研究会,而不赞同设立规模大的法律翻译协会。〔9〕#p#分页标题#e# 此外,中国也宜设立专门的法学翻译奖,因为目前的翻译奖即“资深翻译家”,中国于2004年才开始首届颁奖,而且是文学艺术翻译委员会设立的,所以这种翻译奖不是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而对于比纯文学翻译更为重要的学术翻译来讲,未免受到了极大的忽视与冷落。译者在译著中的署名权也要得到充分尊重,在笔者所考查的现今译书中,“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与“世界法学译丛”译者在其译著署名与介绍上与原著者是并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法律文库”每本译书的背封面也对译者甚至校者做了介绍。这种消除译者的隐身,从而提高译者地位的做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且这对读者也是负责任的做法,读者有权利在译书中获得译者的信息。而且笔者发现有一特例,颇值陈述。现今译书中,邓正来先生翻译的庞德的《法理学》(第一、二卷),封面与侧面上的译者名字的字体大于原著者名字的字体,而其最早的译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上译者名字的字体要小于原著者,其译著《自由秩序原理》封面与侧面上甚至只有原著者名字,而没有译者名字,不管这些做法是否出于有意,但反映了译者身份逐步提高,甚至可以说,在署名上,译者超过了原著者,译著本身超过了原著。或许这已是翻译的最高地位了,即译者与译著超过了原著者与原著。更有利于译者的翻译出版合同这些能够体现与提高译者地位与价值的做法,都应该尽快实行。 笔者更为关切的还有这样两个问题,就是学术翻译批评机制的建立与翻译资格准入制度的实施。笔者以为比较好的做法是创立专门刊物或网站,或在已有的刊物或网站开辟专门的翻译批评与翻译经验交流的空间,唯有如此,才可以使无能无知却胆大妄为的译者望而却步,才可以更好地积累翻译经验、发展翻译理论。翻译资格准入在欧美等国的某些领域已经实施,例如美国在法律、外交与科学研究等技术领域已实施了严格的竞争性翻译考试。〔10〕 而中国当下的法学译者对翻译普遍无知,在翻译训练上又普遍空白,实施翻译资格准入制度意义尤其非凡。在笔者的考查中,当今法学译者有三种产生的方式:自己主动型、他人举荐型与出版社邀请型,其中后两种都是明显的熟人模式。出版社组织翻译不公开招聘,出版社编辑寻找译者只能依靠其与学界的私人关系(现在出版社招聘法律编辑更倾向于名牌大学法学硕士,原因之一便是名牌大学法学硕士有更好的老师熟人)而运作。因为法律类出版社大都在北京,于是翻译者就很多是在北京。而不管是谁,熟人毕竟是有限的,况且又没有严格的高标准的译审制度,这都增加了翻译项目运作的成本与质量的失控。由学界与出版社建立统一的详实的译材资料库,网罗获得翻译资格证书,并具有硕士学位以上,或没有学位但学养同样深切的学人,这样既减少了当下翻译出版熟人模式的运作成本,而且保证了译者的翻译技能,并提高了法学翻译的门槛,避免滥竽充数者浑水摸鱼,更可为全国各地方有志于法学翻译的学子提供致力于学术翻译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