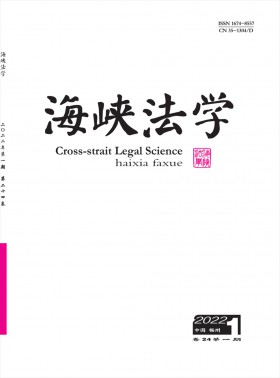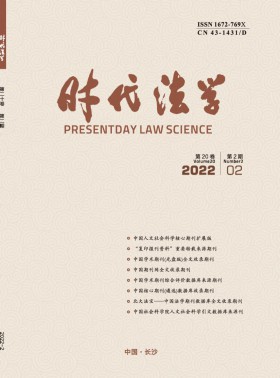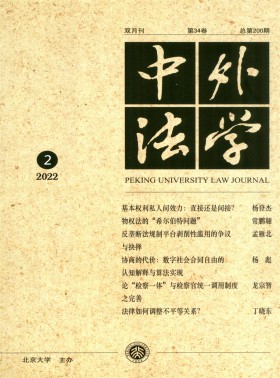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法学研究中的实证思考,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社会学方法又称“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由自然科学移植而来。这种方法认为社会研究的逻辑是假设演绎,科学假说的陈述必须由经验事实来检验,理论仅当得到经验证据的完备支持时才是可接受的。实证的社会科学把自然科学方法论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把自然科学当作科学的范例。 法学研究中运用的实证科学方法主要包括:(l)历史文献方法,即从历史文献中寻找经验材料,从而使法学理论具有历史根据。(2)调查,主要指对现状的调查,可以分为抽样调查和普查。抽样调查的效果通常取决于样本数量和样本的代表性。(3)观察,即借助于观察者的眼、耳、鼻、身等感官,直接感受研究对象的特点。观察方法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个人观察即研究者的观察,这种方法在法人类学、犯罪学、法律实施效果的研究中有广泛的应用。另一类是机器观察,即研究者借助机器设备如录像机、录音机等观察研究对象。(4)实验,将研究对象放在一个可控制的环境中,观察和研究在条件发生变化时对象的变化,即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会导致另一个变量的变化。 历史文献的真实可靠一直是历史考证的关键问题。史料的重要性对社会科学研究是毋庸置疑的。新的史料的发现往往是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但对已有史料的整理也很重要。历史文献的作者不可能将历时发生的每一个事实源源本本地记录下来,总要经过加工、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现在有许多翻案作品,其实就是把过去被史家隐去的东西曝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许多后现代的研究即属此类。这显然和研究者的主观性,包括他们的历史观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过去占主流的罗马法律史学家一直把现代西方法律传统看作是古罗马法的继续,而罗马法具有原生性、独特性、纯粹性、优越性、自我更新能力及其自身历史的连续性,似乎罗马法是优等民族的产物,不受其他文明的影响。意大利罗马法学者孟纳特里运用“去合法化”(delegitimizing)理论或福柯“考古学”的方法提出,“所谓‘罗马法’,其实不过是一种包括非洲、闪族和地中海文明等在内的多元文化的产物”。早期罗马法所固有的重大缺陷,如缺乏一般契约、政府理论,私法实践中的巫术色彩,解纷机制中缺乏强制执行机制,缺乏法律学院与专职法官等,直至公元3世纪大危机之后才获得明显改观。现在人们所推崇的罗马法并非罗马人原生的产物,而是罗马人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非罗马化”的产物(P.G.Monateri,BlackGa乞us:AQuestfOrtheMulticulturalOriginsofthe“WesternLegalTradirion”,slHastingsL.J.479,Mareh,2000)。 在观察、调查和实验时,人们经常会发现,当被研究的对象了解到自己被观察、调查和实验时,他可能特别警惕,他的回答或行为可能根本不是他平时的状态。如在进行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调查时,问卷提出“当你被你的领导或老板打伤,你将采取那种方法解决”,选择的项目有:找本单位或本村的领导,找工会妇联等,找打人者的上级,找司法部门,暗中报复,忍忍算了。 研究对象平时很可能视环境采取私了或忍忍算了的方式,但他考虑到找司法部门解决可能是这道题的最佳答案,又听说这是上级机关或法学研究机构主持的调查,从而对该问卷的回答可能和他平时的态度和行为完全不一样。 研究者应该尽量把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排除,不能先人为主。与自然科学家不同,法社会学家本身的价值观念常常不可避免地带人到研究对象中,因此要想保持价值无涉,保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国社会早己进人了利益多元化时期,在许多强势群体的利益链之下,研究者本人的利益往往也渗人其中。很多时候,持有不同立场的法律研究者,往往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支持自己立场的各种“证据”。所谓客观公正的调查,常常只不过是为固有的立场找根据而已。 社会学研究离不开统计数字,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是法社会学研究的特点。但是在运用统计数字时,必须注意数字的真实性,防止数字造假。如在进行社会治安、环境污染、计划生育等情况的调查时,有研究者经常依赖当地主管部门的统计数字,而这些数字又往往和各种各样的“一票否决制”相关。为了压缩这些数字的“水分”,研究者必须学会运用其他的方法校正。 比如,判断一个地区治安状况,不仅要看犯罪率等指标,还要看当地普通群众的安全感。如果一个地区报告的犯罪率很低,但是群众的安全感却很差,犯罪率的数字很可能水分大。在进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指标、统计数字的比较时,不应一味迷信数据,要注意数据的内涵和可比性。比如,在犯罪率的研究中,由于在不同国家犯罪的定义可能不同,在美国属于轻罪的行为在中国属于治安管理处罚的范围,不了解这个前提而单纯比较中美两国的犯罪率,就毫无意义。在一国范围内,盗窃1000元在一定时期内作为立案标准,修改法律后,盗窃罪的立案标准改为2000元,这样就会使相当一部分盗窃行为“非罪化”。如果不了解这个变化,单纯看犯罪率的变化,常常也会误读。在调解结案率的研究中也是这样。1990年代以前我国民事案件调解结案率为70%多,民事诉讼法制定以后,审判结案率上升,调解结案率下降到30%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以来,又开始强调调解,现在的司法统计中把撤诉的数量也算在调解结案率中,这样调解结案率变为60%或70%多。撤诉可能包括调解作用的结果,但有些撤诉与调解无关。把调解结案率与撤诉率捆绑在一起,有些像文字游戏,而且和以前的调解结案率内涵不一样,是不可比的。 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防止研究的主观性,增强客观性,从而使研究的结论更加客观、公正和可信。但是如上所述,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历史文献、调查、观察、实验等,任何一种对研究基本素材的处理方法,统计、比较、指标的设计等,都不可能摆脱研究者或被研究对象主观性的干扰。 关于如何解决上述难题,一直存在争论。一种观点主张增加法社会学研究的客观性,改进研究方法,在方法上尽量仿照自然科学,从而使法社会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这种观点认为,法社会学应该尽量使用客观的数据、法律指标,如犯罪率、离婚率、诉讼率等等,来描述和衡量研究的对象,“问题不在于是否能把研究对象转变为法律指标,而在于怎么转变的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过分依赖所谓的客观数据和法律指标,过分依赖这种方法的结果是徒有大量的数字,却对其不甚了了。他们所依赖的常常是自己对行为的主观描述和解释,而不管这些描述和解释是否能被别人接受,是否能得到检验。在这些人看来,主观性是社会科学的本性,完全客观的就不是社会科学。#p#分页标题#e# 的确,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自然现象,用恩格斯的话说:“在社会历史领域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但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中无数个别愿望、个别行动发生冲突的结果,“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同上),虽然行为的目的是预期的,但却受到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支配。因此在社会领域,在人们有意识的行为的背后,同样能发现人们的行为的有规则性、重复性和规律性。这就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基础。 虽然法社会学研究很难避免主观性,现有的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包括实验、调查、观察、历史文献,没有哪一种能够保证它是完全客观的,不带有研究者本人的感情、价值因素,避免由于研究对象的种种不真实的表现而带来的误导,但是通过一套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尽量减少主观性,增加客观性。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过程就是一个主观性与客观性互动的过程。总之,按照社会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虽然不能完全避免主观性,但是做比不做强,比完全按照主观臆断和猜想强。 应该看到,评价社会科学研究的标准,既不同于法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规范标准、合法性标准,如某一判决是否符合法律,某一下位法是否符合上位法和宪法,也不同于价值标准,如某一行为是否符合公平、正义,是否侵犯了人权以及各种不同价值之间的关系。它的标准是事实,即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是否站得住,是否真实、可靠、全面。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围内,对某项研究的批评与反批评,往往也集中在引用材料的来源、获取方式、可信度,真伪的辨别,材料所能说明问题的范围,材料与结论的因果关系等等。一项认真的社会科学研究,尽管也难免主观性,有些材料的取得和应用难免有问题,在材料真实性、全面性、可信性和结论之间经常受到质疑,但所有这些在方法论上都是可批评的和可改进的,由此可得出更接近客观真实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