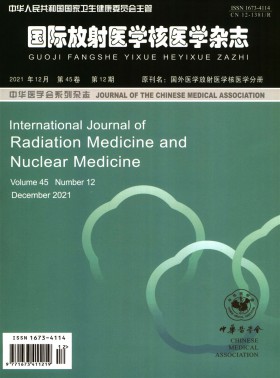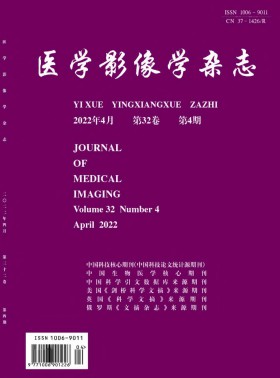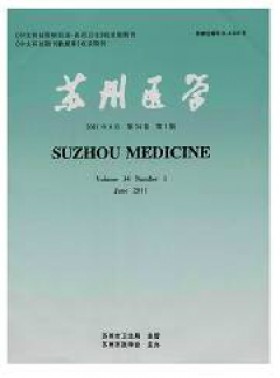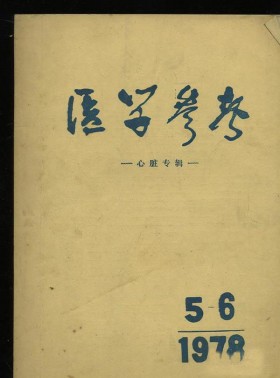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医学伦理学下医患沟通反思探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关于肿瘤治疗现状,一直引发着社会广泛关注,在医务人员群体中更是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其中很多的问题也引发各个层面的反思。跨适应症用药,新药的选择,循证医学证据前的经验治疗,“伪”知情同意……每一个点都在触动社会敏感的神经,不乏涉及伦理的争议。
其中,最关注的就是诊疗过程中医患沟通以及知情同意的问题,其实也是所有临床诊疗过程中的一个基础环节。
回到理论,医患关系有其特征:以医疗活动为中心,以维护患者健康为目的,是一种帮助性的人际关系,是以患者为中心的人际关系。3医患关系中“患者为中心”,以“治疗疾病”为相对单纯的目的,肯定了患者被尊重、知情同意、隐私受保护、监督医疗行为的权利。
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需要明确很重要的一点,医患双方地位是平等的,这一点也是医学伦理学四大基本原则中“公正原则”和“尊重原则”在临床实践中的重要体现。但因为医学较强的专业性,医患双方在专业信息及知识背景上具有不对等的特征,使得医生成为医患关系的主要影响者,在生物-心理-社会复合医学模式的转变下,良好医患关系将保障医疗活动顺利开展,同时可以调节患者的心理状态,利于诊疗正确决策及减轻患者的痛苦。
医学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从认识到实践再到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因此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存在必然的局限性。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提供的医疗资源具有的局限性,也需要通过充分的知情向患者及家属解释,这将有助于合理预期的建立,对诊疗过程更为理性。
需要辩证理解和认识医学伦理学中的“有利原则”和“不伤害原则”。7有利原则是指把有利于患者健康放在第一位并切实为患者谋利益的伦理原则。这是“医乃仁术”的根本前提,也是医学事业的根本追求。但正如认知的改变和进化,不同时期的“有利”措施不尽相同,甚至存在相反,因此要求“与时俱进”。
不伤害原则解读为杜绝有意和责任伤害;防范无意但可知的伤害,把可控伤害降到最低程度;不滥用辅助检查、药物及实施手术。现代医学诊疗常规应用中不乏有创的检查及操作,存在副作用的药物及治疗手段,因此不存在绝对的“不伤害”。作为患者及家属应该理性认识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检查的“神医”无非是骗子的噱头。同时作为医务人员也要清楚,不能以“不伤害”为理由,放弃积极必要的诊治、推卸医疗责任、不作为,一些时机更需要敢于“冒险”。由此可见,辩证理解和认识有利原则与不伤害原则,对于医务人员,就需要锤炼专业理论,以准确把握指征,提供诊疗,其背景更是对医务工作者专业素质、循证医学发展与终身学习能力的要求。
基于上述理论,在伦理原则的指导和约束下,接诊患者构建医患关系,对病情做出基于专业的判断,制定相应的诊疗方案并实施。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医患沟通的过程,医患沟通更是一个体现生物-心理-社会诸多因素的环节。
如果要求概括临床实际工作中医患沟通的内容与内涵,我总结为:目前诊断,目前的主要疾病(包括疾病的特点、存在和潜在的风险,可能的转归结局),诊疗的计划(包括诊疗措施、相应费用、实施方式、潜在的风险以及针对风险我们的预案和措施)。此外在病情变化时、出现医疗差错、事故或不良事件时,存在争议纠纷时会增加相应的沟通。
但是医患沟通中还有非常特殊的一种情况,就是关于临床诊疗方案的选择。不同于心理咨询的“助人自助”原则——咨询者不提供选择的倾向性,帮助来访者自己找到答案。临床诊疗工作正是因为具有“信息的不对等”性质,如果只是简单地要求患者及家属自行选择,是临床医生在某种意义上的失职。
我们的“知情同意”在很多情景,包括涉及纠纷及司法介入的案例中是非常沉重的。首先要强调沟通过程中,医生对有利原则的坚持。
比如非常经典且经常发生的案例:某人因“急性胸痛”急诊就诊,临床高度怀疑“急性心肌梗死”,诊疗上建议急诊导管介入溶栓治疗,患者及家属不以为意,拒绝手术,尽管医生苦口婆心告知有性命之虞,仍固执己见,觉得是大夫危言耸听,甚至拒绝签字了解病情及风险,拒绝手术,要求离院,但最后,出院后病情加重死亡。
类似的案例,即使患者签字存证,当事医生事后恐怕也难逃“是否充分知情告知”的指摘,且不谈类似的情况医生是否委屈或者应该如何免责;暂且为了避免牺牲生命的悲剧结局,围绕医患沟通,更值得我们思考,坚持有利原则,同时就是提升我们的沟通方式、沟通的效率。话术即艺术,谈话前我们要设计沟通的预期、沟通的方式,甚至谈话的语气。尽管是萍水相逢,素昧平生,但危急的病情变化,医生仍然责无旁贷地去考虑如何尽可能挽救“愚昧”,绝不可意气用事、见死不救。
知情同意的初衷或者根本,是我们恪守的“有利原则”。基于专业角度,对于目前的治疗决策,我们心中有顺序和权衡:首先、其次、最起码、无论如何也不应该……
我们的谈话也应该有倾向性,在可以选择的范围中尊重患者的意愿。
由此另一个问题,所谓坚持“有利原则”,个人的判断,基于经验、基于专业教育背景、基于区域诊疗技术等势必存在主观性和局限性,因此应该强调监督机制,比如临床医疗过程,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应该落实好三级查房制度,补充科室-院级-地区级等业内的督导机制,行业内及时更新和制定“什么是推荐”“什么是规范”“什么是红线”等指导意见。
关注知情同意的过程,我们还应该强调和关注其内容。
对患者坦诚全面的交代,是医学伦理学尊重原则的体现。但是很多时候,限于患者的理解能力、个体实际,是否能够承受所有的内容,也是需要个体化设计的。我以为这个时候依旧强调有利原则。对于一个家庭经济拮据、已经捉襟见肘的肿瘤终末期患者家庭,非要强调另有一种疗程数十万元的新药,或可尝试延长生命,结果导致这个已经力竭的家庭,最终在无力尝试这种药物的悔恨和遗憾中送走患者,为生命的最后时刻再度蒙尘。这样的过程,尽管尊重了患者家属的“知情权”,但却违背了有利原则,给患者及其亲属带来额外的痛苦,尽管合法但不合情,不合格更不高明。
“医患沟通中的该说与不该说”也是我临床工作中时常困惑的话题——如果我是他的朋友,我一定不会告诉他真相。但作为医生,我没有隐瞒的权利,因为我不能侵犯他的知情权。但随着临床工作时间的增加,经历了各种情境下的沟通,渐渐地我发现其实并不矛盾,医生的权威和值得信赖,不是依靠隐瞒和众多善意谎言来实现的。
病情是现实,医疗因素之外:经济、家庭、工作等众多社会因素对于选择和决策的影响也是现实。这不是医生的错误也不是患者的错误,它就是不完美的客观现实世界,我们要做的不是创造一个理想的童话世界,而是陪着患者和他的家庭一起面对,一起选择和接纳最合理的那条道路,所谓的合理是“有利原则”下,综合各种因素制定的个体化措施,因此,同一种病情,也可以千人千面。这也是医生存在的价值。
作者:叶圣龙 单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