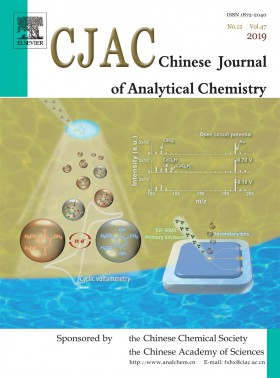分析哲学论文范文1
所谓德育哲学的切近基础,就是指现代大德育的时空拓展,需求哲学层面的反思、批判、总结和概括,因而德育哲学应运而生。
现代大德育的基础性问题,是德育的社会化,是德育社会化的内在趋势和必然走向。这集中表现在:一方面,德育概念的涵量更为丰富和广阔。另一方面,德育运动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
人类社会的德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及发展,规定了德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德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涵量。就内容而言,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就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德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德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功能,尤其是在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德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德育作用,等等,都是德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涵量的基本体现。
随着德育涵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德育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其一,德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德育的社会化,德育亦将成为民众的自我教育、自我德性修养的基本形式,从而实现由国家主体向社会主体的回归。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但这种德育本真化的走势正在逐步变为现实。比如,学校办学自的加强、社区建设的兴起与功能强化等,都突出表现了这一点。其二,德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党的十五大报告曾讲了这样一段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因为它将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存在方式,它意味着文化建设将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随着德育社会化的推进,德育的本质存在方式也是如此。其三,德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建设人本身回归。德育要为政治服务,要为国家服务,要为社会服务,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德育的本质规定之一。问题在于,德育的本真目的任务是建设人本身。德育的社会化、本真化,要求以建设人本身为出发点,这势必推进“主导”者的逐步回归,但这与德育的工具理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因为以建设人本身为主导,将从更为根本、更为长远的层面上发挥出德育的社会意义和功能,将把德育为国家民族服务的工具理性置放于更为坚实的基础上。其四,德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因为德育社会化本身无论内容、形式,还是载体运作过程,都具有更大的普适性、普遍性和社会性。特别是在当今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德性修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仅有过去那种一对一的德育单向运作方式,显然已不能适应当今时展的需求。
总之,德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邃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显然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毫无疑问,德育“领域的发展”,确需德育哲学这一新兴边缘学科的探索和确证。
二、德育哲学的边界、对象和任务
德育哲学思想的实际存在是渊远流长的,但德育哲学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出,却首见于1996年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指南;而作为一个门新兴学科建构,目前仍然处于探索、研究和创作的过程中。
从哲学的视野看,任何事物包括理论学科要获得相对独立的生存权,其基本条件是具有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规定性。因此,探索德育哲学的学科建设,首要的问题是给定它的边界。
第一,学科界定。一般说来,学科界定总是与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必须准确把握其特定视角、特殊层面和内涵应然性的特殊价值指向。黑格尔说,“一个定义和它的必然证明只存在于它的发展里。这就是说,定义只是从发展过程里产生出来的结果”④据此,德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德育观及其行为实践所蕴涵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一般方法论问题。具体地说,一方面,作为理论形态,德育观是关于德育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德育哲学研究首先要立足于这一层面上,但却不是局限于德育观本身,而是探索研究德育观的前提性问题,即追问反思德育(包括其理论和行为实践)运动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一般方法论依据、条件及其应然性形式。另一方面,哲学有两个主要视角:一是真理性认知,即追索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二是价值性把握,即求索事物运动发展的评价性确证。哲学思维的这种方法论原则,运用于德育观及其行为实践研究,德育哲学的对象便获得了真理观与价值观及其相统一的意义。所以总结起来说,笔者以为,德育哲学是否可以这样界定:德育哲学是关于德育观及其行为实践的哲学前提性问题的理论学说。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德育理论与哲学思维的有机契合,开展对于德育观及其实践运动的哲学研究,揭示人的德性修养的前提性根据和条件,揭示德育观形成、运演、发展的历史正当性和价值合理性,揭示德育运动规律的前提性根据和条件及其实现形式,等等。
第二,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主要是与德育学、哲学、教育哲学的关系。在笔者看来,“德育”概念在通常语义上有三种指向:一是德育实践活动;二是德育学科;三是德性培育状态的直接现实。但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作为理论它原本是教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所以能够从中剥离出来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研究领域,实际是标示了它在整个教育事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价值。“哲学”通常有三重意义:一是所谓“元哲学”,即哲学的基本原理;二是部门哲学(包括各种应用哲学);三是指某个领域、某类事物的最高理念或信条。德育哲学作为德育学与哲学的结合体,本质上是以哲学思维解读和创新德育理论与实践,开发其哲学价值和效能。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德育哲学虽然与德育学、哲学等双重“母体”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但三者之间的“边界”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它毕竟要有个学科归类的话,毋宁说它是教育哲学的一个层次,即相对独立出来的一个特殊领域。当然,两者的边界也是非常清楚的。第三,设定德育哲学的边界,还应从辩证思维中得到深入一步的说明。从这方面看,德育哲学主要不是去建立新的具体的德育范式,而是着重考察已有范式的依据、条件性、特性、表达方式以及范式更迭转换的可能性空间;它不是要描述德育过程本身,而是要规范人们在德育活动中的选择、定位和行为理性;它不是要作出德育学层面的结论和成果,而是要探讨、评价德育学结论和成果中超出德育学层次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它主要不是去揭示德育运行的特殊规律,而是要探求反思人们揭示规律的思路、能力和方式;它主要不是去规范和给出德育研究的具体方法,而是要评价这些方法的合理性和可能性,等等。总之,德育哲学植根于德育理论和实践的重大问题,又超越于这些问题而探索其前提性的哲学底蕴,这实际也就是德育哲学学科的基本特点。
三、德育哲学的价值现实
德育哲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其发生的根源,说到底,在于当今时代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育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亟需哲学的介入和哲学方法论的统摄。反过来说,即:对于德育理论与实践从哲学视角作出多方位的分析和研究,从而对于德育的前提条件、基本理念、结构体系、实践范式以及重要的德育现象做出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意义的深层次确证,这就是德育哲学的价值现实。从实践操作的意义上看,德育哲学的价值实现,是整个德育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那么,德育哲学具有哪些价值呢?
第一,解读性价值。从泛意上讲,任何精神文化现象都是一种社会性解读。解读与解释意义相近,它们都是直接面对思想和实践的现实的,但解读更接近于操作实践层面。就德育哲学的解读性价值而论,其独特之处主要在于,一是注入了理想性追求。德育哲学的解读性价值主要不在于对德育现象的映像式、模本式的解释和说明,而是以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为基础,以一定理想性追求为参照,反思、解悟和权衡其得失成败,从而发掘和拓展出新的“历史可能性”。二是注入了穷根究底式的思维原则。哲学的根本特点是不断追索事物、现象的深层次本质,以期不断获得极度而适度的认识成果,因为被解读的“文本”本身就是多层次的。哲学思维表明:“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⑤所以德育哲学的解读性价值,并不满足于德育理论的一般解说,更不是停留在德育现象的表层理解,而是不断追问德育现象背后的“更深刻的本质”。
第二,批判性价值。哲学思维的又一显著特征是它的批判性。在哲学视野中,“批判”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方式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它的核心思想是否定现状和追求未来,其真谛是“扬弃”和创新。“批判”具有物质实践和精神文化两种基本形态。德育哲学的批判性价值主要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它价值归宿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德育的一种前提性批判。所谓“前提”,从逻辑上讲,是指推理过程的确定依据。逻辑结论若要正确,首要条件是逻辑前提必须正确。从行为实践上看,“前提”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先决条件。德育前提性批判的重要价值,就是以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动为背景材料,以哲学思维和德育本真走势为凭籍,不断重新审视德育既成既有的出发点、根据、真理性标准、价值性尺度,不断重新鉴别、选择、取舍和筛定其前提性认知和价值取向,以推动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当然,这种前提性批判又是辩证性质的。因为在唯物辩证法看来,批判就是一种否定。但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即事物内部生发的新质要素克服了旧的质的规定性;同时,恰恰又是由于新事物吸收、联合了旧事物的合理成分,才能真正克服旧事物,实现发展。所以辩证性质的批判,就是一个“扬弃”的过程。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科恩“主张以认同、继承传统为特征的‘收敛式思维’与以批判、超越传统为特征的‘发散式思维’之间建立‘必要的张力’。这一影响深远的见解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教育的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⑥因此,德育哲学的批判性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前提性批判,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辩证性质的批判,由此便孕育了德育的前提性创新。德育的前提性创新,必然带来德育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变革,促进人的德性修养的更新。这便真正实现了德育的前提性批判的价值。
第三,导向性价值。德育哲学的导向性价值是指向未来的。它的特点是前瞻性、超前性和预示性,这与价值本身的内涵是直接同一的。价值概念回答的问题主要不是“现在怎样”,而是“应当如何”。德育乃至整个教育在绝对的意义上都是为或远或近的将来“准备着”,亦即面对未来“应当如何”。这样,“导向性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导向即导引方向,实质是事物发展中内部诸要素的历史性趋势性的必然联系。德育的导向性价值主要有三个层面的指向:一是德育实践活动,其导向价值的观照和实现在于作用于人的认知和心理层面。二是德育学科理论的教学活动,其导向价值的体现和作用在于德育对象的理性和理论层面。三是德育哲学层面,它的直接对象主要是德育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其导向价值在于通过德育的前提性问题研究,革新德育理论,创新德育活动,导引德育不断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德育改革就有一系列前提性问题亟待研究。比如,既要坚持德育的一元化导向,又要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样化社会生活,发展人的个性品质,两者统一的现实倾向性、历史合理性及未来走势的人性根据、实现条件、理想模式是怎样的,它对德育体系革新具有何种价值?又如,德育的功能作用与人的精神世界自主自组织之间应当建构怎样的合理性尺度?因为有个性需要就意味着有选择,而有选择就意味着至少对部分德育预期效应的否定,所以如何培养和造就人的德育需求理性自觉,便成为德育创新的立足点和前提性问题了,等等。总之,德育哲学的导向性价值,生发于较深层次,关乎于德育宏观走向,意义深远而重大。
第四,方法论价值。抽象地讲,上述解读性价值、批判性价值、导向性价值都具有方法论意义。因为方法的实质是理论自身实现过程的“反哺”形式,换言之,拿了理论去运用、去解决实际问题,理论就转化为方法了。所以理论与方法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就更为接近实践的方面看,方法论应当是理论在认识上的深化层次。德育哲学的方法论不同于德育的具体方法论,而是一种宏大而深邃的方法论,具有重要价值。扼要地讲,其一,它对德育一般方法论具有直接指导意义。其二,它是德育工作者实际工作的最切近的理论基础。其三,它为人们的德性修养提供深刻的哲理性视野。其四,它是德育理论创新的重要指导原则,等等。
注: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②转引自《科学学基础》,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③《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3页。
④转引自《哲学动态》1991年第7期第12页。
分析哲学论文范文2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意义上倡言的历史性不等于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放弃康德式近代认识论的思路,打造出一种历史本体论来,方可尽显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真义。本体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首要可能性就是历史本体论,历史作为本体,其指示词就是历史性,并以生产方式作为其对存在的超越性解释,而生产方式作为存在则体现为历史的一种“缺席的原因”,因此是以不在场的方式现身的。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重新解读出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并说明其与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关系,而不是直接去奢谈一般哲学本体论。
【关键词】历史/本体论/认识论/马克思/history/ontology/epistemolog/Marx
【正文】
自卢卡奇提出“社会存在本体论”问题以来,历史能否作为本体而存在就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悬案:“常驻不变中的连续性,作为动态复合体中的存在原则,证明了历史性的本体论趋势,是存在自身的原则”(P700);“对马克思来说,通常对恩格斯来说也是一样,历史性是物质运动的一种不能被进一步还原的本体论性质。”(P734)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似乎已昭然若揭了。然而,由于“历史主义”(尤指自狄尔泰以降的诸历史主义尝试)与近代认识论的奇特结盟,“历史主义”一直都面临着一个尴尬的“两难处境”(PP.148-150),因而这一问始终没能被包括卢卡奇在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们明确问出。缘此,本文试图问出这一问,以求在当代哲学语境下,重新解读出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本体论:本体论在马克思哲学中的首要可能性就是历史本体论,历史作为本体,其指示词就是历史性,并以生产方式作为其对存在的超越性解释,而生产方式作为存在则体现为历史的一种“缺席的原因”(PP.148-150),因此是以不在场的方式现身的。
一
历史作为本体,第一个问题便是“历史是什么?”这既可以用认识论的方式问出,也可以用本体论的方式问出。以认识论的方式问出,历史便是对象,但历史一旦作为对象,时间便与存在一同隐逸了。海德格尔为历史主义悲伤道:“某种被称为历史的东西根本不是历史。”(P24)原因何在呢?海德格尔的解释是:“只要哲学把历史当作方法的考察对象来分析,哲学就不能获得历史的根本。历史之谜就在于:何谓历史性的存在。”(P24)历史作为对象就有可能演变为一种“超历史的东西”,就可能使此在迷失于当前的伪历史之中。这也就是历史主义所以会陷于共同性与特殊性的两难处境中而不能自拔的原因。
海德格尔改变了问题的提法:“‘什么是时间?’这个问题变成了‘谁是时间’这样一个问题。”(P25)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时间就是此在”(P24)。通过此在接通时间(历史)与本体论的线索是海德格尔在历史本体论上的最大贡献,但也是他的最大失误。一方面,他反对把历史作为认识的对象,并通过此在的当下性把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使历史获得了某种本体论意味。另一方面,他又将时间变成了专属于此在的问题,对时间的追问也就变成了对我的追问:“于是,这种追问就是通达和对待总是属于我的时间的最适当的方式。”(P26)最终,这一问终于仍不是向着时间与历史而发的,而是朝着作为此在的我的。正因此,对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始终都存在着“社会存在论”和“唯我论”这两种路向的解释。
但是,海德格尔终归明确阐述了历史性在本体论上的重要地位,他甚至道破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优越性:“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P383)。这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的:“理解存在的活动本身被证明是一种历史的活动,是历史性的基本状态”(P84)。对于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来说,理解存在是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存在中有历史性;而我则要进一步指出,在马克思哲学中,这个判断倒过来同样成立,历史本身即存在,历史性是存在的固有维度。——更重要的是,将历史本身直接指认为存在对于海德格尔式的此在本体论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历史本身在马克思哲学中绝对不是仅仅通过所谓此在的存在辩证法(即此在的在场与不在场)而现身的。
在我国哲学界,也曾有人提出过“历史本体论”,甚至还对作为本体的历史的存在特征作出过非在场的表述:“历史由于是非在场的存在,因此,本体历史的显现离不开语言的历史和认识与理解的历史。”(P43)这种见解的可贵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地提出了“历史本体”的说法,二是对历史的存在特征作出了非在场式的说明。但是,仍须指出,这种见解离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本体论在当代的真实建构的距离还是很遥远的。因为,在这里,“历史首先是历史事实,随后是历史认识或理解,最后也是历史语言”(P43)。显然,此处所说的本体历史的显现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显现,历史作为本体自身的显现方式并未被触及。这至多可算达到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理解高度,即把对存在的理解看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活动,存在中有历史性。然而,对历史首先作事实性的理解是不可能与近代认识论彻底划清界限的。一旦历史的显现方式仍仅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被论及的,那么,历史本体就只能以传统形而上学的样式而固守于客观事实的一隅了,历史性仍未被当作本体论的固有维度。
正因为如此,德里达才说:“如果对存在的最终认识应当被称作形而上学的话,那么现象学的最终成果就是‘形而上学’。”(P302)不论对存在本身作何种理解,只要把它作为一个认识对象,它就是既定的、不变的,就是反历史的,一句话,就是形而上学的本体。所以,德里达认为:“情况恐怕看来会是这个康德意义上的大写理念就是现象学真正大写的观念或者方案……因此结构上说,这种终极目的就是作为源头和变成(devenir)的生成本身。”(P303)总之,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现象学努力如果说有一种历史本体论的话,那这种历史本体从根本上来说同样也没有逃脱康德式近代认识论的窠臼。历史本体的生成特征,即其历史性在这种本体论中仍未得到明晰的标示。
那么,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本体到底又是如何现身的呢?马克思曾说:“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P44),在此语境中,所谓“一切凝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才真正得了落实。借此,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历史是通过批判得到理解的;其次,一旦批判开始了,尽管过去的东西得到了理解,但它们的凝固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历史本体是通过批判而现身的,作为存在它也是建立在不在场的地基上的。这种批判既是一种现实的实践批判,同时从本体论上来看,它又标明了社会存在的历史性。通过这种批判,我们可以切实地看到,历史性正是历史本体的指示词。这也就是说,从存在论上来解读历史,就不能把它当作凝固不变的对象,而必须看到它与批判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内在关联。
二
因此,哈贝马斯对马克思历史概念的误读其原因也正在于他没有领会到,在马克思哲学中,历史性从本体论上来讲不是一种实证概念,而是一种批判概念。哈贝马斯曾指责道:“马克思把社会劳动的概念同类的历史相联系”(P147),而“迄今为止的关于世界历史的学说,把生产方式分为五种或六种,这种学说确认了宏观主体的、单线的、必然的、连续的和上升的发展”(P149)。哈贝马斯虽然看到了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中的重要性,但他仍把马克思的历史概念指认为一种旧式的类的历史概念,且将此概念与一种线性的历史认识论联系在一起。
但马克思在运用历史的这个概念时实际上是十分谨慎的。马克思在讲随着资本的发展劳动条件同劳动相异化这个问题时指出:“这种错乱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单是想象的,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并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9](PP.360-361)历史在此不是哈贝马斯所表述的类的历史,而是暂时性。马克思在历史的和绝对这两个词下打上了着重号,跟着还指出这一过程是内在地被扬弃了的,其用意很明显:反对这种单线性的或所谓宏观的历史;历史性作为历史本体论的一个指征,说明的是历史的内在批判功能。
可以说,哈贝马斯本人并没有迈入本体论的门槛,而停留在近代认识论的界域中。正因为如此,哈贝马斯才对认识和学习有着非比寻常的“兴趣”。然而,一旦停留在近代认识论的视域中,进步问题就成了个难以解决的悖论,不可能克服康德当年所提出的二律背反,因为这是认识论(理性)的宿命。因而,哈贝马斯说:“我们也以这两个领域中的普遍的公认的要求为标准,来衡量经验认识的进步和道德—实践洞察力的进步,即以陈述的真值和规范的正确性为标准,来衡量经验认识的进步和道德—实践洞察力的进步。”(P152)而离开了历史本体论的内在批判能力,这种认识论上的进步也就可能转变为一种辩护性的意识形态了:“我要维护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成熟——有能力为一个制度(系统)的存在作辩护。”(P152)对这种仅从主—客体式的认识论角度出发来认识历史的理论的辩护性的意识形态本质,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曾作过尖锐的剖析。
那么,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作为本体的历史到底是如何显现的呢?是否像海德格尔那样,马克思也仅仅止步于将历史指认为此在式存在本身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历史作为本体在马克思哲学中的指示词同样也是历史性,但这种历史性是不同于海德格尔的作为此在式存在的指示词的历史性的。抑或,它作为一种本体就等于德里达所说的幽灵?就像德里达所描述的共产主义?“在这方面,共产主义一直是而且将仍然是幽灵的:它总是处于来临的状况;而且像民主本身一样,它区别于被理解为一种自身在场的丰富性,理解为一种实际与自身同一的在场的总体性的所有活着的在场者。”[10](P141)如果剔除其解构意味,从本体论上来理解共产主义,并将其转换为历史,那么,这无疑是对历史的本体论状态的一种绝佳说明。历史非旦不是逝去者,而一直都是将来临的,它是丰富的,但目前并不在场;它是总体性的,但这种总体性并不是认识到了的,而是活跃着的在场者;它不是一种僵死的总体性逻辑,而是在实践着的在场者,且通过这种实践而求得与自身的同一。作为本体的历史,并不是在认识论中被识别出同一性或发展的,而是通过实践(活着)而同一、而发展的。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历史作为本体既不是主—客体式的近代认识论的对象,也不是海德格尔通过向此在作始源性回溯所获得的作为存在的存在本身。它通过人们的现实实践活动显现出来,人们的实践活动揭示了当下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这就使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本体论获得了一种现实的批判能力。一方面,当这种能力指向过去时,它就说明了以往的历史;另一方面,当其指向未来时,它又标明了历史的方向。因此,这种历史本体论也不仅仅是“幽灵”,它虽作为一种“缺席的原因”,但对现实却是有其实践的。
在德里达这里,我们再次听到了詹姆逊所说的那个“缺席的原因”:“所有的幻影都被投射到这个鬼魂的屏幕上(亦即投射到某个缺席的东西上……)。”[10](PP.141-142)但历史之所以在本体论上表现为缺席状态,其原因并不在于海德格尔所阐述的所谓存在的辩证法。在此,德里达实际上也被海德格尔蒙蔽了,因为他跟着海德格尔说:“那幽灵并没有一个Dasein(此在),但是没有一个此在并没有什么奇怪……那幽灵,正如它的名字所表明的,是具有某种频率的可见性。但又是不可见的可见性。并且可见性在其本质上是看不见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一直存在于现象或存在之外。”[10](P143)因而,采取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那幽灵”就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之所以在本体论上是缺席的,不在于它有一种关于存在的辩证法,不在于它的不在场这件事(Ereignis)本身,而在于它是一种批判与宣告。因此,正如德里达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马克思是相左的:“1847—1848年间,当马克思命名时,他用了一种历史的观点记述它,这种观点与我提出‘马克思的幽灵们’这样一个题目时最初思考的观点正相反。”[10](P144)对于德里达来说,历史性是由幽灵的非在场引出来的;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本身就是本体,因而它是一种宣告:“就马克思而言,他则是宣告和呼吁一个在场的到来。”[10](P144)德里达意识到马克思的哲学宣告了一个在场的到来,但他不明白马克思是通过什么来作这种宣告的。他只认识到“幽灵”是不在场的,而没有理解到这个当下不在场的历史在马克思的哲学中还可以通过实践作为本体而现身。而有了这种历史本体论,不论是共产主义还是未来就都不再是“幽灵”了。
三
然而,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历史作为本体到底是指什么呢?或者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其本体论功能又是如何通过历史性而表现为批判与宣告的呢?我认为历史作为本体它就是生产方式(或者也可以用詹姆逊的话说是“生产模式”)!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生产方式怎么成了作为本体的历史了呢?在以往,生产方式常常是作为共时性的分析模式而加以运用的,而历史显然更多的是指认一种历时性的过程。
对此,我要强调的仍是:历史作为本体并不是作为认识对象而出现的,因而它既不是共时的结构,甚至也不是历时的过程。一旦作为本体而出现,它就既不表现为普适性的共时模式,并以此来说明所有的时代;也不是作为一个过去了的时间链,并将一个个特殊的事件纳入自身之中。用本体论的固有话语来说,它就是一种诉求:特定的当下存在必然要受到历史性的批判,它必将成为过去,将来的已经在等待着现身。而生产方式作为对人类组织自身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模态表述,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它之提出,目的其实很明确,即用来说明这些关系都是暂时的,都是要发生变化,要被扬弃的。因此,生产方式在哲学上同样代表着一种诉求。理想的或纯粹化的生产方式在现实中从来都是不存在的,而且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它也没有必要存在。它之提出就是要指出,在历史中一直都存在着一种使现实发生变革的内在要求,正是这种内在的变革要求才是历史本体之根,而这一要求就是由生产方式之中的内在矛盾所发动的。而且,它作为一种诉求还呈现为缺席状态,即只有当现实的生产方式受到批判以后,以往的历史才能得到理解。必须注意,那种直接现身而出的生产方式是经济学概念而不是哲学概念。作为本体的生产方式本身是不直接现身的,因为如果一旦现身而出,它就成为认识论的对象而使其本体意味受到伤害。
近来,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与讨论非常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是由卢卡奇所引发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例如有观点就认为:“马克思的本体论是一种人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或‘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论’。”[11]那么,我为什么不取“社会存在本体论”这个流行的说法,而特别提出历史本体论来呢?原因主要有两方面,首先,我认为,“社会存在本体论”这种本体论思维方法,虽然与传统的以“实体中心主义”为其实质的“传统本体论”有了一定的区别[11],但是,这种“社会存在本体论”“从社会存在出发解读存在的意义”[11],仍然把社会存在视作一种可以现成地获得的批判基础,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本体论思维方法仍没有与“实体中心主义”的本体彻底划清界限,它仍是可现身的。其次,在这种本体论中,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仍处于对立状态,例如他们就提出:“马克思又从社会存在出发解读自然存在的意义”[11],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提出这种对立是可以通过实践来加以消解的。在这里,社会存在一方面仍是可作为基础而现身的。另一方面,无论怎样解读,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作为对立的两极的特征仍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只有祭出(生命)实践这个法宝。这样,“实践本体论”就又成了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
有鉴于此,我认为要彻底体现马克思哲学在本体论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就必须找到一个不在现实中直接出场的动态本体。而这个动态本体,我认为就是作为本体的历史,作为存在,它就是作为“缺席的原因”的生产方式。可以说,从哲学上来说,生产方式范畴本身并不是认识的对象,它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原因,作为一种方法,在完成对现实(即当下的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的批判后,最终成为对未来的一种宣告。而且,作为这种宣告,它也不是一种现实的对象(即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现实的制度),而是一种现实的运动。
那么,在哲学之外,生产方式还能不能用来作为说明历史上的其他时代的认识工具呢?我认为,是可以的(当其可以时,它就是历史科学或经济学的实证概念,而不是哲学范畴),但即使适用,也只具有局部的适用性。关于原始社会形态的一些争论至少可以说明,生产方式作为对既往的过去的一种说明方法是必须加以适当的限制的。因此,对于生产方式不应像以往那样,仅仅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相反,它的确更多地是历史的一种“缺席的原因”。
简言之,本体历史在马克思哲学中是作为生产方式而存在的。这种存在是一种非当下存在,是不在场的,是缺席的,或者说是历史对我们的一种注视,而作为人的实践存在方式,它对于过去的现实就是一种批判,对未来就是一种宣告。这种历史本体论关注正是马克思哲学的人文精神的精髓所在,同时,这种关注放弃了近代认识论的视角。历史的本体存在即生产方式,一旦不作为认识论的范畴而现身,过去凝固的东西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它已通过历史性,表现为对过去历史的批判。
在此还必须强调一点,马克思哲学的这种历史本体论与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存在主义本体论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差别就在于:这种历史本体论是通过马克思哲学方法论而得以建构的。虽然现象学的本体论道路也可以说是通过方法论而被打通的,但是,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与现象学方法还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借生产方式来分析社会关系,而这种分析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勇敢地给出关于社会历史的承诺,它并没有躲到此在(我)的存在的原初之境中去求得安慰。借蒂利希的话来说,在这种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哲学最为完满的关于存在的勇气,因为这种分析的惟一目的就是揭示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暂时性,并要求通过革命的实践活动对此加以改变。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本体论虽是马克思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但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所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认识论以及存在主义本体论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例如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中,海德格尔式的存在本体论的渗透就十分严重。这之中最重要的一个理论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哲学方法论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中的地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为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重新解读出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并说明其与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关系,而不是直接去奢谈一般哲学本体论。
【参考文献】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
韩震、孟鸣岐:《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性概念的哲学阐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分析哲学论文范文3
【英文摘要】ThefurtherexpansionanddeepeningofthestudyofMarxistphilosophyarehindereddirectlybytheintellectualthinkingmodeofbinaryantinomywhichisusedtounderstandMarx''''sphilosophyandeventuallytoformtheabstracttheoreticaldogmas.ThisarticleemphaticallyreviewsandanalyzesthetwodogmaswhichhaveimportantinfluencesinMarxistphilosophy,namelythebinaryantinomydogmasof“mature”and“immature”,aswellasthatof“explainingtheworld”and“transformingtheworld”.Thefactisalsopointedoutthattherearenosufflcientfoundationsofscientificprinciplesbetweenthetwodogmasandtheyviolatethenatureofexistenceanddevelopmentofphilosophyaswell.Therefore,overcomingthisabstracttheoreticaldogmaisanimportantprerequisiteofpromotingMarxistphilosophyanddevelopitinahealthyway.
【关键词】二元对立/“成熟”与“不成熟”/“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binaryantinomy/“mature”and“immature”/“explainingtheworld”and“transformingtheworld”
【正文】
我们的生活捉摸不定,世界变化无常,我们需要赋予世界以意义。为此,人们最常使用的心智策略就是“二分法”,通过把事物和世界区分为昼与夜、黑与白、现象与本质、恶与善、真与假等二元对立关系,使复杂的世界呈现出“秩序”,显现出易为人所把握的“意义”。然而,“二分化”实质上是一种“知性方法”,把本来是“整全”的事物“一分为二”,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便是“事物本身”具体、丰富的内容的遗漏和丧失。在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我们运用这种“二分化”,形成了一系列的知性对立关系,并由此逐渐演化为种种理论教条。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亟需超越这些由二极对立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理论教条。本文仅通过对两个教条的分析,来引发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
一、“成熟”与“不成熟”二元对立的教条及其超越
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影响最大的一对二元对立关系无疑是所谓“不成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对立。它认为,在“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断裂,“早期马克思”是“不成熟的马克思”,只有“晚期马克思”才是“成熟的马克思”,因此今天理解马克思,最重要的阐发“成熟马克思”的思想并自觉地与“不成熟的马克思”划清界线并对之采取批判态度。这种观念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具有重大影响,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理论教条而被接受下来。
需要予以反思的是,把马克思思想区分为“成熟的马克思”与“不成熟的马克思”,我们所赖以依靠的根据或标准是什么?这种根据或标准是否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综合以往种种观点,人们主要提出了如下三种有代表性的“标准”。
第一,以“成熟的马克思”为标准。以“成熟的马克思”为参照,来区分“成熟”与“不成熟”,这是人们通常采取的一种做法。它假定,马克思的思想以时间为次序,遵循着不断抛弃不成熟的旧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越来越走向成熟的过程,因此,以“成熟的马克思”为坐标,即可十分清楚地确定“成熟”与“不成熟”的分野,从而达到清除“不成熟”的成分并保留“成熟”成果的目的。
然而,以“成熟马克思”作为区分标准,这种确立标准的方式实质上是把衡量的对象用作了衡量的标准,因而内在地包含着一种逻辑上的“自我循环”。按照基本的逻辑要求,要找到区分“成熟”与“不成熟”的标准,合理的途径是在“成熟”与“不成熟”之外找到一个“第三者”,这“第三者”能提供一种尺度,来衡量和确定孰为“成熟”、孰为“不成熟”、孰为“在成熟与不成熟之间”等等,而不能用本来属于衡量对象的“成熟”来规定同样作为衡量对象的“不成熟”,这道理就如同要确定何者为长、何者为短、何者为高、何者为低,必须找到一把超出衡量对象的公共的尺子一样。“成熟”与“不成熟”是一种互相循环、互为对方的关系,要知道何为“成熟”,必然先知道何为“不成熟”,而要确定何为“不成熟”,又必须先定义何为“成熟”,因此,以“成熟”来界定“不成熟”,不过是在作无意义的同语反复。可见,以“成熟马克思”作为标准,而不能在“成熟”与“不成熟”之外找到某种第三者作为衡量尺度,这样来界定“不成熟的马克思”,等于陷入了一种语义的自我缠绕和自我循环,不能为问题本身的解决增添任何新的有效知识。
其二,以马克思思想演化的时间先后次序为标准。这与上述密切相关,它假定,马克思的思想越到后期,就越成熟,越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而越是早期,越是开始阶段,其思想就越幼稚,就离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越远。很清楚,以此为标准,马克思的早期即是“不成熟”的代名词,而到晚期,马克思的思想达到了成熟的巅峰。
然而,以“时间”为标准,所选定的乃是一个物理学意义的自然尺度。物理时间可以标明早晚先后,但无法处理和规定“成熟”与“不成熟”、“幼稚”与“深刻”等包含丰富思想内涵和容量的课题。在思想史上,晚来的思想不一定比古典的思想深刻,今人的思想未必较古人成熟,晚期的思想未必比早期的思想高明,这是一个稍有思想史常识的人皆明白的道理。因此,纯粹以物理时间为标准来给“不成熟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划界,很显然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其三,以某种权威论述作为标准,即试图以某个思想家在阐释马克思时所持的观点作为依据,来确定“成熟”与“不成熟”。比较典型的,如以前苏联教科书所认定和阐发的“成熟马克思”为依据,以阿尔都塞关于“认识论的断裂”的论述为依据,以第二国际理论家所理解的“真正的马克思”为依据,以普列汉诺夫等人对马克思的理解为依据等等。
问题是,无论哪位思想家的论述,所表现的都不过是他从某一特定视角所作出的理解,其中内在地蕴含着他个人的思想偏好和理论倾向,并必然深受其理论素养、思想视野以及所处时代的限制,因此这种理解可能十分精辟和深刻,但仍不足以作为规定其它思想家理论性质的终极判据。对于“早期柏拉图”与“晚期柏拉图”,哲学史上留下了许许多多思想家的阐发和评判,但今天难以绝对地判定晚期柏拉图必定比早期柏拉图更“成熟”,对“维特根斯坦Ⅰ”和“维特根斯坦Ⅱ”,对于“海德格尔Ⅰ”和“海德格尔Ⅱ”也同样作如是观。比较合理的说法只能是,思想家们的思想虽然在不同阶段存在某种差别和变化,但无论“早期”还是“晚期”,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因而很难以“成熟”和“不成熟”这种二分的框架来简单地予以裁割。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当人们试图把马克思二分为“成熟”与“不成熟”之时,它所凭借的标准其实是经不起仔细盘查和反思的。
那么,是否在上述三种标准之外,还有可能找到其它的“合适”的划分标准呢?我们认为,这同样十分困难。这是因为,上述标准之所以难以成立,并非单纯标准自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设定标准的观念和方式在根本上就是不恰当的,就实质而言,这种设定标准的观念和方式具有鲜明的“先验主义”性质,它企图找到某种超越时空的原则,对经典作家的思想划分“成熟”与“不成熟”,试图把“不成熟”部分剔除而保留“成熟”部分,这种阐释方式违背了人文学科最基本的诠释学原理,遗忘了人文思想存在、流传和演化的特殊规律。根据现代哲学诠释学所提供的洞见,精神科学的思想理论一旦产生,就进入了历史性的时间之流中,交付给了后人的阅读和理解,并在与后人的对话中不断延续和增殖其意义,只要人类的理解活动不终止,这种意义的增殖过程也就永远不会终结。一种理论正是在此生生不息的过程中,生成为所谓“传统”。具体而言,思想理论的流传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开放性。它总是面向未来并对未来有所期待,理论文本的意义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的,“一段文本或一件艺术品的真正意义的发现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2)与理解主体内在的相关性。理论文本的意义不是由原作品单方面地决定的,而是生成于读者与作者创造性的对话中,通过这种对话,理解者和原作的历史间距才真正得以克服;(3)理论传统的自我超越性。“传统”不是一种静止凝滞的“实体”,相反,“生成流变”和“自我超越”是“传统”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或者说,传统根本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时刻保持创造态势的“动词”。
可见,哲学解释学所提供的是一种与“先验主义”有着根本差别的“历史性”立场。坚持这种立场来看马克思的著作和思想,那么,无论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其各自的意义和价值如何,就不能靠某种原则和标准来先天地予以决定,而只能通过后人带着特有的生活旨趣,在与其不断地对话和阐释中来历史性地显示和生成,在某种特定诠释学处境中,也许马克思早期思想会凸显出来,进入人们的理解视域,显现出其特殊的意义,而在另外某种诠释学处境,马克思的中期或晚期思想则可能会受到特殊的重视,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所有这些,都不能以某种先验的“成熟”和“不成熟”的二分法来匡定,而只能用“效果历史”和“理解的辩证法”来予以阐明。
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过程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在判决为“不成熟”之处,却有时恰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与时俱进、取得重大理论成果的思想源泉,而被认定为“成熟”的地方,在不少情况下却恰恰陷入了僵化和教条。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当论景观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当代思想界占有重要一席。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中不少人主要所发掘和阐发的正是被视为“不成熟”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如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柯西克、沙夫以及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学者们等等,他们充分利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有关思想,来批判性地考察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寻求克服现代人生存困境的可能出路,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在中国思想界,学者们也曾通过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开掘,有力地冲击了僵化教条的哲学观念,尤其是它所凸显的人文向度和人文激情,使得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活力,无论在社会思想启蒙的层面上,还是学术观念变革的层面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只能由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和特殊的诠释学处境来解释,如果固守“成熟”与“不成熟”的二分法教条,必然会无视他们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并对之采取简单粗暴的排斥态度。
把马克思思想非得分割为“成熟”与“不成熟”不可,然后把“不成熟”部分作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剔除出去,这种对待思想家的方式在思想史上并不多见。我们把柏拉图、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区分为前期和后期,但没有人认为他们的前期或后期思想是“非柏拉图”、“非维特根斯坦”或“非海德格尔”的,我们都能同意,他们之所以成为杰出的思想家,是因为他们思想的全部历史,至于早期高明,还是晚期深刻,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马克思享受这一特殊“待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种非学术的因素或抽象的原则所致。由此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本身可以通过当代人的阐释焕发强大生命力的思想财富,被人为划定的“成熟”与“不成熟”的先验界线窒息了。
因此,抛弃“成熟”与“不成熟”二分的先验主义教条,实质上就是要抛弃以一种人为的尺度来限制马克思思想创生力的做法,一方面让当代人在与马克思思想的相遇中,获得充分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解除马克思身上的人为束缚,让他的全部思想,在充分的敞开中,不断地生成新的思想道路。这无论对于当代人,还是对于马克思,都无疑将是一件幸事。
二、“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二元对立的教条及其超越
与“成熟”与“不成熟”的二分法同样根深蒂固、影响甚广的另一教条是“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坚持,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马克思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因而是“革命的哲学”,而其它哲学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因而属于“保守的哲学”。因此,对待马克思哲学,最重要的是坚持其“改造世界”的精神,如果试图在马克思哲学的名义下,对哲学和哲学问题进行一种纯学术化的阐发,就会使马克思哲学丧失其真实本性,沦为与马克思哲学精神相违背的某种与旧哲学类似的东西。
马克思是以“改造世界”为旨趣的哲学,这一点恐怕无人反对,但问题是,“改造世界”的哲学是否必然与“解释世界”的哲学相对立?没有“解释世界”的哲学作为前提和依据,“改造世界”是否可能?坚持“解释世界”的哲学,是否必然与马克思哲学的精神相悖?“解释世界”的哲学向度,是否可以在“改造世界”的主张下被剔除出去?
只要对“改造世界的哲学”这一用语进行语义分析,就可以发现其中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这种哲学的根本目的是要“改造世界”,也就是说,要让思想在实践上变为一种现实力量,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这种哲学;另一方面,它表明的是,这仍然是一种哲学,一种“理论学说”,而既然是一种“理论学说”,按照奎因的“本体论承诺”的观点,任何一种理论,都内在地包含着关于“何物存在”的指向,也就是说,只要用语言逻辑的方式表达一种学说,就必然对于“世界为何”作出一种承诺,因而不可避免地对“何物存在”已或隐或显地作出一种解释,否则它就不可能以语言系统、以理论学说的形式存在。因此,在“改造世界的哲学”这一用语里,实际上已蕴含了“解释世界”的内容和向度。
“解释世界”的哲学与“改造世界”的哲学的二分法承诺着,世界上存在两种截然有别的哲学类型,一种是旨在“解释世界”的哲学,另一种是旨在“改造世界”的哲学。然而综观全部哲学史,我们找不到任何一种哲学可以完全归结于其中的任何一类,既没有单纯“解释世界”的哲学,也没有单纯“改造世界”的哲学。
首先,单纯“解释世界”的哲学是不存在的。按照上述二分法,古希腊哲学可以说算得上典型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了,那些最早的哲学家认为感官所见世界是不真实的,它认为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用真正的话语和逻辑,来寻求世界的“原理”和“原因”,来揭示和表明事物区别于显相的本相。然而,深入考察就可以发现,哲学寻求对世界的“解释”,寻求区别于表象世界的“真理”,实质上已蕴含着批判和否定现存世界、要求按照“真理”来“改造”现存世界的意向和冲动,就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按照真理来思考就是答应要按照真理去生存”……‘是’蕴含着‘应当’”,“寻求正确的定义,寻求善、正义、忠孝和知识的‘概念’,于是就变成一项颠覆性的事业,因为所要寻求的概念意指一种新的城邦”,可见,即使在以“解释世界”著称的哲学里,实际上已内在地蕴含着“改造世界”的强烈冲动。
这一点所反映的正是哲学与科学的重大区别。科学的理论抱负在于“如实”地揭示“事实”,对它而言,“价值”和“应该”的问题属于非理性的领域因而应被科学所放逐;与此不同,哲学关于“是”的陈述从来就不是无价值预设的中性框架和判断,而是内在地与“应该”、与“价值”问题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因此,哲学的“解释世界”并不是要像科学一样提供“客观知识”,而是内在地表达着哲学家的人生态度、价值理想和社会政治关怀。在此意义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解释世界”的哲学,在“解释世界”的哲学中,总是内在地包含着“改造世界”的情怀。这一点,苏格拉底如此(只要听听他“雅典的牛虻”的自喻就可清楚看出),柏拉图如此(其“解释世界”的“理念论”最终落实为“改造”现存世界的“理想国”)、黑格尔也无不如此(正如马尔库塞所深入论证的,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所意味着的是宣布“不合理”的现存状态应该灭亡的革命精神)。
同样,也从来不存在单纯的“改造世界”的哲学。因为哲学的改变世界,与工程师、技工不同,它没有别的工具,所直接凭借的只能是思想的力量。思想要有力量,需要的是理性的分析和理论的论证,借用德鲁兹的话来说,需要的是“制造概念”,通过概念来描述和展开一个“世界”。因此,从逻辑上讲,一种哲学首先必须是“解释世界”的理论,然后才谈得上是“改造世界”的哲学。就马克思来说,他首先提供的是一整套关于世界、关于社会历史“是什么”的学说,他认为这种关于“是什么”的学说,揭露了世界的社会历史的“本来面目”,然后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世界、人类社会“应该如何”,“应如何改造”的纲领和主张。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本体性”的前提和根据,后者是前者在行动和实践层面上的自然引伸和体现,前者与后者的关系,借用康德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解释世界”若无“改造世界”来落实,则“空”,而“改造世界”若无“解释世界”来范导,则“盲”。
可见,“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双重意向,其实是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任何一种哲学都具有的特点。深入解剖即可发现,这一点所表现的正是哲学的本性。在哲学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中,“真”具有首要的地位(虽然哲学家们关于真的理解很不相同),没有一种哲学不声称自己的哲学所要寻求的是“真理”,黑格尔甚至把真理称为“上帝”,但哲学追求的真理,总是与“善”和“美”不可分离的,哲学求“真”,是为了实现“善”,是为了趋于“美”,正因为此,我们常说,真善美的统一,是哲学自古以来就追求的最高目标(至于哲学的这种追求,是否合理,是否可能,追求这种统一可能导致何种后果,在此不作专门评论,而只限于指出这一事实)。在此意义上,对于哲学来说,“解释世界”的“真”与通过“改造世界”而达成“善”和“美”,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的事情,人为地把它们分离开来,制造出所谓“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知性对立,所表明的正是对哲学本性的误解。
从哲学史上看,马克思哲学是追求“真”“善”“美”三者统一的最为典型的哲学之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所追求的就是“真”,即要让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和规律给出自己的系统“解释”。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无可否认的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有人用中国古代哲学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来概括马克思哲学这方面的功能,可谓十分恰切。马克思通过“解释世界”,发现了现存世界的“非理性”和“非人性”,确认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改变现状,以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时,马克思所强调的是通过革命实践,来实现“善”与“美”的价值,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哲学又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正如人们所形象地比喻的那样,此时他追求的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真善美,“是”与“应该”、“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完全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构成马克思哲学一体中的两面。
毫无疑问,马克思自觉地确立了“实践”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与他以前的哲学的一个重大不同。但实践观点之成为是一种“观点”,表明它仍然是一种理解现实、解释历史的“理论原则”和“思维方式”(perspective),例如,马克思说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P58),这就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是把“实践”作为理解“对象”和“现实”的一种“理论”。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实践”观点确实具有解释世界、澄明“存在”的“本体论”意义。
因此,无论从哲学的本性,还是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构成而言,“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二分的教条都是难以成立的。片面强调“改造世界”而忽视其“解释世界”的维度,体现的是一种过于“实用理性”的倾向,这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是不利的。正确的做法是分清层次,自觉地认识到,马克思哲学既有“解释世界”的理论识见,同时又有“改造世界”的强烈追求,从而让二者既相关联,同时又各得其所。这将既保证马克思哲学不失其“改造世界”的信念,同时又切实地为哲学的基础理论探索敞开一个宽阔的空间.
【参考文献】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分析哲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传统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绝对真理式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正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哲学、政治学、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体系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但只要我们深入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原因所导致的。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到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从上述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的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
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
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
[1]张奎良.哲学的希望之光[J].哲学原理(人大复印资料),1995(11).
[2]韩秋红、胡长栓.关于哲学发展的时代性沉思[J].哲学原理(人大复印资料),1997(1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分析哲学论文范文5
在一般人看来,中西哲学的区别显而易见,根本不需特意加以区分。其实不然。由于中国人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对古代中国哲学开始研究的,自然而然会比照西方哲学的样子来理解和重塑中国哲学。明明知道中西哲学有重大的不同,中国哲学不是西方哲学,可是在实际研究时却往往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的问题、形态、范畴和概念来论述和要求中国哲学,结果是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因为西方哲学以本体论(ontology,应译为“存在论”)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所以我们也要在中国哲学中找出本体论,却不知将ontology理解为“本体论”本身已经错了。Ontology是对“存在”的研究,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因此,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可能有存在论。但由于首先将ontology误解为“本体论”,因而以为既然宋儒那里已经有了“本体”概念,中国哲学当然有本体论。殊不知传统中国哲学的“本体”概念与西方哲学的存在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
再比如人们在谈论中国传统哲学时开口“主体”,闭口“主体性”,甚至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就是主体性。例如,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一书中就说,中国哲学的特质“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哲学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1]劳思光认为哲学或归于主体性,或归于客体性。“中国哲学传统中,诚然有宇宙论,形上学等等,但儒学及中国佛学的基本旨趣,都在‘主体性’上,而不在‘客体性’上。”[2]这种对中国哲学特质的认定是成问题的。
“主体性”(subjectivity)并不像那些先生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哲学的普遍原则;而是一个非常西方的概念。并且,它在漫长的西方经历了几次重大的变化。主体性这个概念是从主体(subject)这个概念派生的。现代西文中Subject(主体)这个概念来自拉丁文subjectum,,而它又是希腊词hypokeimenon的拉丁文翻译,意思是“支撑者”,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这个词指属性的承载者。这个意义上的主体的意思近于Substance(实体)。因此,在逻辑推理当中,它又是一切谓语的主语(支撑者)。到了近代,从这里引申出灵魂或精神是一切意识状态的承载者或支撑者的意思。根据这种用法,主体是指意识的统一性,与“我”或“自我”基本同义。主体性概念就是建立在这个起源于17世纪的主体语义上,换言之,它建立在主体的一种特殊的(近代西方哲学)语义上。康德是这种主体和主体性概念的最后完成者(上述港台哲学史家心目中的主体性基本是康德意义上,也就是近代西方主体性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黑格尔和马克思尽管也使用主体和主体性的概念,但正是从他们开始,主体和主体性概念在西方哲学中开始了它们自己的去主体或结构过程。一个世纪以来,主体性的衰落早已是现代西方哲学的标志性景观,论述主体性衰落或“主体性的黄昏”的著作汗牛充栋,不绝如缕。一个多世纪的西方哲学家对主体性概念的批判,使得主体性哲学内在隐含的问题暴露无遗,也使得17、18世纪西方哲学的主体性概念注定只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哲学的普遍原则。
近代西方哲学的这两个基本概念的产生不仅与西方哲学本身发展的理路有关,也与近代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关,饱含这方面的内容。除此之外,还与西方语言严格区分主谓语有关。而汉语由于“没有分明的动词,所以谓语不分明,而因为谓语不分明,遂致主语不发明。主语不分明,乃致思想上‘主体’(subject)与‘本体’(substance)的概念不发达。”[3]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可能有“主体”和“主体性”这样的东西。我们不能用中国哲学中没有的东西来表明中国哲学的特质。
有趣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中国哲学的写作者和研究者会不强调或不承认中西哲学的根本不同。然而,这种承认的基本模式一直没有摆脱近代那种比较简单机械的做法,就是先指出西方哲学的特点,然后中国哲学一定与之相反。如西方哲学重思辨,中国哲学重实践;西方哲学重知识,中国哲学重道德;西方哲学追求的是知识的真理,中国哲学追求的则是超知识的真理;西方哲学重分析,中国哲学重直觉;西方哲学求客观世界的真相,中国哲学求内圣外王;西方哲学的核心观念是自然,中国哲学的核心观念是生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彷佛上帝有意安排,中西哲学总是反向而行。这种独断机械的对中西哲学特征的对举概括,几乎没有一个是正确的。
明确中西哲学的区别,决不是将中西哲学作为对立面来观察,来看待。这种做法既歪曲了中国哲学,也歪曲了西方哲学。中西哲学之间的确存在着重大区别,但这种区别不一定是截然相反;它们之间除了区别外也有相近和相似的地方。明确中西哲学的区别,不是要将这二者机械对立起来,而是要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特质,避免西化中国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由于其产生的根源、背景,面临的问题,整个文化传统,思维语言以及思维方式都与西方哲学有根本的不同,它注定在形态上、问题上、方式上和特质上与西方哲学有重大的不同,这种重大的不同决定了我们不能将西方哲学的形态、概念、方式、问题简单机械地加以挪用和平移。相反,我们应该努力提炼中国哲学独特的形态、问题、概念体系和方式方法,为真正的世界哲学作出我们独特的贡献。
平心而论,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那么复杂。西方哲学在古希腊时已成呈百家争鸣的局面,后又融入基督教和阿拉伯文化的因素,到了近代,各民族国家的哲学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与不同,因此,泛泛而谈西方哲学如何如何是很不科学的。中国哲学相对而言要简单些。先秦诸子百家的确精彩纷呈,但魏晋以后除了佛教哲学有些影响外,基本是儒家哲学一枝独秀,诸子学直到清末才方始复苏。当然,这期间儒家哲学还是有许多变化,但其与原始儒学的区别与西方哲学中希腊哲学与基督教哲学或近代哲学的距离,不可同日而语。
但这只是中西哲学比较表面的不同,它并不能决定中国哲学的特质。决定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因素首先在于其起源上的特殊性。中国古代相对完备的政教制度使得学术文化最初在相当程度上竟属官守。班固《汉书·艺文志》依刘歆《七略》分列诸子与王官关系如下: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等等。章学诚在《校雠通议》中也说:
“后世文字,必溯源於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在隶司乐,《诗》领於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有官斯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於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4]
这就是后来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张本。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亦言:“是故九流皆出于王官,及其发舒,王官所不能与。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义。”[5]当然,也有不同意的。如胡适就写过《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的主要论点是“诸子出于王官”说“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6]胡适的意见并非全无道理,班固等人可能确有牵强附会的毛病,但诸子学说亦不可能凭空发生。如果古代的确有职掌文教之官(这一点胡适恐无法否认),是古代思想文化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那么诸子不可能与王官之学毫无关系。由于古代除王官之学外再无别的思想文化资源,它必然构成诸子之学的主要来源。其次,哲学思想的产生需要闲暇。就像在古希腊只有奴隶主才可能从事哲学活动一样,[7]在中国古代要从事学术活动也需要行有余力,并需要有机会接触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先秦诸子若要有所发明,必须以王官之学作为他们学术思想的起点。而在春秋之际,官学变为私学,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提供了接触官学的机会。这也是先秦学术繁荣发达的一个外在原因。[8]先秦诸子的这个思想渊源,加上他们身处一个世变剧烈,危机重重的时代,奠定他们思想现实关怀的基本倾向。
中国最早的哲学家与古希腊哲学家另一个重要不同是他们有共同的经典作为思想的资源或出发点。《庄子·天下篇》说六艺为百家所共习:“……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章太炎亦曾指出:“六经者,周之史籍。道墨亦诵习之,岂专儒家之业。”[9]班固甚至说诸子九流“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10]而古希腊哲学家除了《荷马史诗》外没有共同的经典。更重要的是,这些上古流传下来的经典,大都是政史之书。自先秦以来,就有将这些经典视为史书的传统。从庄子“旧法世传之史”到章学诚的“六经皆史”[11]和章太炎的“六经者,周之史籍”,人们一直将六经看作历史。古人并非不知道,“六经皆官书,特典册之大者耳”,[12]之所以仍认为六经皆史,是因为他们对“史”的理解与近代实证主义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近代实证主义对历史的理解是,历史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纪录。而按近代史学家金毓黼的说法,“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文书草,略如后世官署之掾吏。”[13]这就是说,史之所记,多为政事、政法、政令、政制、政典。由于这些东西都与国计民生和社会政治有关,所以人们很容易将与此有关的文书典籍都算为“史”:“《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于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昭王者也。”[14]不宁惟是。古人向来不把史看作与当下人生无关的断烂朝报,而是看作有关世道人心,经世济邦的经法。不仅《春秋》,在古人眼里,六经皆关人事政治。“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蔽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者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15]作为中国哲学产生的共同的思想资源和出发点,六经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倾向产生了根本的影响。
中国哲学起源上的这两个根本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倾向和基本特质是实践哲学,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自从1958年海外新儒家的4个代表人物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认识》的宣言,将所谓心性之学定为“中国文化之神髓之所在”以来,随着新儒家对中国哲学影响的扩大,很多人以为中国哲学的特质就是心性之学。我们认为,将心性论阐释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和正宗,恰恰会使中国传统思想中真正有普遍永恒价值的东西埋没不彰。我们看到,在心性论的解释下,中国传统的实践哲学几乎被人遗忘,而诸子学研究也一直处于边缘状态。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研究,也不大有人问津。只有心性之学的研究一枝独秀,但也已室强弩之末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现状足以证明,以心性之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解释原则,遮蔽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缩小了中国哲学的问题域,限制了对哲学本身的开放性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中国传统思想,埋没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真正独特和永恒的东西。
当然,像“哲学”这个概念本身一样,“实践哲学”也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它用来阐明中国哲学的特点,因为它同样关乎人类思想行为的一些基本方面。在西方哲学中,“实践哲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实践哲学只是指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广义的实践哲学是指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人的公共世界和政治生活,人的自由活动和人际交往活动的哲学思考。如上所述,中国哲学起源上的两个特殊性使得它从一开始首先就是在狭义和广义两个意义上实践哲学。在外在形式上,先秦诸子就“论实际问题之语,诚较空谈玄理者为多。”[16]而思想去向上,更是无一不是要对世道人心有所思考匡正。孔慕大同,老称郅治,墨尚兼爱固不论,就是杨朱、名家、管子、法家等等,其思想趋向也无一不是实践哲学的。
但这决不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就只是实践哲学,更不是像有些人狭隘理解的,中国哲学只是道德伦理之学。相反,我们祖先形上之思的能力并不弱。他们同样会问“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所生恶起?……季真之莫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议,孰正于其情?孰偏于其理?”[17]“未有天地可知邪?……死生有待邪?有先天地生者物邪?”[18]“夫有形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19]“古初有物乎?……物无先后乎?……上下八方有极尽乎?……物有巨细乎?有脩短乎?有同异乎?”[20]这样类似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问的深奥问题。然而,中国古代哲学家并非一开始就是形而上学家。相反,他们的思想是从实践问题上升到思辨问题。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谁能极之?冯翼惟像,
何以识之?明明闇闇,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圜则九重,孰营度之?
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九天之际,
安放何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出自汤谷,次于蒙氾。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
而顾菟在腹?何闇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九州何错?山
谷何洿?东流不溢,孰知其故?东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顺墮,其衍几何?[21]
这是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许多形上气味强烈的问题的一部分。但屈原并不是玄学家,他本也无意像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那样以探寻宇宙世界奥秘为职志。他是在实践活动中遭遇极大挫折与不幸,在极度痛苦的情况下转向形而上学问题。“屈原放逐,……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伟谲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写愁思。”[22]汉人王逸对屈原形上之问产生的描写固然有想象的成分,亦合乎情理。
我们中国人向来是将“究天人之际”与“通古今之变”联系在一起的。“究天人之际”是为了“通古今之变”;而“通古今之变”必须“究天人之际”。古人向来认为,道通为一。“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23]内圣外王本非二事,“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才会“道术将为天下裂。”[24]因此,我们应该把实践哲学理解为中国古代的第一哲学,哲学的其他方面或其他哲学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当代一些研究者津津乐道的形而上学问题最早的中国哲学家并未在意。“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25]宇宙论问题也好,本体论(中国传统哲学意义)问题也好,既不是单独产生的,也不是最先产生的。形而上学在中国通过老庄、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几个阶段才渐成系统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说古希腊哲学要靠苏格拉底才把哲学从天上带回了人间;那么中国哲学是从人间逐渐向天上延伸,但始终没有离开人间。这是我们中国哲学最可宝贵的传统。
迄今为止,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是人生哲学的观点非常流行。研究者在其他问题上或有分歧,唯独在这个问题上少有异议。殊不知,所谓人生哲学乃实践哲学内涵之一。前面已经说过,实践哲学关心的是人类正确生活的方式和目的,实际上是对人生意义的思索欲探究。因此,广义的实践哲学总是与人生哲学有关。实践哲学的概念完全可以涵盖中国哲学是生命的学问或中国哲学的道德性之类的说法。孔孟老庄固然是要给人生一个引导性方向;西来的释氏又何尝不是。所以,即使包括佛教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是实践哲学仍然是说得通的。
衡诸整个古代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是实践哲学仍然不可动摇。虽然汉代并非如一般人所以为的,武帝以后就是儒家的一统天下;而是“武帝以后,学者犹皆治诸子百家之学。”[26]但“两汉思想家的共同特性,是对现实政治的特别关心。”[27]这就决定了两汉哲学基本的实践哲学特征。即如在被人看成“重知识不重道德”[28]的王充,其动机也完全是实践哲学的:“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机世俗。……况《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29]王充这里说的“是非”,不是知识论意义上的是非,而是“人间是非”。他的攻击目标不在纯知识世界,而在“世俗”。所以说他的哲学也属实践哲学范畴是没有问题的。与两汉哲学并非儒家哲学的一统天下一样,魏晋时代哲学也并非只有玄学。既便玄学,也是实践哲学意义上的玄学。从表面上看,玄学家消极避世,实际却正是实践哲学的考量使然:“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30]玄学家的清谈玄言并非空无内容,也并非在彼岸世界或超验世界。玄学家不像古希腊的犬儒,他们许多人本来都有志世事,迫于环境不得不流于空谈。但从哲学角度看,他们的言谈并不“空”,何晏、王弼玄思精深,但其实践哲学的取向,却是无可怀疑的。佛教哲学总的倾向当然是出世,但作为一种人生哲学或生命的学问,它同样应该算是实践哲学,而不是理论哲学。隋唐时代除了佛教哲学外哲学不甚发达,但基本是实践哲学一路是没什么疑问的。宋明理学被新儒家加以心性论解释后,其实践哲学的本旨往往湮没不彰。虽然宋明理学在形上思维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理学诞生的初衷,却并非是纯理论的。理学产生之原因按柳诒徵的解释是:“(一)则鉴于已往之社会之堕落,而思以道义矫之也;(二)则鉴于从来之学者专治训诂词章,不足以淑人群也;(三)则韩、李之学已开其绪,至宋盛行古文,遂因文而见道也;(四)则书籍之流通盛于前代,其传授鼓吹,极易广被也。而其尤大之原因,则沟通佛、老,以治儒书,发前人之所未发,遂别成一时代之学术。”[31]理学家是“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32]所以他们才能“不以事功为止境,亦不以禅寂为指归。”[33]“明体达用,本末兼赅。”[34]理学在明清之际遭到猛烈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明清哲学是以批判理学或维护理学来区分的。维护理学不去说,批判理学的无一不是以实践哲学的名义和理由。
总之,就像中国历史两千年来决不是停滞不前一样,中国哲学两千年里也是有许多发展的。但是其实践哲学的特质却没有根本的改变和消失。伟大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对中西哲学的特长作过如下的比较。他说:“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35]也许是旁观者清,莱布尼茨的这个观察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研究者却因为囿于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片面理解而看不到这个特征。
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倾向和特质是实践哲学,决不等于说中国古代哲学就只是实践哲学。如果那样认识的话,同样遮蔽了很多重要的东西。“实践哲学”不能包括中国传统哲学所有的东西,这是必须强调的。但它的确是了解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一个可靠进路。不能把中国哲学的所有问题都还原和化约为实践哲学,但中国传统哲学的大部分问题都与之囿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应该是没有疑义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各个流派都有实践哲学的倾向这一点,也是没有疑义的。因此,实践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真正特质,也是应该没有疑义的。
参考文献:
[1]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页四。
[2]参看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页四0二。
[3]张汝伦编:《理学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338页。
[4]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第一》,《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页九五一。
[5]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学》。
[6]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文集》,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0页。
[7]当然,也有例外,斯多葛学派的爱比克泰德就是奴隶出身。
[8]参看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9]章太炎:《国故论衡·原道上》。
[10]班固:《汉书·艺文志》。
[11]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此说实本阳明。王阳明《传习录》曰“五经皆史”。
[12]黄建中:“中国哲学之起原”,《学原》,第一卷,第三期,页三一。
[13]金毓黼:《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页。
[14]龚自珍:“古史鉤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页二一。
[15]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一百三十。
[16]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第11页。
[17]《庄子·则阳》。
[18]《庄子·知北游》。
[19]《列子·天瑞篇》。
[20]《列子·汤问篇》。
[21]屈原:《离骚·天问》。
[22]王逸:《楚辞章句·序》。
[23]《庄子·天下》。
[24]同上。
[25]《庄子·齐物论》。
[26]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312页。
[27]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4页。
[28]同上,第356页。
[29]王充:《论衡·对作篇》。
[30]房玄龄等:《晋书》,卷四十三。
[3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508页。
[32]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五六O。
[33]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第515页。
分析哲学论文范文6
在捷克现代历史上,哈维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出生于布拉格的有产阶级家庭,1960年代开始以戏剧而闻名于捷克的文化圈,并渐成为捷克公共领域内的一位风云人物。1970年代,哈维尔以《给胡萨克总统的公开信》和参加“七七运动”而成为捷克最著名的持,也因此而获罪于当时的捷克政府,几陷牢狱。这前后,哈维尔写下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有《无权者的权力》、《政治与良心》、《对沉默的解剖》等。1989年10月,哈维尔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物,参与了捷克的“”,1989年11月,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92年斯洛伐克分出去之后,1993年哈维尔当选为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98年连任,2003年2月期满卸任。
哈维尔其人其思其行,近几年来,也正逐渐受到我国学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先后作了一些介绍性的研究工作,也曾引起过一些讨论。2003年,由崔卫平编译的《哈维尔文集》,作为内部交流版的形式亦告问世。李慎之先生和徐友渔先生为之作序,对哈维尔的哲学和思想评价甚高。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对哈维尔的理解还存在许多问题。
哈维尔本人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哲学家,不同于我们今天研究的哲学史上的西方哲学家。而且,如有的论者所言,哈维尔的故事比其思想更值得关注。但是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有着独特魅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哈维尔的思想、著作及其实践中,有着坚定的哲学理念的支撑,对于这一理念的梳理,或有其意义。就本文所接触到的文献而言,我们认为,这一哲学理念集中的体现在哈维尔的政治哲学里,本文即试图对哈维尔的政治哲学作一初步的阐述。
一、作为道德的政治
不同于马基雅维利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在方法上也不同于学院里的政治哲学的教授们,没有罗尔斯、诺齐克、哈贝马斯们的严密论证和逻辑推演,
哈维尔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力图将一种人性的尺度、将人类精神和道德的维度带到政治和生活中去。就像批评他的人说的那样,他总是试图将两种不可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道德和政治。在这一点上,哈维尔所做的正如康德所论证的:“在客观上(在理论上),道德和政治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争论。”[1][P138]不同的是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一文附录里的详细论证,变成了哈维尔的思想和行动。
在哈维尔的视野里,政治决不再是权力的游戏和功利目的的手段。他明确的宣称:“政治不再是权力的伎俩和操纵,不再是高于人们的控制或相互利用的艺术,而是一个人寻找和获得意义的生活的道路,是保护人们和服务于人们的途径。我赞同政治作为对人类同胞真正富有人性的关怀。”[2][P136]这是他在作为持时期在体制外的呼喊,作了捷克总统以后,哈维尔依然坚信这种理念,在1991年的《政治、道德与公民性》一文中,他说:“真正的政治——配得上政治这个名称、也是我愿意致力的惟一的政治——就是为你周围的人们服务,为未来的人们服务。根植于政治最深的是道德,因为它是一种责任,对全体人民和为了全体人民通过行动来体现的责任,这是一个可名之为‘更高的’责任的东西,它拥有一个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它产生于意识或无意识之中的一个信念,即我们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别的某处被永远的记录了下来,永远的给予评价,这是‘高于我们’(above-us)的某处,我将之称为‘神的记忆’——这是宇宙、自然和生命的奥秘秩序中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信徒们将之称为上帝,一切事情都要接受其审判。”[2][P194]在哈维尔看来,道德是政治的基础,虽然这种观念从古希腊以来,在政治哲学领域里就不绝如缕,但哈维尔的坚持仍然赋予了这一古老观念以特殊的意义。哈维尔把人的良心看作是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他认为在有道德沦丧危险的社会里,要摆脱这个危险,就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而在哈维尔看来,这个原点就是有个性的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唤醒人的良知。“科学、技术、各种专业知识、专家主义并不是全部。某些东西是更必须的。简单地说,可以称之为精神,或情感,或良心。”[2][P203]近代以来,特别是在功利主义伦理和权力政治的笼罩下,从对政治的作用的角度看,鲜有政治家发出对良知或良心如此的渴盼之声,在此一点上,印度的“圣雄”甘地似或可与之并提。
哈维尔宣称,要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国家必须保持真正的人性,换句话说,国家必须是有精神、有灵魂和有道德的。”[2][P202]国家在这里,已不仅仅是一个实现社会成员目的的工具,而是一个具有德性符合人性的拟人化的实体。如果没有人性和社会价值的支撑,在这个国家里,“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机构……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和自由及人权。”[2][P202]“没有共同拥有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民主政府,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2][P202]即所有国家所能利用的最好工具也将违背其原来大的宗旨,这些工具包括我们迄今为止所能建立的制度,诸如法律、民主制度、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哈维尔认可现代欧美社会发展出来的价值系统,而且作为总统,他表示,要在捷克共和国予以实施。但是,他也认为,西方世界“由于某种普遍的道德危机导致的瘫痪无力,它一直未能利用民主这一伟大发明提供的所有机遇,并赋予业已为其打开的空间以某种意味深长的内涵。”[2][P252-253]这就是说,由于道德的危机,西方的民主等制度并非尽如人意,尽管基督教的道德世界曾经为西方现代民主贡献颇多。哈维尔认为,法律等制度并不能提供富有人性、尊严幸福的生活,它只起保障的作用,而不能给予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由道德赋予。在哈维尔看来,国家,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发展,都有赖于道德进步。这是哈维尔一贯的道德政治信念。
这种道德的政治,体现在政治主体身上,尤其对政治家来说,最要紧的是责任感。政治家不同于一般的个人,他要为许多人服务,而不是局限在自己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他的思想和行动关涉更多人的福祉,因此,政治家要有更多的责任感。这个立场哈维尔贯穿始终。最早在给胡萨克的那封长信中,他诚恳地呼吁:“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您的责任仍然是巨大的。您间接决定了我们所有人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氛围,因此直接影响了我们的社会要为今天的稳定所付出账单的最终规格。”[2][P28]及至他自己当上了国家领导人,他始终考虑的也是在总统位置上他本人可能对民族所造成的影响,他将尽力按照政治理想去做。这是他不仅作为政治家,更是作为一个人的信念,在监狱里,他写出来的信提到一个人的秘密就是他的责任感的秘密,他坚信:“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2][P105]
1996年哈维尔接受美国哈佛大学荣誉学位发表演讲时,在分析了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之后指出,除非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其他别无二途。而这“尤其是政治家的任务”,政治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不同寻常的:“我想,当前这一代政治家……他们的角色是有所不同的,就是要履行他们对我们世界的长远前景的责任,从而以他们的一言一行在公众心目中竖立榜样。他们的责任是勇敢地进行前瞻性的思考,不怕失宠於群众,让他们的行动浸透著一种精神特质(这当然与宗教仪式那种讲究排场不是一回事),去一再向公众和他们的同行解释,政治绝不仅仅是反映个别团体或游说集团的利益。当然,政治是一种为社群服务的事业,这意味著它是实践中的道德。难道政治家们在全球(及全球受威胁的)文明中寻找自身的全球政治责任,也就是说,为人类的生存负起责任,不是比单纯服务社群和实践道德要好得多吗?”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家,哈维尔力图使自己坚信的政治哲学为世界造福。二、生活在真实中
哈维尔的政治哲学的另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他的一句口号:生活在真实中。哈维尔认为:“生活在真实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估量的爆炸性的政治力量。”[2][P62]尽管哈维尔曾经以荒诞派戏剧家闻名于世,但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哈维尔关注现实,重视生活的真实和人性从虚伪向真实的回归。
生活在真实中的提倡,是从哈维尔对当时捷克的社会状态——即他所认为的后极权社会的谎言生活——的批评中发展出来的。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反复使用水果店经理的例子来说明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生活在谎言中的。这位水果店经理在其橱窗上贴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哈维尔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谎言生活。因为,在哈维尔看来,水果店经理从来不去思考他贴在橱窗上的标语,这些标语也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和他们每天买进卖出的生活丝毫不相关,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将这些标语混于洋葱和胡萝卜之间呢?哈维尔的回答是:“很简单因为许多年都这么做,每个人都这么做,这是必须采取的方式。如果他想拒绝,这可能带来麻烦,他可能因为没有照规定布置橱窗而受到责备,甚至指控他不忠诚。他做这件事是因为如果一个人想生存他就必须做。”[2][P52]理由如此简单。为了生存,人们选择生活在谎言之中,因为有无法抗拒的恐惧。“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并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2][P8]原来,生活在谎言中,是一个被迫的选择,是对真实目标大额不切实的回应,是在严厉压制下的无奈,是现实政治和生活压力下人性的扭曲,是一种异化。
在这种被异化的社会生活中,渗透着伪善和谎言:“由官僚掌握的政府被称作人民政府;在劳动阶级的名义下奴役人民;对个人彻底的贬抑被描述成他的完全的自由;……滑稽的选举变成民主的最高形式;禁止独立思想变成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了兄弟援助,因为这个制度被它自己的谎言所控制,它必然篡改每一件事情。”[2][P54]在这个制度下,人性已被扭曲,人们所做的仅仅是接受谎言并处于谎言之中的生活就足够了。这种人性的扭曲,是社会道德的危机。哈维尔揭示了谎言下的生活,也批评了在谎言中的生活,“生活在谎言中导致人类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转而造就了在谎言中生活的条件,这其中自然存在着道德上的维度。它首先表现为社会的深刻道德危机。”[2][P64]谎言下的生活和道德上的危机处在恶性的相互影响的链条上。而社会的道德危机就是社会的堕落,哈维尔试图努力挽救危机,挽救危机的途径只能是生活在真实中。
生活在真实中,按哈维尔的理解,就是人们对强迫境域的一种反抗,企图重新找回自己的责任感,这是一个道德的行动,尽管这个行动中,个人甚至可能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为了实现有尊严的“独立的社会生活”,这样行动是值得的。独立的社会生活,是生活在真实中的充分体现,独立生活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包括自我教育、对世界的思考、自由的创造活动、人际交流、各种自由的民间立场,也包括独立的社会自我组织。”[2][P79]独立生活的核心是人之为人的高度内在解放,它相对的是在压力下和恐惧下的生活,在压力和恐惧中,人和人的心灵是被奴役的,尽管我们似乎找不到奴役我们的具体的人。而且,这种解放不再仅仅是对生活在谎言中的简单否定,而是建设性的“积极敢言”。哈维尔认为,所谓的“持异议者”正是为之努力的群体,他们为生活在真实中的目标创造空间,他们提倡生活在真实中,是对以谎言为支柱的社会的最大威胁。在他看来,他所参加的捷克“七七”运动,就是生活在谎言中与生活在真实之间发生冲突。当然,哈维尔也有把“持异议者”的社会作用夸张化的趋势。
基于对道德的坚定信念,哈维尔以真实的生活来反抗谎言,并希望以此解救人性和道德危机。他鼓励人们鼓起勇气真实地生活,有尊严的生活,勇敢地承担道德赋予人的责任,将人们为之服务的制度改变成为人们服务的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呼吁要把政治建立在真实的存在之上,生活在真实中。当然,哈维尔不仅仅是一个停留在著述和呼吁上的哲人,而是积极的投入到实现生活在真实中的努力中去的。
哈维尔的建立在道德、良心和真实存在基础上的政治哲学,没有细致的概念推演和严密的逻辑分析,尽管它受到西方道德主义政治哲学甚至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但是他的哲学思想不是学院化的,不是系统化的晦涩的长篇论述,而是直接从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观察出来的,并且,也是以此为武器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和政治建设中去的。哈维尔的政治哲学是他个人政治活动的纲领,是他作为政治家的信条,他以一生的出色的政治实践为他的政治哲学作了最生动和最深刻的诠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