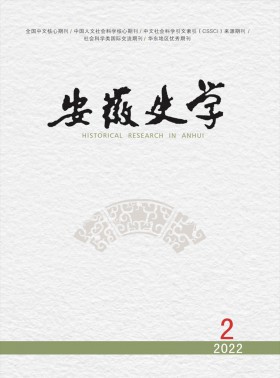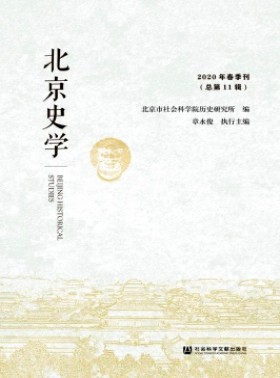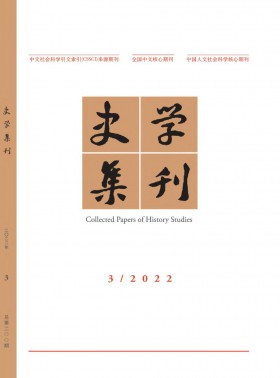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1
历史学的发展,同时也必将波及影响中学历史教学,为了顺应历史学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中学历史教学必须随历史学的发展而进行相应的改革。本文就史学观念的更新与中学历史教学进行初步的探讨。
首先,历史学家对现在与过去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是史学观念更新的表现之一。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二者是紧密联系的。以往由于根本忽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因而实际上割裂了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只是被动地从故纸堆中搜集资料去进行详尽的考订并加以描绘。而随史学观念的更新,这种认识发生了变化,更新了的史学观念把历史研究看作是现代历史学家根据可靠资料对过去的构建。在这个构建过程中,历史学家只能从现在出发,带着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对历史继承性的理解,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念。正如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所言:“古今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他的“由古知今”、“由今知古”的名言正表明了对“古”、“今”认识上的这种联系关系。
相对于史学的观念的这一更新现象,中学历史教师在课堂中授课时必须更新观念,在讲授历史人物、事件、现象时,要认清自己的授课受体(即自己的学生)和授课内容(即过去的历史性的人)双方都有由各自文化培育的对世界的看法,判断事物的标准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兴趣。许多过去发生的事件,当代人是很难理解的,例如当代学生没有亲身经历过“”,他们就很理解它,这还仅仅是发生在近四十年前的事,更不必说发生在久远的过去的事了。历史教师在授课时不应当以当代人的看法去取代过去时代人的观念,这样就会使很多问题不好解释或者解释错了。因此要求中学历史教师的史学观念跟上时代的步伐,根据各种史料去了解过去时代人们的观念、看法,特别是他们的内心意识、心态、情绪,然后再把了解到的过去时代人们的观念和当代研究者从当代水平出发的看法相结合,即把当时社会的自我评价与当代科学评价结合,使学生了解到当时的真实情况。
同时我们要知道,更新了的史学观念还要求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人不能被割裂开来,必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进行综合的总体研究。中学历史教师在评论一个历史人物时,更应看到他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⑤,应通过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去考察和评价,使学生明白这方面人的活动、作用或反映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其次,历史学家对自己与史料关系看法发生变化是当代史学观念更新的表现之二。
更新了的史学观念改变过去认为历史学家与史料关系消极被动的态度,认为历史学家不是被动地搜集史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史料收集者和考据者,认为历史学家是在开始研究工作之前已经有明确的问题,已有当时符合历史学水平的有关自己专题的知识准备,已有适当时代和环境的历史思想,不是无明确地去搜集史料,不是被动地任由史料摆布。正如马克・布洛赫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的目的,人们就可能老是在那些深奥冷僻又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历史学家事先提出的问题和他原有的专业和思想准备,确定了他对文献的选择和对所研究的文献的态度。可以说,正是由于他根据自己的专业方向和研究兴趣努力的结果,才使这些文献成为他的研究史料。
历史教师的传统观点认为史料随处可见,在授课过程中讲到哪儿就引用哪一方面的史料,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引用史料的盲目性,现在从更新了的史学观念中我们发现历史学家事先提出问题和他原有的专业知识和思想准备确定了他对文献的选择和他对所研究文献的态度。中学历史教师要“创造”史料,就必然要改变自己陈旧的观念,要让自己真正明白只有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带着明确的教育目的,这样才能“发现它们的特点”,“把握住它们在一定历史体系中的地位,才能将众多繁杂的史料”手到擒来,为我所用。
总之,不论是史家与过去的关系,还是史家与史料的关系,新的史学与旧的传统史学相比,都把它颠倒了过来。这足可表明史学观念的根本变化。自然,史学观念的更新并不仅仅表现在这方面。其它如对客观历史的综合研究、克服历史上曾经合理的把完整的历史分割成专题史的传统做法,以及打破与相邻学科的隔阂,实行跨学科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史学观念更新的各种表现,这里就不一一阐述,仅选择较为代表性的史家与过去的关系、史家与史料关系加以说明,但是对于中学历史教师来说,更新自己狭隘或不全面的史学观念,让自己首先在观念上跟上时代的步伐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课堂授课焕发出时代的气息。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2
一、扩大和加强世界史教师队伍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应用学科的发展、基础学科的相对萎缩和世界史研究生学位点的合并,世界史教学和科研队伍严重减员,同80年代中期相比,减员达60%-80%,以至于有个别重点大学连世界通史课程都开不完整。[2]在较好的综合性大学,虽设有世界史教研室,甚至还有专门的世界历史研究所,但一般也都只有10人左右的规模。而在一般性大学,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则更少且分散,很难形成团队。甚至在不少高校,由于找不到专门的世界史教师,不少中国史教师或其他与世界史关系更远的教师承担了世界史教学任务。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到世界史的教学质量。当务之急,各高校必须对世界史师资进行较大规模地扩容,以满足一线教学的需要。扩容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
1.优先考虑引进并培养世界史人才。根据北京大学高贷先生的调查统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世界史从业者大都达到或超过中国史从业者。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耶鲁大学历史系、加州伯克利大学历史学系、伊利诺伊斯厄巴那分校、南加州大学和纽约大学历史学系,从事本国史的教学人员只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其余教师都研究外国历史。韩国主要大学的历史系中,西洋史和东洋史合起来占到三分之二比例。俄罗斯历史学教师中约有50%从事世界史。[3]相比之下,在我国大学,从事世界史学科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在整个历史学从业人员中所占份额太少,一般来说,只占到1/8到1/7。这也意味着,在未来5-10年时间内,各高校历史系如要建立起同一级学科地位相称、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世界史学科,必须新补足占全系师资1/3到2/5的世界史教师。而目前中国高校每年所培养的世界史博士只相当于中国史的1/6到1/5,因而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这要求各高校必须不拘一格,用更优惠的政策吸引世界史及其相关专业的人才。相信很快全国有远见的高校都会花大力气搜罗世界史人才,争夺人才的竞争会趋于激烈。如果已有一定世界史研究水平的高校不尽早采取行动,很可能会在未来的世界史学科竞争中败下阵来。同时,为提高世界史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应在科研经费投入、出国留学等方面向其倾斜,使之多同国外大学进行交流,以开阔视野、提升教学水平和学术层次。
2.整合现有资源,优化师资力量。由于新引进的人才,特别是年轻博士一般需要经过多年时间才能积累起较丰富的教学经验,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所以,有条件的高校也可尝试整合校内资源,即跨学科、跨院系地发掘世界史师资力量,如在国际关系、政治、外语等院系和学科中从事与世界史相关的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在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邀请这些人员开设与他们研究领域相衔接的世界史课程。同时,在课题申请和攻关方面,应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这些力量,通过成立相关的专业研究所,如美国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中东问题研究所等形式构建历史系世界史师资与外系准世界史师资的合作机制。上述方法是解决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的应急之举,在短期内有助于高校世界史专业获得又好又快发展;跨院系和跨学科的整合也有可能产生长远的优化效应,但这一效应取决于上述整合能否在实质层面长久地进行下去,并要求与世界史相关的师资力量进行学科教学和研究方法向世界史方向的适当转型。当然,从世界史力量较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教授和学者来充实本校的世界史师资也不失为快捷高效之举。不过这种方法不能只流于形式,比如,聘个兼职教授,但一年只是做一两次的讲座。最好所聘兼职人员能在校开设专业课程,每年授课数月,并亲自指导本科生、研究生进行论文写作。
二、调整和优化世界史课程结构
基于世界史过去作为二级学科的地位,高校历史系本科生专业课程中几乎三分之二以上都是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课程比例一般不超过1/6,这样的课程设置使得对世界史感兴趣的学生不能够从课堂教学中获得更多的专业知识,久而久之会冲淡他们对世界史学习和钻研的热情。另外,在这样一种课程结构下培养出来的历史系本科生,一般来说其视野受到很大的局限,在观察和研究问题时缺乏开放性思维和世界性眼光。他们走上教学岗位,会对中学历史教育导向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世界史课程不仅是历史系本科生应该广泛、深入学习的课程,更应该成为大学通识教育的一部分,非历史学专业的文科生及理工科学生也都应该了解一定的世界史知识特别是世界近现代史知识。从上述理念出发,世界史的课程调整和优化应着眼以下两点:
1.在历史系本科生教学中,大幅度增加世界史课程,健全课程方向。根据调整前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国历史被划分成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两个二级学科,而且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专门史等其他几个二级学科,实际教学与研究的内容也都属于中国史范畴,这就使得世界史的学科配置与中国史相比,处在十分不合理的1:7的状况。[3]为改变这一状况,首先要增加世界史必修课的比例,除原有的通史课,即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等专业基础课外,像这些年发展得较为成熟的世界史方向课如西方文化史、英国史、美国史、国际关系史等可增列为历史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次,近些年在西方国家史学研究领域勃兴、揭示历史学宏观理论和发展动态的前沿课程,如历史社会学、世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欧洲社会史、欧洲经济史等可增列为专业必修课。除此之外,应广泛开设世界史专业选修课,以满足本科生对特定世界史方向的兴趣,选修课以区域史和若干国别史为主,如东亚史、南亚史、拉丁美洲史、欧洲史、非洲史、中东史、法国史、德国史、日本史、意大利史、西班牙史、犹太-以色列史等,各高校可根据自己的研究特色和专业优势来决定开设哪些课程。同时,一些与世界史专业联系很紧密,同时跨越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又非常贴近当代世界状况和现实需要的课程也可以有选择地开设,如现代化比较研究、当代世界政治与经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组织研究、世界风俗史、世界宗教史等。当然,上述选修课的开设需要配备足够的专业师资力量,不是所有学校在短时间都可开设,需要逐步发展,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切实、更有针对性的策略。
2.开设世界史公选课,以满足非历史专业学生对世界史知识的需求,增强他们的人文素养。世界史教育是高校非历史专业人文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长期以来,多数高校在非历史专业中并不开设世界史课程。即便有高校开设,世界史也只是一门注重知识传授,轻视学生素质培养的课程。对世界史的忽略及狭隘的专业教育,使高校学生存在以下缺陷:其一,爱国情感不深厚,爱国主义精神难以形成。其二,保守狭隘,目光短浅,对人类文明及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复杂性不了解,难以同世界上其他文明共容、共处,相互学习。缺乏现代公民意识及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国际意识和世界主义精神。其三,知识面窄,已学知识与未学知识之间不能迁移,较难做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4]可见,非历史专业通过世界史教学实施素质教育在我国高校还存在相当的真空,这要求我们必须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改变过去那种单纯强调历史专业世界史教学的狭隘观念,要在素质教育的视野和理念下重新审视世界史的教育功能、加强世界史的教学和改革。[5]具体地说,世界史的教学和改革应让大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并恰当地定位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地位,从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更加深刻地认识文明的多元性,树立兼容并包的心态和世界主义精神;通过学习西方历史和文化,更好地学习对中国现代化具有借鉴价值和激励意义的科学精神、民主与法制观念,更多地认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提升自己的审美和文化鉴赏能力。如何让历史系之外的学生学到世界史知识呢?对于在历史系本科生中开设的有些世界史课程,如专业选修课完全可以向外系放开选课,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让对某一个方向感兴趣的同学都能加入到学习世界史的行列中来。但是,在历史系开设的很多本科生课程并不适合外系没有专业背景的同学来学习,因为其有一定的难度和深度。比如,在历史系本科生中广泛开设的世界史断代课程,即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世界当代史等课程,是按照循序渐进、层层铺垫的原则开设的,而且课时量相当大,一般要经过四五个学期的学习才能完成,而且因为老师针对的是专业学生,所以讲得比较深。另外,因为这些课程是历史系所有本科生必选的基础课,所以外系同学可以获得的闲置选课空间非常有限。实际上,外系学生也没有选这类课程的必要。非历史系学生更多地希望从宽泛意义上和实用的角度来了解他们感兴趣的世界史知识。这样,高校世界史学科在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必须同时承担一定的公共教学的任务,即深入研究如何针对非历史专业同学开设更为简明扼要、生动有趣的世界史方向全校公选课程。建议课程包括以下几门:世界通史、欧洲史、当代美国、世界文化史、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现代国际关系史等。
三、对世界通史教学的几点想法
相比中国史而言,世界史的教学难度较大、学习门槛较高。这主要是由世界史的学科特点决定的,世界史上下五千年、横跨四大洋五大洲,涉及多种语言、种族、民族、国家、地区、文化和文明,头绪纷繁复杂,许多问题需要兼用宏观和微观思维进行深入思考才能求得解答。世界史教师通常需要经历长时间的教学实践和钻研,才能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而学习世界史的学生也须通过不间断的学习才能清晰地认知某些问题。世界通史课是世界史课程中的重中之重,世界通史教学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生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把握以及对其他世界历史课程的理解。结合目前世界通史教学存在的问题,建议在以下方面作出改进:
1.教学时间及教师的安排。世界通史教学应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并一直延续到大学四年级。目前高校的世界通史课一般安排在大学的一、二年级,学生地区史、国别史的基础薄弱,并且缺乏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素养。[6]针对上述情况,建议将世界通史课移到第二学年进行。第一学年主要讲授世界地区国别史、世界史学理论与方法、各类专门史课程。待学生有较好的基础后,再在第二学年开设世界通史课,并以断代讲授的方式一直延续到第四学年。经验较丰富的老教师一般来说驾驭整体的世界史能力较强,承担世界通史教学任务比较合适。但是,很多学校存在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年轻教师不得不担当重任。在这一情况下最好按照每个老师的研究专长进一步细分通史课程,从而减轻年轻老师的课时量,这样,他们才有更多的精力来备课,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一般来说,一门通史断代史课(如世界上古中古史、世界近代史等)有两到三位老师根据自己的专长共同担当较为合适。当然,他们之间事先要就教学思路、计划、内容等进行很好的沟通和协商。此外,每一个从事通史教学的老师至少应在教学岗位上连续坚守5年以上,这样才可能在通史教学上做到游刃有余。应尽可能给予每位青年教师从事通史教学的机会,这样可使他们不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具有更宏观的世界历史视野,同时,这也是培养通史教学后备力量的需要。当然,青年教师在接手通史教学任务之前,应积极地去听有经验的老教师讲通史课,并主动向他们求教。
2.突出大历史观,特别是文明史观和全球史观。所谓大历史观,指的是对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宏观性看法,当然,也包括对某些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现象的深刻见地。从目前的史流来看,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是较为典型的大历史观。全球史观冲破了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论史观,以世界各国各地区联系的日益紧密为根据,构筑了世界通史的新体系。吴于廑曾就全球史如此阐释:人类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漫长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过程。这个全部过程就是世界历史”。[7]全球史观有效避免了将世界通史讲成国别史或断代史集合的误区。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视角出发,建议将当前诸多高校所开设的世界现代史和世界当代史课程合并为“世界现代史”或者“20世纪世界史”,以更好地体现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及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特征。这一合并不是简单的课程组合,而是站在全球史观高度重新构建世界历史的全局观念。[8]可以说,全球史观顺应了时代形势,也预示了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的未来走向。此外,文明史观也是理解世界通史(尤其是世界上古中古史)的重要视角。张芝联指出,文明史不同于通史,又离不开通史。过去写通史时,一般把历史分成三大块:经济、政治、文化,而实际上往往把重点放在政治事件上,经济和文化仅作为基础和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一笔带过。[9]文明史视角看重历史过程中的人及其创造能力,看重人的历史创造过程及成果,突出不同地区和不同族群文明的特点,以及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如果在教学内容上突出文明史的视角,就能改变以往过分强调社会形态如何演变的问题,就能改变以往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如何发展变化的内容所占比重偏大的问题。[10]世界上古中古史很难用惯常的政治经济史模式来讲述,它揭示更多的是文明的起源、兴衰、成就及文明中心转移的问题。以文明史观来统摄世界上古中古史的教学,就能从多元、立体的层面更丰富地反映人类古代生活的主题,如种族、婚姻、家庭、文化、法律、宗教等,同时还可在不同文明之间做出有意义的比较,由此深化对世界文明共性和多样性的认识。从事世界史教学的教师首先应当深入学习和研究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以期通过通史教学将这些观念传达给学生。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吏观 历史理论 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2-0115-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和史学实际。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综观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理论成就值得关注。
一、对唯物史观内涵和外延的新阐发
史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并不相同,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学术创新历程。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90年代的学术创新以及21世纪以来的学术反思和展望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把唯物史观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克服了教条主义、公式化的理解,恢复了唯物史观的生机和活力。由从过去主要关注阶级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从关注阶级斗争史发展到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关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充分肯定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者以及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从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开始。史学界出现了编写历史学概论的热潮,其实质乃是主张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研究工作自身理论进行探索,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认识和解读。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比较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情况,可视为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著作。前者着重历史科学理论的探讨,强调社会矛盾运动、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民族关系等历史科学的理论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普遍指导作用;后者则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立足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梳理总结出中国史学的基本范畴。在同样强调唯物史观指导作用的同时,更强调了史观、史料、文献学、目录学、史书编纂、历史文学等颇有中国色彩的基本史学理论范畴,其实质同样是探索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从过去过分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转向重视考察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但是,对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方法并未见根本改变,在克服教条主义的同时。仍不免存留着“左”倾思潮的痕迹。冰河已经解冻,史流继续向前涌动,史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等文献作出了新的诠释和解读,主要提法有:1、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历史一元论。2、人类历史始终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前进的;这种矛盾运动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则表现为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3、尽管人类历史的内容和现象纷繁复杂,但它却是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曲折地向前发展的;4、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理论,不仅指明了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途径,而且提供了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1984年9月,全国唯物史观形成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安徽黄山市举行,该会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理论探讨的热烈情景。吕振羽、谢本书、蒋大椿、叶汝贤、郑观卫、苏凤捷等人的观点值得关注。
在第二阶段的认识过程中,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问题、人民群众、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等,这些学术问题的热烈争鸣,反映出学术界对唯物史观丰富内涵的深入挖掘,新见频出。蒋大椿在《唯物史观与史学》一书中对唯物史观及其与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将唯物史观的核心归纳为:1、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2、人类社会及其构成部分均以总体的体系的方式存在;3、在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中,一切社会历史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4、人类社会是运动的、发展的,显现为历史过程。构成历史过程的各种社会现象,也是运动的、发展的;5、社会历史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进化的和革命的两种形式;6、社会历史事物发展的根源,在于它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7、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环境创造了人,人又创造了环境;8、社会历史研究不是一个消极的反映过程,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此外,宁可、林甘泉、漆侠等学者均对唯物史观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了再认识。强调社会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已成学术界的共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被放在一个较为恰当的位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不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而是作为一个体系,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系统地、全面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运动变化过程,成为此期理论创新的亮点。
第三阶段唯物史观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反思和展望。步入新世纪以来,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理性化。已不再局限于经典文献的个别章句及其诠释,也不再引经据典地打经典仗,而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问题。更体现出了一种发展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如李文海考察了唯物史观给史学带来的巨大转变:1、把历史从过去主要描述政治兴衰、王朝更替的所谓“相斫书”,转变成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过程;2、把历史发展从过去看作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过程,转变成看作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3、把历史从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家谱”,转变成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体,同时也充分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和各种社会合力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4、对于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改变了过去从观念到观念、就精神论精神的研究方法,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把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紧紧地联系起来。瞿林东认为人们坚持唯物史观是因为它的真理性优势,并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整体历史;(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历史是个有序的自然发展过程,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才成为可能;(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
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于沛在《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指出:“加强唯物史观的研究,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对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的历史观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认识路线,直接关系到历史学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实现的程度。重视历史资源的开发,认真研究和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是时代的呼唤。这是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民族的自信心和文化的独立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前提是这种学习和研究都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否则,一切就都会走向反面。”朱佳木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中则指出了唯物史观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蒋大椿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提出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严重理论缺陷,必须被超越,这一观点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2001年11月,“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2002年4月,“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07年10月,“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学术对话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开掘。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多重含义。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研究实际相结合,并进行创造性地发挥,使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这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态度。
二、历史理论的探讨深化了对中国历史特点的认识
随着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认识的深入,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区别开来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进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建国后到‘’结束这段时间内,史学界(含史学理论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严重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等于史学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核心就是阶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把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其在地位上低格化、理解上简单化、运用上教条化。”这种认识上的自觉直接促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理论方面探讨的主要问题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问题大部分承续了1949-1966年间史学界的老问题,但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进行了新的阐发,推动了对中国历史进程中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自1983年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先后出版以来,至1999年陈启能等所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出版,其间出版的同类著作或教材近20种。这些著作几乎涉及到史学领域的所有理论问题,史学理论大有形成一门学科的趋势。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一股“史学概论”热潮。质言之,此期有关史学理论的探讨大都集中在对客观历史发展中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问题,而对历史认识、历史研究过程中涌现的以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理论,则是下一阶段的主要课题。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又进一步促进了历史理论的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问题不断涌现,“史学概论”概论什么,成为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这说明历史学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系统构建,而史学理论与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是长期交错的问题,实际上成为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系统构建历史学科自身理论体系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新时期以来,历史理论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提出许多新论点、新命题,拓宽了研究领域,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把握更加深化。在古代史方面,白钢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龚书铎任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8卷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多卷本《中国社会生活史》、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晁福林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等,涉及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等诸多新领域,视野开阔、结构新颖、方法创新构成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在近代史方面,如罗尔纲、黎澍、陈旭麓、金冲及、胡绳武等人对太平天国史、维新派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进步意义、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和革命党人中不同政治倾向人物的分析,胡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力量”及其思想文化上代表人物作用的分析,刘大年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分析等,都是大手笔之作,给人厚重的历史感,启入以深沉的历史智慧。革命与改良、洋务运动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都因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困惑而备受关注。在中国通史研究领域,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誉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压轴之作,其《导论卷》所探讨的历史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水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㈣则被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三、以历史认识论研究为重点构建史学理论体系
新时期以来,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推动史学理论的整体建设,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特色。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对史学理论的体系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意见:1、把史学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历史哲学、史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历史学的技术学科或辅助学科所涉及到的各种理论。2、把历史认识分为三个层次: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3、认为广义的史学可包括历史哲学、具体历史过程的理论概括、历史辩证发展问题、史学流派研究、史学认识论、史学评论理论和史学编纂的理论等七个问题。4、认为史学理论应包括客体论、主体论、主客体关系论、方法论四部分。这些观点和分歧促使史学界对“史学理论”问题作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历史、历史科学和历史学的概念的认识、历史学科的属性、结构、研究对象、历史认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的功用、史家修养等等。这些都为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取得较大突破的领域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历史认识论问题成为研讨热点。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历史认识主体、客体、中介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历史认识的认知结构,历史思维的特点,历史认识的方法与检验等问题。张帆、刘泽华、张国刚、姚志安等人较早对历史认识论进行研究。史学界对这场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和讨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看作是“最能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此期,陈启能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阐发具有典型性,该书作为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包括历史规律问题、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理论、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观、从直觉到科学、辩证的历史思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展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该书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思考。关于历史认识问题。张耕华将历史认识论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部分。张剑平指出:“新时期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少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历史认识的特点和过程以及历史真理的检验等认识论问题的理论探讨;二是对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流派作了较为深入的评述,如对兰克学派年鉴学派,西方人文和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等的研究;三是对如何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认识论的思考。有的学者在对西方历史认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任务;也有学者根据西方历史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较为深入地论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思维的特征,提出较为深人地阐发了科学的辩证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的研究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理论色彩,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澄清了一些错误的史学观念,活跃了史学家的历史思维,规范了历史研究的过程,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但是,众多史学家亦坦然吐露心声,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四、史学方法的更新和多样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
史学方法的研究历来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新时期以来,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运用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日渐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运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三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特别是金观涛、刘青峰的代表作《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曾经掀起了史学方法热的滚滚浪潮,也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吸引了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学家的加盟。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和系统化一方面得益于史学内部的积累,这包括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阐扬;另一方面也受惠于中外史学交流的深入发展。
关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法的总结和发掘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上百篇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由于是连载文章的结集,故其文短小精悍、文笔隽永,不少中青年学者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浓厚兴趣。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是否可以认为,没有评论或批评,也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换言之,不能脱离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史学批评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范畴提了出来。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总结和继承,充分体现出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特色,主要有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等问题的研究。对于历史主义的总结,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值得关注。乔治忠指出:“在历史研究与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应当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令思维方式具备深刻、准确的逻辑性,唯物辩证法还具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主张事物发展的前进性、阶段性,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法则等等思想原则,从而使历史主义具备完整的历史观、方法论和鲜明的立场。”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比较”作为一种古老的方法被史学家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史学界关于比较史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著作约有20部。庞卓恒的《比较史学》、范达人的《当代比较史学》、范达人、易孟醇的《比较史学》、刘家和的《史学、经学与思想》等著作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杜维运在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中这样看待比较的研究方法:“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只有在历史全球化以后,整个世界人类进入历史之中,才有出现的可能。所以比较历史与比较史学在走向全球化的路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更有学者相信比较方法将引导中西史学走向更高的层次。这种比较研究的发展,无疑将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境界。有的学者还把比较方法看作是学科发展的研究方法之一。史学对系统方法、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的运用也是值得注意的。程洪、霍俊江、赵吉惠、赵轶峰提出了重视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观点。
五、对历史学功能的新探索
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古老的课题。新时期以来。史学价值问题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以关注现实著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期,由于“影射史学”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日趋狭隘。“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观点,这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在“拨乱反正”思潮和“史学危机”思潮中重点反思的问题之一。80年代初期史学界重新兴起的“古”、“今”关系、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讨论把史学价值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刘大年、黎澍、苏双碧、孙思白、田昌五等学者对这个问题用力颇多。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随着自由化思潮和思潮的泛滥。学术界对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史学无用论”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也促使学者对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的价值作更深入的思考。白寿彝就历史教育功能阐发尤多。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价值论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有的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些史学价值观点加以总结,王斯德指出:“历史是一部社会教科书,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教化和思想滋养功能,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改造世界、超越自我的强大武器,其核心是启迪心智、智慧人生,使人变得清醒、理智和成熟。以史为鉴,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知社会兴替之道……学习历史可以使我们掌握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增强历史洞察力,以历史的纵深感和深远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领悟历史的真谛,
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发展大趋势,确立科学的理想和信念。”吴怀祺则指出了在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以正确的历史知识、历史思维方式总结历史,认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以安邦兴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史学更广泛更深刻的价值体现于民众之中。因为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精神与民众素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史与文化能否高扬,直接关系民众自身素质的提高、民族自身凝聚力的增强。”史学价值是历史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将随着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而继续发展下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的重要理论成就之一,史学价值论的探讨仍将继续得到史学界的关注。
六、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于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作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任意去裁减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材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导师的某些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常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
其二,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考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具有全球视野。在这方面,有学者集数十年的心血,致力于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和多重背景下观察与思考,还把它们置于同外部世界的比较与联系中进行探索。”《古代中国与世界》是刘家和这方面的代表作。2005年,“《经济一社会史评论》首发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侯建新、马克、刘新成、齐世荣、于沛、李文海、龚书铎等学者畅谈了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问题。在他们看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同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历史的角度,去寻找对某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的答案,将会更加有助于接近真理。”
其三,突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对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白寿彝进行过长期思考,他说:“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瞿林东谈到如何建设2l世纪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历史学时指出:“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还要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可以用来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也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封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有一种信念,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厚重。”
其四,强调了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和发展规律,完善了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建设的进程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实为“”破坏以后的恢复和充实阶段,90年代以后,现代史学史研究形成全面铺开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涉及到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对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开创性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具体在如下领域有所进展: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全面深入研究史学的社会作用、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面貌、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关于易学与中国史学之关系的研究、史学史对历史教育的意义、关于史学批评的研究、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研究、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从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史学等。蒋大椿则把1984年以来连续召开的十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及其取得的成果作为史学理论学科取得整体建设进展的重要标志。
其五,强调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和史学的独立品格。论及史家的主体意识,瞿林东指出:“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来看,史学家们的世界眼光,虽有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但总的说来都是在‘以我为主’的历史视野下发生和发展的。而20世纪的中国史学,尽管面向世界的规模扩大了。但‘以我为主’的视野却发生了变化,太多以他人为主,即以我们自己的史学去适应他人史学的模式。”正是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学者提出研究中注重史家的主体意识和史学独立品格。陈启能指出:“史学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而不受到损害。所谓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就是对于历史真实的执著的追求。一旦失去这种品格,史学就不成其为科学,没有真理和尊严可言。”历史学的根本成就是“对自己学科特性的回归,并努力探索和按照自身的规律和特性进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章开沅则主张史学应该走自己的路。侯云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新时期史学思潮》一文中提出史学要走向自我。田昌五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于沛则提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设想。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4
--------------------------
①DonM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of the eaa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story,p.306.
②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学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问,无论《禹贡》还是《?W德赛》,都反映了人类先民的地理意识。地理学又是复杂的:从横向上看,这一学科存在着文化区域的差异①;从纵向上看,该学科从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众多的分支学科。其中的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人文地理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③,依笔者的专业和目前的学识很难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拟选取某一方面来具体认识它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在选择过程中,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大师阿·德芒戎的思想上。这么做的考虑,是出于德芒戎对20世纪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影响。这从法国年鉴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创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可窥见一般。布罗代尔在开列需要感激的名单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德芒戎,我们从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周围山区的描写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笔下的“利穆赞地区的山地”④的影子。鉴于地理学对于环境史学的贡献以及环境史学同年鉴学派
----------------------
① 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赫特纳(1859—1941)在论述西方地理学史时指出:“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德]阿尔夫雷德·赫特纳著:《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国还被翻译为“人生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尽管译法各异,但都涉及“人”。而“人文地理学”法语词为Gé0graphie humaine,德语词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5--248页。
的学术传承关系①,我们认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开列的地理学家名单中加上阿尔贝.德芒戎,应该是恰当的。②
一、定义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当前西方学界基本区分的地理学两大类别之一,另一类是自然地理学。《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版则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学包括了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和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医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因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解释人类的分布及其特点,这属于人口地理学的范畴。但是不对以下问题予以重视,就不能理解人类的分布:人类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谋生,属经济地理学范畴;人类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劳动工具等,属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范畴;人们在城市和大都会的聚居,属城市地理学范畴;人们的政治机构,属政治地理学范畴;人们的健康和威胁他们的疾病,属医药地理学范畴;当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进而成,属历史地理学范畴。”③
------------------------
① 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Char Miller & Hal Rothman,Out of the Woods:Essays in Environmental Hitory,Pitts— brgh:University 0f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②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德芒戎。
③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对人文地理学的如此繁杂而又密切联系的分支领域,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呢?对于人文地理学问题,阿.德芒戎于20世纪初所做的论述,被视为是“指明了正确的道路”①。从德芒戎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虽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类习俗的差异,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对那些被我们现在归人人文地理学名下的事实,即地球表面上人类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未经整理、未加解释的,也就是没有科学性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科学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殖民活动所导致的我们对地球知识的增长:主要由科学家或具有科学好奇心的探险家进行的航行。”②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定义,德芒戎强调不能泛泛地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因为“它包括不了整个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这些关系中有许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学者所能研究的,它们属于别的研究部门。”③于是,他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④。他之所以用“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概念取代“人类”和“自然环境”概念,是因为他认为,首先,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我们不再把人类作为个体来考虑。通过对个体的研究,人类学和医学可以取得科学的成果;而人文地理学就不能。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是作为集体和集团的人: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作用。”第二,“地理环境这个词组比自然环境的含义更广;它不仅包括可以表现出来的自然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有助
-------------------------
① 见“阿尔贝·德芒戎”,载[法]阿·德芒戎著:《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0页。
②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4页。
③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5页。
④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7页。
于形成地理环境,即整个环境的人类自身的影响。”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定义以及他所运用的定义逻辑对于我们如何界定环境史学富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学自诞生至今,对于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界尚存歧义②。近30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环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体地研究和诠释环境史,因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是见仁见智③。在美国,虽经多次讨论,学者们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史,但是对于“人类”、“环境”等具体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和丰富的过程,对此,大家的理解还是不太一致的。
-------------------------
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6--7页。
② 譬如沃斯特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包茂宏在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时认为又诞生了众多的次分支学科,见包茂宏:《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③ 迈克尔·威廉斯在“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纳什(Roderick Nash)、比尔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参见Michael Williams,“The relations 0fenviron— 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此外,包茂宏在“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还进一步介绍了贝利、克罗农和麦茜特等人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参见包茂宏:《环境史: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而麦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罗农、克罗斯比以及她本人关于环境史的解释,见http://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纪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强调环境史学日益摆脱了初期的道德诉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标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在时间长河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在沃斯特心目中,这个自然仅指非人类世界。这一世界在原初意义上并不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会环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舞台)和人工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无处不在,成了“第二自然”,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表现)①。应该说,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环境——非人类世界。沃斯特的有关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关于环境史的理论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乔尔·塔尔等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城市或人工环境,并提出人工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断②。当然,沃斯特本人的这方面的思想也在发展变化③。
笔者认为。上述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影响着非人类世界的人类,以及人类到底怎样并在哪里影响着自然环境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人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
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p.290--291;pp.292--293.
② Christine M.Rosen &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of Urban Perspec— tive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ournal of Urban History,(may 1994),p.307.
③ 见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页。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人类概念的认识,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点上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考察人类历史开始点的总体假说。马克思提出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的假说后,具体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现实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②。环境史学中的“人类”,也只能是结合着现实的社会环境,并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其内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人的群体或集团,可以简称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会人”;其外延是由人类的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类实践活动构成的环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种设施组成的人工环境,以及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组成的社会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中的人类子系统。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土壤一岩石圈和生物圈所构成的自然子系统,即环境史学中所运用的“自然”概念。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② 参见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至此,我们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义逻辑来对环境史学进行界定。环境史学包括不了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各自内部或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其中有许多方面肯定不是环境史学所能研究的。譬如,自然子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属于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范畴。环境史学则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
这样来辨析,就可以明了环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问题了。作为环境史学中“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的另一方——“人类社会”囊括了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类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着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在创造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环境逐渐地改变了模样①。
————————
① 原生的自然环境又被称为原生环境或第一环境;被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原生环境,如被绿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气和水体、被破坏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环境、次生环境和“人工-自然环境”等称谓。
二、研究对象问题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兴趣于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各自对这一“关系”的具体把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环境史学与人文地理学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如此。
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为例。德芒戎从他的人文地理学定义出发,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一抽象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由此构想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了其范围和界限。他认为,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四大组,即:1)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2)人类社会对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断演进,即文明类型的演化;3)随着自然条件及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而变化的人类分布;4)人类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德芒戎强调,这些就是人文地理学专有的内容;人文地理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这一广阔的领域。不过,从他之后的学科发展来看,不仅人文地理学本身研究的问题随时展在进一步拓宽,而且他界定的内容也并非只为人文地理学所专有。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学同样致力于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与研究。
在抽象意义上,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②。而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家对于相互关联的“人类”与“环境”涵义的认识是逐渐明晰和不断丰富的。从目前欧美环境史学家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种种规定来看,我们认为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的三层次分析模式比较典型:
第一,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
---------------------------
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Profile 0f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因为它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这儿我们关注的是工具和劳动、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设计的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产品的各种方式。一个被组织起来在大海捕鱼的村社与一个在高山牧场养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别角色和季节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决策的权力,无论是环境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一个社会内几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对权力结构的探寻是该分析层次的组成部分。
第三,独特的人类经历的象征一一纯粹的精神或思想层面,其中,感知、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结构成为个人或组织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人们不停地描绘他们周围的世界,界定资源是什么,判断哪些行为会导致环境的退化,应该被禁止,并且对他们生活的目的做出选择。①
这三个层面即三组问题,是沃斯特构建的环境史研究纲要,他自己认为“这个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笔者大体上赞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构,因为其他学者提出的分类大都是这一基本框架内的局部调整。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比较和认识环境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
①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mnental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s 0f Eanh:Perspectives on Modem Environmental Hiaory,p.293.
②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
就沃斯特的环境史纲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对象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域。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可归结为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生活、生产、居住和迁徙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样为环境史学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个层面与之联系最为紧密,而这一层面正是目前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所在。已出版的关于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著述大都属于这一层次①。由此我们可以领会二者间的关联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然而,环境史学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又有着显见的不同。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
① 譬如:唐纳德·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of Sheep: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一一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止于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利用方式与地域的变化等。这些问题所折射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认识,即局限于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中对自然环境的作用。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种“可能论”(possibilism)的论点,这种论点是他的老师、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维达尔·白兰士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可能论”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可能论”虽然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人地关系观,但它与决定论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两者不相容;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可能论与决定论的这一共同之点被称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①。这类论点的提出和持续,与直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当时发展中的科学方法还是以探索简单的、单线的因果关系为标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类推,而尚未认识到形成当今科学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②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地理学家在探求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原因时,做出的大都是与线性科学相一致的简单的、直向的解释——要么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要么侧重人对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③。
---------------------------
①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② 唐纳德·L·哈迪斯蒂著:《生态人类学》,第2页。
③ 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继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后,又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等。参见王恩涌等编著:《人文地理学》,第40--42页。
环境史学恰恰要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止步的地方起步。它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利用开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探讨人类如何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以此来再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史研究使得历史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历史观层面,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一方面,环境史学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史学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要素,而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环境史非常明确地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思考。这正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论述人与疾病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①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证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不断地发生的是相互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分野是不明确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这显然是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双向认识,因而有别于上述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当然,环境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双向认识也是随其研究的发展而逐步明晰的。欧美环境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狭隘的污染或灾难史到全面宽广的环境史的转变,其研究日趋成熟,标志就是认识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②。这反映了环境史家从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转变到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史的全面审视。
--------------------------
①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版,第10页。
② 参见K.j.w.Oosthoek,“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forth.stir. aC.uk/~kJwol/essays.html.
以英国环境史为例,在1970--90年代初,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或城市化与工业污染等问题成为研究的焦点,彼得·布林布尔库姆、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等人先后发表了诸多专题性成果①。及至90年代中后期,有关的研究从污染史拓展到环境史,其中戴尔·波特的《泰晤士河河堤: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环境、技术与社会》是这方面的佳作。波特认为:“泰晤士河与伦敦的关系并非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简单对照。一千多年来这条河与这座大都市共同将自然的作用与人类创造的事业调和起来。人因为对食物和原料的需求而以他们的建筑物和周围的乡村发展了城市。人们通过堤岸、码头以及他们对清洁水的需求和废弃物的排放而塑造了河流……泰晤士河河堤作为一项公共工程,展示了技术在以文化价值观、社会组织和制度为一方,以自然环境为另一方之间的调节作用……当然,技术作为一种分界面,其本身受环境条件和使用技术的社会的态度与习惯的制约。它充满了变数。泰晤士河河堤既
-------------------------
① 布林布尔库姆的有关著述是空气污染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其中,《1850—1900年约克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York,1850—1900)、《伦敦空气污染》(Air Pollution in London)和《19世纪苏格兰的黑雨》(Nineteenth Cen— tury Black Scottish Showers)等文章,是将现代气候研究与历史档案研究融合起来的佳作;而《大烟雾:中世纪以来伦敦空气污染史》(Peter brimbleeombe, The Big Smoke:A History 0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lon— 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87)一书影响了许多后继的环境史家。比尔·拉金和劳伦斯·布里兹的著作则是关于英国河流污染的代表性成果:Bill Luckin,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Ifistory 0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 ry,IOP Publishing Limited,1986;Lawrence Breez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wer Pollution,1865--1876,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1993.参见Matt Osbom,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http://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建构’,并且它还要因应意外的气候、高潮、流沙和这一地区可资利用的原料的质量而作变更。”①波特的研究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既展示了人类如何塑造了自然环境,又展示了自然要素在影响和改变人类文明中的作用。这是一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双向互动观,它凸显了环境史学的目标,即“认识人类如何受自然影响,又如何影响自然,以及影响的结果。”②
环境史学的这种双向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学科发展的态势。20世纪中后期,不仅地理学本身在努力克服过去只重视研究“地”对“人”或“人”对“地”单向作用和影响的局限性,开始全面地研究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且诞生了数门以“人类一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新兴交叉学科,如环境科学、人类生态学和地球系统科学等,它们一致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整体性并对其进行综合研究③。环境史学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等学科汲取了大量的养料,其中生态学尤为重要。生态学研究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集中体现在环境对生物的生态作用、生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以及生物对环境的改造等方面④。环境史学受到了生态学的巨:大影响,较某些前辈学者而言,“环境
---------------------------
①Dale Porter,The Thames Embankment:Environment,Technology,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Akron,Ohio:University 0f Akron Press 1998,p.4; pp.8---9.
②T.C.Smout(cd.),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Natural change and Human Impact,Aberdeen: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3,p.xiii
③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一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性》,第6--32页。
④ 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E·海克尔首先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详见周鸿编著:《人类生态学》,第1--2页。
史学家更看重自然的作用,并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视为一条‘双行线’(two-way street)”。①这一分析非常适合于就德芒戎的思想与环境史学关于人地关系的认识所作的对比。
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同相联系,环境史学又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目的。
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中研究地表人文现象空间分布与变化规律的学科,其目的是要“阐明各国、各地区人文现象的分布规律,着重说明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人文活动,并探讨其形成的原因,预测其发展的趋势。例如,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有的国家工业高度发达,有的国家工业依然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②这显然是对地表各种人文现象的空间分布与空间结构作客观的描述与探讨。德芒戎对法国农村聚落的类型、法国北部与美洲的联系、北海的渔业和渔港、尼日尔河流域的土著殖民和整治工程等问题的研究即是如此。与之相比较,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中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史的新领域,除了要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因果律外,更主要的,是为了比较和反思人类对自然的历史认识和态度,尤其要检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对待自然的种种方式。环境史学要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来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人群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比较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文明中人们关于自然的思想、概念和价值观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以此
------------------------
① Mark Cioc,Bjsrn-Ola Linnér,and Matt Osborn,“Environmental Histo— x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Environmental History,V01.5,No.3,July,2000,p.397.
② 辛润田主编:《现代人文地理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来认识人们对待他们周围环境的不同态度及由此导致的不同结果。由于历史上自然曾以各种各样的灾变对人类有悖于自然规律的开发活动予以了报复和惩罚,因而透过各种各样的灾害而揭示人类对自然的毁灭性开发和戕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探寻人类合理地利用自然以使人类文明健康发展的途径,必然是环境史学的主要任务。由此,环境史学持有鲜明的批判立场。它反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观,提倡网开三面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试图通过对人类与自然关系史的反思和评析,来寻求人类与自然互惠共生之路。沃斯特的环境史纲的第三个层面突出地反映了这一诉求,《尘暴》一书则是他从文化批判的角度研究环境问题的典范。沃斯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发生的尘暴,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文化将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谦恭荡涤殆尽,并以人类对自然的极端狂妄与自负取而代之。它与北美大陆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敬畏草原、感激自然并自我约束的环境伦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①,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沃斯特提醒第三世界国家不要迷信和盲从美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以免重蹈美国的覆辙②。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背景之下,他的这一“盛世危言”是发人深省的。
-------------------------
① 参见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第94--97页。
② 沃斯特著:《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第316--334页。
与沃斯特的作品一样,欧美环境史学界的其他著作大都饱含着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的机械自然观、科学与理性崇拜、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等内容的分析与思考。如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该书从性别的视角描述了人们关于自然概念的变化,并对这种变化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麦茜特将以往科学史中许多被忽视的问题突出出来,尤其是通过对科学革命及其背景的考察,发现在产生近代科学革命的16、17世纪之际,“一个有生命的、女性的大地作为其中心的有机宇宙形象,让位于一个机械的世界观,这里,自然被重新建构成一个死寂和被动的、被人类支配和控制的世界。”①由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了人类怎样将自然概念化,以及有机的自然观如何转变为机械的、死寂的自然观的历史过程,从而加深了对人类“合理地”支配自然并破坏生态环境的历史根源的认识。像这样的对现代文明及其对自然之态度的评判,正是环境史学有别于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之处。
因此,从研究对象来看,环境史学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基础在于二者都在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区别的原因则在于它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从这种联系与区别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界定环境史研究的对象与侧重点,以把握不同时代学科发展变化的脉络。今天,环境史学已表现出更全面地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变化,并合理地解释有关问题的能力,但环境史不能自诩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并提供了最好的答案,也不应被视为“至今所有的编年史的逻辑发展的一个顶峰”。②因为历史学研究的问题像任何其他学科一样,也是变化的、不断发展的,并需要多样化的解释。人类行为如此复杂,以至不能靠简单的因果分析来解释。同样,对人类与环境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也不应采取简单的、一对一联系的取向。
-----------------------------
① 卡洛琳·麦茜特著:《自然之死一一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前言”第3页。
② [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一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2页。
三、方法原则问题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德芒戎是这样规定的:
第一原则 不要认为人文地理学是一种粗暴的决定论,一种来自自然因素的命定论。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就是搅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第二原则 人文地理学家应当依靠地域的基础进行研究。凡是人类生活的地方,不论何处,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总是包含着他们与地域基础之间的一种必然联系。使人文地理学不同于社会学的,正是这种对地域联系的考虑……第三原则 为了全面地说明问题,人文地理学不能局限于只考虑事物的现状。它必须设想现象的发展,追溯过去,也就是求助于历史……
德芒戎规定的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原则对环境史研究同样具有启发。尽管如前所述,他的人文地理学思想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上是单向的,但他关于“人文地理学中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的提法依然值得我们注意,而他将人类看成是影响自然秩序的一个原因,由此而否定环境决定论,这种看法本身在今天尤其值得环境史学家所重视。由于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有千万年之久,其中的因与果事实上乃是相互纠缠和渗透的。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的地位。沃斯特纲要的第一个层面“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即包括对人类有机体的理解。
人类是生态圈中颇为独特的物种,一身兼具三重身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成分,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和创造者①。因此,人类既具有自然禀赋,又具有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类的捕食、生殖、与其他生物争夺生存资源以及对自然环境的依赖等基本生物功能,属于自然秉性。就此而言,由于人在体力和许多器官的功能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人甚至比许多其他生物更不能适应环境。但人有思想意识,有发明创造能力,并组成了一种社会和不断完善这个社会,这是人的社会与文化属性。人的这种属性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类为了得到足够的资源(食物、衣物、居所、能源和其他物质材料等)来维持生存,可以发明各种手段和方式从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去获取,这使得人类成为了惟一能够威胁以至于摧毁自己生存所依赖的环境的生物,而且是惟一的进入了陆地所有生态系统,并通过技术的使用来支配它们的生物②,因此,人类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全面的干预和极其深刻的影响。
------------------------------
① 参见陈静生、蔡运龙、王学军著:《人类-环境系统及其可持续发展》,第49--54页。
② [英]克莱夫·庞廷著:《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第20页。
即使如此,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所作所为仍不得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这是因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节律和功能,人类的作为必须符合自然的规律,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无情的惩罚。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要归结到一点,即地球能否承担和接受人类的发展速度,或人地关系是否统一这个问题。一方面,地球上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另一方面,人类将从自然索取的物质消耗以后,又会将废弃物归还自然。人类与自然之关系的本质即在于相互之间进行的这种物质、能量乃至信息的交换。由于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不同时期人类的技术水平、组织规模和文化程度是很不相同的,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总的来说经历了人类从诞生之初的完全依赖自然并敬畏自然,到利用、改造、破坏与藐视自然,再到今天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强调保护与亲近自然等阶段。这一历史进程表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统一,并在对立统一中前进和发展的。今天,人类社会的问题已成为如何遏制人自身种种的超越了各类生态系统能力的需求,以缓解乃至消除由此而造成的种种压力的问题。由此我们必须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中因人而起的不和谐及其消极后果的认识与研究。
由于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之上,并往往会超越领土、领空的界限,如跨境的水体污染、沙尘暴、酸雨等,这样,德芒戎提出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应当依靠的地域基础,也是环境史研究应当依靠的基础。
德芒戎特别强调人文地理学不要忘掉人和土地的关系,不能离开人所居住的土地去研究人。他说到:“为了清楚地看到一般现象的全貌,最好从特殊的、局部的现象开始去观察这个区域内包含的特殊植物、居民……,去明确某种由一片土地和一群人类的结合而产生的有活力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回到我们的物质存在的直接基础上。人们常常要在对组成一个区域面貌的各个特征进行分析以后,才能更好地理解把人类和环境结合在一起的那些关系。”①德芒戎的上述思想和认识方法也可以为环境史学所遵循。环境史研究同样要回到“对世界认识的起点”上来,这即是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原貌的认识。因为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化,今天我们眼前的山川大地和气候条件远非其原貌。只有深入地了解自然环境的原貌,我们才能找到衡量其变化的基准或坐标,弄清其变化的幅度。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记载的出发点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②当然,自然基础或自然环境的初始状态是相对的,其时间断限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是有别的,这由文明出现的早晚而决定。即使在同一国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不同地区的初始状态,有的早就被破坏了,有的在不久以前尚可以见到。③这样,在具体研究中必然要求根据具体情况而选取不同的地域单位。明确地说,环境史学除了继续运用传统的国别研究单位外,还要加强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这是一种方法原则。
----------------------------
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1页。
② 在马克思、恩格斯笔下,自然基础包括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见:《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页。
③ 此处得益于中国文物研究所的景爱先生的指教,谨致谢意。
至于如何确定所研究区域的范围,则要视研究的问题而定。区域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以小见大,化整为零,而是为了获得对一个区域的人、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了解和认识。这就要求对某一区域的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将涉及到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尤其要注意联系社会文化环境来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们往往是通过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来体现相互作用的。这样,突破学科界限,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相关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融人具体的研究过程,是环境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由此我们看到,环境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环境史学家尤其需要运用生态学、生物学、林学和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知识来理解自然界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但反过来,作为地理学家的德芒戎则强调入文地理学必须“求助于历史”。他说道:“人类在时间中发展,为了理解这种发展,历史的证明和自然规律的认识对我们同样是必要的。”①这一思想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历史研究在一切学科研究中的基础地位。这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如何处理历史学与其他需要借鉴的学科的关系。环境史学的跨学科性质并不意味着历史学的学科特征的泯灭,因为其本质上仍然是通过对有关问题的史料的发掘、整理和解释来再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史,并理解其现;伏。环境史学家也不必成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要做的只是跨越学科边界,熟知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术语、理论和方法,以更好地
------------------------------
① [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3页。
理解历史上的环境问题。①不仅如此,由于环境变迁具有长时段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根源,这一变迁本身及其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影响并不是计算机模型或实验室的实验可以完全地模拟或实验出来的,因而就愈发需要深入有关的历史变迁之中去梳理、归纳和认识,从而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有意义的启示。此外,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具有不同于人文地理学乃至其他研究自然与人类关系之学科的目的,因而不要充当自然科学或别的什么学科的婢女。环境史研究者不要东施效颦,而要清楚自己与自然科学家的不同。这样,环境史学应是以历史学为基础和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环境史学家要做的是在固守历史学阵地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拓宽知识结构,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并提高处理各类资料的能力。
今天,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远离了自然,却又越来越剧烈地干预了自然。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至少是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自然,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人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时,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成为社会分化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②因此,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现时代,我们认识和研究自然环境在什么程度上并以什么方式参与了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人类社会又在什么程度上并怎样干预和影响了自然环境,以探索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途径,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而贡献史学的智慧,是非常必要的。国际史学界已表现出对环境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从中国环境史学的发展来说,笔者认为,我们应摈弃中国世界史学界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宏观中文话语处理的一贯做法,弘扬并改造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灾害史研究的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开展精细深入的理论建设和问题研究。我们既要研究他国以及世界性的问题,更需要研究中国自身的问题,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分析模式和理论框架,实现学术创新,以对国际环境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5
一、加深认识,有效解读《高中课标》中数学史的定位
《高中课标》中的数学史具有双重的角色和地位,要在实践中有效解读和落实,需要加深对数学史内涵的认识.这首先必须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关注《高中课标》中的数学史“应为学生成长为完整的人做出贡献”.为此,理解《高中课标》中的数学史内涵时应该强调数学史如何揭示“数学是且一直是以人为本(people-centered)的”,将数学与人的需求联系起来,为数学提供人文之根.进而“数学也应该以人为本的教”,“将数学史作为数学学习的重要成分”.因此,无论是作为数学本质载体的数学发展史,还是作为数学文化的数学文化史都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为数学而历史,而是为教育而历史,注重通过数学史将数学与学生的需求和发展联系起来,促进学生成长为完整的人.
其次,《高中课标》中作为数学文化载体的数学文化史将数学看成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类文化反观数学,从数学与人类文化整体的关系入手用文化的兴衰系统地解释数学的发展演变.这既要求明确“数学文化表现为在数学的起源、发展、完善和应用的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于人类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方面”,也要求明确“数学知识的内容和结构均由其所属的文化规定,数学知识的研究必须考虑其所嵌入的超越数学的文化结构”.数学文化史强调通过各层次不同文化中数学建构的比较,发现差异和共性.
最后,还需明确数学文化史和数学发展史两者是从不同的视角对同一历史过程审视的结果.前者强调文化是数学发展史建构的“内在”动力,以系统观点分析数学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发展和作用;后者侧重于把数学作为实体,从数学基础、数学与生产实际及自然科学的关系认识数学的本质.
二、厘清预期目标、运用方式及其相互关系
数学教育中运用数学史的理论和实践中常存在脱节现象.首先是《高中课标》中数学史的定位和运用的预期目标存在不一致,没有深入考虑定位转化为具体的预期目标,理论和实践中确立运用数学史的预期目标时对定位认识不深、关注不够.其次,预设目标和运用方式之间关系不清,常以应然来解释实然,或反之.因此,在有效解读《高中课标》中数学史的定位后,应将此定位转化为具体的预期目标,厘清预期目标、运用方式及其相互关系.作为工具的数学发展史可以从激发动机与情感、提供认知帮助、启示数学发展等方面确立具体目标;作为目标的数学文化史关注整个数学学科的发生发展,促进学生是其次要功效,可从数学发生发展的动力、机制、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及其机制、时空地域等确立具体目标.关于运用方式,本文根据数学史料的显著程度及其与所属内容的紧密程度分为附加、直接使用和间接使用三种.具体可参见前面论述.厘清预期目标和运用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助于设计者选择适合目标的数学史运用方式;有助于分析教学资源,了解设计者最倾向于运用数学史实现的目标;最重要的是有助于了解在什么程度上设计者选择运用方式时忽视了某些目标”.
三、重视设计和开发相关资源
《高中课标》中定位的数学史是数学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作为数学文化载体的数学文化史,要求从社会文化视角宏观地解释数学主体、数学活动和数学理论等要素,揭示数学的文化价值及其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向学生展示同一文化内或不同文化间数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方式,超越单纯胜利者认知视角从社会文化审视特定历史时刻竞争性数学研究间的对抗,并基于此重构学生易于接受的呈现方式和教学序列.一线教师的能力、精力和资源等不足以单独完成此项工作.因此,调动数学、数学教育、数学史等相关方面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形成特定工作团队,深入研究和开发相关资源是有效落实《高中课标》相关要求的关键.张奠宙先生开发的一些案例或许是前进的灯塔,具体内容可参见数学教学杂志2002年第四期《中学教材中的“数学文化”内容举例》一文.
所以x1+x2=4k(4k-1)2k2+1,
x1x2=2(1-4k)2-82k2+1.
代入(1)化简得x=4k+3k+2.
(3)
与y=k(x-4)+1联立,消去k得:(2x+y-4)(x-4)=0.
在(2)中,由Δ=-64k2+64k+24>0,解得2-104
k
故知点Q的轨迹方程为:
史学和文学的关系范文6
关键词:年鉴学派/世界体系理论学派/历史时段理论/世界体系理论/采鉴关系
二十世纪是反思的世纪,不仅反映在哲学、文学、艺术领域,而且也反映在历史学。有人曾把十九世纪视为史学世纪,主要鉴于兰克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兰克学派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不可磨灭。但是正如任何理论都有它的时效性一样,它不可能在随时随地都能起到“放之四海皆准”的功能,都有它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所谓“一劳永逸”的真理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兰克学派发展到了顶峰,顶点的出现意味着衰弱的开始,极度繁荣的背后隐藏着结构性危机。正是这一危机促成了史学百家齐放,年鉴学派、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一大批新学派的出现,使历史学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当然,年鉴学派是最有富影响力的一个学派,而且年鉴学派对其他学派的出现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如第一代年鉴学派大师布洛赫对封建制度的差异性和共同性作了宽广的考察,开创了真正的比较历史学,被称为“比较史学之父”。第一代、第二代年鉴学派史学家主要成果在社会史、经济史与文化史领域,但是由于新理论、新方法的采用,由此产生了许多新分支学科的出现,如人口史、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可以说是年鉴学派凯歌进行的时期。1946年《经济和社会史年鉴》更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目的在于进一步拓展历史研究范围,更好地反映年鉴学派的总体史风格。年鉴学派的大发展与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年)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1946年布罗代尔进入年鉴学派的核心领导层,成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的编辑之一,1956年在费弗尔去世后成为该杂志的主编及高等实验研究院第六部主任。他对年鉴学派的最大贡献是于1949 年和1967年出版的《腓力二世和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和《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书。它成了年鉴学派总体史的范本和经典之作,完成了年鉴学派的理论建构,提出了历史时段理论。虽然历史时段理论奠定了年鉴学派总体史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如果不当地运用该理论来分析具体历史时,往往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忽视了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从而产生了所谓的“历史粹化现象”,而与年鉴学派的宗旨总体史研究背道而驰。
正当年鉴学派处于鼎盛时期,50、60年代悄然兴起了现代化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欧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和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从50 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这些新兴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热潮。如经济学界出现了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在政治学界出现了阿尔蒙德等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即政治现代化只有摸仿英国的参议院民主制和美国的总统民主制;社会学界的帕森斯主张现代化就是西化。但是这些发展理论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到了现实的强烈批判。在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潮,反帝、反殖、反霸成了该时期的主题。另一方面,一体化在部分地区出现,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发展问题不再是某国的问题,而是带有世界性的。与此相应,在学术领域出现了一股强有力的“反现代化理论”、“反西方化理论”、“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美国学者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之下,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他认为60年代西方现代化理论将发展看作是发展中国家单独发展,以及把现代化理论假定存在一个普遍的发展模式,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可行性。因此,他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纳入到了世界整体来作综合的考察和把握。
年鉴学派与世界体系理论学派虽然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华勒斯坦也不是布罗代尔的直系学生。但是,若仔细分析历史时段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在思想理论和分析方法上存在诸多共同之处,而且世界体系理论中许多概念直接采鉴于历史时段理论。华勒斯坦曾仔细研读过布罗代尔的著作,而且私人关系极好。1985年10月18至20日在法国夏托瓦隆会议中心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就对布罗代尔的《腓力二世和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15-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的特性》三部著作各抒自见。华勒斯坦也被邀请参加这次讨论会,在讨论过程中布罗代尔与华勒斯坦在许多方面取得共识。1976年华勒斯坦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创建了一个研究机构:“费尔南。布罗代尔中心: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华勒斯坦为什么以年鉴学派第二代领袖布罗代尔来命名呢?1971年华勒斯坦开始写《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并将写好的章节寄给久负盛名的布罗代尔,随即华勒斯坦被邀请为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授课。从1976年开始,华勒斯坦半年在美国工作,半年在法国工作。可见,世界体系理论学派与年鉴学派关系之不一般。如果说以上仅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还不足以说明两者在理论上有何传承或扬弃关系,那么下文将从学理上分析历史时段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学术思想渊源和分析方法上的采鉴关系。
1958年布罗代尔在《年鉴》“论战”专栏上发表了《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从理论上阐述了历史时间的不同层次及其价值。在他看来,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历史事件。它尤如“爆炸掀起的烟雾充满了当是人们的头脑,但爆炸本身却很短促,火光一闪即已过去”。①事件虽发出光亮,但这种光亮却不能穿透这深沉的黑夜,是最富欺骗性的,并不能反映历史背后的深沉本质。传统的历史学所关注的正是这类事件的历史,“事实上,近百年来的历史学,除人为的断代史和个别的长时段解释外,几乎都是以' 重大事件' 为中心的政治史,历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都是短时间。这也许是近百年来科学家们为进一步掌握必要的研究工具和严格的研究方法付出的代价。”②这些事件对历史来说,意义十分有限。它们就象大海中的浪花一样,只是历史的表面现象。第二层次是所谓“态势”、“周期”。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崛起改变了传统史学的时间观念。历史学家在运用计量方法研究价格曲线、人口增长、工资运动、利率波动、生产预测时,需要一种更加宽广的时间尺度。供我们选择的时间可以是十多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一百年,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虽然如此,还不足以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因素。
第三层次,即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结构”。“结构”是指 “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③这种结构长期存在而且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作为障碍,它对人类社会的限制是人类及其经验无法逾越的,包括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布罗代尔曾经这样说道:“在巨大而沉默的大海之上,高踞着在历史上造成喧哗的人们。但恰恰象大海深处那样,沉默而无边无际的历史内部的背后,才是进步的本质,真正传统的本质。而短时段的历史,报纸上就' 当前历史时刻' 所写的一切,不过是海面,是只要载入书籍簿册就会冻结和凝固的表面”。④布罗代尔分别将这三个层次称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
在布罗代尔看来,历史学家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社会的内在本质,“巨大而沉默的历史之海”对历史学家更有价值。不仅如此,他在那篇跨学科研究的宣言书《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说,“在我们看来,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整个时间长河中共同从事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河道”, ⑤“长时段仅是社会科学会商时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之一,应该看到还有其他的共同语言”。⑥世界体系理论在思想渊源和分析方法方面受益于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华勒斯坦同意布罗代尔用“长时段”来书写历史,同时也同意年鉴学派主张多学科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华勒斯坦的三卷本《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就是在总体的宏观整体研究思路指导下完成的。在世界体系周期和趋向上,华勒斯坦采用了长时段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关心长时段社会变化,我们的兴趣主要的是较长的周期,即那些平均为50-60 年,通常被称作康德拉捷耶夫周期,还有更长一些(200-300 年)的,有时也被称为长周期”。⑦世界体系理论对年鉴学派的采鉴最主要体现在概念的运用和分析的视角上。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都存在三种层次:腹心层、中间层、外层。“在经济世界特有的分工中,外层次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而不扮演伙伴的角色。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往往过着炼狱或地狱一般的生活”,⑧中心依靠的供应,但又屈从中心的需求。同时他还认为经济世界的腹心层或中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每次中心需要转移,都有新中心形成。中心的转移都是在斗争、冲突和强烈的经济危机过程中实现的。华勒斯坦全面汲取了布罗代尔的思想,并使之更加系统化。他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带,即核心地区、半边缘地区和边缘地区。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存在着 “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如殖民垄断贸易、当代跨国公司内部转换贸易、国家间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等等。通过这些手段,不断形成新的中心和边缘地区。而在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之间有一个半边缘地区,对邻近的核心地区而言,它呈现出一种边缘化过程,但相对于邻近的边缘地区而言,它又呈现一种核心化过程。显然华勒斯坦在论述世界的三个层次以及相互之间的动态关系时,比布罗代尔更加清晰、有说服力。
在布罗代尔那里,中心与之间存在供应与需求的关系。而华勒斯坦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两个新概念:“融入”和“边缘化”。世界体系论者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16世纪的欧洲产生以后,通过地理扩张和经济掠夺,到19世纪末,西欧殖民体系已在全球建立,从而完成了近代世界体系向全球扩张过程。在世界体系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未进入世界体系的国家以及地区之间存在着一种“融入”和“边缘化”的关系。“融入”是指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不断进入世界体系的过程。由于是一种主动的姿态进入体系的,所以能在体系中占有利位置。如日本“脱亚入欧”的现代化实践;而“边缘化”则指世界体系不断包容新的国家和地区的过程。由于缺乏主动态势,只能依附于中心,现代化进程尤为艰难,如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华勒斯坦在世界划分上存在部分思想继承关系,但是也存在分歧。华勒斯坦认为欧洲经济世界建立时间在16世纪以后,而布罗代尔则认为早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以前,即在中世纪乃至古代,世界已经分成几个有结构的、有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分成几个共存的“经济世界”。
在世界文明问题上,华勒斯坦与布罗代尔也存在采鉴关系。布罗代尔对世界文明持多元论,“乔治。古尔维奇说过' 整体结构(文明)始终是不可通约的,不同类型的整体结构之间的连贯性和可比性其实纯属幻觉'.我认为这句话说得完全合理或基本合理。但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乐于承认这一点”。⑨在讨论世界文明问题上,布罗代尔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文化场”。文化场首先属于地理学的范畴,而不是人类学的范畴。文化场同样分为中心、核心、边界和边缘。他认为在文化场的边缘往往最能认清文明的特征、现象或趋向,同时,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借鉴和拒绝两种方式。布罗代尔对人类文明的未来持乐观主义态度,“未来决不是跑道的终点,也不是摆脱千百年来经历的种种悲剧的障碍,而是人类从诞生以来不断更新的希望”。⑩作为一种文明的世界体系,在华勒斯坦看来,文明是多元的,是作为一种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存在的。虽然在16世纪以前世界上存在着不同文明,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追求科学成了文明的象征。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全球扩展,西方文明成为一种具有主导性的文明或强势文明。对于处于边缘地区的国家而言,由于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边缘地区,因而对核心地区的文明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它们往往陷入两难境地:拒绝接受将很难享受核心地区文明的益处;如果接受,那就意味着放弃自己以前所具有的文明。华勒斯坦认为,未来文明的走向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单一的世界体系被打破,形成多种历史体系;二是现在的历史体系转化为一个不同类型的全球范围的历史体系;三是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他对什么样的体系最可能实现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而且这三种未来文明的形成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演绎而已。
综上所述,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与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学理上的渊源便可窥见一斑。虽然70、80年代,年鉴学派接受了来自各方的挑战,但是年鉴学派有价值的理论思想却在世界体系理论那里得到了进一步“扬弃”。年鉴学派的 “幽灵”依然徘徊于世界史坛,不管我们承认与否。
注释:
[1]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法,《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年版第176 页。
[2] ,同[1] 书,第177 页。
[3] ,同[1] 书,第180 页。
[4] ,张广智、张广勇著,《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91页。
[5] ,同[1] 书,第202 页。
[6] ,同[1] 书,第203 页。
[7]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美,《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第9 页。
[8] ,同[1] 书,第10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