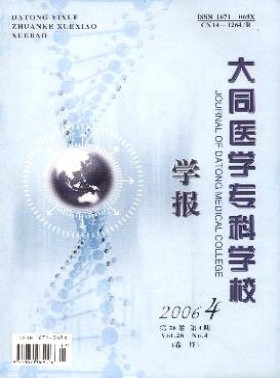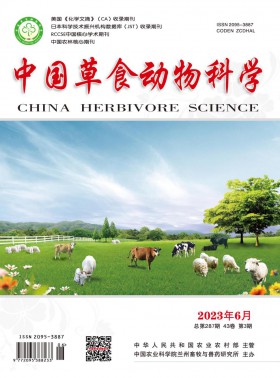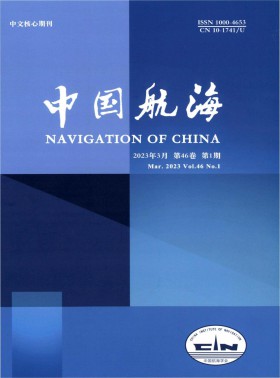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马的古诗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马的古诗范文1
直到2010年夏天,她遇到了女干部杨林会。
孤女
2009年仲夏,巴南区丰盛镇双碑村上空,乌云从四面八方聚集。
“轰隆隆――”一道闪电将村庄照得煞白。一间农舍里,14岁的罗圆圆蜷缩在墙角,明亮的眸子充满了惊恐。
像别的女孩一样,她害怕打雷。以前雷雨大作时,她总会躲到母亲身旁。
“别怕!”面色苍白的母亲总是这样安慰她。
罗圆圆真就不怕了。她觉得,只要在母亲身边,就没啥可怕――不管是电闪雷鸣,还是生活的艰难。
父母离婚后,罗圆圆跟着母亲生活。身体虚弱的母亲包揽了所有农活和家务。
“轰隆隆――”又是一声惊雷。女孩关于母亲的回忆,嘎然而止。
2007年,白血病夺走了母亲,女孩的天塌了――在风雨之夜,她再也没有可以依偎的身影。
渐渐地,原本爱说爱笑的女孩关闭了心扉。她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但她只想和母亲交心。
这时,她遇到了杨阿姨。
女干部
杨阿姨名叫杨林会,是巴南区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也是一位大二女生的母亲。
2009年冬天,她到双碑村参加“三进三同”活动。当地干部告诉她,村里有个漂亮姑娘,母亲去世后变得很忧郁。杨林会当过多年镇街干部,见过很多这样的孩子。她决定和这个女孩结“穷亲”。
在墙壁开裂的罗家堂屋里,杨林会见到了三位“亲戚”:两位坐在条凳上的老人,双手端正地放在膝盖上;旁边,一个少女埋着头不说话,但当别人提到“妈妈”二字时,她会突然抬头,眼中亮闪闪的。
那眼神,揪紧了杨林会的心。
从此,罗圆圆的生活起了一些变化。
她时常收到杨阿姨带来的漂亮衣服,还会收到汇款,100元、200元……足够她交学杂费,还能添置些文具。
每隔几天,她就会接到电话。电话里,杨阿姨特别“唠叨”:“学习怎么样?语文、数学要齐头并进,千万别偏科”、“生活费不够就打电话,正是青春期,要多吃点好的”、“不要和外公外婆犟嘴,老人们抚养你不容易”……
杨阿姨还会来家里看她。“生活中没有过不去的坎。”在布满繁星的夏夜,杨阿姨抚摸着她的长发说,“只要努力学习,你可以改变它。”
渐渐地,女孩心里泛起了涟漪。
“妈妈”
2010年8月的一天凌晨,位于巴南区鱼洞镇的杨林会家,罗圆圆躺在床上,头痛欲裂。
床边,满头大汗的杨林会对着女儿喊:“买药去,快!”
趁着放暑假,杨林会把罗圆圆接到家里。吃过晚饭,她陪罗圆圆逛街,坐在床头说悄悄话――就像别的母女一样。
可是,从来没吹过空调的罗圆圆,被“空调病”击倒了。
“嗯、嗯,好冷……”夜深了,罗圆圆蜷缩在床上。一量体温:39.6。
杨林会给她喂了药。
“头好痛……”躺在床上,罗圆圆的耳朵“嗡嗡”作响,眼前白花花一片。
以前她发烧,母亲总会用热毛巾给她降温。
“现在,没人给我热敷了。”她迷迷糊糊地想。
突然,她感到额头一阵温暖……那感觉,就像母亲的热毛巾。
女孩使劲睁开眼。朦胧中,一只白皙的手在眼前晃了晃,将一条毛巾放上自己额头,然后开始温柔地擦拭――有人在给她热敷!
“难道是在做梦?”罗圆圆将视线转向床边――杨阿姨蹲在床边,不停地用热水浸湿毛巾……
几个小时过去了,罗圆圆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
马的古诗范文2
五年级(1)班
杨思成
成长中的每个道理,都很重要,都是我们长大后成功的秘诀,而最重要的,那便是信心和坚强。
记得有一次,妈妈说:“她上初中的时候,成绩非常好,总是排在前三名里。到上高中时的第一次考试,由于妈妈在上初中时没有住宿,所以不大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每天早晨5点起床,晚上10点睡觉,所以妈妈整天无精打采的,到考试的时候也没精神,由刚入学时的第八名考到了第五十八名,一直成绩优异的她,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背起书包就回家了。对姥爷和姥姥说:”我不想上学了,我学不会了。”姥姥和姥爷听到后说:”一次挫折不算什么,只要你有信心,才会取得好成绩,这次考不好,不一定每次都考不好,所以你要坚强,不怕吃苦,你一定能行的。”妈妈听了他们的鼓励后,又会到了学校上学了,从此,妈妈刻苦学习,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马的古诗范文3
奥尼扬戈出生在肯尼亚,是奥巴马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妹。老奥巴马于1982年去世后,奥尼扬戈一手带大了他留下的六个孩子。
奥巴马很喜欢这个姑姑。在1995年出版的自传《我父亲的梦想》里,奥巴马描述了他1988年第一次到肯尼亚见到奥尼扬戈时的情形――奥尼扬戈是个活泼、骄傲的女性,是欢迎他回到老家的第一位肯尼亚亲戚。
之后奥尼扬戈多次来到美国,又回到肯尼亚。但在2000年,在奥巴马的邀请下,奥尼扬戈获得了赴美探亲签证。之后,奥尼扬戈就宅在了波士顿。为什么来来去去,偏偏这一次奥尼扬戈没有回去?我们以君子之心暗忖:奥尼扬戈一定认为,奥巴马能帮助她留在美国。当时,奥巴马担任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已经三年。
美国的州参议员应该算个官了,不到副省也差不多正厅吧。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每年有几万人进入,留谁不是留呀?这要是在咱这儿,不用领导操心,秘书就能在私底下把事办了。
但是,看来奥巴马没抻这个茬儿。何以见得?2002年,奥尼扬戈以“肯尼亚暴力冲突”为由申请政治避难,遭到拒绝。2004年,移民法院下了驱逐令,要求奥尼扬戈离开美国。你看,奥巴马真是一点忙都不帮,甚至连招儿也不给支。
奥尼扬戈厚道,尽管她又穷又病,但还是时刻关心奥巴马的进步。在奥巴马竞选总统期间,奥尼扬戈悄悄为侄子捐出了二百六十五美元。她不知道,这是帮倒忙。根据美国法律,外国公民或没有绿卡的移民,不能进行政治捐款。
2008年11月,奥巴马选战正烈。离投票还有七十二小时,这个“违法姑姑”被揭出,从天而降砸在奥巴马头上。这是对手的阴谋呀,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手。此乃寻常战术,咱中国人也会,谁要被提拔了,马上要上党委会了,告状信便来了,铺天盖地。
奥巴马赶紧灭火,称以前并不知道奥尼扬戈的非法移民身份,知道后就再也没有跟她交谈过。奥巴马的竞选团队还宣布,将奥尼扬戈的捐款退了。
对于奥巴马的大义灭亲,奥尼扬戈心碎地把脸埋在手心里哭了起来。但奥尼扬戈并不恨奥巴马,都是那冷酷的资本主义让亲人陌路。
但这个冷酷的制度没有把奥尼扬戈赶走,她躲在波士顿简陋的公有住房里,而美国法律禁止政府官员从公有住房里赶走非法移民。
后来,5月17日,美国波士顿移民法院举行了一场长达五小时的听证会,终于通过了奥尼扬戈的政治避难申请。移民法官批准的理由是:如果奥尼扬戈回到肯尼亚,她可能会因与奥巴马总统的关系而陷入危险。这样的结果倒也近人情。
奥尼扬戈终于不再是一名肯尼亚的非法滞留者,但她的身份依然属于“非法移民”,一些美国人的福利她是享受不到的。
这一次,奥巴马是否出手暗中相助?确也真有反对非法移民的组织呼吁奥巴马下令驱逐奥尼扬戈。这一回奥尼扬戈聪明了,她表示不会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奥巴马,恨恨状。但这是政治智慧,她要保护奥巴马。
马的古诗范文4
1992年,经过选秀,霍里成为了火箭队的25号球员,刚刚进入NBA的霍里加盟了当时由汤姆贾诺维奇执掌教鞭的火箭队,汤姆贾诺维奇说:“霍里是个非常聪明的球员,他绝对会成为NBA一流球星。”现在看来,汤姆贾诺维奇的预测并不准确,霍里虽不是一流球星,但却是球队不可或缺的角色球员。开始,霍里在火箭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出场机会很多可惜他交出的答卷实在是令人不满意。火箭曾一度把他交易到活塞,由于交易来的活塞球员没有通过体检,所以霍里又回到了休斯敦。这样的一段经历,改变了霍里以后的命运。1994年和1995年,霍里两次随火箭队登上了最高领奖台,捧起了奥布莱恩杯。此后,为了能够得到前锋悍将巴克利,火箭用霍里、卡塞尔等人与太阳完成了交易。霍里在太阳还没站稳脚跟,球队就用他作为筹码再次与湖人交易,结果尘埃落定,霍里最终留在了洛杉矶湖人,结束了火箭25号的历史,身披5号湖人战衣,开始了他第二段总冠军征程。
霍里的离开并没有成就巴克利的冠军梦,反倒是霍里自己在湖人开创了事业第二春。为湖人效力的几个赛季里,霍里还时常出现在首发阵容中,后来随着新人的不断涌进,他逐渐沦为替补,直到“禅师”杰克逊的加盟,霍里也没有能够改变替补的身份。毕竟,那个时候的湖人是属于“OK”的,能够帮助湖人夺取三连冠,霍里心满意足,什么能比总冠军更为吸引人呢,不是吗?正当霍里庆幸自己能够分享湖人的三连冠时,他的球员生涯进入到低谷,2003-2004赛季,是霍里表现最为糟糕的一年,非但错过了晋级决赛的机会,而且终止了自己在湖人的生活。由于霍里的糟糕表现,湖人不愿意再付出合同与其续约,无奈,霍里只好找寻新东家。要知道,此时的霍里已经拥有了五枚总冠军戒指,对于那些渴望登上最高奖台的球队来说,他的经验最为宝贵。俗语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或许马刺看中的就是霍里的经验,所以将他收归门下,随着霍里的加盟,马刺的好运也来到了身边。福将到哪都是一样的,2005年,刚加盟马刺的霍里就随队夺取了个人的第六枚冠军戒指,让人羡慕不已,此时他的冠军戒指的数量已经和“飞人”乔丹一样的多,着实让人惊叹。2007年,阔别的总冠军再次回到马刺时,霍里的冠军戒指已经达到七枚,让人羡慕的同时不得不感叹他的福气。
除了总冠军戒指以外,只要提到霍里的名字,他那一次次绝杀的场面便立刻浮现在眼前。1995年,火箭队与奥兰多魔术队总决赛的第三场,双方终场前不久打成103平,就在比赛结束前的几秒钟时间,霍里接到了奥拉朱旺的传球,当时还是新人的霍里站在三分线外,能否承担起这个重任,所有球迷都在等待,结果霍里果断出手,球应声入网,火箭凭借霍里终场前的三分命中,赢得了比赛。还没等魔术做出反应的时候,火箭乘胜追击拿下了第四场比赛,四比零横扫对手夺取了总冠军。1997年西部半决赛,湖人队对阵犹他爵士队。在双方的第二场较量中,霍里三分球7投全中,创造了N8A季后赛历史上单场三分球出手全中的最高纪录。精准的三分球,也让湖人没有费吹灰之力就登上了冠军的领奖台,而马龙等爵士队的球员再次与总冠军失之交臂。2001年,湖人队与费城76人队相遇总决赛,比赛第三场,76人队在终场前一分钟落后1分。霍里在全场还剩47.1秒时投进三分球,为湖人队锁定胜局,并且摧毁了艾弗森的冠军梦。尽管当时的76人无法与蒸蒸日上的湖人相比较,但是能够闯进总决赛的艾弗森不到最后时刻是绝不会认输的,所以湖人的夺冠过程也是很艰难的。2002年湖人队与萨克拉门托国王队西部决赛第四场,最后关头落后2分的湖人连续两次篮下强攻未果,国王队中锋迪瓦茨奋力将球拍出,不料刚好被等在三分线外的霍里得到。机会只有一次,如果抓住,湖人就能够晋级总决赛。站在三分线外的霍里拿到球之后,没有任何的犹豫,顺势就将球投了出去,结果霍里投中一个压哨三分球,湖人反败为胜将总比分扳平。赢得这场关键胜利之后,湖人队一路高歌猛进,进入总决赛的湖人上演了完美演出,最终湖人如愿以偿实现三连冠。
放弃大家熟悉的5号,重新改穿昔日的25号,霍里有他自己的想法,或许他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从25号开始,最终结束也回到25号,善始善终。值得一提的是,霍里的25号球衣在母校阿拉巴马大学早已退役,这个号码对他来说确实意义深重。
马的古诗范文5
无数次做在桌子旁,想写下关于妈妈的故事,可就是提不起这支笨拙的笔,也怕这低微的文字,亵渎了我亲爱的妈妈。每当铺开稿纸,眼睛就下起了滂沱大雨,母亲是赋予我们生命的普通女人,一个女孩子,是不能没有母亲的,即使她为人妻为人母。-母爱的伟大支撑着我们的世界。
在我的记忆里,妈妈是个要强的女人,她每天努力的工作,努力的挣钱,只为交纳我们姊妹三人的学费、生活费、资料费……邻居奶奶说“妈妈犹如拉磨的驴,没日没夜的干活,永不停息的挣钱。妈妈今年四十多岁了,可妈妈脸上的皱纹,犹如五十岁的老太太,妈妈的背驼了,眼睛花了,头发白了,走路蹒跚了……这一切都足够证明母亲为子女的复出。这一切的一切就像一个针,无时无刻的在刺扎着我的心,时刻提醒我有有一位无私奉献的老母亲。
读高中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家,离开妈妈。住校的生活不犹是我想家,想妈妈。每逢星期回到家妈妈都会买很多有营养的食物,补充我空虚半个月的胃,我知道这都是她平时不舍得吃的。记得高一开学时因为住校的坚苦,我时常打电话回家向妈妈哭诉对学校的不满,而妈妈每次都是很绝情的训斥我“不准回家”高一第一次过礼拜日,回到家妈妈很心酸的说“闺女,瘦了,背过身去轻试下眼睛,缕了下鬓角的白发“等着,妈给你做饭去!”说着她遍拿上围裙下了厨房,厨房里忙碌的身影,使我热泪满眶。我知道她是心疼我。
我认为妈妈是个命苦的女人,寒冷的冬天,所有人都躲在暖和的被窝里睡懒觉时,我的妈妈天蒙蒙亮时,她便开始一天的忙碌,为了生存,为了让孩子们吃饱穿暖,妈妈冒着寒风,顶着大雾,离开了家,骑上摩托做生意,严寒酷暑,一年四季,从未停止过。记忆里妈妈是没有双休日的。
马的古诗范文6
她的声音非常好听,说话抑扬顿挫,让我不断畅想,她给孩子讲起故事来该是何等精彩?!采访她也真是一种享受,听她讲自己的孕期,讲孩子好玩的事,讲育儿的体会,都像是在听动听的故事。而且,由于她的工作性质有些特别,她的育儿故事也真的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呢!
独特的胎教
我们的播音工作是在高辐射的发射设备之下的,所以很多同事刚一怀孕就反应很大,别说播音,甚至都不能到单位来。而我则是一直在坚持工作,直到产前休假。每天傍晚2个小时的直播,我大概中午刚过就要全身心地投入看稿、改稿。我倒是真不觉得辛苦,回想起来,反而觉得孕期过得特别快,特别顺利。其实孕妈妈需要用工作来调节自己的不适、缓解自己的焦虑。我每天一投入紧张的直播工作,即使有那么一点点孕期的不适,也消失殆尽了。还有,孕妈妈在工作环境里,其实是很享受的,因为大家都会关心你,照顾你,你尽可以和宝宝一起享用周围那么多人的爱。
另外,我也乐于把每天的播音当成是一种独特的胎教,因为宝宝在妈妈肚子里,最喜欢听到的是妈妈说话的声音,我每天都至少说上两个小时,她一定很过瘾!而且由于我做的是经济类节目,糖糖真的从很小就有经济头脑。每次去超市,她看到我们买东西,总要煞有其事地做提醒:“一个就够了。”让我们忍俊不禁。
特意的培养
有不少人都说我把女儿打扮得太时髦了,但这是我特意所为。我觉得审美都是从小耳濡目染,不是说等孩子18岁突然顿悟的。所以,我愿意打扮女儿,也愿意让她自己学着打扮自己。比如她现在就能根据色系来搭配衣服,甚至有次翻箱倒柜地找到了条绿色的窗帘绳来搭她的新绿衣。我不怕别人说我带女儿太物质化了,因为我并没有超出自己的能力去打扮她,只是在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量给她高品质的生活。
每天出门前我都会给女儿精心地准备衣服。这是我自己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也希望能够传递给女儿。对于我来说,这并不需要费太多心思,因为我自己也注重外在形象,所以很自然就做好了。
我也很享受别人夸奖我女儿漂亮、可爱,相信这些不绝于耳的赞美也能提升孩子的自信和审美品位。自信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太重要了!有自信的人,才可能释放更多的潜力。而且我相信这样的女孩慢慢成长起来,反倒不会过于在意外表,因为她对此有足够的信心,我相信她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
特殊的优势与遗憾
糖糖大概2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发现她正在自己念一本我给她讲过的《小羊和狼》的故事书,而且居然在分角色朗读!当然她不认识字,只是凭记忆在讲,但是她能把小羊嫩嫩的声音和狼粗粗的声音以及其他动物的声音学得惟妙惟肖。这可能是我这样的妈妈独具的优势吧,我确实能把故事讲得很精彩,毕竟这是我们的基本功嘛!另外,我还能给糖糖不少别的妈妈给不了孩子的享受和经历:比如她1岁开始就在我们台里给一些节目或广告配音;她有更多的在少儿节目中出境的机会,因为我原来也在电视台的少儿频道工作过。
但同时,糖糖有我这样的妈妈,也有她的遗憾。比如我的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晚上6点到8点,所以基本上不能陪她吃晚饭。记得有一次,她郑重其事地跟我谈:“妈妈,你能不能就坐在这张桌子边,和我们大家一起吃晚饭?!”但是真的特别遗憾,我亲爱的女儿,妈妈的工作性质给了你很多特别的东西,但也需要你承担一些特别的遗憾。这也如同我们的人生,没有十全十美,有遗憾才真实。做妈妈也一样,没有哪一个妈妈可以做到给孩子全部。如果真的能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我觉得对于那个孩子来说,也未必是件好事,他也许就不会懂得珍惜了。
特别的坚持
我认为在孩子的教育上,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她坚持的品质。当然,像糖糖这么大的孩子,谈坚持挺不易的,去参加活动或者节目时,她很难坚持到结束。不过,不管她能否听懂,我都会告诉她,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时间长了,我觉得她越来越能坚持了,越来越能珍惜每一次机会了。前不久,我带她参加了宝宝树举办的晚会,很多参加走模特步的孩子,最后都受不了枯燥的排练退出了,而糖糖一直坚持到最后,因为她不想在最后站在人群中羡慕地看着小朋友在舞台上。
我自己也是一个很能坚持的人,我不会说因为有难度就放弃,有困难就灰心。没有做完工作时,我不会去陪孩子,我不认为那样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妈妈所为。总和孩子腻在一起不一定是好妈妈。我希望自己在很多事情上坚持的态度,能够给孩子带来积极的影响,使她可以做一个坚持自己梦想并为之努力的人,这才是我认可的好妈妈标准。
特殊的角色
有一次,我给糖糖讲了一个怪物的故事,她有点儿害怕。我安慰她,有妈妈在,怪物不会来。可当时又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突然说了一句:“你要是不听话的话,妈妈就让怪物来。”说完我就后悔了,因为我看到孩子的眼神愣了。对啊,我是孩子最信任的人,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我赶紧向孩子承认错误,告诉她 :“妈妈说得不对,妈妈是绝对不会让别人来伤害你的。”
这件小事让我特别震撼,我真是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了母亲在孩子心目中的位置。那应该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妈妈是她绝对信任的人。所以我也感悟,今后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因为想让孩子听话、想让孩子有个好成绩等等原因伤害了她的信任,破坏了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绝对地位。因为一旦孩子不信任你了,她一定会和你的希冀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孩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不光是孩子,她也还扮演着另一种角色,那就是父母心灵的支持者,有时候甚至是支撑点。我经常自己一个人带着糖糖出去旅游,有人问我会不会太辛苦,我说不会,因为我的女儿可以给我最好的帮助:我换登机牌时她会帮我照看行李;我收拾东西时她会提醒我别忘记这个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