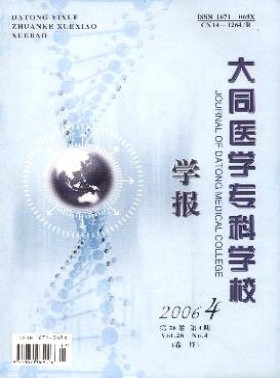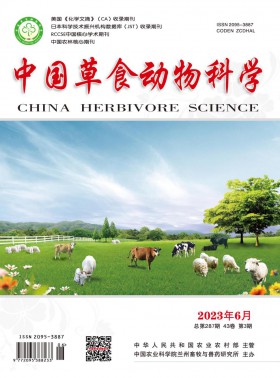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马的诗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马的诗范文1
一个看破生死的圣才
一个说他会在春天复活的幻想家
一个以梦为马的诗人
守侯着梦想
孤单的看着尘世的苍老
全人类的麻木成就了他的
清醒
一个人的清醒
是最可悲
一个人的眼泪
是最孤单
一个人的守侯
是最苦涩
秋天的太阳温柔的
打在那座长满杂草的坟墓上
孤单的墓碑
刻满海子的孤独
一个温柔的灵魂
就躺这座孤单的坟墓里
安详,安静
海子说,春天,十个海子复活
不知道海子是不是真的复活了
不知道海子还是不是孤独的
不知道海子为什么还能这样安详的躺着
不知道海子是否跟着89年的那辆火车回家了
不知道海子是否找到了那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大房子
海子说,我以痛苦而生。
现在躺在那座肮脏的坟墓里
你能难道不会更痛苦吗?
海子说,我不会放弃幸福或着想反
为这,你躺在那座无耻的坟墓里
得到你所说的幸福了吗? 或相反
海子,站起来吧
让我们去看看你醒来时,看看你在哪只鞋子里吧
在怀念海子之前,就发现人是最卑微的,是虚伪的,包括我,海子,一切的活着和死去的人们!跟朋友说,我要消失几天,但是我做不到。才发现我不是一个人了,不能再由着性子去做事了。昨晚,迎新晚会,很热闹。想告诉她,我这里的事!打电话,没人接,不过还是打通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想着她,手机关机的时候更想。还是决定开机了!
她问,为什么开机了?
微笑的告诉她,我就要开啊!
多想告诉她,我想她了!
但说不出口,好了。
一切都过去了
虽然太阳依旧不属于我
马的诗范文2
地上的人儿流着眼泪;
斗转星移星星会改变,
我却仍在任性中徘徊。
如果可以满足我的小小心愿,
那么,我希望,你回来……
你说失去的时光不会重来,
好好珍惜才最现代,
我说我愿意用我的未来换你的将来,
不准你再次离开;
你说会为我做嫁衣,
我说会为你继续努力。
时光果然不再重来,
你在那边看着我徘徊,
我会为你守着那份爱,
哪怕知道你不会再回来。
如果时光可以重来,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那份爱,
让你不会离开。
我将会延续那份爱,
马的诗范文3
初为人母,一切从头学起。没有亲人帮忙,没有其他妈妈互相交流,我的育儿知识基本来自书本和网络。姐姐寄来两本育儿宝典,作者分别是日本人和美国人。姐姐以她养育孩子的经验告诫我:一定要综合美日两国的先进理论,抛弃国人陈旧的母鸡式、填鸭式“饲养法”。近些年来,有识之士一直在批判传统的早期教育,似乎成千上万个爱因斯坦都被我们扼杀在摇篮里了。受这种潮流影响,望女成凤的我决定对女儿进行洋式早教。
根据我浅薄的理解,洋教育就是对传统的方法反其道而行之。想到自己小时候在衣食上受到的过度爱护和行动上遭遇的诸多限制,我对女儿采取“饥寒交迫”的“放养式”养育法。衣服要少穿,方便运动;吃饭随意,坚决不勉强她多吃,饿几回,她自然就会好好吃饭。关键是给她一个宽松的环境,让她放开了摸爬滚打,既锻炼了身体又能养成坚强自信的个性。女儿就这样自由自在地长到两岁九个月。
女儿上了幼儿园小小班。那是一所五星级幼儿园,和一所重点实验小学对口,还教出过几个著名的艺术幼苗。我们费了一些周折才把女儿送进去。在那里,活泼开朗的女儿开始遭遇人生最早的挫折。先是因为不肯午睡,被老师训斥;再是由于上课时带领小朋友们满地爬,还有她的运动速度太快,经常摔跤或把别人撞倒等等。她成了老师眼中的“问题”孩子。我深受打击,原以为自己呕心沥血培养的孩子一定很优秀,没想到……痛定思痛,都怪自己太迷信洋式教育了,忽略了洋花朵在中国可能会水土不服。哎,还是给孩子来点符合国情的教育吧。
为了让女儿尽快适应幼儿园的生活,我下狠心给她做规矩。可是,要把一只顽皮的猴子改造成温顺的绵羊,谈何容易。自由惯了的女儿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能”:睡觉前不能说话、吃饭不能下地、上课不能走动、不能争抢玩具等。她的头脑里根本没有“规矩”一词,一遍一遍的强调,只能加深她对幼儿园的厌恶心理。我不敢一下子要求太多,只能督促她一项一项改进,一点一点进步。但幼儿园是一个共同成长的集体,如果一个孩子在老师眼里长期落后或者与众不同的话,他就会逐渐走向孤独自卑。我开始担心女儿的心理健康。
一天,我去幼儿园接女儿。女儿出来时,我大吃一惊:她的右脸上有三道长长的血痕!我去问老师,老师歉意地说:“是我们没看好。但你女儿说是自己挠的。”回家后,我先表扬她勇敢,不怕疼,又哄了她好久,她才说是某某小朋友挠的。我既心疼又气愤,女儿居然如此懦弱胆小,还撒谎,我忍不住伸手给她一巴掌:“你为什么不对老师说?!”这是女儿第一次挨打,她受惊地躲在爸爸身后,哭了好久,才能开口说话。她的回答令人心痛:“好不容易有个小朋友和我一起玩……”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抱着女儿安慰她:“妈妈不该打你,妈妈爱你。”女儿哭着说:“妈妈,你的爱是免费的吗?”我一愣,她接着说:“我不听话,我惹你生气,你还爱我吗?”她边哭边继续说:“在幼儿园,我表现好,老师才喜欢我……小朋友才和我玩……”哦,原来她的意思是:你的爱是无条件的吗?我为她的早熟而震惊,她还不到三周岁呀!
母爱真的是无条件的吗?这么深刻的问题我回答不出。如今,大多数父母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栽培孩子,试图把他们塑造成一个优秀人物,孩子似乎在替父母圆梦,向着他们有心无力没有成功的目标艰难地前进。我按照所谓的先进育儿法培养女儿的时候, 潜意识里是否也有所期待?
马的诗范文4
福安师范附属小学
四(2)班
林柳君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只要唱起这首歌,我就会想起我的妈妈。想知道我妈妈的故事吗?那你就听我娓娓道来。
从小妈妈对我要求非常严格,学习上只要遇到一些困难,从不轻易帮我解决,而是先让我自己想办法,直到确定我实在没这个“能力”时,才会停下手上的活耐心教我,直到我完全理解为止。不过我老妈常常会出其不意,有时心血来潮,冷不防杀个“回马枪”,来考考我,令我措手不及。有一次考数学,由于一时粗心,把题目的数字抄错了,结果可想而知,我考得一塌涂地。心想这下回家没准有“竹笋炒肉”吃了,一想起那滋味可真不好受!回家一路上心里忐忑不安,我从原来的“喜雀”变成了“沉闷猪”,妈妈真是“火眼金睛”,发觉苗头不对,便问:“柳君,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我只好支支吾吾供认说:“妈妈,对不起!我这次数学考砸了,只得了87分。”,可出乎我的意料,这次没有挨骂,妈妈反倒安慰我说:“没关系,等到家了,我们一起找原因,为什么考得不好,行不?”,望着妈妈一脸的真诚,我如蒙大赦,心想:“妈妈,我真爱你!我以后会更加认真的!”
马的诗范文5
这里就谈谈诗歌创作的“回马枪”吧。
有这么一个传说,说的是几位秀才,冬天赏雪吟诗。其中一个吟道:“一片一片又一片”,众人不知其妙;接着第二句是:“两片三片四五片”,有人开始笑出声来;等到第三句一出,“六片七片八九片”,在座的人全都忍俊不禁,纷纷责问他道:“你这算是写的什么东西?”这时,这位秀才还是不紧不慢地哼出最后一句:“飞入芦花都不见。”此句一出,笑声戛然而止,大家反过来击节称赞:“好诗,好诗!”
《六如居士外集》中,也有一则与这一传说相映成趣的记载。说的是,几位“客人”登山赋诗,唐伯虎扮作“乞儿”,要求属和。当客人让他“试为之”时,他写了一个“一”字便走,客人笑着把他追回来,他又叠书“一上一上”四字。客人说:“我早知道乞儿是写不出诗的!”唐伯虎提出饮酒以后方能作诗。客人便以酒示他说:“你真能作诗,便让你喝个醉。”唐伯虎复大书“又一上”三字。客人们拍手笑道:“你这能算诗吗?”他又再写“一上”二字。几个客人越发笑得前俯后仰。唐伯虎见状,便上前拿了酒壶,一饮而尽,挥笔写成一绝:“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高山上,举头白云红日低,四海五湖皆一望。”“客大奇之”。
这两首诗,也许都是游戏笔墨,但还是能看出“回马枪”的妙处的。这种手法,在现代诗歌创作中,其实也不乏其例。沙白同志有一首诗,开头几句是:“东海里面浪滔滔,滔滔浪里多少岛!远的远,近的近,大的大,小的小”,单读这几句,并不见得精彩,似乎还有点唆。但接着便是这样两句:“好像祖国伸开手,撒出了一把红玛瑙!”人们眼前顿时一亮,出现了一个奇异瑰丽的境界,前面显得平平的诗句,也跟着斐然生色。“远的远,近的近,大的大,小的小”,这时不但不觉得唆,相反,正因为经过作者这样一一指点,似乎才更感到真切,后面那个“撒”字也更显得生动。这些岛屿,无论是远是近,是大是小,全都光辉一片。
马的诗范文6
今天,妈妈给我讲她小时候的事。
吃过晚饭,我问妈妈:“妈妈,你小时候有好玩的事吗?”“那时候好玩的事多着哪!”妈妈笑着说,“有什么好玩的事哪?给我讲讲吧!”我说。“好,我就给你讲讲第一次买雪糕的事吧。记得小时候你姥姥带我去赶集,你姥姥卖甘蔗,我就在一边玩,突然看见一个大人抱着一个孩子从东边走过来,孩子手里拿着一个东西在吃,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一定很好吃,于是我就跟你姥姥要,可又叫不上名字来,心想,这东西看上去像糖,可是太大了,从个头上看像胰子(就是肥皂),就叫它胰子糖吧。你姥姥听得糊里糊涂,见你姥姥不给我买我就大哭起来,我平常是不为买东西而哭的,你姥姥给我平时不舍得给我吃的甘蔗,我不要,一起赶集的邻居给我平时我最喜欢吃的杏,我也不要,就是要胰子糖。你姥姥生气了,就打了我几下,我哭的更厉害了。邻居对你姥姥说你就到那边去看看吧,说不定能买到。你姥姥就带着我顺着那个抱孩子走来的方向去找,走了几步我就看见有好几个人在买‘胰子糖’我就叫你姥姥给我买,你姥姥一看,原来是冰糕(那时候叫冰糕,不叫雪糕)你姥姥就过去问,买冰糕的人说刚卖完了。我心里难过极了,这就是我第一次买雪糕的经历,而且还没买上,不过,不过我从此知道了它的名字叫冰糕。”听完了妈妈的故事我大笑起来。
原来妈妈小时候也是很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