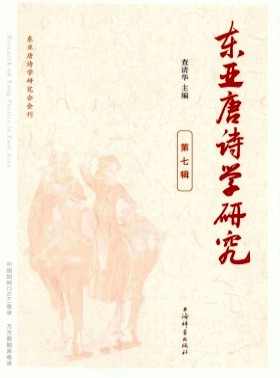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唐诗大全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唐诗大全范文1
无糖水果多用于糖尿病患者的食用。糖尿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于食物的摄取有着严格的要求,对于含糖量高的水果更是望而却步。而对于患有妊娠糖尿病的孕妇来说,低糖水果则是水果中的最佳选择。对其过敏,易发湿疹者不宜食用。
每100克水果中含糖量少于10克的水果,包括柠檬、青瓜、西瓜、橙子、柚子、桃子、李子、杏、枇杷、菠萝、草莓、樱桃、黄瓜、西红柿等。此类水果每100克可提供20-40千卡的能量。
含糖分最低的是柠檬,按照食品营养成分表比对,100克柠檬含糖量为5.1克,柠檬片泡水或拌沙拉都很适合。接下来是青梅(5.9克)、甜瓜(6.2克)、木瓜(7.0克)、草莓(7.1克)、柚子(9.0克)、橙子(9.5克)。含糖量低的水果,比较适合妊娠糖尿病患者。相比之下,葡萄干、桂圆、柿饼、香蕉、芭蕉、鲜枣都属于高糖水果,每天食用量最好不要超过100克。
1、番石榴:番石榴成熟后的果实是淡绿色的,清香可口。番石榴果皮薄,黄绿色,果肉厚,清甜脆爽,心小籽少,果实营养丰富,含较高的维生素A、C、纤维质及磷、钾、钙、镁等微量元素,另外果实也富含蛋白质和脂质。常吃能抗老化,排出体内毒素、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常食保身体健康,是糖尿病患者最佳水果。
2、木瓜:木瓜素有“百益国王”的美称,是含营养成分最丰富的水果,它含有丰富的木瓜酵素,凝乳酶,胡萝卜素等,并含有十七种以上的氨基酸及多种营养成分,具有预防高血压,肾炎,便秘,和助消化,治胃病,的功效,对人体有促进新陈代谢,和抗衰老的作用,所含的木瓜酵素,能促进肌肤代谢,帮助溶解毛孔中堆积的皮脂及老化角质,让肌肤显得明亮清新。所含的奇墩果成分是一种具有护肝降酶,抗炎抑菌,降低血脂等功效的化。
3、雪莲果: 产于云南,是一种纯天然绿色食品,果肉晶莹剔透,脆甜爽口,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蛋白质,及钙,锌,镁等多种微量元素 雪莲果果寡糖含量是所有植物中最高的,果寡糖醇度高,热量低。富含水溶性是纤维,其碳水化合物却不为人体吸收,因此很适合糖尿病人以及减肥者食用,而且具有调理肠胃,促进消化,润肠通便,保护和提高胃肠道功能,还可以调理血液,清除高血脂,降低血糖,血脂,血压,有效抑制胆固醇和糖尿病。
4、柚子:柚子在平时生活中适当多吃些柚子,不仅不会导致肥胖以及血糖升高,同时还具有降血糖的功效。我国中医指出,柚子性寒味甘、酸,适当食用具有下气消痰、健胃消食的作用,除此之外对各种原因所引起的水肿疼痛、咽喉红肿等症状都具有很好的治疗功效。柚子的食用方法有很多,除了可以直接食用之外,还可以将柚子榨汁饮用。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更适合吃柚子,因为在其中含有大量丰富的胰岛素样成分,适当食用不仅可以降血糖,还可对心脑血管有很好的保护作用。
5、柠檬:柠檬是目前水果糖分排行中,含糖量最低的水果。柠檬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具有抗菌、提高免疫力、协助骨胶原生成等多种功效,孕妇经常喝柠檬水,可以为自身和胎儿补充维生素C。
6.樱桃,同样属于低糖水果,因此害怕肥胖的人群在平时生活中可以用樱桃去代替其他的高糖水果。孕妇在平时吃樱桃,还可以起到美容的作用。樱桃中还含有丰富的果胶,这种物质有利于增加加胰岛素的分泌量,从而让血糖平稳快速的下降。因此建议患有高血糖的孕妇,在平时可以多吃些樱桃。
7.苹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一种水果,同时也是大家极为熟悉的,但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苹果也是低糖水果中的一种。苹果性凉味甘,不管是什么品种的苹果,适当食用后都具有明显的补心益气、止咳、健胃和脾、除烦、解暑功效,尤其是一些经常醉酒的人群更应该多吃些苹果,因为它还具有极为有效的醒酒功效。而且由于苹果中糖的吸收缓慢而均匀,因此具有很好的降血糖功效,尤其是餐后血糖。可以说经常吃苹果对糖尿病患者是非常有好处,对于低糖水果有哪些这个问题,苹果也是其中之一。
8、梨:中医指出梨性寒味甘、微酸,具有极为明显的生津、润肺、清热、凉心、消痰、降火、止热咳、解毒等作用。而且梨中所含有的糖分也非常少,因此一些害怕肥胖以及糖尿病患者在平时生活中可以代替其他水果多吃。
9.柑橘,品种繁多,有甜橙、南橘、无核蜜橘、柚子等。它们都具有营养丰富、通身是宝的共同优点。常吃柑橘可以预防坏血病及夜盲症。但是,柑橘好吃,不可多食。因为柑橘性温味甘,补阳益气,过量反于身体无补,容易引起燥热而使人上火,发生口腔炎、牙周炎、咽喉炎等。一次或者多次食用大量的柑橘后,身体内的胡萝卜素会明显增多,肝脏来不及把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A,使皮肤内的胡萝卜素沉积导致皮肤呈黄疸样改变,尤以手及脚掌最明显。常伴有恶心、呕吐症状。孕妇每天吃柑橘不应该超过3只,总重量在250克以内。
唐诗大全范文2
我回顾和总结了一下今年糖酒会的几个看点,供大家尤其是未能出席会议的同仁们参考。
看点一:新会场,新纪录。首次全面启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共使用了9个馆和8个连接馆,室内展览面积达11万平方米,室外广场面积达5000余平方米,规模刷新了全国糖酒会总面积的历史记录,有参展企业3000余家。足见糖酒会的生命力依然旺盛。
看点二:水立方进会场。北京奥运会是2008中国最大的热点。嫁入豪门中粮集团的酒鬼酒巧妙借奥运题材,在主会场把展位创意搭建起一个水立方围起来,非常抢眼。只可惜用材和内部布置差了点,否则一定会被评为最有创意的展位。
看点三:另类企业参展忙。除了食品糖酒企业,越来越多的另类行业巨头加入到糖酒会的行列,呈现多元化趋势。继医药巨头石药集团连续两年参加糖酒会推广果维康VC含片外,今年另一医药大鳄广药集团率旗下5家药厂整体亮相,推出系列植物饮料。另外,有中国海洋食品第一企之称的上市公司獐子岛渔业首次强势加盟糖酒会。有意思的是,连前两年风风火火的戒烟替代品如烟一号也首次参展。他们都希望通过和各类品牌食品酒业经销商联络,整合各类营销From 资源,探索建立杂交跨界营销的体系。
看点四:白酒集体高端突围。19日,全国糖酒会办公室了《2007~2008中国糖酒食品业市场年度报告》,该报告称,全国酒类工业总产值达2619亿元,同比增长25.5%。增长的背后隐藏的是产品集体提价及糖酒业的高档化冲动。这一点在糖酒会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各酒类企业纷纷加大对中高端品牌及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力度,水井坊还把“水井坊遗址”局部复原模型搬到现场。
看点五:葡萄酒势力越来越大。中国葡萄酒消费需求的日益强盛,使全世界葡萄酒企业都把目光转向中国,今年参加糖酒会的中外葡萄酒厂商普遍多于往年,势头凶猛。主办方还专门开辟洋酒专区,甚至场外也有机构组织葡萄酒专业品牌展示活动。亚洲最具潜能的新天葡萄酒去年业绩大为提升,高调出席糖酒会,推出新品牌1600阳光干红系列,还组织新疆美女+跑车进行城市秀酒。
看点六:植物饮料势头凶猛。受王老吉成功的推动和刺激,许多食品厂家纷纷效仿和跟进,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形形的凉茶和植物饮料大行其道。成为今年糖酒会上一道凉丽的风景线。
看点七:粗粮食品大行其道。大豆方便面、玉米方便面,寒地黑土方便粉丝、薯片,膳食纤维饼干,五谷杂粮面等等,粗的有理,粗的流行,正暗合了城镇消费者对粗粮食品的消费取向。
看点八:新品类层出不穷。新品类营销一直是食品行业创新的重要途径,今年糖酒会的新品类也异常丰富。牛奶啤酒、水果捞、板栗粥、玉米油、水果脆片、玉米乳、各式水果奶饮等等。尤其是来自广西的玛氏火龙果酒,品类新颖、口味独特,虽说展位不大,只是市场亮相测试,却引来不少关注。
唐诗大全范文3
当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或告一段落时,需要我们来对前段时期所做的工作认真地分析研究一下,肯定成绩,找出问题,归纳出经验教训,以便于更好的做好下一步工作。下面就让小编带你去看看食堂保管员年度工作报告范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食堂保管员工作报告
时间过得真快,茫茫碌碌中已近年末,转眼间我接管食堂的时间又过了一年了。
回顾过去的每一天,我作为一名食堂管理员,深感到责任的重大,工作压力之沉重。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质量,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全体职工的身心健康。所以,为了扬长避短,今后能把工作干得更好,现就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第一、作为食堂自然是离不开饮食,食堂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假如我们离开了吃的东西是不可能生存下去,所以作为单位的食堂这也是很重要的。作为食堂管理员更应多为的饮食着想,为保证每位学生的身心健康而考虑。
第二、作为一个集体食堂,食品卫生安全是关系到每一位学生身体健康的大事。首先,我们要求每位食堂工作人员上岗前,都要进行上岗前的体检,对体检不合格者不於上岗。食堂是学生用餐的地方,也是对疾病最为敏感的地方,为了使全体职工都能心情舒畅的放心用餐,作为食堂的工作人员,我有责任有义务搞好食堂的卫生工作。不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思想教育、贯彻落实食品卫生法的要求等。通过学习,提高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服务质量和意识。切实做好食堂的食品卫生、餐具的“一洗、二冲、三消毒”工作,工作台做到随用随清,每周对厨房一次大清扫。如发现工作中有不到位之处立即指出,勒令改正及时到位。全体工作人员能够认真做好本职工作,明确职责、各司其职、服从分配、随叫随到,保证了职工的工作正常运转。第三、每天,我一有空闲,就下厨房巡视,与食堂人员取得沟通联系,对食堂工作方面的所需或不足,作详细了解,如有不周,及时作好调控。如卫生情况:由于用餐人数多,前段时期食堂人员不定,使大家身心疲惫,有时没能够及时、彻底地将卫生打扫干净,物品的摆放也不够整齐。为了及时调整好工作人员的心态改变当前状况,我亲自为他们出谋划策,亲临厨房,指挥他们或配合他们一起工作。使天花板、墙壁、灶台、蒸箱等焕然一新,地面、库房等一尘不染。厨房有了明显改观,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全体工作人员更加心情舒畅,干劲更足;同样,良好的餐饮环境,也给就餐人员带来了愉悦。
第三、把住食品进货也非常重要。一百多人用餐需要经常外出采购各种食品,如:肉、菜、蛋、禽、主、副食等。由我和采购员一同去采购,严把没有“检疫证”、“食品卫生许可证”的食品一律不采购,存放时间长的、变质变味的统统拒之门外,严防食物重毒事件的发生,切实保证每位职工的身体健康。在此期间在我食堂用餐的人员及职工无发生任何肠道疾病和食物中毒事故。食品卫生方面做到不能长期存放的蔬菜食品每日采购、可长期存放的食品定期采购。
第四、一年来接待了,大小用餐共计十余次。及时、准确、顺利地完成了用餐接待工作,给各级领导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同时确保了职工的正常就餐。
食堂保管员工作报告
伴随着“突出重点,克难攻坚,为全面提高全市______行业综合经济效益水平和整体竞争实力而努力奋斗”的主旋律,我走过了极其不平凡的一年。一年来,在办公室的领导下,在食堂全体同志的相互配合下,紧紧围绕让每位职工满意就餐的目标,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为免除职工的后顾之忧,千方百计保障全体职工全身心的投入到经营销售工作中去而努力。现就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总结
食堂是我们______公司全体职工用餐的地方,也是对疾病最为敏感的地方,为了使全体职工都能心情舒畅的放心用餐,作为食堂的工作人员,我有责任有义务搞好食堂的卫生工作。一年来我始终坚持对餐具及时清洗消毒,始终保持食堂地面的干洁,由于人多每天都要分两拨就餐,为了使第二拨就餐人员吃好饭,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干净餐桌,换上新的桌布,使第二拨就餐人员也能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就餐。我在食堂负责打饭打菜,经过这一年来的工作,我已经能够对每位职工谁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能吃多少都做到心中有数了,在打饭菜的时候在饭菜量的掌握上自然也就心中有数了,这样既达到了就餐人员的满意,又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同时我还是食堂的保管员,负责保管食堂的油、盐、酱、醋、米等物品,这一年来我始终保持保管帐的帐目清晰,做到每一收每一支都在保管帐上体现,不占公家一丝便宜。
当然工作的同时也不能忘了学习,从我进______公司第一天起,我就已经感觉到这里学习氛围的浓厚,200__年是全省企业文化建的开局之年,做为公司的一员,我有责任有义务去学习企业文化建设的精神实质,通过学习使我懂得了,我们食堂的成立本身就是我们____________企业文化的一种形式体现。我原来认为,我只是食堂的一个小小的服务员,什么企业文化、什么公司盛衰似乎都与我没有什么关系,通过学习我发现我的想法的错的,生活在我们这个______大家庭中,我们每个成员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公司几十号人都吃的是我打的饭,只有他们都吃好了,才有精力去搞经营,搞销售。所以我做为食堂的一员应是感到骄傲和自豪。如果我过去的工作能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更加积极努力的工作,让大家吃上更舒适的环境中吃上更可口的饭菜。为张经理在年初工作会上所讲的“让各项福利事业搞的更好一些,让职工的精神面貌更加愉快一些”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食堂保管员工作报告
课堂和食堂是幼儿园管理的两大阵地。食堂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师生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幼儿的健康成长,直接影响幼儿园的社会形象。因此,我园坚持以党的"____大"精神为指导,以服务师生为宗旨,进一步增强后勤人员素质,提高服务质量,提高管理水平,提高整体品位,努力把食堂办成教师满意、家长放心、幼儿开心的食堂。
后勤工作是做好幼儿园管理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基础所在,幼儿园在园领导的关心支持和教师们的积极配合下,回顾食堂管理工作,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各类制度
1、增强对食堂人员的考核。制订了《食堂人员工作要求及奖惩细则》
2、蔬菜购入采用多人组合法,买菜、付款、验货、过秤、记账分人负责,互相督促、互相监督,园长统一审批。
3、建立食品卫生管理网络,实行食品卫生安全园长负责制,进一步健全《食堂工作管理制度》以及各岗位卫生责任制度,并与所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及安全责任状,做到有岗就有人,有人就有责。
4、进行成本核算,积极施展伙委会的作用,及时调查了解食堂管理及师生用餐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二、提高职工素质
1、增强培训。我园每月组织职工学习《食品卫生培训教材》或对她们进行安全教育,增强食堂工作人员规范操作的意识,提高规范操作的能力。
2、明确岗位职责。我园力求将食堂工作分工细化,组织学习各岗位职责,使之进一步明确。岗位任务的完成情况与考核挂钩,进一步提高了职工岗位意识和服务意识。
3、及时反馈情况。每月由教师对食堂工作进行评价,在评价中提出的意见或建议,我们及时与食堂人员交换,督促整改,在整改中不断提高和完善。
三、高度重视卫生安全工作
1、通过正常渠道采购食品,索取合同摊位的合法证件。在与供货商合作前,我们认真审核证件,明确责任,签定协议。把好采购、验收、取样、浸泡、清洗、操作、消毒关。
2、一丝不苟地做好消毒工作。餐具做到"一用一消毒",小餐具用消毒柜消毒,大餐具用消毒液消毒。
3、食堂工作人员均持健康证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上岗,工作期间能按要求穿戴好工作衣帽,保持个人卫生,环境卫生分人分块包干,保证食堂环境卫生。
唐诗大全范文4
剑网3指尖江湖十全大补汤
【灵芝】+【雪莲】+【人参】+【虫草】+【井水】
剑网3指尖江湖十全大补汤
【炖锅】
剑网3指尖江湖十全大补汤
唐诗大全范文5
袁录怀书记希望借助香港《商务・旅游》杂志平台,向海内外读者特别是海外华侨、华商、华人社团发出诚挚的邀请:“开放的金台将以一流的环境为投资企业提供安全、文明、宽松的发展环境。金台真诚欢迎海内外朋友前来旅游观光,参观考察,投资兴业,探亲访友,祭祖交流,品味源远流长的姜炎周秦文化,感受独具魅力的西府民风民俗,领略古陈仓、新金台的绚丽风光,寻找投资发展新的机遇和平台,金台人民欢迎您!”
“区域综合实力位居陕西省城市区第七位。今年上半年,在金融危机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的情况下,金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仍然保持了15.1%和22.5%的发展速度。金台区之所以在经济危机的不利条件下仍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依靠金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袁书记向记者开门见山自豪地说。
区位优势明显。金台区是宝鸡市的老城区、主城区、中心城区,也是市委、市政府及全市行政中心所在地,以元末太极宗师张三丰修行的道观――“金台观”而得名。金台地理位置适中,自然条件优越。金台区作为欧亚大陆桥之重镇,陇海、宝成、宝中铁路和西宝高速公路、310国道贯区而过,是巴蜀北上、甘宁入关必经之地。整个交通形成“十”字大骨架,构成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在古代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工业基础雄厚。谈到金台区的工业袁录怀书记兴奋不已,向记者侃侃而谈。他说,金台区工业产值占全区GDP的60%以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宝鸡将建成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经济区副中心城市。借助这个发展机遇,金台与天水的麦积区、清水县缔结为友好合作县区,将进一步推动金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金台区域内工商企业云集,有宝鸡石油机械厂、宝鸡卷烟厂、宝鸡机床等部省市属大中型企业6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8户,形成了机械加工、金属冶炼、食品医药、新型建材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好猫”香烟、石油钻采设备、合力叉车、数控机床等百余种名优产品享誉国内外,宝鸡石油机械厂世界第三、全国第一,配套企业近千家。民营企业发展迅猛,其中,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东岭集团是陕西乃至西北最大的村办企业。
文化积淀深厚。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金台区曾经创造了极其辉煌的古代文明,留下了光辉灿烂的历史篇章,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源头。袁录怀书记对金台历史文化如数家珍:7200年前的北首岭文化遗址比享誉世界的半坡遗址还早400多年;金陵河西岸的蒋家庙中心遗址,为西周早期的中心城址,是周文化的发祥之地;金台故称陈仓,三国时期“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历史典故就发生于此;中国文学的明珠――《诗经》,就诞生在这充满智慧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圣地。
旅游资源丰富。袁录怀书记表示,金台区的希望在旅游。为了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业,金台区今年实施了“文化旅游年”建设,按照“突出一线,打造两个核心、强化十个点位、构建四个片区”的思路,正在倾力打造古陈仓遗址公园、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公园、金台观道教文化公园、大唐秦王陵和西府天地休闲观光旅游区及六川河生态文明示范区“四景一区”。利用三至五年时间,将六川河地区打造成宝鸡城区“后花园”。突出西府天地乡村旅游品牌,规划建设金台观道教文化旅游景区,启动金台观大踏步和南大门建设。突出仰韶文化,启动北首岭遗址公园建设。代家湾生态示范园年内建成大踏步土建工程,完成坡面亮化、绿化、美化工作,使“文化旅游年”建设真正落到实处。金台区将以为“文化旅游年”为契机,充分挖掘文化旅游资源,打造以仰韶文化、道教文化、生态观光、都市休闲为中心的四大旅游名片,全力打造西部都市天堂,彰显金台城根文化魅力。
唐诗大全范文6
一、建立健全班规、统一加分标准
好的班级必须要有个详细周密的班规,这样才有利于班级的发展,有利于学生在校期间对自己的约束。新学期开学,我和同学们共同研究,请大家一起思考:一个优秀的班集体,需要来制定哪些规章制度?学生们纷纷举手回答,有的同学说:上课不能讲话;有的同学说作业必须要按时完成;有的同学说:同学之间不能不团结友爱……等等等等,接下来就针对这样的一些现象制定出来一些扣分的标准和加分的项目,同时由于基础不同,能力不同,因此,我还提议对学习基础不好的同学和学习好的同学之间的加分的标准的一些变化,比如一号和二号同学小考90以上加分,三号同学80分以上加分,四号同学70分以上加分,……以此类推,每一天、每一节课的上课的发言、作业的完成、每次小考的成绩、站队的快静齐、劳动任务的完成情况等等诸多方面都有加分的标准,甚至连指甲太长、头发扎的不精神,不能带花样的头饰等这样的细小事情都要每周检查,这样就使学生在平时的学习和纪律、劳动等方面,明确了具体的任务。果然,学生们每天都忙的充实、忙的快乐,他们每完成一个任务,每达到一个目标得到了相应的加分后都非常兴奋,心中都燃起了希望的火苗,学习上的奔劲更足了,而没有加分甚至是扣分拖了组的后腿的学生则感觉的很不是滋味,在其他组员的帮助下也积极要求上进,争取为组争光。高校课堂的计分机制贯穿了班级管理的方方面面,学生们每天到校都抓紧时间学习,争取每次的加分机会,这个模式的运用可以说起到了班级管理上的事半功倍的效率!
二、分组合理,公平竞争
为了使计分管理机制顺利有效的完成并坚持下去,为了使班级的所有层次的学生都有劲头,我把全班分成了5个组,每个组的人员组合都要接近,不能相差太多,那样就丧失了竞争的意义和劲头。我在学生入学的前两个星期并没有分组,而是按照班规对个人进行考核,到了第三个星期后开始计算总分,按照得分的多少进行蛇形排列来分组,同时为了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我还用了一些特别的手段,比如组的得分在班级名列前茅,要有优待,不仅登上班级的光荣榜,而且还可以在这一周随便挑选自己喜欢的座位,每个周五的下午,就要把分数公布,然后进行总结表扬和奖励。每个学生都有一颗积极上进的心,学习不好的同学在考试的时候得到加分的机会少,但是可以通过多发言,多劳动获得加分,比如每个学期的洗窗帘的任务,还没等到我问我分配,就已经被一些眼疾手快的同学抢走了,没拿到的同学只能流出羡慕并遗憾的目光。而且有的时候一些组的分数相对低些,我还故意创造机会给他们,这种竞争一直处于激烈的状态之中,效果简直好得超乎了事先的预想!
三、严守加分标准,健全监督办法
刚开始,学生们还能够按要求执行计分标准,可后来,有的同学就开始偷懒耍滑了。我们班级每天早自习都要进行英语的小考,考单词、考句子、考课文,而批卷子的3个同学就发现了“门道”,他们几个暗自联合,因为怕批卷子的过程中出现问题,所以我要求不能两组对批,结果他们三个组就在不批自己组的前提下完成了三个小组之间的“互利互惠”,这样的事情被查实以后,我对这几个组不仅要扣多分,而且进行了严格的批评教育,并且每个人交给我一份检讨,从心里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之后我又设立了一个监督人,那就是每天一个临时的值日班长,他可以有权随时抽查和处理班级中的一些不诚实的现象,这样就把这个恶习控制在萌芽之中。还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的同学在检查作业的时候拿别人的作业充当自己的作业的,当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被查作业的学生发现,那么就要在批评不完成作业的同时,还要追究检查作业人的责任。每学期末考试前,我都要求学生把所有的作业本都一起上交,我要亲自检查,这样学生不完成的地方就会露出马脚了。所以,此次事情只发生了一次再也没有出现过。上述类型的事情在第一个学期后,就全部消失了,学生们在这样的监督机制中养成了学习和生活的好习惯,完成了从小学到初中的顺利过渡,我们班在上学期期末就明显优于其他的班级!
四、团结互助、共同进步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个组的组长因为怕耽误自己的学习,所以也就不愿意为了组的分数而分散自己的精力,因此这个组处于了涣散的状态,组长埋怨组员不努力,拖后腿,管不好;而组员却认为遇到这个组长很倒霉,每周都倒数第一,想换到别的组里去。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除了找组长多次的谈话,帮助他树立信心,使他明确班级的利益就是他的利益,如果别人不提高,他自己也会受影响,还通过组长的评比来激励组长的工作热情,因为组长的工作多,压力大,所以我会额外每周给组长多加十分,并且一个学期后的假期时间可以给分数多的同学和组长减持一定的假期作业,以资鼓励,而倒数第一的那组的组长是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的,因此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组长和组员们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每个人都努力再努力,争取为组里加分,这样互帮互助的班风就逐渐形成了。
五、坚持不懈,不能虎头蛇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