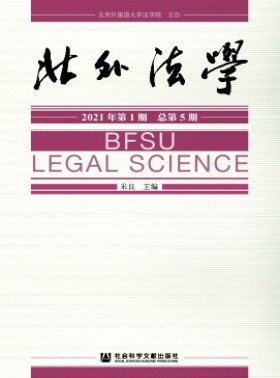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刑法哲学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刑法哲学论文范文1
践行科学发展观,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项艰巨的实践任务。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全部工作对本行政区域的发展具有强力影响。因此,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找准人大工作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着力点,把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贯穿于人大工作全过程。
(一)人大践行科学发展观,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上下功夫。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因此,人大践行科学发展观,就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履职全过程,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具体要把握好三个关系:把握党委决策与人大决定的关系,坚持党委行使决策权与人大行使决定权的内在统一性,使党委决策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把握围绕党委中心与开展人大工作的关系,根据党委决策意图确定人大的工作方向,根据党委总体部署安排人大的主要任务,做到人大工作与党委工作同心、同向、同步;把握贯彻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意愿的关系,既要始终坚持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确保人大工作的正确方向,又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
(二)人大践行科学发展观,要在推进又好又快发展上下功夫。又好又快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精髓。人大践行科学发展观,要着眼经济发展质量、速度和效益的有机统一,把人大监督经济运行的切入点,放在优化产业布局、优化投资结构、优化招商项目上,通过开展调查视察、听取专项报告等方式,切实加强对工业经济、城市经济、镇域经济等重点工作的监督支持,努力促成投资拉动和创新驱动并重、利用外资与直接融资并重、资源利用和资源节约并重、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并重的科学发展新格局。要抓住经济结构调整这条主线,加强对高新技术、信息产业、节能减排、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工作的监督,支持政府加大环保力度,从严查处违规排放行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加快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形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三)人大践行科学发展观,要在加强民主法治建设上下功夫。民主法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保障,也是人大工作的根本任务。人大践行科学发展观,要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发挥代表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中的主体作用;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保证城乡居民选举权的平等;健全公民旁听人大会议制度,畅通民意诉求和民情反映渠道。要努力发展基层民主,以落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抓手,引导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利,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要加强对“五五”普法的监督检查,强化对法律法规的执法检查,深化执法责任制,加强平安建设,努力维护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
(四)人大践行科学发展观,要在创新履职方式方法上下功夫。创新是科学发展观的永恒主题。人大工作要永葆生机活力,就要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在履职方式上有所创新。要创新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方式方法,努力形成决定之前重调查、决定过程讲民主、决定内容求实效的决策机制。要创新行使监督权的方式方法,认真研究分析监督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在规范统一监督行为、深化细化监督程序、拓展丰富监督方式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要创新行使人事任免权的方式方法,建立完善任前考法、供职发言、任职宣誓、颁发任命书等程序,实现党管干部和人大依法任免的统一;探索实行对被任命干部进行年度工作评议,开展部门负责人向人大代表述职述事活动,实现对事监督与对人监督的有机统一。
(五)人大践行科学发展观,要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上下功夫。社会和谐既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目标,又是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按照共建共享的原则,高度关注民生,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要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建设,通过听取专项报告、开展调查视察等方式,不断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和水平,使广大农民群众都能享受到快捷、高效的社区化服务。要抓住教育教学、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就业再就业、劳动保障等重点问题实施监督,支持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破解民生工作的难题,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人民群众。要认真做好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加强对信息的
刑法哲学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 刑法 因果关系 判断路径
一、刑法因果关系中几种主要的学说概要
目前刑法学界有关因果关系的主要学说有条件说、原因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其中条件说认为,理论上所有存在的条件关系都可以成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虽然该学说也对条件关系的形成有所限制,但还是有牵连太广的弊端,因而在刑法判断中遭到摒弃。原因说也被称之为限制条件说,对条件说的因果关系加以限制,缩小了因果关系的外延,但这一学说在认定因果关系上过于随意,也被大陆法系刑法所不容。
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相当因果关系说。这种学说根据因果关系的情况又可以分为客观说、主观说和折中说。客观说认为,某一行为发生的所以状况以及理论上可被预知的后果应当作为相当性判断的基础,刑法因果关系应有法官根据上述标准作出客观的判定。主观说则主张以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能够预见的状况为相当性判断的标准。由此可见,主观说的判断标准似乎过于狭隘。折中说在理论上杂糅了客观说和主观说的一些观点,但其强调,社会普通人无法预见,而行为人预见到的状况,也应当作为判断因果关系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折中说在理论上是比较靠近主观说的。
刑法学因果关系理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陆法系发展演变出“客观归责理论”,在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客观归责理论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从行为人所实施行为是否存在法律所禁止的危险来判断行为与结果是否存在关联;其次,继续推论行为人的危险行为是否造成结果;最后是判断因果关系的几大构成因素是否属于有效范畴之内。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受前苏联刑法学说影响,在刑法判断上主要围绕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进行讨论。前者在判断因果关系时倾向于危险行为只有在社会普通人可以预见的情况下产生危害结果才能构成;后者则认为一种行为在其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当中,偶然地介入其他因素,从而形成了危害后果,事先的行为与事后的结果只是存在偶然的因果关系。这两种学说过于理论化,在司法实践中实施起来很难把握好分寸,所以在刑法理论中逐渐被淘汰。
二、因果关系学说的启示
1.刑法判断中的因果关系学说在不同的法系、不同的司法体制中存在多种不同的学说,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每一学说都坚持各自的判断标准,判断因果关系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在诸多学说之中,没有哪一学说是完美的,每一种学说在诞生之初都不同程度地遭到过抨击,在指导司法实践上不同的学说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实践证明,条件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在刑法学界取得了更多认可,在刑法判断上被广泛适用;原因说在实践中难以实施逐渐被学界所抛弃。所以说,司法实践是检验众多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唯一标准。唯有通过实践证明了的理论才会长久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2.在对刑法因果关系相关理论进行研究时,我们始终无法绕开哲学与逻辑学的影响。黑格尔的因果观念对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条件和因果的关系;德国逻辑学家冯·克里斯在1889年发表《可能性的概念及其对于刑法的意义》一文,将逻辑概念引入刑法判断领域,并首次使用了“相当因果关系”这一概念。由此可见,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溯源于哲学与逻辑学的因果规律是无可争辩的。
3.现存的因果关系理论学说在司法实践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适用。在普通法律案件的处理中,不同学说之间的差异和法律实践中的优劣并不明显。但对于一些特殊案件的处理上,各种学说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争议。实践证明,对于每一例具体的案件,不同理论学说都存在明显的优劣。不同学说之间既有存在争议的时候,也有在同一案件中思路比较接近,相互印证的时候。在有些特殊案件中,一些理论在实践中即使存在冲突的,也是可以共存的。“一流的智力就是这种努力:同时拥有两种相反的概念,以维持期间的平衡。”
三、有关判断刑法因果关系方法的探讨
1.我国法学理论继承了前苏联的法学思想,倾向于大陆法系。所以在判断刑法因果关系时要以条件说为逻辑基础。因果关系理论的争论焦点在于处理特殊案件时没有先例可供参考,所以拥有哲学理论支持的条件说受到学界青睐。另外其符合逻辑性也填补缺少实践经验的不足。条件说根据社会一般人基本的思维常识来看待因果关系,坚持以日常生活中的常规规律为指导来判断刑法中的因果关系。
在因果关系说中,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将条件说作为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基础。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内容使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更为简单。行为人的行为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关系成为唯一的刑法判断关系。《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律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按照这条规定,即使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危害后果,只要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也不得判其有罪,否则便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而将法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适当的出罪同样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2.我们在对众多刑事案例进行法理分析时,应该基于哲学、逻辑学考察刑法因果关系。这时,我们会发现,任何一个结果都不是由单独的原因引起的,每一个结果的产生往往是诸多诸多原因加在一起所导致的。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之中,既有人为的主观行为,也有环境客观条件或者自然现象等等。单独考虑行为因素,也存在很多复杂原因。造成结果的行为可能不止一个,这些行为又可以分为若干种类。之所以要对刑法因果关系进行合理判断,就是要在造成犯罪结果的众多因素中找到影响定罪量刑判决的因素,从而发现犯罪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单纯地依据条件说进行判断,离开罪刑法定原则的有利支撑,我们的判断就掉入了哲学逻辑的怪圈。单纯地适用条件关系的“排除法”进行判断,在具体的案件操作中很难全部实现,因为运用“排除法”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知道这些条件如何作为原因而发挥,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说在司法实践中根本难以实行。
根据上述原因,我们可以意识到,在条件判断的基础上,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进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判断显然比单纯依据条件说进行刑法判断更为科学合理。但百密一疏的是,这样做也有将合法行为划归犯罪的可能性。看来,没有那一种理论可以做到至善至美。为了防止这一可能的发生,我国法学界提倡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我国法学理论尚待提高的司法环境下,依靠法官的谨慎入微来弥补理论的不足。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未尝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3.选择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作为刑法上因果关系判断核心的主要原因:
(1)相当因果关系说也起源于哲学逻辑理论,同样有哲学理论基础。从刑法判断的方式方法上看,相当因果关系学说仍然属于条件说的理论范畴。在继承条件说优点的同时,相当因果关系说以法的观点将因果关系限定于日常生活经验法则之内,以行为发生时普通人的预见标准为标准来判断该行为的合法性。这样的判断方式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意义的因果关系划分出明确的界限。
(2)选择客观的因果关系说使得司法实践中判断刑法因果关系时更加易于操作。理论上的分歧与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完全不同,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各种学说之间存在较大争议。休谟曾经这样说过:“一切深奥的推理都伴有一种不便,就是:它可以使论敌哑口无言,而不能使他信服,而且它需要我们作出最初发明它时所需要的那种刻苦钻研,才能使我们感知它的力量。”我们只有放下书本,抛开各种理论的教条限制,置身于法律实践之中时,我们才能充分验证各种理论的长短、优劣。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功利的、现实的因素总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司法工作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绝大多数案件,我们只不过进行宏观的、粗略的判断就可以解决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关于理论上的分歧并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影响法院的判决结果。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司法效率原则的要求。客观的因果关系说相对于其他学说来讲,更适合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操作。
(3)罪刑法定原则使客观的因果关系说成为判断刑法因果关系的首选。刑法中因果关系的研究更多的依赖于社会经验法则。而社会经验只是针对常规状态下的普通人而言的,对于特殊状况的具体的某一些特殊人群无效。平心而论,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也许对行为人过于苛求。但这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客观代价。无论我们选择何种理论,都不会是十全十美的。完美的理论只存在于空想之中,停留在书本之上,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
(4)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从理论结构上看更具开放性,容易与其他学说相结合,在刑法因果关系判断中可以起到关键的均衡作用。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概括性使它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与其他学说相冲突。这正是当前法治环境所需要的司法理论,对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处理特情况下的具体案件时,以条件关系为基础,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以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判断为中介,以客观的相当因果关系为核心,结合其他学说进行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判断,可以解决很多法律实践上难以操作的难题。
四、结语
刑法哲学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刑法因果关系是一个十分具体的司法实践问题,也是理论界争议最大的问题。刑法界的学者和专家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刑法因果关系虽有它的哲学基础,但它毕竟是一个法律问题,有其自身的特征。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形成了自己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论学说,我国当然也不例外。其实,刑法因果关系仅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一种联系与刑事责任没有关系。但这如何它与犯罪构成要件的关系,它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又怎样呢?很少人论述。在不作为犯罪、疫学上的犯罪中刑法因果关系又各有其特点。
一、刑法因果关系的概念
因果关系本来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后来被引入刑法中。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引起别的现象产生的现象是原因,被引起的现象则是结果,即外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刑法中是指危害结果的产生首先在于客体事物内部具有在这种外在力量作用下产生有害变化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是一种抽象可能性,本来事物存在的实在可能性是朝着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的,由于外部危害行为的干扰,影响原来实在可能性的继续发展,而是原来处于抽象可能性位置的危害可能性变成了新的实在可能性,成为事物发展新的必然趋势,并在一定条件下转变成现实性,就产生了危害结果。
二、刑法因果关系的特征
(一)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因果关系作为客观现象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以人们主观是否认识到为准。当发生了一个刑事案件时,我们首先要从客观性这一点着手,看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否由犯罪嫌疑人的危害行为造成,如果之间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即存在刑法因果关系,我们再去考虑犯罪构成要件,因为一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对他人的行为负责。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案件到此为止就不必再去考虑其它。坚持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可以少走弯路,为迅速的解决刑事责任奠定基础。
(二)刑法因果关系的相对性
原因和结果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辩证唯物主义因果论看来,引起一定现象发生的现象是原因;被一定现象引起的现象是结果。两者对立统一于因果关系之中。由于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原因在一个案件中是原因,但在另一个案件中却是结果,因此要灵活运用。理解刑法因果关系的相对性要注意以下两点:1.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原因是指危害社会的行为。2.作为刑法因果关系中的结果,是指法律所要求的已经造成的、能被查明和确定的现象。在行为犯、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等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中一般不存在解决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
(三)刑法因果关系的时间序列性
从唯物辨证主义的角度出发,原因和结果是有先后顺序的,原因必定在先结果只能在后,顺序不能颠倒。因此,在刑事案件中,我们只能从危害结果发生以前的危害行为中去查找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节省更多的时间,因为因果关系非常复杂,有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果多因,我们可以根据它的这个特征去找出所有的原因和结果,避免了原因和结果的混乱。
(四)刑法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在这里探讨的只是刑法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而不是指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其实,刑法因果关系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第一个辨证的解决了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把黑格尔的观点归纳为这样一个命题:“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规定自己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并不是事物发展的两个互相对立的过程,而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互相矛盾又相互转化的两个方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偶然性背后隐藏着必然性。”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偶然的,但其客体内部有一种向不利方向发展的抽象可能性,这种抽象可能性又是必然的,必然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三、刑法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 这也是刑法学界的通说。形成该观点的原因是许多学者把刑法因果关系当作犯罪构成的一个客观要件了,又因为刑事责任的根据是犯罪构成,当然就得出了上面的结论了。我认为,刑法因果关系只是一种联系,危害结果的发生是由于原因使客体内部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没有关系,它只我们解决刑事责任时的一种思维方式。在刚开始分析案例时,只要分析原因和结果之间是否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就够了,不要考虑态度的因果关系。对于介入因素的问题,借鉴英美法系的近因说的观点就可以了。接下来要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来分析,看结果是否是危害社会的结果,是否是刑法所禁止的结果,主观上有无故意、过失等问题全面分析。
关于刑法因果关系与犯罪论体系的关系我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
首先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来分析。在目前的情况,由于“必然说”和“偶然说”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已经没有多少人坚持了。但双层因果关系说却得到了许多人的人的支持,可能是受英美法系因果关系学说的影响。但双层因果关系说认为因果关系是结果犯的一个必备构成要件,是行为犯、危险犯、未完成形态犯罪的选择要件,而且是一个客观要件。但在分析法律因果关系时却又分析了主观方面,一个因果关系怎么既成了犯罪客观方面,又成了犯罪的主观方面,与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自相矛盾。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考虑因果关系与犯罪论体系的关系。
如果把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仅看作是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即起一种桥梁作用,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案件结果发生以后,看哪些是危害行为引起的就可以了,接下来,再根据犯罪构成理论决定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
双层因果关系是受英美法系的影响,但英美法系是实行判例法的国家,注重实用,而我们国家讲究的是理论的体系化、系统化,各个理论要自圆其说。如果我们真要使因果关系融入整个犯罪论体系中,我们可以借鉴大陆法系的犯罪论。即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在大陆法系中,刑法因果关系是放在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中的,目前理论界的“通说”是相当因果关系说,而该说中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避免了双层因果关系说中的矛盾,而且通过违法性、有责性的判断可以排除一些不应处罚的行为。不像我国构成要件中主观方面、客观方面、主体、客体那样截然分开,有时会自相矛盾。但是要放弃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去接受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也许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认为因果关系仅是一种联系的观点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主编,《犯罪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页
[2]王作富主编,《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刑法哲学论文范文4
2.论康德的德性伦理思想邵华,SHAOHua
3."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解读聂长建,NIEChang-jian
4.理性的有限性与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论迈蒙尼德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思想王增福,WANGZeng-fu
5.策略性均衡:维权抗争中的国家与民众关系——一个解释框架及政治基础尹利民,YINLi-min
6.公民美德与共和——共和主义的视角及其启示张昌林,ZHANGChang-lin
7.论公共行政战略的理性精神——一种三维理性范式观朱国伟,ZHUGuo-wei
8.质疑自甘冒险的独立性廖焕国,黄芬,LIAOHuan-guo,HUANGFen
9.荐证广告中荐证人侵权责任的路径选择和制度设计——来自美国法上的启示蒋学跃,JIANGXue-yue
10.试从文化论角度解释中国经济制度——论"包"的伦理规范加藤弘之,孙一萱,KATOHiroyuki,SunYixuan
11.再分配的制度分析卢现祥,朱巧玲,LUXian-xiang,ZHUQiao-ling
12.制度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及其量化研究胡晓珍,张卫东,HUXiao-zhen,ZHANGWei-dong
13.我国县域工业大气污染损失评估——基于ExternE模型的IPA法卓桂珍,赵定涛,魏玖长,ZHUOGui-zhen,ZHAODing-tao,WEIJiu-chang
14.基于"公地悲剧"视角审视低碳经济刘越,LIUYue
15.女性主义认识论与复杂性科学的价值取向王斌,申丽娟,WANGBin,SHENLi-juan
16.技术代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石卫才胜,WEICai-sheng
17.民主与科学的分与合何丹,HEDan
18.反就业性别歧视视野下的性别平等姜战军,JIANGZhan-jun
19.论新社会运动对当代西方公共政策的影响陆海燕,LUHai-yan
20.论传统法制对宗教组织的合法性要求——以汉传佛教寺院为例谭全万,TANQuan-wan
1.晚清民初尚武思潮的缘起与五四激进主义发生张冀,ZHANGJi
2.先秦儒家话语体系中的大禹传说孙国江,SUNGuo-jiang
3.当代中国"主体性哲学"的出场吴根友
4.哲学的批判性与开放性何萍
5.主体生成论与西方哲学的真精髓戴茂堂
6.希望人学的本体论和价值论随想董尚文
7.人的问题:从主体性的建构、消解到生成翟志宏
8.价值理想与制度设计的断裂——论非人类中心论环境伦理的应用困境郁乐,YULe
9.亚里士多德公正伦理的"实践智慧"——正义的"城邦"与"个人"时代思辨姚站军,姚新良,YAOZhan-jun,YAOXin-liang
10.论康德政治哲学中的正义徐弢,XUTao
11.近代中国刑法之正当防卫制度考析——以法典之文本规则为中心李永伟,萧伯符,LIYong-wei,XIAOBo-fu
12.论自然人人格标识商品化权的性质及民法保护戴谋富,DAIMao-fu
13.刑事诉讼法修改中设立暂缓制度实证调查陈佑武,CHENYou-wu
14.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政府选择楚德江,CHUDe-jiang
15.理性官僚制民主困境的自我救赎陈永章,CHENYong-zhang
16.论中外公民社会权保障路径之差异——兼论我国公民社会权保障制度的发展邓海娟,DENGHai-juan
17.接受图式与大众化陈娱,CHENYu
18.低碳技术转让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潘家华,庄贵阳,马建平,PANJia-hua,ZHUANGGui-yang,MAJian-ping
19.中国低碳经济中可再生能源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李萌,LIMeng
20.低碳产业支撑体系构建路径浅议——以武汉市发展低碳产业为例王亚柯,娄伟,WANGYa-ke,LOUWei
21.低碳经济背景下的政府管理创新路径研究黄栋,胡晓岑,HUANGDong,HUXiao-cen
22.我国低碳出版战略与实施路径研究王灿发,侯欣洁,WANGCan-fa,HouXin-jie
23.论人权与性别平权王金玲
24.女权主义的四个层次邓晓芒
25.现代社会视野下的性别公正问题张廷国
26.女权和人权邵华
27.女性主义之于建筑学的意义汪原
28.女性文学的道德力量与文学的社会学道义问题蒋济永
29.加强对话,将妇女与性别研究引向深入畅引婷
30.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村民自治主流刘筱红
1.中国刑法百年发展的回顾与反思——以台湾地区的几个刑法议题为中心黄静嘉,胡学丞,HUANGJing-jia,HUXue-cheng
2.从法制史的立场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滋贺秀三《从法制史的立场来看现代中国的刑事立法》的介绍及补论高见泽磨,TAKAMIZAWAOsamu
3.清末章董氏《刑律草案》稿本的发现和初步研究孙家红,SUNJia-hong
4.亲历者眼中的修订法律馆——以《汪荣宝日记》为中心的考察胡震,HUZhen
5.谈谈人文文化、民族文化的基础性——从"四个跟不上"谈起杨叔子,YANGShu-zi
6.论有形家园高秉江,GAOBing-jiang
7.乌托邦、现代性与知识分子甘会斌,GANHui-bin
8.《释名》声训的民俗学价值左林霞,ZUOLin-xia
9.空间与实践——西方空间观念的历史演变、局限与出路探析王晓磊,WANGXiao-lei
10.感性是时间的家——从马克思《博士论文》谈起别祖云,文双发,王炳书,BIEZu-yun,WENShuang-fa,WANGBing-shu
11.女性与哲学:倾听不同的故事肖巍,XIAOWei
12.地方性法规质量评估的理论意义与实践难题俞荣根,刘艺,YuRong-gen,LIUYi
13.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卢新海,黄善林,LUXin-hai,HUANGShan-lin
14.户籍与当代中国社会差别——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定量研究李晓飞,LIXiao-fei
15.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合作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朱俊成,ZHUJun-cheng
16.个人账户养老金缺口的精算模型与实证分析陆安,LUAn
17.20世纪30-40年代工业分散化思想述论向明亮,XIANGMing-liang
18.近代中国官利与股票投资者朱海城,ZHUHai-cheng
19.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魏君英,陈银娥,WEIJun-ying,CHENYin-e
20.难能可贵的贡献李锐
21.敢于竞争善于转化李培根
22.《朱九思评传》卷首语王炯华
1."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梁启超后期人生观初探陈泽环,CHENZe-huan
2.后期殷海光与基督教关系考黄岭峻,HUANGLing-jun
3.章太炎的出版自由观考察卢家银,LUJia-yin
4."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对"当代中国哲学"何以作为问题的思考张蓬,ZHANGPeng
5.文化视域中的社会形态初探种海峰,ZHONGHai-feng
6.亨普尔的归纳悖论朱志方,ZHUZhi-fang
7.公司发起人的认定标准:为形式标准辩护李飞,LIFei
8.论夫妻之间的侵权损害赔偿冉克平,RANKe-ping
9.技术侦查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以监听为视角闫利国,徐光华,YANLi-guo,XUGuang-hua
10.现代国家构建与民主化浅析——欧洲经验及其启示戴辉礼,DAILi-hui
11.政治系统论视角下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陈纪,CHENji
12.论当代中国传播的日常生活理论视阈谢加书,XIEJia-shu
13.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双向逻辑及其效果分析——基于Y县的实证研究张云昊,ZHANGYun-hao
14.找回村社:农地收益与农民所要贺雪峰,龚春霞,HEXue-feng,GONGChun-xia
15.从家庭到院舍——农村五保老人供养方式选择自主性研究苗艳梅,MIAOYan-mei
16.女性身份差异性与科学文化多元性——基于女性主义科技史研究的理论基础章梅芳,ZHANGMei-fang
17.国际环境政治中的"认知共同体"理论评述孙凯,SUNKai
18.菲律宾生物燃料政策的制定、调整及启示刘贺青,LIUHe-qing
19.实践本体论若干问题再探——答张立达先生何中华
刑法哲学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 补充原则 宽容原则 现代刑法
在切入正题之前我们不妨讨论这样一个观点,即在一个高度复杂的经济细分的社会人们是不可能放弃理性的制定法的。由于制定的法律具有普遍意义上的适用性,它必然包含有人们所认为的“人世间一切存在所具有的全然优势”。但是,这并不足以否定制定的法律尚且存有漏洞和疏忽的问题。如果一旦人们把制定法的普遍性绝对化,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结果:现存的与发生的一切均处于法律的规范之下——不是合法而为法律所允许,便是违法而为法律所禁止。而事实上,对于有些行为方式,我们试图理性地做出法律评价是比较困难的。往往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评价其为合法,也不能想当然地评价其为违法。也就是说,在我们社会生活中,还有广泛的“法外空间”在。这一点对刑法而言无疑也是适用的。
所谓“法外空间”通常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普通意义上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二是法律上有明文规定却无评价。而我们在这里侧重论述的则是后者。因为前者是极易弥补的,我们一般通过新的立法即可做到。而如何应对后者即法“无评价”则是颇费思量的事。
对一行为举止“既不能适当地评价为合法的,亦不能评价为违法的”。这正是法“无评价”的难题所在。而且那种试图以“没有禁止的”语词来表达上述的复合行为举止的做法也并不完全恰当。试举例来看,在刑法的视界中,紧急避难(区别紧急避险)、堕胎、自杀等实例,即为法无评价之情形的法外空间问题。其法律规则在于,刑法上的相关行为,在特定条件下变得不可惩罚,即不违法、无罪责或者其他等等。往往对此问题,立法者没有加以规范,将它留给了司法实务与学说,甚至公众舆论。拿德国刑法典来讲,就曾有人建议在法典内,如刑法第218a条:不依第218条处罚怀孕妇女,使用“如果…,…是不禁止的。”取代“不可罚”。这样才能确保怀孕妇女的行为不可非难、不违法。当然,这一说法随后即遭到了德国立法者和联邦宪法院的反对。不过,类似的情形,我国刑法典(1997年)也出现过。比如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问题。
那么到底所有与刑法相关的行为举止,是否都能适当地评价为“合法的”与“违法的”呢?通过上面的表述看,答案是否定的。特别是在带有悲剧性的冲突与发生危及生命的情形。比如,极享盛誉的古希腊哲学家Karneades(生于公元前214年),就留给我们极著名的“木板”案例:两位(假定为X、Y)遭受船难者要求助于一块漂浮的木板,但此木板看起来只能承载一人。因而,二人都极力动武,迫使对方拿不到木板。结果X获救,Y溺毙。
若依刑法信条论通说,在不法领域内只有“合法的”与“违法的”两项评价。Y溺死,X爬上木板获救。要评断此案例,只能以可宽恕的“紧急避险”处理。
再回顾一下上述案例,显然,当二者遭受船难者为木板相互争斗时,此际理应认定为违法的攻击。而对抗不法的攻击,在刑法上,又是可以实施正当防卫的。这样一来,两人都有对抗对方的正当防卫权。可是,刑法规定对正当防卫行为是不能反防卫的。如此则势必陷入僵局和死胡同。因为攻击和防卫混合在一起,以至于同一行为既是合法,又是不合法。
自然,由于对此类行为的“无评价”,抑或无计可施,刑法的地位就变得尴尬起来。不论是“罪刑法定原则”,还是“平等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此时都变得空泛和乏力了。因为法外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又意味着法律规范间接地承认对此放弃评价。那么我们就必然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原则来适当填补刑法规范的“无评价”。为此,现代法治国家的恰当做法应是,在刑法中引入道德、惯例、风俗、习惯等补原则和多元风险社会所必需的宽容原则。
一、补原则
作为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补原则,一方面针对国家集体主义与极权主义,保护和防卫人的自由,即保持其相对于较高法律位阶主体(通常是国家)的独立性,并平衡人们之间在法律上的权益;另一方面,也是经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即对抗形式的自由主义。这主要还是涉及国家对自由的保障和支持的问题。如此一来,规定补原则即具备了它的双面价值:积极价值和消极价值。消极意味着国家不允许在个人或团体成员根本不需要的帮助时,而实施帮助行为。积极意味着国家在个人或团体中无人能完成应为任务时提供协助。这些也正是为什么该原则在宪法或其他别的部门法中颇受争议,而在刑法中却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所在。而且由于“刑法不完整的本质”,刑法仅能在保护社会成为势所必需时才能介入。由此可见,该原则不是意在规制刑法的社会功能,而是为刑法的干预设定了明确的界限。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道格拉斯·N·胡萨克在谈到什么是犯罪时所指出的,“依我之见,只有有罪过的、应受惩罚的、非道德的行为才应当被认定为犯罪”。“假如刑法禁止一种行为,而这种行为从道德的角度看公民有权实施,又怎能想象国家因此而有理由来处罚他呢?”毋庸赘言,刑事责任对道德、政治哲学具有巨大依赖性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什么行为具有应受惩罚性,以及国家为什么把一些行为(如杀人、纵火等)规定为犯罪,而把另一些行为(如成年人双方同意的性行为、自杀等)不规定为犯罪。对这一点,不是我们现在才要求人们明确无误的,而是早在17世纪英国的《权利法案》中就表达了类似思想,即国家在创制法律时对个人拥有的道德权利必须予以关注。
二、宽容原则
尤其是在民主法治已蔚然成风、多元风险社会格局略显雏形的今天,宽容所扮演的角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的多。比较东、西方社会,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宽容面临的具体问题,即真理、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在过去乃至今日几乎如出一辙。可人们把宽容当作法律问题加以讨论却是最近才有的事情。
刑法哲学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 错误 概念 分类
一、错误的概念及剖析
美国学者乔治·P·弗莱彻把错误问题看作各国刑法事实上都会面临的处于刑法理论上最困难的12个问题之列,明确其定义尤为重要。英美国家把“不知或错误”简称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事实或法律没有认知(不知)或者主观认识同事实本身或法律本身不一致。前苏联刑法学家别利亚耶夫等认为:“错误是犯罪主体对它所实施行为的法律评价或事实情况错误的认识。”笔者认为相较以下几种定义较为可取,但也非无缺。
有学者从形式上或实质上把错误仅仅理解客观事实上之错误。如:日本学者中山研一认为:“所谓错误是指客观的事实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不一致。”我国台湾地区刘清波认为:“错误者,主观认识与客观之事实不相符合之状态也。即行为人对于犯罪之认识与所预见者不一也。”笔者认为,法律错误是错误中的另一半,即便是在“事实的不知得以抗辩,法律的不知不得抗辩”这一古老的罗马法原则下,随着社会的发展也逐步和缓与动摇。所以,无论是在概念表达上还是实质上,都应给予其必要地位。这里的“事实”范围如何也未明确。有学者把错误的对象表述为社会危害性和犯罪构成事实。基里钦科认为:“错误是行为人对其所实施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那些组成某种犯罪构成之重要因素的情况所产生的不正确观念。”阮齐林教授在《论刑法中的认识错误》一文中指出,刑法中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犯罪构成事实或者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质,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不一致。对于社会危害性是否与违法性相同,这在理论上还有争议,有的认为社会危害性就是违法性,违法性认识错误即法律认识错误。笔者认为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的关系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基于此,社会危害性应为违法性所取代,笔者将在对错误的分类中进行详述。有学者对刑法中错误的定义过于笼统,定义项不够清晰明了,有犯“定义含混”的逻辑错误。如:有论者认为刑法中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实施直接故意犯罪时,对与其行为相关的犯罪情况的不完全(或曰不准确)反映。”这里的“相关的犯罪情况”究竟是指“事实”的情况还是“法律”的情况,抑或是兼具两者的情况,指代不明。旧中国《法律大辞书》中定义“‘错误'是观念(刑法)与现象差异之谓也”(“现象”是指事实还是法律抑或是指二者之和并未明确)。
从以上各学者对错误所下的定义中,可以发现不少观点把错误限制在认识上,这样有犯“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之嫌。笔者认为,刑法中的错误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态度,还包括行为错误,如打击错误(又叫方法错误,在西方刑法理论界受到较大重视,对其理论研究较为深入。但我国一般将其排除)。刑法中的错误包含两个因素:一是作为主体的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人,二是是能为主体所认识的客观方面。从哲学实践观和认识论的关系来看,主体之认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客体是实践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是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方面。整个人类社会都处于主客体之间是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刑法中的错误认识论也不例外。就客观面来讲,刑法错误论中能被主体所认识的客观面包括一切具有刑法规范意义的事物,总体上可以分为事实方面和法律方面。事实错误应当限制为具有刑法重要意义的事实,是指那些被刑法规定为某罪必须具备的构成要件要素和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法律方面应当限制至具有刑法评价意义的法律规范。这样不仅符合罪刑法定主义,而且符合刑法的平等性和谦抑性原则。避免传统的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过于泛化而不易把握,节约司法成本。因此,为准确揭示刑法中错误的本质属性和特有属性,明确其内涵和外延,笔者认为刑法中的错误是指,行为主体对其所实施行为的具有刑法重要意义的事实情况或刑法规范评价有不知或误解以及行为上的差误。
二、国外关于错误的划分及剖析
古罗马法处理错误问题继承了法学家帕乌鲁斯提出的“不知法律不赦”的原则。该原则始于私法领域,后引申到刑法学中来。根据这一原则,以错误的对象为标准通常把错误分为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两类,事实错误是指行为人主观上认识的事实与客观上发生的事实不一致。广义的事实错误还包括在构成要件以外的正当化前提事实的错误,既可能是纯粹的事实,也可能是关于法律的事实(如关于物品的“性”)。法律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法律性质有不正确的认识,广义的法律错误还包括非刑法法规,日本改正刑法草案说明书第21条第1项中的“法律的错误”即属之。狭义的理解该种划分,则与德国刑法学家威尔泽尔所作划分意义相同。此种分类简单明了,概括性强。同时,这种概括也缺少限制,也容易造成误解。因为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有犯“定义过宽”的逻辑错误,这是其所产生的十分重要之问题。二战后,德国刑法学家威尔泽尔以犯罪的成立要件为标准,把刑法中错误分为构成要件的错误和禁止的错误。构成要件的错误是有关构成要件要素上的错误,是行为时事实的认识错误。禁止的错误是有关行为违法性的错误,所以又称为“违法性的错误”,是对规范认识的错误。这种分类为目的行为论者所提倡,在德国形成广泛影响并为现行的刑法典所采纳。但也有不足之处,如“容许构成要件错误”将置于何处?这就有犯“划分不全”的逻辑错误之嫌。在对一个概念进行划分应当遵循的一个规则就是划分子项外延之和必须等于母项的外延,如果划分后各子项的外延之和小于母项的外延,就会出现“划分不全”的逻辑错误。“容许构成要件错误”是指阻却违法事由的事实错误。正当化事由前提事实的错误是对违法阻却事由是否成立的前提“事实”的错误认识,不是构成要件要素的错误。该错误通常也不属于法律错误,但在某些情况下会成为法律的错误。前苏联的刑法理论界大多数刑法学者都赞同传统的两分法,但基里钦科根据错误的概念,把刑法中的错误分为三种:对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错误、对于组成犯罪构成因素的情况的错误、法律的错误或法律上的错误。笔者认为,社会危害性究其本质而言属于法律错误,尤其是在我国。首先,从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定义的规定可以看出犯罪是违反我国刑法所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并且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违反刑法所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违反刑法的行为必定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可以说两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第一,内容和形式相互区别,但这种区别终究是同一事物中的两个方面。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第二,内容和形式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任何事物都有内容和形式两个侧面,都是二者的统一体。形式必须以一定的内容为基础,而内容必须有其外在形式,作为内容的社会危害性就必须以违法性作为形式;第三,内容和形式相互作用,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适合内容。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形式使内容成为某一特定事物的内容。犯罪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统一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其实质内容和本质属性,是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的前提和决定条件,违反刑法是其法律形式,如果把两者对立起来,违反刑法的行为是空洞的,同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就失去了判断的标准。其次,基里钦科在《苏维埃刑法中错误的意义》一书中对误想犯罪究竟是社会危害性错误还是法律上的错误也不明确。